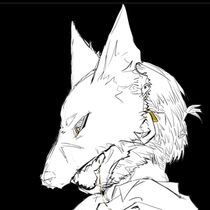












文/君莫非
秋,秀才要进京赶明年的春闱,途经一山时已至正午,虽说秋阳不及夏日毒辣,但到底赶了半日的路程,已是饥渴交加,便在山径边寻了一老树稍作歇脚。
正所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秀才吃饭喝水间,有秋风吹过,只觉药香扑鼻。他暗忖:此处生有野艾,怪道如此草木繁盛之地却无秋蚊烦扰,干脆就在此午歇,下午赶路也好添些精神。又想:我若折上两枝艾杆,之后赶路也能少受蚊蚁叮咬之苦。
秀才说干就干,顺着刚刚的风头找去,果见一片青青艾丛,虽然入秋后的艾蒿略显干萎,但胜在气味浓烈。秀才喜上眉梢,小心翼翼地从小径上探步走去。那艾丛看起来有好些年头,生了一大片,杆杆都有半人高,想来根扎得不浅。秀才从袖中掏出用以防身的短匕,不甚熟练地割了三、四杆艾,拢成一把正准备回头,余光却瞥见艾丛之中似乎有一石冢。
秀才纳罕道:此地野岭荒郊,这坟墓却不似小户人家修得起的,可又无人祭拜,野艾倒比坟头生得还高。又道:我既采艾时发现了此墓,想来也与墓主人有缘,不若稍作祭拜,虽无贡品纸钱,也算表了心意。
近了坟墓,才发现墓前的石碑经年风吹雨打,又无人修葺,早已风化得不成样子。只依稀辨认出几个字来。
“侠……安……身后……”秀才越念越奇怪,这碑上所刻不像是墓主人的名字,似乎是墓志铭?
不过想到自己只是偶然途径此地,又是个年久失修的荒冢,即使想打听也无从下手,秀才只得放弃好奇,朝墓主人做了三揖。
回到树下,秀才把方才割来的艾蒿略作修整,分段别进了自己的袖口和前襟,又把剩余的艾杆收入行囊,垫在脑后,就这么伴着浓烈的艾香陷入沉睡。
再睁眼时,秀才却浑身动弹不得,眼前也不再是睡时的景象。还未等他有所反应,就听见身边传来说话声。
“大哥,你说咱们好端端的在这种树干嘛?”说话的是个年轻男人,约莫十七八岁,衣衫显得有些旧了,但还算齐整。
被他称作大哥的人就不大讲究了,头发乱七八糟地捆着,衣服也旧得发毛,古铜肤色,满脸胡茬,端是副土匪样貌,笑容满面地拍了秀才一巴掌,“明杰啊,你可听说过‘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老话?这山道难走,等树长成了给路人歇歇脚,也算功德一件啊!”
秀才这才意识到,自己这是附身在这树上了,不过听这土匪大哥所言,难不成他们种的就是自己中午休息的那棵?
“您说什么就是什么吧!”那厢被叫做明杰的年轻人显然对他土匪大哥的说法不置可否,若有所思道,“倒是让寨子里的弟兄们来认一认,可以当个地标使。”
“到底是你小子脑袋灵光!”土匪大哥相当高兴,一巴掌重重拍在明杰的背上,拍得他神色一僵。
“走了明杰!让弟兄们来见见咱这新地标!”土匪大哥完全没注意年轻人脸色的变化,兴高采烈地钻进树丛,离开了秀才的视线。
明杰表情无奈,慢吞吞地跟在后面,自言自语道:“大哥真是,一高兴就不知道收着点手劲,回去得找郎中要点红花擦擦。”
秀才听了,忍俊不禁,对着面前繁盛的草丛暗自思量:倘若这树真是我中午歇息时的那棵,这二位仁兄的年纪恐已逾百岁。想来是山精作怪,令我一睹前尘耳。只是不知我见到的那墓穴是哪位先人的?
正想着,只觉眼前一变,已是深秋时节,面前乌泱泱好大一群壮汉,围着一帮吓倒在地的百姓。
“大爷饶命,大爷饶命呐!我们乃江、江阴人士,受了水患才不得不想法子逃难,如今已是、身无分文了!实、实在拿不出什么财物孝敬大爷!求大爷们看在我等多灾多难的份上,就饶了我们的贱命吧!”
江阴水患?那似乎是前朝的事了。秀才在史书上读到过,那时前朝气数已尽,帝王昏聩,佞臣当道,两江地带恰逢水患,更是民不聊生。
秀才很快就在人群中辨认出他刚刚见过的二人,时间似乎过去了不止一年,最明显的便是少年身上的稚气褪去,多了几分沉静。
不过那位土匪大哥看起来倒是没怎么变,此时面无表情地听着那位百姓哆哆嗦嗦的陈述,端是匪气冲天。
气氛有些沉重,秀才看出那群百姓的惴惴不安,而山匪们不少都分心看向沉默着的土匪大哥。
“明杰,寨里还有多少余粮?”土匪粗声问道。
“大哥,前两天抢的那帮贪官油水很足,寨里的余粮已经够弟兄们过冬了。”明杰早有准备,当即答道。
百姓们都松了一口气。
“能匀出来一点给乡亲们做干粮吗?”没想到土匪大哥说的话更是出人意料。
“这……”明杰沉吟了一会,“要是大伙紧巴点过的话,倒是能匀出三五日的口粮,只不过……”
他显然有些犹豫。
“那你带弟兄们先回去,把那部分口粮带过来。”土匪大哥倒是爽快得很,“咱们紧巴点就紧巴点吧,也不是没过过,指不定过两天又有肥羊呢!”
“多谢大侠,多谢大侠!”一众百姓没想到会是这个结果,纷纷感激涕零。
明杰无奈,招呼一声便带着大半山匪离开了,只有寥寥几人站在山匪大哥身边防备意外。
“还不知大侠尊姓大名?”方才说话的那名百姓大着胆子问道。
“王寻恩,不过一介匹夫,还担不起大侠二字。”那土匪,不,王寻恩话虽这么说,不过看得出他很高兴,摸了摸胡茬道,“还请诸位乡亲在此稍作等待。天色也不早了,这条路在山里还算平坦,乡亲们若信得过,我叫几个弟兄来给大家守夜,今晚就在此地凑合一宿,明早再赶路。”百姓感激,自不待言。
秀才心道:此地竟有过如此绿林豪杰,可惜我自诩遍读群书,也不曾见过名叫王寻恩的侠士。惋惜间,眼前又是一变。
“钦差大人,就是这棵树,那群匪人的老巢应该是在那个方向。”秀才定睛一看,十分诧异,原来是上次和王寻恩说话的那名百姓带着大批官兵,往山路上走去。
这这这……秀才没想到世上还有如此恩将仇报之人,一时脑中千言万语,汇成一句:无耻!
可惜他附身在树上,莫说骂一句,就是骂十句百句也不会有人听见,只有树叶刷刷地发出响声。
咦?此时无风,怎的树叶会响?
还不等秀才反应过来,一道又一道箭矢破空而来,官兵们不曾想会遭偷袭,一时间乱了阵脚,除去被流矢射中的,还有被自己人踩跌倒的,更有小人直接蹲下身子,试图用同僚的身体做盾。
箭雨之后,还不等剩余官兵们喘过气来,林中又炸起无数喊杀声,在山谷中有如万丈惊雷,震得众人脸色煞白,胆子小点的直接把兵器扔下,钻进道旁的树丛中跑了。为首被称作钦差的人也没好到哪里,嘴巴一张一合却不知该说些什么,握刀的手抖得有如筛糠,方才给他指路的人更是不堪,已经吓得跌坐在地上,眼睛直瞪着,仿佛随时会晕过去一般。
这等软兵弱将哪里是常年刀口上营生的山匪对手?不多时,绿林好汉们纷纷从草丛中现身,三两下就把尚有抵抗之心的官兵撂倒,其余的人被缴了武器,赶猪似的集中在一处,还特意关照了一下那位钦差和指路之人,把他们带到了王寻恩的面前。
“哟,这不是上次那位大人么,咱们不过一面之缘,您竟然还亲自劳动给咱们弟兄送来这么多利器,真是慷慨啊,寻恩在此谢过了。”王寻恩看起来一点都不生气,笑眯眯地朝那钦差一拱手,倒似真的是在谢他一般。
“你你你……”那钦差气得说不出话来,半晌才憋出一句:“大胆反贼!胆敢绑架朝廷钦差!你可知这是杀头的罪名么!”
“不劳钦差大人费心,我们大哥的脑袋有的是人惦记,您恐怕还得往后稍稍。”那位叫明杰的年轻人对此嗤之以鼻。
“哎,明杰,江湖的恩怨还是不要跟钦差大人多说了,浪费时间。”王寻恩一摆手,看向边上的另一位,“令夫人千金都还好吧?”
那小人以为王寻恩威胁他,吓得面无人色,尖着嗓子叫道:“侠士饶命,出卖你们是我一个人的主意,我卑鄙,我无耻,要杀要剐悉听尊便,可您们大人大量,千万别去找我妻儿的麻烦,她们真的很敬重您!求求您了侠士!!”说着,还往前爬了两步,十分用力地给王寻恩磕起了头来。
王寻恩叹了口气,倒也没拦着他磕头。待他连磕了几十个响头,脑门一片青紫后才轻轻一踢,将那人撂倒:“为什么把官兵引来?”
那人从地上爬起,连灰都不敢拍又跪作一团,畏畏缩缩地看了一眼钦差,道:“钦差大人贴了张告示……说近期要组织官兵剿匪……能提供线索的人就可以免除手续直接在山阳城落户……”咬了咬牙,又说:“这钦差坏得很!说什么灾年山阳余粮不足,要限制落户人口,手续费要整整十两银子!不落户的流民不许入城,也不许和城里人做买卖,他们,他们是想活活饿死咱们啊大侠!!”
“既然觉得他们坏,为什么还要帮他们呢?”王寻恩声音不是很大,脸上仍然带着笑,却把那人堵得脸色变了几变。
“有官府,管我们叫匪,没官府,管我们叫侠。人呐!”王寻恩似慨似叹,转身离去,只留下一声吩咐:“把他们都赶下山去吧。”
秀才望着他远去的背影,分明是得胜归去,那身影却看不出喜悦,反而十分落寞。
眼前又是一变。
远处隐隐传来喊杀声,却听不太真切。
“大哥,咱们的人把山遭都探过啦,全被大批官兵堵着,闯不过去呀!这样下去……”
秀才一看,是一个山匪跟着王寻恩从山上走来,两人的脸色都不大好看。
“我晓得,你不用说了。”王寻恩叹了口气,扶上了秀才附身的树干。
这树长了好些年,也有碗口粗了。
“其实大哥我一直想不明白,你当年为什么要放了那狗钦差?为什么又把明杰打发走了?”那山匪念念叨叨的,“这些年虽说也有不少新加入的弟兄,但到底比不上明杰呀!”
“是啊,都比不上明杰。”王寻恩笑了,“于明杰那孩子可不是池中之物,在咱们这小山寨当军师未免太屈才了。”
于明杰!秀才心头一震,这名字,不正是太祖开国时镇国将军的大名?
“唉,也是啊……要是明杰在,咱们也不至于被围死在山上。”山匪心有戚戚。
“行啦,别在这叽叽歪歪的跟个娘们似的。”王寻恩朝那山匪背上一拍,笑道:“谁说只有明杰有法子?我也有。走了,回山寨,吃完饭我跟大家宣布个事儿。”
这次的场景短得出奇,秀才本以为还有什么人要来时眼前景物又变了。
“霍大哥,是这儿吗?”一个身着武服的中年人站在秀才面前,侧身虚扶了一把身边的人,是个头发花白的瘸子。
“是啊,不用扶我,明杰。这段路我走过好些遍啦!”那位被称作霍大哥的老人拄着竹杖,脑袋朝秀才的方向一点:“你看那棵树,不就是大哥当年种的吗!”
于明杰顺着看了过来,打量了一会,笑了起来:“是了,好些年没见,这树也长这么大了。”
“就在这对面,咱们弟兄几个凑了点私房钱,给大哥盖了个衣冠冢。”老人说着有些哽咽,“大哥是为了我们才死的,为了我们才死的啊!”
于明杰手搭在老人的肩上,沉默了半晌才道:“大哥……到底是怎么死的?”
老人叹了口气:“那些天,咱们山头被官兵围着,不是之前你带着打的那种酒囊饭袋,那是真正在战场上厮杀过的兵痞子,我一眼就看出来了。”
“当时也不知道哪来这么多的闲兵,生生围了咱们一个月,一个月!又不是秋冬,寨里也没存那么多粮,我们省着省着,也眼瞧着粮食撑不了三天了。”
“那天大哥把我们都叫到大厅里,让王伯把剩下的饭菜全烧了,摆了一大桌,告诉我们下午有一场硬仗要打,吃饱了才有力气。可谁知道!”
霍姓老人说到这,泪流满面:“谁知道,大哥在自己的饭里下了毒啊!!”
于明杰一拳锤上树干,惊起了树梢理毛的雀儿。
“大哥说,让我们把他的脑袋交给那狗钦差,让我们全部投降,以后给人保镖护院也好,找块地种也罢,哪怕跟狗抢吃的!也比在山上耗死要强。”
“大哥,糊涂啊!!”
老人哭声嘶哑,在山里层层回响,恍若悲歌。
再睁眼时,秀才还是那个秀才,艾香呛鼻,把他从前尘中生生扯了回来。
他一伸手,摸到脸上满是冰凉的泪水。
秀才收拾好行囊,朝老树深深做了一揖,又凝视了艾丛良久,日头尚未西斜,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秀才走过的路上,不少人都捡到了一份没有署名的诗稿:
先人树木不求报
百年余荫蔽山郊
绿林豪杰今安在?
唯见荒冢漫青蒿
“大哥最后说,让我们不要在他的墓上写名字,一定要写点什么的话,就写‘侠者安求身后名’。”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