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炎—古堡惊魂01-1
SIDE B 尹云繁视角
身下潮湿的触感、令人不快的浓重雾气、腐朽树叶的味道、不甚清晰的古堡轮廓、不时抽痛的神经、俯视自己的陌生人,无一不是提醒她自己现在所在的位置绝对不是刚刚到达的旅馆房间。在这之前最后的记忆是在检查完房间准备发个信息回去报平安。可以肯定当时房间中并没有第二个人存在,而能不知不觉将自己弄昏的人…………
“醒了吗?”俯视自己的陌生人之一——带着毛织帽子的青年——开了口,打断了思路“醒了就走吧。”
自己竟然在情况未明的时候在陌生人面前走神了!被师父知道了绝对会死的很难看!就着起身将表情调整到茫然状态,抬头问:“走……去哪里……?”
带着毛织帽子的青年微笑着回答:“还用问吗?当然是……地狱啊。”
哇哦,这回答可真是…………中二。这么想着,直觉和身上冒了一点点头的鸡皮疙瘩告诉她最好保持迷茫的表情把话听完。
“仔细想想,它应该已经把这一切植入你的脑海里了。”
听着貌似在哪里见过的台词,回忆着,脑海里突然多出来的东西让她整个人都不好了。“无限恐怖……”这可真的不是一个好笑的玩笑。确定她没有恶趣味到搭这么一个场景来耍她的朋友,而自己本身也没有能让人这么大费周章绑架她的家世。抬起手看到手腕上那不知何时出现的黑色手表,上面显示的除了时间和人数还有两行字:【任务:存活三十天;古堡不可毁坏】这次是真的栽了。深吸一口气,再次对上青年平静的目光:“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尹云繁,考古系学生,对灵异事件很感兴趣,算是灵异体质,直觉还不错。学过一阵子武, 所以体力方面我还是有点自信的。请问咱们的地狱旅行团还有空位吗?团名叫什么?”
带着毛织帽子的青年笑了出来,回头与同伴对视一眼,歪了歪头:“我是九方彻,那个是茨城。欢迎来到北炎地狱旅行团,空位是有,就看你能不能活过‘入团测验’了。”
“我会努力。”话音刚落,浓雾有散开的趋势,阳光比刚才更明亮了些,但与之不相符的阴冷的气息却猛地从四面八方压来,就像保护自己的什么消失了一样。城堡大门那露出尖利牙齿的白色精灵雕像更加让人不安,她不由得打了个冷颤,这感觉和平时路过凶宅之类的感觉不同,同样是阴冷压抑却又说不出哪里不大一样,觉得找到不同点挺重要的但是却想不出到底是哪里不同,到底是哪里…………将头发简单盘起,暂时放弃思考违和感,快走几步跟上已经开始行动的“前辈们”,正式开始第一次的“地狱之旅”。
************************************
尹云繁伸手揉揉从清醒过来就一直隐隐作痛的太阳穴,整理了一下目前的信息:“这次的恐怖片是《万能钥匙》,对吧?这部电影我看过,剧情挺坑,基本是只要不信邪就没事。但和记忆当中的有些不同,影片并不是在古堡里进行,所以应该是掺加了其他的电影,具体是什么还不清楚。”
“进入这次恐怖片的人数是10人而现在只有我们3个在一起,一般主神不会放分组的的人离得太远……”
“坏消息,九方,”茨城睁开眼睛打断九方彻的话:“技能和物品不能使用估计血统也被禁了,我们现在只能用最原始的方法找了。”
九方彻翻了个白眼,耸耸肩语气中满是无奈道:“主神这是想玩死我们吧……算了,反正也习惯了。”
“习惯了?”这位已经被主神折腾得懒得计较了?
“这是我们的第三部恐怖片,上一部是禁用道具。”茨城推推眼镜,“先从哪里开始?外围?”
哇哦……被主神也坑的挺惨的嘛,真不知道是该同情他们还是该佩服了。话说回来被坑成这样还没开骂,这小哥的修养不错嘛。
“外围吧,虽说应该不会有什么重要东西但还是别放过了。提高警惕。”
在古堡门口不远处的草坪上发现了一辆破金杯,小心翼翼过去翻了个底朝天也没发现什么类似有用的东西。再向古堡后面绕去,踩着厚厚的枯枝烂叶前行,那不算柔软的触感让人十分没有安全感,仿佛随时都会有什么从下面冒出来抓住脚踝似得。原本应该是花园的地方现在是一片荒芜,花坛里开裂的泥土上有着不少枯萎的花草枝干,可以想象得到如果这些植物还活着这里一定是一个能让人心情舒畅的地方。在枯枝花架深处的小房屋,应该就是园丁的小屋吧。门似乎并没有关紧,茨城伸手将九方彻和尹云繁虚拦一下,让两人退开门的正面范围,自己深吸口气,用力将门踢开。结果门是开了,也直接碎成几片,以他的表情来看他自己也挺意外的。是能力回来了?还是…………好吧,是门朽的差不多了。尹云繁扔掉崩到手中的门板小碎片,跟着进了花园小屋,里面很空,不像想象中那样放满了园艺工具,只有几个沾满泥土的园艺工具和一个装满了红色砖土的袋子。茨城弯腰将袋子拎在手里:“这里有用的只有这个了。”
“玩家茨城得到道具:红色砖土袋*1”
尹云繁的脑海中忽然蹦出来这么一句话。对于自己忽然开的脑洞努力忍着不让自己笑出来,将目光转移到窗外时发现雾气已经散开了一些,不远处的古堡轮廓已经不是那么难以辨认了,好像在哪里见过…………是哪里呢……雾……腐朽的庭院……古堡……古堡……
“尹云繁?想什么呢?”感觉有人接近,猛地转过身,发现是九方彻,硬生生止住马上就要抓住对方将其摔出去的手转而抱住自己:“吓……吓我一跳!别突然从背后接近人啊!”
“呃……抱歉?”九方彻举着双手,表情有些奇怪,仿佛他才是被吓到的那个。
“啊……不好意思,我好像也有点反应过度……”还好没将人摔出去,不然就不是道歉能解决的问题了。尹云繁脑海中的Q版小人夸张地抹了把冷汗,“对了,我想我知道另一部恐怖片是什么了,《The Others》也叫《小岛惊魂》,这座古堡就是那部的电影里的。”
将剧情大致说了一遍后,九方彻皱着眉神情不定地不知在思考着什么。把询问的目光投向茨城,得到了写着“稍安勿躁”的笑脸一枚。好吧,反正自己是“直觉型”动脑分析什么的交给头脑好的去分析好了。记得在庭院某棵树下有着《The Others》里三个仆人的墓碑,等下找找看好了,要是没有还有相册。按照恐怖片的思路,说不定能在那个相册里看到我们三人的照片?等一下,很有可能那三个墓碑上也很有可能是我们三个的名字……要是真有就是妥妥的竖flag了,噗~话说回来,在这儿的三个人对大部队来说才是“走丢”的吧。
“我们去古堡吧,外围没什么可用的东西了。不清楚他们是不是和我们一样的状况,最好尽早回合。”九方彻耸耸肩,“虽然时间还有的是。”
***************************
拍打请轻柔……T T
·接前置
·一如既往角色崩坏
·时间轴在入学一个星期以内
03
入学之后也没看到个老师,接下来该怎么走貌似是随心动了,西芙十分认真地在先去大厅还是先去周围逛一会之间纠结着,然后就看到城堡门口不远处站着的人。
这真是好熟悉的背影。
咦仔细想想我貌似没见过唐草的背影?这是什么一发辨认的诡异技能。
所以说从一开始姑娘你就没有想过可能是自己认错人的情况是吗?!
说实话西芙并没有想过会在这里见到自己的……暗恋对象。
她和唐草应该算是关系特别好的网友,从那个魔法爱好者论坛认识到如今近四年,论坛倒了,人却还在。异国友谊来说这真是难得可贵,西芙还不止一次有冲动去中国见见这位大亲友。
可是在爆照之前西芙还一直以为总是操心她生活的“花花草草”是位萌萌哒的女孩子。
照片里那个深蓝发色看上去面容清秀神色温柔的东方少年简直是某个光屁股小天使箭筒里最有力的那支爱之箭。
她不仅恋爱了,还是网恋。
不仅是网恋,还是异国恋。
这怎么听都是还没开始就强制结束的bad end恋情吧!
大姐大惯了的少女难得露出沮丧的小女生性情,还像是冒了芽就茁壮成长的树苗节节拔高。
然后她竟然就在一个怎么听都很不靠谱的学校遇见了……远在中国的单相思对象的身影。虽然很想少女心一把说什么“这就是命运的邂逅啊”但毫无情趣可言的某人只能对背影发了将近一分钟花痴表示“这都是命运石之门的安排”。
不对她记得这部片子略虐来着?
改天戒掉日本漫画吧。
现在先打个招呼再说!
要冷静,西芙,保持形象!
虽然本性这种东西大概早就在四年的聊天中暴露得一干二净了。她好想掐死当年那个毫无形象吐黑泥的自己哦,简直是活该单身fff团的节奏(´Д`)
她确认自己没有红脸红耳朵之后鼓起勇气伸手扯住了唐草的衣角,对方愣了几秒才转过身来。
西芙自带的大姐头气场瞬间跑到九霄云外,只能花痴一下意中人真人版的杀伤力看起来更大了……
“猜猜我是谁☆”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我是个笨蛋!!!!这是什么自来熟的语气不要太得意忘形啊白痴!!
之后又是一阵沉默,直到唐草不确定的回应,“西芙?”
其实心中满足得都快要下楼跑圈了,表面上女孩只是冲他吐了吐舌头,这个俏皮动作偏偏被她做出了一股子帅气,“我还以为你要认不出来了呢。”
大概是被此逗笑了,唐草十分顺手的摸了摸她的发顶,“如果一开始就是这个表情我大概早就认出来了哦。”
“什么表情?”
“唔,很神气?”
西芙细细思索我给对方的印象到底是哪里不对。
好吧,貌似就从来没对过。
爆炸吧,我。
怀揣微妙的少女心西芙表面坦然自若实则落荒而逃,也就没看见唐草在后面有些担忧地皱起眉。
她现在只想随便找个地方坐着自我反思一下qaq
然后……既然已经在同一所学校了不追到誓不罢休!
姑娘你又土匪气场全开了!
04
“西芙!西芙·米兰特?”
“谁?”
依旧在消沉日常的西芙迷茫地看着看上去比她大了三四岁的青年,隐约有些眼熟,不过作为一个脸盲,看谁都很眼熟。
对方却像是被打击到了的模样,“诶……我是弗朗西斯啊,也对我们有很多年没见面了,舅妈还好吗?”
“弗朗西斯哥哥?”
青年猛点头。
啊就是那个从五岁之后就再也没见过妈妈她哥哥家基因突变成粉发的土豪哥哥啊。这句话不带标点真尼玛绕!几年不见竟然都这么高了……不对我要验证一下。
西芙嘿咻一用力把弗朗西斯抱起来让对方坐到自己肩上。
嗯,这个手感,是哥哥没错!
弗朗西斯捂住了脸,想起8岁的自己天天被比自己了将近小4岁的怪力妹妹举高高的惨痛回忆那熟悉的生无可恋感涌上心头。
还好只是举高高不是抛高高。
这句感慨发自弗朗西斯·不堪回首的回忆2.0
“妈妈很好,她最近和爸爸去马尔代夫度蜜月了。”
“舅舅舅妈感情真好啊,又度蜜月,上个月还寄到我们那边不少明信片呢。”
“嗯,一年一次,一次一年。”
……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觉得好心疼。
不过西芙你真的不准备把我放下来吗!?
弗朗西斯第一次觉得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滋味是这么痛苦,他已经能够理解某部中国武侠小说里面那个装逼的独孤求败为什么求败了。
脚踏实地才是世界的正义!
“姐姐你好厉害你是不是会功夫啊!”
卧槽野生的萝莉出现了,我的精灵球呢。
不对弗朗西斯,把持住自己,你的设定是世界的哥哥不是萝莉的哥哥!
虽然世界萝莉的哥哥这个设定听上去也还蛮带感的。
而西芙歪了歪头思考功夫是个什么东西。
唐草说过那个叫做齐天大圣的人功夫很好……我有和那个人一样的棍子而且很会打架应该算是功夫好吧?
“嗯,我会啊!”
“好厉害——姐姐你教教我好不好啊(☆_☆)”
女孩简直能放出“KiraKira”小星星的眼神实在是让人无法拒绝,西芙完全没有经过大脑过滤地回应了娇小的金发少女的期待。
“好呀!”
说起来功夫应该怎么教?等回去问问唐草好了他是中国人一定知道的吧。
西芙·绝不误人子弟·挪威好师傅·米兰特再一次发挥了对心上人的全身心信任,当然你说她单细胞也没有问题。
“哇师父好,我叫Lee white,请多指教!”
“我是Sif mirante,请多指教www”
Lee抬头看向从刚刚起就一直在掉线状态的弗朗西斯,头上两根疑似呆毛的天线抖动了两下,“这位先生也是,你好啊。”
“呃……你好。”
说真的西芙,还是让我下来吧。
字数:2020字
求评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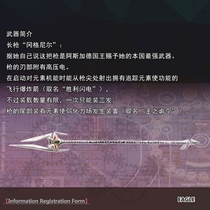



有人说,西欧的天气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夜里很冷的天气,这一点的确应该同意,而在深冬之中的1月,这里更是不管白天晚上一样的寒冷。
洛羽闲到达这座城市是在两天前。先用潜水艇行驶到废弃码头中,再用黑羽的飞行能力沿着无人的路线飞到了目的地。
本次接引元素使的工作也是进行得十分顺利,这座城市中住着的那个元素使已经同意去学院了,而洛羽闲现在只是在等他与家人做最后的告别。
寒风吹拂着洛羽闲身上御寒的风衣,偶尔还将一两片雪花带进衣领,让他感受到一丝寒意。
元素使对于温度的感受比起人类会迟钝一些,这样的天气,对于他来说,也不过只是有点冷罢了。
离约定的时间,还差两个小时,洛羽闲也不想一直傻站着,于是便在人类社会的大街上,漫无目的地走了起来。
即使是寒冷的冬季,但热闹的地方还是会热闹的,街上行人来来往往,路边咖啡厅有人悠闲地读着报纸。
有些奇妙,甚至让洛羽闲产生一种自己也是这些人类中一员的错觉。
哈,当然,这也只是错觉而已,元素使,早已是脱离人类的存在了。
应该说是进化么?或者说是……
“哈,找到了,怪物!”就在这时,一个十分违和的声音从洛的背后响了起来,让他稍微愣了一下。
是敌人。
洛羽闲的判断非常迅速,发现是背后的是敌人的同时,几乎是瞬间,就将元素神按在身上,开启了铠化。
“哦,理解得真快啊,不错,我就喜欢你这样的。”那个声音一边这么说着,一边似乎是掏出了手枪。
“砰!砰!”两声枪响,都在黑羽铠甲上弹了开来。
但这两声枪响,却像是巴甫洛夫的灯泡一样,在人群中炸开了更大的反应
恐慌,然后逃离。
对于死的恐惧,人类和元素使,都没什么不同。
“呼~还真是个‘硬’茬子”那人又适当地评论了一句。
由于黑羽是比较紧身的铠甲,所以是直接生成在风衣内部的,所以即使挡住了子弹,风衣上也不幸的被划破了两道。
随手拽下风衣,将黑羽的头盔和翅膀完全生成,洛羽闲这才缓缓回过头来。
“啧啧,还是条大鱼啊。”出现在洛羽闲视线中的是一个穿着毛边风衣,长着一头张狂红色乱发的青年,他双手中的两把有些复古的自动手枪应该就是那两声枪响的元凶了,“看来我真是走运啊,竟然在这个犄角旮旯的地方遇到了被称作‘黑龙’的S级目标啊”
“……黑龙?”洛羽闲并没有把这个词与自己联系到一起。
“背生黑翼,力量无匹,带来灾难的恶兽。”他继续解释起来,“总之就是这么回事吧。”
洛羽闲皱了皱眉,也没有太在意对方的话:“你是什么人?”
“哈哈,我也不知道啊。”那人回答,“不过你可以叫我松茸,这是会杀掉你的人的名字哦~”
“杀掉?”洛羽闲不信道,“用你那小手枪么?”
和刚才那两枪一样,这种程度的枪击是无法击破洛羽闲防御的。
“不信?”松茸扯着嘴角露出稍有些狡诈的笑容,“总之,我可是提醒过你了,不小心死掉的话,可别怪我哟。”
“滴——!”
像是有什么电子装置被打开的声音,接着,洛羽闲感觉到一阵耳鸣,甚至有一些头晕。
“唔……”出于谨慎,洛羽闲后退了一步,“你做了什么?”
“砰!”回答洛羽闲的是一记枪声,同时子弹直击在了他的左肩上,直接将肩甲完全打碎了。
洛羽闲陡然一惊,这家伙的枪怎么忽然变得这么强了?
“Cool!”松茸双手向外一张,像是西方人发表感叹的那种样子,“这东西真的很好用啊。谢谢你啦,Doc~”
“砰砰砰砰砰!”双枪连发,由于铠甲无法防御对方的攻击,洛羽闲只能迅速退避,不过即使如此,也有两枪射中了他,铠甲变得支离破碎起来。
意外的棘手啊……洛羽闲心里沉重起来,不过只是几秒,洛羽闲的心里就有了计较。
无法守,那么就攻吧!
右手向后一挥,和开发金乌时候一样,凝聚出了完全由元素构成的刀刃,同时猛地前冲,就要斩向松茸。
“没用的,笨蛋!”松茸的笑容狰狞起来,又是一枪打出,瞄准的却是洛羽闲的刀刃。
“铿!”令洛羽闲惊讶的事情发生了,那刀刃,竟是片片碎裂。
“砰砰砰砰砰!”又是连续的枪响,没有刀刃的洛羽闲更是避无可避,直接被子弹击中。
“喀嚓”铠甲完全碎开,而洛羽闲身上,多了两处枪伤,一处是左腿,一处是左手。
“咕……”痛觉袭向洛羽闲的神经,这对他来说,也是久违的感觉了,这让他想到了自己年幼时前那段岁月。
那时,他还是垃圾山的小小拾荒者,虽然一度成为过混混头子,不过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人物。
而现在,他却是让世界为之侧目的特殊存在“元素使”的重要人物。
与之相对,也担负着重要的责任,所以。
不能死在这里!
“哦!”忽然振奋精神的洛羽闲猛地握起拳头然后张开羽翼飞了起来。
反应过来的松茸虽然跟着发出枪击,却是鞭长莫及了。
行至高空,空气变得稀薄起来,那种耳鸣和头晕感却反而完全消失了,洛羽闲这时才发现,原来并不是对方的枪变强了,而是用了什么手段将自己弱化了!
“反元素力场……”洛羽闲忽然想到迷子某次和自己提到的这个词语,若有所悟,“是这么回事啊。”
“……似乎是人类针对我们元素使而发明的特种武器的样子……”迷子当时是这么说的。
毫无理由的强会让人心生退意,但有迹可循的强大却一定有着相应的弱点。
现在自己已经发现了它的弱点之一——范围
一旦拉开距离这个力场的效果就会完全消失,相反的,在那个范围内,削弱也是极其显著的,随便一颗子弹都能打碎自己的铠甲,这是非常异常的……
曾经洛羽闲也是试验过的,基本上只要是对人使用的武器,连通用的那些狙击枪都能完全防御住才对。
现在却连自动手枪都防御不住。
看来是无法使用铠化了。洛羽闲的眉头再次皱了起来。
不过,对方也只是个手枪使,即使自己没有铠甲,对自己的伤害也有限吧。
那么,不妨再试试,这所谓的“反元素力场”……他的极限在哪儿!
那一头,手扶额头望着天空的松茸眼巴巴地看着猎物在天上死活不下来,也是心急如焚,这时他倒是想起了同伴里那几个全副武装带着外骨骼装甲的家伙,他们应该会有飞行能力吧。
正当松茸几乎就要放弃天空中那个猎物时,对方忽然势头一转,下降下来。
“哈!太棒了啊!黑龙!”松茸兴奋地微微蜷起身子,仿佛野兽那样摆出迎击态势,“今天,就让我来……”
“屠龙吧!”
“砰砰砰砰!”弹丸迎向飞来的黑色身影,却因为对方的超高速而难以命中。
“啧……”眼看对方将要迎面撞上来,松茸不得不退避开来,然后对着他的背影继续开枪。
几个来回之后,松茸打掉了几匣子弹,却再也没有碰到洛羽闲一根头发。
“该死的,飞来飞去,跟个苍蝇一样。”松茸逐渐烦躁起来,“等我回去,一定在系统上给你改个外号。”
浑不知自己在人类中即将名声受损的洛羽闲这时倒是计算出了反元素力场的大致范围。
半径100米的球体
在这个范围内,元素使的实力会受到很大影响,尤其是将元素外放来使用的各种技能,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
从受弱化的程度来看,元素质化>远程攻击>近身攻击>身体强化。
以元素质化为理论依据的铠化受到影响最大,铠甲脆弱得连子弹都挡不住了;其次是射出羽毛作为远程攻击的黑羽风暴,只能割破对方的衣服;而鸦之爪几乎没有受到什么弱化;而对身体本身的强化更是完全没有受到什么影响,不然的话,黑羽高速飞行产生的气压都能让自己窒息才对。
得到这个程度的情报,自己受这伤应该值回来了吧。
不过,竟然把自己打伤,还是让人有些不爽呢,至少,再给他留点纪念才行啊。
“嘿……”
一边这么想着,洛羽闲再次下落。
这次,不是试探,而是,一击必杀的进攻!
“哦!来啊你这怪物!”松茸烦躁地以手枪应对着,准头比起刚开始时已经大有不如。
而洛羽闲正是抓住他那一丝烦躁中露出的破绽,趁虚而入,想要发起致命一击。
洛羽闲飞来,松茸下意识避开,却不料这次对方竟然忽地一个打弯,再次袭向自己。
“什……”松茸一惊,却是来不及回避了,只能将双手挡在身前。
这却正如洛羽闲所料。双手鸦之爪齐出,直接打飞了对方手中双枪,同时右脚一踩地面,竟将松茸直接带离地面。
松茸反抗不及,回过神来时已经到了一百米左右的高空中了。
“该死的怪物!你给我放手!”松茸下意识地骂道。
“好。”而洛羽闲的回答却是出乎他的意料,同时,他也真的就这么松开手了。
松茸忽然反应过来,这可是在高空,对方真的松开自己的话自己不是要摔死了么?
意识到这一点的松茸忽然奋起,一把抓住洛羽闲的双脚,然后就紧紧不放了。
“唔……腿上伤口被牵动,让洛羽闲疼痛起来,”怎么,不是你让我放手的么,你自己干嘛抓得这么紧啊。
“闭嘴!死怪物!”松茸一边这么说着,一边却发现将自己带到空中的这个家伙,用一种嘲讽的眼光看着自己,心中猛然不忿起来。
接着……狠狠一口咬向了洛羽闲左腿伤口处。
“……啊啊啊!混蛋给我松口!”洛羽闲一下子就被疼得浑身抽搐起来,连背后的翅膀都无法好好操纵了。
导致的结果,自然是……坠机。
两人在高空打了几个旋,下坠加上旋转的加速度让两人先后失去意识,坠落到了不同的地方。
而等到洛羽闲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喷泉的中间,正在被路人围观着。而与自己战斗的那个人,却是不知所踪。
无奈的叹了口气,洛羽闲试着坐起身来,刚好看到不远处的外挂大钟。
“糟糕……迟到了。”
万幸这次自己来接的元素使刚好是治愈能力,也省的自己回去之后被迷子骂一顿了。洛羽闲心中这么想着。
顺带一提,之后洛羽闲发现自己这次受的最重的伤竟然是咬伤。
或许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之后他穿的裤子从黑色西裤变成了牛仔裤。
至于那个人类,死了还是活着,洛羽闲并不关心,不,也许死了的话他会高兴也说不定。

镜子前面。
繁复的法阵一点点地被刻画出来。点亮的蜡烛按照图纸上那样排成奇妙的阵型。
虽然看上去这幅场面很庄严但是实际上……因为镜子位于女厕所而且是固定的,所以事实上法阵被摆在了女厕所里而且那些被夺魂的人的身体也摆成一排躺在了厕所的地上。
“在厕所里举行的邪教仪式还真是闻所未闻……”raynor这样吐槽道。
“你觉得要是给这幅场景命名应该叫什么?”虽然脸色苍白非常虚弱还贴着一张道符神似中华僵尸但是志在给全队插遍flag的素女缘坚持观看仪式并且还在跟raynor聊天。
“呃……邪教都是臭狗屎?”
“……”一旁在布置仪式的siren决定当做没听见这两个人说话。
总之复活仪式进入了开始阶段。
siren念出图纸上记录的晦涩拗口而又奥妙的咒语。冗长的咒语终于吟唱近半之时,一阵高声的大笑从楼下传来:“你们以为可以就这样逃走吗!”
紧接着一个黑影携带着强大的气流破窗而入。
那是个异常漂亮的女人,女性的象征异常饱满,整体曲线也十分漂亮。身材甚至胜过队里最好的vice不少。眼角向上翘起,显得分外狡黠。睫毛纤长,顾盼生情,唇瓣鲜红而微翘。再结合刚才那珠圆玉润的声线,不得不让人称赞这是上帝的宠儿。
如果是在平时,那么raynor可能还会调戏一下这个近乎完美的女人——但是不是现在,这个女人恐怕便是这场恐怖片的boss之一,这个地方巫术的发源者witch,当然不是适合用来调戏的对象。不过——
“虽然是很漂亮,不过一个不知道活了几百岁的老婆婆在说什么呢。”
却是必须嘲讽的对象。
队里战斗力强大的都被封锁在了另一个空间,对于巫术有压制的siren正在念咒,那个莫名其妙出现的陈泽逸也没有什么战斗力,noki这个精神力者现在也是派不上用场,新人之中在这边的阮戎看起来也不是很好用……
总之情况十分危急。好在年龄永远是女人的痛脚,特别是老、婆、婆。raynor的仇恨拉的非常稳。
不过这也带来了极端疯狂的攻击。witch强大的念动力带着隆隆的气爆声席卷而来。甚至厕所外走廊上那些装潢华美的家具也碎成了木片化作利刃向着raynor极速飞去。
(这女的开挂吧!no pitch no down!)
在心里吐槽着,raynor却也连忙躲进了边上的房间。念动力的洪流携着木刺轻松洞穿了走廊尽头的房门将它也化作木质利刃的一部分。紧接着利刃全部收回,在witch身边缓缓盘旋着。
“那么,年轻的小、弟、弟。你准备好接受惩罚了吗?”
(鬼才会准备好!会瞬间爆炸的!)
不过raynor也不会愚蠢的喊出来暴露位置,但是很快他发现这是徒劳的。身边的影子全部蠕动起来,然后轻易的发现了他并且向他包围过去。此时witch也移动到了房间门口。不过木质护盾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阴影组成的护盾。
(……好像已经绝路了?还真是被秒杀啊。嗯?)
此时心灵链接感受到一个新的信号,raynor连忙通过链接向对方传达了目标。
witch脸上露出猫戏老鼠的玩味表情看着这个年轻的娃娃脸被阴影逐渐包围起来。
然而异变突生,阴影开始挣扎起来,witch对它们的统治不再绝对,甚至她的权柄正在快速的被一个强大的力量碾压过去。witch惊讶地回头看去,从厕所走出一个安静帅气的美男子,而那对于阴影绝对的操控权来源正是这个男子。
(不得不说那个什么主神……虽然看上去是一个光球但是还是挺靠谱的。)
这个能力是步叙安在主神空间通过借入不少支线才得到的,操控阴影的能力。居然轻松碾压了这个世界的boss级人物,这让raynor十分的惊讶。
witch看不透步叙安的深浅——这个人轻松从自己手上夺走了阴影的控制权,虽然看上去没有什么可怕的力量,也许是自己走眼了……
witch详细思考着眼前人的实力,顺手却用念动力将raynor砸飞了出去。raynor像一颗炮弹直接砸穿了身后的墙进入了另一间房间,房间之中烟尘弥漫,甚至吊灯也坠落下来,然后其中便没了声息。步叙安却是奇怪的站在原地,什么也没做,像是要死守厕所。
“这位小哥,看你也是巫术的使用者,为何要和那些自诩正义的卫道士站在一起呢?不如和奴家一起征服世界如何?这具身体也可以随你使用哦?”
witch用魅惑的语气一边说着,一边搔首弄姿,泄露春光——她误以为步叙安是一个可以拉拢的对象,而且她自信这样的诱惑正常男人难以拒绝。
但是她不可能知道主神这个bug一样的存在——更不知道在她被封印的这么长时间里人类男性出现了一个奇葩的分支——基佬。
所以她的诱惑理所当然的失败了。
此时一道金红色身影直接破开了这栋别墅本应该结实的墙壁,极速飞射而出。伴随着“你们这群杂种竟敢随意使用本王的身体?!!!!”的怒吼,一拳轰在了witch因为异变慌忙张开的念动力护盾之上。那是一名龙化的少女,翅膀因为愤怒而不断地扇动着。紧接着一个转身,巨大的龙尾狠狠甩在了护盾上,整个护盾都摇摇欲坠起来。witch不得不把更多的精神集中在前方以面对这条怒龙的袭击。紧接着抓住mimcar甩尾产生的空隙,念动力顺势推出,猝不及防的mimcar瞬间被远远的推开。
“大意了……那就先干掉剩下的那些吧!”
将mimcar甩了出去,女巫操控着念动力杀了个回马枪,极速攻向守在厕所门口的步叙安——这时候她来不及考虑对方的实力了。
步叙安连忙召集身边的阴影组成护盾,守住自身。而强大的念动力却是摧枯拉朽一般破坏着阴影的盾牌,被击溃的阴影像是融化的雪水一般流进地面回到了原位。好在临近黄昏,屋内的阴影相当充足,浓厚的阴影翻滚着组成防御试图抵御强敌,又很快被冲散。但总算是拖慢了对方进攻的速度。
当步叙安被念动力甩出去并且在空中优雅美丽地吐了一口血之时,下一个阻挡者也已经准备好了。
刚刚复活的sieben顺手拆下了厕所的钢水管猛击向来势汹汹的念动力,物理学圣剑在他手中成为了奇妙的宝具,硬生生拦住了念动力的来势,强大的反震使得他虎口崩裂钢管也慢慢开始有一些扭曲——就在这时念动力却如退潮一般离去。龙化带来的强大肉体使得mimcar即使以极快的速度撞在墙上也没有受很重的伤害,反而是墙更惨烈一些。紧接着她就一个鲤鱼打挺起身再次冲向了站在走廊中全力驱使念动力的witch。
强烈的危机感迫使witch连忙收回念动力,念动力以极快的速度跟在了mimcar的身后,同时她也驱使就在自己身边的自卫的念动力迎击——她很清楚这名龙女的强大,所以她使出全力想要一举击溃mimcar。
mimcar顿时陷入了维谷之境,她不得不停下来阻拦身后袭来的那部分,而原本的前方那部分却乘机给了她重击。接连的打击之下,即使是肉体强大如龙也会受到伤害,何况只是拥有血统的mimcar——她背部的龙鳞有一部分已经碎裂甚至脱落,暴露出来的肌肤更是血肉模糊。
看到如此大好局势,witch嘴角勾起一丝没人欣赏的摄人心魄的笑容。
然而她已经被瞄准镜牢牢锁住。
之前raynor被击飞之时步叙安没有任何动作不是他不关心队友,相反他利用之前witch聚拢的影子保护了raynor。这使得raynor受攻击看上去很恐怖,实际上没有受多大的伤。
而raynor轻轻地换上了灵类子弹,就等着witch露出破绽的这一刻。
心跳早已控制到完美,整个人像是钢铁灌注一般纹丝不动,将witch得意的表情看的一清二楚。然后——
将准星锁在了witch太阳穴上,
扣下板机,
子弹被激发并且以可怕的速度射出枪膛。
然而。
一切突然失去失去色彩停了下来,整个世界只剩下黑白灰,又渐渐变亮,被白色所占据。
(这家伙还有底牌?不,不对……)
raynor很快否定了这个判断。因为白茫茫的空间之中,他只能看到一个逆着光的高大背影——而那明显不是witch,
当raynor还陷在迷惑中时,对方已经自顾自的开始了说明:“你通过了我们初步的测验,成为了一名真正的队长。”
稍有停顿,对方紧接着说道:“详细的队长权限你应该清楚的吧,我就不多说了。到时候就会知道了。现在我要告诉你一个最重要的事情,那就是作为一名队长,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对方突然转过了身。当raynor反应过来,对方已经在的他身侧,并拍了拍他的肩。
这把raynor惊出一身冷汗——因为对方有心的话,自己恐怕已经尸首分家。
“如果你不想失去所有的伙伴的话,就好好的努力吧!”
raynor转过头去之时,对方已经化作一团光芒,紧接着破碎,化成光的碎片,缓缓落到地上。然后世界又恢复到了彩色。
仿佛被按下了“播放”键的录影带,子弹继续飞行,并且按照raynor预定的轨迹,顺利击穿了witch的太阳穴,将对方的头部都轰成了残渣。
紧接着siren的十字架也如预定中一般回旋谢飞来,击碎了witch剩下的无头尸体,并且给予了那还未来得及逃脱的灵魂创伤。随着凄厉的鬼啸,那灵魂慌忙逃走。
“看来短时间不会回来了……”raynor用瞄准镜观察到那灵魂渐渐消失在虚空之中,通过心灵链接向队友汇报道,“啊,真可惜,还想趁热来一发呢,都碎了啊。”
然后他就收到了来自mimcar和素女缘的鄙视情绪。
“话说,你们刚才……”玩笑开过,raynor询问起其他人关于刚才遇到的奇妙情景,但是其他人都表示没有遇到,只有看过原作的素女缘推测,这可能是队长的认证过程。
(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吗……)
主神你抄袭没问题吗?虽然脑中有一瞬间出现了这样的吐槽,但是下一个瞬间脑中就不由得出现了下面的那句话。
“如果你不想失去所有的伙伴的话。”
中二病的金发少女、蓝瞳的面瘫牧师、黑发的插旗狂魔军师、幼小的精神力者、沉默的小偷先生……这些不知道什么时候、渐渐开始当成同伴的人。
(当然、不想失去啊。)
这样想着,raynor从废墟里站起身来。

感谢Yuki桑的赞助!
感谢Yuki桑的赞助!
感谢Yuki桑的赞助!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文笔渣渣!汤姆苏!内含天雷!不介意我是个一年级水平的就进来吧【捂脸
不要打我!
——
睁开眼睛之后,眼前一片黑暗。
昏昏暗暗的光线让我又感到一阵眩晕。
我居然没死啊。
试着轻轻抬起手臂,肩膀上被藤蔓洞穿的伤口还在流着血,刺眼的鲜红通过紧实的一圈圈缠绕的绷带,以剧烈的疼痛来向身体的主人提醒着它的存在。
起碧姐还是手软了呢……毕竟平时都是那么腼腆害羞的人……
绷带……是琴帮我包的吧。
治愈的效果没有想象中的好呢。
稍微适应了四周的光线,右眼中浮现的4F的情景,然而我却发现我左眼所接触的世界依旧没有半点光明。
为什么会这样……我没有伤到左眼啊。
难道是起碧姐后来伤的?
不对啊,她没有理由在我昏迷后还要伤害我的眼睛,毕竟她并没有打算杀死我啊,我活着出了挑战。
等等,我活着出来了!?
我好像突然惊醒了一样,腾地站了起来,但因为四肢的酸麻和左肩的疼痛又重新跪倒在了地上。
“唔……”
因藤蔓缠绕而淌着鲜血的膝盖重重的磕在地上,我轻哼了一声,却没有心思在意自身的疼痛。
我活着出来了。
我出来了。
那么,
也就是说……
起碧姐她死了吗!!?
我兀自瞪大了双眼。
怎么会这样!……
起碧姐她……死了?
为什么!
明明她那么强的……
没有理由,会死的啊!
能够这么简单的攻击了我,她当时应该也不在负伤状态。
是假的吧!那个起碧姐一定是假的吧!
起碧姐,不会弱到那种普通人都能简简单单的杀死她的地步啊……
对,就是这样!
我用没有受伤的右手使劲的按压着自己的太阳穴,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对啊,那个起碧姐很有可能是假的。
不是很多动漫都是这样的吗,像是挖掘人心的弱点什么的,让NPC伪装成一群跟主角有联系的感情要好的人。
对啊,就是这样。
真正的起碧姐那么强,不可能那么简简单单的就被拉进游戏,我平常也没怎么见过她玩游戏啊。
没错,所以,这个起碧姐很可能是假的……
没关系啊,这是个游戏,没关系的……
不过,为什么出现的是起碧姐?
不对,假的,是假的……
假的假的假的假的!!!
我的头脑开始混沌,我深吸了一口气,强迫自己暂时相信这个猜测。
我放下了按着太阳穴的右手,让它撑在地上,然后自己靠着墙,慢慢的站了起来,一瘸一拐的试着迈出脚步。
此刻的我明白,如果想要证明自己的这个猜测,只有询问他人。
询问他人,他们看到的boss到底是什么样的。
果然还是要问问琴她们,希望他们看到的并不是起碧姐就好了。
混乱中的我并没有察觉自己猜测中种种不符合常理的地方,只是希望去相信着。
扶着楼梯的扶手,慢慢的下了楼之后,我回到了房间。
房门撞到墙壁发出了“咯”的一声,我有些急切的将头探进房间里,却发现里面空无一人。
琴呢?
怎么不在……
我皱了皱眉头,心中总有一种不大好的感觉徘徊不去。
希望是错觉吧。
我关上了房门,朝着楼梯口前进。
不在房间的话,莫非是去找吃的了?
不能等了,要赶紧问一下她看到的boss是什么样的。
然后,在途中,我听见了几欲让自己昏迷的噩耗。
————
一路勉强搀扶着楼梯的扶手往下走,却奇怪的一个人都没有看到。
诶?大家都,到哪里去了?
就在我这么想着的时候,一个黄发的短发少女出现在我的面前。
大概比我矮一点的样子,一个看上去酷酷的很帅气的少女。
“那个……”我向着她走近了一步。
这个好像是叫柚的少女,看起来心情很不好。
“有什么事吗?”她冷淡的向我看过来。
“我想……问你几个问题。”我泯了抿唇,有些紧张地看着她。
少女点了点头。
“请问……你在挑战里看到的boss,是什么样子的?”
柚皱了皱眉头,似乎对我的这个莫名其妙的问题很不解,“boss……有什么问题吗?”
“拜托了!请告诉我!这是很重要的事!”我有些激动。
柚看了我一眼,开了口:“是一个戴着帽子长得挺可爱的小姑娘,还有一对兔子耳朵。”
她顿了顿:“啊,还抱着一只奇怪的兔子。”
我瞪大了眼睛。
她描述的那个人……不就是起碧姐吗!!!
柚又看了我一眼,有一种欲言又止的感觉。
“其实……有件事,我还是想说一下。”她吞吞吐吐的开口。
“你们队……除了你……”
“已经,全部……”
————
我的头脑就像是要炸开了一样,各种不安定的东西在里面搅动着,像一只只嘶吼着的野兽,在地狱的边缘惨叫着。
他们看到的,是起碧姐?
我们队里,除了我一个人,其他都全灭了?
怎么可能!!!
我捂住了脑袋。
即使认识的时间很短,但是不管是安静较小的琴,暴娇的仲言,板着脸的津泽,就连没怎么交流的花棂,对于自己来说,也是很美好的存在。
对于很少接触外面世界的我来说,
都是难得的,朋友。
特别是琴,我很喜欢那个病弱却有礼貌的小姑娘,尤其她还是自己的被监护人!
等等,我好像知道这只眼睛是怎么回事了。
我用右手覆上了我空洞的左眼。
因为,琴死了。
我失明的眼睛,跟琴不能见光的左眼……
吻合了呢,就连左肩的伤。
难怪,有治愈效果的绷带连镇痛的效果都减弱了。
因为,它的主人,死掉了。
……最重要的是起碧姐!
为什么起碧姐会在这个游戏里啊!!
我在柚面前睁大眼睛跪坐了下来,一下瘫在地上。
这样想起来,很多地方都不太对啊。
平常都不玩游戏,除了吃吃吃什么都不管的那家伙,突然拿着这样的游戏光碟回家,还硬逼着我玩。
好奇怪!
再加上,起碧姐……
好奇怪啊!!
为什么会这样。
不对……我要去问清楚……
问清楚!
没有管顾身后那人有些担忧的眼神和急切的话语,我挣扎的爬起来,然后跌跌撞撞的往Morica所在的厨房跑去。
那样的背影,已经不能单单用狼狈来形容了。
就好像是失去了人生所有的希望一样。
“呵,你终于来了吗?”站在一边的Morica笑意盈盈的看着我。
“上次就说过了啊,这次来找我是想换什么情报吧!”
我急切的就要拉住Morica,却被她灵活的一下就躲开:“阿拉~这么心急的触碰一个异性可不是什么礼貌的行为呢。”
“不要闹了!”我受不了的大喊。
“起碧姐!起碧姐是怎么回事!”却没有再次去拉她。
“啊,是那个一战的boss吗?”眼前的异瞳少女露出了嘲讽的笑容。
“真是可怜呢,一个人来到这种地方。”
见我又要耐不住大喊出声,Morica伸出一根手指制止了我:“阿拉阿拉,虽然知道你心急,但是不是有一句话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吗~”
“不要试图去惹怒我哟~”
在我看来,现在的Morica,精致的脸上,那满满的恶意像是要溢出来一样。
金红色的异瞳里也只剩下了兴趣,那种看戏一样的眼神。
讨厌的感觉。
就好像上次被我借鞋弄得面具龟裂的家伙不是她一样,像这样,把我们的人生,当成游戏。
好讨厌!!
但即使如此,我始终还是听从了她的话,慢慢的平静了下来。
见我不再那么激动,少女慢慢的又开了口:“起碧那孩子啊,很害羞呢。总是怯怯的,胆小得很啊。”
“所以就因为这样,被自己的能力反噬,然后,把自己关在了这个结界里。”
“于是啊,就被我拉进了这个游戏呢。”
Morica向着我的方向走近了一步:“那个孩子真是可怜得很。”
“进来之后,经常一个人缩成一团颤抖着抹眼泪呢。”
“还一直说着一句话啊……想回家什么的。”
我的思绪炸开一片。
我突然想起来了,我昏倒之前起碧姐说的那句话。
【对不起啊,句号】
【对不起……】
【句号……】
【句号……】
【我……】
【我想回家……】
那时起碧姐颤抖的话就像是哭的撕心裂肺一样,有一种撕裂了内心的悲伤。
起碧姐……
起碧姐!!
“你说的这些……是真的吗?”
我紧紧地握着拳头,想尽量使自己的声音不再那么颤抖。
我没有忘记,这个游戏叫真实谎言。
眼前这个人的话,并不一定都是真实的。
“撒~谁知道呢?”少女“咯咯”地笑了起来,清脆的声音在有些空旷的厨房里回荡着。
“想要知道最真实的情报的话,就必须用器官来换哦~”
“不过啊——”
她恶劣的笑着,伸出细长白皙的手指指向我的心脏。
“这可是很重要的情报呢,恐怕不是你能很轻易的付得起的啊。”
“说不定,要用你的性命交换哦~”
“那么,你是想要活下来,还是想知道情报呢?”
……怎么办。
“啊。不对!”像是惊讶着自己的失言一样,“如果死了的话,知道这些情报也没什么用了吧。”
“如果想真正的有所行动的话,一定要小心慎行哦~”
我已经一刻都不想呆在这里面了,所以我拖着伤痕累累的身体,提步就往外走。
“阿拉,脾气真是坏。”
“好心给你一个建议好了。”
清脆优美的声音不断在我的脑海里回响,让我感觉刺耳无比。
“要交换情报的话,需要的不一定是自己的器官哦~”
我停步,刷的回过了头。
果然,这才是这个游戏的真正意义吧。
玩游戏的人并不是我们,而是这个所谓的NPC!
————
就这样恍惚的出了餐厅的门,句号跌跌撞撞的往外走。
Morica的话,他并不是没有听进去。
想要知道真相的话,他不能死。
所以,死的只能是别人了。
必须,杀死他人……
这样想着的句号,没有注意眼前的路,也没有注意先前告诉自己情报的黄发少女柚在他出门的那一刻同样进了厨房。
所以,在路过喷泉的时候,迷茫的他把一个与自己身高相差不多的“成年男孩子”撞入水中了也不自知。
直到听到那声入水声,和少年担忧的呼唤。
“小晏你没事吧?”
句号盯着他们看了一会儿,随即转身就要走。
好像做不到啊,杀人什么的。
就算是刚刚这样简单的事情,也做不到啊。
如果刚才那个会游泳的少年没有被拖下去的话,他也会跳下去的吧。
他好像,杀不了人啊……
“那个BOSS叫作……起碧,对吧?和你是什么关系?”那个刚从水中出来的少年朝着句号喊道。
沉思中的句号忽略了那个声音,他只是低下了头,低声呢喃。
怎么办……
“起碧姐……”
我做不到啊。
怎么办……
父亲……
我是不是……又要被丢掉了?
我从船上跳下来之后,在海面上跑了好几个月。
……
其实并没有,好几个月是现实中因为作者发懒所以坑着的时间,其实在作品的时间线中,我只跑了几天就到达了我的目的地——一个位于北欧的小研究所。
这是我之前呆的地方,原本是打算到了元素学院之后再回来这里拿走我的东西,但在船上徐然的占卜告诉我说这里出事了,因此我就将这一计划提前。
某种意义上说这里也算是我的老家,但显然,现在家里的这些人并不欢迎我。
“注意,背叛者——编号40105出现!全员,准备迎击!”
看样子我弃(bian)暗(jie)投(tou)明(di)的事情已经传到这里了。
这里的所有安保力量都全副武装,在研究所内外布阵,当我出现在研究所建筑物的入口前方的时候——
“开火!”
——随着一声令下,铺天盖地的弹幕火网便朝着我快速袭来。
只不过,这点程度的攻击,我只要即使召唤出蛇群织成防护网就能轻松防御。
我注意到他们所用的枪械和子弹,那些并不是能致命的类型,看起来他们是要活捉我而不是要处决我。
“赫尔,说话。”
我叫出赫尔发动噪音攻势,所有敌人立刻丢开手上的枪械,一边捂住耳朵一边在地上打滚哀嚎,弹幕射击也因此停止。
“直接废掉他们的听觉好了,赫尔。”
赫尔接受了我的命令,加大了噪音的强度和频率。
不只是鼓膜,这种程度的噪音震动搞不好会直接损毁他们大脑皮层的听觉中枢。
这样一来,他们就不再有反击的力量。
研究所内部,除了和外面一样的武装安保外,还有一些带着各式各样实验性武器的研究人员。
他们全都不是我的对手,我两三下就击倒了所有朝我发起攻击的人,一路走到我的房间前面。
根据徐然的占卜,研究所的人应该已经对我的房间下手了。
所有能搜刮的全部搜刮走,所有能销毁的悉数销毁掉。
而装着我姐姐的那个铁处女棺材,说不定也在销毁之列。
这种事我绝对不允许它发生。
我直接毁掉了房间的电子锁,推开了门。
在门的内部,我看到我的房间被搞得一团乱,各种家具和物品散落一地。
但那是我后来才注意到的事,在我开门的一瞬间吸引我注意的,是站在那里面的某个人。
既然立绘已经画好了,那我就不详细介绍她的外貌了,总之是个年龄和我相仿的女孩,一头及腰长发自军帽底倾泻而下,高挑傲人的身材被军装紧紧裹着,令人目不转睛。
但更令人在意的是她手上拿着的银色长枪,以及她眉毛底下那双眼睛中投射出的冰冷骇人的视线。
直到这时,我才回想起了这件事:
这研究所的战力并非只有外面那些安保和研究人员。
这里还有着能和元素使一对一单挑的人类。
被称作此处王牌的女人,元素猎人布伦希尔德•艾斯帕德。
我面前的这个人就是她。
“洛基,你回来了啊~”
她看到了我,开口道,
“我真的好想你呢~所以就呆在你的房间里等你回来~”
照设定来说,我跟她应该是猎物和猎人的关系,但事实上我俩算是同事,平常关系也不错,我都直接叫她“布伦”,而她也常常用很亲昵的方式和我说话。
但这一次不是。
虽然话语的内容给人很亲切的感觉,但她说这些话的语气却是毫无情感的棒读。
如果非要说那里面蕴含着什么的话,应该就只有和她的视线一样冰冷的憎恶跟冷漠吧。
“呐~你觉得我等你回来是要和你做~什~么~呢~?这可是在你~房~间~里~哦~!”
“看你的语气和架势,应该不是想和我做什么令人愉悦的是吧?”
我唤出两条蛇缠在手上。
刚刚用过赫尔的噪音已经消耗了我许多体力,要是考虑到续航的话,现在的我不能使用赫尔跟芬里厄——如果我能早点想起来这边还有她在的话就不该那么浪费MP了。
斯雷普尼尔并不适于室内战,而且将它与我的身体融合的技能我还不是很熟练,在对上布伦的时候用自己不熟练的能力无异于自寻死路。
综上所述,我目前能使用的就只有耶梦加得的蛇群了。
“没有啊~我还和你做相~当~令人愉~悦~的事哦~”
布伦的脸上闪过一阵恍惚的神情。
“那就是~~~在这里杀了你啊!!!”
突袭。
布伦举起手上的长枪朝我刺来。
那长枪光是枪刃的部分看上去就很重,但她却能以她那副并不强壮的身体灵活运用,她的实力也由此可见一斑。
“唔——!”
我一侧身闪过这记长枪突刺。
布伦的长枪枪刃上带有高压电,虽说一瞬间的触碰并不会造成多大量的电流贯穿身体,但那伤害也还是不容小觑。
见我躲过突刺的布伦,顺势将长枪朝着我的方向用力一扫。我则是及时让右手的蛇冲上天花板缠住灯架,把我整个人拉了上去,这才躲过第二击。
布伦将扫空的长枪挥到后背绕了一圈,再次将枪头指向悬挂在灯架下的我。
接着她左右旋转枪身,随着发出“咔”的一声,枪尖处射出了某样高速飞行的物体。
我把悬挂的身子朝旁边一晃,及时躲过了那物体的撞击,但它却击中了支撑着我的灯架。
轰!
飞行物在撞击之后发生了爆炸,将灯架整个炸散,失去支撑物的我也从天花板上落了下来。
若是我就这么落下去的话,一定会被现在布伦架在那里的长枪刺穿身体,然后被高压电烤成肉干。
右手上的蛇刚才跟着灯架一起被炸烂了,所以这次我挥出左手的蛇缠住枪刃。
蛇的身体在碰到枪刃的时候发出了噼啪的崩裂声,【魔】元素所组成的魔物也会对物理电压产生反应,那条蛇会代替我成为被烤焦的肉干。
但在蛇完全死亡之前,它用尽了最后一点力气把枪尖从我的下落路线上扯开,让我免于穿刺之苦。
然后我就直接撞在了布伦身上,把还因为情况剧变而稍稍显露讶异的表情的她撞倒在地,而我则是骑在她身上。
这样子看上去有点糟糕啊……
“我居然没有听从吾王的教诲,把你这种人当作同伴!”
当我把因为下落而贴到布伦胸口上的脸挪开之后,就听见她这样喊道,
“元素使都是敌人!是这个世界的渣滓!”
她试图右手举枪刺我,我及时用我的右手按住她的右手,同时召唤出大量的蛇把她的手臂死死缠住,加强束缚的力道。
好极了,现在的样子看上去更加糟糕了……
“我只是突然觉得他们那边比较好玩啦,玩腻了的话就会回来的。”
我对她说道,
“所以,我们还是朋友吧,布伦?”
这些都是我的真心话。
“绝不!依照吾王的旨意,元素使应当被悉数诛杀!我绝对不会再犯错了!”
布伦抬起左手朝我挥拳,却被我同样以左手接住按在地上。
糟糕度进一步上升……
“欸,为什么会这样?你以前不是一直陪我玩的吗?”
“吾王赋予我的使命胜于一切!即使我曾经被一时的情感所干扰而迷惘,但那也不能否定我应当去做的事!”
交涉失败。
原本我还想着把布伦也拉到学院去的呢。
看样子这是不可能的了,我和她终究还是变成了敌人。
真是太令人伤心了……
不过,伤心归伤心,既然已经是敌人了,那我也不能就这么放她不管。
现在来想想看吧!我要用什么方式来弄死她……
……
对了,那个的话应该不错……
“布伦,虽然我还没正式进入学院,但我还是学到了一些东西哦。”
“?!”
我放开了她的左手,并开始在我的左手掌上聚集【魔】元素。
“那就是被过量的元素侵染的人,会变成怪物哦!”
我在海底研究所看到过的那些被光叔称之为“侵染者”的怪物。
美女被转化成怪物之后再被杀死,没有比这更悲惨的死法了吧?
“你、你要做什么?!”
“侵染你啊!”
我瞄准布伦的胸口心脏的位置,伸出聚满了【魔】元素的左手。
元素使主动做出的侵染行动,似乎只会让触碰到的部分产生变化,所以我决定先改变人体最重要的器官之一的心脏,先在生理上让她发生变异。
再来就是大脑,在心智上让她堕落。
“不……”
我这还是第一次见到布伦脸上出现这样混杂了恐惧和惊慌的表情。
“不要……”
我的手就快要接近她的心脏了。
“不要……!”
只要再一会儿,她就会变成非人类的怪物。
“不要对我做这种事!”
就在我的手快要碰到她的时候,她将刚刚被我释放的左手臂猛地抽了回来,挡在胸口处。
这么一来,被我碰到的部分就不再是她的心脏,而是她的手臂了。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在手臂被侵染的那一瞬间,布伦发出了混合了哀嚎和尖叫的声音。
“我的手!我……唔哇哇哇哇哇哇哇——————!!!”
她的四肢和身体开始剧烈扭动,爆发出极其恐怖的力量,挣脱了右手的束缚之后又把我从她身上推倒在地。
她的左手已经开始产生异变,原本白皙的皮肤开始发黑,同时像被印版拓过一样出现狂乱的文字和符号。
这就是被【魔】所侵染的肉体……
刷!
等我反应过来在她挥枪的刀光剑影间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她的整只左手臂已经被她自己切了下来。
侵染的范围就只在那断臂上而已,她身体的其它部分依旧是人类的身体。
就算没有亲身体会我也看得出来,人类的肉体被侵染的时候会产生巨大的痛苦。
一般人难以忍受这种痛苦,意志薄弱的人说不定会因此产生自我了结的念头。
但在怎么说,为了祛除这种痛苦而自行截肢什么的,都太乱来了。
被切去肢体的痛苦,难道就会比被侵染的痛苦轻吗?
“我……宁可断手断脚,也不允许自己被你们的污秽所污染……”
布伦捡起断臂的袖子扎在左手臂的切口上,强行止住了血流。
“太乱来了吧……”
我看着地上已经不再抽搐的布伦的断臂,说道,
“……不过,就是因为你这么喜欢乱来,所以我才会喜欢你呢。”
“……你又想用花言巧语蒙骗我吗?”
布伦用剩下的右手抓住长枪,指向我的头部。
准确地说,是指向我的头部和躯干连接的部位,也就是颈部。
“没有啦,布伦,你是很有趣的女孩呢。”
我再次召出造物,不过这次只有耶梦加得一条。
因为我已经预判到布伦接下来的动作了。
“死吧,菲克修恩。”
即使只剩独臂,但布伦挥舞长枪的势头仍然不减。
但那仅仅是势头而已,仅仅只是“看上去如此”而已,实际上无论是威力还是速度,都比她两只手都在的时候要弱一些。
光是“弱一些”就足以让我的回避和躲闪动作轻松不少。
我趁机移动到她的左侧,才让缠在我手臂上的耶梦加得发出攻击。
攻击方式是撕咬,攻击目标是布伦的断臂处。
“!!!!!!!啊啊啊啊啊啊啊————!!!!!!!!!!!!!”
耶梦加得张开大嘴咬住了目标,一口将绑在上面当作绷带的袖子和血肉一起撕下。
伤口再一次遭到重创的布伦的动作被剧痛逼停,身体也失去了平衡,单膝跪了下去。
短时间内让这么漂亮的女孩发出两次惨叫,我也是够人渣的呢。
不过因为这是战斗,是双方为了希望而投身其中的绝望的战斗,所以我没有错。
“我说你‘乱来’的意思是,明明是在战斗中,却还能这么毫不犹豫地切掉自己的手臂,削减自己的战斗力。”
趁着布伦因剧痛而无法动弹的时候,我让耶梦加得缠住她的脖子。
“我回来这里只是想把我姐姐带回去,所以不要阻止我,不然——”
耶梦加得露出尖锐的蛇牙,抵在她喉咙的部位。
“——就算我再怎么喜欢你,也不得不忍痛割爱。”
“啧……”
布伦砸了一口,
“我还没完成吾王交给我的使命……我还不能死……”
“我当你同意了哦?”
我把耶梦加得留在布伦脖子上,自己则在因为战斗而变得更加混乱的房间里寻找我要的东西。
幸好他们还没有对姐姐怎么样,她的铁处女依旧很完好地保存在那里。
我又翻出一些没有被搜走或者销毁掉的东西,全部打包在一起,和铁处女一起扛在肩上,同时用布伦掉在地上的长枪里的爆炸箭在墙壁上炸出一个通往外面的缺口。
我走到外面,回头看了看因为被蛇缠着脖子而只能恶狠狠地瞪着我的布伦。
差不多也该放开她了。
“耶梦加得——”
放开之后要马上处理掉她,否则以后就麻烦了。
“——咬下去。”
说时迟,那时快。
耶梦加得的蛇牙明明已经触碰到她的喉咙了,但她却还是能在牙齿咬下去之前用右手掰开蛇头,并把整条蛇从脖子上扯了下来。
除了布伦本来的反应速度了得之外,这应该也跟我的体力已经大量消耗,影响到了造物的运动能力有关。
被扯开的耶梦加得摔落在地,又被起身的布伦一脚用鞋跟刺穿头部,消散成了虚无。
“菲克修恩————!”
“拜拜咯,布伦。”
趁着她还没冲出来,我赶紧开溜,没入研究所外茂密的树林之中。
“没能处理掉布伦呢……算了,以后有机会再见面的话再说。”
我拉紧了扛在肩上的铁处女和其它行李,稍作休息之后便踏上了回去的旅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