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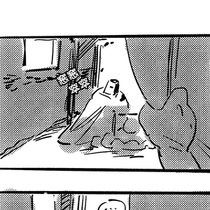

因为后面太弱智我甚至在思考要不要关联友友们……
但是春晚……!!
有要改的叫我嗷嗷嗷哦来不及了我的疯狂星期四没写到啊啊啊啊啊流泪
第三章·案情讨论
白日里行人摩肩接踵的小街现时呈现出另一重意义上热闹非凡的模样。
五颜六色的灯光闪烁着,将地面映照得色彩斑斓。冷却的棉花糖与爆米花的气息相互交织,在夜风中发酵,营造出空洞的甜蜜。穿着可笑蓬蓬公主裙的案犯躺在地上,黄色的警戒线圈定一片区域,将尸体与纷乱的人群分隔开。蓝色制服的牧羊犬在尸体旁边窃窃私语,寻着血迹嗅闻寻找夺命子弹的踪迹。嘈杂惊慌的羊群温顺地从道中经过,无暇他顾,步履匆匆地抵达被救护车与担架围绕的临时羊圈。
两种相似却又绝不相同的白衣人在羊圈中穿梭忙碌,一类脸上总挂着几分焦急,另一类眉眼间浸透了看破生死的冷漠。
流山凛皇穿过五颜六色的志愿者,搭手帮医生把伤者抬进救护车后,还没来得及拭去额间的汗,一转脸便瞅见自家小狗和同事呼哧呼哧抬着担架跑过来了,后边还跟着抱着小孩的红发女士。
“琉斗!”流山凛皇先是不动声色松了口气,紧跟着连忙让路,把他们送到另一辆救护车前,让伤者上了车,才递上毛巾说,“辛苦了……没事就好,我说怎么没在安置点看到你。”
名冢琉斗的护目镜早不知道飞哪里去了,棕褐色的头发蓬乱一团,四处乱翘,他弯腰扶着膝盖呼呼喘气,回答:“哈啊……、本、本来是想找你的……但是没找着,场内被害情况比较严重,我就帮夏目小姐运送伤患——幸好有麻生来了。”
麻生虎太郎气喘匀了,他随手擦了擦汗,爽快一摆手:“小事一桩!送完这个我还得赶回去。啧,里面要搬的太多了。这豆腐渣工程到底是哪个混蛋建的啊!”
夏目星砂扶着车,累得说不上话来,无力地摆摆手表示无法参与该话题的讨论——刚才近距离被扩音器爆破的结果就是脑子里嗡嗡的,直想吐。
名冢琉斗递给她一瓶水,直起身子呼噜了把头发,不但没捋顺还让自己的一头翘毛更加蓬松。他也不在意,只接道:“那肯定谁办的活动谁建?……我也还得回去一趟,除了帮忙之外我刚才在混乱间有看到一个可疑的人,我要去寻找一下她有没有留下踪迹。”他大概描述了当时的情况,总结道,“感觉像是奇奇怪怪的邪教徒。”
流山凛皇摸摸名冢琉斗的脑袋,扬起无奈的微笑:“注意安全。我接到别的命令,恐怕不能与你们一道。”
名冢琉斗非常理解:“好,估计你们要忙死了。”
在几人说话间,救护车亮起了灯,乌拉乌拉驶离现场。没了倚靠,夏目星砂也不得不直起腰来,她挤出几分力气,说:“不用管我,我歇一会儿之后就在这里帮忙了。
几人就此分开。名冢琉斗回到场馆,在麻生虎太郎“啥也没有啊,你该不会是看花眼了吧,就算没有这么乱估计也不剩什么了”的旁白中,挠挠后脑勺,回忆道:“不会吧,我记得她还做了个奇怪的手势呢。”他模仿对方古怪的手势,又思索了一会儿,无果。
麻生虎太郎抬起地上的伤者,招呼他:“来都来了别神神叨叨了,快干活吧!”
———————
紧张忙碌的救援工作一直持续到半夜。名冢琉斗回家后倒头便睡,一直睡到第二天天光大亮,才悠悠醒转。
他一摸旁边,凉的,便知流山凛皇整夜未归。名冢琉斗心想这次事件影响甚大恐怕难以收场,加班也很正常,随即鲤鱼打挺一骨碌起……!
——不但没起来还差点儿滚下了床,他悻悻地甩动小狗尾巴爬了下去,打开电视洗漱去。
W市电视台里正在播放W市头条新闻:“……截至目前已造成43人死亡,其中外籍遇难者11人……”
主持人字正腔圆地念着稿子,将死去的人类变作一个个冰凉的数字。
名冢琉斗叹气,只觉空气寂静了许多。他咕噜咕噜漱口,之后拖着步子走到客厅,给流山打了个电话,准备问问情况。
电话没通,流山的短信倒是一秒就到了:在开会,开完给你打。
名冢琉斗琢磨着这会开起来肯定没完没了,于是他又拨打了前同事的电话。
这次倒是很快就接了,对面传来一道慵懒的女声:“喂?哎呀这不是名冢嘛,怎么了?”
“浅井姐——”名冢琉斗听到那边的吹气声,就知道对方铁定在外面偷偷抽烟,他倒是没有拆穿,单刀直入地问,“想问问情况怎么样,凛皇开会我联系不上。”
浅井真宙“喔”了一声,换了个姿势,懒散地压在栏杆上:“打探消息你问流山不就得了。光是叫声姐就想我告诉你未免也太容易了,想的美。”
“……”名冢琉斗只好使用更加高明的话术,“你又偷偷溜会了吧我不会和司长打小报告的!事成之后我们请你,听说最近酒吧里要开展劲霸星期四活动!有很多炸鸡和饮料哦!”
嘁,失策了。浅井真宙顿住,两秒后弹掉烟灰,若无其事地回答:“行吧。说好请我啊。还有,消息换消息。电话不好说,一会儿在你侦探社见。”不吃白不吃。
十几分钟后,把锅扣给泽城的浅井真宙堂而皇之溜号,踏进侦探社的大门。
名冢家一层是侦探社,此时大厅的电视中,正在播放前线记者突击安乐堂HIROKI遗体告别仪式的报道。
“哦,我的天使——”浅井真宙立刻捧心抹泪,深情地望着HIROKI的谷子阵,“真是绝美的谷阵,以后都要成为海景房了吧……嗯?”
噼里啪啦的声音陡然响起,突入画面中央的SENA犹如困兽,红着眼用力将哥哥的挂画扯下。画轴飞舞,在半空甩过一道靓丽的弧线,扇飞桌上徽章七七八八,叮叮当当掉在地上。
画面内外一时均陷入了沉寂。
摄像机的画面在广大观众的注视之下开始晃动,伴随着记者“因发生放送事故,暂时中断,如给大家带来不便尽请谅解”的背景音下,彻底变成了黑屏。
名冢琉斗索性关闭了电视。
“……真是可惜了绝版谷。”浅井真宙耸肩,注视着黑漆漆的屏幕,在无人可见的角度里扬起了一抹耐人寻味的笑容。
—————
……
“所以说警察局里面肯定有内鬼。”浅井真宙瘫在沙发上,哈欠连天,“作案工具已经确定是存放在库房的老型号,但案犯生前行迹显示他没有机会接近活死人特别搜查司,而近日进出库房的人——看,有这么多。甚至司长都进去过喽!”
“你刚才不是说案犯精神状态不佳,难不成是报复社会。”名冢琉斗仔细查看仓库进出登记表,疑惑道,“体温感觉不太对劲……怎么安城也在里面。”
浅井真宙摊手:“哦,我抓他问了,他说他进去摸鱼。”
“既然是安城的事情,那似乎也挺正常呢!”名冢琉斗暗道在这方面警局大部分前同事实乃半斤八两,他指指表格,“正常人体温不会低于36度吧,比如这个34.8的,除非是活死人,不然我只能想到体温检测器坏了。”
浅井真宙抬起眼皮扫了一眼,漫不经心:“可不是嘛,司长的体温还异常地高呢,带病工作真是辛苦喔。”
“不过司长在这个期间去仓库,又是在场安保负责人,估计要排查好一阵了?”
两人嘟嘟囔囔,转而讨论起永山究竟是不是看不顺眼活死人买凶杀人——毕竟有福神记者拍照证明他在事发前和死者起了争执。
在话题飞到司长和双子星究竟有没有私人恩怨之前,流山凛皇踏入房门,阻止严肃的案情讨论会向八卦大会发起冲击。
他偏头望向浅井,有礼有节地打了招呼,才在名冢琉斗亮晶晶的眼神下坐下,道:“永山若是想要除掉谁,不必将自己置于嫌疑人的范围之内。但他似乎知道更多内情,当日福神采访的时候曾说他在调查什么,他却对此讳莫如深。”
“那你们开会开了什么了?”浅井真宙翘着二郎腿,不紧不慢地问。
“大抵是些当日情况的梳理。”流山凛皇笑容不改地回答,双手抱臂——这在心理学上通常被看作是一种拒绝及防备的姿势,可他的态度却很从容,让人看不出端倪,“总结下来要点有三。其一,舞台倒塌的直接原因是承重柱数量不足且有一根断裂,而主办方甚至没有监控。
其二,有观众表示在混乱中看到可疑邪教徒。”
他将视线转向支着耳朵的名冢琉斗,搓了搓对方毛茸茸的脑袋毛,随后将目光水平移向浅井,继续道:“其三,罪犯使用枪支来源搜查司,警局中有内鬼。仓库进出记录你们应该看到了。”
浅井真宙将滑落的发丝别到耳后,挑起眉梢,也笑:“是啊,所以说罪犯的人际关系还在进一步调查中嘛。那舞台是谁建的他们查出来没啊?”
“大型项目建设政府都有备案,经核实供应商是望日会社的十八手外包。”流山凛皇语气平淡,客观叙述道,“望日会社负责人当晚也出现在现场,他对事件表现的十分冷淡。虽然也有人怀疑姬城楝具有作案动机——因为他对OBLATION的活动方针存在不同看法,但目前尚无切实的证据。”
名冢琉斗支着下巴:“望日会社的人不好接近呢……奥,不过再几天酒吧有一个劲霸星期四的活动,听说预约情况十分火爆。也许可以去撞撞运气?人多口杂的地方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其他人都没有意见,浅井一瞧时间到达正午,速速开溜去吃午饭。
名冢琉斗则和微微皱眉的流山凛皇勾肩搭背,把他的胳膊薅进自己怀里:“你是不是还有什么没说?”
流山凛皇松开眉头,轻轻颔首:“警局毕竟出了内鬼,话我不可尽说。琉斗,你怎么看待幕后黑手的动机?”
名冢琉斗摸摸下巴,煞有介事地说:“司长的话,他现在还排除不了嫌疑,可对他而言这件事完全没有什么好处。另外,他知道内情。
姬城楝……我听说他想改变OBLATION的过激黑暗风格,但是望日会社旗下的娱乐公司已在筹备海选,他没必要为此大动干戈。可舞台又与望日脱不了关系,他有可能提前知道豆腐渣工程会塌。
SENA……我不太关心明星八卦,只隐隐听说他们火起来的原因主要在猎奇表演,粉丝之间争执不断,SENA也可能与哥哥产生龃龉吧。
邪教……摸不清邪教徒行事的逻辑。如果他们的目的是让全人类升天,那昨晚难不成只是制造恐怖袭击?”
流山凛皇补充分析:“本次事件中除HIROKI外,活死人未死一人,却因警局的态度及HIROKI的死而牢牢占据了舆论上风。有心人若想借此倒逼搜查司在一些事务中让步,也犹未可知。”
“嗯~”名冢琉斗转换思路,一拍手,“那研究所也算既得利益者吧,不是说他们在研究新的营养液吗?量大管饱非常管够。活死人的利益与他们间接挂钩。
我下午打算去一趟教堂附近转转好了,顺便问问朋友有没有听过研究所有什么传闻。”
“好。”
TBC
感觉好多流水账(擦汗(流水账之后我要开始弱智了!!!!
第四章·男科医院
名冢琉斗到达教堂附近时,太阳还热烈地挂在头上。
清澈分明的日光落在巴洛克风式花窗上,映射出五彩缤纷的光。微风拂过,林荫道两旁顿时沙沙作响。
名冢琉斗举步走入道中,目光变得锐利起来,不着痕迹地向四周打量,搜寻可疑人物。
皇天不负苦心人,就在他张目四望之时,一身穿黑袍的可疑男子鬼鬼祟祟地靠近了他,苍蝇搓手:“阿巴阿巴您好阿巴,年轻人,我想给你介绍一下我们伟大的天父,全知全能的神,阿巴神。”
名冢琉斗一愣:“?你说什么神?”难不成要带走全人类的神叫阿巴?这名多少有点……弱智。
男子端详他的表情,从中品味出一丝不信,旋即神秘兮兮地掏出一瓶药水:“我知道您可能不会相信我,但我知道,如果展现祂的神迹,你一定会改观的。这可是无敌的变性药水哦!无论谁喝下去都可以变成女孩子哦!”
瑰丽的蓝紫色液体在玻璃瓶中晃荡,呈现出异常绮丽的色泽。名冢琉斗心说这什么玩意,这什么神,这不是一个邪神吧!!有几个邪神啊到底!
名冢琉斗慌忙迅速地摆脱了热情的传教士。回忆起男子信誓旦旦的面庞,他的内心不禁升起一丝怀疑——这东西难道真能变性?
名冢琉斗的探究心很强。这个疑问停留在他的心头,犹如蜻蜓立于荷尖,存在感十分鲜明。甚至于连线人告诉他研究所似乎有离职研究员失踪的传闻,名冢琉斗也只是收下资料没有细听。
真的能变?真的假的?
名冢琉斗内心的警惕逐渐被好奇压倒。
晚饭时流山凛皇提溜住小狗耳朵,问他怎么心不在焉,名冢琉斗老实回答,眼睛滴溜溜地转:“好奇变性药水是不是真的能变性。”真的有那么神奇吗!这可是变性药水耶!
流山凛皇斟酌少许,不知道脑补了什么,安慰他:“想变成女孩子有很多方法,你要是需要的话我可以帮你联系变性手术。至于这个——陌生人给的东西好孩子最好不要吃。”
他二话不说倒了一半不明液体进鱼缸里,想通过此种方式分辨药水是否有毒。
圆鼓鼓的金鱼恣意游弋,扇形鱼尾在水中飘逸舞动,朝气蓬勃。
但在外行人的眼中很难分辨出金鱼的公母究竟有何变化,于是流山凛皇只能总结:“应该没毒,但是不知道对人体有什么影响,最好别喝。”
名冢琉斗捏着小瓶子点了点头:“确实很奇怪,颜色就很奇怪。”哪里都奇怪,怎么想都很可疑。
——所以这玩意到底能不能变性?
抱着这个疑问名冢琉斗陷入沉眠,落入梦中。
梦中,他从无影灯刺眼的灯光下睁开双眼,流山凛皇正在脱手套,见状对他微微一笑,亲切地问候道:“你醒啦。恭喜你,手术非常成功。”
名冢琉斗顿觉不妙,前所未有的危机感从尾巴毛一路炸到天灵盖。他颤颤巍巍地感知到:怎么、竟然、【哔哔——】和【哔哔——】都没有了!!!!
他伸出手去摸,眼里却只看到两只短短的、毛茸茸的狗爪子。他急得汪汪大叫,却被面带微笑的饲主提起后颈毛,搂在怀里,捏着飞机耳说:“别担心,很快你就会适应的。”
名冢琉斗一个激灵,不禁悲从中来,小狗喷泪,胡乱蹬腿,折腾半天终于顺利地落到地面。
——然后彭的一下变成了穿着粉色公主裙的青春少女,被白马王子流山凛皇哄着关进了城堡里。
第二天一早,流山凛皇是被小狗汪汪大哭的叫声吵醒的。
“……嗯?”流山凛皇神智迅速回笼,一个鲤鱼打挺爬起来就满世界找狗,“琉斗?琉斗呢?!”
床上,肉眼可见的没有!
床底,也没有!
细听声音,来自卫生间!
“怎么了?!”流山凛皇着急忙慌地闯进卫生间一看,名冢琉斗正背对着他扒在洗手台上抹泪。
名冢琉斗耳朵动了动,转头呜汪一声喷泪,操着明显的夹子音喊道:“凛皇!!!我的【哔哔——】再起不能了!!!”
“……啊?”流山凛皇的表情中出现一丝裂痕,他试图在混乱中捋清线头,迟疑地发问,“你的声音怎么……?”怎么变夹了。
名冢琉斗悔不当初,用夹夹的声音夹夹地回答:“我就是……那个……好奇到底有什么效果所以就喝了一小口呜呜汪!然后声音就变成这样了!!我晨【哔——】的【哔哔——】也莫名其妙下去了然后我就发现它它它它立不起来了!!!!!嗷嗷我要杀了那个邪教徒!!!!”
流山凛皇的表情罕见地出现了一瞬空白,他消化了几秒,终于开口做出评价:“……这很难评。不听话乱吃陌生人东西是要受到惩罚的。”
鸡儿无小事。为了名冢琉斗的身心健康,他憋住笑容,一本正经地建议:“要我说还是去医院吧。”
名冢琉斗风风火火着装完毕,就被流山凛皇夹去了男科医院。
男科医院两侧张贴着大幅蕉氏广告,门前人来人往,都是些戴着口罩行色诡异之人,大家擦肩而过都不看正脸,生怕被别人认出。
而在医院门口,名冢琉斗抬头望着硕大鲜红的男科医院四个大字,眼含热泪,满心悲怆。
天啊!怎么会这样!这就是变性药水的威力吗!!!
名冢琉斗心里眼泪啪嗒啪嗒,泪如泉涌。他蠕动着,亦步亦趋跟在流山身后,蔫头巴脑垂着耳朵,一点也张扬不起来了。
流山凛皇拍拍他的肩膀,一掷千金挂了最贵的号,插队进去了。
男科圣手挂着慈祥的营业微笑,告诉名冢琉斗不能讳疾忌医坦白道来,名冢琉斗泪眼婆娑不敢隐瞒。
男科圣手听完,也很无语。但是秉持着服务业就要有服务业的敬业精神的理念,他还是慈祥地帮助名冢琉斗检查了萎靡不振的【哔哔——】。
“可能是激素水平的问题。”男科圣手给患者希望,“给你开点药,观察一下。”
名冢琉斗不敢说话,连连点头答应。
流山凛皇保证看着他好好吃药,早日康复。
但名冢琉斗当日的心情始终不太美妙,他憋屈得慌。他先是撸起袖子气势汹汹冲向教堂,没找到目标,又像恶犬看门一样守在门口对任何经过的人虎视眈眈,瞪圆了眼。
名冢琉斗守株待兔,待了一天啥也没有,连个黑斗篷的影子都没瞅见,膨胀成一团快要爆炸的气球小狗,气哼哼被流山牵走去公园散步消火。
到了公园没等俩人走出几步,就听见有人大喊:“救命啊!!!”
怒在心头的名冢琉斗一撸袖子,扭头一看!
一位穿着长风衣的行色匆匆的可疑男子正拉着一个不断凸起的行李箱,小跑而过。
“好哇人贩子!你跑什么!!”憋气一天的小狗终于找到了宣泄的渠道,咻的一下就冲了过去,冲刺屈膝起跳抬腿一气呵成,给了对方一记凌厉的飞踢,把人措不及防踹倒在地。
名冢琉斗还觉得不解气,插着腰一脚把正要爬起来的人摁在地上,低头没好气地审问:“拖着个人你想干嘛!你干嘛把人塞进箱子里!!”
姗姗来迟的流山凛皇收起手机,把行李箱打开,头也不回地和名冢说:“需要报警的时候叫我。”
TBC
速速水(……
男科大医院有胆你就来!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特么抽到变形药水的时候我就在想,没有哔哔不就是女孩子吗(??
六一等不及了赶时间先传了需要再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