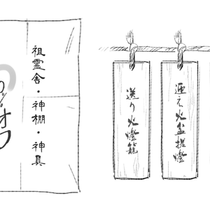横山由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她仍旧为受邀而紧张,握住剑柄的手也有些发抖,仿佛无论哪个姿势都有被打落的风险。但是,她已经在舞台上了。
……对手呢?
她四下环顾,却没见到任何人影,只好独自一人上路。似乎是为了与她的剑匹配,舞台拨给她一匹马与一副盔甲,盔甲的外壳被擦得锃亮。一个洪亮的声音在幕后传来:“我册封你为骑士!”
她用的剑也是骑士剑,这说不定是个好兆头。因为舞台回应了她的想法,让她踏上自己希望的那条道路。她会在这里站住脚,还清付学费时欠下的款项,变得和那些大小姐们一样……至少,由美是这样希望的。
她看向路旁,一个纸人正用纸板做的手臂,一下一下地敲打比它小上一圈的另一个纸人。这一幕实在有些荒谬,因为纸上不仅没有脸,连一点花纹或图样都没有,让人怀疑舞台怎么会如此粗制滥造。难道是她的想象力不够吗?
“住手!”由美驱马上前,“放了他——你为什么要打他?”
“他丢了我最好的一只羊!”纸人对她挥舞手臂,男人的声音从幕后传来,“我要扣他三个月的工钱,来弥补我的损失!”
“可你已经扣了我六个月的……”小纸人抱住了自己的头,尖细的声音明显属于孩童,“我一直在,白白地做工……”
“把工钱还给他。”由美抽出剑,指向那个大些的纸人。后者在原地蹦了两下,终于从身上撕下一张纸,递给了小纸人。见到小纸人高举着纸跳了跳,由美满意地收回剑继续前行。她又与一支通体白色的军队厮杀,打得满头是汗、浑身钝痛,但最终赢得了胜利;她还斩断了一队受迫害者的锁链,让他们免于监禁和苦役。然而,她的对手依旧没有出场,让一切都像一场独角戏,虽然过瘾,却不够尽兴。
越过一片茂密的森林后,她觉得自己见到了此行的终点。那是一名抱膝沉睡的独眼巨人,坐着时都比最高的树还高。这就是最后的对手吗?她抬眼看去,发现一名少女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居高临下地望着她。
渊上白鸟。
她知道这个名字,不如说没听过才不正常。作为樱班的班长,以及执行委员长,白鸟的名字在许多人口中出现。贵族派,侯爵小姐,对人温和有礼,格外擅长声乐。是由美此前没机会认识、之后也不打算交际的对象。
“已经可以了。”白鸟低声说,轻得好像一句叹息。
“才刚刚开始。”由美抬起头,向高处的华族举剑。
“我或许,可以明白你的想法,横山同学。”白鸟依然站在那里,落下来的眼神竟然是哀伤的,“一路到现在应该很辛苦吧,我——”
“不、不可能懂的吧。”由美的目光越过剑锋,看向白鸟腰间的胁差——这家伙甚至没有拔刀,“你站得那么高,离我太远了。”
白鸟沉默了片刻,脸上的表情竟然像是真切地被刺伤了。但这怎么可能呢。
“也是啊。”高处的少女自嘲般地摇了摇头,向空中迈出一步。华族小姐没资格说自己的生活困难。和那些庶民比,应该说,她交了天大的好运。
巨人的外壳纷纷剥落,露出其中褐色的骨架。由美眨了眨眼,意识到那是一架风车。白鸟降落在地,轻柔得像是一滴雨,没有激起任何涟漪。由美忽然听到幕后传来的哭声与笑声。在她离开后,那笔工钱又被抢了回去;她与之激战的军队只是一群绵羊,撞痛她的是羊角;受迫害者们是真正的罪犯,并不应该以那种方式得到拯救。胁差割裂穗带的声音极为轻微,几乎没有传进她的耳中。
“骑士的时代已经结束了。醒来吧,堂吉诃德。”
这就是世界结束的方式,不是一声巨响,而是一阵呜咽。






如果世界上有尴尬大赛评选的话,小泉悠悠无疑可以凭藉——富家千金落魄扮村姑,苦生计卖礼物被前任上门这一光辉事迹入围。已知悠悠是人吉的店员,人吉正面临着即将被百货大楼并购的困境,而现在上门砸场子的她前任又恰好是百货大楼的股东之一,求解她是怎么隔着大陆和大洋被找上门的?
这世界还能再离奇一点吗?
小泉悠悠绝望地想着,平静的表情下面是颤抖的心和冰冷的手。而在她对面,她的未婚夫……不,应该说是前任,正拿着她刚卖出没多久的怀表似笑非笑地看着她。他甚至还体贴地把刻有情话的那面对着她,无声地质问着当掉定情信物的某人。气氛就这样僵硬地凝滞在那边整整一分多钟,炎热的夏日没有空调的诊疗所此刻尬得悠悠手脚冰冷,而创造这尴尬气氛的始作俑者就像无知无觉一样保持着他那光彩照人的笑容。
直到国木田佐纪感觉不对出来寻人,她撩开帘子,抬头看见了一身华服的维克瑟伦·贝勒伦斯和他的黑衣保镖们,跟在他们身后看起来像是黑帮的不良分子,以及像是石雕一样凝固在那边的悠悠,不禁发出了这样的疑问。
“嗯?这里好凉快……咦?这么多人过来避暑吗?”
“Pour l’été? Non, je suis ici pour quelque chose de très important(避暑?不对,我是过来处理一件要事的)”
成功引来话事人的维克瑟伦慢条斯理地收起了怀表,然后缓步走到小泉悠悠的身边,低下头贴在她耳畔低语。他无视了她小幅后退的动作,撩起悠悠垂下的碎发,体贴地替她捋到耳后。
“Avez-vous quelque chose à expliquer?(你有什么要解释的吗?) ”
“羽川秋夕子です?”
维克瑟伦几乎算得上是咬牙切齿地念出了她的本名。
好消息还真有比那更尴尬的事情。
比如说在前任上门控诉的基础上,还被前任揭穿掉马了。
“Pensez ce que vous voulez visser.(随你怎么想吧,维瑟)”
悠悠生无可恋地回道。但即使在这种社会性死亡一般的困境当中,她也坚强地铭记着自己作为店员的骄傲,所以她很快就想把诊疗所拉出这个小少爷迁怒的范围。
“ Bref, laissez vos hommes revenir en premier.(总之先让你的人回去)Ils sont innocents(她们是无辜的)”
维克瑟伦脸上的笑容逐渐消失,他甩出一张空白的支票,抓起悠悠的手腕就往外走。在经过国木田佐纪身边的时候,他漂亮的眼睛扫过了这个优雅的女人,然后用他最礼貌的口吻说道。
“Je remboursais tout ce qui était dans la boutique à mon prix et, en échange, je prenais mon homme avec moi.(所有的东西我都照价赔偿,作为交换我的人,我就带走了)”
国木田佐纪表示其实也没有多礼貌,但是能听得出来他抓着的悠悠非常不情愿。
“Attendez, vikselen, dites-les de s’arrêter!(等等,维克瑟伦,叫他们停下!)”
维克话音刚落,身后的黑帮成员就像是接到了什么指令一样拿起东西打算开砸。他们比不上训练有素的保镖,其中一个看起来十分稚嫩的年轻小伙子还一边砸还一边碎碎念。
“可别怪我啊,我也是受人指使的,你们得罪了人不关我的事啊,冤有头债有主!”
时间倒回这场奇妙的对峙开始之前,留学的小泉悠悠接到家里的消息回国,结果发现家里的产业突然破产清算暴雷,她和家人失去联络又因为好心救助他人而被骗走了路费。于是失去大小姐身份和财富的她变成了一条没有生活自理能力的咸鱼,不得不可怜地流落街头。幸好在被人骗去窑子里面之前,她被善良的国木田佐纪收留,不仅填饱了她的肚子,开导她不要寻死,还教导她如何利用自己的学识去自力更生。感受到这份温柔的她感受到了自己过去的不成熟和幼稚,决定借此机会抛弃掉过去只知道享受他人成果的自己,做个能够用自己双手生存的人。所以她为了回报佐纪,用假名小泉悠悠呆在了诊疗所当店员。为了给店庆祝五周年纪念日,身无分文还不会攒钱的她在前不久当掉了原本打算送给自己前未婚夫的生日礼物,想请大家吃饭。然而就是这么好巧不巧,原本以为再也不会相见的人拿着被当掉的东西又出现在了她的面前,还成为了要逼迫人吉倒闭的黑恶势力之一。
对于这个故事,大孙子发表了重要的讲话。
“这里是小说吗?”
他那一道特别响亮的声音过了混乱,敲进了所有人的脑海中。不知道从什么时候钻出来看戏的大孙子发出了这样一声惊为天人的感叹。无论是来砸店的,正准备阻止砸店的,还是拉拉扯扯的那一对,都不由自主的停下了看向这个家伙。打破气氛的罪魁祸首无所谓地扭过头嘀咕道。
“我还以为京都不流行这个呢……哦,这段话对气势毫无帮助,声音应该再大点……”
“这!里!是!小!说!吗!”
“潮得我都快风湿了!”
“你别看不起人啊,咱们是过来砸店的!”
一个吃瓜许久气性很大的黑帮成员怒吼道。
“原来是过来砸店啊 我还以为演电影呢……”
大孙子恍然大悟地说道,然后非常好心地给予了一个建议。
“你们真要砸*那个女人*的诊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