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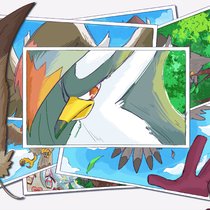


第二天一早,陆淮是被揪住耳朵痛醒的。
“好啊你这死丫头,有胆子弄丢自己一只眼睛怎么没胆子回来见我们呢,汉考克这死小子也是,好手好脚带出去的人,就这么送回来了!”瑶姐姐的嗓门一如既往地响亮,陆淮看着汉考克在边上赔笑的样子,差点没忍住笑出声。
“死丫头你还有脸笑,仔细你的皮!” 瑶姐姐嘴上不饶人,手指却心疼地轻点了几下陆淮的脑门。“受了这么重的伤还这样子睡在外头,赶紧滚到床上去!”
陆淮下意识抬手按了按左眼松垮的绷带,又慢吞吞地顺着瑶姐姐的力道从地上坐起来,“我这不是回来了吗……还是舍不得姐姐酿的梅子酒啊。”
“呸,少来。” 瑶姐姐嘴角一撇,“全身上下也就你那张嘴最讨喜。”她眼圈红了红,扭头冲汉考克喊,“呆站着干什么,给我们阿淮眼睛都骗走了,还不去给她弄点吃的!”
“哎——哎好好好,您别急哈,我这就吩咐厨房……”汉考克连连点头,逃命似的消失在楼梯转角。
瑶姐姐拉着陆淮往屋里走,嘴里念个不停:“就出去几天,瘦了这么一大圈!命硬也不是这么拼的……医师有没有说需要注意什么?我等会儿去小金街裁点软布,给你做个眼罩,你要绣什么花样的?”
“嘿嘿,我就知道姐姐对我最好了,我要银线绣的蛇!”
瑶姐姐翻了个白眼,“真是蹬鼻子上脸了,还要银线绣,几个眼罩都不够偷的。你且等着吧,晚上我给你送过来。” 她的声音像针线,微微缝合乐陆淮心里某个破口。
没一会儿,楼梯口响起一阵脚步声。光端着个托盘上楼,热气腾腾的饭菜香味一路跟着他窜进屋里。
“啊,是你啊。”陆淮一见他,嘴角一咧,“我就知道汉考克那家伙会拜托你来送饭。”
“他给我报酬了。” 光冲两位姑娘点点头算作招呼,把托盘放到桌上。
“嘿,看来我俩确实是一路人,赚钱嘛,不磕碜。”陆淮端起碗闻了闻,眼睛都亮了,“生滚鱼片粥!这儿的厨子可没这手艺……你还会做饭?”
“你不会?”光难得反问了一句。
陆淮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往嘴里舀了一勺粥,含糊地发出被烫到和好吃夹杂的声音,倒是一边的阿瑶有模有样地模仿着陆淮的语气,“学做饭干什么,煮熟能吃就行了,一个菜要洗八个碗,麻烦死了!”
陆淮不语,只是一味地吸溜粥。等到碗底见了光,陆淮麻利地收拾好碗筷,阿瑶看出光和陆淮有事要说,先行告辞了,临走前她嘱咐陆淮:“我知道你这倔丫头闲不住,我也就不劝你了,但求你偶尔想想我们还等着你回来,行不?”
陆淮低声应着,抱了抱阿瑶:“知道啦,姐姐。”





作者:林树
评论:随意
本文为世界计划东云姐弟骨成年if同人
东云彰人在过去二十年的人生里一共坐过两次跳楼机。
高中毕业那年,他和队友们一起去了凤凰乐园庆祝。毕竟某位几乎每周一游的乐园头号粉丝为了备考,已经忍耐了不少天。白石杏和青柳冬弥都轻快地答应了提案,可他们的队长是个一旦做起来就勇气惊人的家伙,他总觉得这样特别的庆祝不会简单结束。果然,应了他的猜测,小豆泽心羽表示自己想要挑战新装修的刺激项目。
于是他们来到了一座高大的跳楼机装置前。
彰人曾被说过像是“看起来就很精通各种休闲娱乐活动的大师”,实际上却连只需要抬起一块屏幕的电子游戏都不算常打。他知道自己太专注于目标和理想,尽管如此还是会有意识地告诉自己没时间浪费,乐园这种地方如果没人邀请也许这辈子都不会主动去。因此要说他一点都不担心也是假的。
他叹了口气,刚好被某位聒噪的家伙捕捉到。多亏了杏在旁边不断对他使用激将法,吵吵嚷嚷也足够转移他们两个人的注意力了。冬弥在一旁念着只是垂直下降就没有被甩飞出装置的恐慌,其它装置除了失重,还会有超重和离心力等等的影响,自己应该学习大家挑战自我之类的话。然而忍不住腿软发抖的他最终还是被自己和杏联手按回了一旁的长椅上。
——害怕的感觉啊,真是久违了。
该说是巧合吗?以前国中的时候,他曾经和家人来过——妈妈带着绘名和他,老爸还有自己的事要忙。当然那时候还没有这个新造的露天装置。城堡藏起了惊恐的尖叫,本就难懂的片假名扭成了花体,装点在高大华丽的外壳上极具迷惑性,主题场景观光的表面活动吸引了不少人前来排队。
因为造型精美,绘名几乎在看到城堡的瞬间就说要来这里。他们一边顺着螺旋梯子上楼,一边看着周围五彩斑斓的景象,还时不时讨论着“这个好像你”,顺水推舟地来到一个带着栏杆的昏暗小房间。屏幕上播放的影片里吉祥物依旧蹦蹦跳跳,但坐下来摸到安全装置的那一刻,一股寒意瞬间穿过脊骨,让他忍不住用力抓紧了安全杠。
是啊,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毕竟还是个小鬼。他听见妈妈在旁边对绘名说害怕的话就握住她的手,却意外对上了绘名转回头时的视线。他心虚地撇开了眼睛。
“啊,彰人要是怕了也可以抓着我哦?”
“谁要怕这种东西。”
“一会要是发抖了绝对会好好嘲笑你的。”
“我看发抖的人是你才对吧。”
明显是挑衅的话语,他用强撑着的被吓宕机的脑子这么想,没有注意到绘名颤抖的尾音。不管在街头还是在家里,这个那个全都对他如此狂妄,他当然要证明自己不是幼稚的家伙,也不会为了这种东西害怕。
毫无疑问他失败了。他低估了跳楼机的威力,看来哪怕是跳楼机也并非光有觉悟就能解决的。尤其是当它爬升到城堡顶部开着的窗口时,他在一瞬间窥见了俯瞰乐园、甚至俯瞰城市一角的顶端的景色,却在眨眼间又快速坠入被高强囚禁的黑暗。全身的血液好像都在那一瞬间涌入大脑,细小繁密的血管胀得就要崩开;内脏也悬在躯干里揪得发疼,僵直了的身体内心有块像果核一样的地方,触电一般麻。
还不如没有那扇窗口的好。
他的潜意识里冒出这个想法,又被自己吓了一跳。突然一只手紧紧地抓住了他,微微出汗的掌心贴着他粘得死死的,蛮横得让他手足无措。
这家伙,肯定已经怕得不行了吧?他握住了绘名的手。绘名的尖叫声混沌地回响在脑海,他现在只觉得自己由内而外地、完全宕机了。所有的感受里只剩下自己与那只手相连着,像一针麻醉剂,让他暂时抛却了从顶端高速下坠的悲伤。触电的范围随着药效迅速扩展,一阵酥麻从内脏直冲天灵盖。
人生中第一次坐跳楼机,彰人就那样一直看似冷静地过完了全程。
莫非,其实还有点享受……不,实际上只是人触了电就会变得动弹不得吧?直到灯光亮起,绘名拨了拨乱掉的碎发,尴尬地松手移开,他才反应过来:也许绘名是把他和妈妈的方向搞错了。
双脚突然悬空,装置的启动终于让他回过神来。现在的他看来,当时的城堡也没有多高,至少比这个全敞开的新装置低上不少——升上顶端向下看时,他是这么想的。他早已见过比那天的景色更壮观的画面,下落时也不再有被困在高墙里的无力与悲伤。
他成长了,他能独自撑过失重瞬间血液和内脏出于惯性的上浮,独自承受席卷而来的恶心、麻痹的感觉,还有队友们的声音在身边逐渐由喊叫变为欢呼。然而他没法像她们一样抛下一切享受起来,全因他早已先入为主地体验过那一番掀翻天灵盖的酥麻,连通着那个人和自己一样的血。
怎么回事呢,明明已经成长了,却还是觉得少了什么。不再害怕本该是好事,他却为缺失的某股情感莫名地惊慌起来。
东云绘名躺在浴缸里,回忆着那时候的事。水温正好,入浴剂也是常用的款式,湿暖的空间内亲切的液体包裹着她的皮肤,就像泡在羊水里,一切都朝着最初的生命回归。
“喂,别在这里就睡着啊。”
一双手扶住了她的脸。绘名顺势靠在上面,慢慢睁开眼,看到浑身都是泡沫的弟弟坐在浴缸的旁边,头发正洗到一半。两年前第一次看见这副景象时她曾一下子惊醒过来。
“有什么关系。浴缸就是用来消除疲惫的嘛。”
“是,是。你刚刚都快把脸埋进水里了,想要永久消除疲惫吗?”
“不知道是谁害的,真的很累啊?”
“所以说很不爽你那种说法。早就说过今天不会简单结束了,知道这点还要自己贴上来的不是你吗?”
两个人都沉默了。事到如今他们还是没有习惯这样的关系,隐秘、扭曲,靠近又拉远,就像坐上跳楼机,让人心有余悸。
彰人这小子毕业的那年和组合里的伙伴去了吧,好像玩得挺开心的样子。我们有多久没有,纯粹地为了玩,一起出去玩过了呢?像是没有借口就不行一样。绘名重新缩回浴缸里,给弟弟留了半边的位置,想让他充分地瘫在里面,却被他贴了过来。
“那边,给你留了位置。”
“不要动。”
这家伙颇有“你睡完了轮到我睡”的气势,就这样埋进她的怀里。
“真是的,这样我会更想睡啊……都睡着了要怎么办。”
她用毛巾搓了搓弟弟湿漉漉的头发。彰人这家伙,只是这种的时候的话还是挺可爱的。
挺可爱的吗?
他不知道姐姐那时握住自己的手并非情急之下认错了方向,也并非下意识的本能。真正的答案就藏在绘名回头那一瞬间,对弟弟神态敏锐的捕捉里。要说她不害怕是完全不可能,可她更想妈妈和彰人都有心去享受这次玩乐,临阵脱逃也太逊了,自己要做被刮目相看的那个,谁也不依赖——如果没有注意到彰人别开的视线。话到嘴边又变成了挑衅般的言语,她的紧张一点也不比谁少。
原本只是半出于担心半出于害怕地握住彰人的手,想要拿出姐姐的帅气,可刚窥见那层开阔风景就突然间极速下坠的不甘打了她个措手不及。明明一寸一寸爬上来的时候费了那么大的力气,连机器运转的声音都听得清清楚楚,凭什么非要被打回底端不可?一想到这些她就不禁觉得烦躁,手上也加大了力度。
然而彰人居然回握住了她,没有挣脱开,也没有自暴自弃地放着她的行径不管。
不会吧,难道真的难受到了这种程度?
当然有余裕来思考这些已经是后话了。她只是在那一瞬间平静了下来,所有的不甘和悔恨都被排山倒海而来的、雷击般麻痹的失重感冲刷干净。尽管距离被称为快感还有很长一段距离,她却发现自己并不讨厌这种感觉。这时候的一切都变得如此纯粹,剥开一层又一层的外物,无限接近自由落体的自己,几乎断绝了与世界所有的联系,除了那只紧紧牵着的手。
唉。没法不在意啊,毕竟留着同样的血,就算分作了两个人也会因为惯性仍然合在一起,久而久之连血肉也与对方镶嵌着不断成长,已经无法想象没有对方的生活了。只因相比他人多了这一点的惯性,他们的关系也被搅得扑朔迷离。
如果谁也没有注意到那份感情就好了,干脆一开始就没有产生最好了。察觉到了之后又该怎么面对?不过是互相把这份心意掩埋在酸涩的隐痛中,期待着永远不要被发现,又期待着有朝一日掀翻一切的契机能够爆发。
一条血脉联系起的两股生命,本应如此向无始无终的前后延伸,却因这份悄生的意识与自我对立,于是原本清明而稳固的关系也变为阶段性、有死性的。
被意识到的罪才得以成为罪。
“你说,我们现在算是什么关系?”
第一次做完那天绘名也像那样累得睡着了。彰人懊恼自己有些孩童般的冲动,明明已经思考好要表现得更成熟。
昨晚又通宵画画了吧。理智从惯性手里重新夺回掌控权,他看着绘名闭上眼睛后更加明显的黑眼圈,一点一点收拾着残局,如同失重般的官能体验一点一点被心惊胆战的后怕侵蚀,谁都清楚这样的事情会有什么后果。他把绘名放下,有些恍惚地逃进浴室,他们居然真的走到了这一步。
自己无所谓吧,倒是绘名那样的性格,之后又会如何呢。他想着想着,突然发现自己流泪了,混合着淋浴的水一起流淌在地上。
“你说,我们现在算是什么关系?”
“……已经,不是单纯的姐弟了吧。”
“嗯,说得也是。”
你的姐姐怎么可能会没注意到你红红的眼角。你所有的悔恨、后怕和不甘,她怎么会没有。她是年长者,是个傲娇又倔强的人,同时也是你的共犯,是首先要承担这份责任的人。
漫长的水声和窗外的大雨一样煎熬,等着弟弟从那里面出来也变得焦躁无比。东云绘名把每一滴即将夺眶而出的泪水吞进了心里,只是用那样平淡的语气开口,问着不算问题的问题。真不像她的风格,连她自己都要这么感叹了,可她不是向来如此吗?适时沉默,适时关心,一直一直看着同一个人,看着他的成长,他的悔恨与不甘,还有他熊熊燃烧着的觉悟。
“不那么单纯的姐弟,也可以做吧?”
事到如今可别露出一副全怪自己做错的表情啊,就算有错也应该先惩罚身为姐姐的我才对。如果对自己的姐姐也露出那样的觉悟,可是无论如何都逃不掉的。万一,万一一切都结束了,你也应该回到正常的生活中,不要继续做一个像我一样的人。
会这样想的自己果然是个傻子,明明已经知道不可能了,但哪怕是无数根针也希望自己可以多挡两分钟再走。哈哈,正是这样刺痛地把恐惧的泪吞进去的啊。
窗外的雨一直下了很久。睡过一次的绘名反而没了睡意,况且正是她生物钟里醒来的时间点。彰人躺在旁边,眼眶擦得红红的,手也缩进长长的袖子里。她把睡着的弟弟抱在怀里,看着他的表情一点点放松下来,自己也一点点合上眼睛,像他们小时候那样。
至今以来他们几乎携手走过了彼此全部的人生,哪怕时有摩擦也在缓慢而平稳地向上攀爬着,就算在各自的世界里不断下坠,握紧的那双手也从未松开。他们本来能平稳地,或是互相挣扎着地到达顶端的。如果爱上一个人是一种最终想与其成为家人的感情,那么从出生开始就是家人的人该怎么办呢?
强烈的引力拉扯他们回到现实,面对那份由于分不开的本能吸引而异常诞生的感情。也许是从某个雨天开始,他们拥抱、接吻,甚至做了无论如何都不能再被亲情饶恕的事。他们都心知肚明,爬上去时很艰难,下坠却意外地容易。想要重回正轨几乎不再可能,每次他们要划清界限,要像克服自己的平庸之才那样托着二人的关系再度上升,总会在刚能透过光亮时就重蹈覆辙。
在意志与引力的对抗赛里,对于梦想,他们是赌上了人生要向上的;对于二人的关系,他们却无法控制对下坠中的失重世界心驰神往。全身的血液集中于某一处的感觉,直冲天灵盖的触电酥麻的感觉,感官受到的危险的刺激支配全身,经历过一次这样禁忌的失重体验就再也无法回到从前了。
实在太舒服、太舒服,就连负罪感也变得可爱,好像在嘴里咬开了一颗多汁的柠檬,酸涩的味道溢满了全身。
他们无法成为世人眼中正当的伴侣,可那又有什么关系呢?血浓于水的羁绊并不输给任何人,他们不需要再一点一点地磨合生活,不需要再结为家人组建家庭,生来就是一心同体的。
一如往常的生活,一如往常的拌嘴,只是在昏暗隐秘的角落里,短暂沉浸于高速下坠的失重中,这样就足够了,一份滋味就足以被保存起来一点一点回味很久。
一份甘美的危险,让人心有余悸的滋味。
将来的某一天也许他们会被对抗现实的无奈所淹没,但只要还能去往失重的世界,抛开常规的一切,他们总能找到一条自己的生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