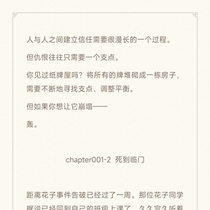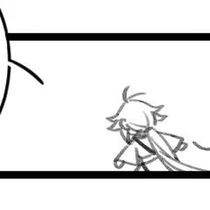仍然是极限赶工,极限胡言乱语,在公司摸鱼有种古怪的背德感(在说什么
只是略微提到的友友们就不关联打扰了!有任何问题随时抓我修改。
总字数5181
————————————————
“感觉如何,还能适应吗?”
“光线没问题?录摄角度OK,画面清晰……好,那我就开始下一步了哦。”
“别急,别急啊青柳老师,我毕竟不是这方面的专业人士,万一有差池,害老师少了一个腰子什么的,呃,虽然问题也不是很大,但还是不太好吧。”
“好了。已经顺利切割开了。嗯,青柳老师的脂肪层看起来很健康。”
“现在……”
“在不致使器官脱离的前提下,我会缓慢移动你的脏器。”
这间实验室现在看起来完全就是一间实验室。
纯白的,符合人们印象的,还有躺在床上被宰割的试验品,以及穿着白大褂像切牛排一样切割活人的科学家。
躺在实验床上,面前撑着手机支架,通过手机上的实时直播观看自己被“开膛破肚”的青柳佳直眨了眨眼,一些无意义的废话文学与猎奇影片镜头在这颗精明的脑袋中交织闪现,光怪陆离,试图干扰他的思维。
这间实验室现在看起来完全就是一间实验室。
这间实验室没有窗。本来就没有。现在伊织都不仅把门锁上了,还用一架金属架子堵在门前,断绝一切可能干扰实验进程的要素。
原本室内的布局被重新构建,此时无用的桌椅和仪器被推挪到墙角。伊织都把她从临床学科那里捞来的可移动病床放在房间正中央,请青柳佳直躺在上面,还贴心地铺了一张小熊毛毯,以确保床板不会太硬使人不适。
两盏不知道原本被用在哪里的聚光灯此时打在青柳的正上方,过于亮的灯光晃得人眼睛疼痛,让青柳产生了自己就快要流泪的错觉。他想,他可以为自己保证,自己现在流出的泪水完全是生理性的,是这两盏讨厌的灯害的,不包含一丝一毫被胸腹处细微残留的痛觉刺激的可能性。
但他的躯体还会因刺激而流泪吗?
活死人的躯体已经变成一滩死肉,难道说他的角膜或虹膜依然活着,还坚持不懈地展示自己的脆弱,想要以此来表明些什么?
“伊织。帮个忙,来看一眼。”
青柳佳直稍微仰了一下头,声音听起来甚至有些困倦,他询问正小心翼翼摆弄自己脏器的同事,“我流泪了吗?”
伊织都便探头看了一眼,然后肯定地回复:“你没有。”
“对于人体而言,眼泪是没有意义的副产品。”
“达尔文。”
她的同事兴致不太高地回答。
人体不需要眼泪。
活死人没有流泪。
青柳佳直暂时让双眼离开了手机屏幕,短暂地闭目休息。
他的大脑被麻醉药侵扰了,他需要与麻醉的效用做抗争。
但是他的问题显然让正忙碌的伊织都颇感兴趣,她停了下来,开始思考这个问题。
“你认为神经性的疼痛会刺激活死人的泪腺分泌泪液?”
女性研究员偏头思索,两手的手套上都沾着暗色的体液,活死人没有鲜血可流,身体内沉积着日渐一日浓郁粘稠的死血,伊织都对该场面的可怖没有正确认知,她开始滔滔不绝。
“或者是因为眼部的角膜或虹膜受创?但实际上青柳老师并没有流泪,那或许是大脑对现在的场景有了预判,脑部调出了从前的回忆,让你有了这样的错觉……”
她忽然顿住,像是有些兴奋,又像是遭遇挑战一样,皱起了脸。
“但是实际上……”
伊织都慢吞吞地说,“活死人真的不会流泪吗?”
*
伊织都得不出这一问题的答案。
她本人极少哭泣,不论生前死后,都少有相关经验。
生前,在其他孩童因种种缘故嘤嘤哭泣时,伊织都只能站在一旁,做一个静默的旁观者。至于死后……
“需要我给你一棒子?”
细川亘看着被递到手上的一截钢管,面色平静地回望面前向自己提出此等需求的职员,“伊织小姐,在此之前,我想先确认一下这截钢管的出处。”
总不至于是你从研究所什么地方现场拆下来的吧?
伊织都察言观色,从领导无波澜的面容之下嗅出了这样的质疑。但这对于她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以回答的问题,因为——
“这是岩叶先生借给我的。”为了安细川亘的心,她还特别贴心地补充道,“请放心吧,这是岩叶先生的私人物品,没有使用所里的经费。”
“哈哈,那不愧是报销又得算到我头上了吧。”
私人物品是一根钢管,并且会被携带进入办公场所,还出借给同事……
细川亘沉默了一小会,然后无言地摘下眼镜,抬手捏住鼻梁轻轻按压。很难说作为上司,他究竟有没有因下属的贴心补充而更加放心,只是此刻难以言说的疲劳是如此真实。
“……我明白了。”
他将眼镜重新架回鼻梁,再度平静地开口,“那么,让岩叶先生来做这件事不是更妥当吗,你找到我,与需要我“敲击”的理由是?想知道活死人在足够大的刺激下是否会反射性流眼泪?”
伊织都小幅度但快速地连连点头。
“很精准的概括,修改一下可以作为论文的题头了。”她颇为中意地露出喜色,“岩叶先生正好有其他事情要忙,如果所长也抽不出空的话,那我就再去问问其他人……其实我已经尝试过支起眼皮使眼部干涩和强光直射,效果都不怎么好。”
在这种放在活人身上可称拷问的尝试之中,伊织都确认自己还是无法流出半滴眼泪。
“既然常规性的和反射性都无法取得预想的效果,最后我想再试一下精神性刺激是否能导致泪液分泌。”
置身约莫十平米的房间内,伊织都真诚地陈述她在常人听来离谱怪异的需求。这是一间偏僻阴冷的边角房间,位于研究所长走廊的角落,门上没有挂上门牌,平常鲜少有人涉足。
但这里的用途在所内并不是什么秘密。
房间内活着的人类只有一人,大大小小的玻璃展示柜占满整个房间,长达2-3米的小型鳄鱼一动不动的趴卧着,每一只玻璃柜上都贴着实验室通用的白色标签,标签上打印着一排数字,所有数字散乱而无规则,缺失的编号令伊织都浮想联翩。
房间顶部打着观赏用的灯光,从上而下的橘黄色暖光没法让活死人的皮肤沾上任何暖意。伊织都对着玻璃柜内的变温动物眨眼,巨大的蜥蜴抬着眼皮,一动不动。
“你对它们感兴趣吗?”
现场唯一的活人无声地来到伊织都身后,语气中听不出太多情绪。他好似也把自己视作一块平平无奇能够行走的肉块,散发不出任何热意,反而令伊织都伸手搓了搓手臂上的皮肤。
“当然。”伊织都假作若无其事地转开视线,像是个上课走神被抓包的学生,“对所有事物保持好奇心是我的职业素养。”
见上司赞赏似的点了点头,伊织都忍不住又回头看了一眼那条一动不动的鳄鱼。
鳄鱼忽然抬起外侧的眼皮,内部的白色孔膜仍覆盖在眼球上,那双白蒙蒙的眼珠正对上伊织都带有探究的视线。
女性研究员心头一跳,连忙将话题转回“正轨”。
“我自己动手的话,生物本能——不知道还剩多少——可能会对我的行动造成阻碍。”
伊织都双手合十,从合拢的手掌上方偷瞄细川的脸色。
“所以,以防万一,所长——”
“能帮我这个忙吗?”
*
从结论来说,痛觉导致的精神性刺激仍然没能让伊织都得偿所愿。
不过,她倒也不能说是一无所获。
“你是指,收获了一条断臂吗?”
细川亘意有所指,手下略一用力,将伊织都手臂的骨节扳正,活死人的骨头发出了清晰响亮的咔嚓声。
伊织都再一次意识到自己并不会因为疼痛而流泪,但活死人的痛觉究竟被什么控制仍然是个谜题,她走神开始思考,嘴上飞快的回答:
“至少从我个人这个样本来看,身体上的疼痛并没有传达给我的大脑,或者说,传达得很有限,并没有引起精神性的泪腺分泌。”
“但是,这只是你的个人样本。”
细川垂下双眼,不紧不慢地回答,“据我所知,有相当一大部分活死人在这方面没有异常反馈。”
“那就更奇怪了。”伊织都立刻接口,已经顾不上自己的手臂仍在他人的掌控之下,“理论上说,我们的肉体已经经历过一次死亡,生体机能一度完全停止。活死人不需要呼吸,不需要进食,生物存活需要的基本行为对我们来说都不再必要。”
女性研究员的表情古怪,在笑脸之上,她的一边眉毛高挑着,另一只眼却微微眯起,两边面颊不协调的肌肉调度让她的笑容在橘色暖光下变得有些诡秘。
“肉体已经死去了,理应是这样的。可是,许多人却还能哭能笑,我们的泪腺为何还在工作?甚至于……为什么我还仍有痛觉?并非单一样本的个例,而是活死人共通的表现——活死人仍残留痛觉。”
“为什么?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大脑变成了我们唯一的死穴,只有脑部还“活着”,或许连带着神经也仍然存活?”
“痛觉。”
伊织都长长地喘了一口气,语气越发莫测,“受伤害时引起的肉体上的痛觉,是感受器接收刺激作祟,是神经元传输给脊髓与大脑的信号。”
“我想,我们这些活死人的大脑与脊髓或许仍然以某种方式“活着”。我相信这或许是某种病变,曾经肆虐的“某种毒株”未被我们击败或消灭,反而留存在人类体内,与我们共存,改变我们的形态,以至于死人复生……”
“如果能够证实其活动方式,如果能证实其中原理——”
“证实这些,伊织小姐,你想如何?”
细川亘忽然开口打断研究员的慷慨陈词,像是水闸忽然被拧紧了闸口,最后一滴未来得及止住的水滴啪嗒落下,砸碎室内的空气。
他没有抬头,伊织都却隐约感到有什么东西在暗处盯紧了自己。
“——”
这让她猛然闭上嘴巴,接下来险些忍不住从喉管里涌出的危险发言被阻断在口腔内,咀嚼磨碎后又咽下,不再露出半点声响。
伊织都的眉角小小地跳动,她的表情被一点点地,调节回到了正常的笑容频道上。
“啊呀,啊呀。”
活死人慢吞吞地收回自己已经被简单固定好的手臂,再次合拢双手,做出作揖讨饶的姿势,“只是好奇,好奇而已。绝对没有要违反规定私下研究哦,完全没有这个意思。”
“而且你看啊,所长,如果能够搞清楚神经元活性的问题,或许大脑移植就不再是梦想了呢?”
伊织都视线瞟向一旁玻璃柜里的鳄鱼,五分真心,五分虚情地感叹,“如果在人类身上可行,那么其他物种自然也有成功的概率,生命的形式将不再重要。”
“说不定换一换大脑,我也可以体验一下做鳄鱼的感觉呢?”
细川不置可否。他只是缓慢地推了一下眼镜,遮去了面上可能展露情绪的所有细节。
“很好的设想。”
他说,“那就以这个为课题,写一篇论文给我吧。不可以动这边的材料,经费会另外给你批下来的。”
*
如果将人类的大脑换入狗的躯体。
……人类会成为一条有思想的狗吗?
伊织都暗自认为,这种疯狂科学家才会探究的问题,似乎不是很应该成为她的开篇课题。
不过,虽然只是一时急需转移上司,才在当场紧急抛出的议题,倒也不能说完全不令人在意:
如果人类最终被证明能够只依靠脑(或者连带一部分脊髓)存活,并有办法保持脑部永不衰竭,那么,未来人类的生命形式将会被如何重新定义,就将成为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论题。
这样的人类是否还需要繁衍?
她的专业遗传学是否会成为废纸学科?
与其看活生生的亲人友人在身侧一天天老去,最终步入死亡,是否会有人选择先一步动手,令不愿失去的人转变为与自己相同的形态?
伊织都无从而知。
但她清楚地知道一点——
“如果受害者都有概率活过来的话……那杀人犯这一行是越来越不好做了呀。”
远处的电视新闻正反复播放着偶像演唱会上惨死的新闻,画面模糊不清,应该是后期特殊处理的结果,即便如此,画面上仍旧红白一片,背景中的骚乱与惊慌足以让观看者还原其本应展现出的惨状。
“真惨啊。”
旁观者发出浅薄的惊叹,夹有一丝惋惜,更多则是猎奇式的情绪。伊织都远远地看着那块巨大的电子屏幕,上面又开始重头播放演唱会开始的一幕,放大的偶像的面部特写,她分不清是哥哥还是弟弟的那一个惊恐地张大双眼,随即屏幕被染红,一切开始模糊,被拉远的镜头中人体从高空坠落。砰!一切都搞砸了。
这可是明明白白的恶性事件啊。有人在暗中注视着活死人们,瞄准我们的脑袋。只要扣下扳机,就一下,杀掉活死人确实比杀掉活人要难一些,但难得不多。
在没有多少行人的中央公园内,拎着一大筐“实验素材”的伊织都若有所思地停下脚步。
隐约有某种声响……熟悉的,隐秘的,让人联想的某种声音传入耳畔。
“好像是抓挠……被装在盒子里的实验鼠有的时候会挠出这种声音。”
女性研究员忍不住小声自言自语,目光扫过周身。
中央公园大而空旷,三两借道的行人都步履匆匆,不远处有人似是刚刚出行归来,长风衣紧紧裹在身上,风尘仆仆,走路带起尘土。
伊织都看着男子走近,猜测对方的行李箱一定重得出人意料,因为那只黑色的箱子就连在平整的地面上被拖行,也发出响亮的轰鸣,噪音在经过伊织都时更加震耳,遮蔽了之前能够听到的某些细小声响。
“……”
伊织都忽然意识到,有什么不太对劲。
那只行李箱……
那只行李箱内?
“……是我听错了吗?”
原本仰头瘫坐在一旁长椅上的男性也猛然做起,扭头看向拖着行李箱的男人离开的方向,“我好像听到了什么声音……这是在开什么愚人节玩笑吗?”
伊织都看向对方。男人染着跳脱张扬的头发,佩戴大大小小的饰品,气质中却透出清澈的纯然。他像是完全被周围的情况弄迷糊了,慌张地从椅子上爬了起来。
“应、应该是朋友之间在开玩笑吧?”男人不怎么自信,但又非常努力地想要说服自己,“总不会是……”
“如果不是玩笑,那就是性质非常恶劣的刑事事件了。”
伊织都打断了对方的话。
她活动了一下曾遭敲击的手臂,把手上提着的铁笼放在脚边,然后双手拉住男人的手臂,郑重交代:
“人命关天,你先报警!”
“那你呢?”
被她紧紧抓住的加西亚·范忍不住问。
“我先追上去!”
“可是你、万一追上去遇到危险怎么办?!”
伊织都动作一顿。
“……别担心,我是活死人。”
她拍拍对方的胳膊,自然地笑起来。
人命关天?
伊织都忽然想到,这里存在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
如果在呼救的并非活人,而是活死人。如果打开箱子,就会看到人类的肢体零散分离,头被砍下,身躯扭曲地被塞在行李箱里——
这样的情况,还能算是人命关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