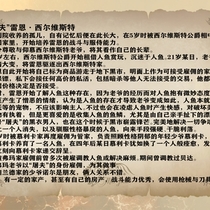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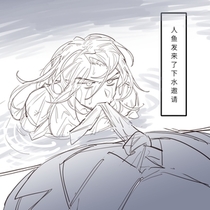





第一封信
*这是一封字体华丽的信,信纸来自香榭丽舍大街最有名的路易斯书店,中间夹杂着细碎的金屑,是最贵的那一种。
致——很久不见的雷:
嘿,我最亲爱的好哥们,自从你去新大陆游学以后咱们已经快一年没见面了。虽然中间也收到了你寄来的几张明信片和两封信,但我仍然更希望与你本人当面畅谈。
在新大陆过新年的感受如何?希望你喜欢我寄的圣诞礼物,这是曲奇帮忙一起挑选的,他说他也想念你,真的。
再过三个月左右人鱼节就要开始了,作为一个成熟、可靠的绅士,今年我收到了人鱼节的邀请函,除了我自己,还可以额外带一个人进去。没错,我可以带你一起去逛人鱼协会,在人鱼协会的长廊中漫步,看着身边有数不清的人鱼游来游去,这是多么有趣的一件事!
所以,你会到人鱼之都来跟我一起见证这令人激动的画面对吧?
以及,瓦伦丁日快乐!
回见。
艾克兰
1905年2月14日
第二封信
*也是质地很好的信纸,同样是整齐的花体字,但绝对不会让人觉得浮夸。
亲爱的艾里:
你的信已经收到,我当然不会错过这件盛事,毕竟我们已经因为上学与这个节日擦肩而过很多次了。
你送的围巾很漂亮,我很喜欢,下次不要送了,那是女式的(你故意的对吧)。
新大陆是一个令人着迷的地方,粗野但充满活力。顺便一提,我上个月在大陆中部的辛辛那提动物园见到了濒临灭绝的旅鸽,她们真是群可爱的鸟儿,不应该这样轻易的灭绝,太令人悲伤了。我有很多见闻想分享给你们,也许等回国以后,我可以写一本书。
在离开前,我还有一些事情需要处理,但我一定会在人鱼节开幕之前赶到人鱼之都的,到时候再见。
向你的家人问好,也向曲奇问好。
保持健康。
你的雷蒙德
1905年3月17日
第三封信
*这是一封电报。
我已经到达人鱼之都,住在城西的亚特兰蒂斯酒店,比预计的提前了一些。我准备在这座城市多待几天。问好。
雷蒙德•温特
1905年5月9日
第四封信
*又是熟悉的浮夸花体字和洒金信纸。
亲爱的雷:
我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告诉你。鉴于写小说都是先抑后扬的,我就首先直白地告诉你坏消息吧:人鱼节我不能来了,不仅如此,我原本打算愉快地当纨绔子弟的计划也要泡汤了——我要去皇家海军当一个微不足道的渺小士兵去了,我很难用单词来准确描述内心的悲怆,唯愿亲如兄弟的你能通过灵魂的共振与我通感。在你接到信的时候,我大概已经被我父亲亲自押送到了军营里。我抗争过,但是失败了,因为我的父亲让我在入伍和早日订婚之间二选一,而面对这种选择题,我很难不选择前者。
基于已经说完坏消息的基础上,我将为你,我亲爱的好兄弟补充一条可以让你高兴一点的好消息。虽然我无法亲自前来,但我还是想办法从别人那里搞到了一张很不错的鉴赏会请柬给你。虽然上面的姓名不太对头,但是人鱼协会的查验通常都很潦草,只要请柬本身是真的,你能轻易地拿着它穿过人鱼鉴赏会的那扇大门。想必你已经看到这东西了。唯一的小麻烦是,你得找一个符合上面描述的人假扮成你的随从一起进去,哈哈!(最后这里两个字写得尤其大些)
请务必在人鱼节结束以后来海军驻地探望我,入伍这事我得好好跟你发发牢骚。顺便,曲奇那几天也会回到人鱼协会去做身体检查,你有空的时候可以去看望一下他。
真挚的爱。
艾克兰
1905年5月15日
*雷蒙德•温特放下信纸,捡起桌面上那张带着高雅香气的硬质请柬打开。一张手写的便笺从里面滑落出来,上面写着被邀请人和他的随从的简单信息。
受邀人:威尔•巴顿先生,金发,27岁,出身威尔士,是商人的儿子,衣着一般比较朴素。
随从:李,55岁,与受邀者相反,是个衣着浮夸的老人。
这真的只是个“小麻烦”?他叹了口气,好想揍信纸对面的人啊。
第五封信
亲爱的水兵艾克兰先生:
恭喜你最终也没有逃脱入伍的命运,踏上了你兄长的老路。你不能来的确很遗憾,人鱼之都是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这里的人们对人鱼的自豪超出了我的想象,我在街道上邂逅了人鱼糖果,人鱼面包,人鱼馅饼,人鱼时装店,人鱼咖啡厅……等等,似乎一切物品都能想方设法与人鱼扯上关系,再冠上“人鱼”这个词汇。我尝了一口人鱼糖果,味道非常好,我随信给你寄了一份,记得认真品尝。
感谢你的邀请函,我在刚收到它的前几天愁得头发都快掉下来了,但天可怜见,现在这个问题基本上已经解决了。完成任务的关键点是我在两天前,愁苦地在酒店的餐厅吃早餐时,遇到了乔伊•安克森,他也是来参加人鱼节的。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安克森,就是公学时,隔壁宿舍的那个粉色头发的第一名。虽然当初只算是普通熟悉,但是他在课堂上的出色表现和很少见的瞳色发色组合都让我很难忘记他。感谢他的醒目特征,虽然毕业以后已经足足五年没再见过面,但我还是在他进入餐厅的第一时间就认出了他。令人伤感的是,他的左眼上多了一条疤痕,以那条疤的显眼程度而言,我很难想象当初是多么令人心碎的伤口,尽管本人轻描淡写地说是在做实验时不小心发生的事故,但我还是很难释怀。
不知道是岁月改变了他或者是其他的什么原因,安克森他看起来,和当年不太一样了。我不太好形容这是种怎样的变化,但这必然跟他脸上的疤痕没什么关系。不过他待人依旧很亲切,我们聊过了毕业这些年发生的事情之后,在天南海北的闲谈中他提到自己认识一个本地的化妆师——上帝啊,这正是我所需要的!
于是我邀请他来化妆成那位李先生,和我一起参加这次的人鱼鉴赏会,他同意了。今天上午,我们去拜访了他的那位化妆师,那位优秀的女士很成功地用一点道具和化妆品把安克森装扮成了一位看起来值得尊敬的老者。再过十个小时,我们将去参加这场盛会,我现在充满了对明天的期待。
保持健康。
你的雷蒙德。
1905年5月20日


阳光争先恐后地从被拉开的窗帘缝隙里钻进房间落在了仍在熟睡的兰伯特的脸上,强烈的光线使他皱了皱眉头微微睁开双眼但立刻又闭上了眼睛,就好像他的眼睛感受到了激烈的疼痛,他呻吟一声抬起手挡了下刺目的光,而后翻了个身将清晨抛在了身后。
但是苏西可不想就这么放过他。
“你打算睡到什么时候,小狗,”她在床边坐下伸手抚摸兰伯特的脸让他转过头来,但他只到了仰视天花板的角度便怎么都不肯动了,“坐起来。”
尽管兰伯特仍旧连眼睛都睁不开,但他还是听话地用手肘支起身子迷迷糊糊地勉强维持着坐姿,薄被从他身上滑下露出了在他皮肤上的点点吻痕和间或出现的咬痕。或许因为尚未清醒,他半睁着的双眼看起来朦胧而无神。
“这可怎么办,我的小狗还不愿意醒过来呢。”苏西扶着兰伯特的脖子让他抬起头而后凑近他的脸庞吻上他的双唇,这是一个蜻蜓点水般的轻吻,却足以让兰伯特清醒大半,他的双眼恢复了一些神采,就在他正想贴近苏西的脸颊继续刚才的吻时一个巴掌落在他脸上,这一下虽然不疼却够响。
“醒了吗?”苏西甩了甩用来打人的手,“五点了,我们该准备了。”
“才五点……”兰伯特打了个哈欠甩甩头,抓了抓自己的头发,“干嘛要这么早。”
“我们要做的事可多了去了,为了不让人看出破绽光是让你看起来像个人样就要花不少时间。”
“什么叫看起来像个人样……”他不满地嘟囔一声,但却被苏西听了个一清二楚。
“简单来说就是要你看起来别太像条狗,正经人类可不会被操了一次就天天缠着别人来操自己。”
“那怎么了,不是很爽吗?”
苏西摇了摇头,“到时候记得把你这幅不动脑子的傻样也给我收起来。”她按下房间里的传唤铃等待佣人的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