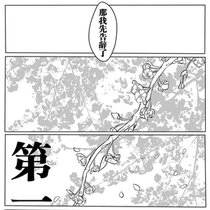前接:http://elfartworld.com/works/95548/
——妖异是由于人的欲念才化形的生物。
比方说猫又的魔性来自人妄图将死者复生的执念,雪女的恐怖出于冬日大雪封山的恐惧,姑获鸟的凄鸣是对逝去的未能出生之子的挽歌。而他们作为异世之形存在至今,最初的缘起自己大概都早已忘却,但是继承了的那份欲念会刻在骨子里,成为一种不可见的标记。尽管妖异和人,无论是外表,行为举止,还是自己的准则都截然不同,但有些地方却又极为类似——如同把人的某种情感无限地放大后安置在自己身上,从此所有的行为都会凭依着这份执念。
但妖异通常很惧怕承认这一点,因为他们认为他们与人不同。人的内心有太多空洞,会把自己连同周围的世界一起吞噬。然而妖异的产生却正是源自那里,只是没人能理清这份因果。妖异的产生和人的历史始终是纠缠不休,发生过各式各样的故事,有的与之为善,有的与之为恶。即使从妖异的角度来说,没有了人的历史也实在是漫长平淡又无趣的日子。而从人的方面来看,缺少了妖异的存在,也就少了很多口耳相传脍炙人口的故事。妖异既是神明,又是祸津鬼,人类会用词将之区分开,但其实所有妖异都是一样的,都只是八百万神明里的一部分。
彼此纠缠着,也就这么过了千余年之久,对两边来说,千年也都是很漫长的一段时间了。
不知为何,在试图甩开身后穷追不舍的追杀时,三千院忽然想起了在自己很小的时候,有个人讲故事时对自己讲过的这段话。连带着当时的蝉鸣和和果子软糯的甜度,都非常不合时宜地在脑中浮现了出来。战场上分心是大忌,这点他作为零式的教官再清楚不过,但是记忆并不是能单纯靠理智控制的东西。像是潮水,一旦蔓延开来,就算褪去,湿度也会留在那里。
而无论是在回忆里还是现实中,初夏的蝉声都似乎从未停息。
帝都夜话·转
七月一日前夜。
从SPST的舞会提前离场后的三千院在回去的路上尚在思考着他和石野中尉到底是如何认识的,而那句不知从何而来的话却一直噙在嘴边没能离去。非要说,那种念法有点像和歌,但向来不对此类文学感兴趣的自己又是从何得知,实在是令人费解。至于石野中尉就更不可能了——从自己与她初次见面起,石野中尉就不曾开口说话。
从三千院住的地方到洋馆的距离其实并不近,不过比起做车,三千院还是更喜欢用自己的腿走路,尤其是在晚上。在黑暗里他两只眼睛所见之物的差距不会太大,反而会给他种安心的感觉。七月的夏天是潮湿的,但是又不会像梅雨时节一样一味地让人心烦意乱。水汽夹带在夜晚的风里附着在裸露的皮肤上,刚好可以缓解热度带来的不适。蝉声也只是低语,不曾高声,和着风声一起,吟出一首风物诗,在这种气氛里行走和思考无疑是惬意的。他稍微松了松领带,衬衣系到顶端的扣子也解开了两个,穿好的礼服外套也脱了下来。在这一刻他觉得提前离场真是个无比正确的决定,否则这条路大概会熙熙攘攘都是离场的同僚,即使没什么兴趣,大概也要被强拉着跟人聊天或者找个其它地方去续第二摊。与其那样消磨一整个晚上,他宁愿遵从体内的生物钟回家后休息片刻后就睡觉。
反正也不止一次被人评价过古板得简直像是江户时代走出来的老古董了。
走到某处的路口时,他意外地发现,不知何时起,身周竟是一片寂静。不仅仅是没有人,连风和始终不断的蝉鸣也都消失了。生物对危险感知的本能让他站住了脚,只是身遭并没有任何动静。三千院看了看四周,也并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之处。他的右眼虽然捕捉不到颜色,但是在夜晚看东西却会比常人清晰许多。即便如此,周围除了道路,树,邮桶,和忽明忽暗的路灯,并没有任何超出他认知的存在。
蝉鸣声就在这一刻复又响了起来。摒弃了之前的细声低语,换做高声的鼓噪,伴随着落叶与突然大作的风声,从天而落。
以及刀刃。
三千院这么多年随身一直带着一把匕首。
那把匕首并不是很锋利,不如说有点钝,上面还带着一点修补过后的锈痕。看得出来主人是很珍惜的在保养它,无奈太过年久,还是免不了失了初时的锋锐。有学生问过他为什么随身携带的会是这样一把武器,明明有其它的可以选,其实三千院也说不上原因。非要说,他从那个改变命运战场带回来的唯一一件武器,就是这把匕首了。也许只是他自己心魔作祟,但他就是觉得那上面多多少少还带着曾经的影子,于是自然而然地就带在了身边。
——从天而降的锋锐力度大的惊人。
若不是他用匕首拼死格开,现在八成已经身首异处了。他借着格挡的力度身形往后退了几步,与对方迅速地拉远了距离。依稀能看到来人一身黑衣,从头到脚,包括后面那副羽翼,都几近和夜色融为一片。没留给他什么思考的时间,对方身后的羽翼带起风,空气发出近乎悲鸣的呼啸声,夹带着彻骨寒意的太刀直直冲着他的面就刺了过来。
刀刃刺入血肉的喑哑声响在风声里简直就是不值一提,甚至比不过周围的蝉鸣。
但自体内传来的震动,则是另外一幅光景了。明暗不定的路灯下的影子格外纤长,只是再无论扭曲变形,人类的影子也不会是那副模样。相比之下,带着巨大羽翼的天狗的影子倒是更容易让人视作人类。毫无疑问,那是异世的妖兽,发出的嘶吼和鸣啸声让一身暗色衣服的对方也倒退了一步。
只是三千院似乎并没有产生任何变化。
他脑中产生了一瞬的空白,等清醒过来的时候,对方已然主动跟自己二度拉开了距离,而且比出的架势更为谨慎。手里有点陈旧的匕首已经多出了两道崭新的斩口,提醒着三千院方才发生的事情。
“尔等如此荒谬之物,为何不就此引颈就戮。”
——我不是。
“违逆理数与天命之所在,为何还能如此存在于世。”
——我不是。
右眼所能看见的事物越来越清晰。之前在黑暗里能看的的只是个大致的轮廓和少许细节,如今却能看清对方的脸上带的面具是何模样,甚至连衣服上的花纹都愈发清晰地落在眼睛里。然而依然没有颜色,唯有灰度,无限的黑与灰,却不见丝毫的白。他很想反驳对方说他只是人类,但是右半身传来的躁动让他无法说出这句话。方才被刺伤留下的伤口几乎没有留太多的血就自发地止住了,浅色衬衫里隐隐透出右臂上逐渐变深的黑色虎纹。
——我是……人。
三千院稍微后退了几步,对方或许是以为他要借势冲上来,姿势多少谨慎了些。灵魂的一侧在叫嚣着让他就此冲上去与对方就此厮杀一番生死各安天命,但这无疑是将他作为人的最后一点理智也丢失殆尽。自从在试验里曾经妖化过一次认识到自己体内的异常之后,他再也没有将那份模样现于人前。并非由于会减少寿命之类的完全无法成为理由的理由,只是至少,他想保留他作为人的意志,人的思想,人的形态。
于是他逃了。
或许对方没料到自己会就这么转身逃走,隔了那么一瞬后,才又传来了羽翼拍打空气的响动。
——在阵前逃亡的军人都是可耻的。
这是无数次三千院在零式里对学生说过的话。如果放在普通战场上,他毫无疑问会转过身堂堂正正地拼尽自己体内最后一丝力气与对方厮杀,即使对方是妖异也一样。然而或许是血腥气彻底激发了体内的鵺,此时的三千院仅仅是辨认自己前行的方向就几乎用尽了心神。讽刺的是,与脑内散漫神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右眼之中越来越清晰的视野。若是当下他去反击,体内匿藏的妖异便会如同破壳而出一般将自己卷入其中。对他来讲,杀人和被杀都无足为惧,军人在战场上磨练出来的觉悟足以战胜死亡,但以「非人类的模样」死亡,却始终不是件能令他接受的事情。
可惜有言曾道跑不如飞,双腿能达到的速度还是低于双翼在空中前行的速度,就好比猛虎也无法在速度上越过鹰隼一样。三千院反手格挡开尾随上来的刃锋,两相摩擦间甚至溅出了细小的火花,在夜色里显得格外突兀。匕首上传来的力度一下比一下大,昭示着对方本不多的耐心大概已经被自己的举动消磨得所剩无几了。
“……到此为止。”
天狗将身形于半空中停留了一瞬,长刃如冰,乘着黑色的双翼挥下的风势,宛如真正的猎鹰般破空而下,刃尖直指心间而来。
“既无法立足于任何一边,便不应是世间之物。”
三千院看见了无边无际的大雪。
除了远处树木投射到地上的阴影与自己以外,满眼所见皆是无垢的纯白,这是他自从接受改造后再未在他眼底出现过的颜色。世间万物总有颜色,即便没有,很快也就会被沾染上,落在他的右眼里,统统都变成了灰调子。他往前走了一步,脚底与雪粒摩擦发出了簌簌的声响,雪粒落到皮肤上,很冰,但是身上却不冷。自从遇见天狗后一直就骚动不已的身体半侧此刻也平静的宛如这无边落雪,所有的热度和受伤的痛感都消失了,四肢百骸只充斥着放松后的惬意。如果不是还多少碍着礼节一类的,他几乎就想在这片大雪里躺下来了。
正在他思考要不要就此付诸实践的时候,他看到了一只黑猫。全身黝黑,唯有四蹄雪白宛如踏雪而来。似乎是哪里绑着铃铛,在黑猫跑动的时候,会有声低低的“叮铃”一声响。黑猫犹如闲庭信步向着自己踱步而来,铃音也就随着他的动作,一声一声,由远及近。铃声在耳边越来越明晰,但明明黑猫与自己还有段距离,却如同在耳边一般。随后几个轻巧的动作,黑猫在自己的膝盖上跳了一下,就跃到了他的肩头上,脸颊甚至能感受得到它扭头间蹭到自己脸上的胡须,而铃铛的声响却就此消失了。
雪也就此停了。
然后响起的是夏日的蝉鸣,一片皑皑白雪中的蝉鸣多少还是有点诡异,三千院有点头疼地闭上眼揉了揉自己的额头,等到再睁开眼睛时,猛然撞入眼中的夜色竟让他一时没能适应。除了躁动稍微平复下来,所有的疲劳和痛感又重新涌入了身体里,不仅仅是右肩,靠下些的位置也被浅浅戳了个不大不小的伤口,此刻血还在顺着皮肤留下,把自己的白色衬衫都洇出了一小片红,和隐隐透出的黑色虎纹交错在一起。而在自己的对面,天狗已然落在地上,尽管带着面具难以判断表情,但从眼神露出的杀意来看,可以肯定并不是什么愉悦的表示。然而不知为何,对方只是站在那里,却没有在此时向几乎无力行动的自己拔刀相向。
“汝为何人,为何相阻于我。”
三千院这才发现自己身后不远处还伫立着一个似曾相识的人影。他带着帽子,手上的折扇从春季拿到夏季,终于不会显得不合时宜。镜片后的眼睛微笑着,一脸平易近人地对着天狗打起了招呼。
“年轻人,精神就是好,大晚上的还在这里胡闹……啊,敝姓有栖川,只是个路过的写书人。”
记忆里和现实里的蝉鸣声,彻底重叠在了一起,再也无法分辨。
————————————————
临时盒饭因此没图,之后会有插图版,到时候出了这个会删(。
以及感谢鹰狩先生我写的烂写不出鹰狩先生的帅气(……)我不擅长写打戏你们都知道的我尽力了我真的尽力了(哭着
等插图版来补足帅气值吧,之后还有一篇容我们 慢慢发(。



我是八月三十一日冬至。
小时候,每天起床第一件事是生火,然后烧水,做饭,打扫庭院。
神社只有我跟婆婆两个人,有一天婆婆出门了,回来的时候她带了四九。
四九认识字,我找到一些有图画的卷筒,他能念出上面蜗牛爬一样的东西是什么。我问他为什么看得懂,他说他也不知道,就是认识。
我问婆婆的很多问题婆婆不告诉我,问四九就知道。
山上的生活很好玩,四九来了以后更好玩,除了婆婆不让我们下山。
山上也有可怕的东西,比如神社里头的祠堂,我看到就不敢靠近,还有小溪尽头的山洞,我好奇进去过一次,里面又黑又冷还找不到路,要是四九没来找我我一定会死在那里。
我不是没想过出去,好几次走到护绳前看外面的山道,然后我回头看,婆婆和四九都不在,后来我就回去了。
我学会了爬树,四九学会了打猎,冬天来之前我们能存到足够食物过冬。我们有种土豆和番薯,每次米快吃完的时候缸里就添了新米,灶台上有时还会放着新鲜蔬菜和糕点,我很开心,那时候没觉得奇怪。
婆婆偶尔出去,我看到她下山,但我总觉得她没离开过,哪怕一个人在树上时也这么觉得。
闻到血我会想吐,没法看着四九剥那些猎物的皮,但他每次打猎我都要跟着,反正拾柴是我的事。
我没见过其他人,感觉也不需要,因为不管我在哪里摔倒和迷路四九总会找到我,有四九在我就能回家。
简单的床,四季轮转的风景,鸟居秋天穿红叶,冬天戴雪,为什么我会觉得那种生活比现在更有家的感觉?
***********************************************
“冬至先生。”
八月三十一日冬至端着茶碗一言不发,对面的年轻女性朝他微微倾身:“冬至先生?”
冬至回过神来对上她询问的眼神,放下茶碗冲她一笑:“千叶小姐泡的茶太好喝了,我一时忘了要说什么。”
年轻女子收回视线坐直了身,抿着礼貌的微笑垂下头。
冬至盯住她微红的耳根,他眼里这位容易揣测反应的未婚妻,交叠的双手盖着红字大写的无聊,安静的眉心挂着黑字楷体的方便。
冬至挂起笑脸压低语调:“我有荣幸预约您下个月花火大会的行程吧?”
“我会为您准备最棒的和服。”说完,他便登上了回家的人力车。
庭院里的鹿威接满了水,敲在石头上发出“笃”的一声。冬至摘下帽子递给一旁的仆人:“新招的庭师在哪?”
“安佐濑先生今天没有来。”
冬至解斗篷的手停住了,仆人接着帮他脱。
“明天再叫他过来。”
“明白了,老爷。”
------------------
“你知道吗,井上他带去的人是个半妖。”
“真的假的,这已经不止男女通吃了吧。”
“可能半妖有什么我们都不知道的好处,是吧,八月三十一?”
“哦,可能是心意相通吧?我的话只要心意能相通,哪怕对象是一匹马也行啊。”
西装革履的年轻人们哄堂大笑,其中几个人乐不可支地搂住自己身边盛装打扮的同伴,陪在他们身边这些穿着漂亮和服妆容精致的少年,几乎看上去就像美丽的女人,举手投足间挤满了大量复制粘贴的闪耀的不伦不类。
冬至坐在他们之间举杯示意,他笑着喝酒,继续参与话题,眼神却越过了人群往空气飘去。
车子驶回八月三十一日大宅时天已经完全黑了。
“老爷要见安佐濑先生吗。”
“嗯?”
“他现在在茶间等着。”
在仆人伺候下换好浴衣的冬至“啊”了一声,想起昨天确实吩咐过让他不见到自己就不能回去。
拉门拉开的动静吸引了安佐濑,看见有人走进来他连忙正坐行礼。
对方手里提着灯就那样照了过来,安佐濑下意识侧过头抬手挡住过于明亮的火光。
冬至提灯凑近安佐濑,眯起眼从上到下缓缓扫视,又抬起视线仔细审视他的脸,两人之间的距离越靠越近,近到可以感觉到对方的呼吸——
“……冬至?”
照着安佐濑整个人的灯光往后退去了,安佐濑也放下手,声音不太确定地又重复了一次:“是冬至么?”
“好久不见了,四九。”冬至冲他笑,给了安佐濑一个大大的拥抱。
------------------
“这茶汤味道好怪。”
“这是咖啡。”
“笑?为什么?”
“拍照片。”
“剧院?”
“今晚有新节目,我们去看。先给你买点新衣服。”
“那个,”安佐濑看着周围走来走去的人群,停下脚步,“庭院怎么办。”
人行道旁的商店玻璃反射出冬至的身影,他也停住脚回过头。
“结婚以后我就是下任家主,你的工作由我安排。”冬至笑着对安佐濑说道,“现在你要陪我。”
------------------
“晚餐就安排麻布幸村可以吗?”
“可以,跟四九说吧。”
“老爷您约的千叶小姐看戏吃晚饭。”
冬至皱眉张嘴看向仆人:“该死,我把这事忘了。”
“要取消预约么?”
冬至两手用力一扯外套领子:“不用。”
街上摇曳的灯光像一群游来游去的小丑鱼穿插在行人间,金发男人陪同身穿和服的年轻女子走过两侧站满店铺的人行道。
“今天谢谢您了。”
“哪里,我才是要感谢妳给我的夜晚增添光彩……”冬至话说到一半笑容僵在脸上。
安佐濑抱着树丛那么大的花束跟一个高大的绅士走在一起有说有笑,走进千叶身后的街角。
“失陪一下。”冬至盖上礼帽从她身侧跑了出来。
街上的风景从视野里奔跑而过,人们的惊呼声把冬至拉进下一个转角。
聚拢的人群围着纷纷落落的花瓣在街道中旋转成一个圈,冬至摘下帽子走进去,从里面拾起一条围巾。
冬至把四九的围巾丢到卧室茶桌前,一手拎着清酒瓶子给自己满杯,报纸和资料散乱地铺在周围。
一口干了杯中物,冬至皱眉瞪着眼前几份关于人忽然消失后又出现的旧报导。
“神隐吗,还以为这种事最近都绝迹了。”把空杯子放在一则标题“狐狸请客?”的杂志文章旁,冬至手指不耐烦地敲着杯沿,“会回来的吧。不,他必须得回来。”
***********************************************
好痛。
左眼好痛,睁不开,好像烧热的木柴从我的大脑里刺穿过去一样,痛得看其它东西都像蒙了层雾似的模糊不清。
一些画面和声音不断交替闪回,我感觉像坐在黑暗里看坏掉的有声电影片段。
我看到四九担心的脸,还有断掉的护绳,我听到四九问我怎么了,我看到四九他…看起来非常年轻?
我看到断掉的注连绳从大榕树之间挂下来,四九叫我等他,他离开以后我看到洞穴的石壁和地上的泥土。
我看到山道远处有些人影在晃动,落叶铺满了山头,我眼前钻出来一个黑影,比手画脚嚷嚷着头发,看这头发。
更多的黑影跑出来,喊叫着找到了找到少爷了一拥而上。
***********************************************
冬至躺在被窝里,抬起手盯着掌心,然后像是要确认什么似的又揉了揉左眼。
拉门拉开一条缝,仆人的声音跟在挤进卧房的阳光后面说道:“老爷,安佐濑先生找到了。”
鹿威跑在庭石上方接着水,冬至走进和室,抽了抽鼻子,空气中飘散着淡淡的甜味,像是花香。
冬至走到熟睡中的安佐濑旁边,皱眉说:“臭死了,去拿香烛来。”
仆人端着茶走进来,收走了一人份的餐具。
冬至拿掉嘴里的烟管,表情跟刚进帝都铁路车站那时的安佐濑一样:“你见到妖怪了?”
披着外套坐在褥子上的安佐濑放下茶碗:“嗯。”
“有这样的事啊,那你们说了什么。”
“我就问了跟我有关的妖怪的事情,他们说那妖怪叫朝濑。”
“等等,你说什么。”
“我问了他们妖怪的事情…”
“不,你说他叫什么。”
“朝濑。”
冬至起身拉开拉门,往外头左右环顾,重新把门拉严实:“四九,你以后别查这件事了。”
“为什么?”
“还有也别再和那些妖怪来往。”
“但是我……”
茶碗啪地打翻在榻榻米上,冬至拽起安佐濑的衣领恶狠狠瞪住他:“你是我的庭师,我说什么就是什么!”
===============================================================
文笔为零的打卡 内容也流水账 感觉好耻啊
弄成这样的局面对不起安佐濑
只是要推动一下情节 请把这个看作助攻
对第一人称说不清楚的地方补充点说明
冬至小时候的记忆跟实际情况有出入,提到的婆婆就是狐巫女,为什么这样大概是法术影响
家里人来带走冬至的那天打破狐狸结界时弄瞎了他的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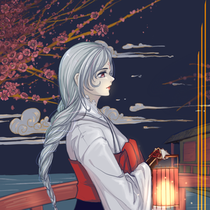


反正格式都会被吃,已经没有格式值得去排了。
he亲妈看着你们心惊胆战
努力一下这周收尾,放着一直没空写也好难受,最近状态成迷就凑活着看吧【哭晕在厕所】
不知道放哪里不要打我【抱头】
——————————————————
“清理干净了?”
“嗯。”
黑色的雾气沿着冰块之间的缝隙钻进了冰霜傀儡的体内,从它的内部开出一朵美丽又残忍的兵刃之花,在冰块凄惨的破碎声中,庞大的傀儡被肢解成大小不一的碎块散落在地上,不知道有多少傀儡被这种简单粗暴的肢解手段破坏,放眼望去只有满地的冰块铺满了地平线,密密麻麻地让人没有下脚的地方,而且只是看着就让人感觉背后一股凉气。
薇塔塔背着手看向远方的一排城墙,刚刚那里被什么爆炸波及了一样,城墙倒塌激起一片尘土,小卓尔精灵聚精会神地看向那边,不知道心底在想些什么。
折途张了张嘴想要叫她,却又想不出什么理由,简短的对话之后讪讪地闭了嘴低头查看亚修的伤势。
红发的勇者头枕在折途的大腿上,胸口随着平稳的呼吸上下起伏着,只是从他紧皱的眉头看来并没有睡得有多舒服,折途也不会揣测别人的梦境,用手指戳了戳对方的脸之后继续去检查亚修身上是否还有遗落没有处理的伤口。
“你竟然能把他放倒诶……真了不起。”
薇塔塔的声音在头顶响起,折途抬头看去,女孩逆着光面对他,脸上的表情似笑非笑,话语的单词中毫无赞赏之意。
“是啊,我之前还是黑医来着。”
亚修压地折途的腿根有些麻,尝试轻微移动了一下会惊醒正在睡觉的人,折途放弃了调整姿势,顺便用平淡的语调回答了少女的问题。
两者之间又重归寂静,远远地有什么东西的哀嚎声传来。
十分刺耳。
想不出来到底说什么,折途干脆伸手招呼薇塔塔过来坐在这边,后者也干脆地朝这边走来,整理了一下裙子坐在刚刚扫干净的地面上。
两个人之间的沉默还是持续着,各自想着心事,虽然坐在一起,但是仿佛却相隔很远。
“你的剑。”
薇塔塔顿了顿,继续开口说道。
“剑鞘是后来配上的吧。”
“是啊,我还以为没人会注意呢。”
折途瞥了一样被放置在身侧的银剑,白金的剑柄和漆黑的剑鞘怎么看都不搭配,甚至连做工也是天壤之别,下一秒薇塔塔伸手够到了那把剑,将它从剑鞘中抽出来,锋利的剑刃似乎在颤抖,在风雪中冷冷地泛着寒光。
“不像是你这种人会拿着的剑啊。”
薇塔塔绕有兴趣地打量着剑身上铭刻的精灵文,虽然大部分的花纹和字迹都被折途胡乱打磨掉,但是总有那么几个字被他当成花纹留了下来,薇塔塔反复辨认着这些残留的字迹,想要从里面读出点什么。
“是—”
“献给最伟大的神,光明与……嗯……看不清……”
毫不留情地打断了折途的话,薇塔塔眯细了眼睛,看着那些被磨的破碎不堪的痕迹。
“柯旭。”
两个人异口同声地念出某位神明的名字,也恰好二者相互对视,两个人都想说些什么,但是又没有人打算先开口。
“我知道……”
“原来你知道啊。”
折途话音未落,薇塔塔就像是抢答一样踩住了他的话尾。
“这么糟蹋其他宗教的圣物之类的东西,你还真是不怕被天罚啊。”
“无所谓,来更多的苦难对于我来说也没什么,柯旭的信徒……那群家伙又不关我事,不如说又烦又吵。”
“喔,真是大胆啊你……”
疑似是什么圣剑的银剑被薇塔塔随手放在一边,看来她也不是对这件事很上心。
“那么,剑鞘去哪了?”
话题被引回,薇塔塔侧目看着折途沉思的面庞,对方正在无意识地咬着手指。看来以后可以用这件事情笑话他,薇塔塔笑着。
只是大概没有机会了。
“卖了。”
“……当时好像是,忘记了,总之是吃不上饭要饿死了。”
“反正留着也没用,就拿去卖了。”
轻描淡写地几乎不像是折途本人做出来的事情,更像是他道听途说的无聊故事。
“啊,还有,这个送给你。”
终于是舍得把注意力从亚修身上移开,折途从腰包里掏出一个小小的黑色绒袋,里面鼓鼓囊囊地塞了不少东西,漫不经心地放到薇塔塔小小的手心里,紧接着就继续低头盯着亚修的睡脸。
薇塔塔用指腹轻轻摩挲着绒布中的突起,随着动作的起落能听到小布袋里的物品相互碰撞发出好听的叮咚声。
金属的碰撞声。
“刚刚还说吃不上饭要饿死了。”
女孩微微一笑,看上去像是嘲讽又有点落寞。
“现在不一样了。”
在余光的末端,薇塔塔察觉到那人脸上罕见的笑容,只是很快又被他一贯的漠不关己掩盖了,折途继续低着头捣鼓着什么,好像在他眼里亚修身上有着数不清的伤口等他去治疗。
“一路顺风。”
简短的告别之后,薇塔塔站起身来,缓缓地走向倒塌的城墙,在折途眼中,她的背景就像是炎天下舞动的阳炎一般,燃烧着。
“现在只剩我们两个人了……”
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说给谁听一样,折途紧盯着远方的巨大冰柱和缓缓移动的冰霜傀儡。
“完全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开始说起好,对于你这种人来说我真的是非常不适应,到底该如何和你相处,这种事情我根本想不到头绪啊。”
变得喋喋不休起来,甚至变得不像自己起来。
“十足的笨蛋、一根筋、脑子不拐弯、自以为是、控制欲强。”
简直是自己最讨厌的类型。
“你到底那点好啊?”
在向谁抱怨?
“啊这种事情什么的,真是麻烦死了……”
将脸埋在双手手掌中,断断续续地泄露出来的话语也变得模糊不清。
“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啊……”
【你喜欢莉芙的哥哥吧。】
——不喜欢,最讨厌了。
原本应该是这样的。
但是为什么现在,一句反驳的话都说不出来了。
只要放空下来,那句话就不断在脑内重复着,等待着折途的回答。
很久之前应该记得那个问题的答案,感情在心底发酵,堵塞在喉咙间,压地折途的内心直直地坠下去,不知道要沉到何处的深渊中,那些沉重的感觉紧紧地掐住了自己的脖子,勒出道道红痕,它狞笑着,等待着折途从内心最隐蔽的地方挤出的答案。
有液体从指缝中滴落,不知道被谁拭去。
勉强撑起沉重的眼皮,亚修首先看到的是折途的脸,跟往日折途他处处隐藏自己的感情比起来,现在的光景看上去十分稀奇,那张脸现在布满了泪痕,哭得红肿的双眼没精神地耷拉着。
“搞什么啊……”
似乎是注意到了亚修的转醒,折途的眼中闪过一丝惊讶的神色,任由亚修的手拂上了他的脸庞拭去那些斑驳的痕迹。
许久没有修剪过的刘海遮住了折途的眼睛,两侧的发梢也已触及肩头,虽然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但是确实地从折途那里传达来了安心的感情。
“我以为药效还会更持久一些。”
折途漫不经心地握住了亚修抬起来的那只手贴在脸上,极力稳定住自己颤抖的声线,药效还没有完全过去,现在亚修也只能做出一些简单的动作,只要再过上一会就能完全恢复如初了吧。
“恢复地挺快,什么时候醒的?”
“大概是你说自己是黑医的时候。”
“…………”
“下次——”
一道突兀的声音打破两人之间的对话,之前被薇塔塔破坏肢解的冰霜傀儡又颤颤巍巍地站了,正在缓慢地朝这边走来,那些本应该被破坏的一干二净的武器也被傀儡紧握在手中,傀儡无言地继续靠拢过来,空气似乎也被这肃削的杀气冻结住了。
“——”
能看到亚修的在拼命说些什么,只是耳中什么声音都听不到,折途漠然地拿起搁置在一旁的佩剑,随着清脆的金属碰撞上,宛如镜面一样的刀刃上倒映着不同以往的坚定和杀气。
“——”
“没关系的。”
宁静的疯狂。
再次握上剑柄的手从来没有有过如此有力,想到接下来的战斗折途甚至有些期待。
因为某种不知道名字的感情而充满了力量。
亚修的声音远远地在身后已经听不见了,折途舔了一下因为燥热有些发干的嘴唇,对着比自身高大了不知道多少倍的杀戮傀儡架起了剑。
“没关系的。”
“让我来保护你吧”
瞳孔因为兴奋而缩小,心脏在胸腔中乱跳着。
圣光包裹住了剑刃,似乎没有能够阻挡它继续前行的障碍。
犹如残血的夕阳下,银色的发丝在空中飞舞着。
“到时候……”
冰屑与鲜血溅满了天空。
“再告诉你我的秘密吧。”
“亚修——”
在一片赤红中,青年的回眸一笑深深地烙印在亚修的瞳孔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