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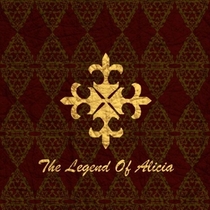
昨天司龙倒下之后我一直是混混沌沌地状态,眼前不停的有一圈圈的白色光圈,耳边是嘈杂到几乎要爆裂的声音。
后来听他们说,司龙的身上出现了很多血手印。几位男士将他扔在了水池里,那些手印才下去了一点点,没办法我们把司龙送进了他住的屋子里面。
昨天从神社回去之后,我就开始不停地打喷嚏,迷迷糊糊地睡了一个小时之后喉咙痛得无法说话。给营地地医学生看一下说是扁桃体发炎,勒令只能留在营地休息。那个感冒药似乎有安眠药的功效,我只能躺在营地的帐篷里面。
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早上了,喉咙依旧是灼烧的痛感,只是头不是那么晕。朝月小姐告诉我她昨天去看司龙的时候,司龙在说着梦话,似乎将朝月小姐当作了椿小姐,说了一些很孩子气的话。
我知道司龙在遇到筱和家之前的样子,也知道之后的样子。虽然椿小姐对司龙关爱有佳,但是始终还是将他当作继承人培养,对他的要求十分严苛。
司龙独自在这个幽闭世界里面成长,如同在黑暗中开出的缅栀子一般。他是希望,也是明天。他拥有了可以独当一面的美好品质。
但是他还缺些什么。
我希望将他缺失的,教给他。虽然我并没有什么立场说我一定能做到这一步,或者说我可以圣母心泛滥到这一步。对于路边的失业人群,我尽管感觉可怜,却不会在第一眼便生出如此宏大的感情。
只有司龙。
吃过早饭【干粮】之后我便踏上了去神社的路,包里带了一点向医学生讨来的退烧的药物。因为夜晚过于危险,所以并没有人在那边看守着司龙。这点让我非常不放心。
不过说起来,那个孩子似乎也已经习惯了独自生病的感觉。不像我……每次我生病的时候,都有十五陪在我身边。
这也是我得教他的。
我腿程慢的很,虽然出来的时候还早,但是走到神社的时候上午已经过去一半了。
照例去手水舍洗了手才敢进入神社【第一天来的时候有人很敷衍的洗了手,司龙好像很不开心的样子。】
司龙并没有醒过来,只是神色比起昨天刚倒下的时候好多了。我隐约记得那是怎样痛苦的表情,以至于它在我朦胧的梦里面无限放大,变得狰狞而影响深刻。
我也看见了他们所说的血手印,在那棕色的浴衣上面简直触目惊心。还好已经淡了很多。司龙似乎很不舒服的样子,在被子里面缩成一团。我伸手摸了摸他的额头,却因为没有触摸过发烧病人所以不知道怎么样才算烫手,只能塞了个体温计在他嘴里面。
我从来没有照顾人的经历,一直都是十五在照顾我。十五从来不会生病。
司龙含着温度计很乖的样子,没有用力咬,也没有挣扎,平平地躺在那里。过了一会我拿出来看了一下,应该是三十七点八度,还是烧的挺厉害的。
我的司龙要从害羞包变成发红的害羞包了。
边上有退烧贴,应该是朝月小姐他们留下来的。我撕了一个帮司龙贴上,然后坐在边上的椅子上开始看自己拿过来的八月份物理研究报告周刊。
不会照顾人……的话,陪着坐着还是会的。反正司龙很乖。
“一真,是不是有人跟着你?”
松海一真闻言转过身去四下张望,花了点时间才在一块突出的岩石后面看到有点眼熟的身影。作为一家之主的一真平时少不了和其他家族的人打交道,因此略微想了想才回想起那人是谁。
“内屋先生……?”他试探性地喊了一声,躲在石块背后的人影动了一下,然后带着尴尬的笑容走了出来,正如他所猜想的,是在祭典上捡到了扇子,又拉着自己到处打听寻找家人的那个黑肤青年。“我继续往前面走走,你快点跟上来吧。”松之丞见两人似乎认识,略微点点头打个招呼,便转身继续往迷宫深处走去,进之助略带着点好奇地探头张望两人,可惜走出来的并不是可爱的女孩子,因此看了几眼也兴致缺缺地跟着走远了。
“呃,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和舅舅他们走散了,正好看到你想跟你一起走,不过看到你们是整个家族一起行动,怕有什么不妥……那个,我真的没有什么不良企图。”
内屋衣御有点慌张地解释着,没说几句似乎察觉到自己的辩解苍白无力,挠挠头转开了视线,又忽然抬头急切地表明自己的无敌意。
作为曾经被人类所“背叛”而灭亡的武家,在复活之后心存怨恨与怀疑再正常不过,尽管从刚刚松海家人的表现来看他们似乎并没有对内屋的行为有明显的不满,却也只是表面上看来而已。况且就算是在和平的年代,这样鬼鬼祟祟地跟踪别人也是违法的行为,两个人还远远没有熟识到能够开个玩笑就将这件事翻过去的程度,如果松海一真因此发怒,恐怕……
想到这里,内屋衣御又是垂头丧气又是手足无措,慌张得几乎想转身就逃走,却又深知这时绝不能做的便是逃跑,最后他只能紧紧闭上了眼睛,等待松海一真的反应。
发怒也好,怀疑也好,觉得恶心也是难怪的,早知如此,还不如在迷宫入口看到他时就大大方方地上去打招呼,怎么也不至于到现在这个地步。
内屋衣御的脑海中百转千回,令他瑟瑟的叱骂却始终没有降临,他只听到松海一真轻轻叹了口气,他说话前似乎总是习惯叹一口气,仿佛这短短的一声就能把万语千言都传达出来。
“内屋,你的手臂被烧伤了。”
最后得到的是一句羽毛一样轻飘飘的话。
内屋衣御抬起头,看到松海一真正在随身的小包里翻找什么,片刻之后递过一个碧绿的小盒给他。“……这只是普通的烧伤药,实在是有点寒酸,是我自作主张了……”见他呆愣着并不伸手去接,一真似乎误解了什么,有点窘迫地收回了手想把那盒药膏放回包里,内屋衣御这才恍然大悟,一边慌慌张张地摆手示意自己并不是嫌伤药普通而不收,一边想去拦一真,又觉得自己冒失,急出了满身的汗,最后索性心一横,一把抓住了一真比他细了一圈儿的手腕。
一真倒是不如他想的那样惊讶,只有点诧异地看了他一眼,这一眼仿佛比翻滚的岩浆还要烫上百倍,内屋衣御又像摸了火似的赶忙松手,背着手活像是被父母训斥的孩子,左右思索半天,最后结结巴巴地说了句对不起。
一真稍微睁大了点眼睛看着他,停顿几秒后还是伸出手,把那个碧绿的小盒塞到内屋衣御手里去,抓着他的手让他攥紧,不至于滑落,然后便微微行了个礼,转身离开了。
只留下雷鸣般的心跳声。





人是会欺骗自己的。
远坂唯名从很久以前就知道这件事。
人是会欺骗自己的。不论什么身份地位,不论人格优劣高低,人在真相面前总爱遮住双眼,捂住耳朵,对摆在眼前的事实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像是这样就能说服自己,事情总不会坏到那样的境地,又或者有些事情从未发生过似的。
他盯着手里一家三口的照片发了一会呆。
搜救队现在所在的这家废弃化工厂,曾经的用途在搜索的过程中逐渐变得一目了然。散落在各处的古怪白色粉末与一笔笔交易记录,让前一天还在因邪教祭祀的话题而各处奔走寻找线索的众人皆心生出一种难言的古怪来,一直以来遭遇的非科学的离奇经历,也因这一处赤裸直白的交易表的出现,而生出了一种别样的现实感觉。
该怎么说呢。
或许比起怪力乱神的邪神祭祀之类的事,反而是这里的这一类事情因有前例可寻而叫人稍能放下心来。至少这里的一切,说白了——也不过就是那么回事嘛。
一日不见人影的榛名今天也出现在了队伍里,小警察推拒了众人的担心,笑着拍拍自己的胸膛,显出毫无异状的模样来。而唯名无言的站在他身边,看那张与自己一般无二的脸上细小的变化。同胞兄弟的眼窝微微凹陷,血色褪去了一些,在露出些微憔悴容色的同时,气息却极平稳,目光一丝不乱,显得像是当真没有什么异状的样子了。
榛名偏过头,兄弟二人目光相接,双方都平静而坦然,弟弟甚至还有余力活泼的眨了眨眼。
唯名于是就拍了拍他的肩膀。
他像是明白了一些什么,没有询问对方的行踪,也没有问他这之后的打算。
就像榛名也只是看了一眼他手上的照片,然后轻轻叹了一口气一样。
那傻小子最后对他说:
“大哥,我好像挺久没给爸妈打电话了……你说他们这一趟公差也该回来了吧?”
他沉默了片刻,回答:
“……是啊,就回来了。……出去之后给他们报个平安吧。”
这段对话就在这里戛然而止。
唯名没有加入对地下保险柜的搜索。
当众人对那些药粉猜测纷纷时,他正盯着在这里找到的两张照片,分不清自己到底是想要叹气,还是因早有预想而更加烦心起来。
背面写着凉宫家的照片上,一家四口人的身影同山庄电视柜中那张照片上的人一一重合,而另一边,另一张照片上牵着父母的手笑得露出门牙的小女孩的轮廓,就这么一点一点同他记忆中的那副音容叠在了一起。
唯名想起那天夜里。他走出那个令人窒息的黑红色房间,不祥的雨水一直落下,连月光也不再洒落在他们身上。
他忘不掉自己看到的那一幕幕,心越发坠下,脚步越发沉重。
可在目光触及那人时,心头种种却又忽地淡去,一时间没有其他话要说,只相对沉默。
——然后唯名就这样抬手拥抱她。
……
化工厂内,搜索仍在不断继续。
唯名攥紧了两张照片,连带着先前捡到的军刀一起小心的收起。
他挥开脑中的其他杂念,暗自想着:
白石沙耶香。
从第一次见面起,她便她自己是白石沙耶香。
……或许至少在这件事上,她是没有骗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