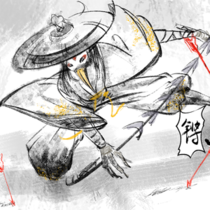作者:白梓
备注1:虽然有些悲伤,但应该是个HE吧
评论要求:求知、笑语
我虽然留有她的影像,但也不常看,因此记忆里的她多少都有些模糊了,当她的仿生复制体出现时,我还是不太能确信那就是我三十年前的恋人。
当我看见她时,她也发现了我,虽然变化很大,但她的面部识别算法还是认出了我,便笑着对我说:“好久不见。”
我该用什么样的情绪和语言去回应隔了三十年的相遇?是要哭吗?说话时要不要哽咽?眼泪是仅仅湿润眼眶,还是流落双颊?
我比我想象中的要平静地多,只是点了点头,说了声“好久不见。”
我的回应像是触发了什么,她的身体保持不动,头颅却开始震动,发声器里传出的语句变得零碎而缺乏逻辑。
“大海、列车、月亮、星河,”她说,“逃跑、飞行、坠落、D24C。”
“你还好吗?”我嘴上说着关心,脚上并无动静,仅仅是看着她的眼球缓缓突出,皮肤崩裂。
“嘭”地一声,她的脑袋爆炸了,青蓝色的冷却液和她的仿生脸皮一起泼洒在我面前的强化玻璃上,缓缓滑落。
在我无言地注视这一切时,一个男人推开了门,他看着玻璃内的场景,呆滞了几秒,然后有些自暴自弃地坐在地上,抓着脑袋自言自语着。
“只是第一句对话就让思维逻辑模型崩溃了,到底是哪里出错了啊……”
“真没道理,这没道理的!”
我并没有多说话,毕竟我只是受邀前来测试仿生复制体的,对这些前沿科技并不熟悉。如果谈论的内容是做菜,我大概能给出一些不错的建议。
在那位工程师自怨自艾之时,我听见了“咔嗒”的一声轻响,自玻璃窗后传来。冷却液与脸皮在重力的影响下滑落于地面,虽然窗户仍污浊不堪,但至少能看清其中的情况。
她的合金头骨只剩下一半,只由一根钢铁脊椎连接身体,可怜地倒挂在上身,仅剩的右眼看着我。
“好久不见。”她用金属的声音问候。
我和她曾是恋人,当时我们都刚刚高中毕业,都喜欢星空与大海,总是梦想着攒够钱,去海滨城市走一趟。她总说,希望到达海边时,夜空无云,繁星能与海的倒影一同闪烁。
她平日很内向,在镜头面前却无太多顾虑,我把她所有浪漫且疯狂的想法录成视频,发到了网上。那鲜活的生命力随她的一言一行迸发,引来了许多身心俱疲的社会人追捧。
我已经记不清当初拍下那些视频的原因了,不过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感谢我记录下了她的音容笑貌。
他们总说:“她给了我追求梦想的动力!”
他们总说:“很抱歉你们的遭遇。”
他们其实不必抱歉,毕竟时间总会治愈一切。
在她死后,我确实花了不少时间走出阴影,但那也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
我结婚生子,过着自己的人生;我忘记了她确切的样貌,只记得少数印象深刻的只言片语;我赚够了钱,和妻子、女儿一起去了一趟海边。
见到大海的那年,我已经三十多岁了。
那时我才发现,星光原来如此微弱,再清澈的夜空也无法让星星的光落在海面。
仿生复制体,在这个时代算是一种潮流科技,虽然在十几年前便有了第一个仿生复制体出现,但真正进入商业化阶段,还是近几年的事看,而商业化的关键在于拓扑算法的出现,让模拟人格复制未曾备份过的死者人格成为可能。
通常来说,复制活人的人格要比复制死人的人格简单,但人们常常更需要后者。
公司选择了她作为自己仿生复制体产业的营销重点,在数不胜数的已死的名人中,她是最便宜的,她的父母轻易地贩卖了她的人格权。
在人格模型的设定下,她的自我认知为“拥有人类记忆与自我的人形,既是人类,也是机器”,并无太多自我怀疑的情绪,也没有自毁倾向,但距离完全运行还有很长一段距离,需要大量的实践和测试。
不知是愧疚亦或冷漠,她的父母并没有参与后续的模拟人形测试,因此公司的人找上了我,希望我能帮忙。
“毕竟在那些播放量最高的视频里,她提到你的次数和她的梦想一样多。”公司的营销总监侃侃而谈,“而且再见离世多年的生死挚爱,也是一个不错的热搜话题,归根结底,这个时代人们最需要的是感动,而不是过气的死人。”
想法很不错,实践有难度,作为营销的一环,我与她很难配合。不知为何,她的仿生复制体和我聊不过几句便会崩溃,有时会失控自残,有时会影响到头部硬件当场自爆。
我每天都会在饭店打烊后去公司一趟,妻子还以为我外遇了。不过等我对天发誓了好几次后,她的疑虑也就打消了。
她倒是不太关心我在做什么,只要不是外遇就好。
就那样,过了十几天,测试了十几次,她也崩溃了至少十次,公司的工程师终于找到了问题所在。
“严格来说,”他严肃地说道:“现在的你,不是过去的你,而模拟人格认知中的你和实际的你有太多差别,因此影响了逻辑算法的运作。”
“现在的我,当然不是过去的我。”我平静地说道:“已经过去三十年了,一点成长也没有不就是巨婴吗?”
“话是这么说,但你还记得当年的自己是什么样子的吗?我希望你能模仿18岁的自己,用当年的样子去和她对话。”
我沉默了几秒。
“很难。”我认真地说道:“加点钱的话,我可以试试。”
我看着玻璃里的自己:大腹便便,头发稀疏,虽然常去染黑发,但还是不可避免地看见几条白色的发丝,因为常年在厨房工作,皮肤出油很重,重点是那双眼睛,过于麻木了。
她过去总是夸我的眼睛很好看,原话是“就像藏着星星一样”。
如果她真的还活着,会对现在的我失望吗?
应该是失望到爆炸了。想到这,我忍不住笑了起来。
屏蔽墙缓缓升起,她出现在我面前,低沉的眸子忽然亮了起来。
“好久不见。”她说。
我为了如何回应想了很久,如果是三十年前的我,等了三十年再见到她,到底会怎么回答?我攀着过往的记忆,塑造着年少的自己,得到了一个回答。
“你回来啦。”
我说得很难为情,这并非演技的一部分,而是真的感受到了强烈的尴尬。
在我的预想中,我应该是用如释重负的语气微笑着说出这句话,但话到嘴边,却以一种别扭且抗拒的状态说了出来。
她似乎并没有察觉到我的不适,也没有失控或是自爆,仅仅是望着我。
我没料到她会什么也不说,便搜肠刮肚地想要主动找个话题:……“我有好多话想和你说……你还记得以前我们说好要去海边吗?”
“我的记忆就留在那个时候,不过比起以前的事,我还是更想听听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她顿了顿,继续说道:“你变了很多。”
我瞄了一眼摄像头,这次测试和工程师的预期不同,她意识到了我的变化,意识到我与18岁的少年全然不同,却没有出现自爆的情况。
但按照之前的方案,无论发生什么事,只要能继续聊下去,不要停。
“……我现在是厨师了。”
“你做饭确实很好吃,但你当初不是想当飞行员吗?”
“你走了以后,我还是没拿到航空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在垃圾大学里混了四年,也没学到什么,就回家继承了我爸的饭店了。”
“太可惜了……”她抿嘴道:“我觉得你是能做到的。”
“哈,谢谢夸奖。”
“我以为你很讨厌子承父业……”
“没办法,当时他急病发作走了,和你一样突然……总是有很多没办法的事。”
她沉默了好一会。
“那之后呢?”她问。
我也沉默了好一会,不知道该不该继续说下去。
“我结婚了,”我还是说了出来,“我有了一个女儿,现在八岁,喜欢唱歌,每次去KTV总是抢着要点一些卡通里的主题曲,我老婆觉得她有天分,想给她报一个钢琴班。”
“唱歌和钢琴是一样的吗?”她有些迷惑。
“她觉得都是音乐,也算沾边,而且钢琴档次更高一点,比唱歌好多了。”
“你怎么想?”
“……我没想法。”
不知为何,一股强烈的疲惫感涌上了心头,我看着她精致的脸庞,下意识地扯出了一个勉强的笑容。
“再之后呢?”她问。
“再之后,我就站在这里,和你说话了。”
“三十年,不应该只有这几句话来概括。”
她看起来有些难过。
“其实也发生过很多其他琐碎事,但好像都没有讲出来的必要。”我看着她的样子,故作轻松道:“别想太多,生活也只是生活而已,要聊聊以前的事吗?”
“白廷。”她忽然叫出了我的名字,让我不由得有些紧张。
“怎么了?”我问。
“你可以抱抱我吗?”她问。
我想起了她自爆的情形,犹豫了片刻。但最后,我还是看了一眼摄像头,点了点头。
我和她之间的那扇门自动打开了,我走了进去,她只有一个上半身,腰部连接着支架,无法移动。她朝我张开了手臂。
我应该顾虑自爆的危险性,我是一个家庭的支柱,我是一个孩子的父亲,我应该停下,应该保证自己的安全,但我还是走了过去,抱住了她。
她对比我记忆中的温度冷了许多,但这也正常,毕竟说到底,她也只是一个由有机合成物、金属以及算法组成的仿生复制体,真正的她早已死去。
“我才发现,”我在她耳边说道:“原来时间治愈不了什么,时间只是杀死了过去的我,让新的我,代替了过去的我。”
我说:“我还记得一些过去,确实有很多无法忘怀的故事,但那好像……”
“……好像已经是别人的故事了。”
她更用力地抱着我,但力度尚可接受。
她说:“……无论如何,我还是很高兴,可以再遇到现在的你。”
她松开了我,笑着看着我,笑着笑着,停了下来,不再动弹。
我放开了她,然后看向冲进测试区的工程师。他又哭又笑,状若疯癫。
“她妈的!怎么又崩溃了!”他把手里的文件摔到地上,“明明已经接近成功了!”
“别激动,”我平静地说道:“我找到解决办法了。”
“你找到什么了?你懂个屁的算法!你就只是做饭的!你知道离散数学吗?知道拉姆齐问题吗?知道四色定理吗?你什么都不知道!而知道的还要加班!天天加班!天天加班!”
我没再说话,只是等那位工程师冷静下来,颓废地坐在地上后,平静地阐述自己的想法。
屏幕里,公司的首席科学家喋喋不休地介绍着仿生复制体的前景,说着各种难以理解的名词,就在大家快要昏睡过去时,公司发言人及时放出了一段三十年前的短视频。
视频里的少女大谈自己和男友的梦想,时不时做些夸张的表情,又扑向镜头后的主人,让两人的笑声交响。那已是三十年前的影像,人物的衣着装扮,放到现在有些老气,但那蓬勃的欢乐与情感仍能让如今的人们感受共鸣。
“……她曾是一个鲜明的存在,在短视频年代红极一时,给予了无数人追寻梦想的动力,她曾有过星空与大海的美梦,却因疾病不幸离世,留下了自己的父母……以及深情枯等三十年的恋人……”主持人用夸张的语气,故作煽情地说着,“……仿生复制体,能弥补一切不曾期望实现的遗憾,我们以基因数据与生活信息,结合拓扑算法,在缺少人格备份的情况下重塑了完整的她!”
少女走入镜头,她有些紧张,不安地看着周遭喧嚣的一切。
在她身后,一个少年也悄然出现,他双眼蕴泪,嘴角上翘,胸膛起伏,呼吸略显沉重。
“那男的也太他妈年轻了吧,这三十年是怎么保养的!”老婆靠在我身上,惊讶地说道。
“说不定别人家里特别有钱呢?现在科技这么发达,只要舍得花钱,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那也是,那个姓马的也是越活越年轻……”老婆看了会,又惊道:“不对啊,那男的怎么看起来这么像你?”
“那确实,有我一半的帅气。”我冷静地说道。
“得了吧,减减肥还能有那么点说法,现在你就是坨猪肉而已。”老婆毫不客气地说道。
小而急促的脚步声由远及近,我的女儿跳上沙发背面,扑倒在我身上,压得我有些喘不过气。
“猪肉,今晚我要吃辣椒炒肉!”她欢呼道。
“行,今晚就做辣椒炒肉……”我看老婆眼神不善,连忙补充道:“只做够你俩吃的分量,我吃素,我减肥,好了吧?”
女儿吵吵嚷嚷了好一会,忽然自己回房间画画,我这才有机会将注意力重新放回屏幕里。
在那个摇摇晃晃、模仿着手持录像机风格的镜头里,少年与少女牵着手,走向了星空与大海。他们身前幻象无人机构成的虚拟场景,虽然是假的,但以如今的技术,几乎能以假乱真,甚至出现现实中不曾有过的景象。
海面静止了,如镜子般反射点点星河,海风吹来,拂过少年与少女的发丝与衣角。她踮起脚,举起手,似乎想要抓住星辰,一时不稳,带着少年摔入了藏星的浪中。
我看着他们,他们看着对方,无忧无虑地笑着站起,然后奔跑在星空之间。
年少的梦得以成真,即便大海与星空,他与她,都只是谎言。
“辣椒炒肉没辣椒了。”我说。
“我已经负责洗碗了,你总不能还要麻烦我去买菜吧?”老婆说。
我思量了一番,郑重说道:“欣欣已经八岁了,也该学一下买菜。”
她的眼神说明她还在思考,但脑袋却已缓缓地点下。
“有道理。”她说着,笑着看我。
我们齐声笑道:“阿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