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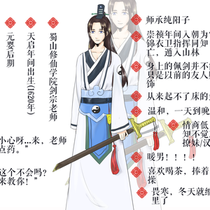


★版本持续更新中★
PET-NET社区
一款线上全息宠物社区游戏
开发商:DUOLC公司
·每个人持终端注册后可用相应设备登录,首次登录会获得一片自己的庭院及小屋,并可从五种猫、五种犬、五种鸟中选一只初始。
[后续收到意见,在初始中加入五种兔子]
·初始
猫:美国短毛猫、英国短毛猫、狸花猫、加菲猫、异国短毛猫
犬:吉娃娃、沙皮犬、巴哥犬、京巴犬、博美犬
鸟:八哥、鸳鸯、家鸽、喜鹊、白眉田鸡
兔:狮子兔、英国垂耳兔、英国安哥拉兔、多瓦夫兔、中国白兔
·宠物的动态、声音、手感和习性由高科技模拟,极度仿真,只此一家哦!(广告词是这么说,但是还是会有点不同之处吧)
·包含猫、狗、兔、鸟、鱼、宠物猪、蜥蜴、乌龟、蛇等常见宠物,如果有想增加的品种可以给公司写建议书,不久后更新的时候可能会增加哦❤
(没有虫类宠物与魔法生物)
哪怕是同一品种,每只宠物的生理参数、性格参数也都有所区别,面对玩家同样的动作可能会做出不同反应。偶尔可能会出现与品种整体性格相差很多的个体,不是bug哦!
·按照宠物习性将它们照顾得当、经常和它们玩耍的话会增加【玩家好感度】。
随着与宠物相处的时间增加会解锁相关剧情,宠物对玩家的好感度不同会解锁的剧情也有所不同。
玩家好感度越高触发【个人随机剧情】的可能性越大,随机剧情可能包括获得道具(如宠物外观、稀有道具等等)。【稀有道具可针对稀有宠物进行捕捉】
·与其他玩家互动会增加【社交度】,玩家的社交度的不同可能会触发宠物的【互动随机剧情】。社交度很高的情况下有极小概率直接带回同品种的野生宠物使其变成家养。
·宠物之间互相有【宠物好感度】,初始宠物好感度都是50%,没有生殖隔离的宠物互相之间好感度达到80%以上可以生小宠物。
宠物的相处可能会增加互相之间的好感度,也可能减低好感度,玩家可以尝试通过各种方式改变好感度增加/减少的情况。
·可以通过做【社区任务】如帮玩家/NPC购买宠物饲料、帮忙送信送水等事情赚取金币,也可以氪金,金币可用来布置庭院、装修小屋、购买宠物外观和购买各类道具。
·路上会游荡一些野生宠物,有对应道具的话可以捕捉它们。捕捉不同类型的宠物需要不同种类的道具和诱饵。
也可以直接和野生宠物中不怕生的个体玩耍,但是万一触发【被野生宠物抓伤】的剧情(概率和你现实中与这种动物玩耍被弄伤的概率相近),玩家就会进入游戏中的医院,花费一定额的金币打疫苗后才能出院。
每种野生宠物游荡的区域不同。
稀有宠物每周刷新一次,每次只刷新一只,刷新地点在一定范围内(例如A固定在某片竹林刷新,B固定在某个溶洞里刷新,C固定在某条小溪里刷新。)
除此之外还存在玩家完成【特定事项】后有一定几率获得某些宠物,如在街道上跳一段孔雀舞后有一定概率获得一只孔雀蛋,摆出神烦狗表情自拍上传到社区并获得十个以上的“赞”之后有大概率获得一只幼年柴犬。
---
因为自己要用到就把设定写一写了,欢迎能联网的任何人来进行PN上的互动www
没写到的部分可以自由地……




计字2163
-----------------
8.
海晓风在水里挣扎。
他掉进水里以后只因为冲击停了两秒,然后就往下潜了不知多深抓住徐若霖的手,接着往上游,却发现自己怎么都动不了。
澶湖他是很熟悉的了,几乎每个小学春游都会来这玩,他也来这里春游过五次——有一次没来是因为海晓晓生病了——每次都要游上半天的泳。但是现在这个湖像是黑洞夺取光线一样把他往湖底拽,暗流在水里四处搡着他。
他浑身痛得想死,手里的东西也沉得要死,坠得他几乎要沉进湖底。左手抓着枪,右手抓着人,全靠两条腿把自己往上扑腾基本是不可能的,这他也知道,可是他不想放开,也不能放开。
——那都是徐若霖委托给他的东西,还有徐若霖。
他记得徐若霖的话,带着枪去那个网咖,如果有可能,带着他。
所以,枪和徐若霖他都不能放开。
他努力仰起头,向着上面黑色的水面伸出去那只握着枪的手。
——都不能放开。
水流彻底吞没了他,他的腿失去了力气,整个人都毫无反抗地开始往湖底沉没。
好像有只手握住了他的手腕,柔软冰凉,只是箍得他发痛。
——这么拗的感觉,像晓晓似的。
这是他最后一个念头。
平玄殷用力地拖着男孩儿从水里爬了出来。
本来今晚运气不太好,既没有遇到有趣的事情也没能遇到请自己吃甜品的人类,回家路上却看到了两个有意思的家伙在单挑那群霸占了月湖很久的寒豺,而且居然赢了,虽然最后被寒豺的首领吓得拔腿就跑。她的好奇心一下就被拎起来了,暂且不论这两个还小的人类是什么来路,光是这身手她也已经有十几年没见过了。于是她便跟着他们和那头特别大个儿的寒豺一路跑到了澶湖上面的澶松崖,却正好看见大个儿寒豺把两个人类轰到了湖里。
那寒豺当真是凶得很,饶是见了几百年风雨的她也吓了一跳,在那家伙还没把注意力放到自己身上前就从山头跳了下去,哼哧哼哧地把那个还能游两下的娃娃给捞了上来。
现在把他捞上了岸,平玄殷倒是有点手足无措,到底要怎么处理这个被她救了一命的男娃娃,她救他的时候可没想到这个问题——何况现在他手里还拉着个死人,手捏得死紧,掰都掰不开。
她抬头看了看天,满天繁星已经隐去,东边开始亮起来,最黑的时候已经过去了。
“要不然,就扔到这得了?”她自言自语起来,人类看到他们所惊诧的事情时的表情一直是她最感兴趣的。
有人从她背后轻轻走了过来,衣服擦得道旁杂草沙沙作响。
“何人!”
她猛地回头,只见个小小的小姑娘停在当地,白裙子黑鞋子,一双眼水光闪闪地正看着她,好像马上就要哭出来一样。
我吓着她了?平玄殷自忖。
一双小手轻轻地拍着他的脸,暖暖的,软软的。
海晓风的脑子有点迷糊,他下意识觉得这是晓晓,可是晓晓不会这样,如果他不起床,她是绝不会从被窝里爬出来的。
然后有画面从他脑中闪过,红色的阳光,结冰的湖面,红色的星空,黑色的湖水。
海晓风稍微睁开点眼睛,灯光晃进他的眼。
——我没死?
他试着活动了活动手指,没什么障碍,但手里空空如也,枪也好,手也好,都不见了。
“徐若霖!”他一下睁开眼睛。
眼睛的聚焦有点困难,只能看清楚头上似乎是个没什么特色的圆灯,正散发着还算柔和的光,只是天花板白煞煞地刺眼。隐隐的痛感重新回到他身上,有点不真实,但很快就清晰起来,变回了那种要把他撕裂的剧痛,男孩忍不住啊地叫出声来。
“醒了。”有个男声传进他耳朵,然后一只手抓着他的肩膀把他扶了起来。那手骨肉匀停,不过力气倒是不小,他的骨骼被捏得咔吧一声,痛得他差点又背过去气。而海晓风本能地感到这人来势不善,伤口又疼得他想骂娘,于是男孩儿选择闭上眼继续装死。
然后那手又在他脸上拍了两下:“睁开眼,我知道你醒着。”
海晓风心知躲不过,只好睁开眼,努力把视线聚焦到眼前。
面前是个大概有三十岁上下的男人,一脸没睡好的表情,正坐在茶几上盯着他;旁边沙发上窝着个小小的女孩儿,一双水汪汪的眼睛上下打量着他。
“小子,名字?”男人抬了抬下巴,带着股不屑。
海晓风反应了反应才明白过来是在说自己:“啊?啊……海晓风。”
“他呢?”男人朝着地上点了点头。
“谁?”海晓风一愣。
“死人。”男人似乎有点躁,“我妹妹叫我来给你们两个收尸,看你还活着就把你弄来问话了。那个死人是谁?”
他有点麻木,顺着男人指的方向低头,看见有个人躺在那里,衣服看不出颜色,左臂从大臂中间断掉,胸口到腹部一道长长的伤口,两腿古怪地扭曲变形着,最可怕的是一杆银白的长枪从肩头一直贯穿到下腹,血已经干了,枪头上沾着暗红的痕迹。
徐若霖。
海晓风觉得他就是跟他开玩笑,就像前两天他斩钉截铁地说要他带晓晓去他家那样,现在像条死鱼那样躺着的徐若霖下一秒就应该坐起来朝他做鬼脸说吓到了吧,可是他怎么都不坐起来。
他想去晃晃他,伸出手又缩回来,不敢碰他。
“……他死了?”男孩儿讷讷地问出来。
“死了,死因是利器所致的开放性伤口和贯穿伤。”
海晓风一时间觉得脑袋发蒙,徐若霖荒腔走板的歌声好像还在他耳朵边上,现在唱歌的人却悄无声息地躺在地板上。
“喂……”
半晌他从沙发上滑下来,瘫在尸体旁边。
“……你怎么会死啊。”
昨天晚上还像指挥厨子那样指挥他。
上周还把他当猴一样的耍。
前几天还说带他出来散心。
“直接导致他死亡的,应该是这个东西。”那男人蹲在他身边,手弹了弹还扎在徐若霖身体里的那杆枪。
海晓风想起枪尖上那阵让他的速度急剧降低的阻力,他突然明白为什么徐若霖要把他甩到空中,为什么一定要比他先入水,为什么对自己说“我保证你不会摔死在湖面上”。
——从一开始,他就是那个决定要牺牲自己的人,到最后也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