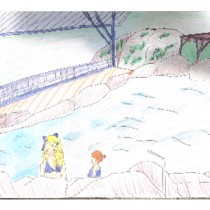



这世界上尽是些不讲道理的成年人。如果教育真像他们以为的那样容易——有没有一种简单的方法能让他们理解,其实最需要快点成长的是他们自己?
——梦幻海王
我看了看手里的绳索,又看了看白色阳伞内部涂鸦一般的文字,差一点儿就笑出了声。
绳索的末端系着比我年长的人们,像这样牵着绳索,真有种获得了生杀予夺权力的感觉。不过也只是错觉而已吧!不管是我还是这群大人,在这个游乐场里都只是神秘力量的玩物。
先前在告示牌上看到的红字仍然在脑海中鲜艳地闪烁。
成长须知:
大人都是骗子。
是暴徒。
是野兽。
是刽子手。
拴住那傲慢的脖子。
缝上花言巧语的嘴。
教给他们孩子们的道理!
我轻轻揉搓手中的绳索,摇了摇头。单凭孩子的力量,通常无法反抗对他们施以暴行的大人。如果他们侥幸成长起来,那时的反抗也绝非是孩子们的反抗。若是在这儿童乐园里,孩子们具备比成人更多的力量,就可以让大人们尝尝厉害了吧!
但是好可惜啊,我想要报复的人没有一个在这里。
那件事发生一个月后,妈妈带我去餐厅吃饭。她点了许多我喜欢吃的东西,殷勤地要我吃点这个,吃点那个。可是我只吃了一点点,就吃不下去了。
妈妈焦急地看着我:“怎么了,佑树,怎么不吃了?”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我只是在家里偷偷吃了一点零食。因为是偷偷吃的,所以我没有告诉妈妈,而是保持着一贯的笑脸说道:“只是吃饱了!谢谢妈妈,剩下的妈妈自己吃吧!”
“那怎么行呢?这可都是为你点的啊!”妈妈把奶香四溢的蛋挞递到我嘴边,笑着说,“来,佑树,啊——”
可是,我真的吃不下。妈妈见我不肯张嘴,脸色立刻沉了下来。
“是不是你爸爸跟你说了什么?是他让你不要吃我的东西的吗?”
我摇了摇头:“没有呀!”
妈妈却不肯听我说,只是一个劲儿地试图把蛋挞塞进我的嘴里:“欠款已经还上了,再也不会有人来找佑树的麻烦,妈妈也再也没有去赌过了!妈妈已经改过自新了,为什么还不肯原谅妈妈呢!为什么不肯吃?这些都是你最爱吃的东西啊,为什么,佑树!”
餐厅的服务生注意到不同寻常的状况,已经向我们这边走来。见状,我立刻一口咬住蛋挞,一边咀嚼,一边笑着对妈妈说:“妈妈,你看,我吃掉了哦!”
“那就好,那就好……”妈妈如同呓语般重复着,死死地盯着我,直到我把蛋挞吞下肚子。期间服务生询问她需不需要帮助,她似乎找回了一点儿冷静,温和地将对方打发走了。而后,她的目光紧紧黏在我身上,用温柔的语气说道:“那剩下的东西,佑树也能全部吃完吧!”
啊,好恶心。
笑着送别妈妈以后,回到家里之后,我几乎是立刻冲进了厕所。不用把手伸进喉咙里,胃部涌上的酸味早就一股脑地涌了出来,稀里哗啦地填满了马桶。那本该是我最喜欢吃的东西,明明妈妈也用心地记住了,为什么如此令人恶心呢?
爸爸不在家,阿姨也早就走了,我反复不停地按下冲水马桶的按钮,想象自己的眼泪也一起被冲走,想象着我自己也一道被冲走,在汹涌的旋涡里,即便是大声呼救,也没有任何人能听得到。
鲜明的红字浮现在我的脑海,手中攥着许许多多的绳索,就像阿娜尔姐姐系在我手腕上的气球。
我好想和爸爸妈妈一起来游乐园玩啊。
从梦幻岛回到酒店休息了一会儿,吃过午饭,大家又要出门寻找出去的办法了。竹村奶奶在大堂的沙发上睡着了,她最近精神好像不太安定,被烦心事困扰的大人都会这样的。
虽然不是很想叫醒她,但她睡得不太安稳,好像在做噩梦一样,还是叫她起来比较好。
这样想着,我轻轻摸了摸奶奶的手:“奶奶,起床啦——”
奶奶睡眼惺忪,看起来还是有些没精神。我建议奶奶回房间休息一下,但奶奶说自己没关系,而且很有精神。说着,她摆出了几个很健美的姿势,表现她现在活力四射。
但我总觉得能从这几个姿势里看到熟悉的模样。小夜子姐姐最近肯定有在奶奶面前秀肌肉吧!
最近和大家一起出门的时候,都没见到奶奶,不知道奶奶去哪里了。我问奶奶最近都去哪里了,有没有危险,奶奶说只是在乐园里逛了逛,没有遇到什么危险。鬼才信嘞!肯定是奶奶像功夫大师一样,轻轻松松地把所有危险都躲过了,所以才一点危险都没遇到吧!
“那奶奶有没有找到好玩的东西呀!”
奶奶笑了笑:“很可惜——没有什么有意思的东西。佑树想玩什么呀?如果是奶奶知道的玩具,可以试着给你做一个。”
我想了一下:“我想玩塞尔达传说旷野之息……”
班上的好几个同学都有,我也想玩,但爸爸不给我买游戏机,我只能偶尔蹭蹭其他同学的。
很显然,这超出了奶奶的知识范围。奶奶艰难地重复了一遍:“……塞尔达传说旷野之息……我、我去问问澪这个怎么做……”
奶奶真的要做啊!说实话,我真的想知道,她会做一个switch出来,还是做一个林克小人出来。但这样为难老人家并不好,我赶紧改口:“还是竹蜻蜓吧!”
奶奶不再一筹莫展,点点头说道:“噢噢,这个我知道!这个没问题——嗯……那佑树,稍微等一下哦。”
她坐电梯下楼,过了好一会儿,她拿着一个用稻草扎成的竹蜻蜓出现了。
“好耶!”我立刻欢呼了起来。我搓搓竹蜻蜓的竿,两片稻草扎成的旋翼旋转起来,像一只蜻蜓一样,扑簌簌地飞到了天上。在最高点处,它慢慢落下,最终停止旋转,掉在了地上。
我跑去把它捡了回来,又放飞了一次。奶奶慈爱地看着我:“佑树喜欢就好,我还怕现在的孩子都看不上这种手作的小玩具了……”
她还说要问问澪姐姐,“赛尔提狂野侄媳”要怎么做,做好的话再带给我。本来已经不抱期待了的我,现在反而十分想知道奶奶到时候会做出什么东西来。
趁着还没出发,我跟奶奶分享昨天在儿童乐园的见闻。
“佑树好像一直想去儿童乐园?怎么样……有趣吗?”
除去像是停尸房一样的寄存柜,会吃人的流沙还有要把大人扔进湿垃圾桶的气球小孩,儿童乐园还算是好玩吧!
但去掉这些,好像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我用一句“很好玩”越过了所有问题,又问奶奶:“奶奶觉得,大人们都是骗子吗?”
“诶?”奶奶有些吃惊地看着我,“大人都是……骗子?有谁这样告诉佑树了吗?还是说……这是佑树自己的想法?”
“因为昨天在儿童乐园看到,告示板上是这样写着的!虽然很快就变回原样了,但应该没有看错!”
奶奶摇了摇头:“……这里真的太古怪了。除了这个,告示板还说了什么别的吗?”
我装作努力回忆的样子:“还有……嗯……只记得要缝上大人的嘴了!”
因为那短短一瞬,是不足以让一个孩子记住告示板上的全部内容的,如果我说全部记得,反而会显得我有些古怪。
奶奶眯起眼睛,显然是觉得很不妙。
她摸摸我的头说:“奶奶……不觉得大人全都是骗子。不过,确实会有因为各种原因说谎的时候。不论大人还是孩子,都会有这样的时候。”
我也这么觉得。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都是一样的,有诚实的大人,也有满口谎言的大人。
奶奶看着我,很认真地对我说:“把这些……忘记吧。还有那些气球人、古怪的家伙,湖里的东西……不要去听他们说话。佑树,自己之前是怎么想的、怎么看待世界的…就一直坚持那么想就可以了。”
我点点头,却又觉得很遗憾:“要是不好的大人在这里就好了。”
奶奶愣住了。她有些迷惑地问道:“佑树希望不好的大人在这里吗?那样的话……不会更糟吗?”
但很快,她明白了我话中的意思,表情变得复杂起来。
我像往常一样笑着,说出一直以来内心所想的话:“因为……在这里死掉的话,也不会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吧?”
“死”这个字,很轻易地触碰到了奶奶柔软的神经。她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口中喃喃道:“不、不会的……不要在这里死掉……不会有事的……不该有事的……不……”
……我刚刚的说法,是否有些过分了?我赶快安慰奶奶:“没事的奶奶,不要怕,因为大家都是很好的人,所以……应该不会的吧!”
因为大家都是很好的人,所以我不会希望他们在这里死去。我只会恨那些应该付出代价的大人,只会希望拴住他们傲慢的脖子,缝上他们花言巧语的嘴,将他们寄存在柜里,假装自己忘记取出,松开手中的绳索,把他们扔进有害垃圾桶里,真可惜他们都不在这里,真的好遗憾啊!
奶奶却突然蹲下,用她那双粗糙的手抚摸我的脸颊,像是要确认什么一样,看向我的手腕和耳后。做完这些近乎仪式的动作后,她将我紧紧抱在怀里,在我的耳边说道:
“没事的,佑树,别想着那些事情了。你会好好地从这里出去的,一定只是还没有到时候而已……再等一等,再等一等。……到时候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大人,总能再见到的。”
“嗯!”我也紧紧抱住奶奶,“奶奶也不要担心,无论如何,我都会好好照顾自己的。”
奶奶的身体颤抖着,她好像一直有后悔的东西,有害怕的东西。那样的事情,很明显是小孩子不该知道的,所以,我也从没指望她会告诉我。如果我还能长成大人的话,到时候再来问奶奶,不知道是不是来得及呢?
但在这之前,还有很多很多未知的冒险在等待着我们。
拥抱片刻后,我和奶奶手牵着手,走进了门外的人群之中。
在进入游戏中心未果之后,大家又一起来到了过山车旁。
吵吵嚷嚷,热热闹闹,共计十五人一同坐上了老式木制过山车。因为想坐的人很多,我又不是非要玩这个不可,就让其他兴致高涨的游客先上去了。期间桃山和阿娜尔姐姐似乎觉得不妙,不想玩了,立刻有其他的人补上他们的位置。
就在过山车将要启动的时候,我抬头看向过山车上的标牌。那里本该是“NETOTOTO!!异界绝命疾行!”的牌子,现在只剩下几个不祥的字符:
“N、O、命、疾行”。
现在无论说什么,都已经太迟了。过山车吱吱呀呀,缓慢地爬上最高点,像是随时都会散架一般。爸爸曾经告诉过我,过山车的运行原理就是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爬得越高,飞驰而下的速度就越快。看着那似乎比太阳还要高的过山车,我总觉得一阵目眩——从如此高空跌落的话,绝对会死的。
车子在最高点停了下来,但仅仅片刻,吱吱呀呀的响声就和乘客们的尖叫声一同响起,过山车以近乎狂热的速度冲过第一个大回环,一头扎进了水中,又极快地冲破湖面,旋转着冲向天空——
没乘上过山车的乘客乱成一团。阿娜尔姐姐立刻蒙住了我的眼睛,不让我看到发生了什么,但从她的指缝里,我仍然看到了过山车在空中停滞的那一瞬间。
似乎是注意到我仍在偷看,阿娜尔姐姐将我的身体也转到另一个方向。
但我理应知道它,以及他们的命运。
我想起高高飞到空中的竹蜻蜓。明明飞得那么高,那么远,最后却总要落地。
在我的背后,载着十五名乘客的过山车,就像竹蜻蜓那般,迎来了他们的命运。








我写 我写.jpg
字数:3781
请看,自私的爱人者:D
+++
阿娜尔 又一次 临阵脱逃。
+++
爱情啊!爱情!能够凭自身的意志为爱而死是最美妙的事了,如有情人相殉,又是天堂一般。普通人们希望他们的爱人能守节、这是因为他们没有权利、不能像帝王那样直白地要求她们和他一起去死。
阿娜尔不止一次有机会拥有这特权——她的前恋人中、有那么两三个是愿意陪伴她下地狱的。天啊!可是当机会摆在面前,阿娜尔总是选择逃跑!
有那么一回,他们坐在湖中央的小舟里。
船底破了一个洞,对,就和安卡太阳穴那儿的一样,都是要命的地方。安卡尚且柔软的身体歪倒着,半边都在水里,两只眼睛透过柔软的发丝,都直勾勾地看着阿娜尔。湖水洗掉了他的血,他依旧是那个英俊的足球队后卫。他粗鲁、轻率、大脑空空,总是打断阿娜尔的话题——就为了问她在哪儿能找到他的破烂足球——而死亡洗掉了他所有的缺点,留下的是一具优美的、静谧的、眷恋地注视她的外壳。
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个恋人!
直到湖水能够托起阿娜尔的裙子,她仍捧着他的脸颊,爱怜地吻他纤密的睫毛、他丰盈的嘴唇,她撬开他不算整齐的牙齿,从他的口腔里汲取了最后的温暖。
直到这一刻,她都是甘愿和安卡一起殉情的,就像他们原本说好的那样。
……可安卡的尸体突然开始低沉地呻吟并吐出味道极其恶心的气体——就像是实在憋不住的呕吐物,还混着明显的腥味儿。
没人受得了这个!至少阿娜尔没能忍住。她猛地推开安卡,早餐的残骸泛上她的胃、烧着她的喉管……一路掉到足球队后卫的头发里,让她想起他曾喝得烂醉如泥时的样子。
啊,当然,即使在那一刻她也爱着可怜的安卡!呕吐物可阻挡不了爱情。
……只是,这份爱,随着安卡停止的呼吸一起消逝了一点点。
——它不再是平等的了。
阿娜尔挣扎起来。她咬、她掰!草绳勒着她的皮肤,不愿放她走,可最终她抛掉它、游回了岸边。她伤感地在岸边坐了会儿,发现自己的手机还在船上,它和她的前恋人连同快散架的小船一起彻底沉掉了。
【我还爱着安卡呢】
是的,是的,当阿娜尔在麦田换上救生衣的时候,理所当然地想起了前锋……嗯……他好像是打棒球的?棒球有前锋吗?哦算了这不重要,重点是她还好好地记得他。
带着幽幽划船的时候,阿娜尔试着将自己代入了安卡的位置。她摇着船桨,感受着它是如何推开那些缠结的稻草,柔和地看着这个年幼的姑娘:哎呀哎呀、我当时也是那么可爱地晃着腿吗?我有好奇地去看水面下的游鱼吗?她看上去有点害怕……是的,是的,那时候我们也处于危险中哪!虽然是自找的那样一条船,但我们也不曾离开它、直接跳到水里去。
她琢磨得十分认真,将这段宝贵的时间完全献给了死去的安卡。直到她的桨被勾住,扯出一截胳膊来。安卡?是安卡吗?阿娜尔险些这么叫了出来,而她的胳膊向外伸展,手掌正放松,准备马上执行潜意识的指令——把这东西丢下去!连桨一起丢得越远越好!
可幽幽也发现了它,好奇地看向那条稻草做的胳膊,问她:“姐姐,它穿着衣服呢!我们能把它带回去吗?整个儿带走。”
阿娜尔立刻清醒了:这可能是一条线索。于是她尽量小心地把桨收回来,可双手却发着抖。
上帝、她想,万能的上帝……
啊,她到底要祈求将他完整地带回来、还是祈求他真的和那些稻草连在一起呢?
阿娜尔不是个忠实的信徒,无法分辨上帝是否保佑了她。总之,稻草人的手毛糙糙地张着,像等着谁把它拉起来。但它的手臂断开了,整个被湖底的稻田扯了回去。最后那根胳膊无力地跟着桨被挥动了几下,也沉回了水里去。
阿娜尔在它完全沉没前拍下一张照片。它看上去……像极了人类,甚至拥有类人的立体五官,她抚摸了它好几遍,从记忆里把她的安卡的脸拽出来,反复确认那不是他。
小舟就在这段时间里漂到了湖心岛边,其他人也遥遥划船来了。坐在一起的幽幽穿着救生服,问她“姐姐,我们去岛上看一看吧?”
离开这条船、到陆地上?听起来不错,但阿娜尔迈不动腿。稻草,和稻草,这地方铺满稻草,和湖面上并没有两样,就好像他们还没有离开那片如榕树般纠结的区域。
“不,”阿娜尔说,“也许我们该留下一个人看船,万一它漂走了,我们可就回不去啦。”
于是小姑娘一个人向岸上迈步——也就差那么几十公分——没有尖叫、没有挣扎,她匪夷所思地沉入了湖心岛与船之前的短短距离。阿娜尔立刻趴到船舷去抓她的手,可她抓了空。这地方像片沼泽,一下就把小孩子完全吞下去了。
【我的天,得下去找她吗?】
阿娜尔因这想法险些哭了出来(她这时忘记自己估计过要救一个半人才能去天堂的事儿了)
她把桨伸到幽幽沉下去的地方,做了几个呼吸的心理准备,可能五秒,可能十秒,反正也没太久——结果幽幽从另一侧水域又冒出来了。除了身上湿漉漉的,她看起来一切正常,还活泼地对她笑:“阿娜尔姐姐!救生衣把我托上来了!”
阿娜尔并未因此感到慰藉。
她刚参透了一件事:要是我掉下了船,安卡不会救我,只会扯着我一起沉得更彻底,对,就像那些稻草人会做的那样。
她甚至恼怒起来了:如果我那时候又想活了呢?天,他根本没有那么爱我吧!
回到岸边,阿娜尔立刻找了叫万象一元的那个博主说话——她花了一整天琢磨要和谁坠入爱河,好在去地狱或天堂的路上有一只手可以牵——啊,最好是离开这个古怪游乐园之后还能一起玩几天啦。
那就要找一个居住在日本的人了。
白沢玉是个看起来可靠又认真,这是很可靠的,她喜欢听这些人说他们擅长的东西;而万象一元的轻快和松弛也很让人着迷,人总是得吃点甜的。
……是的,阿娜尔得吃点甜的。于是她选择找万象闲聊。
——嗨嗨,我能不能叫你一元君?
——我们来交换新情报吧,一元君?
她绕她精心打理过的发梢、向他发送带着酒窝的微笑,就像一天前向岛田做的那样。她惊喜地发现他们有合得来的地方:比如觉得沉在水里、完全缠在一起的稻草人很可怜啦(确切的说,万象一元觉得那很恶心,不过在阿娜尔看来,让人觉得“恶心”本就是一件非常值得可怜的事情了),觉得以身涉险不是什么聪明的做法啦……他们甚至还聊了《绿野仙踪》和画龙点睛的典故。
“话又说回来啊,要是能够阻止'点睛’,一元先生会想做吗?”阿娜尔问,“Neto没有眼睛,点上的话,说不定会变成什么神呢。”
“如果危及生命的话还是要保护一下自己的吧!如果什么事儿都不会发生,就随他去。”万象一元说。
是啊,是啊,保护好自己。
是啊,是啊,只要 保护好自己。
+++
阿娜尔站在过山车边。
佑树君不打算坐过山车,而白沢玉打算试一试,于是几分钟前,自觉已经找到安全规则的阿娜尔也跟在了白沢玉身后,看准机会坐到他身边。
她对于这老旧的游乐设备当然有担心,连心脏也轻微地在发麻。可短暂的思考过后,白沢玉一点也不犹豫地往前走。偷偷打量他,觉得这个东方人的身姿好看极了,指甲剪得很干净、眼神锐利得令人心动。他的神情总是严肃,让她想逗他露出其它表情,看他笑、看他哭……哎呀,和心仪的人意外殉情,这不是也很浪漫吗?如果这辆车出了什么问题,这个年轻的日本人会绅士地护住她吗?
阿娜尔想入非非。她要捂住自己的脸,才能叫白沢玉不看到那过分快乐的微笑。周围的人商量着要坐哪儿,可她不用考虑啦!他在哪儿,她就在哪儿……
她这么考虑着,想要撒娇请白沢帮她搭上安全栓。可就在要说出口时,那麻痹感像蜈蚣一样,迅速从心脏攀上了她的后颈,放在衣服内袋的仙女棒也“嗤”地自燃。她的直觉叫嚣着危险,可理性根本不知危险在何处。
因为不安而逃跑?这太蠢了!
阿娜尔试着忍耐逃走的冲动,可是那战栗根本无从抗拒。当听到桃山的声音时,她再也按捺不住地从座位上跳了起来。
白沢玉疑惑地看了她一眼,阿娜尔咬住嘴唇:“哦,我觉得最好还是别……”
天啊,【我的仙女棒自燃了我觉得这过山车不安全——】这理由也太愚蠢了!
她试着找到别的借口,对,她是那么聪慧,很快就找到它了:“玉君,你记得那块倒下的维修标牌吗……!这附近没有Neto玩偶,如果是有什么把它推倒了呢?我们还是先去其它地方看看吧?!”
她近乎央求地看着白沢玉。他一定意识到她的不安并非空穴来风,可他只是安静地说:“我们在上来前就知道它倒下了,不是吗?”
……他不打算走。
他要涉险看到底这是怎么回事儿,就像车上的所有人一样。
阿娜尔,阿娜尔,他是多么有担当!多么令人心折啊!你更喜欢他一点了不是吗?你不要和你心仪的人共同冒险吗?你们之间一定会有更深的羁绊……
“不、我、我还是……”阿娜尔讷讷地摇着头后退。
什么殉情!什么心仪!在生命面前,它们都不值一提。眼泪几乎要溢出阿娜尔的眼眶了,但不是因为难堪,只是出于对未知的恐惧。
她寻找着同盟,可除了桃山以外,再没有第二个人决定要离开座位。大家都紧张地等待着项目开始,也有人好奇地向她们张望。她们空出的位置很快被似乎相识的两个青年男女填补,所有人都在检查自己的安全设备,白沢玉也不再理会她了。她面色惨白地站在过山车边,格格不入,像一个幽魂。
阿娜尔冲下台阶。
佑树君在竹村奶奶身边,他们相互守着。阿娜尔想要跑去万象一元身边——他是一定会理解的!人们要优先保护好自己的生命,她做的和他想的一样,他一定可以安慰她。
……可远远地,她看见万象一元的脸。
平和地,放松地,与己无关地。在小小的争执和骚动后、在过山车启动的噪声中,在人们的惊叫之中。他悠闲地拿着记事本,像在悠闲的午后品鉴一部文艺电影一样看着那部小小的车。
无关结果,只是打发时间。
阿娜尔慢下脚步、移开视线,她换了方向往佑树那里走,他正担忧地仰着头……如果遇到什么可怕的事,他一定会吓到的!他们该别开头,就像万象一元那样,将那些可怕的事当作和自己无关的东西。
可——阿娜尔回头看一眼那辆正往高处冲去的车,想,我差点也在那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