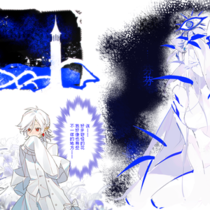








曾经,有一位少女。
拥有天赋之才的少女,在十分年幼时就绽放出了惊人的光芒。
无论是多么苛刻的评论家,在看过她的演出,听过她的歌声后,都无法吐出一句批评的话语。
可是这样的少女,却有着无比害怕的东西。
不是过于轻松的星途,不是已经注定的未来,不是终将到来的结束。
少女害怕的,只有一件事。
那就是孤独。
于是,在那个午后,少女撒了谎。
对着她最为亲密的挚友,少女伸出了劝诱的手。
明知她或许会选择其他的道路,明知她或许会过上不同的人生,明知她或许会更加幸福……
少女还是选择把她拉进了自己的世界。
只是为了让自己不再孤身一人。
可是少女的赌注仍旧落空了。
她选择的挚友虽然努力追赶着自己的步伐,却仍旧只能散发出微弱的光。
少女只要稍微动动真格,再度转身,便无法寻见挚友的影子。
对挚友做出了那样残酷的事,少女,却仍旧是孤身一人。
无法忍受孤独的冰冷,无法背负罪恶感的重压。
少女选择了逃走。
没有一句解释,少女的身影便从挚友身边消失了。
少女来到了遥远的汪洋彼岸,试图在那里寻找自己的栖身之地。
也试图在这片更为广阔的天地,寻找能让自己不再孤独的对手。
然而,少女还是没有找到。
无论走到哪里,少女始终是孤身一人。
于是,在那光芒万丈的射灯之下。
少女从自己最为绚烂的舞台上,一跃而下。
……………………
“是吗?原来我,没能拯救你啊……”
在倾塌的世界间,真音仰望着冰冷的太阳。
“对不起,明理。我没能遵守约定,和你一起成为最闪耀的明星。”
“但是,我不会再让你孤身一人了。”
向着广阔的天空,向着无尽的世界,少女全力跃起。
然后……

两封信都已经被拆开,并翻来覆去地打量过。深雪与白鸟对视一眼,暂时排除了恶作剧的嫌疑。她们曾经见过那个地下舞台,也清楚想要获取什么必然要付出代价。如果这是一场赌博,那么她们的闪耀,她们的希望、她们未来的可能,已经被尽数压上牌桌。赢家通吃,败者一无所获。
但是,为什么舞台为我选择的对手是你?
疑问萦绕在她们的对视间,但两名少女都谨慎地没有开口。她们并肩而行,却各自乘着电梯下坠,在机器的轰鸣中身披闪耀的礼服,再朝着灯光迈出一步。
天鹅羽毛的头饰。高马尾。墨蓝与灿金。时钟形状的腰带扣。三枚长短不一的羽毛坠子。把一只苹果切成两半,也不会比现在的她们更像;少女们看向对方,宛如镜面中映照的自己。只不过,泪痣的位置提醒她们,这并不是自己的影像。
两柄胁差相交,刀刃摩擦出吱呀的响声。就连武器也完全一样。
深雪的语气中没有惊异,只是感叹:“原来你也想梳高马尾啊。”
不知为何,白鸟从她的话中听出了自己需要辩解的东西:“——我觉得它更适合你。”
“不,那不符合我的角色。在你身边的女仆,不应该有太多自己的性格。”
这不是白鸟想要听到的话。她皱了皱眉,试图改变深雪的想法:“你又在说这些了。我一直把你当作我的朋友,我的姐妹,我的半身。”
如果一次不行,她就一直一直说下去。白鸟有自己的执拗之处。然而,深雪只是摇了摇头。
“是你一直在做梦。有个和你一样的人真的好吗?”
两人之间立起一道玻璃,白鸟如何抬起手,深雪便会如何转动手腕,不迟不快,正好如同镜子一般。白鸟将胁差砍向镜子,却宛如切进一片平滑的水面,轻而易举地深深没入;她看到刀尖从同一个位置穿了出来,正好抵住她的纽扣。她茫然甚至于惊慌地收手,深雪同样退后一步,将下半句话说了出来:
“你知道吗,我不是你的半身——是你的替身。”
“……什么?”
灯台忽然一转,白鸟下意识地抬手挡住那刺眼的白光,却见它照向拉开的幕布后,宛如默片般的黑白画面。这一幕是深雪与渊上夫人,对坐于一间无窗的小室内,桌上只燃着一根蜡烛。
夫人的字幕打了出来:“入净土”的仪式,你都准备好了吗?
深雪只是点了点头,回答:是的。
这是……什么?白鸟惊愕地朝那段一无所知的过去走出一步,忽有凉水从头顶落下,浇遍她的全身,湿透的衣服沉沉地坠落地面,水膜化作一身轻薄的素装。她面前出现了一座长桥,尽头屹立着一座白山。
“生清已毕,当拜见无明桥。”
听到幕后传来的深雪的声音,白鸟仿佛追问,又仿佛自言自语:“是那个……现世与黄泉之路?”
这次没有人回答她。但她知道,三途河宽八万余丈,深八万余丈,上之急流有青赤白黑黄五色鬼,中有千丈利剑沉浮流动,二十寻毒蛇;下有老鹰乌鸦等待捕食。她脚下的桥以黑金、黄金、白金架设,然而放在这一片望不到头的河上,比一把刀的锋刃还要细。
白鸟远远地看过去,在桥的尽头,有一个白色的身影。与天,与水,与山,与亡灵同色。她踏上一步,奔流不息的河水如同哀哭。无所依凭仅是苍茫的天空与千万年间并无丝毫动摇的山岳一同发出质问。
“汝在尘世时,是否修善根布施?是否在高处建寺庙,在低处建宝塔?知否在大河泛舟,在小河架桥?是否为饥者施以食物,为寒者施以麻衣?是否施就、施饭、施杖?”
白鸟回答:“我一切施舍和善根都没有。但是往昔千石千贯、中期百石百贯、近期十石十贯向神社寺院捐献,也举办大神乐,每日奉养千人。”
“拿出你的证据。”
“由四花的花瓣、十六花的花瓣、三十六花的花瓣、四十六花的花瓣、五十六花的花瓣、六十六花的花瓣、七叶八瓣九品的净土花瓣作为贴身的护身符,我才能来到这里。这就是证据。”听了她的陈述,那白影翻出琉璃镜一照,花瓣竟然片片飞散,黯淡失色。
渊上白鸟是个善良的人,这并非虚言。她会攒下钱来布施,也乐意为人扶门或撑伞;然而,她没有那种机会。出门的时候,总有一个或几个仆人跟随,而她拿去给父母、要捐赠的钱物,也不会真的被送到需要的人手中。
而对白鸟来说,意识到的事情只有一件:入净土者,过无明桥者,扮演的角色均为亡灵。而这是现实中发生过的事情。
“深雪,”她的喉头发紧,声音被风吹得散了,竟有些像哭声,“你替我去大神乐了吗?”
呼啸的狂风卷起她,将她从白山的入口抛了进去。白鸟看到了一排长桌,其上供奉的米饭茶水是什么,她已经知悉了。这是枕饭,也称份饭,葬礼时用于供奉死者。入净土者要把这茶饭吃下,以示自己身为亡灵。
“所以我的病才会好起来。”白鸟喃喃自语,“即使你不做这些——不,即使他们不让你去,我也一样不会有事的。”
持板斧的五色鬼从白山的四面跳入,环绕着白鸟跳起舞来。白鸟仔细地分辨着,没从那些面具下发现她熟悉的那双眼睛。然而,那个白色的幽影再度出现了。它首先从东方的入口跳入,从西方的出口跳出,又从南方的入口跳入,从北方的入口跳出,最后挥出两刀、划下一个巨大的叉,山顶受了这样的重伤,从裂口处洒下纷纷的纸屑来,飘飞之态有如落雪。
白山被冲破,仪式就结束了。所有的乐音都停了下来,仿佛视线完全被吸住了一样,白鸟久久地盯着那白色的身影,看着她在山间穿行、看着她顺势落地扯开白纱、看着她向自己冲来,看着她如同云雾般的青色发尾、她透彻而毫无杂质的红色双瞳、她斩落自己纽扣的银色刀刃。
深雪。深雪啊。
纽扣落地,白鸟却丝毫没意识到似的,一直抬着头看向深雪,唇角慢慢地勾起一丝笑容。
“我想看的就是这样的你。拿走我的闪耀,然后发光吧,就像我也能发光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