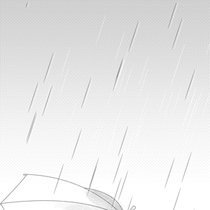占卜师明显不愿再过多地提起自己与夏绿书的过去,或是给出更多的线索。也许这是占卜师们的通病,他们在根本上有着与吟游诗人相通的地方:对命运的推崇或说是过度的迷信,对诗意语言的偏爱,对捉摸不定、如云如雾的东西的欣赏。也就是说,除去那条“去西花园”,冒险者们不会再从塞西尔那里得到其他什么。
雪精灵倒觉得这样挺好,比起操纵语言,在与人的交谈中获得信息,她更偏好、也更擅长行动,与占卜师的对话让她不快乐,虽说她也一直不快乐,但那种失去什么的氛围还是会产生影响,细雨一样将沉郁洒在她身上,淋得她湿漉漉、身上沉甸甸。他们与塞西尔告别,从藏身的那栋楼走出,沿着道路往西花园,也就是拉文-坎前进。
正是他们低头走路的时候,天空中细细碎碎地传来一阵声音,像是什么东西在咬着钢铁,也像是不安的潮声,黑色的海浪卷着雪白的泡沫张开嘴,然后这无边无际的怪兽喉咙里就窜出来什么东西,也许是海蛇,也许是丑陋的鱼,总之不会让人安心。加莉娜没去过海边,也就不觉得这一阵阵由远至近的鸣声像海潮,只觉得它吵闹并且不合时宜。伴随着声音出现的是天空中交替闪烁的红色光线,那也许和之前自己裂开的门、亮起的灯一样是某种魔法,否则它怎么能将光线散发得那么远?年轻的巡林客对世事的了解还远不够多,在她有限的经理和知识中,只有点起的狼烟能在较远的地方被人看见,那是远在加莉娜存在之前,深林城的雪白色的城墙刚被垒起的时候,为了应对北方的威胁,雪精灵们用大理石建造出深林城高高的围墙,而在于那些讨厌的非人生物或其他什么斗争的时候,狼烟就承载起传递消息的作用。那么这红色的光芒是否和狼烟一样,代表着某种警示,是入侵或战斗将要打响的前兆?加莉娜并不明白,她甚至还想着:红色的光,也许是这奇怪的城市在长明灯外罩上一层红色的薄纸,毕竟这里的人审美不太好的样子……不管怎么说,也算看过妈妈年轻时看到过的风景啦!
“临时天气预报——一分钟内将会降雨,请各位注意回避。”
是夏绿书的声音。
加莉娜抬头看了眼天空,受到周围建筑物发出的奇异光芒的影响,她并不能通过天空来判断接下来的天气:“雨竟然需要回避?”
她的话相当能体现雪精灵的某种特质。在深林城的雪精灵中流行着这样一种不成文的习惯,满一周岁的婴儿会在冬天由父母带到室外或推或抱地淋雪,等到他们能跑会跳能进行游戏,则会在成年长辈的看顾下用冰水浇遍全身,然后排着队跳进冰湖,只有完成这种古怪的仪式,他们才算是合格的雪精灵儿童。目前有不少其他种族的雪城居民也加入这项活动,或许这就是深林城的独特民风。
“听起来有些危险,”尼格勒说,“也许我们应该找个屋檐避雨。”
他说得很对。
于是冒险者们就近窜进旁边临街店铺的屋檐,它的玻璃门外是闪着白光的招牌,上面写着雪精灵无法理解的词汇。不一会儿,预报中的雨就淅淅沥沥地下起来,伴着雨声落下的是一些小型器械,它们在雨幕中维持着一个较低的高度,机身上突起的圆形探头缓慢地旋转一周,似乎是在寻找什么。在它们搜寻到自己所在的地点之前,冒险者们就闪进自动裂开的玻璃门里,躲在一排横着的货架之后。小型机械的飞翼声从左到右,又从右到左,在确认蜂鸣一般的声音不会再出现后,他们才从货架后走出,带着好奇与警惕打量这个临时的藏身之地。
天花板上有规律地排布着长条状的玻璃柱,将整间店铺照亮的白色光芒就是从这里发出的;货架三横两竖地摆放,三横间距相等,两竖分别贴着店铺两边的墙,货架由一层层的铁架子构成,上面摆放着许多奇怪的东西;这里没有店员,倒是有个柜台一样的地方,桌面上放着个有些像首饰盒的装置,不知道是拿来做什么的。靠街的两排货架上摆着包装奇怪的商品,不明材质的柔软贴片包裹住一团气,加莉娜拿起一包摇晃几下,其中传来零散事物相碰的声响,她凑向货架看说明,小纸片上印着“薯片”字样。雪精灵盯着那包东西看了片刻,没有任何心理负担地拿着这包东西走到门外屋檐下,将其丢进雨里。
雨水“滴滴答答”地落下,声音不断向外扩散,倒也不是雨滴拍在铁片上的声音,加莉娜观察过后,只能得出“薯片”外包装不是铁的结论。在发现这样的试探没法测出这场雨是否能对物体造成损害后,雪精灵没什么所谓地伸手作出一个接雨的动作,让手掌和手腕露在雨中。她的手触碰到雨水,液体是符合常识的冰凉,一下子就从巡林客的指尖上滑过去坠向地面,只留下些许蜿蜒的水痕。加莉娜将手收回,她反复握拳感受,又搓搓手指,雨水沾过的地方留下一些粘稠的质感,让人想起蜗牛爬行过后留下的透明粘液,最后,她又把手指凑到鼻尖,雪精灵抽抽鼻子,闻到一股淡淡的味道,她说不上那是什么,可这些信息已经足够让她作出判断。
加莉娜回到商店,甩着手走到货架旁对队友说:“我想最好不要淋到外面的东西。”
尼格勒点点头,说:“我们可以找把伞。”
翼族少年正站在“两竖”中离店门口更远的那个前,这排货架与那三排横着摆放的有少许不同:它更多由玻璃组成,每排玻璃上都摆着包装成组的商品,那都是些透明玻璃管,里面装着清澈的液体,五颜六色,十分鲜艳,货架前头包裹在透明物质里的小纸片上写着“最新口味营养剂上市!多种口味,带你体验四季!”。出于好奇,加莉娜忍不住伸手摸了一把,冰冰凉凉的,十分舒服。
卡尔在靠近玻璃门的柜台旁找到几把长柄伞,莉莉在旁边的货架上找到包在奇怪包装里的防水斗篷(包装上写着雨衣),在经过一阵“是否该付钱”“拿什么付钱”“我看你羽毛不错”——这话来自加莉娜——的讨论后,他们拿着这些东西离开便利店。雪精灵套着斗篷打着伞,心情愉快,她透过透明的伞面看向天空,差点做出转伞的傻事。之前那场不会带来任何损伤的言语争锋被她视作小小的胜利,这让她保持住短时期内的心情愉快,此种轻快犹如不承载任何负担随着气流东奔西跳的肥皂泡,在上升的同时也在被消耗,最终“啪”一下破裂,垂下几滴欢乐过后的泪水。但此刻加莉娜是快乐的,她又故意落在最后,踩着路面上不那么平整的地方汇集的浅水洼,抬头看混杂着不明物质的雨水拍打在伞面上,水渍在路边铁杆子上圆球的照射下折出七彩的光,这副景象足以说明钢铁都市的雨水的确蕴含着危险,而雪精灵却觉得它看起来像一条被巨人拧弯的彩虹。
他们出发向西花园。
卡尔走在前头,在进入到这个古怪的梦中世界之前,外出游历的工匠学徒正巧停留在菲薇艾诺,出于性格,拉文-坎是他乐意去的地方,太阳暖融融地照在身上,轻风送来花香……或者找棵树靠着,在凉爽的树荫下看看天空草木,也能渡过一段相当不错的时光。现在的菲薇艾诺显然不能带来这样的惬意,不知由什么构成的雨水啪嗒啪嗒地落在身边,空气潮湿又粘稠,就像某种即将凝固的胶质,而行人则是不幸被困的可怜虫。
“注意天上。”加莉娜说。
在出声提醒之前,雪精灵就已经将自己藏在路边一条巷子里,两道高墙切出狭窄的空间,周围没有光照,一个能躲避小型飞行器械的地方。翼族和侏儒也随着闪身,他们贴墙站立,片刻后,一个方方正正的盒子飞过,盒子上方插着高速旋转的铁叶片,盒子前还有个突起的半球型玻璃片。等这东西飞过,他们再次站到笔直宽阔的路上,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在到达目的地之前,这样的“捉迷藏”还会进行很多次。
突然,像是察觉到什么一样,加莉娜环顾四周,指望找到点值得怀疑的东西。城市里的居民似乎对夏绿书的预报很信任,或者说他们习惯于听从夏绿书的指示过生活,所以街上没有其他闲逛的人,之前的飞行器械也已经转去另一条道路,不再可能对他们投以注视,可那中“有人看着”的感觉始终跟随,从便利店开始,直到现在。最终,一无所获的巡林客皱着眉头离开,没有看到墙角上那个闪着红光的机械,就像是眼睛。
不知过了多久,他们终于走到一片开阔地,钢铁制的路牌上用通用语写着:西公园。
眼前的公园没有任何母亲描述过的样子,在德鲁伊的话语里,这里在春之女神和大地之母的庇护下总是葱葱郁郁,不同层次的绿色铺展开,整个花园像堆满了碧玺、绿柱石、祖母绿和绿玛瑙;纯净的水流分出舞台与观众席,银月诗会就在这天然的露天剧场举行。母亲的话语是多么温柔,她尽力为自己的孩子描述出世间美好的样子,在她心中留下善意与希望……她怎么会想到加莉娜有一天将看到这样的拉文-坎呢?绿色全没了,曾经为植物输送养分供它们生长的土壤似乎被抽取生命力,给人一种死人脸般的灰白感觉,还带着久病的枯槁。刺穿泥土的是一支支绿色的分叉金属,像一只只濒死的手伸向天空。尽管心里明白这些东西大概跟路上那些挂着灯的铁杆子一样,是被造好之后竖起来的,加莉娜还是不可避免地认为这些绿色金属如同白天造访过的“眼珠”酒吧里那些藤蔓一样,生长自地底某个不可言说的诡异生物。
雨还在下,也许今夜不会停止。水滴拍在地面的声音逐渐变了样子,这些声音先是有了节奏——沙沙沙,沙沙沙——让人想起吞食海岸线的潮水,散发着难闻腥味的咸水涌上来,击打岸边的巨大石块,潮水声发起狂来,嘶吼着。近了,近了,那艘载满疯子的脆弱木舟在天空中眼睛的注视下驶向不可为人所知的远方,夹杂着哭与笑的吟咏却越发清晰,那些合该被诅咒的舌头说出这样的字句:
“呼啊!呼啊!西罕诺!伶伶!莱伊亚!”
“西罕诺!伶伶!莱伊亚!”
随着呼喊,钢铁森林醒过来,犹如迎接晨光的苏利文,那些伸向天空的手抖动着,舒展着。它们在寻求什么?莫非天上也挂着一个钢铁月亮,还是过于庞大的痛苦或疯狂逼得它们抛掉理智,只能哭喊去寻求什么东西的首肯,以得来一个解脱?这实在不应该,钢铁没有生命,也许一部分工匠有着对自己事业的浪漫理解,可不,没有生命的造物活不过来。人们也许会对壮美的建筑产生敬意,那敬意是为着完成这庞大工程的人;人们可能被纤细优美的设计夺去心神,也是庞大的信息流自上而下冲刷;诗人献上赞美,为其中曾经发生、可能发生的故事……它应该是死的。人不能像对待有生命的活物一样去对待它。
加莉娜一阵恍惚,四周太过安静,只有雨声,幕帘似地将她隔绝,潮水说秘密似地在她耳边低语。悬挂在绿色枝条上的手摇摇摆摆,笑吟吟的,对待同伴一样热情:“快来”“与我们融为一体”“很舒服很舒服”“来吧”。雪精灵像被温暖的水浸泡,她感到久违的轻盈,能飞鸟一样越过苦难与风暴,去往与逝汀里尔不同的应允之地。
西罕诺,伶伶,莱伊亚。
雪精灵抬头,看到一棵树的枝条末端挂着灯,灯中闪烁出奇异的光芒,“眼珠”酒吧里的藤蔓似的,那东西眨眨眼睛。
加莉娜想吐。
“加莉娜?”
翼族少年发现队友的不对劲,他的呼唤敲破之前裹在她身上的那层厚重粘液,一阵微风吹过,四周的空气似乎变得洁净起来。巡林客小跑几步,跟上停下脚步的队友们,出于自尊,她没有说出自己停下的原因,不想被认为是一个连雨声也禁不住的多愁善感的可怜虫。雪精灵板着一张脸,硬邦邦地说:“走吧。”
路上他们经过几张长椅,广场上常见那种,带靠背,两边是扶手。长椅似乎只在灯下出现,带着金属色泽的灯光照在长椅上,现出蜷在椅子上的那团东西,是人。短暂的一瞥足以让加莉娜看清他们脸上的表情,似梦似醒,在欢愉的边缘挣扎,伸出手想抓紧,却什么也留不住。这副样子在深林城很常见,这座较菲薇艾诺受到更多世俗困扰的城市位于寒林中的城市紧邻苏利文山脉下的雪原,冬季尤其不好过,雪城中的人们得准备足够的越冬物资,食物、柴薪、日用品……寒冷首先让身体僵硬,一些物资不足够的人会拿酒精代替炉火,让自己暖和起来,不至于在冷意带来的睡意中离去。或者玉米酒吧里那些生活不如意的人、想要暂时摆脱什么的人,酒精麻痹神经,也能带来虚幻的解脱。梦总会醒,温暖快乐的永宁乡并不挽留迷途的旅人,冰冷的现实世界刀子似的剜下美好图景,不愿面对的高墙从遮蔽双眼的雾中显露身躯——就是这样的表情。
梦是人对现实撒的谎,沉溺于梦境能做成什么事呢?加莉娜实在看不起这样的人。
看看酒馆里的那些人吧,让来自不知什么地方的管子刺破皮肤,将自己连接在另一个生物身上,如同挂在林梢的蛹;公园长椅上的那些或坐或躺的也一样,精神仍在寻求安慰,想要挣脱扎根于物质世界的躯体,正在蜕壳的昆虫一样撕裂己身,然后回归土地,成为下一个循环的养料。我不会这样,雪精灵对自己说,我不会这样软弱,我会完成必须要做的事,用血肉滋养哀伤之火,用必死之人的尸体燃起复仇的柴薪,他们的灵魂将在永冻地狱徘徊,任由野兽撕咬,冰霜覆盖——这是复仇女神给予的权利。
我发誓。
他们很快来到一个路口,有两三条岔路向深处蜿蜒,前面的路牌同样用通用语标明地点:喷泉广场、绘画街、乌拉尼亚雕像。卡尔站在路标下回头望,在一片烟雨朦胧间看到神殿区的轮廓,只要拿到“书”,他们就能拥有回到自己世界的钥匙。
“……哪里可能有书?”加莉娜问,她的语气依旧不好,现在又多出些许急切。
尼格勒沉默一会儿,说:“也许我们可以去乌拉尼亚的雕像那里看看。”
出乎意料的,雪精灵点点头,对翼族法师的意见表示赞同:“毕竟他改变了历史。”
莉莉和卡尔没有其他意见,他们沿着标识指出的乌拉尼亚雕像的路上走去。公园里的道路不如之前走过的宽敞,只比供旅人行走的林间小道宽一点,环境却比真正的树林差太多,许许多多铁做的木头围绕在身边,这里的人用假的代替真的,还要为它鼓掌叫好。远处似乎有音乐,雨音干扰旋律的传递,他们并不能清楚地听见乐音,雪精灵只能感觉出这并不是她熟知的节奏与调子。蜿蜒的道路并不长,冒险者们很快就走到道路的尽头,那里又是一片较为开阔的地带,环绕在四周的、叫人厌烦的铁林木被叫人厌烦的白色路灯替代,空地的中间立着一个巨大的铜像,大概有3至4米高,从长而尖的耳朵和颧骨来看,这显然是一位精灵的塑像。
塑像正前方的铜基座上刻有他的名字:乌拉尼亚·凯法塔夏。
“嗯……好高啊。”卡尔感叹。
的确挺高,四人中最高的雪精灵还不到铜像的腰部,要是她跳起来,也许够得着乌拉尼亚垂下的手,可书不会放在那种地方……也许只能靠翼族,让他们飞到半空查看了。加莉娜想着,忍不住看向尼格勒雪白的双翼。
“也许我们可以先检查能看见的地方。”莉莉提议。
在雕像后头,他们意外地发现一个熟悉的身影——
“嘿、嘿、嘿,小崽子们,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那人没个正形地背靠雕像坐着,那是一块因为有遮挡而没被雨水打湿的干燥地面,地上东倒西歪堆着几个空酒瓶,他小小地打了个酒嗝,然后伸出手挠挠自己的后颈,正是指点他们前往中央信息中心、“眼珠”酒吧里的那个落拓法师。
尼格勒问他:“你怎么在这儿?”
“夜晚散个步而已,嘿,不觉得雨中漫步特别有情调吗?”像是被自己的话逗乐,法师自顾自地笑起来。
“真巧啊,你知道书怎么拿吗?”加莉娜问。她懒得和人打些没必要的机锋,说话为什么不能直接,一定得绕来绕去,诗人似得说些酸腐屁话?更何况,法师说着雨中散步的乐趣,腿边却横着一把明显是使用过的雨伞,这人还不诚实,何必多费口舌?
“你们想要什么书呢?”他懒洋洋地问,“是梦中之物凝固而成的那一本?还是海潮彼岸愚人注视的那一本?又或者星空深处变化莫测的那一本?哈哈哈!”
法师的话让加莉娜想起初入公园时感受到的那股震撼与压迫,想起雨声变化而成的潮声,某个潜在深渊之中的不可名状之物,以及伸向天空祈求的双手,他们说什么来着?哦,对了,西罕诺,伶伶,莱……
“我想要属于夏绿书的那一本。”
翼族法师果决的声音将加莉娜扯回现实,她不再置身于充斥疯子的木舟,被狂风巨浪抛接,而是重新踩在踏实的地面上。
“啧,真是个实用主义者,小心看不到魔法的本源。”法师抱怨。
“那不如都给我?”
法师耸耸肩,咕哝着“真是不可爱”,接着摸摸索索地从衣兜里掏出个什么在翼族少年眼前晃了晃。那是个书本模样的胸针。
尼格勒伸出手,手心向上,手掌平摊在法师面前。
“不给你,哎嘿嘿。”
他嘻嘻嘻地笑着,收回胸针,一幅“你们拿我怎么办”的表情。
“是你让我们去找书的欸!”卡尔委屈地抱怨,“让我们去城中心的也是你!”
法师反而逗他,说:“可是你们没找到,反而被我找到了。”
“我看到了就是我的,”加莉娜说,她的语气很平静,手扶在刀柄上,“拿来。”
“嘿、嘿,冷静一点。”法师做出一个“放轻松”的手势,“给你就是了,小孩子(说到这里,他扬起下巴朝卡尔点了点)太容易生气可不好。”
卡尔鼓起脸颊,皱着眉头瞪他。
“唉,会长不高的,看看你们。”法师叹口气,像是真心在为这群未成年的身高担忧。
在注意到雪精灵瞬间握紧的手后,他很快转移话题,再次亮出手中的书状胸针:
“话说回来——你们知道了吗,这是什么?”
莉莉·索达利斯语气冷淡地说:“如果你知道的话,就不要卖关子了。”
“它是夏绿书的信物……看你们的样子,也已经知道她睡着了吧?”
“有话直说。”雪精灵回答。
“我做不了梦,但你们可以……我希望你们能回答我一个问题,然后,它就归你们了。”
“人为什么会想做梦?”
——这是什么问题?!狂怒再次降临,如天火烧尽森林,蓬勃的情感又一次占据加莉娜的大脑,她紧紧闭上嘴巴,恶狠狠地将头拧向一边,眼睛紧盯地上水渍倒映出的乌拉尼亚,预言者的眼睛看向未来,看起来有些忧郁,也许是在为菲薇艾诺今后的命运担忧,又或者感伤来源于他的性格。雪精灵的大脑被破碎的话语填满,充满力量的词语匕首一般在她的心灵上刻画,她甚至有种让雨水浇熄怒火的冲动。会做梦与想做梦不一样,睡着后不受控制是一回事,主动追求梦境又是另一回事……为什么想做梦?当然是因为没有了,失去了,再也不存在了,如果不在梦里遇见,那时光的流水会将珍藏的容颜带走,时间的力量是可怕的,最锋利的铁、最坚固的石头也抵不住这力量。
由于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加莉娜错过了队友的回答,最终,胸针被交予卡尔,由他保管。
尼格勒最后问道:“你认识夏绿书吗?”
听到这个名字时,法师露出怀念又怨恨的神情,却没有回答翼族法师的问题。
这时,加莉娜开口了:“塞西尔说她和夏绿书是好朋友。”
“她当然是,哈哈,她永远都是!”法师的情绪发生变化,他的笑声不再有那种刻意的轻佻,强烈的情感使他的嗓音变粗,第一次,他露出带着强烈讽刺的表情。“正因为她是,所以她永远去不了那里……哈哈哈!”
看到他的变化,加莉娜的嘴角拉开,咧出一个笑容。说到底,眼前的男人与夏绿书与塞西尔又和她有什么关系呢?她只想回到现实,继续自己的复仇。可这世界和法师刚才的问题实在叫她恼火,她受到苦难的折磨、时常受到激情的控制,那眼前的人凭什么有余力做出那幅轻松的样子?所以她借用语言的力量,恶毒地将自己的愁苦转到对方身上,指望片刻的轻松。怨恨比单纯的恨意更复杂,爱与恨指向同一个目标,过去与现在不停拉锯,怀念时对方现在的可恶模样冰水一般从头浇下,诅咒时过去的快乐悄然浮现,又忍不住想起那人的好。这样的情感是沼泽,陷入其中的人一点一点沉下,触不到底,怎么挣扎也够不到岸边,能抓住的只有脆弱的枯木藤蔓,最终,淤泥在头顶聚合,世间的美好再也不见,他彻底毁了。
“那你又是谁呢?”尼格勒问。
“我是海勒姆·黑尔斯,一个疯子,只是个可怜又无助的老疯子而已。”
法师海勒姆开始抛一些五颜六色的光球,像在表演戏法一样。
眼见海勒姆不再有对话的意向,冒险者们转身离开,沿着道路向神殿区走去。雨仍然在下,但远处的红光已经暗下来,这大概预示着什么。走到一个十字路口时,冒险者们的正前方与两侧忽地涌出许多小型飞行器,密密麻麻的,蜂群一样。尼格勒摆出施法的手势,却发现这些小东西只是在面前停留片刻,它们朝着侵入者的半球玻璃闪着光,有点像昆虫的复眼,而后飞走,仿佛对眼前的人失去兴趣。接下来的路程很顺利,这里不再如之前那样是荒漠中的海市蜃楼,是旅人永远无法达到的道标,他们试着往更深处走,发现那让他们离目标建筑遥不可及的屏障消失了。很快,那栋横躺三角柱状的玻璃建筑出现在眼前,神殿区与卡尔记忆中不同,这可以理解,是这个城市奇怪,而在一片建筑中,只有这栋拥有玻璃外墙的建筑没有其他神袛独有的特征,预示他们推断这就是夏绿书所在的梦神神殿。
“也许是那个胸针的作用,”翼族法师推测,“之前塞西尔也说过,要带着夏绿书的信物才能进入神殿区,到达梦神神殿。不过……”
他顿了顿,继续:“塞西尔说她无法靠近夏绿书的信物,海勒姆却能将书拿在手里……”
“也许她只是不想去触碰。”莉莉回答。
卡尔和加莉娜没有加入对话,雪精灵撑着伞哼着小曲,看起来心情不错,侏儒低着头摆弄书状的胸针,他穿着防雨斗篷,所以能将两只手空出来。
“啊!”他发出一声惊呼。在他手上,胸针的书页被打开,卡尔眯着眼睛,念出刻在书页上的文字:“夏绿书与……两位挚友。”
“我们到了。”雪精灵冷淡地说。
他们推开门,被一阵白光吞没。
tbc.
——————————————————————————————————————
全文8152,暴躁毛妹,在线报复




10099
-------------
14.
两个精灵缩在树林的阴影里躲过了这群精灵主义者的搜查,当他们鬼鬼祟祟地又回到密道入口旁边时,天空已经只剩下西边的一丝光亮了。
前一天晚上他们在那间旅馆中过夜,薇塔塔甚至没有机会看到天空;今天她看得到天空,却发现这里的菲薇艾诺别说是月光,连星星都无法看到。
当群星消散时。
薇塔塔忍不住想起这句诗句,那是一年多前一个白色的精灵在她店门口卖唱时说过的诗句,他说“当群星消散时,他们终将醒来”。
那时卓尔小女孩心想,群星怎么会消散?它们是一个一个的世界,世界怎么会消失呢。
现在这么看,群星果然已经消散了,那个假冒诗人的男人说得没错,他在死前真的留下了那么几首真实的诗歌。
“就算躲在这里,如果他们搜查整个西花园,我们也会被发现。”幼猫·福玻斯在薇塔塔少见地发愣时提出新的问题来,“就算我们躲进地道,怎么重新隐藏起密道的大门?”
“……对哦。”小女孩挠头,“我没想到这点。”
“我听闻法师们都拥有自己的魔宠,如果我们中的一个人是法师的话,就可以让魔宠替我们做这件事了。”珂旭牧师妄想得振振有词。
“问题是我们都不是,而你的神术大概一点用都没有。”薇塔塔没好气地翻了个白眼,“我有个主意,你先给我滚下去,剩下的我来解决。”
幼猫好像想说点什么,但在开口之前就被薇塔塔两手推着给推进了地道,在他的背影消失在黑暗中后,女孩尽可能地集中精力,将那些细碎的草叶、苔藓甚至泥土缓缓地浮起数十厘米的高度,就在地道入口的正上方——她从没用漂浮术做过这么细致的事情,一般情况下她只是用这种能力给自己倒杯茶而已,但现在的环境逼着她不得不挑战一下自己的极限。
好在那些东西漂浮得很稳当,薇塔塔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地从那扇打开的木板门爬了下去。当她确定自己的头顶已经在木板门关上也不会被砸到的高度时,小女孩将撑着木板门的木棍给放平了,接着她解除了漂浮术的控制。
她听到那些泥土甚至小石头叮叮当当落在木板门上的声音,接着是苔藓块的闷响,最后是柔软的草叶沙哑的回音。
看起来问题不大,至少可以在这种黑暗的环境里骗过几次那些白色精灵的眼睛。
薇塔塔松了口气,接着三下并作两下麻利地下了梯子,回到了飘着淡淡垃圾臭味的地道里。
“所以呢?如你所愿现在我们在安全并且臭气熏天的地方了,接下来我们干什么?”她有点没好气,如果按她的性格就会直接杀出一条血路去梦神神殿,而这个珂旭牧师待在身边让她什么事都没法放手去做,薇塔塔的耐性已经差不多到极限了。
“还有别的路吗?在这个地方待着也不能算是安全。”幼猫露出“如你所见我看不到周围的环境”的表情来。
“没有,到头了,这是条单行道。”薇塔塔叹了口气,点亮一个小小的淡绿色光球,让它悬挂在森精灵的头顶,“我不觉得他们会跑来这边搜查,但毫无疑问现在那些主干道是不能安全通过的,而我们要去那座神殿就必须通过主干道。我们又不能从房顶爬过去。”
说实话我觉得现在杀过去还比较快,小女孩把这句话咽回了肚子里,她已经足够见识到了这个珂旭牧师啰嗦说教的能力,如果她再说点这些“善良”的牧师所不愿听见的话,就怕下次他再开口的时候她要忍不住把这家伙的舌头给割下来。
“他们总不能一直封锁着主干道,多影响市民生活啊。”珂旭牧师说着好像理所当然的话,“我们可以试试看他们打算封锁多久。”
“你觉得这群纯血疯子在乎屁民的生活?”薇塔塔总觉得自己在这种地方吐槽就是输了,“他们要是封锁一周你就一周不出去?等到人家打开地道就会发现两具饿死的尸体你信不信?”
幼猫也发现了自己话里的问题,稍微沉默了一下:“……或者我们先回到博物馆那边?从办公室溜出去,看看能不能弄两张市民证。”
“回博物馆倒是可以,市民证大概率是搞不到的,咱们一没有钱二没有路子。”薇塔塔耸肩。
“你不是一直希望搞清楚海勒姆·黑尔斯为什么要欺骗我们吗?”珂旭牧师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两眼突然开始发光。
“当然了,现在说这个做什么?是要增加我的不爽吗?”提到那个老疯子卓尔牧师就没好气,那顶装模作样的礼帽又在她眼前开始晃荡。
“我们从博物馆出去就去找他,问清楚发生了什么。”幼猫把自己的拳头放在另一只手里,“等搞清楚了之后,再回这边看看。虽然我很不想这么说——希望现在那些暴徒已经达到了他们的目的,不再封锁博物馆那边了吧。”
“问题是你怎么去找他?我可是不认路。” 薇塔塔一脸的不置可否。
幼猫挠了挠后脑勺:“先去看看吧,不然我们还能做什么?”
小女孩打呵欠:“那你前头带路咯。”
幼猫·福玻斯充满干劲地向前走了几步,接着停下了脚步。
“还是你带着我走吧,我看不到钢丝。”他话里有点抱歉的含义。
“……到底还要我带路……”实际上还在青少年的小牧师龇牙咧嘴地走到森精灵前面去,“别忘了,我要把那个老疯子的帽子塞进他嘴里的时候不准拦我!”
幼猫似乎一时语塞:“你……随意。”
15.
薇塔塔掀开本来应该在桌子下面的木板门时,并没有遇到预想之中的阻力,看起来那个名叫塞西尔的高等精灵女性回到办公室之后并没有把那张桌子给推回去,她也不知道到底该说这姑娘干得好还是说她太没警惕心了。
——毕竟他们走掉的时候谁也想不到他们还会再回到这里来。
外头的天色彻底黑透了,但博物馆内似乎还有些脚步声,薇塔塔贴着办公室的门听墙根,走廊上还有靴子铁掌敲打在地上的声音,以及不知什么人用精灵语低声交谈的声音。
她听不太真切,但毫无疑问那群纯血疯子还没有滚蛋。
“喂,外面还有人诶,你跑回来干什么?”卓尔小女孩压低声音跟同行的森精灵说话,“你要是说要从博物馆里一路杀出去我倒开心。”
然而幼猫·福玻斯没回答她,他好像陷入了自己的思索中,此时盯着书架上的书一言不发。
都在这种情况下了,他还有心思在这儿发愣?
薇塔塔有种想把这个菜鸟的脑袋拧下来看看那里面都是些什么构造的冲动。她离开房门回到窗前,拨开百叶窗的叶片向外看——不知为什么,百叶窗似乎是这里的流行设计,他们前一天住的旅馆是这样的窗帘,今天白天去的咖啡馆也是这样的窗帘。薇塔塔总觉得这种窗帘过于轻薄,失去了那种给人安心的厚重感,这种设计她怎么也喜欢不起来。
庭院里还有微弱的灯光在不规则地闪烁,似乎是那些巡查者手里的提灯。从灯光看来人数也并不多,大概他们的工作也要到尾声了。而远处传来的喧哗声也变弱了,那些人不是被抓走了就是被放走了吧,薇塔塔叹了口连她自己都没察觉到的气。
“他们大概快走了,我们再待一小会。”她也不管幼猫到底听到没有,自己说过之后就缩回了头,百叶窗的缝隙合了回去,房间里再次回归昏暗。
而幼猫似乎微不可闻地回答了一声。
一味的等待显然不是薇塔塔的性格,她开始在办公室里这里摸摸那边翻翻。这个办公室里满是她看不懂的书,什么《生物演变考》《世界关联性论丛》《通道能量基研究》《不同世界间趋同演化案例》,光是名字就让小女孩一头雾水,看过几个书脊之后她就只觉得眼晕,再也不想看第二眼了。她最后得到的结论只有一个,就是从桌上的名牌来看,这是他们馆长的办公室。
本来她就不喜欢学习和看书,小说还可以看两眼,这种不知所云的晦涩文献完全在她的理解范围之外。
“桌上只有一台不知道可以用来干什么的机器,抽屉都锁上了。”珂旭牧师突然发声,吓得薇塔塔一哆嗦。
“要说话就先喊人啊!”她小声抱怨这个愣头愣脑的家伙。
抽屉上着锁不是难事,只要她的刀子还在她手里,哪怕这张木质的桌子要她把整个锁头都挖出来也难不住她。她本想说“撬开不就得了?”,但想到那家伙迂腐的说教又把话给咽了回去。
而幼猫好像故意的一样转头看着窗外,又一言不发了。
“你能不能再幼稚点啊?”她差点就笑出来了。
薇塔塔真心实意地觉得这个人好好笑,这种动作再加上他的那种表情,就像在催促着她说,邪恶的卓尔精灵,我现在看不到你的动作,你快撬锁告诉我抽屉里都有些什么线索。
在她眼里,这个森精灵的珂旭牧师明显从一开始,从他们还在火车站的时候开始就完全不信任自己这个临时的队友——不如说,他甚至没把自己当回事,只觉得自己是个没什么本事的小孩子,对待她的态度和他们的幼童如出一辙。虽然这并不是什么坏事,但幼猫·福玻斯这个人显然对于什么都不在乎,无论是这座城市的未来还是这里的现状,在这点上就连薇塔塔这个公认是铁石心肠的卓尔精灵都比他要多出一份怜悯之心,而他只去怜悯那些多余的东西,仿佛例行公事一般。在薇塔塔看来,他现在唯一在乎的只有自己能不能回到那边的菲薇艾诺去,至于其他事情,一律与这家伙无关。
而他却满嘴都挂着仁义道德,好像这么做珂旭真的就会看这个虚伪的家伙一眼那样。
说到底,这家伙现在真的还接受着珂旭的眷顾吗?薇塔塔替他画了个问号。
她从怀里摸出另一把刀来,这把刀刃薄背厚,非常适合用来切砍硬质的东西,无论对象是木头还是骨头。
刀子毫无阻力地没入锁头旁边的木头,这张桌子的木质和做工都相当不错,薇塔塔简单粗暴的撬锁方式被任何一个家具匠人看到大概都会发疯。她毫无顾忌的破坏行为在寂静的办公室里带起一阵喀啦喀啦的噪音,是个人站在那里都会知道有人在暴力开锁,而那个有事没事都会去找点事的珂旭牧师却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像个王八。
锁头从最中间的抽屉上脱落下来的时候,她还是忍不住啧了一声。
——虚伪的白色精灵。
“为什么你会认为,把自己的发现告诉同伴,是一件幼稚的行为?”幼猫·福玻斯再次突然开口,这次没能吓到薇塔塔。
“我说过这样的话吗?”小女孩伸手把失去看门狗的抽屉拉出来放在桌上,“我如果不说,那肯定是因为没必要。”
不过这家伙到底在想什么,要怎么说她,她都无所谓了。现在这个情况下,蝉在她身上放着,黑暗的环境里只有她能看得清楚路,而不使用神术的肉搏战里也显然是她占上风,这个森精灵在她身边的唯一意义就是挡箭牌,他再说些什么对她而言也不痛不痒,大不了当做被蚂蚁叮了一口罢了。
被她撬开的抽屉里放着一叠文件,薇塔塔被抬头的一行字给吸引住了。
《关于金属蝉的研究报告》。
“哎呀……”小女孩差点笑出声来,简直是刚瞌睡就有人递枕头,她正对这个来路不明的吊坠犯嘀咕的时候就有这么一份文件出现在她面前,就算她再怎么不喜欢看书,面对这份文件也只有笑着打开的份了。
“众所周知,十数年前起,菲薇艾诺的空气开始急剧恶化,与此相对应的则是夏日里的急剧减少的蝉鸣……”
报告的前面几乎都在叙说菲薇艾诺的空气质量在这数年中变得如何如何令人不堪忍受,而环境变得如何差劲,最后他们如何在西花园发现了这个东西等等。薇塔塔迅速地翻过这些无意义的部分,进入这份报告的正题。
——那枚金属蝉到底是什么?
那后面有许多假说,有些假到让薇塔塔看一下都想要嗤之以鼻,但这些家伙却觉得很有道理,让卓尔精灵忍不住想问问这间博物馆是不是不存在理解常识的人了。
之后的一条被用红色墨水批了重重一行大字的假说倒是让薇塔塔起了兴趣。
“无稽之谈!”红色的墨水这么写道。
而那条假说明明白白地写道,这只蝉或许是与另一个世界的衔点。
薇塔塔用食指的指甲在上面无意识地轻轻敲打:“就是这个无稽之谈了吧,我们要用到的……”
“上面怎么写的?”珂旭牧师终于结束了他的装聋作哑,做出像是脖子痛那样的表情困难地扭头过来。
“这上面说,这个蝉可能是这个世界和‘另一个世界’的衔接点。或许指的就是我们的世界了。”薇塔塔心情正好,不和他计较。
“这样吗?”幼猫又开始看着窗外走神。
“虽然这些人看起来不信咯……喂,你在听吗?”她看着森精灵的后背挑了挑眉毛。
珂旭牧师不作回答,只是反问:“还有呢?”
“没了啊?还是说你想听他们把所有蝉都杀光了这件事?”薇塔塔长叹一口气,把文件递到他面前,“不信自己看。”
“不用了。”幼猫摆摆手,只是两眼发直地看着窗外。
16.
在薇塔塔蜷缩在馆长办公室那张宽大的扶手椅上已经打起了轻鼾的时候,幼猫·福玻斯将她叫醒了。
“外面已经没有声音了。”他仍然保持着那安稳又没有感情的语气,“我觉得可以走了。”
两个精灵偷偷摸摸地从办公室门口探出头去,漆黑的走廊上空无一人,远处的嘈杂声也消失了,看起来那群血脉之理的恐怖分子确实已经撤离了。薇塔塔蹑手蹑脚地从黄昏时塞西尔给他们指的路返回到大厅,看起来由于那群纯血疯子的搅局,所有的安保人员都被吓回了家,而他们甚至可以大摇大摆地从大门走出去离开。
大厅的巨龙还在那里孤单地站着,白骨被融化进浓得化不开的夜色。白天的骚乱没有给这头沉睡的龙骨带来什么影响,看起来以后也不会有什么影响,就算这个菲薇艾诺毁灭,它也会静静地站在这里看着精灵之城的终末吧。
就像一头沉默的、真正的古龙那样。
她最后看了一眼那具似乎泛着火光的龙骨,从博物馆的大门离开了。
按幼猫的说法,博物馆的这片地方应该对应的是另一边菲薇艾诺的商区,他们只要向着东北方向走就能抵达神殿区,而现在应该仍然横在主干道上的血脉之理就是他们绕不过去的路障。
“所以我还是觉得,像现在这样躲躲藏藏还不如直接杀过去。”薇塔塔打着呵欠嘟囔。
“不要节外生枝,自找麻烦。”幼猫又开启了他的谆谆教导模式,“我们不知道在这里受伤了,甚至死了,对我们的灵魂和肉体会有什么影响,必须谨慎。”
小女孩在浓浓夜色里翻白眼:“那不还是你不够强,有足够的能力的时候什么都不用怕。”
两个仿佛相反色的精灵在空无一人的大街上相互说着废话,世间最无聊最没有营养的对话也不过如此。
但这段对话很快就被不远处的身影给截断了。走路摇摇晃晃像是喝醉了的中年人,头上戴着装模作样的平顶礼帽,身上穿着一样装模作样还皱巴巴的燕尾服,除了海勒姆·黑尔斯那个老疯子以外,薇塔塔无法再做他想。
身体在她的大脑反映出海勒姆这个名字时就已经擅自动起来了,她用已经暌违了一年的最高速在一瞬间闪到了那家伙的背后,在这个疯疯癫癫的梦学家反应过来之前扼住了他的喉咙,在他喊出第一句“抢劫啦”的时候,如自己所愿地把他的礼帽塞进了他的嘴里。
在珂旭牧师反应过来并且赶过来之前,小女孩已经把海勒姆两手捆了个结实,拖死狗一样地拖进了旁边的暗巷,熟练得就像早上把吐司塞进嘴里。
当幼猫急匆匆赶到这个仿佛杀人越货未遂的犯罪现场时,正撞上薇塔塔拿着刀尖对着海勒姆的眼球比划。
“我劝你嘴里少几句瞎话,不然我让你这个老东西往后说一辈子的瞎话。”卓尔精灵凶相毕露地对着中年人龇牙咧嘴。
幼猫罕见地没阻止薇塔塔的过激报复行为,只是轻飘飘地让她冷静点:“别这么冲动,这样我们什么问题都得不到答案。先带他回博物馆里面再审他。”
被从暗巷又拖进了博物馆的海勒姆还在呜呜叫唤,直到幼猫把被薇塔塔塞了个结实的帽子从他嘴里扯出来,这个疯疯癫癫的中年人才得以顺利地继续他的呼吸——薇塔塔塞住他嘴的手法简直是要把他给憋死一样。
“救命啊,抢劫了,抢……”海勒姆缓过来点劲又开始吆喝,直到看到薇塔塔手上被揉成一团的帽子才知趣地闭了嘴。
薇塔塔咬着后槽牙说话,一副咬牙切齿想把这人吃了的表情:“老东西,你中午跟那骗谁呢?”
“啥?什么骗谁,我没骗过你们!” 海勒姆一边挣扎一边嘴硬,被薇塔塔把刀架在脖子上才消停了一点。
“你跟谁说蝉在博物馆呢老疯子?”她用刀背顶着海勒姆下巴,还顺便问候了对方的男性先祖,“而且你这么晚了还敢在外头逛?你逛个【哔——】呢?满嘴没实话不怕鬼爬你背后吗?”
幼猫似乎觉得薇塔塔的脏话有点不堪入耳,咳嗽了一声岔开话题:“你说那只蝉在博物馆里,然而我们却不是在里面找到的。”
“它的确曾经在那里,谁能想到它现在不在了呢?”海勒姆翻起了白眼。
珂旭牧师好像也有点按捺不住自己的脾气,但还是耐着性子和他讲文明话:“但根据我们的消息来源,它本来不应该在这里。”
疯疯癫癫的梦学家开始胡搅蛮缠:“谁啊?你怎么能确定不是他在撒谎?”
薇塔塔把刀往他肉里使劲一推:“它恐怕从来都不在那里,老疯子,我警告你最好说实话。”
海勒姆开始发出夸张的嚎叫,卓尔精灵举起帽子作势要塞回去,这家伙就从善如流地闭上了嘴。
“那东西就是从西花园的塑像那里发现的,它现在还在那里,要是这东西在博物馆我们早就拿走回家了。”小女孩一脸嫌弃地撇撇嘴,“要不是你那满嘴的胡话我也用不着在全是垃圾臭味的密道里呆上那么久。”
“你引我们到这里来,然后我们就遇到了血脉之理的排查,我们很难不怀疑你。”幼猫说话的气息有点不稳,薇塔塔觉得自己听到了他深呼吸压制自己怒气的声音。
中年人似乎想耍点花言巧语:“嘿,欺骗你们,尤其是这么美丽的小姐,对我有什么好处呢?”
“谁知道?有趣?满足你那变态的好奇心?还是说你根本就没正常过?”薇塔塔觉得自己现在只能用看垃圾的眼神看这个疯子,用看流浪狗的眼神都是高待他了。
“如果你也是从我们那个世界过来的人呢?你不希望我们回去,是因为你怕你也得回去。”幼猫捏着海勒姆肩膀的手指咔咔作响,海勒姆嗷嗷的叫起来,“或者,你就是破坏皇室差分机的人?你想让我们成为你的替罪羊?”
听到差分机这个词,海勒姆的表情再次迷离起来:“嘿、嘿,差分机啊……差分机,那东西会把彩虹拆散,叫它们永不再编织。”
他带着一脸疯癫而喜悦的笑容,好像被用要捏碎肩膀的力道抓着、又被刀指着喉咙的人不是他,他只是个戏剧之中的旁观者一样。
“你妈的,就是你把差分机弄坏了?”薇塔塔手一滑差点把刀捅进他嘴里。
“不、当然不?血脉之理接到消息有人要破坏差分机,然后当天,差分机就损坏了,而后支持血脉之理的贵族当政了——你不觉得太巧了吗?”海勒姆也被吓了一跳,使劲摇头,还小心着不被薇塔塔的刀划破脸。
“我当然觉得太巧了,所以一开始我就觉得这是血脉之理干的,我是真的讨厌那群无趣又没有任何美感的家伙。”薇塔塔放松了手上的力度,她怕自己下次手滑真的把这家伙捅得再也说不出话,
海勒姆似乎觉得刀刃的钳制放松是自己的舌头管了用,便继续说着花言巧语,“不过,这种事,说到底和你们有什么关系吗?你们在做梦,你们是过客,你们只要抵达了神殿,哪怕是血脉之理也追不进去,哈!”
“他们的行为恐怕会令珂旭不悦。”珂旭牧师好像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定位。
“他们拦在我们的路上,我想要过去就得杀过去,而我可不想让我自己身上溅上那些无聊家伙的血——谁知道你是不是血脉之理的狗腿子?” 薇塔塔觉得有点反胃。
“可他是人类啊。”幼猫好像有点懵。
“谁知道那群疯子会用些什么人去当他们的爪牙。”薇塔塔看着梦学家露出一脸的嫌恶。
“嘿!血脉之理可不收人类会员!”海勒姆大声抗议。
在讨厌血脉之理这点上他好像倒和薇塔塔站了统一战线,但这点相同被小女孩给有意忽略了:“你说告诉我们去西花园找蝉的人是在撒谎,你又凭什么?难道你知道是谁告诉我们的吗?”
“那蝉被送来研究过,还留下了研究报告,之后又被送回去了——这事儿我可不知道。”梦学家两眼看着龙骨吹口哨。
“你他妈不知道哪儿说出来的这么多?老疯子!”薇塔塔差点又把刀捅到他脖子里。
“嘿、嘿!你们想引开血脉之理吗?我可以帮你们。”海勒姆开始提起交涉条件,“你难道不想知道顺利通过的方法吗?我告诉你吧,嘘——别让那个死板的家伙听见。”
“他又挡不住我。”薇塔塔把刀往他下巴上又顶了顶,“我劝你嘴里最好说点实话,不然我可不知道我会不会真的捅穿你的喉咙。”
“你去引开他们?这样,你还能活吗?”珂旭牧师多余的怜悯又开始作祟,“我不知道那群极端的人会那么好心。”
“闭嘴,他活不活不关咱们事。”薇塔塔没好气地回了一句。
海勒姆伸长了脖子,贴在在卓尔精灵长长的耳朵边嘀咕:“皇家保卫队里还有台差分机,只要把它炸了,血脉之理一定会过去——你猜怎么着?他们的人其实没你想象中的那样多。”
“哈?一台差分机就够乱了,再来一次?”卓尔小女孩瞪大了眼睛,“你是什么侏儒的亲戚吗?爆炸爱好者?”
饶是薇塔塔也被这家伙的想法吓了一跳,这么喜欢爆炸的人她上次见到的还是个在她家商店门口放超大烟花的侏儒,被她连轰带撵的赶走了。
“我之前才见到过一个侏儒,他和他的队友都很矮,一定是生太多气的缘故。”中年人继续他的牙尖嘴利,“不过,你们问了我这么多问题,也让我问你们一个,如何?”
“……问吧。”幼猫在薇塔塔开口之前答应了海勒姆,但这家伙虽然嘴上说得爽快,表情里却颇有些“这是你这辈子最后一个能问出来的问题”的意思。
“你们觉得,人为什么会想做梦?”梦学家又戴回了他那癫狂面具一样的笑容,薇塔塔看着这个表情就有种想把他的脸皮给剥下来的冲动。
——就算说出口也就是说说而已,她的确算是个凶残的家伙,这点她承认,但小女孩倒是从来没干过这种灭绝人性的事。
“我为什么会想要做梦?”幼猫换回了他那平稳的语气,柔和而安静,好像刚才那个差点失态的人不是他一样,“在醒着的时候我不会、甚至不敢去做的事情,在梦里都可以大胆地做。现实中已经无法补救的遗憾,梦里的自己永远都能力挽狂澜——”
珂旭牧师甚至带了一点笑容:“做梦是从不如意的现实当中逃亡的方法里,最安全、同时也做轻松的一种,试问我又怎么可能不热爱它呢?”
“说得好像你很热爱现在这个情况一样。”薇塔塔翻了个白眼,“我从来都不想做梦。从一年之前我就开始做噩梦到现在,就在此刻当下我都在做着噩梦——我说真的,要是真有梦神的话,我倒希望他哪天晚上能让我别做梦好好睡一觉,别让我再长黑眼圈了,那东西用多少眼霜都去不彻底。”
她没什么要特别怀念的东西,名叫薇塔塔·拉雅特·德拉娜的女孩早就失去了她名字里所包含的一切,她当下的世界就是这个小小的卓尔精灵的唯一,而她自己又本来就是个现实主义的姑娘,那些影子般的梦境只是她现在好不容易步入正轨的生活的绊脚石。
谁想要过去的影子去影响自己现在的生活?梦境越美好,醒来的时候就越悲伤——既然是梦,那总是会有醒来的一天的。
如果做梦的话倒是让我梦见那些我想梦见的东西啊。
这句话她没说出来,如果说出来免不了又要被这个疯疯癫癫的中年人拿来做一番文章,而她已经听够了这家伙的疯言疯语,要不是要留着这家伙问出通过盘查路障的方式还有做挡箭牌,她早就给他捅个透心凉了。
海勒姆张开嘴想说什么,但远处传来的另一声巨大的爆炸截断了他的话,疯癫的中年人打住自己引起的话头,哈哈大笑起来。
17.
“这又是怎么回事??”薇塔塔尖叫起来,她已经不顾周围会不会还剩下血脉之理的残党了,今天的事情发生的实在太多,她的小脑瓜要炸了。
“哦呀,炸了炸了!要走就趁现在哦?”海勒姆开心地跺着脚,似乎是因为手被捆起来没法鼓掌,这家伙直接用跺脚代替了。
“到底是为什么炸了??”小女孩持续尖叫,“你这个该死的老屁到底干了什么!!”
梦学家一脸的得意:“只是个闹钟做的小小装置而已,哈。”
“……走,我要你给我们当盾牌!” 薇塔塔一阵无语,稳住自己之后便一把把海勒姆从地上扯起来,抓住用来捆他手而撕下来的这家伙的燕尾服后摆,朝着博物馆后门冲去。
“结果这事还是你干的——你猜我要是把你交给血脉之理会怎么样?”
幼猫按她的安排,带着他们在小路暗巷中穿行,而目标正是神殿区的梦神神殿。
就算是在高速逃亡的路上薇塔塔也不忘威胁一下这个老疯子。她实在是无法理解这家伙的思维,在没有魔法的世界里寻求魔法也就罢了,但这个世界甚至能把“门”那样高端的法术用得出神入化,而他们的生活水平已经远远超过了能够使用魔法的那一边的世界,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真的是人心不足蛇吞象,怪不得这群贪婪的家伙被珂旭抛弃了。
血脉之理倒是真的和海勒姆说的一样,在爆炸发生之后他们也开始骚乱,之后都向着那个方向涌去,没人再去费神照顾路上的那些劳什子。而他们在这群家伙反应过来之前就穿过了主干道,在没人追上来找他们麻烦的情况下看,这些人真的无暇顾及排查什么市民证了。
“告诉我们进入梦神神殿之后要怎么做。”现在的环境嘈杂又混乱,幼猫回头看了一眼海勒姆,却差点撞上面前的垃圾箱,薇塔塔清晰地听到他不耐烦地啧了一声。
海勒姆好像没听到他的话,只是自言自语地嘟囔:“真是可惜,原本应该能有更好结果的。”
“你想还要什么结果?”薇塔塔气不打一处来,“想要我们替你解决了血脉之理?不好意思我没有那么高的正义感也没那么多时间——不如说现在的这些混乱才是我最喜欢的!”
“你的目的是什么?你认为你对秩序破坏得还不够切底吗?现在罪案已经无法阻止了,等我们确认了梦神神殿的事情就把你交给卫兵!”幼猫虽然不敢回头,嘴上的工夫却一点没减。
“没时间了,你还要去招惹那群纯血疯子吗?”如果不是手上扯着海勒姆,薇塔塔很想跳到幼猫头上敲他两下,“他们要是回到路障上就麻烦了,还要杀过去才行,到时候你又要啰嗦!”
说话间他们已经穿过了神殿区前的最后一条主干道,原本仿佛逃避他们的神殿区如今不再后退,那层无形的障壁已然消失,造型奇特的神殿近在咫尺。卓尔精灵这时候才发现,白天看起来似乎灰蒙蒙的这座神殿却在夜幕星河般的灯光里闪烁着奇异的光芒,薇塔塔能从它的墙壁望进去,却看不真切,就像梦里的景象那样,似乎永远蒙着一层浓到散不开、却又像是故意不去阻挡窥视之人的雾气。
——只要推开这座神殿的门,就可以回到家了。
不知从哪里来的这股信念灌注进少女的脑海,大概也同样在珂旭牧师的脑海中回响。幼猫奔向梦神神殿的大门,而薇塔塔抓着一个成年男人一跃而过神殿区外的矮墙,一时间有如神助般几乎恢复了巅峰时期的身手。
“就在那了!”她大声呼唤珂旭牧师开门。
接着薇塔塔手上忽然一松,抓着一个成年人的重量突然消失了。
卓尔精灵发出愤怒的咆哮:“他跑了……!”
在她回头的时候,一阵熟悉又有些微妙区别的白光从神殿的方向将她包裹,而海勒姆仍然带着他面具般的痴笑,站在白光之外向他们挥着手。
“再见啦。”他的口型似乎这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