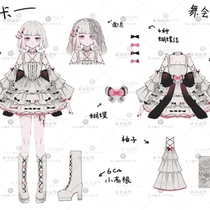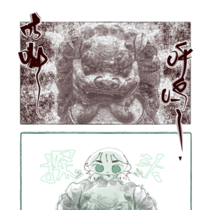(1)夫人之死
帕斯特苔姆家的子爵夫人死了。
漆黑的房间,神色各异的五个人里,只有跪在床边上的少年表现的最为平静,医生宣布完死讯后,抬头看了一眼默不作声的子爵,便离开了房间。众人安静了半晌,房间才传来低低的抽泣声。
“闭嘴。”发声的是子爵,他瞪了一眼身边哭泣的女人,头有些僵硬的想往床上看,但是不知为何克制住了,重重的叹了一口气后就走出了房间,身边哭泣的女人见子爵完全没有带着她的倾向,又抽泣了几下便也跟了出去。
房间经过短暂的喧哗,又陷入了沉寂,不知道过了多久,少年站了起来。
长时间的跪坐让他起身的动作异常艰难,在他的身后站立着一位穿着管家服的白发老人,等到少年站稳,才上前走到他的身边。
“少爷,教士已经离开了,他让我把这个交给您。”摊开手,递上前的是一个三角形的教徽章。
“把她处理了吧。”
少年接下,对着管家吩咐道“还有,让后院的人提前离开。”
“是。”
门打开又被轻轻的合上,至始至终,少年都没有回头,他长久的看着自己的母亲,看着,希望能永远记住她的脸。
他弯下腰,把三角徽章轻轻的放在长眠不醒的母亲枕边。
“我的整个灵魂都充满了欢快,
犹如我的整个心身欣赏的甜美的春景。”
“我独自一人,
在这专为像我那样的人所创造的地方领受着生活的欢欣。”
“……”
“晚安。”
我的母亲。
(2)清理
坎走出门的时候,候在房间门口的侍女便递上了早已准备好的毯子,子爵夫人早在初有临终迹象的时候,帕斯特苔姆少爷便准备了大量的冰块备在房间,秋天本就有些凉意,子爵夫人的房间更是犹如冰窖,人们都待不了太久,唯独坎少爷一直留在房间内,女仆有些关心的替他披上轻毯,说:
“少爷,请跟我来。”
说着往前走,少年搓了搓手,把有些挡眼的刘海拨到一边,露出一张极其白皙俊美的脸庞,细长的睫毛下,他的瞳孔是纯粹的丝毫没有杂质的金色,鼻梁高翘嘴唇偏薄,长时间的低温使得他看起来有些虚弱,然而接下来要做的事又不能让他停下来休息。
“该偿还了……”他的声音消散在走廊的空气里。
女仆领着他走到了早已准备好的“观景台”,拿起白发的老管家给他递上的单片眼镜,看着视线正下方花园那对亭子里的狗男女 即便是坎也难得的有些情绪激动。
他的情绪化早在7岁那年就被克制了,此时也不过是放大瞳孔,身子略微前倾,他那灿烂的金色的眼瞳看起来明亮又美丽,然而被这样注视的对象,却即将坠入地狱。
此时的二人还毫无知觉的抱在一起,女人的长裙被掀起,一双大手在她露出的大腿上随意抚摸,在一路上人为制造的安静环境里,他们仿若忘我的亲着,丝毫不像是在刚刚才经历彼此最为重要之人的逝去,即便她们一个是逝去之人的妹妹,而另一人则是逝者相处多年的丈夫。
……
丽实在太高兴了,她等了这么多年的东西终于实现,天知道在那该死的寒冷的环境里面她抖的都快站不住了,却还得装作悲伤的样子是有多么不容易!天呐…神明在上,她终于…终于代替了姐姐,可以正大光明的站在这个男人身边了,无数次在床上被男人营造的美好梦境也没有这一刻来的让人喜悦。她跟着眼前这个即将相处一生的男人来到后花园后便忍不住的抱住了他与他亲在一起,或许是仆人长眼,或许是天在帮她,路上居然没有遇见一个仆人。
亲着亲着,连束胸都被狠狠的扯掉留下道道红痕,她正准备提醒男人轻一点,却发现胸口有奇怪的滴落感。
像是水滴滴在身上,然后顺着皮肤留下来。
身上的男人也没有了动作。
“xx!xx你怎么了?”她推了推男人,实在是这个重量有些沉重,却没想男人直接被她推倒了下去。
而暴露出来的她的胸口,裸露的皮肤上是大片大片鲜红的血液。
“啊啊啊啊啊啊啊!!!!!!!!!”
她大叫着往后退,但是又很快扑到那个已经没有生息的男人胸口,男人的眼睛没有闭上,脸上包括胸前已经被鲜血染红。
“来人啊!来人啊!老爷,老爷你这是怎么了!?来人啊!”
这一刻丽慌张的根本无法思考,她一边叫人一边用颤抖的手去探男人的鼻息,却发现完全感受不到。她害怕的整个人都在发抖。
很快有仆人过来,丽抬头,泪水模糊了她的双眼,用袖子去擦却弄的脸上到处都是血,这副凄惨的模样简直让陪伴在她身边几十年的女仆感到不可思议。
看清来人,在这种响动下来的居然是自己熟悉的女仆,丽感觉自己很很幸运,她伸手想去拽女仆的衣服——
“快,快把子爵带去—————”
唰——
话音没落,天旋地转间已然头首分离。
“咚——————”这是来自远方的丧钟。
也是女人人头落地的声音。
这一刻,无论是杀人的女仆,还是在远处观看的少年及仆人,都不约而同的站立抬头,看着远方掩映在群山中高高的尖塔。
群鸟自丛林飞向天空。
那是圣塔,而钟声,正是由回到教堂的教士敲响。
敲钟人离开家,手持丧钟走街串巷,祭奠死去的亡者,通告其姓名。
人们默哀。
云层慢慢积聚…在阵阵风声中,一场大雨即将降临这座偏远的城镇。
它将冲刷地面上的污渍…
(3)过去
“凡事让人幸福的东西,往往又会成为他不幸的源泉。”
女人慢慢的合上书,保养完美的手揉了揉趴在腿上的紫发男孩,看着那和外祖父一般澈亮的金色眼睛,里面闪烁的满是好奇和不解。
“坎…我的孩子…你现在幸福吗?”
“我不知道,母亲,”男孩摇头“什么是幸福?”
“幸福,就是坎现在陪在我的身边,我感觉很开心,很满足,而且希望永远这样看着你。”
“原来如此!”年仅7岁的少年有着很强的学习力,他开心的说:“那坎也觉得很幸福,因为坎会也会看着母亲,陪着母亲,永远!”
……
“母亲,你在喝什么?”
“我的妹妹…她找到了可以治妈妈病的医生,我只要喝了它,身体很快就会好起来。”
……
“你在干什么!!!”
“少…少爷,我,我在给夫人准备汤药。”
“我看见你往里面倒东西了!”
“少爷!”
女仆被男孩指出的那一刻,慌乱的连碗都端不住,她迫切的想离开这里,却被男孩挡住路。
“少爷…少爷我没有”
“我都看到了!把碗给我!!!!”
男孩上去想把女仆手里的碗夺过来,视野里女仆的表情从一开始的慌乱害怕,逐渐转为一种狠毒。
“啊!”
她在男孩伸手扯碗的时候猛地松开手,任由男孩因为惯性摔倒在地,碗砸在桌子上碎开,崩裂的碎片划伤了男孩的额头,而碗里的热水更是撒了他一身。
“啊!”
…
“父亲…”
“你为什么会去厨房?”
“父亲我看见——”
“闭嘴!”男人根本不听他解释“坎,我对你很失望,不要仗着你作为我独子就为所欲为,你那母亲肚子不争气,而你,凭你的作为,根本配不上我帕斯特苔姆家长子的位置!”
…
“你好,少爷,请问喊我有什么事吗?”
“我知道你现在家里情况很严重。”
“少爷你想干什么!?”
“别急…”
少年慢慢敲了敲面前的桌子,“我知道你很忠诚,不过你也知道忠诚换来的是什么,我那姨姨…知道你家庭状况但是从来没有帮过你吧。”
“…”
“我可以帮你。”
在昏黄的夕阳下,巨大的落地窗将阳光分成几块,氤氲空气中漂浮着的粉尘在阳光下闪烁发光。坐在窗前的少年自信的笑着,摆了摆手,便有白发的老管家把厚实的信封递给女仆。
“辛苦你了…相必你很清楚…谁才是主人。”
…
“少爷我错了…我错了我不该给夫人下药”
曾经傲慢的女仆现在像条狗一样趴伏在尊贵的少年脚边,祈求着他的宽恕。
“抓到你了…”
少年看着她抬手,女仆吓了一跳,正准备躲避却发现他只是摸了摸自己额头上的痕迹。
然而这却更可怕,那双明亮的黄金瞳翻涌着的是只有她能看到的,隐藏在无底深渊里翻涌升腾的黑暗恶意。
“想活着,就得帮我做俩件事…”
“以后把药放到子爵的碗里…以及…”
“哈…”
“到时候我自然会呼唤你。”
…
“少爷。”
“医生,辛苦了。”
“是这样的…夫人她患有一种遗传心脏病,您请我来检查以及是比较严重的后期了,可能她活不了——”
“等等,她身体还有别的问题吗?”
“没有,少爷。”
“我明白了。”
—END—


经过三章主线的游玩,现有未能打卡成功/主动退企的角色名单如下:
死武专方(退学):
工匠——秦莫
武器——澹临、靳风
魔方(失踪):
魔女——毛月
如有错漏请群内私戳企划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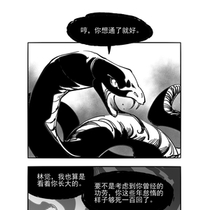


——————
这个故事从头说起的话,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雷涅的家人都还活着的时候。很久以前他和他的家人朋友都生活在一个闭塞的小村庄里,连头上到底是什么人在管着这里也不太清楚,城里的新鲜事儿传到这里要花上好几年。大部分人的全部人生就是在这里出生劳作结婚生子,到过的最远的地方是镇集,因此坚信着城市是完全用瓷器砖砌成的,昂贵又易碎,去城里的话一定要万分小心。去过城里的老人则会讲一些离奇的见闻,比如城里的人饲养全身都用黄金打造的假鸟,喂给它宝石它就会动弹,就跟真的鸟一样,但唱得比真鸟好听多了。
当然后来雷涅知道了,城市也不过是这个样子,更没有人饲养什么黄金做的鸟。但那个时候他已经没心思关心这种细枝末节,又或者这种细枝末节总是猝不及防地戳痛他:城里的小作坊里有售卖黄铜做的机械鸟,身上镶嵌着花花绿绿的彩色碎玻璃,拧了发条就会摇头晃脑地发出鸟鸣似的音乐声,多看那么一眼店主就会凑上来拼命推销,好像身边没有这小东西是个重大缺憾似的。由于多看了它一眼,雷涅被迫从店主这里知道了这小鸟的全名是“首席夜莺”。
雷涅张了张嘴欲言又止,迈开的步子停了停,终于还是忍不住说:“夜莺哪里是长这样的?”
“这样好看啊,唱得和夜莺一样嘛。”
“夜莺的叫声也不是这样啊。夜莺叫声……”
他说了一半,忽然觉得自己在浪费口舌,不再理会店主,大步离开了。谁在乎夜莺到底是怎么叫的?也没有人在乎这小鸟是黄铜还是黄金,身上是宝石还是碎玻璃。这就是雷涅讨厌这些细枝末节的原因,总是这些微不足道的东西拖慢他,扯痛他,浪费他一心一意复仇的时间。
总而言之,这最早是一件不值一提的事情,不管是城市,金色的机械鸟,还是在故事里歌声婉转优美到让人落泪的夜莺——都不过就是那样。城市也不过是石头砖头建起来的,夜莺的叫声也不过就和别的鸟差得不远,根本不是什么叮叮咚咚的音乐。他反倒不明白为什么在书本故事里夜莺是种特别的鸟,他努力回想,大约是在他的师父给露缇娅念的书里的故事。他在猎人行当的师父露西娅女士——现在是露西娅嬷嬷了——在因伤退出猎人这行后变得越发慈祥,后来加入教会当起了照顾圣女的嬷嬷;因此雷涅在猎杀血族时救下小女孩露缇娅时,首先想到的就是把她托付露西娅师父。这大概也是好些年前的事了,那时候的小女孩露露还没有被选作圣女,耳朵还能听得见,可以听露西娅嬷嬷念念书里的故事。“……它是国王的花园里最珍贵的宝物,所有人都被它的歌声感动,连国王听过它歌唱后也落下眼泪,乞求它住在宫殿里为他唱歌……”
雷涅一定是碰巧在那里,听到露西娅嬷嬷给小女孩念的这个故事。他想起上次在小作坊里的事,感到更加困惑:“夜莺到底有什么特别的?那种鸟,长得也普通,叫声又细又亮……”
露缇娅露出了一些雷涅比较熟悉、经常在他因为看不懂哪个单词而发生误解的场合会看到的表情,那种无奈中带了一丝被煞了风景表情。她们大约说了些“故事的重点不是真不真实,而是这故事想表达的是什么”之类的话,雷涅记不太清了,倒是记得露西娅师父那罕见的、微妙的笑,她几乎微不可查地叹了一口气,说:“我倒希望你别见到‘夜莺’。”
故事到底为什么是围绕着“夜莺”展开的?雷涅觉得自己忘记了什么,或者说是这原因曾经有人向他提起过,但他没有放在心上,以至于现在需要这个答案时怎样也想不起来。他只好继续往前回想,在那个已经非常遥远,他决意不再回去的村庄里,他还是个普通农民的时候,夜莺在他们那里是种常见的鸟,叫声还算好听,但总喜欢在夜里唱歌,有时会让他觉得吵闹。在那种村庄里天黑了就该睡觉了,爱在夜里吵闹的动物都不太受欢迎。离开村庄之后他就没再听到过,也许是无心去听了。他还记得躺在床上,外面树丛里声音细而清亮的小鸟叽叽喳喳地唱着歌,而他的妻子在他身边发出缓慢悠长的熟睡后的呼吸声。
从他人的角度来说,那也是不值一提的事,和城市、机械鸟、故事里的夜莺一样,雷涅的故事也不过如此。十年前的这天,他从邻镇的集市回家,天光已经大亮了,村子里却很安静;他闻到一点血腥味,觉得有些不安,于是加快了回家的步伐,然后他看到自己的妻子,自己所有家人都被吸干了血,随意地扔在地上,早就死去多时了。他不太愿意去回想当时的心情,他们生活在一个不富裕,很闭塞的村庄里,对“血族”或“吸血鬼”这个词都不太熟悉,那就好像一颗听说过名字的星星,突然从夜空掉下来砸中了他的房子一样,让他感到陌生又荒诞。但是当他选择向那些吸血鬼复仇,去加入了猎人工会,到过了那些大城市之后,他又发现他的故事也没那么特别——就和真正的夜莺一样,实际上是种很普通的鸟。有那么多人和他有差不多的经历,失去了差不多数量的亲人朋友,还选择了差不多道路。
好像他的全部都不值一提,拥有过的和失去的都没有什么意义,他即将在这里,一个荒凉野地里死去也是微不足道的事。
不过他还是没有想起关于夜莺的,一些非常紧要的事情。可能是因为他太痛了,疼痛让思维变得混乱。他受过很多次伤,他的师父尽力训练过他,但他前半生只是个农夫,也不去结交猎人伙伴,所以对受伤已经习以为常,所幸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搞丢什么身体部件。他感觉到也许这一次他真的要死了,他失去太多血,被他追杀的吸血鬼已经逃走,这条路线不会有普通人经过,他也没有给别的猎人留标记。
血还在从他身体里离开,疼痛却没有消失,好像血管里的血都被疼痛替换了。他觉得手脚冷得已经没有知觉。他到底忘记了关于夜莺的什么事呢?“国王即将死去了,因此他陷入癫狂,在幻觉里看到死神带着他做过的所有好事坏事来质询他,他疯狂地大喊驱赶那些幻觉,仆从都不敢接近他,都只想等着他咽气。这时候从窗外传来了美妙的歌声,那夜莺回来了,为它的国王唱起最后一首歌。国王安静下来,在那歌声里落下最后的泪水,陷入永久的安眠。“他想起那个故事的结局,然后他好像突然要想起来了,但是头痛欲裂,不能去仔细思考和回想。他就要死了,脑子里有太多东西,来不及一一去想。
他听到奇怪的歌声——在他想起夜莺的结局的时候——不怎么好听,听不出调子的歌,他身上浓郁的血腥味里混进了一丝丝礼拜堂里熏香的气味,昏沉视野里隐隐透来怪异的蓝色光芒。有人把手伸到他颈侧探了探他的脉搏,然后擦掉了他脸上的污渍和血迹。
雷涅终于想起来了,那件紧要的、他忘记的关于“夜莺”的事。这些年他心无旁骛地战斗,满脑子都只有复仇和猎杀,心里给自己定好的结局就是死在猎杀血族的战斗里,毫不在乎自己的身后事,于是自然而然就淡忘了这件事。人们要么避讳死亡,要么是看不上那些人的行径,仅有的和他有交集的猎人也不会特意提起那群特殊的猎人,那群不再参加战斗,转而专门为猎人收尸,发死人财的“夜莺猎人”。而他一旦想起来了,那些细枝末节就一涌而出:他想起露西娅师父有个旧识就是这样的“夜莺猎人”,那老猎人身上正是有这样怪异的混合着尸臭血腥的香味。他听到收尸人用夜莺当名称时感到困惑极了,于是问了出来:夜莺到底有什么特别的?
他的脸被那个夜莺猎人擦干净了,那猎人把灯凑近照他的脸,于是雷涅也睁开眼,看到一张熟悉的脸、熟悉的眼睛,正是露西娅师父的那个旧识老猎人。老猎人被诡谲的蓝色灯光照得怪异恐怖,比起夜莺倒更叫人想起那种抢夺腐肉的鬣狗。他笑了起来,说道:“是你啊?放心吧,你不会死的。”
“噢,”他又说道,“费用露西娅已经付过啦。”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