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期中作业没写完,人又很崩溃
挤牙膏也挤不出东西
我道歉了(……让我五百字打个卡吧
——————————————————————————
“你到底是什么人呢?”这句话,沈芙在这十几年间已经说了无数次了,每当她将面前的男人拦下来,问出这句话的时候,他都会拉一拉他的帽檐,然后的沉默地走去楼梯口,又或者是小院子,或者是转身将手中的猫塞给她。
避而不谈,沈芙倒是很了解他的性子,从小时候,当然指的是沈芙的小时候,这家杂货店就一直开着。
谁也没有想到在钢筋水泥的都市里还会有那么一条小巷子,尽头还会藏着一家小小的无名杂货铺,店主是一个看起来二十来岁的男性。经常是用黑色的披风或者卫衣兜帽将自己的身影隐藏在黑暗中,沈芙唯一能看见的就是他那双金色的眼睛。
这应该不会是个普通人吧,沈芙这么想着和他搭话,可可爱爱穿着洋服的小女孩一直觉得自己是十分有魅力的人,至少大家都会觉得她可爱得不行,没有人可以阻挡她的甜甜一笑。
“那,那个……”沈芙用自己觉得最可爱的笑容朝着柜台后的男性问道,“您好!请问您知道这边的路该怎么走吗……芙芙,芙芙我迷路了。”——当然怎么可能迷路,无论是进来还是出去都是一本道,闭着眼睛往前走就可以回到喧闹的大街上。
“……”对方那双眼睛像是可以洞察一切一样,瞥了一眼女孩却一言不发,只是站起身,拎着女孩子的衣领,提着她把她放在了门外。然后伸出手指了指面前这条路,再挥了挥手像是告别一样回到了杂货铺内,随着一声“哐当”,沈芙意识到他把自己无情地丢了出来还加了一道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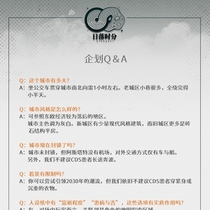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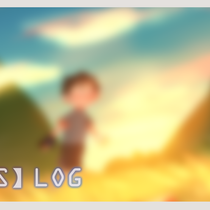


1326
承接http://elfartworld.com/works/8093109/的伊孚视角
补完一下汗塞西老师的决战
————————————————
由契约带来的力量撑裂了皮肤表面,不属于自己的魔力仿佛食人蚁般啮咬着血肉,带来针扎般的痛感,左手的贯穿伤仍滴答着血液,砸在泥土里。
在这种绝境下伊孚甚至还有些庆幸,过度的痛感与疲惫分庭抗礼,才让他已经破破烂烂的精神与肉体还能吊在钢丝上不至于坠落。好在自祖父那里继承的杖剑的足够可靠,泛着漆黑幽光的藤蔓发出整齐的断裂声,掉落在地上不住蜷曲颤抖着,像是被齐根斩断的壁虎的尾巴。
他为自己已经无可救药的幽默感扯开了嘴角,又因牵动了伤口而紧咬牙关。
“还不肯放弃挣扎吗。”
金属的破空声骤然而至,伊孚叹了口气。以他的力气已经格挡不住刺剑,只能选择狼狈的滚在地上去躲避攻击。下意识地想用双手撑起身体,但渗进伤口的泥水引发的剧痛让他的手臂不住痉挛,差点再次跌倒在地。
“哧——!”在布料撕裂的同时,伊孚的后背也被划开了一长条伤痕。他拼命压榨出身体残存的一点点力量,爬起身逃走。刺剑像是吞吐着的火舌,又像是毒蛇游走的信子。伊孚背上的汗水刺激着伤口,让他的行动变得更加生硬。 喉间像是有团不甘罢休的火焰在蒸腾着,将柔软的内里炙烤出带着腥味和甜腻的血沫。
等等……好甜的味道……这是……
仿佛能带着身心一同堕落的甜腻让他无法抬起手脚,那甜美的,让人麻木的味道像是东方医馆中熬制的芙蓉膏,却又胜过百倍。就连“糟糕”“来不及了”的思维都来不及传达到四肢。脚下的泥土龟裂,粗壮的藤蔓癫狂地从地面破土而出,让他不禁踉跄。
“啊。”
早已喑哑的嗓子已经喊不出话语,嘴唇徒劳地张合了一下。疼痛从身体内外炸裂开来,像是利剑一般搅动着他的神经。巨大的伤口从右肩一路撕裂到左键,皮肉翻卷,露出鲜红色的组织。他的杖剑被踢落在一旁,而他本人的境遇也比这把剑好不到那里去。他像是被顽童踢走的腐烂水果一般被踹到墙角,冰冷的刀刃抵着他的喉咙,暗红色的血珠沿着刀尖渗了出来。
“死吧,”,塞西的眼睛里仿佛有青色的火焰在燃烧,“负隅顽抗毫无意义。”
伊孚看到了从她眼中倒影出的自己,精疲力竭,奄奄一息。
这就是,最后了吗……那么,起码有一些事,想传达到。
“我一直……感到…… 很抱歉,阿泽维多。”
他用手抓住利刃,徒劳地阻拦着死亡,剧痛感反而让他打起了点精神。
“因为我说了那种不负责任的话,你才会遇到危险的吧。”
伊孚的手无力地松开,落在地上,像是布娃娃被扯断的臂膀。温热的鲜血蜿蜒着,被黑色的泥土吞噬着。
“如果你真的,想要我的命的话……”
冰冷的,带着铁锈味的液体滴落到他的脸上。暗红色的血液从苍白的手掌内满溢而出,流满了整个剑身。
“快……跑。”
塞西的声音像是从另一个空间传来一样,扭曲而又沉闷。握住剑柄的左手颤抖着,却缓慢地将刺剑从墙壁与手掌做成的刀鞘中抽出。她身后那最后一簇藤蔓摇曳着,如果它们能发出声音,想必是癫狂的、对血肉与生命充满渴求的吼叫声吧。
“……咯……哈哈哈。”
在生死之间的游走过久的精神已经脱离的正常的思维范围,疯狂大胆的念头立刻从他的脑子里冒了出来。不如说,这是一个非常风元素裔的决定,亦是极为伊孚·温图斯的举动。
意志牵动身躯,精神突破禁锢,烙印汲取生命。冰凉的水反转成炙热的火焰,裹挟在狂风中,缠绕在藤蔓上。响应着战锁的痛苦,荆棘之火如同楔子,让不安分的藤蔓匍匐在地。塞西也跌倒在地,她的身体抖若筛糠,仿佛亦在承受那可怕的灼烧之苦。
皮肤在灼烧,皮肤在干枯,皮肤在撕裂。
血液包裹着他,黑暗包裹着他。
伊孚失去了意识。

Jesse死在四年级的夏天。
May从电话里得知了这件事,她没有哭,只是觉得不可置信,一句轻飘飘的“节哀”就能宣判另一个人的死亡吗?她根本不信,直到她给Jesse打了第十个无法接通的电话。
Jesse为什么不接电话呢?
May甚至有点费解,死亡,多大不了的事,巫师的寿命很长,又有13次可以重来的机会,他们从小就知道自己的与众不同和优越性,与凡人相比。
死亡,死亡。
......太遥远了。
这时,May好像才记起来,Jesse是个凡人。
死了就是死了,干脆利落,没有重来的机会,用肉体与钢铁抗衡,用肉体保护肉体,撒旦在上啊,怎么会有人做出这种蠢事?May会在意他曾眼睁睁看着一个孩子在他面前死亡吗?May会因为他没能救下一个鲜活生命而对他充满怨恨吗?
她想起刚刚那通电话里的人说Jesse是个值得尊敬的小伙子,他挽救了一个孩子的生命,于是“公正”的上帝就用他自己的性命与孩子交换么?好像今天伪神必须得带个人上天堂似的——
天堂。
撒旦的子民是到不了那里的。
正如阳光照不进黑暗,或许,May死后也见不到他了。
分别是必然的事,巫师和凡人,在寿命的长度上就截然不同,May曾想过,她和Jesse会分手吗?抑或等到死亡将他们分开?第一次恋爱的小姑娘,总是胡思乱想,原先“分别”是多么难以接受的词语,可是现在看来,好像也并不是那么难,至少从刚才起,May一滴眼泪也没掉,只是心脏在“砰砰”跳动,像杂乱无章的鼓点。
谁都没想到,这段恋情竟会戛然而止,生活的琐碎没有分开他们,此时May倒希望他们的恋情终止于相看两相厌,可是每个具有悲剧意味的宿命总是会让最美好的停在高潮,接着,所有阴暗丑恶纷至沓来,洪水一般淹过。
May甚至想学会遗忘,可是,她注定铭记。
新学期的第一天,Lacey见到了May。
她的装束自从跟...交往以来就大变样了,原先是利落的单马尾,高高束起,跑动时会随着动作摆动,发尾像一簇绿色的火焰。
现在披散下来,看起来倒更加娴静了,不过在这个时期,这样的打扮就看起来有了令人感伤的意味。
——Jesse说过,May把头发披散下来更可爱。
不过除此之外,May看起来就没有什么异常了。
她相当平静,乃至她的所有举动都看起来怪异得过了头,Lacey自从知道这个消息以来,就很担心她,可是当看到May没有自己预想中那样难过后,Lacey却并没松下口气。
果然,她不详的预感成真了。
May在大厅等待永远不会出现的Jesse。
一连几天,May都在等待,她的等待那样专注、期盼,仿佛总有一天,她的男朋友会出现在走廊尽头,牵起自己的手。
但这样的等待注定是漫长、枯燥、且无望的,Lacey陪着她一起等待,一直等到黑夜侵蚀白天,夕阳被月光浸染,May才转过头,失落地说:“他又放我鸽子了。”
Lacey看着May的脸,像逃避什么似的别过头,哑声道:“或许,他只是有事在忙。”
May没发现好友的眼眶有点红,她像是接受了这个说法,脸上漫起一层红晕,嘟嘟囔囔地说:“兴许吧......可他连一条信息都不给我发。”
Lacey不作声,她一直沉默。
李芽是个来自中国的女孩子,住在201寝室,May的隔壁。
或许是因为语言不通,她看起来总有点怯生生的,听说目前在努力学习英语,不知道进度如何。
May回寝室的时候,正撞见这个女孩正笑着抱着只黑色的鸟,和她的室友Lacco说些什么。
Lacco看见May,笑着打声招呼,May却很心烦意乱的样子,李芽笑盈盈地转过头,在视线越过May的肩膀时一顿,脸色骤然僵硬起来。
这女孩缩着脖子,有一双圆滚滚的眼睛,很灵动,正看看May的脸,又瞧瞧她身后的走廊。
May觉着奇怪,却被Lacey叫进屋里。
“学长今天有和你去约会了吗?”她漫不经心地摆弄窗台那盆风信子,蓝色的花瓣在她指间碾揉,她似乎没注意这些可怜的花朵正在冒出汁液,直到May从她手里抢救下它们。
“没有。”May忧愁地叹口气,“他最近总是很忙,也不知道在忙什么——他是不是厌烦我了?”
“怎么会?”May兴许没发现Lacey笑得有点勉强,她兀自沉浸在纷杂的思绪里,倚在窗边望着花坛的方向失神,Lacey有点紧张地随着她的视线望过去,却只看见一片空旷。
“刚刚那个女孩,她叫什么名字?”李芽磕磕绊绊地说。
“怎么了?”Lacco看她一眼,向来没精打采地眼皮破天荒稍稍抬上来些许,这姑娘的脸颊肉肉的,有圆润的弧度,总是看起来很困倦的样子,李芽很喜欢和这个室友亲近——她总觉得Lacco像个大型的人形抱枕。
李芽闭紧嘴巴,没敢说话:就在刚刚,她看见May身后跟着个身影,远远地坠着,看不清面容,但应该是个男人——并且,看其他人的反应,她们看不到这个灵体。
按中国的说法,李芽是天生的阴阳眼,猫眼象征通灵,她从小就可以窥破三界屏障,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因为这个,小时候经常邪祟缠身,动不动就发高烧。最凶险的一次,是她的邻居太太病逝,老婆婆仙逝于凌晨两点多钟,阴气最盛,她生前没有子孙,于是很喜欢李芽,把她当亲孙女看待,魂魄刚刚离体时是最糊涂的时候,老婆婆喜欢李芽,就遵从本心,来将李芽带在身边。
那时李芽还小,以为这是婆婆要带自己去新地方玩耍,于是傻乎乎跟着她走,当家里人发现的时候,李芽小小的魂魄几乎快要走到黄泉了。
因为在这上面吃过苦头,李芽向来对这事讳莫如深,在中国,活人身后跟着魂魄不是什么好兆头,她于是神神秘秘地摇头,模棱两可地说:“没什么,只是,你以后跟她保持距离吧。”
在晨课上,May困倦地眯着眼,她昨晚睡得很不好,在梦境里,她总是不可抑制地梦见尖锐的刹车声、孩童刺耳的哭叫、软绵绵的毫无生气的尸体,和,和被鲜血浸染的马路。
这是什么意思?她做了一场预知梦吗?接连几晚梦见这种东西,对巫师而言显然不正常,脑子很痛,这使得她一整天都没有什么精神。
Lacey在问起她糟糕的脸色时,她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隐瞒了自己怪异的梦境,但这样下去仍然不是办法,或许某位老师有办法解决这件事?可是,她潜意识里却在排斥讲述这样的梦境。
茶室里空无一人,或许除了学校里那些看起来都严肃得像教授的古板英国人,没人会频繁地来这儿待着。
May从前经常和Jesse在这里喝下午茶,热恋中的情侣待在哪都能甜蜜得起来,只是自从开学以来,May却再也没等到过男友的身影。
她有点生气,又很难过,泡好的红茶已经很久不再冒热气了,被她心不在焉地一圈一圈搅出来年轮似的漩涡。
水流形成的圆圈像是深邃的暗流,她停下动作,低头盯着漩涡中心,像是在与深渊对视,这时,May似有所感,面无表情地抬头望去,窗外枝叶繁茂的大树下,白色的人影一闪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