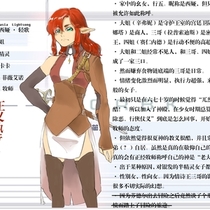本次长期将不再开设新群,规则详见相关页面(http://elfartworld.com/projects/1425/)公告。
长期可参与角色为:
一期及二期未爆角色(如想参与请向企主申请)。
新捏角色(自觉审核)。
其中翼族角色将新开放一个名额。
如果第一次长期参与的角色想继续参与第二次长期,请确保他在第一次长期时的剧情结束了哦。
此外,在暗月城的冒险结束后,暗城议会的剩余成员经过讨论,决定交给每位参与冒险的冒险者一个种子,他们可以选择自己认为合适的地方种下。
而第五季也愿意协助冒险者们前往他们想要前往的世界(限已知世界)。
在战斗中损失惨重的暗月城议会也打算招募新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