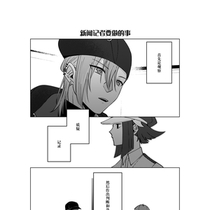日记的形式,谈谈了诶里克森对米路通缉令的看法。
Ooc在我
今天是12月31日,距离离开铃兰内湖已经有些时日了。
本以为到源头查看,一路闯到了铃兰湖内都没有发现什么。
反倒是回程的时候,湖骸遗留下的液体和圣母像溢出的液体相似。
教会和此次事件逃不开关系,即使迟钝的我也察觉到此事,但是这几周却安静的异常。
除了,米路的通缉令。
听说是在湖骸入侵期间,趁乱带着名为珍珠的圣女逃离的。
这个孩子事情略有耳闻,他是已故[圣女]米娜的弟弟 ,一年前米娜用自己最后的愿望交换了用于治疗疫病的良药。
而医治的病人就是现在教会猎人米路。
米娜,印象中是一个温柔可爱的孩子, 曾经还给大家送了自己编制的花环。
印象只停留在此了……我没有勇气对他们有过多的接触。
我帮不了他们什么的。即使是米娜送予的花环也没有收下,我无法帮助他们逃离死亡的命运,也不应该收获他们的好意。
米路的通缉令,我只能将它撕成碎片扔进垃圾桶里。
如果不去追他们,他们也无法得到善终。背叛的溃烂会一点点吞噬那个孩子身体,直到死亡。
而我能做的事情是什么?把他从逃离的希望中带回绝望,还是将他杀死在爱人面前?再把绝望的圣女带回断头台上?
让所有圣女明白,逃跑只是徒劳无功,只会白白浪费重要之人性命。
我做不到,无论哪种情况我都不希望发生。
……
明天就是新年,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仿佛明天只是往常一样的日子,如果只是平常的日子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