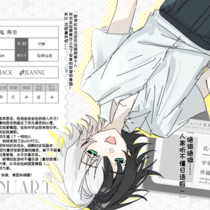*
“还有人……”王珲的声音发着抖,“还有人活着吗?”
哪里都没有传来应答,只有她自己的话语在狭窄的墙壁之间来回碰撞,仿佛是对她踉跄步伐的一种效仿。王珲喘着气,身体靠上其中一边,蹭下一片黯淡的血迹。她其实已经不太记得这些伤口分别是怎么来的了,枪或者刀,一次令人眩晕的坠落,或者只是平坦路面上的一颗石子;但她不会弄错结果:她已经非常虚弱,仅靠自己的力量,想要走出这条危机四伏的地道难于登天。然而就算停在这里休息情况也不会有任何好转,除非她真的能够就这么睡着;因此,她还是继续向前走去。
地道里并没有任何照明。王珲还能够向前走,一是因为这里没有岔路,二是因为双眼多少已经适应了黑暗。可她毕竟不是猫、蝙蝠或者别的什么夜行生物,自然也看不出前方几步远的地方正窝着一团异样的阴影。她走过去,脚尖踢进一团柔软且略带温度的东西里。王珲难以克制地跳了起来,还好及时捂住了嘴,几乎没叫出声。
阴影没有动。王珲犹豫了一会儿,终于还是蹲下身去;凑近之后,她总算看出这东西——这个人是谷菰。她连忙伸手探了一下,呼吸还在,就是极为微弱。放着不管的话,他一定会死在这里……再说,想要走出这里,多一个人总归多一分助力。
王珲打定了主意。
*
“我要急救一下,看看能不能把他叫醒。”王珲说。
“嗯,那你过急救。”佘晴满说,“你们状态都太残了,我就不给你算减值了。”
“不减她也只有初始值啊……”谷菰忧虑地看着王珲的角色卡,“我就剩两点血了,你别把我……”
“搏一搏,单车变摩托。”王珲毅然道。她挑出两枚十面骰拢在手心里,闭着眼睛念念有词地摇晃了一阵,然后撒向桌面。骰子们骨碌碌地滚着,渐渐停了。
王珲看见一个“0”。“好耶,大成功!”她说,视线去找第二个;谷菰已经向椅背瘫下去了。
“另一个也是‘0’,”他说,“100,大失败。”
王珲不说话了。她盯着骰子好一会儿,最终把目光投向身为KP的佘晴满。
“你……嗯,你,”佘晴满考虑着说,“你太虚弱了,在蹲下来的时候失去了重心。你下意识地用手撑了一下,结果混乱之中按在了谷菰额头的伤口上。谷菰HP-1,不过因为这一下,你也被疼醒过来了。”
“好好好,谢谢KP捞我,”王珲双手合十高举过头,一连摇晃了好几下。她转向谷菰:“你是兽医对吧,你应该有正经医学和急救吧!快快快救一下,靠你了!”
“我先救一下我自己,”谷菰重新坐好,“我要用我带的绷带把我头上伤口包扎一下……哦哦哦3点,这次是真的大成功了!我能回多少血?”
“急救只能回1点。”
“蚊子腿也是肉。好吧,那我再急救一下王珲,”谷菰摇着骰子,“真正的医生——”
他的声音中断,因为真正的医生roll出了99点。两个人一起看向桌子另一端。
“我只有1滴血了,”王珲说,“我要死了。”
佘晴满抓了抓头发,努力寻找着放水的角度。“先不扣血了……这样吧,谷菰你在包扎的时候手忙脚乱,绷带一大半都缠在了王珲身上;剩下的那些被你失手掉在了地上,一骨碌滚出去好远,全都弄脏了。你之后使用急救的时候不能再获得医疗包的加值了。”
“一个伤口只能急救一次对吧?”谷菰回忆着规则,“你还有没有别的伤口是一个小时内造成的?”
“没有了,其他都是旧伤,”王珲小声说,“但你还可以孤。”
谷菰思考了一会儿。这个团跑到现在他还没用过孤注一掷。“好吧,”他决定了,“我还带了医用胶布!我要用胶布再试一次!”
他不应该这么做的。十位骰露着“9”,个位骰亮出“7”,两枚骰子宣告着他们的急救计划彻底破产。佘晴满尽职尽责地告诉他:“你把胶布贴歪了。”
“贴哪儿了?”王珲还在努力,“要是没贴在伤口上,我能不能……”
“贴你嘴上了,”谷菰说,“就是你说的孤注一掷!”
*
这一桌团在此之后又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并以调查员团灭做结。
*
Summary:“你这样是我绑的,我这样是你打的”——断章取义自谷菰。
为什么Summary放在最后,因为不这样的话太容易剧透了。
虽然内容处理成了一起玩桌游的样子但根本没管角色性格就这么随便写了,OOC的话就当成中之人用OC在玩吧(爽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