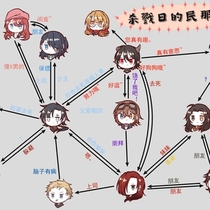“让圣女来开场,教会是故意的吧。”一名血族强忍着才没有捂住自己的鼻子。
“那些背叛者能跟那些圣女一起生活这点,还真令人敬佩。”艾维斯附和着身边的同族,圣女的味道实在是令血族难受。
圣女终于退去,场上的战斗开始。
“我去前面看看。”艾维斯道。
“好。”
艾维斯来到栏杆旁,向下看去。场上两人你来我往打得精彩,但因为不可重伤不可杀戮的规定,终究有些束手束脚。
“啊,可以光明正大的打架啊,好想去,只要死不了,喝多少都可以吧,好渴啊---”旁边一名偏棕色皮肤的青年自语道。他轻舔嘴唇,环顾高台上的人,似乎在寻找充当对手的存在。
“你是嗜血?”艾维斯对青年道。
青年回头看向艾维斯,露出略显疯狂的笑容。“对,我是,怎么,想跟我打一架吗?”青年再次舔了舔唇:“看上去你的血味道应该不错,让我喝一口怎么样?”
“没有任何缘由让你喝是不行的,不过……”艾维斯露出笑容,“我叫艾维斯,向你发出挑战,如果我赢了,给我你们嗜血的月函。当然,如果我输了,你可以来喝我的血。”
青年的笑容越发疯狂:“我叫艾博迪,我想你的血能让我喝个饱,成交!”
艾维斯右手持剑,看向艾博迪。艾博迪没有拿武器,但是指甲变尖变长。随着开场的信号,艾博迪以极快速度冲向艾维斯,尖利的指甲直奔艾维斯的脖颈而去。艾维斯以左手进行格挡,手掌被划出了深深的伤口。
艾博迪舔了舔指甲上的血迹,笑意更深。
“看来你是没有经验的菜鸟,真是走运,好久没有喝到古血的血液了。”
艾博迪再次攻来,他的速度很快,且双手都可作为武器,艾维斯以剑防守,走位躲避,时不时找机会反击,但在艾博迪不要命的攻势下,终究有失误的地方,很快,两名吸血鬼身上都挂了彩。
刺剑袭来,艾博迪带着疯狂的笑容,任由剑锋穿过了他的手掌,他就那样抓住剑身,让艾维斯无法收剑去防御,同时右手猛地往前挥出,期待看到艾维斯左手被削断或者脖颈被划开的样子,然而,他的手在距离艾维斯脖颈几厘米处停住了,身体也无法动弹,随后在一股力量的拉扯下,被重重的摔在了地上。
“这种不要命的打法还真是麻烦。”艾维斯将剑指向艾博迪:“看起来,是我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