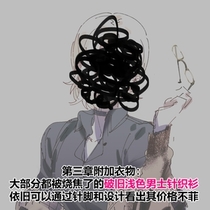“对不起……”不知道是谁说了一句道歉。
“没事的,”小精灵努力仰起笑脸,“我已经习惯了母树不在的日子,也习惯了未成年的样子……只是有时候在想,如果母树能回来就好了。”
苏安手心紧紧攥着那枚涌动着和雷伊精灵相同气息的种子,轻声问道:“已经没有办法拯救了吗……”
“不,还有一种办法。”雷伊族长不知何时出现在众人身后,他看了雷昂一眼,无悲无怒。“母树种子里蕴含的生命能量或许能让母树恢复过来……只是,那个可恶的窃贼,当年我们搜遍了他全身上下也未能找到和树种有关的东西……”雷伊族长抚摸着母树干枯的树干,“若是能找到树种,我们也不至于这般……”
“雷伊族长,您可否告知我们,当年发生了什么?”雷昂终于按捺不住心中的好奇,开口问道,他想知道,被困在骨山的那群人,和眼前的雷伊族长,到底谁才是那个罪人。
“你愿意听,老朽也未必愿意讲,不过陈年旧事罢了。贪心不足,以貌取人,多简单的道理。好了,我会派人送你们出黑森林,以后再也不要来了。”雷伊族长显然不愿自揭伤疤,那是雷伊精灵一族深至骨髓的痛苦,他们成为了没有母树、没有归宿的精灵,丑陋的面容被人类当成魔族对待,只能露出自己最凶恶的一面,撕咬不怀好意的入侵者,保护着仅存的柔软。
苏安犹豫了一下,树种庞大的能量对于一个精灵来说何其诱人,那将是他成为不死的存在,可是看着因为悲伤低着头的小精灵,和背对着他们的雷伊族长,那个背影坚毅而苍凉。苏安下定决心,摊开了手掌:“族长,你看这个,是不是你们母树的种子。”
“什么!”雷伊族长激动地转身,黑色长袍带起地上的尘土。他仔细端详着这颗淡绿色的、散发着无限生机的树种,光芒明灭的频率与他的心跳渐渐吻合,属于母树与母树的孩子的气息交织相融,雷伊族长颤抖着双手接过那粒种子,以无限的虔诚送入母树体内,跪着祈祷母树的重生。
树种的光芒在进入母树的一瞬间变得耀眼,像一颗新的心脏,在母树的躯干里跳动,把自己的能量传输至母树的每一寸枝丫。接收到能量的母树也开始发生变化,干枯的尸体舒展开来,饱含生机的翠绿重新绽放,树根深深根植于大地。深坑也被填满,龟裂的大地缓缓合拢,受到树种生命力的影响,地上又长出了花草植被,铺上了一层柔软。不过几次呼吸的时间,母树便恢复的差不多了,温柔的光围绕着她,光如流萤,轻拂过雷伊族长老泪纵横的脸。
“孩子们,我回来了。”
黑森林内。
雷伊精灵们摸着自己的心脏,那里涌出一阵熟悉的暖流,如春风拂面,暖阳相照。“母树?母树回来了?!”他们停下自己的任务,不顾一切地奔向母树的方向,看到了那棵魂牵梦萦、重获新生的巨树,感受到了母树的爱抚,皆是泣不成声。
拢霁叹了口气,倚在朔身上,说道:“苏安也真是的,故事也没听到,还把树种白白送了出去。”
“但是你好像并不遗憾。”朔难得地笑了。
为了表示感谢,雷伊族长邀请他们参加为了庆祝母树重生的舞会。魔法容器暖黄色的灯光使得气氛更加温暖,配合着母树充满生命气息的光芒,整个场地如梦如幻,宛如仙境。雷伊精灵虽然容貌上稍有缺陷,但是精灵一族的能歌善舞一点儿不落下,他们拍打鼓点,边唱边跳,虽然人数少了些,但那份欢乐是无比真切的。
之前的小精灵小跑着过来拉艾丽莎,他很喜欢这个不怕他的龙族大姐姐:“姐姐要一起跳舞吗?”
艾丽莎愣了一下,有些手足无措:“我不会跳舞啊。”
“没关系,我教你呀,很简单的。”小精灵牵着艾丽莎的手就跑向人群,带着艾丽莎和他们一起舞蹈。艾丽莎学的很快,引来了其他雷伊精灵的赞叹,艾丽莎也被他们的喜悦所感染,裙裾翻飞,跟着鼓点,舞步轻快像在山间飞跃的狐。
雷昂和苏安并肩坐着,看着和雷伊精灵玩到一起的艾丽莎,雷昂突然问道:“苏安,精灵族都是如此能歌善舞吗?”
“恩。”
“我好像还没有见过你跳舞呢。”雷昂笑着看向苏安,暗示之意溢于言表。
苏安思忖了一会儿,他只会基本的交谊舞,目光扫向雷昂右肩,那里的伤还没好,若是和其他人一起跳……苏安把这个念头狠狠掐死在了摇篮里,老实回答到:“我只会交谊舞,其他的不会。而且,我的舞伴受伤了。”
雷昂看向了自己的右肩,那处伤口使自己抬手都疼,更别说跳舞了。突然想到了什么,雷昂神神秘秘地叫苏安:“苏安,你靠近点,我有悄悄话给你说。”
苏安侧头靠近了一些。
“不够,再靠近些。”
苏安又近了一些。
雷昂伸出左手扳过苏安的头,吻了上去。突如其来的柔软触感惊到了苏安,他瞪大双眼看着面前的人,他紧闭双眼,睫毛因为激动而微微颤抖,每一次都像羽毛轻轻搔弄着苏安的心弦。因为离得太近,苏安甚至能看见雷昂脸上细细的绒毛,以及白净皮肤下害羞的红晕。
苏安还没来得及反应,雷昂就离开了他的唇,他伸手去摸自己的嘴唇,似乎还能感觉到之前的温香软玉。
“苏安,记得,你欠我一场舞哦。”苏安呆呆地看着雷昂说话,脑袋里嗡嗡的,只是机械地点头答应。雷昂也忘了自己脸上还一片红,笑骂一句傻子,便有些心虚地转头去看跳舞了。
拢霁和朔倒是在全心全意地欣赏舞蹈,难得放松一下,加上雷伊精灵的舞蹈确实好看,怎么可以错过。
世上妙事无数,譬如久旱逢甘霖,譬如星月兼程佳人等候,再譬如你看向他时,他也在看你,美妙物事千千万万,那时却偏只有那一人在你眼中,又能在那人眼中看见自己的倒影。
朔和拢霁这般相望良久,拢霁打破了平静:“你看我作甚?”
“没什么,只是觉得若是刚才不看你,会有遗憾。”朔回答道。
“你看了,现在呢?”
“和平常一样。”朔扭回头去继续看舞蹈,拢霁挑眉一笑,也将视线转向人群。
一阵光芒闪过,雷伊族长已出现在荀无疾身边。荀无疾坐在树杈上晃荡着腿,见着来人,笑着打了个招呼。
“听老朽的族人讲,阁下似乎精通隐匿。”
“哦,那个啊,是我小时候自己琢磨的,没办法,就想活着嘛。”荀无疾笑笑。
雷伊族长学着荀无疾的样子,也坐在树杈上:“老朽说的是这个,又不是这个。不过每个人都有不想说的事,老朽也不强求。不过老朽有一句话,可能冒昧,阁下心中的执念,终究会害了阁下。”
荀无疾伸了个懒腰,漫不经心地回答族长:“那又如何,自己认定的路,哪有知道难就半途而废的道理呢。对了,族长你听声音也不老啊,为什么总是老朽老朽的?”
“自己选的咯。”族长因为母树复活好像很开心,留下这句话,便又回到了族人之中。荀无疾想了想,几个翻腾跳下树:“嘿!跳舞吗?带我一个啊!”
苏安看着他们的眼睛,敌意、仇恨、自卑、失落……太多太多的东西充斥着他们的眼眸,苏安已经看不见本来属于精灵的纯净了,唯一能安慰他的,只有他们属于正常精灵的气息。苏安运起魔力解开了二人身上寒冰的束缚。思考了一下,开口说道:“我们只是游历的旅人,听说这里是精灵的领地,想在此休息一会儿。”
雷昂从腰间的空间容器里摸出几瓶疗伤的药剂,递给精灵,微笑着说到:“这是疗伤的药剂,你们先用着。”术士冷冷地看了他一眼,侧头不语。雷昂楞了一下,保持着递药的姿势不变,疑惑道:“你的伤,不用处理吗?”
“我们雷伊精灵从不接受人类的东西。”精灵挣扎几下试图站起来,又踉跄着摔了回去,依旧拒绝了雷昂的药剂,从自己的黑袍中取出一些药粉,随意涂抹在伤口处,又吃了几粒特制的药丸。雷昂尴尬地收回手,讪笑了几下,将药剂分发给自己的伙伴,治疗之前受的伤。荀无疾已经从包里掏出药酒,涂抹在淤青处,细细揉着。
“你的方法好特别啊。”雷昂附在荀无疾耳边悄声说道,药剂流行的时代,居然有人会使用药酒。
荀无疾笑笑,低声回到:“我母亲教给我的,我觉得很管用。”
“对了,那个被你打伤的精灵,怎么样了?”
“放心,我下手有数,一会儿就醒了。”话音刚落,昏倒在地的那位雷伊精灵悠悠转醒,他的同伴立即喂他服下药丸,精神慢慢好了许多。他们三相互搀扶着站了起来,服下的药丸起了作用,他们走路也不再踉跄了。
走了几步,雷伊精灵回过头来,脸上挂着讥讽的笑:“你们要是愿意的话,就来吧。”说着向森林深处走去。苏安六人面面相觑,犹豫了一下还是跟了上去。恢复的雷伊精灵走的很快,不一会儿便在这不见天日的森林里失去他们的踪迹。
“要不要我去探探路?”荀无疾自告奋勇。
拢霁摇了摇头:“不行,我们现在天时地利都不占,一旦落单,后果不堪设想。”拢霁拿扇子轻轻敲了敲额头,指了一条路,“我们走这边?苏安你说呢?”
苏安闭眼感受了一下森林的气息,他寻找不到属于母树的、强大的、生生不息的气息,精灵的领地里没有母树?苏安心下好奇,继续放松自己的精神感受着森林的一举一动……忽然,苏安受到了一种呼唤,他不知道是谁在呼唤他,甚至说不出来那种感觉,但直觉告诉他,应该回应这份呼唤。睁开眼,苏安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我感觉到有个东西在召唤我,我们走这边看看吧。”
再度出发,小队的气氛变得沉闷起来,荀无疾不大喜欢这种气氛,开始把自己之前的遭遇说出来:“这个雷伊精灵,好像特别仇视人类。”
队内唯一的人类——雷昂看向荀无疾:“二蛋,为什么这么说?”
“我之前和那个法师战斗的时候,能感觉到他的战斗经验还是很充足的,我的攻击位置他都能判断出来,同样也能找到我的致命之处才对。但是,他和我战斗之时,与其说是搏斗,倒不如说是驱赶。”
“我也有这种感觉。”一直沉默的朔也发言了。“他们对我没下杀手。”
“只有你,雷昂,第一次偷袭也好,第二次法阵的冲击也好,都是下的杀手。不置你于死地不罢休的那种,艾丽莎和苏安只是连带的。看来雷伊精灵和人类之间有着很深的恩怨啊。”
艾丽莎揉着右手腕,她之前太用力,手腕现在还在发疼,问荀无疾:“这就是你不杀他的理由?”
荀无疾听完夸张的后跳,结果没踩稳差点摔倒:“你疯了,这里是他们的领地,我那属于自卫,要是真杀了精灵,我怕这儿的雷伊精灵都出来收拾我们。”
雷昂听了荀无疾的话情绪有些低落,任谁也不想当那个拖累队友的人,苏安伸出手拉住了他的手,用力捏了捏。雷昂有些讶异地看向他,苏安也微笑着看向雷昂,微动嘴唇,雷昂清晰地读出了唇语:我在。
沿着那个方向一直走,眼前渐渐开阔了起来,出现了一条小道,只是小道两旁出现了零星的白骨,森然可怖。伴随众人的深入,道旁枯骨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完整,能看出大致的整体,直到一座骨山赫然出现在他们眼前。
白骨森森,骨山四周盘旋着灵魂痛苦的哀嚎,他们似乎想挣脱什么,却被牢牢束缚不得脱身。周围散落着衣服的碎片,年代久远,已经看不清上面沾染了什么,旁边散落着看上去还不错的武器,六人都有了自己趁手的武器,对这堆质地颇佳的武器不感兴趣。
“你……你是人类对吧!救救我们!我们也是人类……”一个灵魂发现了雷昂,迫不及待地扑了过来,却只是穿体而过。
雷昂一惊,试探性的问道:“你们为什么会在这里?”
哪知灵魂体不听雷昂的问题,只是绕着他们乱窜,念念有词:“魔精灵……他们都是魔族!魔精灵杀了我们!把我们困在这里……放了我们……救救我……杀……杀光魔族……”苏安听着亡灵的话语,脸上出现一丝错愕,很快又将其掩盖下去,恢复正常,他晃了晃头,试图将因为看见亡灵而出现的念头驱逐。
艾丽莎转了几圈,像是发现了什么一样:“这里有魔法阵的能量波动,说不定就是这个能量阵困住了他们。”
“那我们现在就去解开它。”雷昂说着就要跑向魔法阵,却感觉自己被人拽住,扭头一看……“苏安,你什么意思?”
苏安拽住雷昂的手腕,荀无疾也走到雷昂面前,郑重地劝他:“雷昂,别冲动。我们现在都没搞清楚,雷伊精灵这里发生了什么。贸然释放这些被雷伊精灵囚禁的灵魂,招致怎样的后果是我们现在能承担的吗?”
雷昂还想再说什么,苏安将手轻轻搭在他的左肩:“雷欧,别去。”
“为什么?苏安你还是要继续相信他们吗,哪怕事实已经在你眼前了。”苏安都不支持自己,这让雷昂心里有些烦躁,他不明白苏安为什么无条件地在袒护那些丑陋的雷伊精灵。苏安也很无奈,他选择相信雷伊精灵,只是因为感受到他们体内属于精灵的善良仍然还在,这让他不知道如何开口说服雷昂,只能固执到外人看来都有些无理取闹地看着雷昂。
拢霁拉着朔绕着骨山走了一遍,什么有价值的都没有发现,反而被乱窜的亡灵嚎得脑仁疼,不由得问:“似乎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我们走吧。”这些灵魂……好吵。
“雷昂,走吧。要是事情真如你所想,我们也会陪你回来解开魔法阵的。”艾丽莎过来拍拍雷昂,安慰道。
雷昂低垂着头,和其余人一起离开这里。正在此时,苏安余光瞥见一抹微弱的光芒,挣扎着冲破白骨的掩埋,他走过去捡了起来,发现是一个破旧的空间魔法容器,上面附着的魔力几乎消耗殆尽,它原本的主人早已化为白骨堆积在这座骨山。苏安很容易就从容器里取出了里面的东西……
那是一颗泛着柔和绿光的种子,散发的奇异的魔法气息——那是生命伊始、万物初生的气息,那是何等磅礴而纯净的生命力啊。
“这上面……和雷伊精灵相似的气息。”苏安喃喃道。
“那就去问问他们,这个,说不定可以当换取故事的筹码哦?”拢霁见这东西似乎有用,之前的郁闷一扫而光,脸上笑容浮现,惹得荀无疾在心里暗暗吐槽。“走吧。”
森林的路如老树盘根,交错纵横,几人很快又迷失了方向。有了前车之鉴,现在大家都警戒地看着四周,保持防御队形,将近战能力弱一些的雷昂和拢霁保护在中间。树木之间的黑暗仿佛隐藏了无数敌人,每行一步,都将有暗箭飞来。
苏安觉得有人在暗处窥视他们,越向前走,离那股视线越近……苏安浑身肌肉都紧绷起来,额边冷汗直冒,一个若隐若现的魔法阵在手心形成,准备随时召唤出弓箭进行战斗。
“砰——”有什么东西从树上掉了下来,几人俱是吓了一跳,荀无疾的尾巴都不由自主地蹦了出来。
定睛细看,发现那是一个长着尖耳朵的小胖子,深棕色的短卷发,浅黄色的皮肤,金色的虹膜,塌塌的鼻梁,眼睛和脸的的比例让人觉得这是一个恐怖娃娃。
树上掉下个小胖子,伊则个脑袋先着地。小胖子倔强地爬起来,手里还小心翼翼地护着一串深红色的果子,脸上还有未干的汁水,看见苏安他们,愣在了原地,一动不动。艾丽莎看着小胖子矮矮小小的,离成年精灵的身量还差得远,大大的眼睛里充满无辜,还有忍痛憋出来的水汽,看样子确实是摔疼了,走过去将他抱在怀里,温柔地问道:“你疼吗?”
或许是第一次被精灵以外的族群抱在怀里,小精灵更呆了,反应了好一会儿才对着艾丽莎傻乎乎地笑起来。他的脸肉肉的,笑起来让人感觉软软的,忍不住上手捏两把。
“真的好软啊!”荀无疾一边捏一边感叹,被苏安拍下了狼爪子。小精灵到不觉得荀无疾的动作冒犯,反而觉得开心,这群人,好像一点儿也不怕他呢。苏安试图用最温柔的语气向小精灵阐明自己想要找雷伊族长的目的,小精灵爽快的答应了。
“你们是客人吗?”小精灵牵着艾丽莎的手,之前那串深红色的浆果也分了一些给他的“新朋友”,自己也在一颗一颗地往嘴里送,浆果甜丝丝的,悠悠地直达心底。
“是啊,”艾丽莎回答道。“你的族人原本是要带我们去休息的,但是他们走得太快了,我们又不认识路……”
小精灵摸了摸鼻尖儿上的小点点,声音有些低:“他们都是这样的……都很害怕被再次伤害,所以,对不起啊……”
“不需要道歉,是我们走太慢了。”拢霁笑眯眯地说,可能狐狸的笑容都具有某种魔力,小精灵看得呆了一下。“那……那个,也不是故意不让你们跟上的,这里布下了很多法阵,只要起了贪念,就会被杀死……你们都是好人……”小精灵低下头看着自己手里的浆果,声音更低了。
雷昂想起之前荀无疾的推测,联想到雷伊精灵对外人的恶意,愈发好奇:“冒昧地问一下,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你们为什么会害怕陌生人?是发生了什么吗?”
小精灵直愣愣看着雷昂,辨别了他身上属于人类的气息后,眼底闪过一丝惊悸,小肉手猛地攥紧,别过头去,不再说话。雷昂吃了个闭门羹,也猜到了这雷伊精灵与人类有过纷争,想起骨山那处的亡魂,雷昂心中有些迷茫了。苏安看雷昂有些精神恍惚,伸出手去拉雷昂的手,却被避开了,不死心的苏安直接一把拽住,强硬地掰开雷昂紧握成拳的手,执拗地和他十指相扣。
“别多想,就当听个故事吧。”
荀无疾回头看着因为手拉手落到了队伍最后的苏安和雷昂,肉麻的舌头都吐出来了,酸,真酸。
“你还没有成年吗?”朔仔细打量小精灵,一点儿也看不出来他有成年的迹象。
小精灵见不是人类在问话,回答道:“是的。但其实我已经到了成年的年纪了,只是……我无法接受成年祝福而已。”
“为什么?”
小精灵没有回答,而是用手指向了前方。
龟裂的大地默默展示着战斗带给它的伤痕,几点青翠的苔藓只不过是徒增荒凉之色,巨大的深坑沉寂中倾诉那争斗的惨烈。最触目惊心的,是那棵枝干虬结,如同亡者奋力挣扎伸向天空的手的枯树,那原本是雷伊精灵的母树,可是它现在树干斑驳,断裂的树根合着泥土翻卷,伤口干燥缩水,毫无生机,静默地立在那里,变成雷伊精灵的象征,变成他们的伤疤。
“你们听过……魔精灵的传说吗?”在树上观察四周的荀无疾用腿勾着树干吊下来,表情故作阴沉地看着雷昂,篝火跳跃的光芒在他脸上变幻出可怖的阴影。雷昂吓了一跳,就差一药剂瓶砸在了荀无疾脸上,雷昂旁边的苏安动作迅速地实现了这个愿望,一巴掌呼在了荀无疾脸上。
拢霁手中扇子轻摇,心安理得地享受着艾丽莎的发型设计,笑着开口道:“大概是因为什么不可抗的原因入魔的一些精灵吧。”
荀无疾翻身下树,找个空地自己坐下了:“不是哦,传说是一整个支系的精灵都是魔精灵,我刚刚观察四周的时候开了一下狼眼,正巧看到传说中那片黑森林,就想起了这个传说。还说这群魔精灵嗜血残忍、邪恶残酷,还肆意奴役其他支系的精灵呢。”
“不可能。”一直沉默寡言的苏安开口了,“精灵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的记录,你在胡说。”
荀无疾挠挠头,嘟囔道:“我也是听说的啊,听到啥我就说啥嘛,怪我咯。”
雷昂感觉到身边苏安的不悦,开口解围:“传说嘛,不见得是真的,万一只是捕风捉影呢?”
“那不如我们明天去看看?狼狼,黑森林离这里远吗?”艾丽莎倒是对此添了几分好奇,百闻不如一见,若是近的话,就去看看吧。
“以我们的脚力来说,不算远,早起出发的话,中午之前就能到。”
“那就去看看吧,正巧我也好奇呢。”拢霁扇子利落一合,旁边朔也点头表示同意,雷昂看了看苏安,也表示愿意一去。
荀无疾耸耸肩,又跳上树枝:“那你们一会儿早些休息吧,我守上半夜。”
“我到时候守下半夜。”不等拢霁说话,朔自告奋勇接过了守夜的职责。
次日,一行人很快抵达了黑森林外围,这里的树木格外的高大而且密集,遮天蔽日,正午的阳光几乎被遮挡殆尽,残存的光线顽强地在地上形成星星点点的光斑。在这样压抑的环境下,六人很快就迷路了。
“真是……不安啊。”荀无疾太阳穴直跳,这可真不是什么好兆头。再看其他人,也是一脸凝重与不安。
“人……类……”声音自林中传来,喑哑嘲哳,像紧闭多年的木门缓缓开启,恐怖难听。“去死吧!”利刃裂空而来,直取雷昂咽喉。由于事发突然,饶是听到声音开始警觉的雷昂,躲避也不彻底,利刃擦着右肩飞过,带着血迹直直钉在树上。
见一击未得手,暗处的阴影发动了第二波袭击,伴随着吟唱,一个紫黑色的魔法阵展开,无数的荆棘刺自阵中飞射而出,直奔雷昂。
“保护雷昂!”荀无疾拔剑出鞘,一跳跳出了攻击的范围,跃到了树枝上。狼眼开启,黑森林的黑暗再也无法对他造成视线的阻碍,并立刻做好了反击姿态。与此同时,苏安把雷昂拉倒身后,艾丽莎上前一步,双手在身前进行格挡,粉色的魔法阵光芒闪耀,一面流淌着植物系魔力光芒的盾牌凭空出现,以强硬的姿态抵挡住了所有荆棘刺的攻击。
“抓住你了!”荀无疾瞬重华闪到一个黑影背后,长剑横扫。黑影也不惊慌,手中法杖抬起,紫色的魔力流转,藤蔓从黑影袍中钻出,朝着荀无疾张牙舞爪,企图将其缠绕。荀无疾心知不妙,急停在树枝上,脚尖轻点变换方向,躲避藤蔓的缠绕。黑影法师战斗经验不俗,荀无疾偷袭不仅没得手,反而落了下风,黑影操控藤蔓穷追不舍,一时脱不开身。
另一边,拢霁和朔也进入战斗状态。朔先是施展一个青色的魔法阵,狂风怒号而过,巨树被吹得摇摇晃晃,一个黑影踉跄了一下,眼尖的朔立刻发现了敌人所在,拢霁轻声吟唱,对朔进行了时间加持,朔突刺的速度加快,呼吸之间就来到黑影面前,趁其不备抬腿就是一个膝击,结结实实地砸在黑影小腹,紧接着一个横踢就将黑影踹下了树,来到视野广阔、更利于拢霁发挥的地面。黑影之前被打了个措手不及,被踹下来反而冷静了,纵身而起,朝一个方向飞速逼近。
拢霁眼光一扫,那里正是那颗插着那把刀的树,知道了这就是用刀的那位,嘴角冷笑:“想的倒美。”手中白玉扇展开,细微的机关声响起,细小的针朝黑影腿部飞射而去,黑影不设防备,长针入体,痛苦异常,朔此时赶到,二人交换了个眼神,朔立刻拎起这个黑影刀客,双臂用力将他扔了回去,使上自己精巧的格斗术。拢霁轻按白玉扇侧的紫色花纹,针尾的天蚕丝带着针回到扇内,拢霁便开始依照朔和黑影刀客的战斗形势从旁辅助。
艾丽莎撤回到离雷昂和苏安较近的地方,警惕地环顾四周。苏安接过雷昂的止血药剂,咬开试管塞,看向伤口,冒出黑色的血:“刀上有毒!”
“啊……没事,我这里还有解毒药剂,这是外用的,你先用这个,再用止血药。”雷昂闻言也不着急,药剂系的学生还缺药吗?从包里摸出两瓶药剂,递给苏安一瓶,自己打开一瓶直接喝了下去。
苏安照着雷昂说的做,又从魔法容器里掏出绷带,给雷昂实行简易包扎。
艾丽莎心头莫名开始焦躁不安,直接将这种感觉说了出来:“你们快点!我有种不好的预感。”
“艾丽莎!你们快跑!还有一个人!啊——”荀无疾的咆哮从密林深处传来,由于方向的不同,借助狼眼,他看见了还有一个术士在吟唱,法杖通体流转着魔力的光芒,吟唱越久,威力越大,顾不得自己还情势危急,荀无疾扯着嗓子提醒同伴,不料被法师的藤蔓抽飞,结结实实地砸在了粗大的树干上,吐出一口鲜血。
但是已经晚了,一个比之前的魔法阵庞大的法阵在三人头顶缓缓展开,花纹繁复耀眼,艾丽莎调动全身魔力开启防护盾,准备迎接法阵的冲击,苏安也不闲着,寒冰凝结的保护罩牢牢护着三人。
光柱轰然而下,轻而易举便击溃了保护罩,全力轰到了艾丽莎的保护罩上,过强的冲击力迫使艾丽莎膝盖弯曲以缓解压力,地面也渐渐出现了裂缝。
“我……有点……撑不住啊。”艾丽莎感觉自己五脏六腑都在压力下错了位,一股腥甜用上喉头。苏安伸手搭在艾丽莎肩头,将自己的魔力缓缓渡到她体内,弥补她魔力的流失。雷昂忍痛伸出右手握住苏安的手,也将自己的魔力渡给艾丽莎,同时也不忘了从魔法容器里掏出各种加防御、魔力以及回复体力的药剂用在三人身上。
术士显然不满现在的状况,他高举手中法杖,黑袍无风自动,大声吟诵神秘的咒文,空中法阵光芒更甚,光柱蛮横地冲破了防护盾,首当其冲的便是艾丽莎,蕴含魔力的光柱湮没了艾丽莎的身影,巨大的痛苦使得她惨叫出声。
“你他妈的!”荀无疾罕见地爆了粗口,过往的经历使他不愿再看见自己的同伴受伤,几个后跳加瞬重华闪出老远,在黑影法师眼里失去了踪迹。“跑了?”黑影法师鄙夷地笑道。
拢霁和朔也听到了艾丽莎的悲鸣,朔加快了打斗的节奏,拢霁也全力配合,争取尽快赶过去救援。
光柱消散,术士瞪大了双眼,喃喃到:“怎么可能!不可能!你怎么可能还活着。”
艾丽莎站在原地,双臂张开,血肉之躯死死护住了防御力不高的二人。衣服未曾遮挡的地方、破损处,乃至于脸颊眼尾,粉色的龙鳞翕张,闪耀着粉金色的光芒。就是这些龙鳞,卸掉了绝大部分的魔力冲击,饶是如此,艾丽莎也不好受,内里想必情况严峻。
“偷偷摸摸的,算什么东西!”艾丽莎右手握拳助跑几步,挥拳砸向术士所在的树干,或许是雷昂药剂的属性加成,抑或是之前二人魔力的传输,又或是她自己心中的怒火,树木应声而折,术士跃向空中,后方挽弓搭箭准备就绪的苏安一箭贯穿了术士腹部,带着冰魔法的箭矢在术士体内外结成了冰。
此时,拢霁和朔也结束了战斗,将黑影刀客用冰封锁住,赶来助战,虽然先前有不小的消耗,但是雷昂在,这些都不算事。离开了舒适的施术环境,术士显得左右支绌,不一会儿也败下阵来,被冰链锁住。
“二蛋呢?”雷昂环视一圈,唯独不见荀无疾的身影,想起刚刚他就一个人去和敌人缠斗,不由有些担心。
“我在这里。”荀无疾将昏迷的黑影法师扔到那二人旁边,从树枝上跳下来,他的模样很精彩,头发里还扎着小树枝和树叶,身上清晰可见的几处大面积的淤青,嘴角还挂着血渍。“你们放心,二蛋没有逃跑,二蛋就在附近。”看着几人目光里的担忧,荀无疾挠了挠头,扯出一个微笑。
“才不是说你逃跑呢。”艾丽莎跌坐在地上,她有些脱力,想休息一下。
苏安来到被冻得只剩头在外面、尚有神智的两人面前。蹲下,平视他们:“你们,也是精灵,对吗?”
“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