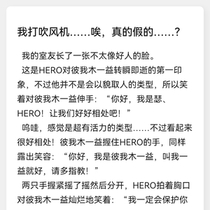字数:1342
+++++
“这在VR游戏里常见吗?”一足鸟仰着头问。
“非VR里挺常见的啦,卡bug,就不知道这边是不是故意用的黑科技。”周一坐在天花板上回答。
一条水蛇自在地在他们之间游走,周一随手一戳,飞溅的水珠眼看要滴到一足鸟脸上,却在半空中一改方向,犹犹豫豫地贴上了天花板。
这太怪了。物理引擎的问题?一足鸟欲言又止。止得不完全成功,至少周一完全注意到了。
“鸟哥,鸟哥,你有没有什么想说的?”他一手比作喇叭一手握拳假作麦克风,只恨还缺两只手框成镜头。
“没有,我天性不爱说话。”一足鸟赶紧低下头,假装在沉迷公共频道。
真是奇怪,在连头盔都摸不到了的此刻,系统面板及聊天界面竟然依旧存在。公共频道的消息刷得飞快,有人在求助如何制服被激怒的水管的(答曰:吹曲子给它听),有人发现自己的“房间”是停尸房睡着硌得慌,有人问他要不要换来法老陵寝睡,有人就着七彩炫光在大圆床蹦迪,还有人在房间里演出维纳斯诞生的。
相比较之下,只要忽略“床和洁具都固定在天花板”这一点,305B这间配置堪比四星级酒店标间的房间简直普通得让人意外。
可是有人乐于平凡,就有人不甘寂寞。
“我们也可以演名画啊,演宙斯伸胳膊那张……那张画叫啥来着?我觉得还挺好玩的!”
周一盘腿坐在床上,往身上披了半拉床单,上半身前倾、从指尖到上臂都直直抻开。这真的非常形象,看到这一幕的人都会觉得名画之名呼之欲出,但一足鸟移开视线,坚定地说:“我也不记得了。”
其实没忘,叫“上帝创造亚当”。但一足鸟既不想当上帝也不想做亚当,只好强硬拒绝和周一联袂演出世界名画——尽管操作简单还能顺势演出get down,但四步变身全自动洗衣机实在太怪了。
《四步玩转世界名画复刻》
步骤一 一方倒立
步骤二 双方伸手
步骤三 指尖维持在几乎相碰位置
步骤四 指尖接触,进入get down阶段!
——以上305B游玩指引,由游戏主播周一热情总结并发布在公屏。
“周一,想想办法。这样摇人不现实。”一足鸟说。
“鸟哥,想开点,可能下一个人知道该怎么办。”周一躲开水流说,“大不了我们轮流睡地、嗯、天花、呃...随便啦,来都来了。说来不知道这里隔音怎么样啊,会根据空间不同完全隔音吗?”
红发的主播随手敲了敲墙。这看似结实的玩意立刻像超级玛丽里的金砖一样开始往另一侧凹陷,还闪起了半透明的涟漪。
“哈哈哈打通的话是不是会有奖励?这算消消乐吗?”周一敲得更起劲了,墙对面的景色逐渐变得清晰,隐约可见有另两道身影正慌张地跳起来,还能模糊地听见人喊:“呜哇这墙怎么了?是不是隔壁在做什么!”
是的,确实是,但马上就会结束了!
一足鸟纵身一跃去抓周一的手腕,决定舍身取义拼着get down梅开二度也要阻止墙被打穿。不幸的是,人在着急时容易用力过猛——一足鸟失去平衡准备摔个倒仰——回过神时也站上了天花板。
仿佛被脚后跟踩稳的清脆声响踩中七寸,游动的水蛇“哗”地散了架。“异常”也随之烟消云散。水渍普通地摊在“地上”;衣柜里的熏香散发着幽香,一足鸟已经握住周一的手腕、但这次两人并没有开始自转。
“我去!”周一感慨地吐出一口气,“合着我们回来得先倒立哈,这不和人每天打赌就亏了。”
一足鸟也难得松了口气,嘴角往上抬了五毫米,只是他还没来得及张嘴——
“你好我想玩世界名画模仿!!”
……有人以指尖上举的姿势推门而入,正巧碰着了一足鸟的头顶。
一切都晚了,一切都完了。
【Get Down*3人版,启动!】







作者:青芒子
评论:随意
备注:
1.看到火种脑里都是梅梅,忍不住下床爬出9k的告白信,虽然主角是银色泪滴和阿褪,但其实都是为了梅梅。
2.世界观属于老贼,设定部分来源于银色泪滴废案,维克废案,叛律者废案,其他设定都是私设,ooc预警。
3.哑巴阿褪,不方便用第二人称,使用了男性龙祷出血流的设定。
1.
迪克达斯大升降梯旁的赐福,阿褪正沉默地擦拭着自己的猎犬长牙,盔甲上覆盖着繁复的雕花,在暖黄的赐福下泛着冷冽的银光。冷酷无情,暴戾恣睢。在大赐福里的各位都是这么评价阿褪的,只有罗德莉尔摇了摇头,捏着自己红色披风的衣角,她初来乍到,不敢大声言语,却在这件事上出人意料地坚持着,“阿褪大人,是一个很好、很温柔的人。”
阿褪听到一定会很感动,他正好下了几个墓地采了不少墓地铃兰,送给罗德莉尔精进她的调灵技巧正好。但如今他正在和阿什米在脑袋里争论不休。
“大人,我的大人,梅琳娜大人是不会为了这件事停下她的脚步的,即便我告诉了她夏波丽丽葡萄的事情,她也没有回应,你又何必耿耿于怀?”
“阿什米,你没有看到吗?那个火焰能够使人癫狂,我在里面看到了绝望和火焰,黑色和黄色交织在一起,他们好像在侍奉它——癫火。”阿褪一面回忆着自己在颠火村的经历,想到自己被目含黄焰的大老鼠咬死,想到自己看到那村民入魔般跪伏在黄焰之下,自己的脑浆也随之燃烧起来的经历,就不免发怵。
“我知道的,大人。但交界地还有更多可怕的事情,你知道盖利德吗?那里被猩红腐败所控制,一旦踏入你的血肉就会逐渐腐败,最终变成行尸走肉,游荡在那片土地上。”阿什米冷静地劝说着,阿褪在利耶尼亚捡到了她,她说自己刚从地底逃出来,希望能放自己一马,作为回报她能够增强力量。
当时的阿褪刚击败了满月女王,拿到了第二片大卢恩,还没决定之后去哪,见她没有恶意,也就答应了。阿什米融入了阿褪的身体里,也意味着她能够听到阿褪说话了。阿褪也开始可高兴坏了,拉着阿什米从烤陆生海鞘的味道到魔法学院里的螃蟹打人超疼说了个遍,多亏阿什米不是人,不然早被烦死了。
阿什米常常在阿褪身体里注视着他,知道他最喜欢去探索地图摸箱子,最宝贝他的猎犬长牙,知道他全神贯注的时候会下意识咬嘴唇;知道他怕黑,知道他最讨厌墓道里的小怪兽,每次都得先给自己身上上几个圣防御。
他哪是冷酷无情,他只是太孤独了。
直到那一天,那个粉发的女孩在赐福边现形,她留着贵族样式的过肩卷发,右眼是浅淡的金色,左眼之上却横亘着一个爪样的诅咒。她没有看向阿褪,而是看向了自己,杀意乍现。
但少女只是沉吟片刻,“……你的身体里,还住着另一个人吗?我没有从中感受到恶意,就交由你判断了。你好啊,另一个你,我名为梅琳娜,正在和这个人一起旅行,我们可能得共同度过一段时间了,很高兴认识你。”
阿褪虽然面上还是不苟言笑,内心早就在放烟花庆祝了,“阿什米!木头终于跟我说话啦!她在关心我欸!你听见了吗?呜呜她人真好。”
阿什米第一次觉得这个家伙好吵,不去理他,而是朝着少女微微点头,“你好梅琳娜,我是阿什米,很高兴见到你。”
梅琳娜闻言只是微笑,配上旅行者套装的她此刻就像是涉世未深,背着家族跑出来冒险的单纯贵族小姐。但她现在却和自己类似,半透明的身体散发着微弱的蓝光,是不得不依附阿褪存在的灵体状态。
“今日时间不早了,明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早点睡吧,晚安阿什米、托雷特和阿褪。”
“欸……!”随着梅琳娜消散在夜空中,黄金树的树叶如雨般飘落,像是碎落的黄金,两人眼中皆是一惊。
“她居然能听到你说话!”
“她居然能听到我说话……”
“这真是……”“我很抱歉。”
“太好了!”阿褪此刻正咬着唇,那双有些龙化的竖瞳里多了一些以模仿他人而存在的仿生泪滴看不明白的情绪,但她能感知到他现在很高兴,几欲落泪的激动,“她能听到你说话的话,我就能和她说上话了,我有好多好多事情告诉她,白金村和白金之子的事情,那个盲女的事情,还有那些黑夜骑士。”
“我真替你感到高兴呢,大人。”道歉的话没能说出口,不知为什么,意识到自己和阿褪有所不同的阿什米心里闷闷的,像是被菈妮的暗月魔法冻住了,怎么也化不开。
2.
见阿什米不愿再说,阿褪只好泄了气般向后倚在满是黄金树树根缠绕的墙壁上,盔甲发出一声脆响,有个小袋掉了出来。
那是指痕葡萄。
在他即将离开魔法学院的时候遇到了那个盲眼女巫海妲,她说还需要指痕葡萄就能看到神的指引了。之前她便拜托过自己收集所谓的夏波丽丽葡萄,被黄色妖火灼烧过的眼球,但她似乎并不知道,说那是甘甜美味的葡萄。
很怪。
随之便是在颠火村后,阿褪发现山上还坐落着一座教堂的废墟,教堂一般都会有好东西,于是阿褪骑着托雷特就朝那赶去。半路却被迫下马,红灵入侵,那人眼中迸溅出的黄焰和癫火如出一辙,黄色的颠火划空而来,火星飞溅,脑袋被火星砸到后剧痛难忍,像有什么要顺着神经和脑髓长出来似的。
阿褪只好持盾躲闪,红灵借机逼近,那人耍得一手战矛,对着盾牌又戳又踹。阿褪之后收了盾朝后翻滚,一面与之周旋,一面悄然在曲折如犬牙般的长刃上涂上带着火伤的油脂,在对方向前戳刺的空档,跳起横劈,红色的火光与战矛相接,金鸣铿锵。那人被火焰灼伤,朝后退了几步,手中闪现出黄色的印记,一朵黄色的火焰便腾空而出。
“小心!”
阿褪躲闪不及,只能举盾防御,但撩起的火焰还是几乎把他掀翻在地。不对劲,阿褪看向这个陌生的红灵,自己不是第一次被入侵了,但是这个红灵,或者应该称他为“灼烧指痕”维克,他攻击模式很是单一,没有使用战技,远处用癫火偷袭,近了就是战矛,不像是褪色者,更像是徘徊在交界地不得往生而失去理智的本地人。很快,阿褪便用盾反让对方一个踉跄,趁机抓着龙饗印记腾空而起,手掌幻化成亚基尔的头颅,随着吼叫吐出岩浆一般的烈焰。破防的维克很快抵挡不住,消散在原地,随机在原地留下了那颗指痕葡萄和那把战矛。
带着指痕烫伤痕迹的眼球,汩汩流出金黄色的泪水,似乎能听到痛苦的悲鸣。那把战矛也浑身布满了灼烧的痕迹,自内而外的燃烧着。阿褪不禁倒吸了口凉气,这到底是怎么一种恐怖的火焰,竟然蕴藏着毁天灭地的能量。
“大人,没事吧?”阿什米关切地声音响起,“对不起,我似乎无法在这里出现助你一臂之力。”
“我没事。”胸前和手臂上的盔甲已经有所融化,滚烫的金属烙进了皮肉,但他还是故作轻松地摆了摆手,拾起那把战矛朝前方的教堂走去。
“那个维克似乎是不想让我们接近这里。”一觉踏入倾圮的教堂,就发现原本塑着玛丽卡石雕的位置旁,一个指头女巫扮相的少女低垂着头颅,胸前和身下都满是血污。血的气味已经有些发臭,但是浓稠的血液还未凝固,在地面上泛着白光,意味着她其实刚死亡不久。
“即使引导早已破碎,也请您登上艾尔登之王。”阿褪喃喃道,他鬼使神差地想要触碰少女的面颊,苍白的,甚至有些发青,头发一丝不苟的束拢在帽子里,除胸前外服饰还很整洁,手里还握着圣印记,似乎临终那刻都还是神最虔诚的信徒。
悲恸在身边蔓延开来,尝起来像是亚人的血,腐朽的棺椁和金属的味道。阿什米意识到这似乎是她的大人第一次为陌生人悲伤。但她真的是陌生人吗?他似乎在透过她看着某个人,死那个在风雨交加的夜里,周围满是尸体的王侯礼拜堂里的女巫。
每一个褪色者都会遇到属于自己的女巫,他们会一起旅行,一起冒险,一起成为艾尔登之王。但是大人的女巫一开始就死了,他亲手用她的血染红了立誓布,他从一开始就是孤身一人。哦不对,陪伴着他的还有托雷特,牛与马的混血种,以及那个名为梅琳娜的虚弱灵体,虽然能行使女巫的职责,但无法在赐福以外的地方出现,更别提大人无法言语,更多的时间里只是梅琳娜向阿褪诉说着这片土地原来的故事。
“大人……”阿什米不禁出声,“她似乎是自杀的。”
“嗯,她握着这把匕首捅向自己胸口的,但是为什么呢?现在能拥有女巫的褪色者已经屈指可数了,她的褪色者怎么不在身边?”
“或许他已经失去了赐福,永久地沉睡在某地了吧。”现在的褪色者大部分已经看不见赐福了,那个指引他们前行的神之恩赐,这也意味着他们失去了重来的机会,为了保命只能碌碌无为的在交界地游荡着。
但阿褪这次没有回应她的话,而是握着那把自燃着的战矛若有所思。
3.
在进入王城之前,阿褪答应阿什米,帮她打倒了碎星,当然也有为了菈妮的私心。阿褪或许一辈子都不会知道,阿什米最喜欢他在红狮子城庆典的样子,阿褪和狼人布莱恩、战士壶亚历山大,以及很多很多慕名前来的褪色者、英雄们齐聚一堂,推杯换盏,引吭高歌,壮士出征的离歌雄壮而哀伤,似乎是在为交界地最后一位将军所唱的挽歌。
盖利德的战场上满目疮痍,四处都是倾倒的战旗和零落的盔甲武器,无一不昭示着这里曾发生过一场鏖战。碎星将军拉塔恩与女武神玛莲妮娅在这里打了一战,碎星下身被腐败侵蚀失去理智游荡在战场上半死不活,玛莲妮娅身受重伤下落不明。
于是大家在红狮子城给这位曾经深受民众爱戴的将军举行了庆典,引来交界地最英勇无畏的战士来击败碎星。那天阿褪破天荒的喝了很多酒,战场上血残阳如血,黄沙漫天间碎星大箭破空而来。
“当心!”阿褪按着阿什米向前扑倒,那只带着陨石重力的大箭就擦着头皮飞过,“我来引敌,你们就上前痛快一战吧。”
阿什米能闻到他的颈间还残留着酒的味道,通过盔甲的细缝,那双龙眼似乎还有些迷糊,但是他已经进入状态。碎星似乎认出他会是最终与他决战之人,一开始就针对阿褪出击,身边不断有战士向前冲去,又被碎星一刀斩于马下。阿褪的身形本来就很娇小,但在碎星面前简直是芝麻和西瓜的区别。但即便如此,阿褪一刀劈下龙首的能力也不容人小觑。
血染红了黄沙,阿什米虽然能够模仿阿褪的能力和武器,但是人的理解毕竟有限,这把猎犬长牙在阿褪的手里像是活了一般,向着敌人露出狰狞的獠牙,砍劈切割无所不能,鲜血随着动作在黄沙里开出灿烂的红花。
而碎星似乎修习外神的能力,一颗颗巨型陨石从天而降,把地面砸得千疮百孔,无数人葬送在这招之下。只有亚历山大勉强能用自己坚实的外壳硬抗下这一招,阿褪和阿米什只能东躲西藏,以免被砸成肉饼。
“阿什米,用圣之防御!”
“可是大人!”你不在这里面啊!
随着一道刺目的圣光,碎星挥舞着大剑的手一顿,身后跃起一个小小的影子,奥桂尔的咆哮震彻天地,大家都不得不捂住耳朵缩在阵法里抵抗着。碎星身子一僵,但很快恢复过来,扭头大剑随即向后挥去,却被巨龙吐出的腐败气息喷了一身。
碎星痛苦地嘶吼,大剑朝阿褪一砸,地下瞬间多了一个深坑,阿褪虽然用龙头卸了部分力,但是这一剑还是实实在在砸在了他胸口上,喷薄而出地血液撒满了银甲。只差一招碎星就将自己置之死地,但是随着燃火的刀刃一击侧劈,本就染上猩红腐败的碎星就像是一座岌岌可危,满是蛀眼的木塔,被这根火柴轻易地点燃。
随着碎星不堪其负地倒地,随即被其他人围上前去围攻。和自己张得一模一样的阿什米扛着还在滴血的猎犬长牙,朝着自己伸出了手,自己嫌重穿着的轻甲在她身上镀上橘色,背后的披风随风飘动,英姿飒爽。
当晚的庆功宴上阿褪喝得醉醺醺的,说要拔狼哥的毛给她织毛衣,阿什米只好暗暗现形拉住他不安分的手。一旁的布莱泽还不知道他旁边的阿褪打起了他的主意,还在邀他吃酒。
“阿什米,今天我很开心。”大家都醉得七倒八歪时,阿什米和阿褪坐在观星台上俯瞰那片战场,远处一轮明月伴着潮水送来湿气,天上重新出现的星子明暗晦涩。
“大人,我也是。”
“我是说,和你并肩作战,我很开心。”
“大人啊……有没有人说过,你其实很温柔呢。”阿什米知道阿褪不会再回应,因为他已经累得睡了过去,阿什米悄然显性,让他枕在自己腿上,仰头望向重新流动的繁星,“真美啊,原来这就是真实的星星啊。可惜……”
4.
阿什米原本以为在希夫拉河底的诺克隆恩就是他们诀别之地。在那之后,大人将成为艾尔登之王,而她将会统治地底世界,成为永恒之王。
但未曾想到阿褪会因为要前往树根底层重返地下,导水河边他俩再次相遇。王是不能相见的,两王相遇必要拼个你死我活,阿什米本有自信击退所有来犯者,但那是她的宿主大人,那个她拼尽一生想要模仿的对象。
“大人……太遗憾了,我们之间不能共存,这一次我将……”阿什米的声音止不住地颤抖,她在恐惧,她在悲伤,无论结局如何,都不是她想要的结果。
“阿什米,在战斗之前,我想和你说个故事。”阿褪没有出手,只是把他的剑重新背回背上,他又换了件铠甲,后背是厚重的毛毡一般的披风,似乎有点像是布莱泽穿着的那套。
“你还记得我们在镇静教堂遇到的那个入侵者维克吗?我在雪山的准王监牢里遇到了他,他已经疯了,盔甲上都是被指痕溶解的痕迹,就和那个红灵一模一样。但是他却没有使用颠火的祷告,而是古龙的龙雷,传说中的龙王兰斯桑克斯是他的朋友。他是最初圆桌厅堂里的英雄,是最接近王的人,但是他自甘堕落授赐了颠火,变成了这般不人不鬼的模样。”
“是么?”在离开阿褪的这段时间里阿什米学会了独自思考,虽说连智力都是模仿而来的,但这一次强烈地感受到阿褪话里的不自然。
“你也不相信对吧。”阿褪轻笑,“我也是。我在雪山入口遇到了夏波利利,他说不要烧了那个可怜的女孩,我才是那个火种。”
“巨人大锅的火焰,原来需要火种才能点燃啊。”阿什米并不知道这段秘辛,只能随声附和道,“你是说,那个维克也是为了烧树而受赐癫火的。”
“对,癫火是混沌的力量,能够将世界的一切化为乌有。”
阿什米心中一凛,抬头与阿褪的目光相接,金色的眼眸里有火焰在跳跃,似有燎原之势。阿什米喉头一紧,干巴巴地开口:“大人你、受赐癫火了,你怎么能抛弃这个世界的生命?你怎么能?!难怪呢,梅林娜已经不在你身边了。”
阿褪没有回话,而是躺倒在瀑布旁的礁岸上,导水河的上空是绚烂的繁星,虚假的星空呈现出瑰丽的紫色,给地底世界的人民带来一丝重返陆地的期盼。
“你和阿梅说了一样的话。但是如果我不成为火种,那么要烧树的人只能是阿梅。旅行的终点,就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同伴在面前烧死,这像不像是玛丽卡跟我们开的玩笑。”阿褪有些自嘲地说,但笑容里却遮掩不住的落寞,“然后我就明白了,维克一定是知道了这件事。他不想让他的女巫牺牲,于是选择癫火。但他又过于愚蠢,没有三指女巫的教导,穿着衣服就接受了三指的拥抱,最后才沦落成如今这般自甘堕落的下场。”
“所以你成了癫火之王。”
“是啊阿什米,我已经成不了艾尔登之王了。终有一天我脑袋里的这玩意就会顺着我的眼睛,我的耳朵里爬出来,侵占我的身体,驱使我的行动,那都不是我。”
“是癫火借你的躯体降临,是神降……”阿什米轻声吐出最后的结论,交界地已经有多少年没有神降?破碎战争之前?巨人之战之前?还是拉达冈成为王夫之前?那都太久太远了。诺克一族便是以造神的名义将她创造出来,但却招致了无上意志的愤怒,将他们砸入了地下百年。
无上意志尚且如此,更别提以混沌为最终目的的癫火之神。不行,绝对不行!她绝不允许交界地变成一片火海。
“我想请你帮个忙。”阿褪朝着阿什米伸出手,“杀了我,我烧完树之后,如果失去了理智,你就把我杀了吧。如果癫火很棘手的话,可以找阿梅帮忙,她说过,再见到我的时候一定要给我送上命定之死。”
阿什米望着那双被指痕灼伤的手,背过脸去不愿面对,“我的大人啊,你又何必如此……”
5.
梅林娜即使在赐福处也不常出现,似乎是徘徊了太久而导致的灵体虚弱的缘故。但是阿什米没跟阿褪说过,她其实看得见梅林娜的灵体,淡淡的蓝色身影,和阿褪面对面端坐在赐福前,像是一起旅行的同伴那样。
梅林娜有时候会和阿什米搭话,她离开赐福的大半时间都在沉睡,无法及时给阿褪提供帮助,于是她时常会询问阿褪的近况。他们又旅行到了哪里,阿褪今天都下了几个墓地和洞穴,和大赐福的同伴们相处得怎么样,还有帕克过得好吗——那个亚人裁缝,她似乎很关心他。不,应该说她很关心阿褪身边的一切。
那股被冻住的感觉又来了。她一直能感受到作为宿主的阿褪的感受,一开始她还会天真地开口问阿褪,为什么你看到墓穴就有夏亚果实那种又酸又甜的味道,为什么你被黑夜骑士揍趴下的时候内心有股火星蝶烫烫的感觉。
阿褪也是好久没人和他说话了,于是也絮絮叨叨地回答着。我看到墓穴既高兴有宝藏又害怕藏着什么恶心人的坏东西,所以说是酸酸甜甜的,是吧托雷特,就跟你喂你吃的果干一个味啦。黑夜骑士那个混蛋有什么好说的,天天骑个马用铁棘扎我屁股,不讲武德,火大,十分火大!
原来这是失落的味道啊。阿什米这么想着,继续和梅林娜说着阿褪的事迹,梅林娜听得很认真,赐福的暖光熏得她面颊有些发红,时不时评论几句,这一夜就这么过去了。当阿褪睁眼之时,她便悄然离去。
阿什米曾问过原因,梅林娜没有明说,她呢喃着她的记忆和使命,似乎格外的重要。现在阿什米明白了,梅林娜害怕与阿褪有过深的羁绊,就像是褪色者和他们的指头女巫那样,生死相依。她太温柔了,害怕阿褪伤心,她从到来那一刻起,就知晓自己牺牲的命运。
人类可真是迷人,银色泪滴一族自从被创造出来的那一刻起便要求模仿强者,学习他们战斗的方式,学习他们御敌的思想,这一切都是为了挽救永恒之城。但是她在阿褪身上学的最多的却不是这些,而是学习怎么成为一个人。他随手撒落的火星,都在秋风过后燃起了熊熊大火,让邯郸学步的她几乎要在这片浓烈的感情之火里焚烧殆尽。
于是她再次和他踏上了旅程,去到雪山之巅,巨人大锅边上。巨锅深不见底,俯瞰似乎能看到风雪在锅里肆虐,巨锅的边缘绵延数十里,抬眼便能看见璀璨的黄金树。可以说这里是除建立在黄金树下的王城罗德尔外,最接近黄金树冠的地方,也难怪玛丽卡要出征前来打败巨人,封锁巨人大锅。
阿褪牵着托雷特走了许久,北风把他的斗篷吹得猎猎作响。不知过了多久,他停住了脚步,前方有一簇小小的赐福,幽黄的光辉在皑皑雪地里显得如此单薄。
“到了。”阿褪取下了猎犬长牙,摩挲着这把陪伴他最久的老伙计,“这把刀就送给你吧。碎星那一下,帅呆了!”
“嗯……”
“对了,我攒了不少锻造石,不知道你们黑夜武器能不能用得上,用不上送给铁匠吧,他巴不得800卢恩全收了呢。”
“好。”
“还有这些依灵墓地铃兰,你现在不是灵体了,还能用吗?我还有几个骨灰大哥大姐,你如果用剩了就拿给他们,别浪费了。”
“还有……”阿褪絮絮叨叨说了不少,几乎要把托雷特的木箱给掏空,托雷特一脸嫌弃地嚼着干草,似乎在想自己主人发什么神经,对着空气说些什么。
离开了地底只能作为灵体存在的阿什米微微一笑,“我知道了,大人。我一定会给你带到的。”
“好……”
阿褪深吸一口气,向大锅探除了手,只见一条火舌从锅底窜出,瞬间攀附在阿褪的手臂上将其点燃,随之而来的是整个上身,再到脑袋,阿什米只觉眼前一黑,两人便坠入了大锅的深渊里。
6.
耳畔是风声,阿什米再次醒来的时候只觉得天地间亮得惊人,周围盘旋着飞龙和龙卷风,巨石破碎形成的断垣残壁竟飘浮在风暴的中心,比建筑矮数百倍的阿褪整艰难地在其间跳跃着。
“大人,这是哪里?”
“大人?大人!”
但阿褪就像是没听到她说话一样,穿梭在倾斜的建筑里,同那些凶狠野兽们斗争着。虽然用癫火引燃了黄金树,但似乎神降未如期而至,她的大人还在这里,真是太好了。
“阿什米,要是你能看到就好了。”阿褪翻过了屋顶,站在一处庭院里,那些繁盛的花朵和精致的雕像无一不显示着这里曾经的辉煌,镀金一般的植物就像是自己的故乡那般。
“大人,我在看呢。”
阿褪卸下了头盔,想要在这里休整片刻。却不曾想红灵再次入侵,是“叛律者”贝纳尔,他的铠甲像是一头公牛般雄壮,胸口刻有小型野兽群的花纹。扛着的两蛇交错如锤的吞食权杖也绝非凡器。
他是怎么来到这里的?他不是在火山官邸里吗?
但是阿褪还是没有注意到敌人的逼近,被火烧过之后他似乎复活就变得十分困难,伤口恢复的速度也变慢了许多,以至于他不得不停下来喘口气。
“大人!小心啊!”护主心切的阿什米像是受到了神的感召,就这么凭空出现,替阿褪扛下来那一下跳劈。身后的阿褪随即召唤出龙雷径直投射出去,霹雳雷惊,贝纳尔吃痛地以手撑地。
“你烧了树,你竟敢……烧了自己的女巫!”贝纳尔悲痛地呐喊出声,“你这个叛徒!连自己女巫都保护不好,和那些盲从黄金律法的废物一个样!”
我听不见,看不见,也不会感到迷惘,只会朝下定决心走的路前进。贝纳尔所穿戴的聚兽铠甲如是说。阿褪力竭躺倒在地,阿什米也维持不住身形,只能重新回到阿褪的身体里,好在他两又能对话了。
“废物……”只听阿褪心里这么感叹道,“还是第一次有人这么称呼我呢。”
“大人,贝纳尔应该是具有成王资质的人,他是初代圆桌厅堂的成员吧。”
“是,他是其中之一,而且他烧了自己的女巫,但黄金树却没有燃烧。之后的他便背弃了黄金律法,转而投靠亵渎君王拉卡德,以屠杀褪色者为己任。”
“听不见也看不见,真是很无赖的做法。”阿什米见阿褪掬起一抔黄土,将贝纳尔就这么埋葬在这处远离交界地的天空之城,“火种不能是无辜的少女,只能是我啊……”
阿什米听到了阿褪话中那点命中注定的使命的意味,一如那日梅琳娜单薄的身躯蜷缩在赐福前,少女的脸庞一如既往的波澜不惊,话语却是那么坚定不可动摇,“那是我母亲给予我的使命,现在也是我想要去做的事情。”
本是同伴的两个人,不约而同的选择牺牲自己成为火种,以保全另一个人。无独有偶,交界地也曾有两位褪色者这么做了,一人烧了女巫,一人受赐了癫火,但都无济于事。因为只有梅琳娜才是火种,才是燃烧黄金树的命定薪柴,也只有同时被二指和三指选中的阿褪,才能成为艾尔登之王啊。
“前方已经没有阻止我们的人了,”阿褪弹了弹身上的尘土,重新站了起来,瘦小的褪色者在巨大的圆顶庭院里有些摇摇欲坠,“阿什米,我们再来一次,释放命定之死,然后杀了王。”
7.
死亡是什么感觉呢?在遇到阿褪前阿什米其实感觉不到的,作为人造生命,感情其实是弱点,诺克斯人曾想剥夺这一切以求创造出能够弑神的人选。
她不允许害怕,不允许去畏惧死亡,她是最终要成为王的人。她曾对那些贪生怕死的褪色者嗤之以鼻,但她在阿褪体内却见到无数的死亡。为宿命心甘情愿而死的罗杰尔,为使命慷慨赴死的菲雅,为理想爆体而亡的亚历山大壶,还有不屈服命运战死到最后一刻的狼哥布莱泽、米莉森。他们处于本能的畏惧着死亡,却能在最后死亡到来的那一刻甘之如饴。
人类真是有趣的生物。
恐惧……像是穿过安瑟尔河的阴风,带着腐败生灵的刺鼻气味,让人生厌。但当在石舞台上真的感受到的时候,阿什米不由自主地双腿发颤。
前一秒还在和她弹冠相庆的阿褪,下一秒就双手捂住自己的眼睛痛苦跪地,阿褪说不出话来,只能发出呜呜地悲鸣,黄金色的泪水从他指缝中流出,溅落在地便成了黄色的、扑不灭的癫火。
“阿什米!杀了我,快!”
“大人,对不起,我做不到……”阿什米感觉自己被恐惧抽走力气,全身上下如灌了铅般沉重,只有泪水是自由的。在被模糊的视线里,看着她的王在逐渐消失,那股来自异世界的灵魂失去了赐福的庇佑,被癫火取而代之。午夜梦回,阿什米时常想起那股幽怨的味道,她从未胆怯过自身的死亡,而是在恐惧阿褪的离去,那些美好愿景在那一刻里分崩离析,尽数破碎。
火烧起来了,火舌和热浪虎视眈眈着石舞台中唯二的薪柴,黄金树的内部发出绝望的呻吟,要塌了,要塌了,整个世界要被付之一炬。阿褪的盔甲被融化了,取而代之的是耀眼的火焰燃烧着的头颅,内部扭曲缠绕成诡异的符文,似乎多看一眼便会被抽取灵魂。
“阿什米,辛苦了。”有什么人拍了拍她的肩膀,夺人的黑炎从身边掠过,撩起一阵凉风。阿褪,现在应该是癫火之王的胸口多了一把黑刀,象征着死亡的黑炎喷涌而出,与癫火纠缠在一起。她身前的粉发少女还是一袭旅行者套装,风尘仆仆像是匆匆归来的旅人。
对面的癫火之王没有理会,而是燃起手中的火焰朝四周播撒,在顷刻间膨胀了千百倍的癫火面前,那把短刀小的可怜。但梅琳娜只是在身边升起了护盾,将自己和阿什米保护起来。
阿什米艰难地控制着自己的双腿站起身来,一旁的梅琳娜粉发飞扬,宵色眼眸似是故人归来。只见癫火的左手缓缓伸起,握住了那把短刀,黑红色的火焰灵巧如小蛇般窜上手臂,又被另一只满是癫火的手在途中拦截。
两股力量在一具身体上扭打了起来,盔甲早已在烈火的进攻下融化,只能勉强看出之中的人形。交界地的民众曾为了追求死亡,祈求让亚基尔的龙炎灼烧他们的身体,但即使身体与焦炭枯骨无异,他们的灵魂还是无法解脱,只能靠灼烧理智变得麻木。
癫火之王无力地跪倒在地,癫火里包含着愤怒朝着黑炎进攻,但黑炎就像是泉水一般源源不断地从刀口流出,每走一步就浇灭一簇火焰。
梅琳娜缓步走出结界,她的斗篷散落,很快被火舌吞没。她无视那股使人陷入癫狂的火焰,紧握住那只左手,就像是他们在赐福前做了千百次的动作那般,将卢恩化作力量,更强的火焰迸发出来,像是开了闸门的水库,黑炎将两人笼罩在其间。
“永别了,褪色者。”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