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荐配合音乐The Last String-Jacoo食用』
今天的大海,比以往要热闹不少。船只停泊得比以往哪一日都密集规整,高高挂起的旗帜在蓝天之下鲜明耀眼,举着香槟的镇民群众和带着徽章归来的船员们正在欢庆。声音远远地传过来,有兴之所至的模模糊糊的闲聊,还有高歌和大笑,让一贯怕吵怕热怕人多的人都不自觉远望出神。
真是难得,有这么快活的日子。
雪维利尔抿了一口小酒,侧着靠在墙壁形成的阴影里,半是惬意半是糊涂地眯了眯眼睛。
今天是属于海员们的节日。船只都靠岸开放展览了,甲板上的高脚杯和阳光一样温热透亮,沙滩上也满是参观庆祝的人。雪维利尔兴致忽起来看看,又懒得下去玩,就在最近处的酒吧高台上找个阴凉处坐下。
实话说她酒量不太好。今天她不知怎么的很有兴致和冲动,就点了酒;只是没想到,这才一杯就有些懒困。
喝吧,最多不过回家贪睡一觉。雪维利尔不在乎地想着,又抿了一口。酒液润上她的双唇,给平时的淡色带来轻红湿软的水亮,连着双颊也有些泛潮。她渐渐觉得身上发热,就拨开额角的碎发,闭上眼睛感受恰好吹来的风。
穆萨也是来游览的。相比起大街上,她更喜欢大海——尽管现在的大海也很吵。
她喜欢看着小孩子们举着玩具飞奔过细沙的样子,喜欢阳光温热地抚摸她的肌肤的触感,还有似乎随着节日一起欢快起来的海浪声。不论如何,她是喜欢节日的氛围的。
她过来得早,在沙滩上陪着小朋友们玩了一会,被折腾得身心俱乏,就到最近一座高塔上来寻清净。谁想才一上来,就看到雪维利尔这幅独自倚倒醉醺醺的景象。
好好的节日,她怎么一个人?
穆萨看得好笑,径直走过去坐在她对面,悄悄地也不出声。雪维利尔感觉有人来了,睁开眼睛,看见在风中微微飘扬的灰发和那双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失神的眼睛。
她愣了一下。“穆萨?你也来了。”
穆萨点头,一边把外套脱掉搭在椅子上。“嗯,我上来休息。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喝酒?”
雪维利尔举了举高脚杯。“不好吗?”
“你很少喝酒的。”
说得不错。雪维利尔一向觉得,酒精使人精神恍惚失去自控能力,虽然一时快乐,但实在不是什么好东西。不过今天是节日,喝一点也不妨事。尤其现在只有自己一个人,有风阳光和大海,多自在……
……哦,一个人。
雪维利尔终于觉出哪里不对了。看看底下金黄的沙滩,节日哪有一个人过的?
那就再喝一口吧。
雪维利尔仰脖把杯中红酒一饮而尽,杯底残余的液体仍是优雅摇曳的酒红,看得穆萨有些茫然。
今天的雪维利尔……真是说不出来的特别啊。
她这么想着,眼疾手快一把夺过雪维利尔才要伸手去拿的红酒瓶:“看你这样子……你今天喝了多少?”
“不多,也就两三杯……”
“……”
两三杯就能喝醉了……?穆萨看向手里红酒,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雪维利尔半点没觉出穆萨的惊讶,仍道:“你要来点吗?”
“……不用了。”否则待会就要出现两个迷迷糊糊的醉鬼了。
雪维利尔闻言放下杯子,探究地看向穆萨。穆萨对上她略显涣散的眼神,头痛地叹了口气。“要不,去沙滩散步醒醒酒?总在这里待着,会不会有点闷?”
她本以为雪维利尔会推拒一下懒得走动,但出乎她的意料,雪维利尔答应得相当爽快。她们收拾好东西走下酒吧高台,细沙遥遥返出的白亮不像在高处望见的那样明快,反而有点刺眼。
雪维利尔下意识望向海的方向,那里有过于热情的阳光。她不适应地皱起眉,将披肩展开披在肩头,遮去大部分光线,才垂着眼慢慢地往前走。
这时穆萨才发现,雪维利尔的步子很稳,大约真的只是小醉;而自己这个“下来走走”的提议,才有点荒诞。沙滩不比高台凉爽轻快,何况自己刚刚才从这里上去。
……不,不对。她希望雪维利尔能下来走走,这是真的,一点也不荒诞。看到她独自在远离众人的地方小憩的时候她就是这样想的。
于是她试探地问道:“你想去海边看看吗?”
雪维利尔一时没有回答。她看见停泊的大船,那上面仍有走下来的观览客与船员;浪花在船下,涌上来又退回去,永不止息地留下易逝的白色泡沫和沙子间深色的湿漉痕迹。
她现在有点大脑放空。好像想去做点什么,又不知道能做什么,模模糊糊的。
她费力地想了想,终于对穆萨道:“都听你的。”
真是难得。穆萨越想越觉得此时的雪维利尔可爱至极,像是懵懵懂懂的小孩子。她几乎是安慰地柔声道:“好,那就去海边。”
远望大海其实是她们都很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大海很蓝,很深,很静,很遥远又近在眼前,望着它的时候有无限的遐想。
雪维利尔坐在沙滩上,盯着柔软的细沙,忽然问道:“你有的时候,会来这里看海,对不对?”
“嗯……嗯?”
“有很多次……我在这里见过你。”雪维利尔像是在喃喃自语,“但我没有告诉你,也没有去找你。”
她不等穆萨追问,就继续道:“因为我想,你那时候可能想一个人,独处,想一点只有自己知道的事情。”
穆萨无言以对。她的确时常会来,也的确有许多不愿被撞破的心事。可她没有想到,已经有一个人在她背后悄无声息地注视了这么久。
有很多次……她在注视着自己的时候,都在想什么呢?
穆萨忽然有点茫然,甚至悚然。她低下头,没有说话。
雪维利尔几乎没有注意到她的反应,仍自顾自地问道:“穆萨,你看海,是什么感觉?”
穆萨知道她在问什么。心里想着什么,就会感觉到什么——可她自己也说不清楚。里政府的战争、火山场的异动、受此牵连的那么多常人,还有雪维利尔……她已经数不清楚有多少次,雪维利尔突兀地出现在她的思绪里。她总给穆萨一种微妙的错觉,好像有哪里错了。
何况更多时候,她只是在情绪里对着水纹发呆。如果连面对大海都不能让心静一些,那生活里还剩下什么呢?
于是穆萨绕开了雪维利尔有意无意想问的,轻声答道:“没有什么感觉,我看不太清。大海有点像一个蓝色的色块……但还是很好看。”
雪维利尔不知道这句“看不太清”指的是她视力不好,还是其他那些事。她只知道穆萨很快就能看清了,从后者的意义而言。
她犹豫了一会,道:“我也很喜欢看海。如果还有机会,我们可以一起来看。”
穆萨眨了眨眼睛。“我们现在就在一起看海啊。”
雪维利尔没有说话。
浪声就充斥了她们身周,让气氛不至于凝固,也不至于被其他声音打扰。两种不同的心事在富有韵律的海浪之下潜涌。
一声——又一声。笃定的循环,永远也不会停下,从这个世界对她们二人产生意义之始至现在,预示着泡沫的破裂。
雪维利尔忽然开了口。“穆萨。”
“嗯?”
“我想说一件事。”
“……嗯。”
“我很对不起你。”
“嗯……为什么?”
“因为……”
雪维利尔停顿了很久,似乎纠结于应该如何解释,又像是因为不敢面对而止步不前。但她终于道:“……我并不是一个坦诚的人。有些事我没有告诉你,或者说……我知道你是什么人,但你并不知道我。”
她深吸了一口气。“我们是相对的。”
一只海鸥划过天空,弧线不留痕迹地画出孤单的弧线,又倏地消失在视野尽头。穆萨忽然意识到这些话都是极其严肃的、认真的、也许不能明言却也再明白不过的。
一根隐形的线悄然串起了她刻意忽视过的一切,曾经的怀疑被照得无所遁形。她的心猛地颤抖起来,却把刚刚浮起的念头重新压下去。
相对的……对立的……敌对的。她和什么人才是敌对的?这不可能!一定是……
是的,一定是她喝醉了,所以说了些胡话。穆萨强硬地告诉自己。也许她不明白这些意味着什么呢?
可是……她从来是一个那么清醒的人啊。她怎么会不明白?她为什么要告诉自己?
穆萨的思绪由混乱变得空白。如果眼前的一切难以理解或接受,她宁可自欺欺人装作什么都不知道,似乎不去想就不会发生。
就当是做了一场噩梦那样,她只是不慎多想了。
沉默变得无比恐怖。人群欢乐的笑闹声因遥远和模糊而显得不真切,而沉默在这一瞬间永恒。耀眼的阳光在遥远的地方连成夺目的一片,却在她们身后留下阴影。
也许这样就过了很久很久。
穆萨的嘴唇动了动,终究什么也没说出来。她几乎是逃避式地踉跄着站起身,不敢看雪维利尔的眼睛。“……对不起,我想起有点急事,要先回家了。你……祝你玩得开心。”
雪维利尔只能点头,站起身,一言不发看着她匆匆远去,背影被过强的阳光照的模糊不清。
她恍惚间回到了无数个她们之间告别的时刻,也是这样,只不过她们会微笑着向彼此道别,说下次再见。
她忽然惊觉,好像自己总是在目送她离开。那头银灰色发已经刻在她脑海里,她描绘得出阴天、晴天、微风拂过、雨滴落下时发丝轻轻晃动的样子,知道它远去时有多么美多么温柔明亮。
然而这一次是她亲手送她、推她、强迫她离开的。
这个念头掠过的瞬间雪维利尔几乎不能呼吸。她不敢再看她远去的瘦小的背影,重新回身望向大海。欢庆的旗帜竟然如此扎眼,在耳中放大的他人的玩闹声让她忍不住全身战栗。
她没有醉,从今天第一眼看到穆萨开始她就完全醒了,醒得极其苦涩。
这是她近几日反反复复辗转难安的心事——快要开战了。她装作一个正常人,已经藏了很多年,过了很久属于自己的日子,如今终究不能再藏下去。很快她就会投入这场战争,从世俗的世界消失……
……再以敌人的身份与穆萨相见。
难以想象那会是什么样子。她应该会痛恨自己吧?
所以雪维利尔说了那些话。以这两杯酒作为坦诚的借口,暗示穆萨自己并不是她一贯认识的那个人,总好过在不久的将来,粗暴地告诉她什么叫做势不两立。
可她除了隐喻这段可笑的谎言,给彼此一个分道扬镳的铺垫,其余什么也做不了。接下来的一切……失望也好、决裂也罢,那都是不容她更多加思考的事情。
因为她很清楚地知道,她骗谁都可以,唯独不能骗穆萨;她对谁坦诚都可以,唯独也不能对穆萨。这从根本上是无解的。
雪维利尔疲惫地闭上眼睛。黑暗在她眼前透出灼烧酸涩的红光,刺得她想要流泪。
随它去吧。
End.
【一个很重要的注解】
关于为什么雪维利尔会向穆萨透露两人敌对,我是这么想的:
首先,她们两个是可以超越友情的朋友。雪维利尔不愿意骗穆萨,但是需要通过欺骗来服务组织的时候,她毫不手软。
然而现在雪维利尔要上战场,魔法师身份要被里政府查知,穆萨不可能不知道。
雪维利尔不愿意彻彻底底把穆萨骗了,让这份友谊因此变质,所以她主动坦诚了自己的身份,给彼此一个缓冲的余地。
但是她又不敢直接告诉穆萨,自己是个魔法师,她怕会她们两个都会崩溃……所以她只能简短地暗示。
可能这也是雪维利尔在这件事上能做到的唯一的坦诚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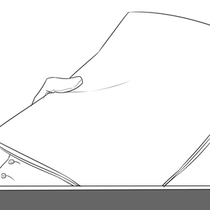


这里其实还包含了第三章的部分内容,因为第三章摸鱼了hhh所以就放到终章一起讲完w
————————————————————————
01
神社这边热闹的就像前几日的祭典。警察们和来寻找失踪人员的相关人士把这里堵的水泄不通。沸沸扬扬传开来的少女失踪案今天忽然就在这神社边被找到了熟睡的少女们,她们迷迷糊糊的被警察和家属围着,似乎对自己的失踪并无所知。
橘树小心翼翼的躲开人群,四下打量着神社周边。他在这里并不是因为跟这些少女有什么关系,而是在试图寻找某个熟悉的身影。
如果不是鬼濑家的女仆怒气冲冲的把无瓜的伞甩在他面前,他也不会去造访好兄弟的破茅屋,也自然不可能发现无瓜已经好几日不在家中。橘树仔细排查了一下近期帮内派出的人员,并没有无瓜外派的记录。心下生疑的他自然把这事情跟失踪挂上了钩。
所以顺着线索,他准备来这边碰碰运气。
不过看起来他运气不错。头顶的乌云慢慢聚集了起来,或许也是拜它所赐神社才会被人们察觉到异样。橘树一路摸索着很快就找到那个熟睡的大汉。
“……哥……老哥……醒……醒醒……”
无瓜睡的迷迷糊糊的,觉得有什么东西在拍他的脸,橘树断断续续的呼唤声传进他的耳朵里。
“……嗯?”无瓜发出一声模糊的鼻音,揉了揉眼睛醒了过来。天空中的乌云也好似宣告这个雨女(男)的清醒而快乐的降下了淅淅小雨。
无瓜撑起身,简单打量了一下四周,这是一片他并不熟悉的森林。
“我们这是在……哪儿?”宿醉让他觉得有些头疼,干渴灼烧着他的喉咙,“我在祭典上好像喝的有点多……”
“你何止喝的有点多。”橘树递给他一葫芦水,“你知道你睡了几天吗?”
“几天?”无瓜咕咚咕咚把水壶喝了个光,因为着急甚至还呛了一口。他咳嗽着,这才发现自己的胃也空荡荡的。
“久到人家大小姐都不愿意等下去了。”橘树丢了个物件过来,“你祭典当晚跟人家说去解手然后就一去不复返了。老哥啊,没想到你还是个负心汉?”
无瓜接住了这个东西,发现是自己的伞。他努力转动迟钝的大脑,试图拼凑起醉酒之后的记忆,但是他什么都想不起来。无瓜虽然很容易醉,但是每次喝酒都很注意,即便醉酒也不会超出太多。
“这可真是太失态了。我居然会喝到不省人事……”无瓜把伞丢在一边,痛苦的抱着自己的头。这时,一样东西从无瓜的衣袋里滑了出来,掉在了他的腿上。
橘树也注意到这个小东西,拿起来仔细端详了一番。
“恩?老哥。你原来还去神社里求过桃花吗?”
那是一个御守,看起来有些眼熟。无瓜想起来祭典那天春摔倒的时候脱手而出的那个御守,似乎跟这个很像。
“与你无关。”他抢过御守。“这不是我的东西。”
“是那位大小姐的吗?”橘树玩味的笑道,“你们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无瓜回忆起喝酒之前的事情,他想起了十文字说到的许愿酒池,想起了他为春斟酒时的行为,这让无瓜觉得耳朵发烫。他抚摸着御守,布满老茧的手抚摸过御守表面的纹路,他发现上面还有春因为抓空险些摔倒而脱手掉落在地所沾上的灰尘。无瓜小心的弹了弹灰,这时他又想起了他之前不小心听到的春和太田小姐的谈话。
“我不过是她夏日突然降下的一阵暴雨罢了。这个时候离开,或许也是好事。”无瓜自嘲似的嘟囔着,“人类和妖怪……不会有好结果的……”
橘树看着无瓜像玩变脸一样一会儿笑一会儿郁闷的,大概也猜了个七七八八。不过作为寿命比较长的一方来讲,妖怪爱上人类早晚只会徒增悲伤。
“老哥,要我帮忙的话尽管说。”他拍了拍无瓜的后背,“我会算你便宜一点的~”
02
春若有所思的摆弄着衣服上的蝴蝶结。
祭典的回忆一直在她的脑中挥之不去:烟花炸响的声音完全盖住了保镖先生的后半句话。她无法看到他的脸,也无法触及他的嘴唇,甚至连全良和千岁两个幽灵也对此闭口不提。
春到最后也没能知道保镖先生叫什么。他们只是伴随着震耳欲聋的烟花声默默的品着酒,直到对方醉醺醺的报告自己需要去方便。
在那之后,保镖先生便一去不返。
春摸了摸自己的手,仿佛上面还残留着保镖先生掌心微凉的温度。
‘春是不是还在想那个负心汉?’全良压低声音问千岁。
‘小孩子不可以随便乱讲。全良,姐姐不是告诫过你不要再提这件事了吗?’
‘可是你看春她现在这个样子,惠小姐她们也都很担心啦。’
“保镖先生才不是那样的人!”
春咬紧下唇,手指攥紧了衣服下摆的布料。关于这个消失的一干二净的男人,她已经听够了关于他的负面言论。全良也好,惠也好,亦或是女仆们,对于春在祭典当天深夜被警察们送回来这一事上都表现出了极度的不满。最终导致的就是可怜的中介人成为了他们怒气的宣泄点。
‘但是都过去这么久了,他就像从人间蒸发了一样,说不定早就暴尸野外了!’全良的声音由远及近,话里的每一个字都重重的砸在春的心头。‘说到底,没有了伞和契约,你们什么都不是。’
‘全良,不要再欺负春了好吗?你都要把她说哭了。来,跟姐姐去别的地方玩。让春先静一静,好吗?’
“……”
春把脸埋进手掌,小声啜泣着。原本一直努力维持的城墙被全良刚才的一番话全数击碎,泪水止不住的从指间倾泻而出,落在和服的布面上,摔成了几瓣。她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甚至都没有听到惠敲门的声音。
“小姐?”惠敲了两次门。失去视力的人的听觉总会十分灵敏,平日她甚至都不需要特别询问,春都会在她敲响第二次门板之前回应她。这有些不太对劲,惠这么想着试探的喊了一声。
对于她的呼唤春依旧没有回应,惠紧张的把耳朵贴向门板,她隐约听见屋内传来一些轻微的声响,似乎是有人在努力压抑着的哭泣声。于是她小心翼翼的拧开门把,打开了门。
屋内没有开灯,窗帘也拉的严严实实的,只有打开门从走廊泄进来的一片光亮,让人能够勉强看清里面的情况。
春蜷在火炉边的高背靠椅里,泪水早已打湿了漂亮的高档和服布料。她似乎用尽全身力气将自己紧紧抱住,全无她平日的那份宁静。
惠小心的拉开女主人的手,抬起她已经哭花了的憔悴的面容。
“没关系的,小姐。难过的时候就应该要大声哭出来。”惠温柔的为春拭去脸上的泪水,轻轻抚摸着柔弱少女的后背,轻声安慰着。“小姐有什么烦恼,都可以说给我听哦。”
春心里最后的一道防线也已经崩溃,她紧紧抓着惠递过来的毛巾终于忍不住放声大哭了起来。
“我,我是不是,是不是太过心,心急了?”她抽噎着,抬头询问到。“保,保镖,先,先生,他。他,明明,告,告诉了,我,他的,名字……呜呜……我,我还以,以为……”
惠张开双臂将号哭的少女抱住,轻轻拍着她的后背帮她平稳呼吸。惠没有接话,只是静静的等待春把话说完。
“他,他只是,说,离,离开一,一下,下的。呜呜呜。”春把头埋在惠的臂弯里,“你,你说,你说他,是不是,遭,遭遇了什么,不测……不,不然,为什,什么,伞都,都没来,拿……”
惠轻轻抚摸春的头发,在她耳边轻声安慰道:“也许保镖先生被什么麻烦的事情缠住了也说不定。”
“可是……我的心……很难受……”春哽咽着,从惠的怀里抬起头,“惠,告诉我……保镖先生他……我们……还有可能吗?”
“人生漫漫长路,你们不过是并肩前行了一段旅程。倘若保镖先生和小姐您的缘分未尽,或许终有一日还能再见。小姐能够想这么多,说明这次经历让小姐您成长了许多,也不算什么坏事。”
春乖巧的点了点头,在惠的帮助下站起身。她现在觉得原本压在心头的某种东西消失了,或许这正如惠所说的那样,她的确是成长了吧。
“啊对了。过些日子镇上将要举行消夏的舞会。”惠终于想起最初的目的,“我想提议小姐参与一下,正好也能散散心。”她拉起春的手,“或许能让您发展一段新的邂逅。”
春破涕为笑,“该不会是因为你们当天都想去参加舞会又担心没人照顾我才找这样的说辞吧?”
“真是的!果然瞒不过小姐您呢!”惠调皮的用指尖轻点春的鼻尖,“不过大家也是担心您才会提出这样的方案呢。”
春笑着点了点头,“偶尔参与一下也不错。那就提前给她们节一下上个月的工钱让她们买漂亮衣服吧。”
女仆们欢笑着,穿着提前一天准备好的漂亮裙子一个接一个的步入宴会大厅。随后惠也牵着被大家打扮的漂漂亮亮的春走了进来。
从阴影中走出来之后的春,再也没有发布过什么护卫的任务。只是重新回到了那段平淡又不太平凡的日常之中。和保镖先生的那些有的没的的说法也都随着时间慢慢淡去。除了‘丢失’的御守以外,春依旧和往常一样平和而安静。
会场被布置的十分华丽,人群中不乏端着高脚杯托盘像游鱼一般穿梭着的忙碌的侍者。然而说实话,舞会对一个失去视觉的人来说只不过是一场人声嘈杂的音乐会罢了。但是春不是很想坏了平日悉心照顾自己的姑娘们的心情,所以她只是叫人搬了一张椅子,在靠阳台的位置坐了下来。
全良和千岁也被这热闹的气氛吸引了过来,一边对舞池中的舞者们品头论足,一边讨论过往试图邀请春共舞的男士们有何目的。
不过所有的邀约春都拒绝了。气急败坏的男士们的讨论声偶尔也会传进她的耳朵,但是这又与她有什么关系呢。
一首曲子终了,乐队又奏起另一首舞曲。春听的有些厌了,她摸索着走上了阳台,这里的空气比房间里面轻快的多,微微潮湿的味道让她觉得十分舒服。
全良和千岁忽然不吱一声的跑开了,春就靠着阳台的栅栏发呆。混着湿气的小风吹过她的脸颊,风中隐约混着一声沉闷的雷鸣。
雨降的很突然。就像那一夜。
轰鸣的雷声带着豆大的雨点滚了过来,落在了春头顶花架上。雨水从紫藤花的间隙滑到春的肩头,偷偷的没入布料的纹路里。
悉悉索索的声音响起,一阵凌乱的脚步声从春的身边擦过,似乎是在外乘凉的客人为了躲避这突如其来的降雨而跑回馆内。这让春回忆起了某个夜晚,那个让一切开始的夜晚。
正当她陷入回忆的时候,一阵不紧不慢的脚步声将她唤回了现实。接着,她发现落在身上的水不知被谁挡住了。
春的心久违的悸动起来。
“你怎么总是忘记带伞。”那个熟悉的声音从面前的上方传来,“夜晚的风很凉,不避雨的话会感冒的。”
“这是夏天的最后一场雨了。”春笑着说:“让我再多听一会儿雨声吧。”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