樱花尽谢,初夏的熏风轻柔地卷动着纷落的花瓣,扬起一阵阵粉淡的花雨。
浓浓的月色倾洒在外廊下。
从屋檐下仰望夜空,几缕纱雾一般的淡淡云彩飘过,一轮青幽的圆月明朗晶莹,一览无余。
时值刚刚入夏,难得轻盈澄澈的大气充盈着初夏特有的丝丝暖意,流溢在这一片被月光静静笼罩的庭院里。
“切,无聊。”
打破这一宁静的人此时正闲散地侧卧在廊下小酌,右肘支起托脸,左手倾杯慢饮,闲淡而漫不经心。
长长的几缕金发蜿蜒而下,月光照在其上仿佛一道光影流动的金色泉水,流光溢彩。
金发下的黑袍看似漆黑如墨,却又不时地隐约显露出一些如幻似梦的精美花纹,一看就不似凡间之物。
或者说,现在廊下这个正在百无聊赖之人其本身,就透着一丝非人的气息。
他手边不远的地方,摆着佐酒的烤口蘑。
庭院里枝繁叶茂,嫩翠欲滴。枝叶随风摇曳,婀娜多姿。
然而这人的注意力却全然不在眼前的美景之上。
时不时地,他那双颜色清浅的眸子就会越过敞开的纸门飘向身后室内,然后又带着几分显而易见的不耐和嫌弃转了回去。
那人视线所指,只见悠悠然有二人面对面端坐,其间静静地摆放着一局残棋。
月光如水洗练,通过敞开的木门倾斜下来,即便没有点灯,室内一切均清晰可见,几颗暴露在月光下的棋子也显得圆润如玉,熠熠生辉。
而廊下那人的影子也不知有意无意,正好也落在这棋盘正中,带着一番孩子气一般把棋盘挡去了大半。
一如那人此时不忿不耐的背影。
近卫不禁觉得有些好笑,低头看着那斑驳的影子,嘴角隐隐一勾。
好在自己和对面之人都不是在以凡人之眼视物,否则被这个桀骜的家伙一搅,这残局可真真下不下去了。
“本因坊阁下,请继续吧。”
对面之人已经许久没有落棋,近卫也没有催促,淡淡的一句提点之后,又是一番长久的沉静。
期间几乎能够听见廊下之人不耐的磨牙声。
有点耐性啊……
近卫无奈地摇了摇头,只好决定改变策略。
“本因坊阁下,您在犹豫什么呢。”
对面之人终于晃动了一下一直不动如山的身影,细看之下,端正放在膝头的,掩盖在长袖下的右手似乎也在簌簌抖动。
“下一步该您落子了,”近卫乘机追击,继续诘问。
“…………”
“您说什么?”
“呜呜……呜呜……”
乍听之下只是呜咽,但是仔细听来,却有带着一些几不可闻的人语。
从那人背后,风声飒飒而起。
而此时的庭院内却是一时的风息月静。
廊下那颗金色的头颅此时也转了过来,浅色的眸子眯了眯,直直看向近卫对面那个深色的身形。
“您大声一点?我听不到。”
“棋子……棋子……”人声终于喏喏地扬了起来,混沌不清,带着几分成年人的沙哑,能听出约莫是个已过而立的男子之声,“棋子呢……”
“棋子在这里啊?”近卫一手托起棋盘边黑子的棋笥,不动声色地向前一送。
对面之人背后的风声更大了,近卫散落在肩膀上的长发朝后飘起,纸门也被吹得有些摇动。
“簌”地一下,近卫只觉得眼前一缕金色一闪,那个廊下的身影便已经闪身到了自己身后。
也没见他有什么动作,却只在片刻之间,风声戛然而止。
一切又都恢复了宁静。
近卫笑了笑,不动声色地用眼神制止了身后那人蠢蠢欲动的后续。然后回身向着对面的人微笑道。
“您在找这一颗吧?”
与话音同时扬起的,是一直放在身侧岿然不动的右臂。只见近卫揽袖一摆,五指成勾便向对面那人的门面抓了过去。一个虚空抓举的动作行如流水一蹴而就,待到他将右手展开,掌心便静静地卧着一枚黑子。
“是这一颗吧?”
“呜啊…………呜呜啊…………”
对面的躯体仿佛发疯一般扭动起来。
接着——
噗地一下,那个身影陡然不见了。
刚才还端坐着对弈之人的地方此时只余一方灰色的铺垫,纸门外夏风又起,卷着花瓣扑入屋来。
尾声
“所以为什么要搞得这么麻烦啊……!”
不满的声音听得近卫差点笑出声来。
“如果让你来,这颗棋圣(注1)所爱之棋就会被你轻而易举地捏碎了吧?”
“那有什么关系,不过是个充满怨气的付丧神而已。”
近卫摇摇头。
“‘御城棋’(注2)被废止之后不久,棋圣本因坊秀策大人又与世长辞,这一颗时常被大人握在手中的心爱之物,想必是感念对方善意许久,耐不住寂寞化身成了付丧神吧,”近卫将棋盒棋盘收拾妥当,然后起身将廊下的酒具拿进屋里,重新注满。
“物感人情,也不失为一段佳话。”
“切……没趣……”不知道忽然想起了什么,名为“花叶”的妖异翻了个身,有些困惑地问道,“依稀记得你以前是不喜欢这些的,怎么忽然变了?”
闻言,近卫没有说话,只是将重新盛满温酒的酒器推了过去。
——等待你转生的时光漫长,这些只是我排解无聊的手段罢了——
END
注1:本因坊秀策(1829年6月6日-1862年9月3日),日本江户时代的围棋棋士,被许多人认为是围棋黄金时期(19 世纪中期)当中最伟大的棋士。
这里捏造了一个在他下棋之时,喜欢取一枚黑子在手里摩挲的梗。
然后这颗棋子在其死后化身成了外表和秀策一模一样的付丧神,却因为找不到秀策最爱的那颗棋子(就是他自己的真身)来模仿秀策的举动而盘踞在一副棋盘上纠结不去。故事的开头,棋盘的主人把这幅棋盘送来乌鸦的神社消灾。
注2:御城棋:1644年幕府建立了“御城棋”制度,出战者有“棋所四家”和其它的六段棋手。名门望族也可破格参加。参加“御城棋”被看作与武士们在将军面前比武同等高尚。不久,各家围绕“棋所”头衔展开了反复激烈的争夺战。这一时期是日本围棋史上的重要里程碑。1853年美国舰队兵临日本,要扣关登陆,整个日本朝野震动,形势告急。围棋界也因此而趋向衰落。于是1862年终止了“御城棋”制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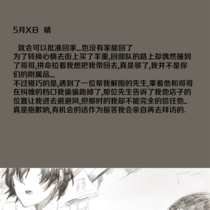









本篇涉及与有栖川老师凶案讲解互动(http://elfartworld.com/works/95926/),稍许剧情重复
后接浮世绘 下 →【http://elfartworld.com/works/96105/】
上下众生相共组一幅浮世绘
======
夏日浮世绘 上
文月入伏,不知是白昼渐长,又或是祭典众多,总觉得人也好妖也罢,全都兴奋起来,山上山下都格外热闹。来神社的人总是说着祭典的活动或是衣着该如何搭配,来神社的妖也开始聊起赏夜樱的乐事与天狐大人的美酒。
每到此时,筧常想,庆典与祭祀前,无论是人或是妖,都是一样的。
标新
在夕神乐结束之后,常世禊祓的同袍们陆续从大殿里离开,或三两结伴,或与殿外的朋友回合,或独自寻一个安静之处,万灯赏樱祭很快就要开始了。
赏樱处格外热闹,若事先两方没有达成约定,即使是目力高强的妖异在此时一眼望去也无法找到自己的同伴。往常的赏樱祭,筧常与景纪一道入场又常寻着僻静处,也未曾分散过。今次因着筧独自入了常世禊祓进了正殿,两人自然也就分开了,待祭祀结束后,筧才惊觉现下已是无法找到对方。
站在正殿门口又挣扎了片刻,筧被大大小小密密麻麻攒动的影子晃的眼晕,只好放弃了与景纪的汇合,正想寻了一处准备独自赏樱,刚巧遇见了同样是独自一人的九条。
九条皓是前一阵子才认识的鸦天狗,虽然同为常世禊祓的同袍,却是小小的一只,当是刚从山上下来没多久,正是对什么都好奇的时候。
两人第一次遇见还是梅月初,天已回暖,神社后山上的樱花过了盛放期,枝头还有花但来一阵风就落成花雨。那日天色太好,加之习习微风,熏的稻荷狐蹲到山中鸟居上躲懒,正有些迷糊连身形都现了出来,九条皓就这么落到了鸟居另一侧。
降落后的鸦天狗第一句便是,“没想到这山上还有樱花,我以为只有山里的樱花才会开到这个时候。”
筧听闻感叹,心想不知道是谁家的小妖下山来玩,懒懒看过去才发现对方身着的是常世禊祓的织羽。
不过就算如此,也是刚下山的小妖了。筧一边如此想着一边开口回了句“此处并非最佳,若是想看山上全景,汝可向上飞上九丈,或是去到山顶石那处。”
九条毫不犹豫的将两处都试了一遍,直至重新落回鸟居上仍赞叹着新位置的出色。
看着如此兴奋的小妖,筧突然也起了兴致,想要逗弄对方一番:
“同胞下山时日尚不足月吧?”
“啊,是的,刚有半个多月。”
“哦,觉得人间如何?”
“有很多以前没有见过的东西,还有吃的,无论是人类还是别的都很有趣!”
“因汝入世时日尚短,给汝一个建议,还请务必知悉——切勿小看人造半妖。勿要因着是异世之物是伪物而小觑,其能力远长于半妖,其中佼佼者可堪妖异。若是不想吃亏,还请牢记。”
在鸦天狗惊诧的目光中,筧戴着不知从何处取出的鬼面冲着对方眨着眼:“前辈的建议,要听从才好哦。”
以为只是一次偶遇, 未曾想九条却在几日后再度路过了神社,然后下一次,如此往复,两人便慢慢熟络了。
“八尾坂桑,这边这边!”
筧刚刚被九条皓发现就收到了热情洋溢的招呼,想着目前并无必须回合的对象便从善如流地接受了邀请。
“九条君未和同伴一同吗?”
“没有呢,那家伙有要一起赏樱的对象,善良的我决定成全这个见色忘义的友人。”
“哈哈,如此反而能专心赏樱,到也不负良辰美景。”
“现在这样能见到八尾坂桑也是很好的嘛,上次八尾坂桑提到的那家和果子店我有去呢,人间还有这么棒的店,没有错过真是太好了。”
“所说当是八条那家吧,手艺和配方均是代代相传,算起来也是间百年老店了,吾辈还曾同上一代一道探讨所谓新式的西洋菓子呢。”
“果然是老店才有传统的味道。不过西洋菓子同和果子似乎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样子和口感完全不一样。说起来我知道离八条不远有一家西洋菓子店,八尾坂桑要不要一起去看看呢?”
看到望向自己的九条满眼的期待,让原本并不支持西洋菓子的筧竟一时不忍拒绝。
又不由想到,人间总是在向前走着,比起老妖来果然小妖更易接受新事物,反倒是明明喜于观察人类的自身若是只坚守对传统的喜好,大约早晚也是要被抛下的。
同样作为老妖的稻荷狐这般反思后,似是对西洋菓子的抗拒都小了很多,索性就此接下邀请。
“唔…若是没有超出两条街的距离,依照年内的领地范围当是可以去到的。恩…就待下次天气好时如何?”
“好!太棒了。这么好的事请我能多喝三坛!”
“天狐大人的酒可非凡品,三坛,三瓶就怕是足够九条君醉到现了原形的。”
“哈,我可是海量,八尾坂桑这是什么表情,不信我吗?等下我们拼个看看是谁先醉…啊,樱花树间的灯亮了!”
被九条的豪言壮语逗到的筧正以折扇遮掩笑容时听闻惊呼,望向樱树的刹那满目夜樱骤然绽放,在灯笼的暖光中摇曳着。
立异
许是三巡之后,筧听到远处传来的哄闹声便知晓今年的定番已经开始,四下望去,果然有两处已见醉态。
见惯如此的筧笑了笑回过头正要调侃九条,却见对方两眼直楞,低头一看才发觉方才以聊下酒,已是两瓶下肚。
未想刚合饮两瓶就已至此,如此情况筧已不敢再让对方继续喝下去——无需一瓶,大约再来三盏就怕是要醉倒了。难得的赏樱祭,在第一批就阵亡总是可惜,为此筧只好将酒瓶移到自己面前,给直楞的九条皓手中塞了颗酸梅,寄希望能解酒稍许。
在安顿好小鸦天狗后,筧意重新看向景纪。之前寻不到的好友,竟在同九条寻找赏樱地点时遇见,不得不叹这就是缘。
“刚才遍寻汝不见,未想还能在赏樱祭上遇到。该说好久不见吗,景纪。”
“并未有很久吧,上月不还见过,在和果子店。”
“确实,然而看了当月刊的《异言》,吾辈突然体会到‘许久不见分外想念’这句了呢。”
“哦哦,筧你看了那个啊。”
“嗯哼,不打算讲讲吗,吾友?吾辈可是深信此事并非汝所为,才耐心等到现在才问。”
“恩,正如筧你所推测的,动手的凶手并非我本人,我不过是知情不报而已。现在就由我来还原现在已是谁都不知道的真相吧。”
随后景纪便如先前所说,原原本本毫无保留的将完整的经过讲述出来。不知是否是已经过了些时日,说的人除了微不可察的兴奋外相当平淡,反倒是筧这个听的感觉惊诧不已。
不知是该担忧好友的身体是否有影响,还是该说这岂止是知情不报,已堪比助纣为虐。然而事已至此,无论如何想,结果已经注定了。
有栖川景纪作为一只猫又有着非常态的缘起经历,这也造就了对方对于“初始本源”的探求,从自行思索到看遍人间再到入世做人。这本没什么,然逐渐升级的不仅是探索方法,还有对方愈发迥异的思想。曾说要做人看看,现在已不将生死看在眼里,更有甚者会为这般危险的死亡体验中获得的见解而激动。
筧抱着暮商,一边看着好友一脸开心的样子一边无可奈何地痛苦着。
约是看着自身的表情太过苦闷,胡来已久的猫又主动开口“安抚”:
“别那么惊讶,那个孩子是个好孩子,应该反而是被我吓走了。”
“不管有何种原因,间接直接都有两人死于她手,实在看不出哪里是好孩子了。”
此时景纪也终于露出了些许惊讶的表情——
“这还真是……我以前还没看出来,你居然想法这么像人啊,吾友。”
“人与妖均有其则,个把人命对妖异来说或许不算什么,但那孩子还维持着人类的身份便应当守着人类的法则。或许对好友而言她未曾加深伤害便是好孩子了,然对人类而言,早在她主动动手时便不在‘善’‘好’的范畴内了。”
“若是无人加害她也不至如此,正是有因才有果。”
“确有加害在前,但她明明不只一种方式化解依然毫不犹豫动手了,事后还这般写出来,此非人类的善所为。况且她先对汝泼了毒药,若非景纪为妖而非人,怕是吾辈再也不能同吾友继续在此共饮了。”
“既如此,对方希望我就此在她眼前消失,那我还是就此消失的好。”毫无不满的,景纪将杯中的残酒一饮而尽,“这样我们也就互不亏欠了。”
面对靠坐在樱树下的友人,筧突然感慨起来。
其自化形起对“本源”的索求理解,以及长久以来对人类的观察揣摩体验,让他从各个角度有所了解,甚有所同化。然无论是对人命的淡漠还是哪怕事涉几身安危亦有恩必偿的独特行为,有栖川景纪所遵皆为妖的规则。
一直在努力理解人类的感情与规则的猫又,哪怕已经融入人世到对化形已有不适,却没有彻底抛弃妖异的随性而为。几个百年过去也未曾改变,可谓学习抵不过固化的本性,若是无人点透,怕是又会有几个百年如这般过去。
筧正想着就此点明,刚酝酿出措辞只见景纪已靠着树沉沉睡去。
“与你这冥顽不灵的人相识,当真是孽缘。”
恋心
在天狐大人也会参加的万灯赏樱会上,众妖均是情绪高涨。于是在开怀畅饮之后,总有酒量低的大妖小妖现出原形,或唱或笑或聊,更有甚者会打闹起来。此景若出在平常时日,多少会惹出不快,然在赏樱祭上反倒被左右当做下酒料让气氛愈加热烈,最后往往演变成群体醉酒,只剩少数偏冷地带尚有存活。
往年都会发生的事情,今年也不曾例外。
现时赏樱祭已过半,面对着身边一个醉倒一个入眠,无奈进入中场修整的筧重新围观起周围的妖异们,以期可以找到其他友人。就在漫无目的的搜索中,筧发现了在远处的仓松,与同为山犬的妖异共坐在一块地榻上。
原以为是与其他友人同坐,筧正要转移视线却发觉仓松喝酒谈天的另一方不仅是生面孔,比起妖异更似半妖。
山犬的半妖身着浅色花柄和服,笑容里有着年轻人特有的纯真,周身洋溢着少女甜美的气息。如此看来,这位当是之前提及的同伴咯?
今年赏樱祭之前的安魂祈祀夕神乐,筧是同仓松一道在正殿参加的,结束时本和着流动的方向边走边聊,却发现仓松的步伐较流速要更快。
“仓松很是急迫呐,这是在外殿有约吗?”
稻荷狐本是随口调侃,没想山犬露出了同世间的家犬见到主人一样喜悦的神色,说本次约了难得的同伴一道来参加万灯赏樱祭。
虽说仓松本就是开朗活泼的性子,时常是欢快的样子,但此刻如此明显无需猜测的欢喜,反而有情况。
“唔,让同伴独自在外殿没问题吗……?”
“进正殿前已经特意托付给绫人帮忙照顾了,应当没什么问题。”
“如此周到,很是细致啊。”
“这是当然的,白白这么可爱万一被其他山犬看到一定会被带走的。”
嘴上说着紧张的话,脸上却是得意的神色,筧一时被仓松那灿烂的笑容晃着了眼竟不知该说些什么好,正巧到了殿门,索性就此分别了。
回想毕再看现下,仓松似是说了什么逗趣的话,惹得半妖少女笑了出来,而仓松也一边笑着一边劝着酒。虽然仓松这位当事人并未察觉,目光中柔情隐约可见,两人的相处已是融洽得无需外物。
说同伴大约只是托词,这分明是陷进去了嘛,仓松。
就在稻荷狐在内心调侃时,山犬二妖世界的旁侧却喧闹起来,似是有鵺喝醉了,正摇摇晃晃地唱着和歌,周围也一同合着拍子哄唱,甚至有同样醉意上头的狂骨踩着拍子扭起来,哄乱的气氛便如此逐渐向外扩散着,眼看就要波及到二妖世界。虽说这种程度的醉态尚且无伤大雅,不过如此继续下去有谁现了原形胡搅一通也只是早晚的问题,届时对于妖异来说不算什么的混乱对于半妖来说还是不妥。以及仓松不断的劝酒,估计那可爱的半妖离醉酒也就两三步之差了吧。
很是不妙呐,这个发展。
虽说并非切身相关,然而为了友人的路程不至于太过艰难,还是帮一把好了。
作为一个自诩善良的好妖,筧当即折了一张小犬的符咒送至仓松,片刻后便见到仓松收了符咒后立刻将“同伴”拦腰抱起,及时从混乱的边缘撤离。
万灯赏樱祭对于妖异来说醉过了今次总还有下次,而半妖若是卷入酒鬼中错失美景当真惋惜。现在看来那位应当不会辜负良辰美景了。应当吧……?
围观恋爱剧完美落幕的稻荷狐正心满意足,突然尾巴一沉,刚想是哪个酒鬼踩上去了,回头才发现是九条皓彻底醉倒回了原形,睡滚到了尾巴上。
哭笑不得的筧本想着将九条送交给同来的友人,奈何之前并未了解其同伴的讯息,现下也无法询问,似乎直接带回神社修整一晚更为适宜。
再回看身边睡的不知今夕何夕的友人,筧只好一大一小打包带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