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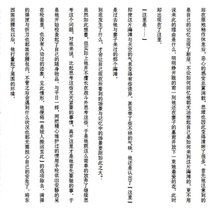






在耳边的低吟,充满了绝望,试图反抗的吼叫,忽远忽近…这时突然被一片漆黑包围,寂静,孤独,绝望…随后身体突然浸入如同血液一样的液体,身体也慢慢地下 沉,向上伸手祈求被拯救,却因此不小心吐出了最后一口气,窒息…血红色的液体渐渐变得滚烫,像火焰一样烧灼着皮肤,绝望地大口吸气,嘴里却像吞进了一只火 蛇,从气管一路燃烧到肺……
他睁开眼大口喘着气,眼前,是家里的破旧天花板。“你又在做噩梦了。”“嗯。”少年只是低声回应了下,侧身支起了身子。一滴滴豆大的汗珠从头发滑落,滑过少年的脸,滴到床上。
“还好吗?喝点水吧”眼前的男人提着水壶走过来,扔给了少年毛巾“这几天又没有休息好吧”“只是有点累,没什么的。”接过毛巾的少年潦草地擦了几下头发,起身就要往外走,却被男子的大手抓住了手腕,“一会,记得回来练习”
“好的父亲。”少年回头看着眼前这位面容憔悴的男人,却发现充满血丝的眼球和眼角匆忙擦去的泪痕,“您…又想起母亲了吗?”
他嘴角微微抖动了下,随后勉强地笑了起来: “哪有…你去忙你的吧!”
说来也奇怪,少年开始记事的年纪非常的晚,大概六七岁,他才开始记事。而对于童年的事,父亲也是不怎么提。
从少年记事起,他的母亲就已经不在了。他是父亲一手抚养大的。而关于母亲的事,父亲也闭口不谈,每当少年问起时,父亲甚至会莫名地发怒。
清 晨的村子,被盖下了一层薄薄的雾,微风带着微微有些潮湿的空气吹拂着不知名的树木,树叶被吹起来,落在少年走的石头路上。每三天,少年都要帮父亲去不远处 的药铺取药,几年来父亲的腿一直不见好转,连大城市里的医生也说,这病治不好,但是也没什么大碍,只是两三天会有一次酸疼感而已。
进 了药店,扑面而来草香味和干货的苦味混杂的奇妙味道。“呦,来啦”从柜台后面冒出了一个瘦小的老头,黑色的小圆帽就像他遮住眼睛的小墨镜一样的奇怪,“你 父亲的药,咳咳,给你准备好了”少年拿起小药包,对着老头鞠了一躬表示谢意,老头摆了摆手不知是笑还是咳嗽了一下,一边说着“年轻人还是不喜欢说话啊”一 边回到柜台中去。
走出药店,阳光已经变得有些刺眼,薄雾也已经褪去了。提着药包的少年轻巧地跳着台阶,快步地走着时,却注意到一边的 两个老人偷偷地对他指指点点。不知道为什么,老一辈的老人们并不是特别喜欢和他交流,换句话说,少年经常从老人们眼神中看出一种不属于这个村子的感觉,就 算他们多么奋力地掩饰。少年向那两位老人招了招手,老人们随即挤出笑容回应了一下。
“父亲,我回来了”少年推开门,把药包放在木桌上。当他走进厨房准备煮水时,却发现父亲坐在火炉前对着火焰发呆。“煮水喝药了!”少年催促后,父亲回过了神,有些晃悠地接过了药包。“您没事吧?”“没事没事,只是有点想你母亲了…”父亲揉了把脸,微笑着拍了拍少年。
午饭之后的时间,充斥着小孩子们追着打闹的笑声,和老人们唱的奇怪歌曲。少年也正伸着懒腰准备小睡一觉时,却被父亲叫了过去。“去山里砍点柴吧”父亲盯着火炉的火焰,眼神有些迷离“可是下午是全村的集会啊…全村人都在一起我一个人没回来也不合适啊”
大概是离火炉有些近,父亲的额头渗出几滴汗…“叫你去就去呀”父亲开始有些不耐烦地吼起来了。不喜欢被强迫的少年啧了一声,气愤地站了起来,提着斧头和篮子气愤地摔了门出去了。
————————————————————————
回过神来,天已经泛黄。少年擦了擦额头的汗水背起扎成捆的柴,伴随着木柴摩擦的声音摇摇晃晃地向山下走去。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少 年开始刻意地去注意风吹过树木的声音,那声音就如同树木在低吟一样,不时让人觉得他们就像森林的守护者,保护着属于森林的一切一样。少年也开始注意经过的 山路中那些花花草草,大概是因为从记事以来就一直在玩弄花花草草,还是因为经常光顾药店的原因,少年喜欢观察花草,也许,更是一种天生的喜爱吧,就像有人 喜欢动物,有人喜欢歌唱一样。有些沉醉在自然中的少年晃了晃脑袋,想了想还要去参加村里的集会,便伴随着树木的低吟,快步向山下走去了。
带着木柴回家后,跑去参加全村人都会来的集会,听年长者对村落的建设,本应如此…
本应如此。
为什么村子会灯火通明?为什么村子里这么热闹,吵吵嚷嚷?是已经开始庆祝了吗?
在 少年眼前的,不是欢天喜地的庆祝画面,更没有大人小孩的欢呼声…而是血红的火焰吞噬着的一座座房屋,是一声声被淹没在折断柱子后面的呼救声,是孩子一声比 一声虚弱的哭声。年轻人从柱子后面爬出,想要扑灭火焰,又被一根根砸下的木板盖住。炽热的浓烟盖住了天空,吞噬了还来不及投下月光的月亮。风声盖过了火焰 中绝望的惨叫声,又被不停的折断木头的声音盖过。空气中弥漫着木头燃烧的味道,令人作呕的味道,以及绝望的味道…
火焰,绝望,肺部燃烧的火蛇从嗓子窜出,从炽热变成温暖,最后火焰变为血红色的液体,在血液中慢慢上浮的他从黑暗中看到了一点点熟悉的景象。
少年的记忆如同被不停敲打的镜子,飞溅的碎片映着过去的一切,寒冷的雪天,与狼群度过的日子,以及,狼群被村里人杀光时的景象…那彻骨的孤独感…
他想起了寒冷的月光下,那一声虚弱而又悲哀的孤独的长鸣,想起了曾经咬着牙说出的那句话…
“我从没有这么,讨厌过人类”
“救我!!救我!!!”一声哀嚎把少年拉回到现实,被火焰吞噬的村庄,少年向着声音的方向看去,是一直在一起玩到大的玩伴。
“这里!这里!!”如同看到了救星一样,男人忍着疼痛挥着手,“我的腿卡住了!帮我一把!”男人的腿被一块木板压住,而火焰却一点点向男人靠近…“这里很不结实,稍微有点差错就会塌掉!帮我一把!”
少年站在原地,因为心中莫名的仇恨而犹豫着:这个村子的人,是当年屠杀自己亲人的人,却也是抚养自己成年的人。仇恨与感恩混杂在一起,选择的恐惧让少年流下了不知所措的眼泪。左脚抖动着想要迈出去,踩在地面前却停住…
“你在犹豫什么!快来拉我一把…”看到对方变得犹豫不决,男人从责怪慢慢转变成恐惧“你……快………快…………”男人颤抖着伸出手“咱们……是朋友的…………对吧……”
少年抬起头看着伸出手的男人,他的眼中充满着恐惧,失望,还有一丝丝孤独……
少年想起了那孤独的感觉,孤独的长嚎……
“不 想再经历一次这样的孤独…不想再失去任何人…”这样的想法从少年心中爆发了出来,他踩下了迈向男人的一步,“坚持住!”他飞奔向男人,然而不长的距离,房 子却随时有崩塌的危险,害怕来不及的少年,一边跑一边流下焦急的眼泪。而另一边,看到伙伴冲过来的男人,管不了抹去鼻涕和眼泪,伸出手想要抓住这最后的稻 草,“快!!快!!!谢谢!!谢谢!!!!”
就差一点,就能抓住他的手,就差一点——
男人头上的木梁突然一声巨响,他的表情还来不及从欣喜若狂转变,整个房屋就坍塌了下来,淹没在了火海中…
少年因为没站稳,狠狠地摔在了地上。眼角的泪水还没干透,新的泪水又打湿了眼眶…少年只是这样蜷缩在火堆旁,默默地流泪……
——————————————————————
【两天后】
“我 不知道自己是讨厌人类…还是喜欢人类了…”少年抱着膝盖缩在树根旁,“不管讨不讨厌,一切都过去了!你这样下去是不行的!”“那我该怎么做…”“去大城 市!和别人接触接触!诺!这个!绿林故都!我在那里的动物朋友们也不少,可以帮到你的!”“嗯……谢谢……”“打起精神!奥利安吉!
“不管你的伙伴们是什么种族,只要是朋友的话,就不要失去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