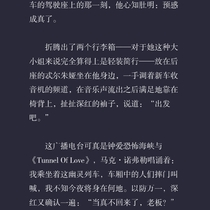作者:【十二招】庸某人
类别:同人。是日本手游《A3!》里的伏见臣(饰演「沃尔夫」)×七尾太一(饰演「零」)的剧中剧衍生,秋组第二回公演的活动剧情加上年初的官方售后的故事。
备注:煮了我cp的饭好快乐www
mode:笑语
“哈?你的意思是沃尔夫只要等着,什——么都不用做,就能变回原样吗?!”红发的女孩拉长了声音,她伸出手抓着自己的同行者迫使他转圈,将头顶毛茸茸的兽类耳朵和尾椎后面显眼一根的动物尾巴展示出来。
“明明他都变成这个样子了?”她在试图用实际行动展示自己的质疑。被她抓在手里的男人脸臭得像什么似的,似乎被女孩大呼小叫的动静吵到,头顶的耳朵不安分地抖了抖,尾巴也低垂着小幅度扫动。
是烦躁。
倒是那位一直没什么表情的可疑科研人员耸了耸肩,镇定自若像“有人被基因污染导致长出了动物耳朵和尾巴”这件事像只是一团空气。
“零,相信我的判断。”奈依摊开手,他真懒得看这两个人到底现在是个什么亲密的姿态,总之自顾自地说下去,“你们误入的那个实验室,我也用你们的取样验证了,结果也给你们看过,那些东西早就失活了,他是安全的。”
话虽如此,可耳朵和尾巴不应该是长在人类身上的东西。零纠结地看了看沃尔夫,话语间似有犹豫。
但是相处了这么久,零就算不张嘴沃尔夫也知道这小丫头要蹦出什么话来。于是他打断:“用不着。我们继续走。”
未尽的话语就此截住。
微小的担忧从零水蓝色的眼睛里一闪而过。
她点点头。
基因污染的影响不能说完全没有,他的情绪较之过去更加劣化,躯体污染却反而加强了他的综合生存能力。
零自从知道他的这套兽化特征触感迟钝之后,就会在休息时目光灼灼地凝视着他的头顶,更确切一点,是那双动物耳朵。
还能怎么办,低头给她摸呗,反正没啥感觉。
好在零也只关注耳朵。
她大部分时间注意不到沃尔夫的尾巴也会产生反应,并非被风吹拂,而与情绪有关。沃尔夫这人不过分善变——真要说起来,他的好心情并不多,一条尾巴最能外显的情绪无非也就是烦躁和不耐。因此零更是无从解读这人多出来的兽类特征用的是哪一套肢体语言。
但沃尔夫自己是清楚的,不知何时起他听到零的声音,都会不自觉地抖抖那双尖尖的耳朵,听力敏锐是一方面——想往后撇,又不知道为什么,于是若无其事地收回来。
他没见过狼,更不知道狗,在这个黄沙一片的世界里只有人类在苟延残喘,今天也是没有希望而寻找希望的操蛋日子。所以沃尔夫自然也想不到,那是手还没摸到脑袋就已经耳朵向后飞迎接对方爱的摸摸的信号。
整顿一下物资就可以从奈依的神秘据点离开,两人骑着摩托都已经走出百米开外,零突然一蹦:“啊!我忘东西了!”
“哈?事到如今?”
“我们人造体的一点、唔、小玩意啦!”她回过头去看了看早已沉没在地平线里的科研所,因思考而停顿数秒,“嗯……下次再说吧!”
“啰嗦什么,回去取不就好了?”他的眉头皱起来,手上方向一转便向来时路折返。零轻呼一声贴紧了沃尔夫的后背,嘟囔道:“明明我自己回去就可以的……”
啊?是又有了什么鬼主意啊。沃尔夫了然地嗤笑一声,略直起背,让零能更舒服地把她整张脸都埋在他的后背里。
新换的皮质大衣,沃尔夫现在基本只套着一边的袖子。零坐在他后座上的时候,沃尔夫就用穿了一半的大衣罩住她,女孩会自然地用剩下的一半布料把自己裹起来,依靠在他的背上,像给自己筑了个小窝。
沃尔夫特意停下脚步,反正就算不进去也听得见他们说什么——凭空长出的动物耳朵似乎连原型的特征都一并赐予了他。嗅觉要比过去敏锐,听力更是呈指数级增长。
零的声音还是很有活力,就沃尔夫来评价,其实有些吵得烦人了。
可听不到的话,会觉得有些不适应呢。
那天女孩无知无觉的跌落又再度从眼前一闪而过。
“可是……沃尔夫这样真的没问题吗?”
怎么又绕回这个话题了啊。
房间里的奈依和沃尔夫同步地叹了一口气。
“啊、我倒不是不相信奈依的话……”她听起来有些踌躇,半晌,还是迟缓地说,“嗯……沃尔夫他、会感到痛苦吗?”
在说什么废话啊这家伙……男人感到一种相当的无奈,躯体却像放松了一样卸掉紧绷的力气。
不。
不高兴吗?还是会为零无时无刻的担心而欢欣吧。
头顶的耳朵似乎又轻轻地撇到后面去。
“当然不——啊。”奈依像是想到了什么,语调一转,“那家伙大概会觉得痛苦也说不定呢?”
“诶、那么——”
女孩的急切询问马上就被打断,奈依说得相当意味深长:“大概需要忍耐吧。如果那种忍耐对他来说是难以承受的程度的话?”
这种话零是绝对听不懂的吧。沃尔夫没忍住搓了一把额头,太阳穴突突跳着,那家伙绝对是说给在场外的他听的啊。
他其实大概能理解那个看着就有坏心眼的半吊子人造人研究员说的是什么事情。
话虽如此,沃尔夫自认为他对他本人是什么情况再了解不过了。
我啊,对零没有那方面的想法。所以也不会做什么就是了。
那段时间零迷上了新的编发造型,搞得隔上几天沃尔夫就要和零火红的长发纠缠不清。扯到她的头发害她喊痛,沃尔夫是没什么愧疚心的——只是零实在是太吵了,这家伙本来就很能闹腾,生出附耳后更是吵得很明显了啊。
所以沃尔夫只能认命地坐地上捋顺零的头发,任由那些发丝环绕在他两手之间。
女孩偶尔会心情很好地哼起歌来。
要专注于和不听话的长头发搏斗,所以就算有点吵闹也没关系了。沃尔夫皱着眉头,什么阻止的话也没说。
嘛啊……倒也没人想过让零自己编头发、或者打理一下头发长度之类的事情。
被基因污染后零就变得更烦人了。
零的头发编成辫子,某种程度上也成了她的武器之一。不经意间的一个甩头抽到人身上,啪一声响,如果是裸露在外的皮肤,马上就能被抽起一条红肿的痕迹。
可零停下来不动的时候,她的头发就像她的人一样乖顺了。
遭到谜一般的基因污染而赶往奈依实验室的连日赶路里,因为总是找不到庇护所,他们无可避免地感到疲惫,终于在某个正午找到了一片可以将就落脚的废墟,也就原地坐下来休息了。
沃尔夫还记得当时的情状。
他确实感到了行动沉重,身体变化带来的不适也好,高强度的路程也好,恶劣的天气环境也好,明明哪个单拿出来都没可能拖累他。可身体的迟缓不容作伪。
“呐沃尔夫,去休息嘛?”女孩推搡着把他推到荫庇之下,“我去看看车子和物资喔。”
沃尔夫顺着零的力道躺倒,硬逞强在这种形势下毫无意义,何况这些事情交给零,沃尔夫是放心的。
啊,我对零原来持有的是这个等级的信赖吗……?
他出神地看着零轻巧的背影,她翻动物品的摩挲声、检查金属的叩击音、细小随性的哼唱声……才提升的听觉叫沃尔夫拥有了不自觉捕捉这些声音的能力,再睁开眼时,沃尔夫慢半拍地意识到,自己竟然看着零发呆看到睡着了。
然后他意识到零正压在他身上,准确的说,是她也正枕着他的腹部睡觉。
他能感到她的气息,更能听到她规律的轻缓呼吸。
沃尔夫撑起上身。
原本是想要叫醒她的。
女孩背对着他,平时会被她谨慎地缠在脖子上的他的旧围巾此刻被她展开盖在腰间,而他前两天才给她编好的辫子此时像条小尾巴一样随意地盘在地上,只留了一个毛茸茸的圆润末端。
沃尔夫看了一会儿,突然伸出手把那条辫子解了开来。
零被这个动作弄醒了,她含糊不已地嘟囔着“是要出发了吗”之类的话爬起身来,披散的火红色长发从她的肩头滑落,像一团云一样落在她刚刚依靠着的他的腹部。
沃尔夫突然感到一阵细微的痒意,没来由的骚动,他从来没有哪一刻像现在这样,想将她扯到自己身上,想捋顺她的头发,想拨开长发的遮挡,想咬她许久不曾裸露在外的肩颈的皮肤。
还没睡醒吧,我。
男人直挺挺地躺着不动,被扰了清梦的女孩坐在地上,没能睡醒的困惑叫她连小脸都皱起来,脑袋一拧,眼皮都不掀开地怒视着那个罪魁祸首。
啊——所以这种时候你就不要撒娇了啊——
沃尔夫冷静地死了一会儿。
她彻底离开了他的身体,女孩半梦不醒地抱着那条旧围巾,如瀑的红发垂在她自己的肩头,从颈窝和锁骨里顺滑地落下。
果然都是基因污染的错吧,不然的话,为什么我……
沃尔夫面无表情地低气压,看着零气鼓鼓地抛下他走向摩托车的身影。
红发随风鼓动着。
唇齿间似乎又产生了细微的空虚。沃尔夫的视线追随着。
我啊、有朝一日一定要在那里留下点什么。
要在她身上留下我的标记才可以啊。
零又将旧围巾环在脖子上,无知觉地将颈窝藏了起来。
—Fin.—






*听着打卡里提到的钢琴曲写完了
*又是一如既往只记得把醋给泼出来就完事了的东西。
*有非常多余的感性描写。
*字数:3252(含小标题及重复的句子)
你知道“唱片”或“磁带”吗?是的,一片中心镂空的圆盘、一个内部由齿轮状的卷盘缠起一卷卷黑色塑料带的长方体盒子。
置于唱针下,在转台上开始旋转。
置于播放器的空槽中,随着咔咔声将带子从一边转向另一边。
——这是A面。
翻转唱片,将另一面置于唱针下。
翻转磁带,将另一面嵌入播放器的空槽中。
——这是B面。
明明在刻录在同一个媒介上,两面却发出了不同的声音。对此,你又怎么想呢?
当然,我知道你已经得出自己的答案了。
现在,分别听听A面和B面的声音吧。
-A面-
黑色的键、白色的键。
纤细的指节、交错的指节。
和音、杂音。
一首毫无章法的乐曲,而后是没有敲下指节却兀自弹奏或修正的琴声,杂乱的音符从下压的琴弦里流出来,乱七八糟地散落在地上——这根本算不上是在演奏。
“啊啊啊啊钢琴活了啊!”穿着校服的男性发出了尖叫声。
“哎?”穿着校服的女性反应慢半拍地歪了歪头。
夜晚的学校,两个毕业已久的学生,和仿佛在呼吸、仿佛在吼叫、仿佛在躁动着的钢琴,空气中充斥着不协和音。假设从内部上锁的音乐室是一个密室,那么,可以明确的是,将穿着校服的男性称之为A,女性称之为B,音乐室内,此时此刻,没有除AB以外的第三个人类,不论死活。
然后——
“唧唧!”密室内发出了第三者的声音。
是一只红松鼠,在钢琴的腹腔中穿梭,将琴弦向下压,将螺丝、弦,甚至是木制的外壳都撕咬得松动而摇摇欲坠,使得有着漂亮黑色皮囊的钢琴内里溃烂不堪,发出失真的惨叫声。
“哈哈,哈哈哈。”男性干笑两声,“还以为真的有鬼呢。”
……
1、2、3、4,5。
无论怎么走,向上的台阶总有盈余。
“你知道彭罗斯阶梯吗?”她这么说了,“透过视觉的错位,展现出不可能的…‘无限’的光景。” ……就像是,现在的状况。
“那是什么?”提问的人已经将脚步迈向阶梯的拐角。绵延无尽的长蛇般的楼梯折出一个新的角,稳稳地承托住了他的鞋底……当然,这只是经过主观加工的说法,事实上,他只是在几乎一眼望不到头的阶梯上又踩过了一层。
“一个有名的几何学悖论。假设我们被困在四维……或者更高维的空间里,假设我们所在的世界受到某人的操控的话……罢了。到现在为止,阶梯数到多少节了?”
“我看到尽头了,但是……”男性犹豫着放慢了脚步。
661、662、663、664,665。
“666。”女性接过了他的话,先一步踏上了最后一节阶梯,楼梯的尽头是一座宽敞的礼堂,里面已经有人了。
“看来我们已经来到阶梯的奇点了。”她笑了笑。
-B面-
黑色的键、白色的键。
无形的指节、不存在的指节。
和音、颤音。
漂亮的韵律随压下的琴弦处发声,一下一下,以《小星星》开始,在琴键上由慢而快地跳跃着,仿佛能看到窗外有流星闪过。实际上,流星从天上撒下来已经是两周前的事了,或许这是两周前的星星的余热吗?杂乱地在琴键上左右跳动的星星仿佛迸发出了灼热的火星子,想伸出手去触碰的时候,星星的温度与音符一同落到了地上,发出了干脆的声音,没有再跃起来。
“这就是那个所谓的自己在弹的钢琴吗?”一个看起来还是能穿上校服的年纪的男性敲了敲陷入寂静中的立式钢琴,就像是在确认某个野生动物是否还有呼吸一样,钢琴没有回应,他就顺势把琴盖合上了,黑与白的齿列被关进了木制的嘴唇中,不作一言。
“它应该还在这里才对,但不清楚具体的对象是谁,就算是寻人寻物魔法也需要具体的媒介……”一旁的男性抓着形状奇特的叶子、蜥蜴的断尾一类的东西,沉思片刻后作出结论:“把钢琴拆了吧,用里面的琴弦或者螺丝钉之类的做媒介。”
“故意毁坏财务罪最低的刑罚是……”一旁的第三个男性正要开口,此刻,钢琴却先撬动了唇齿,音符发出轻快的跃动声。几人看向那架钢琴,琴盖仍是合上的状态。音乐室内的四人并不知道,但这一曲是麦克道威尔的《女巫之舞》,琴壳内未知的世界里正以极快的速度弹跳出一个接一个清脆的跳音,像是音符一个个跳进翻涌着绿色浪潮的坩埚中,飞溅出无数无害的水花。心头鹿似乎正不自觉地随着女巫的舞步而撞得头破血流,好不容易才随着乐曲渐渐缓和的节奏而得以找回自己的呼吸。四人不约而同地对视一眼,最终四人中唯一的女性开口问出了最关键的问题:
“现在要怎么办?”
“不知道,要不把钢琴砸了?”手上捏着奇怪的巫术道具的男性看待世界的方式总是很干脆。钢琴叫嚣着又弹起拉赫的《小丑》,像是正发出轻盈又让人头晕目眩的抗议声。即使琴板盖上了,也能从四处跳跃的音符中明确地感受到像有两只手正快速地在八十八个交错的黑与白的琴键上跑动着,平稳而精准、如节拍器般牵动人的心跳的乐声,就像是面前并非是一个需要他人操纵的乐器,而是一个自行轮转的纸带八音盒,随着不知何人打好孔的长长的带子,吞进去,在既定的孔洞处发出空灵的乐声。
“一千美元以下的罚款、社区服务、缓刑,以及一周的象征性监禁。”似乎对本地法律了解颇深的男性一边说着一边掰出四根手指。
“别的不说,我觉得它弹得挺好的。”唯一称得上是学生的男性发表了中肯的评价。
“那怎么办?钢琴又不会说话,我们怎么知道它想要什么?”捏着蜥蜴尾巴的男性叹了口气。
“或许…它想要的是一场合奏?”女性用指腹摩擦着盖上的琴板,琴壳内发出温和的低鸣声,像是一只正打着呼噜的幼兽。
黑色木质生物轻柔的呼噜声,慢慢地、渐渐地,转为风暴般的嘶吼。当然,一台钢琴自然发不出野兽的怒吼声,只是错落而杂乱、时而低沉时而尖锐的乐声渐渐变得刺耳了。
“好主意!”像是学生的男性身先士卒地拿起贴着墙面放置的吉他,稍微试了下音,“我已经准备好了!”
“好。”女性清了清嗓子。
“我不会。”干脆的男性作出了干脆的回复。
“要不试一下那边的尤克里里?它只有四根弦,相对好上手一点。”已经轻车熟路地把吉他挂在腰间的高中生指了指一旁墙边如面试者一般等待被选择的乐器们。
“这个?”
“不对,那个是贝斯。四根弦的那个才是。”
“这个?”
“对,那夏露露呢……?沙锤吗,真是古板又缺乏新意的选项啊,罢了,也很有你的风格。那么——
“开始表演吧!”
……
也就是说,这就是一个临时组建的乐队被愤怒的钢琴赶出音乐室…的十分钟前发生的事。
“它干嘛这么生气?”始作俑者不解地一边在楼梯上奔跑着一边发问。
“大概是因为有人连c和弦都不会弹吧。”女性冷冷地回道。
“话又说回来,你们有没有听到后面的脚步声?还有……斧头、摩擦地面的声音。”四人中最小的男性一面说着一面频频回头,脚下的影子被阶梯拉得长长的,像是被折成了数叠。
“比起这个……”存在感略低的男性低头看着自己的鞋子,准确地说,是看着脚下的阶梯:“这条楼梯,我们已经……”
“走了666节阶梯了,对吧。”跑在最前的男性停下脚步,楼梯的尽头是一座宽敞的礼堂,里面已经有人了。
“……”一个陌生的女性不知正说着些什么,她转过头,朝四人打了个招呼:
“初次见面。”
“请说英文。”气喘吁吁的男性如此回答。
-杂音-
“所以,你们的名字是?
“……
“这是哪国的名字?
“好吧,亚洲人,欢迎你来到奥庇沙……开玩笑的,这里是美国,埃芬市,罗卡里兰高校。
“开场白…或者说结束语已经说完了,那么,你们想怎么样?想回去的话,我这里有认识的小叮当和任意门,又或者…你想组个临时乐队吗?因为我们这里有一两个音痴所以那边的钢琴很生气,是的,音痴是在说我自己。
“哼…你们能答应就太好了,希望你们能让它满意……你是说希望渺茫吗?我会期待的。”
-和音-
称不上和谐、称不上优雅、称不上漂亮,甚至略显狼狈的一曲随着最后一个音符、最后一根颤动的弦、最后一句即兴的歌词落下而画上休止符。三个人弹唱,而另外三个人坐在音乐室的椅子上只负责了鼓掌,据说,“这是最好的安排了”。
钢琴没有眼睛、钢琴没有嘴、钢琴没有毛发、钢琴没有四肢,“钢琴”并不是活着的生物。
穿着校服的男性手中的红松鼠在安静的音乐室内一跃而下,蹦跳着跑向那架有着漂亮骨架与外壳的钢琴,就像寄居蟹找到了全新的壳,它钻了进去。
被沉默所充斥的室内,不知是钢琴或是松鼠送来了一曲《月光》,月亮温柔而沉静,如隔着层纱幕般垂下眼睑,圆而白,投来明朗而慈悲的目光。
某个人轻轻哼唱、某个人弹起和弦、某个人打着拍子、某个人跺着脚,某个人轻叹出声:
“真是…像魔法一样。”
“这种话,现在才说吗?”
钢琴没有眼睛、钢琴没有嘴、钢琴没有毛发、钢琴没有四肢,“钢琴”变回了它应有的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