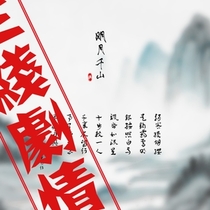吐槽露露的应怜剑寒
应该会有导演剪辑和评论轨(??)
女孩儿与陆仁并肩走着,沉默如斯。
“你是不是不高兴?”陆仁偏着头,目光落在那面具空茫的眼窝上。
“没有?”
“那是生气了?”
“你是不是白痴啊。”
陆仁还是皱着眉头。他的左手悬在刀柄上,之间轻轻叩击,那长刀随着脚步在腿侧滑动。他时不时的踏过一些冰屑,那些渣滓发出细碎的呻吟,在脚下纷纷破碎开去。斯林特尔像是在生闷气,又好像在出神,沿着街道走着,看不出目的地在何方。
佣兵发现自己落下了两步。女孩儿灰色的短发随着她的脚步飞扬着,间或露出一点儿白暂的后颈。小弩不知道被丢在那里,只余下老旧的鲁特琴拍打着女孩儿的腰背……陆仁赶紧移开目光。
斯林特尔忽然停下了脚步,她转身朝着陆仁露出了促狭的笑容。佣兵看不见她的眼神,但还是生出一种小心思被看穿的局促感,令他忍不住想要掀去那碍事的面具。
陆仁的心脏艰难的搏动着。他想起斯林特尔耳语似的请求时,灰绿色的眼镜里都是些沉甸甸的悲伤,而现在戴着这个冰面具的姑娘,除却出神似的疏离感,几乎可以称得上神采飞扬。
“又看些什么呢?”女诗人似乎在明知故问。
“你在生气?”陆仁又怀疑的问了一句,这蠢得像卡壳一样的问题令她环抱着臂膀,停下来思索了好几秒种。佣兵可以看到女孩儿搭在臂上的手指飞快的弹动。
“白痴。”她宣布道,“你打算一辈子问这种蠢问题的话,我还是继续当做不认识你好了。”
“好好好,你高兴就好。”陆仁摊了摊手,此刻他甚是疲倦,似乎有某种不重要的危险感让他感到倦怠不已疲于应对。眼见着牙尖嘴利的女孩儿又要开始新一轮的胡搅蛮缠,他歪了歪嘴角,“你知道吗,之前我大概是遇到幻象了。”
“什么幻象?”
“你拿着刀来杀我。”
“像这样?”斯林特尔抽出她的猎刀,刃尖一挑。陆仁叩击刀柄的手停下了。女孩儿发出轻笑,把那柄沉重的小刃往旁边丢弃,“我又不想杀你。”
佣兵所不了解的自己正在叫嚣。
“你现在有十七个问题想问我,真正重要并且有意义的只有一个。”斯林特尔站定,她从不离身的小刀斜插在身边的地面上,那的确是一把好刀,绝不仅仅是用以削水果或是切割鱼肉。他们不再走动,风却并未止息——只是愈发暴烈,带着从永不解冻的冰隙中灌来的寒意。
“你是谁?”
“答对了。”
陆仁紧紧的抿起了嘴唇。
“想不想知道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那女孩儿竖起手指抵在唇边,像是在说一个秘密,“你一直在怀疑我,‘她是邪神的帮手吗?她隐藏了那么久吗?她说的话都是谎言吗?’,对于你来说斯林特尔一直在世界的边缘,时不时的就滑向界外的迷雾中去了……我本可以平平淡淡的就这么过下去,或许会回德莫拉找那个诺言,或许会随着你回到遗都。”
“从人的猜疑中总会生出鬼来的。”
陆仁换手,长刀出鞘!燃烧着的长刀斩断了风,直取女诗人的面具。斯林特尔不闪不避,佣兵刀光一滞,没了势头。那面具应声碎裂,挥发殆尽。
“猜错了。不是它。”诗人惋惜的叹了一口气,她抬眼看着陆仁,“你的刀就这么软弱吗?”
“我从不做对不起兄弟的事情。”
“那你可以做一些对不起你喜欢的那个姑娘的事情。”斯林特尔还是那副模样,灰发灰眼,表情倔强。但是陆仁可以看到她眼里满溢着蓝紫色微光,让他想起冰封森林里的盐沼。
可那是什么?陆仁不记得自己看到过这种东西。佣兵再一次举刀,刀尖却微微颤抖,游移不定。
“你在害怕什么?”诗人的手指顺着陆仁斩断面具的轨迹滑过自己的脸颊,一道血痕突现,烂漫的人类血液从那道伤口上溢出来,斑斑驳驳的染红了她的衣服,“这样?还是这样?”
陆仁看不下去了。他无法再直视女孩儿被利刃切割开的身躯,在寒冷的空气中温热的颤抖。
“停下。”他说,“不要再……”
佣兵想说无论你是个什么东西都不要再摆布她的身体了,但这话卡在他的喉咙里怎么也吐不出来。斯林特尔还站在他面前,没有被分尸,胸口也没有插着他的长刀。
---------
#怎么办露露的心理描写自己去看啦!
中接 elfartworld.com/works/95758/
---------
陆仁没有感觉到长刀上传来斩断人体的触觉。但是刀内永燃的火焰熄灭了,像是把炭火插到了雪堆中。本应该如同流光般的一斩却中途停顿,这长刀卡在斯林特尔的心口。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陆仁感觉到了刀上传来的心跳。艰难、虚弱,柔软得不可思议。
“答对了,但是你不及格。”
女孩儿露出一个笑容,像平素斯林特尔会有的那种促狭。就算那长刀插在心口,也没有血,也如同没有斩过,像是斩了一道烟。她抬手握住刀身,把那冰凉的金属更深的压进自己的胸膛。
斯林特尔一步一步的靠近陆仁。
佣兵感觉到刀上传来的心跳渐息。
“有些事情当为而不可为。”她说,“你可以不做英雄来杀了我,我满足你。你把风筝的线斩断了,想要风筝飞去哪里呢?”
陆仁张了张嘴,没有说出话来。
“你可以向我们许愿说想要斯林特尔活着,可是已经死去的人就像已经断裂的刀,是挽回不了的。她已经死去这一概念是你造成的,也是你必须背负的。你燃烧一千次,最后得到的还是撮灰烬。”
“从人的想法里也是会诞生事实的。”蓝鹭疲倦的叹了口气,有什么东西和那个碎裂的面具一样开始碎裂蒸发,直到消失殆尽。
女孩儿灰色的眼睛失去了光彩。她咳嗽了一声,低头看着自己心口插着的长刀。
“不是你的错。”她说。
陆仁的手很稳,没有颤抖。或许随意的颤抖会让她觉得痛呢?诗人离他很近,而他却不能张开双臂去拥抱她⋯⋯因为他握着的刀深深的陷在女孩儿胸膛里。
女孩儿的吻像雪一样,随着最后的吐息融化了。
尾声:永冬
“⋯⋯翅膀拍击的声音杂乱的充斥了四周,剧痛纠缠着诗人的眼睛,像是在火山中煮出的气味混合着黏糊的恶臭环绕着小湖。
“我不害怕你,因为你只是存在于人类思维中的恐惧。”
她什么都看不见,却能听能嗅。比雪更冰凉的东西触碰到了她的皮肤,在剧烈疼痛中的昏暗视野里,戴着雪白颅骨的怪物不断的迫近——它与之前有一点不同,看上去突兀的现出弓似的长角。
汝食吾之肉,饮吾之血。
它嗡嗡的说着,长角破开空气。
诗人摸索着,将沉重冰凉的猎刀入手。 ⋯⋯”《诗酒谣》
斯林特尔握着沉重的猎刀,她还没有抬起手,就被小臂上一阵尖锐的疼痛击倒。
她什么都看不见,但是在沉重又尖锐的疼痛下能感觉到有什么东西穿过骨骼的间隙和血肉,把她钉死在冰凉的冻土上。
她不知道自己发出了怎样的惨叫,因为夜鸦用不知道是骨骼还是棘刺的东西穿过了她的咽喉。
她想起了那个手指化为枯枝,眼窝里填满羽毛的姑娘。
可是这次还有人在等着。自己或许不再会被抛下,不再会被唾弃,不再会孤身一人⋯⋯
但一切却在这种时候结束了。
向时间之外的无限混沌许愿⋯⋯
还有人在等着我。
尾声:德莫拉
正值春初,湿润而温暖的风从海中奔袭而来,笼罩了整座城市。在更加靠近原野的地方,果树未能醒来,一枝金色的枯蔓零落的缠绕其上,颇似已死的蛇。
男人行走在成片的墓碑之间。这些林立的石木排列得极其紧凑,几乎可以肯定下面并未埋葬着尸骸。诺言大步行走,用指尖掠过那些墓碑的顶端,像是在检阅暴雨之后零落的花园。诺布百无聊赖的坐在一处残破的雕像上,羽翼半阖。
没过一会儿烟雨突至。
“你觉得这些人里面还没有死的人看到自己的墓碑会怎么想?”
“或早或晚,总会用的上。”诺言停在最靠里也是最老旧的那个墓碑前,在整个墓园破败但整洁的映衬下,它显得分外脏污。
“你这次为什么假扮成诗人?”
“因为诗歌只是谎言的堆砌。”
男人垂着眼注视着墓碑上的姓名。
“何为人类?”
“死与生的螺旋。籍由一方终结,又借另一方起始。而未知是我们终要打败的敌人。”
在泥泞之间所书的是诺言二字。
“何为悲哀?”
“曲终人散,物是人非。”
诺言的衣物渐湿,在他的背后,本应该是双翼的地方显出一道阴影。或许是那被称为审判的伤口再度裂开而鲜血淋漓,或许是有翼的蠕虫正攀附着他的魂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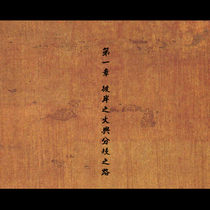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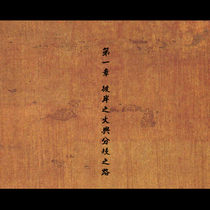





钱糖收拾一下思路,回了学校去。
自己迟了一个星期返回学校,校长默许的情况下又忽悠掉了一个期末考试,按照年级来说,自己依旧是一年级,教学内容无非都是理论之类的东西,钱糖听的头昏脑涨,按照她自己的话来说,不是实践,哪里知道该怎么去做这些事情——魔咒、炼金、魔改、生物、魔药、变形以及常识。这是学校里最基本的几项学科,之后加入的部分体能上的项目也是基于魔法之上才行,这让钱塘苦恼不已。
第一学期,应是自选两门科目就好,钱糖不偏科——理由是门门都差,再来一说科目,钱糖总是能想到一位老师,让自己苦恼不已的炼金老师,以前被老师送了好几颗炸弹,现在留心想想,可能也就只有这位老师最好凑近乎。
钱糖又背起自己的单肩包,摸着路到了Shadow家门口,每届一年生教的课也都一样,在课堂里拾起学业的可能性似乎不太大,钱糖打算在老师家碰碰运气。摁下门铃之后,钱糖耐心等待打算碰运气,毕竟她自己也不知道Shadow老师在不在家里。
“咔哒。”门打开,钱糖看见出来的是其他老师,心想自己不会是找错门了吧,顿时脸色都有些白,心虚的垂下头“对、对不起!!找错人了!!”话丢在原地自己就羞愧的跑走了。
Shadow的声音从屋子里传出来“谁啊?”门口的达梓也没反应过来,不过见人面熟,知道钱糖也是一个爱吃糖果的女孩,之前和Shadow有点争执,所以留着点印象“是那个叫钱糖的学生,不过现在人……”目光远眺,又转到屋子里看着捧着糖罐的Shadow“跑走了。”
钱糖躲在远处的墙边大喘气,接着就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龌龊的不行,以后不能再做这样的事情之类种种,沮丧往寝室走去,不过到了寝室门没进,身子微侧走过大门,走到寝室大楼边上去,寝室楼边上有一条绿化带,丛丛灌木之间有一个不容易察觉的小土包,钱糖没有走进灌木丛中,只是蹲在一边的过道上。
事情再折回去五年,钱糖跟着二年生去抓捕魔宠的那段时间里,家里来了一个老鼠小偷,后来也就是自己的魔宠,不过虽说是魔宠,但什么也不会做的钱糖自然签不了什么契约,老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其中一段时间里跟小家伙合伙去偷Shadow老师的糖果,再后来老鼠寿终正寝,它活得比其他魔宠都短了很多,钱糖不知道小家伙为什么会死,给对方安葬之后偶尔会过来看看。
钱糖蹲着到了天黑,站起身子,往寝室走去。四人寝室安静的不行,钱糖回到自己的书桌边上,几位室友离开的时候好心的给自己留了笔记本,可是自己看不懂,来回翻了一会,倒是和一些凭空生出元素的能力杠上。说来还是学习的问题,之前一些物质转换之类的都不好好掌握,凭空生成自然是难。
钱糖撑着下巴拿起室友的笔记,翻到第一页去看起来,一些老师在课上来回讲了无数遍的东西人也有细细记下来,五象互生互克,魔咒专心语调平稳,生物属地属性决定之类种种,钱糖看的一知半解,她和上书了之后,依旧打算从炼金入手。
原因也有,钱糖记性比较好,想起来小时候跟着师傅学武的时候,师傅也有粗谈过炼金。
“骗人的东西。”
不过钱糖想想,可能师傅讲的和这里的不一样,不过钱糖看着本子上圈起来一个“以物易物”,心中思索一会,去泛起箱子找画阵笔,带着笔记急冲冲的下楼去,又走回原来的灌木丛边上。
歪歪扭扭的画了一个小型阵法打算尝试,去刨了一点土,又去折了点小树枝,按照互辅的位置摆好,想要施法的时候发现自己没把魔杖带下来,又匆忙上楼,难得有了激情,对于钱糖来说自然是好事情。
凭着输出靠念的本领,在钱糖的碎碎念中,钱糖的双眼盯着土和树枝糅合在一起,最后又回归成泥土,一块略微僵硬的泥土掉落在阵眼中央,钱糖看着那块泥土,一时间没有缓过神来,为什么泥土和树枝混合在一起变成的还是泥土,这不符合以物易物的道理啊。
钱糖想把泥土拿起来带给Shadow看问原因,手指刚触碰到泥土之后,泥土就碎成一堆落在画阵的纸上,晚风一吹,大部分的泥土随着风一起回归到了原本来的地方。
钱糖什么挫折没受过,抖了抖白纸,放弃了把泥土带回去的念头,夜晚绿化带这一块没有装路灯,看起来阴森森的,钱糖被夜风吹的发慌,缩起脖子往寝室走去。
夜色把所有的泥土都拢的黑乎乎的,钱糖心想一定是自己没有天赋而已,想来没有天赋什么事情都可以谅解了,不过看到手里那张画的歪歪扭扭的魔法阵,钱糖又给自己找借口——如果是用毛笔来画,肯定不会画的这么丑了……
接下来的日子里钱糖没有像晚常一样颓废,虽说有天赋打底坐着借口,可是如果再不练习,怎么能毕业。
一些高危的炼金实验要在老师的监督下完成,其他的简单玩意自然就钱糖偷偷摸摸在寝室后面的绿化带那块完成了,之前的配置来说……钱糖翻了翻朋友的小笔记本,可能是物品的精细程度和品质太差失败的原因,这回自己又是再一次趁着白天有空坐起同一个试验。
说来奇怪,本子上也没有说泥土和树枝混在一起会变成什么,钱糖这么执拗于这种东西,屡屡失败是自然,她把处理好的泥土和树枝摆放在魔法阵上,拿起法杖,又一次的碎碎念起来。
泥土和树枝重复之前的模样糅合在一起,树枝被泥土揉碎消失,最后还是同样的泥土块落在阵眼上。
钱糖有了心理准备,碰下泥土就见重复的碎落一地,钱糖看着泥土,泥土不会看着钱糖,只是在没风的条件下静静躺着。
又失败了,钱糖站起身,把泥土倒在一边的绿化带里,见自己纸里头的泥土似乎跟以前变得不同,倒在原来的地方才看到清楚,泥土的颜色比起原来的土壤来要深上一度,钱糖不开窍的脑袋终于是明白了道理。



写在前面:全篇日常……
————————————————
霍钱匆匆赶到的已经是第二天晚上的事情,钱糖嚼着糖果泄愤,单肩包可见的扁了许多,不过见到人的时候还是扑了上去。
之前怎么埋怨都不及现在见面的激动,霍钱看见几乎未变化模样的钱糖,一时先诧异,接着很快接受了设定,抱起妹妹到怀里,紧紧拥住“之前都到哪里去了……”钱糖圈住霍钱的脖子,吸了一口气,在胸腔里兜了一圈再吐出来“去上学了,就忘记回来了”
话说的有些心虚,霍钱不应该知道那种地方,一来两人对外虽然是互称兄妹,但是并无血缘关系,再者就是钱糖误打误撞遇到引路人,二话没说答应之后就去了学校,事情做得匆忙,霍钱这里一时钻了空,既没有受到钱糖的入学通知,不清楚自己的妹妹到底去了哪里,又由于近年来的奔波,知道百慕大一块有一个秘密组织,具体不明,霍钱一个世俗之人,自然不会把秘密组织和妹妹联系在一块,那封信也就是霍钱寄出去的万分之一封,不过等到世界上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再去找人的时候,霍钱就停下写信,自己随着业务到处奔波去了。
“傻瓜,这都能忘记回来!”霍钱又气又笑,无论妹妹说什么自然也有她的道理,送人一个爆栗之后就不再深究,他看向一边的林保安,保安看见霍钱,又看看钱糖,感慨岁月是一把杀猪刀的同时,想起个事“你就不用说什么谢谢了,对了,房东有点话想找你谈谈,关于你房子的事情。”林保安摸了摸下巴扯嘴角,这块小区由于经济开发,房价自然高了起来,霍钱这样占着一层空房不用,房东自然苦恼。
霍钱也露出焦躁的表情,抱着妹妹跺了跺脚,钱糖注意到还有林叔叔在,便顺着霍钱的身子下来,拉住哥哥的手,霍钱顺着握紧钱糖的小手“他还住老地方?”“那是。”霍钱对林保安摆了摆手,重新握紧钱糖的手“跟林叔叔说再见,我们走了。”“嗯,林叔叔再见。”
“好、好……”林保安对两人微微点头,目送他们出了家门,关上门,心上还在嘀咕:糖糖这小妹怎么这么多年都没变化过似得?
“谁?直接打电话不就好了?”防盗门上传出失真的声音,霍钱不耐烦的回话:“不是你叫我过来的?谈房子的事情。”,人回来的时候是下午,可时差的让霍钱昏昏欲睡,他没有倒时差的习惯,这种时候脾气就会差的不行,那头声音停顿一会,两人听到挂电话的咔哒声,便看见门打开,人从门里出来“进来吧……嗯?”钱糖看见人停顿,她也陷入思考,然后还不等对方说话就想起来是谁“哦!你是那个…超爱哭的哥哥!”“我爱哭?!开什么玩笑!”房东被人这么一说就来了气,说来现在的房东应是老房东的儿子,霍钱知道消息的时候也就随口一句“子承父业”,现在钱糖这么一说,又是想起了一些细节。
“你就是爱哭!我没开玩笑!”钱糖小手一抬指着人说话,之前一时没认出人只是房东也长大了不少,“我吃个糖你就哭成那样,还不是爱哭!”“你还敢提那件事!”房东一被戳了软肉就炸,八年前自己托朋友从国外带过来的糖果,原本都已经信誓旦旦的跟女朋友有惊喜要给对方,结果一把被钱糖抢过去吃了,人当时还高中生的,和一个小屁孩抢剩下的糖果,不料还被钱糖揍了一顿。
之后跟女朋友解释了一下来龙去脉,结果最后还是掰了。整件事情无不体现着房东的智商,不过之后消失的钱糖成了借口,初恋的破碎让自己怀恨在心。
现在倒好,人又不知道从什么地方钻出来,指着自己说爱哭,房东也才懂事没多久,一副有种你再说一次再说一次我就打你的表情,被霍钱挡在前面。“你爸呢?”房东看见霍钱,想起正事收起小孩子心思,握紧的手松开,给两人拿了拖鞋,他往屋子里走去,“他去西藏度假了,这里交给我管……你们先去客厅坐一会。”霍钱松开手,钱糖自己先埋进沙发里,霍钱坐下时看见房东从书房里拿着一摞纸出来,看两人都在客厅,不避讳的边走边说,语速稍快,看起来是有些紧张“这里的文件你看一下,我想把你在这里的房子收回去,经济补偿肯定是有的。”霍钱拿起文件随意的翻,找着关键字看“那你让我们住哪里?”房东一个咯噔,又握紧拳头“你交的房租本来就很少,没赶你出去就很不错了,你还让我给你找房子住?!”“房租是你爹当时明码标价的,我只是照价付款,你可以再回去找找,他肯定有文件放着的。”“你!”房东毕竟还是年纪轻轻,一时语塞,钱糖觉得两人火药味十足,不介意再添一点,含着糖果含糊说话“爱哭鬼,干吗这么坏想赶我们走……”“我没有!”房东又被激起来,腾一下站起身,低头看见霍钱盯着他的目光,又挪着身子坐下。
霍钱叹气,若是他爹过来还好商量一些,现在这个小鬼头意气用事,倒是难搅和,主动让步“要不这样,以后我把房租按照现在的价格的两倍交了,不过你得把我家重新装修一下。”钱糖先是一愣,坐直身子靠近霍钱,疑惑不解:“老哥你什么时候这么有钱了?”“你不在的时候。”“哦……”钱糖闭口不问,看房东权衡,房东显然是被霍钱的豪气震惊到,以前人穷的一塌糊涂,现在的霍钱让房东捉摸不清,后者把慌张明显的写在脸上,霍钱身子向前倾,敲了敲桌子“可不可以?”“啊、行、可以…”房东慌张点头,事后觉得不对劲时,屋子都已经装修好了。
钱糖之后还是回学校去,在霍钱身边呆了三个月,听人感慨了七年的故事,有时霍钱看向钱糖,揉了揉人的头发,总得说点什么,而说到内容却又大相径庭。霍钱不清楚女娃为什么一副长不大的面孔,他自己在岁月中显得佝偻起来,而妹妹依旧玉树婷婷,霍钱想,人早就成年,不谈男女之事,作为家长总会担心。
钱糖在想另外的事情,如何跟哥哥解释学校的事情,以及在学校中的学业问题,留级七年估计也就自己做得到,如果是能够名正言顺的毕业自然是好事。
七年之后的魔武让钱糖找到正确的道路,也是之后的事情,若钱糖真有成为魔法师的资格,应当对于其他魔法——不说熟练,至少应该掌握才对。
“糖,你要是能长大一点就好了。”霍钱扭了扭妹妹的小脸蛋,无奈的说,钱糖一顿,现在的自己应该也有二十左右了,一直都是十三岁模样也不太好,回去之后请教一下老师…一想到学校里某个老师一直都是小孩子模样,目光中突然闪过鄙视,咬紧了糖果:“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