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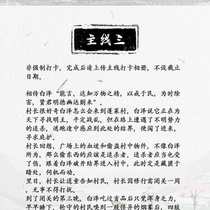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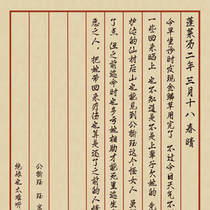



1 吉泽海音 积分:0
2 深山野造 积分:58
3 路西达·科利斯廷 积分:5
4 清梢 积分:11
5 春日透 积分:21
6 甘糟伊佐生 积分:12
7 犬饲翔太 积分:14
8 星野纯夏 积分:0
9 岛城林 积分:0
10 星乃升 积分:4
11 花月星菜 积分:0
12 柏原令 积分:0
13 武田阳葵 积分:0
14 岡田志 积分:0
15 西四辻真昼 积分:0
16 紫苑未迟 积分:0
17 符观一 积分:0
18 京極応挙 积分:0
19 三日月和野 积分:0
20 浅野建一 积分:10
21 纸名梅音 积分:0
22 白日梦 积分:45
23 里卡多·马拉泰斯塔 积分:0
24 蜂须温冬 积分:0
25 伊滨青里 积分:0
26 李旬 积分:0
27 有马薰 积分: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