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后一段!(
啊啊啊啊啊终于写完了!!!第一次从一开始预热到结束参完的企!!认识了很多小伙伴真的超开心!!谢谢企划的大家!!!!
以及可能还是有些逻辑BUG,请轻一点揍我【鼻青脸肿的说着
感谢各位友情出演【鼻青脸肿的递上鸡腿儿便当
谢谢阅读!
——————————————————————————————————————
•日出
埃斯特在沙漠中逆风而行。
翠绿与黄金色交加的眼睛不带一丝感情地注视着前方,亚金色的头发向后飘起来,发尾有着稍稍的青色,露出带有些许羽毛的尖长细耳。
他将围巾向上再拉了一点,明明差不多已经要早上了,风沙却吹得天空都昏暗起来,阴沉得令人绝望。
一如他一路而来所遇见的那些死亡。
比如那个,与已经死掉的金色头发的少年一起倒在血泊中的,口中还在喃喃着什么的濒死的黑发少女。
还有之后所看见的,以不同的方式在这里终结自己的生命的人。
不,是神,与魔。
——但是,多可怕啊。
曾经坚定地去执行的事情,毫不犹豫地去相信的事情……
为什么现在开始动摇了呢?
为什么已经记不起来了,是为了什么而开战的呢?
那样的信念,是什么时候开始因为有了太多裂缝而土崩瓦解了呢?
埃斯特猛地抓住这具身体心口的衣服。
他……
是什么时候开始厌倦了战争的?!
仿佛一切都被谁命中注定了的剧本,最终是为了什么呢?
埃斯特停下了脚步,因为浓重的血腥味就在前面。
无数带着伤口的尸体七零八落地躺着,埃斯特无暇去顾及。
因为他看到了,两个以安详的睡着了一般的姿态倒在那里的少女。
“告诉吾啊。”
埃斯特在无人理会的这片毫无生机的土地上低声地自言自语。
“为什么呢?”
“呼……呼……”
埃斯特狠狠地将那把之前是罗利捡来的,现在已经断成两半的剑丢到一边。
他的身后是三具尸体。
精疲力竭地勉强站立着,埃斯特举起已经伤痕累累的左手,凝视着小指上那个小小的,闭上的翠绿色眼睛的图案,然后沉默地用那只手将黏在脸上的发丝拨到一边,再擦掉嘴边的血迹。
“……还想着把围巾还给赫瑟尔呢。”埃斯特讪讪地牵起围巾的一角,看着上面残留的血迹,“已经不能还回去了……。”
双腿已经快承受不住,但埃斯特知道如果现在倒下去,就再也没有力气爬起来了。
“结果连这一次的神皇大人长什么样子都没有看见,呵呵呵。”埃斯特自嘲地笑了一声。
“如果可以做出选择的话,要是下一次能作为一个普通的孩子,普通的活着就好了。”
他仍自言自语着。
“我才是……连能够慢慢了解这个世界的权利都没有呢,罗利。”
风沙不知为何在此时竟缓缓地平息了,有耀眼的光芒从天的那一边缓缓升起来。
埃斯特转身面对那光芒,直跪而下,虔诚并坚定地合拢双手,做出祈祷的手势,然后闭上眼睛。
“黑夜终将过去,星光总会黯淡,一切只为最终的破晓。”
他仍自言自语着。
然后直直地跪在那里,保持着祈祷的姿势。围巾随风飘扬,身体却未动分毫。
太阳升了起来,阳光温柔地洒在冰冷的、有着死去了的埃斯特灵魂的、罗利的身体上。
他仍保持着祈祷的姿势。
-THE END-
接上黎明临前昏暗之时!
分段发装个笔【ntm
到这里开始可能有些逻辑BUG……请轻一点揍我【土下座【。
感谢残风友情出演【ntm
欢迎阅读!!
——————————————————————————————————
•曙光
罗利迷茫地打量着四周,姆蕾森林的影子早就不复存在,入目只是苍凉的灰黄色,空气中飘浮着淡淡的血腥气息。
还有……身旁躺着的,似乎是睡着了的绿发年轻人。
罗利附身去探他的鼻息,随后僵在原地,瞳孔不可置信地收缩着。
“死……死掉了?”
那……这里是?!
他又为什么会突然恢复身体的掌控权?!
难道……
“埃斯……特……埃斯特?!”
罗利惊惶地站了起来,抱住自己的头,努力在心里呼唤着。
然而什么回应都没有。四周是令人心悸的死寂。从前那道冷淡却不失生动的声音,此刻什么回应都没有。
但是……手上的契约符文……还在。罗利看着自己左手小指上那个睁开的金黄色的眼睛图案,稍稍松了口气。
至少你还活着。我可以这样相信吧?
接着罗利费了很大劲将那位年轻人埋葬了,他想把那把剑意思意思插在被埋葬的年轻人旁边,但无奈沙子是流动的,剑按上去不一会儿便滑下来。其实也可以插得更深一些,但在沙漠里还是保存些体力比较好——光是埋掉那位年轻人,罗利就已经气喘吁吁了。无奈之下,只好暂时将那柄剑带着。
一回头猝不及防地看见一个被沙子掩埋了一半的血淋淋的脑袋,罗利吓得一跳退开两步远。
“埃斯特之前在这里和谁发生过战斗吗……?”罗利一边朝着不知道哪个方向走着,一边心想。
“——因为是战争啊。”
“……?!”罗利被脑海里突然响起的声音吓了一跳,随后喜悦得竟不禁脱口而出:“……埃斯特……!!”
“傻,不要在这种鬼地方随便张口呼吸。”
“哦……”罗利紧张地闭上嘴巴,但还是忍不住地笑,“你还活着……太好了。”
“没什么好的。苟延残喘罢了。”埃斯特淡淡地回应着,如果现在罗利可以看到的话,就会知道他现在整只成大字型躺在自己精神世界里——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平面,“听着罗利,刚刚吾和一个杀马特打了一架,现在的情况不大乐观。毕竟吾不是干这一行的。总之要吾恢复到之前的力量程度要用的时间不短,在这期间吾无法保证你的安全。……”
罗利听见埃斯特仿佛歇了一会才继续说:“……虽然吾知道汝也会点魔法,但是死亡沙漠越往里走越荒芜,作为自然术士,一旦在里边遇到危险,不仅汝会死,吾也活不了。所以吾等离开这里吧。”
“……埃斯特?”罗利有些迷惑,眨了眨眼睛,“你不是要……参加战争吗?你的伙伴也许还在前面等你?为什么……”
“汝以为凡界的身体很强大吗?”埃斯特仿佛翻了个白眼,“照汝的体力能走到这里就不错了。而且伙伴什么的……吾总是一个拖后腿的家伙,他们不会希望见到吾的。不过,要说同伴,汝和吾才是那种关系吧?”
“是、是吗。”
“……”
“……”
罗利站在原地愣着,两方沉默许久。
“……罗利。”
“是…?!”
埃斯特突然出声,罗利下意识绷直了身体。
“……也许是吾太自以为是了。吾等只是共生体的关系……明明是吾一直在单方面的利用汝,扰乱了汝的生活,不仅带汝进了这么危险的地方,还在这里指手画脚的……。抱歉。因为这场不知何时才能结束的神和魔的战争,把没有任何罪过的汝等也牵连了进来。抱歉。”
“没、没事的……”罗利有些不知所措,“我并不觉得……埃斯特你在利用我啊,是我自己说要帮你的……能为别人做点什么,能有存在的意义,我觉得……很开心啊……倒不如说我乐意被你利用呢。在世界上行走了这么久,我还是第一次…除了植物和动物以外,有谁肯发自内心地在意我的想法,即使那是一个与我相隔数千万年的神……。我…感到很荣幸啊,埃斯特。”
“……”
又是一阵沉默,罗利小心翼翼地呼唤了一声:“……埃斯特?”
“——所以吾说过汝迟早有一天将死于心善啊,愚蠢的凡界精灵……”接着传来的是埃斯特闷闷地发出的声音。
罗利不知道该回答什么才好,怯怯地走了两步,又立在原地。
然后又是,该死的沉默。
“解除契约吧。罗利。”
“……诶?!为什么……”
“吾把吾的力量借给汝。虽然还不是很完整,但也许足够汝逃出去了。……呵,不管是从前还是现在,吾都是一个逃兵呢。”
忠诚,欺骗,相互奉献。
也许这场战争教给他的,并不全是……令人悲伤的东西。
罗利还未开口,刘海挡住他的表情,埃斯特已经就着灵魂体飘了出来,腰部以下的身体已是完全透明。他用那双没有任何重量的手掌,轻轻抚上罗利的额头。
有金色的光芒从他们身上散发出来,但只是一瞬间就消失了。
罗利低着头,埃斯特不可置信的看着他。
“汝……为什么要抗拒……”“埃斯特才是笨蛋!”
埃斯特被罗利突然间的发言镇住,一愣一愣的。
“为什么要这样……难道你……以前也做过这样的事情吗……那样云淡风轻地,以不重视自己的态度……”罗利的身体狠狠地颤抖起来,像是在忍耐着什么似的,“重视你的人……会因为你这样一意孤行的举动而伤心呀……”
“罗…利……”埃斯特一瞬间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他也从来没有说过,自出生起,甚至到这一次转生之前,除了那位大人和……另一个谁以外,也没有谁发自内心的在意他的想法。
甚至,那位大人还曾因为相信了他,一度遭遇不测。
“献祭这种事情,我也会呀。”罗利看着发愣的埃斯特,坚定地开口。“就算这是一场会输的战争也好,会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也好,会中途死去也好。让我再帮你一把吧,埃斯特。”
话音刚落,温和的绿色光芒便向着埃斯特袭来,在他身体下方和身体周围凝结成了符文繁复的魔法阵。
“?!”埃斯特感到有些不对劲,事情的主导权一瞬间换了掌握的人,他想要躲避,却因为契约的原因无法离开太远。
“这边好歹也是……精灵的自然术士呀……”罗利颤抖着眯着眼露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然后低下头,片刻便有水珠沿着脸的轮廓吧嗒吧嗒地往地上掉,弄湿了一小片沙地。“埃斯特……你可是有同伴的家伙……你有着不可以轻易放弃的命运。而我和你不一样,是直到不久前都还懦弱地连走出去看看这个世界都办不到的胆小鬼啊。比起这样没用的我……你要出色得多,你能够毫不犹豫地作出决定。你看……现在我还在因为恐惧死亡……手在不停地……”
在不停地,发颤呢。
即使如此,罗利还是没有丝毫要解除魔法阵的意愿。他带着红通通的鼻子和还未干涸的泪珠抬起头来,认真地盯着埃斯特,就连瞳孔也在左右颤动着。
“……一味的害怕与退缩是没有意义的。至少我已经下定了这样的决心了。埃斯特,谢谢你能……成为我的同伴。就算被利用,也不一定带来的全都是坏事呢。”
罗利破涕而笑,又有一滴泪珠沿着他的脸滑了下来。
他拿出之前捡到的剑,划破自己的手,让血液滴在魔法阵上。
然后,他平静地闭上眼睛。
这场景是否似曾相识呢。
有什么湿润的东西,将埃斯特脸颊上金色的泪状刻印模糊了。
他还以为,神是不会……
无形的绿色藤蔓从法阵里挣扎着生长出来,纠缠住埃斯特与罗利的身体。埃斯特愣愣地看着罗利的脸渐渐变得苍白,失去生机。然后,他被藤蔓簇拥着消失在这具已经没有灵魂的空壳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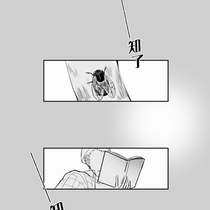
这是上上次神魔战争时期的埃斯特(……)
只是为下文做铺垫,也没什么其他的卵用(……)
感谢神皇友情出演(……
欢迎阅读!
————————————————————————————————
•黎明临前昏暗之时
埃斯特依稀记得,似乎是被魔女干预了的那次战争。
散发着暖金色光芒的那位大人筋疲力尽地倒下,池中的水被血染红,眼底一片黑暗,埃斯特走上前握住他的手。
“这次大概……要输掉了呢。”
那位大人的眼睑动了动,意识到被谁触摸着后,叹息般的笑着说了这句话。
“对不起……”埃斯特的神情不得不波澜不惊地滞在那里,“都是吾的选择失误了。”
“那不怪你。”那位大人艰难的喘着气,“是我太鲁莽。这应该就是……对我的惩罚了。”
埃斯特忽的抓住他的两只手。
“您不能死。神皇大人。”
神皇只是微微睁了睁眼表示惊讶,刚张开嘴要说什么,被埃斯特阻止。
“埃……”
“这是被吾的过失所造成的错误的结局。所以后果要由吾来承担。”
“请恕吾在此时的无礼。您的肩上是整个神族的命运,您的陨落意味着神族的陨落。所以您不可以死。”
神皇愣了愣,无力地半敛上眼睑,苦笑了一声:“你还是那么忠诚得固执呢。现在……这并不能挽回什么。”
“如果吾说吾就是为挽回而来呢?”埃斯特笑了笑,抚上神皇一片灰暗的眼睛。“神官的力量由天赋予,神皇是天的使者,天的代言。而作为神官的吾,总有将力量回归于天的时候。”
“埃斯特……?!”神皇发觉不对,想要起身,全身的疼痛与疲惫却使他动弹不得。“你……”
“吾为您的耳朵,您的眼睛。请坚信这一点。”埃斯特如同神皇所说的那般固执地继续着,“星星会指引您身前之道路。”
漫天的星光从夜空中洒下来,温顺地围绕在埃斯特与神皇周围,神皇的额头上出现了一连串泛着金光的符文,随后金色的魔法阵漂浮而出,埃斯特割破自己的手腕,血液如涌泉之水溢出,洒在魔法阵上,几乎要将金黄的符文变为血色。
“埃斯特……不……住手……你知道这样做的代价是什么吗?!”神皇感受着体内的力量渐渐盈满,身上的伤口开始逐渐愈合,眼前的黑暗也渐渐散去,心却如坠冰窟。
“这是……吾自己的觉悟。”埃斯特强撑着让自己的声音听上去还算正常,“还有……吾的请求。您不可以为此感到负担。黑夜终将过去,星光总会黯淡,一切只为最终的破晓。”
然后埃斯特的身躯与衣物一起化作金色的光芒,和那星光一同涌进了神皇的身体。
那之后的事情,是下一次转生时方才知晓的了。



我不是故意黑谁的,我只是想活下去!
我和弗蕾亚不一样!不要混为一谈!
==1248字==
“弗蕾亚。”
熟悉的声音惊醒了沉浸在自己的遐想中的弗蕾亚,让她把注意力从无名之城外星光点点的景象投向那声音的来源。
那人身材纤细,穿着轻便的皮甲,站在建筑物的阴影里,脚边趴着一只不停哈气的小型犬,撇着的嘴角透露出被勉强做某种事的无奈和苦涩——是弗蕾亚意料之外的人,伊格•斯图亚特。
“咦,竟然是伊格?”
弗蕾亚一副故作惊讶的表情,朝着伊格摆了摆手。后者没好气地叉着腰,径直走到坐在石块上的弗蕾亚面前,以居高临下的姿势盯着弗蕾亚面带微笑的脸。被她称作茶砖的小型犬本能地预感到了某些事情,兴奋地在她脚边不停地转圈。
“阿拉,虽然弗蕾亚的身材矮小,不过伊格应该不是来炫耀身高的吧——”
“弗蕾亚小姐。”
“哈?”
突如其来的带着尊敬感的称谓让弗蕾亚一时间连惯用的语调都忘记了,眯起的眼眸里写满了疑惑。在她的印象中,伊格并不喜欢开玩笑,尤其是在知道所有关于弗蕾亚的玩笑最后都会以令人尴尬的沉默收场这个前提之下。
和弗蕾亚所想的一样,伊格以一种很严肃的语调将话题继续下去,完全没有开玩笑的意思。
“弗蕾亚小姐,关于您的身份,您有什么想解释的吗?”
“菲诺女神的牧师呀,弗雷亚确实是大家印象中的坏人喔,这件事情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有好好确认吧?”
“我是说,你的职业。”
伊格一字一顿地吐出这句话,脸色变得像是茄子一般的糟糕。
这个时候,弗蕾亚已经能够感觉到某人的视线正在关注着这边事态的发展。那是带着好奇和恶作剧般味道的目光。
啊,原来如此。
歪着头大致整理了一下思绪,弗蕾亚确定了现在的情况和接下来她该做出的回答。
“娼妇呀。”
“…为什么你要说的那么直接!”
“伊格~~~所以娼妇是什么意思啊?”
“谢谢你弗蕾亚,莉芙我已经问完了所以请求你不要继续追问了好吗!”
从坍圮的建筑后面跑出来的莉芙一下子拦腰抱住了伊格,一脸笑嘻嘻的表情。
“嘛,果然是莉芙让你问的嘛。”
弗蕾亚难得一见地没有趁胜追击好好地戏弄伊格一番,说完这样的话就躺倒在原本她坐着的那块大石头上了。
好不容易摆脱了莉芙的纠缠,伊格筋疲力尽地坐在了弗蕾亚的身边。而维持着一脸不知好歹的狗样的茶砖,早已被伊格狠狠地拎起来丢到了一边陪着莉芙去了。
两人之间保持着一种奇怪的沉默,直到弗蕾亚率先开口。
“为什么刚才用敬称啊?”
“‘小姐’有时候是蔑称——”
“刚才不是这个用法吧?”
“好吧,莉芙原话——要对弗蕾亚有礼貌。”
“原来如此,礼貌地询问着不堪入目的问题呢。”
“不堪入目的是你啊,色情牧师——我觉得这才是你的职业吧!”
这一污蔑性的称呼却让弗蕾亚露出了十分高兴的表情,她伸出食指在伊格的眼前晃了晃。
“色情嘛~弗蕾亚倒是不介意,不如说,很喜欢呢~”
“我要与你划清界限。”
伊格毫不犹豫地把位置挪远了。
“弗蕾亚倒是希望大家能够更坦诚一些呢,欲望可是生命与生俱来的呀,德鲁伊应该比普通人更明白这一点喔?对了,下一次还有那样的工作的话,请务必不要忘了弗蕾亚而自己上哦?”
伊格好像在生气地说着些什么,不过弗蕾亚已经把帽子盖到了自己脸上,就着无名之城周围破碎星海的亮光,沉入一片粉色的梦乡里了。
弗蕾亚小姐——请问,这样的生活真的好吗?
真是好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