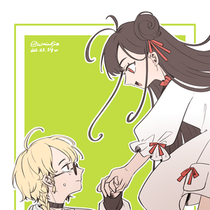眼前的兰令牌自行车辐条闪闪发光,御镜把去霍格沃茨要带的大箱子绑在它的后座,用两条带钩子的皮带固定住。她下意识地拍了拍斜挎在腰间的猪皮小包,听见英镑和银锡可混在一起碰撞发出令人安心的声音,名叫“羽毛笔”的小猫头鹰被她打搅了睡眠,在包中发出不满的咕哝声。她费力地推动自行车,辐条的光芒闪烁,又渐渐暗淡。假期结束之前她总要和外婆都子争论有没有必要把这台自行车擦得这么干净——这里和伦敦唯一的相似之处就是连绵阴雨和藏在坑洼老石板路里的淤泥。但外婆总是坚持她应该推着一台干净的车去“拉文克劳”上学——她有时候管霍格沃茨叫拉文克劳,有时候反过来。她作为一个“麻瓜”对霍格沃茨印象很好。“他们让你找的裁缝活儿不错,证明他们是好学校。”都子外婆每年假期都会戴上蛤蟆大小的眼镜,整齐的针脚接在摩金夫人长袍店的魔法针脚后面,帮御镜延长长袍的袖子,“选的蓝色也很好看,很有品味。”她说,御镜很难跟她解释,拉文克劳的蓝色不是她选出来的,她是被选的那个。
“……美国人要到月亮上去,我看他们真是多此一举。”都子外婆走在兰令牌自行车的后面,象征性地拖着印了霍格沃茨校徽的行李箱,“但是你们这些巫婆可以坐着扫帚去月球,对吗,没准儿你们学校的那些个教授早就去过了。那上面肯定什么都没有,要不然美国人才不会费劲再上去一次。难道美国全是瓜?”“麻瓜,美国有巫师,他们管普通人叫麻鸡。”“美国人什么都知道。”“也不一定,巫师通常和麻瓜们保持距离,他们彼此难以理解对方的生活方式。”“有什么难以理解的?”“……”御镜叹了口气,推着沉重的自行车,夹克下的旧毛背心里全是汗,她的鞋子也挂上泥,她想着要从哪里开始解释巫师的生活跟麻瓜有多么不同,但外婆早就有自己一套生活的规则,就算对她施了遗忘咒,她的身体也会按照既定的机械程序运转起来。
“巫师不怎么吃米饭。”
“难以置信。”
我们家以外的地方也没人吃米饭。御镜暗忖。但外婆似乎理解了。话题迅速切换回到月球的事情,这不赖她,渔夫们的收音机整天在说这件事。外婆说着说着,她们背后,大海的方向太阳升起。
“你也可以坐着扫把到月亮上去,听说月亮上有蟾蜍,说不定就是你们古代的巫婆留下来的。”
“…不行,我飞得没那么好。”御镜憋了一口气,自行车被她推过一个深深的水坑,外婆灵巧地躲开飞溅的水花,行李往御镜的方向歪倒,她赶忙用肚子撑住座椅,口袋里的小羽毛笔又急促地叫了一声。
“也是,你连自行车都不敢骑。”都子外婆笑起来,帮她扶正了车子。“要不然我们也不用这么早出门了。”
“…扫帚和自行车又不一样。”
“哪有什么不一样,小丫头都一样。骑在车上瞻前顾后,生怕摔破膝盖,回过神来车轮子早就翻天了。”都子外婆像是一只狐狸一样弯着眼睛,语气带着温和的嫌弃。脚下和缓的上坡路逐渐平整,平直的海岸线被城市参差的屋顶吞下。御镜看到火车站顶楼的钟表,被阳光从三点钟切割成明暗两半,肥大的海鸥粘着旅客的脚踝,又被高耸的行李推车赶走,不情愿地起飞又降落。外婆的话语还未停下:”上车试试。你就是缺乏一点勇气。“
——你就是缺乏一点勇气。
火星比月亮更加明亮扎眼,伊蕾娜的头发在垂暮夕阳剩下的那一点光芒中又被染成火星一般的红色。湖上吹来湿乎乎的风把她的头发从耳朵前面编成不怎么好看的结,丢在脑后。
“别这么僵硬,魔法物品能感觉到你害怕。”伊蕾娜的声音从发旋上方响起,御镜才发现她紧紧握住扫帚柄的手腕不自制地发抖。“放松。看前面,别看脚下。”
“看前面,别看脚下!”都子外婆弯下腰,这次她使劲了,她双手就能卸下行李箱,稳稳地扶着后座,御镜根本不会倒下。车座跨在御镜的裤子下面,她吞下一口口水,踩下踏板——
——禁林沐浴在红色的余光中,每一棵树都分到一束红色的束带,她们向前飞,伊蕾娜的手套在御镜手指的前方一点,斯莱特林长袍墨绿色的内衬时不时出现在她眼角,她们绕了一圈,飞向魁地奇的门柱——练习还没开始,御镜照课上教的那样僵硬地侧着身体,腰肌几乎抽筋,而伊蕾娜很自然地配合她的重心歪过去,她们绕过最高的那一柱。夕阳擦过拉文克劳的塔楼。恋恋不舍地和上头的瓦片道别。伊蕾娜稍微提起小臂,扫帚向上倾斜,御镜下意识地弓下腰,几乎要贴在扫帚上。“哈哈哈,没事啦,别像个蟾蜍一样。”她说,而身前的女孩根本没听进去,她拉高扫帚,出现在淡紫色夜空中,月亮银色的轮廓和拉文克劳的塔楼离他她们越来越近。
辐条快速转动,吃着御镜腿部的力气,她看着前方,无视广场上肥大的海鸥,都子外婆在她身后跑了起来,风声越来越大,身上的汗水冰凉,衬衫贴在她的胸口。
——风声越来越大,她们升高,不去违抗风的轨轨道,扫帚的头部放平,伊蕾娜的胳膊从御镜的肚子和扫把中间穿过,像是腰带一样强迫她抬起来:“好啦,我们慢慢飞,慢慢飞。”虽然她口中安抚,但语气中难掩兴奋。御镜将信将疑地放松身体。任由伊蕾娜安全带似的搂着,跟着她一起向前。远处的星星开始显现。“我最近可以很快找到猎户座了。”伊蕾娜说,她信守诺言,平稳地前行,“你告诉我的很有用,只要找到猎户座就能找到别的,那颗红色的…”
“参宿四。”
“它很明显。”伊蕾娜指着天边的一颗星星,“这样我就能找到参宿七,就像迷宫的底边一样。”她的手指划向参宿四的斜对角,“再往左就是大犬座,我以前总是从大犬座开始画,考试对错全凭运气。”她比划着,风托着她们飞向星星,星星却不会变大一丝一毫。
御镜顺着她的手指看那些逐渐清晰的光点,脑海中想象出在桌面上摊开的星图。伊蕾娜搂着自己的手臂很温暖,让她紧张的脚尖更冰冷。
搂着自己的手臂。
她低下头,看到伊蕾娜的手臂;她抬起头,伊蕾娜另一只手正在指着星星等她判断对错。
她们在飞——准确地说,是御镜在飞。
从一年级开始她就没能成功离开地面两米以上,现在她们冲着猎户座悠然前行。
与风一起灌入她口中的兴奋与恐惧让她差点呕吐,她迅速伏下身,只想降低一点点的高度,但扫帚却突然失重一般顺着她的身体干劲十足地俯冲——伊蕾娜发出兴奋的,犹如猫头鹰一般的尖叫,她听不到她在笑,风把她的笑声裹走了,她只能感到她贴着自己的肩膀不住抖动。
海鸥们如同白色的浪花从她兰令牌前头分开,飞散,辐条“扎扎”地快速转动,火车站的钟楼变得高大又立体,脚蹬犹如奔跑的双腿那般从僵硬地阻力中解放,她调转车头,绕过长椅,回头看到都子外婆不知何时回到行李旁,抱着手臂看她。御镜没有停下来,转身向她冲去,海鸥们不耐烦地再次起飞,兰令牌扑向小柜子一般的行李箱,她死死捏住铡——
——草坪气味已经灌入鼻腔,伊蕾娜指着星星的手兴奋地在空中挥舞,她不能依靠她!御镜的脊椎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仿佛挣脱了恐惧的锁链,身体被跟不上的重力抬起,只拉起一点点这不听话的扫帚她几乎用光了所有的勇气,拉扯脸颊的风戛然而止。
“你胆子好大啊。”伊蕾娜在她身后,笑得声音嘶哑。“看来不用我帮你也能补考过关嘛。”感到身后的重量突然减轻,伊蕾娜要掉下去了!御镜猛然回身想要抓她,僵硬的膝盖放开,脚尖稳稳地插进湿润的土壤。
“怎么啦?不去吃饭吗?要赶不上我复习魔咒课的时间表了,你答应我的。”她微微皱眉。
“…马上去。”
“别发呆,要赶不上火车啦,快去吧,小巫婆。”都子外婆催促道。
——御镜翻身回到地面上。
御镜翻身回到地面上。想着到了伦敦要不要告诉伊蕾娜她学会骑自行车,但又懒得解释自行车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