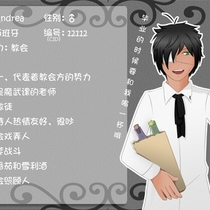*大概是普通故事的结尾了
*接莫医生那边的剧情 因为没商量细节不太一样
*前任(不是)们都有出场 一句话太少就不响应了 私心一发助攻ooc了不要打我嘿嘿嘿
*其实比起荔枝人是普通更想打这个助攻 trust me 这对她来说意义重大真的(
**我就是要打这个tag澄子你别笑有本事打我呀
——
其实我很喜欢爱川医院。
无论是湖也好,亭子也好,宿舍也好,食堂也好,餐厅也好,哪里都很喜欢。
和我一起在这里的还有很多人。我有幸认识了一些,也有很多只是远远地看着。
牙医先生是个很有意思的人,虽然表面上看不出来。当时我正站在湖边往下看,他从水里冒出来的时候我吓了一跳,真的。
椎名医生是个有些害羞的人,但是他真的很好,很认真也很温柔。情人节的时候我们一起做了巧克力,意料之外的好吃。那天,我走了之后,药剂师先生还带了一些回去送给另一个人。在这里有这样值得他在意的人,我觉得很开心。
保田先生是个非常温柔的人。那次他想帮我拎包,我还以为他要牵我的手,愣了一下呢。
不过啊,最后他还是牵着我的手去电影院了。那是一种很陌生的感觉,但我不讨厌。后来我们看了很多电影,我几乎从来没去过电影院,保田先生似乎也意外地差不多,两个人一起,还是挺新奇的体验。
等我意识到的时候,已经是第三个星期的最后了。
时间从来没有这么快过,我想,即使是那段日子里也没有。
大概是星期三的时候我路过莫医生的办公室,他似乎在拿着一封信函有些烦恼的样子。我下意识地就走近了门边,门是开的,他抬起头就看见了我。我和他打了招呼,莫医生倒是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示意我可以进去。
是遇到什么烦心事了吗?我礼貌地询问他,不介意的话我可以帮忙的。
莫医生有些局促地揉了揉头发,放下了手中的纸张。我看见信纸抬头的标记,似乎是来自爱川院长。
这一定是比较重要的事情吧。
后来莫医生还是给我解释了。这一周的搭档配对出现了一点疏漏,没有他的名字,院长确认是她的工作失误,就给他和同样状况的六个人发了这样的一封文件。我接过信纸,一下就被上面的条件吸引了。
“自己和全家终生免费医保卡……这不是很好吗?啊,可以和一个人无条件离开医院也不错啊,或者和有搭档的人接触一下也不是不可以……”
我忍不住捏着信纸,看着莫医生的眼睛吐露了心声。
“这个,简直,根本就是白赚的交易啊!”
莫医生直直地盯着我。
也许我说的太直白了一点,他的表情依然没有放松,似乎还是有着什么困扰。即使我们又聊了一会儿,话题闪闪烁烁的,直到最后也没能讨论出个所以然来,莫医生把信纸连着信封一起收进了抽屉,宣告着这件事情的暂时搁置。
大概,对于我来说很简单的选择,对他来说就有着不一样的意义吧。我在回宿舍的路上这样想到。如果是我的话,能拿到全家的终生医疗简直就像中了头等彩票,说什么也不会放弃的。
不过啊,如果“全家”要求直系血亲的话就麻烦了呢,希望院长不会那么教条吧。
之前,我在翻活动手册的时候看见了星期六的特别标注,“空白的一天”。在星期六的时候所有的搭档会解除身份,希望大家都能和心仪的人共进晚餐。
是这样的日子呀。
我在星期五下午道别的时候,向保田先生提起了这件事。
因为我知道他有那样一个人,是神前医生。
我问保田先生,星期六晚上我能不能送他去见神前医生。他有些奇怪,不过还是答应了。
保田先生真的是一个非常温柔的人。
要说这样做的原因,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忽然有种冲动想去看看他们,看看他们在一起的样子,和他们道别,注视着他们的背影走向夜光中去。
我想他们一定会有很好的未来。
晚上,我无意间从包的夹层里找到了我的手机,原本以为没有带过来的。尽管几个星期没去碰它,开机之后电量竟然还有那么一格,翻盖的旧手机果然在这个方面要出色不少。我沿着未读短信翻下去,一条一条地看。
大哥发了好几条短信关心我在哪里,大姐的也有,我想他们应该从别的渠道了解到了情况吧,不会到现在还在担心的。要是给他们添了这么多麻烦,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了。
小公主也发了不少东西过来,一开始是分享学校发生的事情和抱怨房东什么的,后来就开始问我在哪里,怎么不回她短信。最后一条是说她联系上大哥了,让我照顾好自己。
她真的长大了好多。我忍不住想,大家都在逐渐成熟起来啊。已经有好几年没见到茶色了,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了呢?
我忽然就有点想出去看看。
星期六的下午,我在约定的地方遇见了保田先生,他穿着一件长风衣,看起来比平时要郑重不少。我想,我知道原因的。
一路上我们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天,无论是怎样无趣的话题,保田先生都会接下去。走在旁边的时候,我注意到他似乎有一点点紧张,大概是我的错觉吧。
其实上午我们的搭档关系就解除了,神前医生应该也找过保田先生,我这样猜测。即使这样他还是愿意和我出来,让我陪他走这么一段路,大概象征是大于实际意义的吧。
我喜欢这样象征性的东西。
我们到的时候,神前医生已经等在那里了。现在离晚餐时间还有一会,也许他们还有些事情要做。我不打算多加猜测。
互相打过招呼,神前医生对我点了点头,似乎并不意外我的出现。我原本是有些话要说的,到这个时候却忽然不知道如何开口了。看着他们的眼睛,我弯下腰去。
“两位,请多保重。”
脱口而出的是这句话,我自己也有些惊讶,不过,我想我知道自己要说的是什么了。
“保田先生和神前医生都是非常非常优秀的人,到这里,能认识你们,我真的非常幸运。”
我又鞠了一躬。
“请你们一定要幸福。”
保田先生微微瞪大了眼睛,随即反应过来,露出一个笑容。神前医生直直地看着我的眼睛,认真地点了点头。
这样就好了。
回去的路上我从包里拿出了手机,有一个来自大哥的未接电话。也许是逐渐变暗的天色带来了些许凉意,我搓了搓手,神使鬼差地打了回去。响到第四声的时候,大哥接了起来。
“符子?”
我忍不住轻轻笑起来。
“嗨,是我。”
“我之前以为手机没带呀,昨天不知道怎么就翻出来了。”
“嗯嗯,挺好的。医院很棒啊,大家也很好,还有免费的电影看呢。”
“你和大姐怎么样呀,店里呢?”
“啊,我知道啦,挺好的就好。小公主的短信我也看到了,她现在呢?”
“住在你们那儿啊,那就没关系了,我还担心来着呢。”
“好的呀,我也不知道……应该很快就会出去了吧。”
“嘿嘿,没有这种事情啦,你想太多。”
“是说就算谈恋爱……”
我停下了脚步。在面前的路灯下,站着一个我有些熟悉的身影。
“等下……”
我放下手机,试探着向前走去。对方被笼罩在朦胧的橙色灯光之下,眉眼看不清晰,手上似乎还拿着什么东西。
“莫医生?”








*计字8081
*手撕贝尔
*flag,flag,和flag【。
|14|痛为何物
你们的同伴,已经被“取代”了。
他说出那句话,轻飘飘地。
冷风顺着衣服的后领吹到背上,跑出的一身热汗似乎在瞬间变成了冰。
“你什么意思。”
从我嘴里发出的声音古怪嘶哑到扭曲,不像是人说话的声音,更像是少年残存的灵魂用这具身体的牙齿和舌头摩擦出来的咆哮。
“他们已经被衍冬裔‘掏空’了……和那些人一样。”贝尔的声音变得有些不太真实,像是一张窗户纸那么单薄,感觉随时会被外面呼啸的寒风吹破。
“你不是带人去找他们了么?”嘶哑的声音在继续,“他们被‘取代’了,那你派去的那些人呢?他们也被取代了?还是说,只有我的队友们被取代了?”
“援军还没有赶到,他们就被取代了……”
“你说的是阿伦德尔——那个吟游诗人他们,还是我们的队长?”声带在在颤抖。
“都是。”
“呵。”
少年的声音轻蔑得比风中的冰花还冷。
“我相信眼见为实,在不能确定他们的状态之前,我不会轻易对他们下手。”叙泽特在一边接上了话,显然她知道少年不冷静的弱点,高等精灵似乎是见惯了生离死别,对她的这些友人也只是多了些“眼见为实”的判断而已。
说着走着,城墙已经到了面前。
“他们躲在某个房间里……”贝尔顿了一顿,“如果你们执意要找到他们,那么就只能挨着房间搜查了……”
“你不知道他们在哪里么?”
少年的那些愤怒似乎再度沉入了意识的深海中,现在我的思维竟然前所未有的清晰。
“我需要注意的事情确实有点太多了……所以没有注意到他们到底进了哪个房间。”
“也难免。”我点点头。
“这一带没有你的同伴以外的……”
“他们不是敌人。”我截断他的话,贝尔似乎被噎了一下,不再说话了。
“他们不是敌人,过去不是,现在不是,以后也不会是。”我推开一间房子的门,里面空空如也,就像少年刚刚来到无名之城时那样寂静。
“但是他们现在已经不是你认识的那些人了。”
“我不相信那些那么坚强的人会这么简单就被变成傀儡。”我走进隔壁的房子,里面只剩下些许篝火的残灰,看起来不久以前还有人在里面居住。
“衍冬裔的力量是你们无法理解的……”贝尔似乎咽了口唾沫,“他们把人变成傀儡的方式不是靠意志力就能够打破的。”
“那你也太小看意志的力量了。”我摸了摸胸口,少年的心仍然在痛,一个被半梦妖所占据的身体、一个本应该已经消失的灵魂都能够保持这种感知,被当成傀儡这种事情又怎么会让这些人轻易地失去理智呢。
贝尔叹了口气:“所以衍冬裔并不是依靠暴力把他们变成傀儡的……”
“不管如何,我是不会轻易对他们下手的。”我往街角走去,叙泽特似乎打算往左搜索,“我相信我的队友们。”
“和你们这些武人真是讲不通道理……”
“那就不用讲了。”我转身走过路口。
菲利普短促地叫了一声,拍了拍翅膀。
对面是四个熟悉的人影。
两个高的是诗人和游荡者,稍矮的是战士和风裔德鲁伊。
“你看,他们已经被取代了……”贝尔的声音又在耳边响起,“就算你去确定什么也只是徒劳。”
“你稍微安静一会。”我咬着后槽牙,贝尔的声音消失了。
他们的表情警惕而犹豫,游荡者反手握着匕首,瑞贝利安在挥舞着剑喊叫着什么,只是被艾丽西亚拦住了。他脸上似乎受了什么伤,一片的惨白淡红,还有水泡似的东西在那右半张脸上成群地肆虐。
好一个惨不忍睹。
淡白的雪花从我们和他们之间飞过,将他的声音截断在层层叠叠柔软的冰晶里。
你们还好么?你们是我认识的那些人么?你们是敌人还是朋友?
无数的问题堵在我喉咙里,如鲠在喉。
艾丽西亚手里抓着瑞贝利安,看看我们,看看诗人,一旁的卡利亚时不时地插句话,他们似乎在商量着什么东西。
如果真的如贝尔所说,他们已经被同化成了衍冬裔,那么现在他们就应该是在商量对付我们的对策。
——但如果不是那样。
诗人终于转过头来,嘴唇翕动着似乎想说什么,却又抿了起来,气氛一时变得比天气还要寒彻骨髓。
六人就这样对峙着,谁也不肯先开口,谁也不肯先动手。
艾丽西亚红榴石样的眼睛里满是悲伤,水汪汪地。
——不对。
中间的小路上传来轻而匆忙的脚步声,有人正从那条巷子里向这边跑来。
——如果她已经成了衍冬裔,怎么还会拥有这么清澈的眼神呢。
“你们这些异教徒去死吧!”
人未到,声先闻。
——不对。
清亮而具有穿透力的声音,说着恶毒的诅咒,却透着一股子的喜悦。
——有什么东西不对。
灰白的小脑袋从巷子里冲出来,奥列格往前扑了两步站住,勉勉强强没滑倒在已经积了一层薄雪的地上,背后跟着一个森精灵的女孩。
“你们这些异教徒!”
他抬头,脸上是难以掩饰的喜悦,看到我们之后却僵在了原地。
——有人在撒谎。
七个人分站三处,风愈发凛冽,空气却仿佛凝滞。
然后诗人拔出了刀。
风声能阻断人的低声交谈,却无法掩盖再轻不过的金戈之声。
他举起手,那刀很旧了,少年还在的时候他就在使用它,只是刀刃仍然锋利,还能在蓝月下反射出明晃晃的冷光。
阿伦德尔向前迈了一步,漫天飞扬的风雪里看不清他帽檐下的表情,叙泽特明显地紧张起来,杀意瞬间喷薄而出。
诗人松手,刀掉在地上,叮的一声轻响。
——缴械,再通用不过的表达和平的方式。
瑞贝利安冲他喊了什么。
诗人没有理会战士,他径直朝我们走来,白雪在他脚下被踏出一个个灰黑的鞋印,他穿过白色的风,走到了这场对峙的中心。
“你这异教徒要做什么!”侏儒睁大眼睛喊叫。
他伸出了手,雪花落在他手上,很快竟然积了一层白色。
“异教徒!”
诗人的帽子被风卷起吹飞,他的脸彻底露了出来。
他面色惨白嘴唇发青,然而那双银河一样坦荡的眼睛一如少年初见他时。
雪落在他身上,他固执地伸着右手,维持着那个握手的姿势。
奥列格跑向他,抓住他的手。
叙泽特快步走去,细长的手指放在一大一小两只手上。
身体不自觉地做了动作,走向前,然后握住了那只带着些微硬茧的手。
一瞬间少年的记忆闪过了大脑。
“他叫奥列格·尤里·谢尔盖。你可以叫他这一串长到反胃的名字,也可以叫他队长。”还是个小少爷模样的阿伦德尔放下了排笛,“我叫阿伦德尔,是个吟游诗人。”
什么东西碎了。
像是从梦中的深海里冒出的气泡,放大,稀薄,然后破碎成泡沫,被海水推向四面八方。
大脑的神经在剧烈地疼痛,抽搐,然后仿佛被切断般出现了瞬间的意识空白。
“你们竟然能够击破我的法术……我的确小看了你们。”
仍然是那个充满磁性的华丽男中音,只是现在那里面没有了我之前所听到的各种情感,只剩下些阴鸷的狠毒。
“所以说谎的人就是你了,对吧。”我按住太阳穴,那里仍然在一跳一跳的钝痛,像是有把小锤在从里面往外一下下地击打,“你到底骗了我们多少?”
“你们觉得呢?”他发出嘲笑。
“不管你骗了我们多少,我们都要把这些几倍几十倍几百倍的还到你身上。”阿伦德尔狠狠地吐出这些字,像是从牙缝里吐出刀子。
泰拉·贝尔咯咯咯地笑了起来,我几乎能想到那个男人笑得浑身颤抖的样子。
“刚刚还被我玩弄于股掌之中的家伙,也敢放这样的厥词?”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欺骗我们的!”奥列格抬头,看着白色狂风背后的深蓝天空。
术士又笑了起来,声音黏腻得令人作呕。
“这么说吧,你们这些无知的异教徒来到我所掌控的领域时,就已经成了悲荒之神御座之下愚昧的玩物。我只不过是让你们听到的东西变了一变,你们就相信了我所创造的假象,还听从我的指令杀人,真是一场漂亮的戏——算是我的杰作之一吧?”
“你从头开始……就在欺骗我们?为什么?”奥列格的拳头捏出了些噼啪声,我从不知道这小小的侏儒吟游诗人还有这种力量。
“当然是为了我们崇高无上的神。”声音不再从耳内传来,而是从头顶落下。
我抬头,白色的风雪中落下了灰色的法师,泰拉·贝尔湖蓝的长发在北风中翻卷,仿佛狂舞的毒蛇。
“你为了你的神,连普通人的性命都不顾了么!”侏儒小小的身体似乎装不下那么多的愤怒,那些怒气全部化作了语言从他口中泄出,“没有人,世界还是世界么!你的所作所为,不是为了神,而是要毁了库瑞比克!”
——那些人是无辜的。
——精灵少年也是,布衣女孩也是。
——那个痛骂我的男人也是。
——一切都是被扭曲的谎言。
“可笑,为了悲荒之神的再临,区区蝼蚁,死不足惜——不,为了萨玛斐的荣光而死,这是你们的荣幸。”
他挥手,侏儒抱着头跌倒在地,痛呼不止。
“那个半血的卓尔杂种,你真是最狠的人啊,我都没有想到我只是说了一句话,你一个竟然能干掉那么多人。”他朝我笑,皮肤已经不再是我在那楼下看见的白皙细致,而是仿佛无生命的灰色,色彩粗粝犹如无名之城的砖石。
他的话语本该激怒少年残存的意识,那些情感的波动此时却全部消失了。
少年的也是。
我的也是。
“你欺骗了我,让我去杀死无辜的人。”
心中的海洋毫无波澜,仿佛被冻在了比未写之年还要寒冷的深渊。
“那不是因为我欺骗了你,是因为你心中本就有那份残暴——卓尔本性的残暴,小杂种。”
月亮在海面上升起,血一般的污秽赤红。
“他们不愿动手,你却开了这个头。然后你的同伴跟随你杀人,他们的手沾上了他们不愿沾上的血。”
红色的月光将冰封的海面染得仿佛血海。
“然后你带着他们杀人——一路杀掉所有阻碍你们的人,杀掉有可能影响你们行动的人。”
冰面裂开了一道伤口,无底无穷的深渊中仿佛有巨龙在悲吼。
“记住我的名吧,残暴的小杂种!”
他大笑,笑声将冰面震碎,巨龙带着漫天红色的液体,咆哮着飞出深渊,冲向那血红的月亮。
“吾名呼曰,残虐解放——”
|15|跃龙碎月
红月被巨龙绞碎,化作无数火雨流星坠落在浮冰飘零的海面。
光消失了。
有种声音从我身体里缓缓地升上来,像是肺泡被搅乱的喘鸣。最初我以为是过度运动之后的生理反应,它却在渐渐地放大,变成我所不熟悉的悲鸣。
——愤怒。
——是这种感觉么。
——少年的愤怒,还是我的愤怒呢。
那声音冲破我的声带,带着血的味道。
“你愤怒了么?”
他在笑。
“是因为无法接受自己暴戾的一面而愤怒么?”
他在笑。
——不对。
——不是。
——不认可,不正确,不可能。
——本不应该被那些东西影响的。
——辱骂也好,激怒也好,傲慢也好,都是少年的弱点。
——不是我的弱点。
——我不应该出现这种情感的。
“就算你再怎么改变了,你还是一个残酷暴虐的杂种。”
他在我头顶笑着。
“闭嘴。”
陌生的声音从我嘴里发出,不是少年的,也不是我的。
——那是谁的呢。
“残酷的不是我们,是你。”
——是谁在说话。
“你为了你那些变态的爱好和所谓的信仰,利用你能利用的人,让他们替你满足你的杀戮欲。”
——是“我”啊。
“你甚至在利用你自己的信仰。”
——不是少年,也不是梦妖。
“萨玛斐给了你衍冬裔的力量,你就利用它加强你骗人的能力,骗了冒险者们,骗了瓦尔哈拉小队,煽动我们相互战斗,妄想我们自相残杀。”
——是一个活着的,在世界上拥有一席之地的“我”啊。
“是,某种意义上你成功了,非常成功——前无古人的成功。”
——那是不再游离于这个物质的世界之外的感觉啊。
“但是你忽视了我们的力量,我们拥有的你永远也得不到的力量。”
——那是“我”啊。
“我们拥有的力量,叫做信任。”
我终于在这片白色的风暴里看清楚了他的脸。
“你不会理解,因为你永远不会有可以放心地交付性命的人!”
泰拉·贝尔蓝灰色的眼底空空如也。
真正的没有了心的人,是这个法师。
“你的理论我不能理解,也没有理解的必要。”
他收起了笑容,蓝色的晶体生物从他右肩腾起,那小生物身形一瞬间暴涨,半透明的冰蓝双翅遮蔽了半边天空,夭矫的身体弯出完美的弧度。
那是太古时代传说的生物,它们代表着权力、力量和残酷。
——那是“龙”。
“让我的宠物教给你们什么叫做力量吧。”
术士挥手,蓝色的的晶体在空中尖啸,长长的尾巴划破半透明的白色风幕。
“去吧,龙影。”
它向我背后扑去,我听到艾丽西亚本能的惊叫。
“给我从天上滚下来!”
两支铁箭击碎了那被叫作龙影的生物一边翅膀。
“蓝,好厉害!”风裔女孩的声音又响了起来,这次伴着闪电和藤蔓,龙影被她死死捆在了绿色的牢笼中。
利刃出鞘声冷冽如冰,高等精灵剑指天空:“这大家伙很强——是我的猎物。”
电光闪过,龙影发出了哀鸣。
“去吧,去狩猎你的猎物!”叙泽特厉喝。
拇指扣住弓弦,肩背手臂逐步锁死,弓背开满,铁箭飞驰。
——一切都自然而行云流水,和二十年以来无数次做过的一样。
铁质的箭头穿透贝尔的左肩,带着法师单薄的身体向后疾飞,他发出痛喝,龙影似乎想要转头去搭救自己的主人,叙泽特当然不会放任它那样走掉,从剑上生长出的霹雳照亮昏暗的天空。
铁箭嵌入砖墙,深蓝色的血液顺着他的白衣流下。
“你害死了那么多的人,现在我就用你的血去祭奠那些无辜丧命的人。”
又一支箭,干脆利落地穿透法师的右肩,挣扎的男人被结结实实地钉在了墙上。
“你记住,我要在你身上开上一千个洞,给我查好了。”
抬脚,向前一步。
“第一箭,祭被你挑拨而互相残杀的冒险者。”
他想要举起手施法,那只右手立刻被穿透,灰色的墙和灰色的皮肤都被他蓝色的血浸满。
向前,第二步。
“第二箭,祭被我杀死的精灵少年。”
由于疼痛而蜷曲的左手也被穿透。
继续向前,第三步。
“第三箭,祭被我杀死的布衣少女。”
左脚。
第四步。
“第四箭,祭被我杀死的人类战士。”
右脚。
一步,又一步,一箭,又一箭,箭头穿过皮肤和肌肉的声音不绝于耳,世界都在沉默,宇宙间只有男人的惨叫和我单调的计数。
左小腿,右小腿,左膝,右膝,左大腿,右大腿,左小臂,右小臂,左大臂,右大臂。
他的血管里流的似乎不是血,而是流动的冰。
腹部,胸口,喉咙,头颅。
被钉在墙上的已经不再是人,而是一块覆盖着破布的烂肉,箭用完了,刀尖继续穿过他的身体,雪地被染成了恶心的蓝黑色。
连惨叫也没有了,天地间一片静寂,只有刀刃扎进肉体的声音在继续。
继续,继续,继续。
——这是复仇吗。
——还是后悔呢。
——抑或是愤怒。
——这是——
——本能——
——杀戮的本能。
“够了!”
谁在吵闹。
还没有够。
离一千还很远。
不要阻止我。
让我完成——
“够了!停手吧!”
女孩的声音带着哭腔。
不要阻止我。
不要打扰我。
不要妨碍我。
“停下!艾丽已经在哭了!”
有人踢了我肩膀一脚。
为什么能够踢到我的肩膀?
啊。
原来我跪在地上啊。
刀落在地上,全身都带着那衍冬裔之血的腥味。
为什么会这么累呢。
面前是泰拉·贝尔血肉模糊的尸体,头上是天空和月亮。
血滴在地上,在深蓝色的雪水里激出涟漪。
滴答。
滴答。
滴答。
愤怒消失了,悲哀消失了。
“我”消失了。
少年还在带着悲哀怒吼,我却如同置身世外。
我还是那个半梦妖啊。
如同一场笑话。
笑声从胸口闷闷地传出来,带着血和眼泪。
这个世界还是把我排斥在外。
无论我是不是活过。
|16|雪虐风饕
菲利普尖厉的声音穿过愈渐稀薄的风幕。
它在躁动,空气中有什么气息让敏感的雀鹰感到了不安。
狼崽喉间发出低低的呜咽,祖先遗留在它身上野兽的血液似乎也在告诉它危险的逼近,它正用力拽着它主人的鞋子,似乎想要逃离什么。
“好了好了……”侏儒小小的手抓着我的手臂晃动。
有滚雷似的声音从地底传来,膝盖下的地面似乎有些异样的震颤。
“我们走吧……”他拍着我的肩膀,“去别的地方看看……”
天色好像突然黑下来了。
虽然原本那轮蓝月出现之后天色就没有亮起来过,松林里的长夜似乎一直延续到了无名之城,但多少还有些光亮从风雪之间投下来。
只是连那些可怜的光亮也忽然不见了。
地上的雪被风卷了起来,连着衍冬裔深蓝色的血一起。
诗人喊出了声音。
“那是什么……!”
伴随着巨物撞击地面的声音。
冰冷的碎片在我反应过来之前击中我的背,巨大的冲力带着我向墙上撞去。
胸口被撞在砖石上,一口空气被从肺里挤了出来,胸骨碎裂般地疼痛着。
砰。
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
建筑被击碎了,地砖出现了裂缝,房顶的碎片落在我面前。
——彻底黑掉了啊。
——光也是,雪也是,尸体也是,同伴也是。
——全都不见了。
感觉有些恍惚,像是被封在梦境中那样恍惚。
少年这么想。
黑色的、冰冷的空气在鼻腔和喉咙里,湿润得有些不自然。
像被埋在雪堆里一样。
——不,自己并没有过这种经历。
蓝猛地清醒。
似乎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梦里有泪水有鲜血,有朋友的笑容和同伴的呼唤,有激烈的战斗和呕血的呼唤,有痛彻心扉的失去和熊熊燃烧的愤怒。
可是总归感觉是个梦,梦里没有一点真实感,自己是个旁观者,什么都做不到。
身下是凸凹不平的地面,少年觉得自己好像还留在那个无穷无尽的长梦里,连呼吸都被阻挡在黑暗中,一丝光也没有,一丝风也没有,一点声音也没有。
他试探性地伸出双手,指尖触碰到的是粗糙的墙砖断茬。
看起来是被埋在瓦砾堆里了啊,他自忖。
有一点点的鸟鸣声顺着缝隙漏了进来,非常熟悉,就像熟悉自己的手指。
“菲利普?”他坐起来,却狠狠碰了下头。
“你是说这里面有人啦小鸟?”女孩子的声音隐隐约约地传进来,带着些他所不喜欢的调笑。
又是唧唧喳喳的叫声。
这时候不管外面是谁,出去才是第一要事,少年揉着被磕痛的后脑勺这么想。
“外面有人么!”他扯着嗓子喊起来,这才感觉自己很久没说过话了,喉咙干涩,一口带着腥味的空气呛进气管,少年咳嗽得仿佛要把肺翻出来。
“在这里啊……”金属撞击石头的声音响了起来,女孩似乎在用什么武器刨挖那些瓦砾。
有风溜进来了,冰冷的,带着些奇怪的异味。
然后头顶开了一个口子,少年抬头看到的是漫天的星子和蓝色的月光,少女在边缘向他俯身,月光从她后面照来,蓝看不清她的脸,只有那头雪白的长发一直垂到他面前。
“你没事吧?”她发问,像是另一个男孩曾经攀着绳子向他伸出一只带血的手。
“真是够呛啊……”少年站在已经被方才落下来的巨大冰块砸得摇摇欲坠的城头环视无名之城,“太多了,先在这里休息一下吧。”
城墙上本来也站满了傀儡,只是那些脆弱的东西已经被两人接二连三地打下了城墙,十多米的高度把它们摔得碎成了一地冰碴,拼都拼不起来。
“是够呛呢。”紫色的女孩一手掐腰,黑色的雾气在她身边不停涌动,她正踮脚指着中央广场的那根冰柱,“我的队伍在那里——你看到那道红光了么?那是我们的队长。”
从内心来说,也许是因为他由于一半的卓尔血统而受人排斥,蓝一直不喜欢卓尔精灵,甚至到了厌恶的程度,即使他并没有真正接触过卓尔。而当他没有注意到这个女孩的种族时,他倒是完全不讨厌她——也许和这个叫薇塔塔的卓尔精灵刚刚救了她一命有关。
不过,注意到了以后,他也没有讨厌她。
“看起来很强啊……小心。”一支冰箭朝着女孩射了过来,被少年一刀砍成了两半,化作白色的冰尘。
“我们的队长是个脑回路一根筋的家伙呢……”她挥手,数把红黑色的刀枪随着她的指挥击碎了一个跃上城墙的冰傀儡,看起来那家伙就是方才放冷箭的那个弓兵,只是它的行动早就被女孩用神力捕捉到,它的一举一动薇塔塔都已经了然于胸。
“那是夏德娜赐予我的眼睛。”女孩这么告诉他。
弓兵变成了几块碎块,落下了城墙。
“不过,很强,是真的。”她眯起眼睛,像只晒太阳的奶猫。
——不,也许是只幼狮呢。
“真巧啊,我们的队长也是个一根筋的家伙——只不过很弱就是了。”蓝干笑两声,他忽然觉得瓦尔哈拉的那些脸开始变得不清晰,依瑞斯,伊利亚斯,奥列格,阿伦德尔,叙泽特,瑞贝利安,艾丽西亚,都是些无比熟悉的名字,他却怎么都无法把这些名字与面孔对上号,即使经过那么多的事情,都是同生共死过的友人,他还记得几个人坐在篝火边弹琴唱歌的时候,奥列格让他唱唱父亲教给他的猎歌。
然而那些图像似乎在慢慢地消失,纳斯塔的脸也在模糊,只有父亲的脸和川途的脸还深深刻在他脑海里,像是被烙在木板上的图画。
用火在木板上画画的,是谁来着?
他只记得那双手小而白皙,上面有长久干活勒出的红痕。
“说回来,你的灵魂居然还在啊……我还以为你已经被梦妖吞噬掉了呢。”女孩向着城下俯身,那里不知何时多了无法计数的傀儡,虽然很小,但是已经层层叠叠地攀上了城墙。
“这个我不太清楚……不过看起来是完蛋了呢。”少年蹲在城头,敌军像是海浪,前赴后继地拍在城墙上,他们清楚地感觉到脚下的震动,世界似乎在崩溃。
“早知道就不上城墙了……”女孩撅起嘴,脸鼓成了个小包子,“不过这么小小的傀儡,感觉可以一口吃掉。”
“说不定它会在你肚子里大闹呢?”蓝伸手把一个手掌大小的傀儡推下去,这种大小的东西让他感觉甚至有点可爱,菲利普也在飞来飞去地玩着那些傀儡,似乎还相当的欢快。
“哼……”女孩一脚把一只有二十多厘米的傀儡给踢了下去,“咱们还是快点赶到神柱那里比较好喔,他们似乎很吃力呢。”
“首先咱们要解决这群蚂蚁啊。”少年掏出了个火折子,这东西还是奥列格给他的。
橙色的火很快就烧起来了,森林被引燃了,城墙被大火熏黑,傀儡在火焰中发出嚎叫。它们融化,蒸发,空气里都充满了它们的尖叫,萨玛斐好像在通过它们发泄什么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