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诺布觉得自己躺在一片冰凉而极度平整的地面上。虽然不清楚自己身处的状况,但她还是没有睁开眼睛。四周还安静的像是死了一样,连一点空气的流动都听不到。
耳机好像不见了。眼镜也戳的自己相当难受。
真是糟糕的状态。
就连衣服也都好像不是自己原来的衣服,但除此以外,或许并没有本质的不同。毕竟身上也本就没有什么有纪念意义的东西,也没有什么需要依靠外物才能再认的回忆。诺布听到了人的存在,于是慢慢的蜷缩起来用手指将一绺男性的声音堵在耳外。
“……■■■?”
好像是有人在呼唤另外一个人。
不过和自己没有关系吧,现在的状态怎么说也只是从一个没有人认识自己的地方来到了另一个没有人认识自己的地方。她慢慢的睁开眼睛,确认自己所有观察的目光都会被眼镜温和的掩饰掉。看起来有人已经早早的恢复过来,正在房间里走动。
或许不能称之为房间,不过是一个更加有意思的牢笼。由于角度的问题,诺布只能看到四面墙壁以及上面的门。看不到光源,看不到换气设施,看不到除了想被看到的东西之外一切的东西。她用指腹擦了擦自己所能触及的一小片牢笼的材料,心知凭自己仅有的眼镜材料没有办法给它造成什么破坏。
监狱是为了监禁而存在,牢笼为了观赏而存在。
蜷在冰凉坚硬的地面上确实很不舒服,在诺布感觉周围声音变多了之后才悄悄的起身,躲在别人视线的背后。她虽然很舍不得双手堵住自己耳朵时候所能听到的令人心安的血流心跳声,但还是放下双手开始倾听别人的交谈。
“……至少我们通过Lai知道了这是什么片子了。……我是Javier Ryan,是个警……”说出这番话的男性不知道为什么停顿了一下变了话锋,“曾经是什么已经无所谓了,唯一肯定的是你我都是一样的,是要在这里存活下去的伙伴……”
伙伴吗?一下子就把所有人都捆在一起。不过这里会眉来眼去的熟人还真是有够多,想到这种事诺布就开始不高兴的用舌尖抵着牙齿,烦躁的在心里咒骂着。如果有一个警察在这里,总觉得事情会变得更糟一点。虽然说危机下的集权或许是最优的选择,但是电影里最让人印象深刻的也就是警察那个角色。
平凡、智慧、天赋、爱心、经验和权利。
最后他死了,还拖累了别人。
理性、要理性。诺布这样说服着自己,没有根据和有偏见的怀疑都是非理性的,非理性就代表着无法取得最优解,不是最优解就代表着失败。她死死的盯着下方的门上似乎有什么意义的符号,避免与任何一个人首先发生目光接触。
《Cube》在三年前看完了三部曲,前几天才又复习了一遍一和二。说到底,诺布不喜欢除了第一部以外的其他作品,相应看的时候也没有太花心思。
后悔了吧混蛋。她这样对自己说。
有人在看你了。她这样回答自己。
在被询问了包括了三围之类算不上太隐私的问题之后,其他人终于停止了所谓的社交意向,只有一个坚持要叫自己为诺诺的女性,依旧在试着表达她毫无根据的善意。
“……我们都经历过一样的事情,会保护你们、等回到主神空间以后你们也会拥有力量——”
对于这个诺布倒是挺担心的,力量意味着权利,意味着话语权和人与人之间的分歧,人与人之间的分歧意味着伤害的风险。况且能够就自己的人估计也仅有自己。
“……大家都能活下去。”说完了这样毫无底气的话,对方居然伸出手来表达更加亲密的善意,在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情况下就被捉住了手。
凉、紧张的薄汗、拘束的肌肉线条。明明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下去却试图在给别人带来希望的女性,小心翼翼的说着话的女性,笑容都快要僵硬的女性。
可惜诺布早就忘记了手要怎么和别的有机物接触,只好同样僵硬的勾了勾手指,回应了一个不算善意的紧握。
【请不要再和我说话好吗。】这样的句子,也被她自己困难的嚼碎,还给了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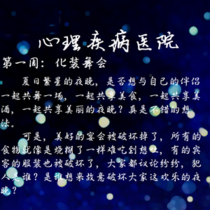
文手也能玩CP球呢=3=
同一CP的图在右边→→→→→
摆在一起秀恩爱【ni
.
CP球
.
“这是什么……球?”
手指的触面是圆滑的,顺着一定的角度向下延去,触感坚硬但并不冰凉,没办法打破——不仅仅是因为对象本身质地坚硬,还因为现下的空间施展不开手脚。
球又向一侧倾斜了。
“唔?Thorn?”贝雷特急忙稳定身形,然而因为他的动作,球似乎滚动得更加厉害了。
……因为球里头有两个人的缘故。
Thorn好像并不安分,两个人并不同步导致了球不断移动。
贝雷特摸索着拉住了Thorn,球咕噜噜地翻滚着,两个人一下子摔到了一起。
“痛……”他一手撑着地面,另外一只手却还拉着Thorn的手,他看不见——Thorn让他不要取下黑布,所以在与Thorn分别前,他一点拿下它的打算都没有。
Thorn回握住了他的手。
——贝雷特。
他在他手心上写下了文字。
——好像仓鼠……
后面的字迹因贝雷特想要起身的动作而变成了一条线,球摇摇晃晃,Thorn拉住他的手,他顺势一拽,两个人一起跌坐在地。
“唔。”贝雷特低吟一声,把Thorn拉过来,牢牢地揽在怀中。
球不再转了。
好像因为两个人都安定了下来,所以球也不再随重心的改变而移动。
贝雷特喘了口气。
这种程度的运动其实还不足以让他的身体有太多的疲惫感,但是Thorn在,他一直紧绷着神经。
好在球只是四下滚动,并没有给他们带来额外的伤害。
“还好吗?”他问怀中的Thorn。
向后靠在他身上的少年似乎笑了,空气的流动仿佛也因此变得令人愉快。
——很有趣。
Thorn在他的掌心里写道。
贝雷特也忍不住勾了勾唇角,拉住了他写字的手。
“我觉得像现在这样……也很好啊。”
近在咫尺的气息与温度。
他看不见,因而这样的感触变得更加清晰。
心跳似乎在不知不觉中加速了,贝雷特轻轻吸了口气,没有惊动怀中的Thorn。
而后者又开始动作了,他撑起身体,这一举动让已经平衡了的球体再度发生变化,摇晃的圆球让重心相当难以维持。
“唔……!”
没有料到这一下的贝雷特措手不及。
然而,趁着重心改变的瞬间。
他悄悄吻了吻Thorn的唇角。
“796,511,258.”
“Clear.”
在得到Raincad确认安全的指示之后,Moriar跟在陆仁后面进入了房间。而前几个确认安全的房间都安稳度过,他虽然不至于认为后面所有质数的房间都会完全安全,也觉得一般在刚开始的时候规律不会有太大变化。只不过房间颜色的变化让人眼花,其他一切都很好。
然后,在这个时点,他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时点。第一个进去领头的陆仁……就在他眼前硬生生大变活人似的……消失了。
他眨了眨眼睛硬是没敢挪动本来径直向前的脚步,在原地愣了两秒钟才反应过来。然后他试探性的动了动脚,小碎步一般继续向前走,直到发现继续向前并不会像先前那样突然消失掉到异次元空间才放下心来。
应该没死。他想了想如是下了结论,在心中把这个突发事件归为主神小婊砸的恶趣味。然后他好笑的发现他现在居然会担心队友的安危,明明才认识没多久。就当做是个好的转变好了,他试图露出一个带有温暖意味的微笑,但是显然失败了。
后进来的人看到这个房间只剩下他一人而没有看到领头的陆仁,表现出的混杂恐惧的惊愕可比他明显也厉害的多。他尝试着给他们解释他也没完全搞明白仍然一团浆糊的莫名事件和自己的猜测,最终还是叹了口气简洁的开口。
“……他消失了。”
为什么会消失?怎样消失?会不会有下一个消失的人?他死了吗?消失之后发生了什么变化?他猜测着面前人会产生的疑问,然后找出仅有一个自己能回答的问题补充。
“没有触发任何陷阱的痕迹,就是直接消失。”
说完这句话他就不再参与队友的讨论,只是兴致缺缺的打了个哈欠。他静静等待着所有人讨论的结果,思绪开始漫无目的的游走。直觉告诉他那个名叫陆仁的年轻佣兵不会死,直觉嘛,这么有小说主角气质的人。他也觉得自己以这个作为评判别人是否死亡的标准有点儿戏,但他就是——确确实实的思考过自己是否正在被人书写。
……Well。
“……619,403,404.”
“Clear.”
……?
高温。
在踏入房间的一瞬他就察觉到了不对劲,空气急剧升高的炙热温度清晰的告诉他只要是个人都撑不下去体内的水分就会被蒸发净尽。失误吗?念头闪过便消失。他向来不在意这些,况且连他的队友现在也无心在意判断者的那点失误。炼金术……氮气……液化……液态氮的温度是……零下一百九十六摄氏度?降温?
他的大脑在一秒间闪过了无数念头,甚至已经超过了他平常最快的思维速度。无数杂乱的思绪间甚至还混杂着“天哪这就是被煮熟的感受吗”这种无聊的想法,所有思绪飘忽而过最后沉淀在底部,大脑中的某个部位在他脑海中具象化的成为一张网精确的筛选出了一个似乎可行的答案。来不及过多思考,他下意识发动了炼金术的血脉能力。空气中的氮气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化为无色无味的透明液体。
……
看来还算有效。
他松了口气,感受到房间的温度正慢慢趋于正常。似乎是因为经历了一次生死关头,他的目光不再漫不经心反而像被挑起兴致似的专注起来。
他感觉到只有他工作时才会有的兴奋和专注的情感如火焰在他胸口跳跃,在发动能力取得效果之后甚至生出了一种掌握一切的感情。他像遇到了什么莫大的挑战似的燃起了与之同等的热情,这种感情如藤蔓蔓延生长满布全身几乎连指尖都快忍不住颤抖。而他的表情却表现出与此完全相反的沉静,甚至弯起眼睛微不可查的微笑。
Time’s up.
他摘下眼镜轻声念,淡绿色眼眸里眸光流转仿若有星辰闪烁。
工作时间到。

Wow.
初醒时大脑一片混沌还没来得及思考现在所处的状况就已经下意识发出了赞叹,Moriar眨了眨眼睛试图让仍然模糊的视线清晰,然后才摸索着戴上眼镜。
他微微扭了扭脖子,略微的不适感让他十分怀疑昨晚是不是落枕了。不过很快他就抛下了想这些杂七杂八东西的闲心——周围歪歪扭扭横七竖八躺了十来个人,除了一同度过上一部恐怖片的几位以外还多出几个陌生面孔。当然令他不由自主发出惊叹的并不是这些,而是这间房间的极其有趣的构造。
前后左右上下各有一扇门,白色墙壁上的独特花纹。两点极富特点的特征足以让他这个死宅,虽然没看过也能判断出,这部恐怖片的名字似乎是叫……Cube。
会移动的立方体。他试图在脑内寻找着有关这部电影的信息,但显然对此印象不深的他只有一个模糊的判断。这么说只要在原地就行了吗?他尝试着找出些蛛丝马迹,但很快否定了这个猜测,因为门上的奇异字符和展现在面前的全息影像清晰的告诉他这只不过是主神这个小婊砸借了个设定。
还真是挥之不去的单机游戏感啊。
他莫名其妙的感慨着,再加上——他先前在主神空间兑换的炼金术师血统,这种感觉就更强烈了。他甚至无法在这些地方感到危机,尽管他知道在这里的死亡并不是儿戏而且确确实实的死去。但是所有超科学的东西都出现了,似乎主神的兑换表里还有类似复活币的玩意儿吧?
那么死亡又算什么?无非是花更多的代价就可以读档的存档而已。好吧,至少很有趣。他耸了耸肩决定不去思考这个哲学范畴的问题。
在他神游思维发散的时候似乎新人都已经完成了自我介绍……噢,还有一位。他感兴趣的探了探脑袋,正好碰上在上一部恐怖片与自己一队的Raincad在问那位……姑娘,三围的问题。
“86,61,93。”
哟,这么直白的姑娘还真少见。他的兴趣愈发浓厚起来,甚至有闲心吹了声口哨跟着这位同甘共苦的兄弟一起调侃。
“冷美人,女……”
他想起上部恐怖片某位姑娘的英勇表现,目光瞥了一眼旁边的司柠茶,音量明显小了不少。
“……不会又是个女汉子?”
但是三无少女正戳他的萌点啊——凌波丽还是他学生时代的女神。他挑了挑眉,似乎在纠结于继续搭讪与否。不过名为诺布的少女显然没有顾及他感情也没有任何要搭理他的意思,只是自顾自的低头自语。
接下来的时间他除了在考虑用“嘿,姑娘”搭讪是不是会让人觉得轻浮,就是在思考怎样在适当的时候表现一把自己的男友力。当然也不全然是这些——还有今天晚饭吃什么。
他漫不经心的接过Ryan扔过来的枪械,用新兑换的能力一一将枪支转换成小刀,以及应那位名字毫无存在感的东方雇佣兵的人的要求练成了一把小太刀。当然没人会注意到他其中玩了个恶趣味的小游戏,把那把太刀转化成了栗山未来那把刀的样式再转为正常。
他将练成的小刀按顺序抛给自己的队友,然后注意到陆仁和Ryan一起对立方体的攻击显然没有什么效果。这才是RPG游戏的尿性。他眯起眼睛露出一个仿佛被挑起了兴致的笑容,如果需要找钥匙的地方全都能暴力破解还打什么游戏啊。
他听着少女声音清冷简洁明了的介绍,思考着脱出的方法。三无少女智商高这是动漫的普遍定律,或者也可以说是他看人的直觉,总之不出所料,在Ryan询问过诺布全息影像上的内容时,几乎只有几秒的停顿。
“Work them out, you will get 200, bitches.”
“那这个呢?”
……再次稍稍停顿。
“FIRE.”
那位东方人雇佣兵在这句话之后像是听到什么指引般只丢下一句“我去看看”就径直向上爬,而这之后的反应让他莫名生出了几分惺惺相惜的意味来。
火焰啊……他叹息。然后想到什么似的自嘲一笑意外的陷入沉默。
他的指尖习惯性摩擦着刀柄,金属的冰冷质感让他感到安心和归属。他觉得这同样也是他这辈子都逃不过的梦魇,他们这行的人总有什么难以愈合的伤疤会在心里留下阴影。他的显然与火焰不同。他从不畏惧孤单一人在黑暗的长廊里行走,也不惧怕冷漠的看着队友死去后愤怒的眼神和恶毒的诅咒。他大半生的精力都放在枪械上,并不怎么会与人打交道,所以对于这些小插曲向来不为所动。团队只是他活下来的工具,况且遇到状况时他们的任务就是保护像他这样的技术人员。
他半点愧疚都没有,这就是在那个世界活下去的准则,只是会感到无趣……以及孤独。情感毕竟是件奢侈的东西,不过在这个有违常理的世界他认为可以奢侈一把。
只要有枪。他在心里自语着,反反复复的念。
只要有枪,他就能无所畏惧。他与这种杀人器械几乎已经血脉相连无法分割,握住枪就像是握住了身体的一部分。在刀柄反复不停的摩擦已经使那片金属变得炙热无比,他的动作微微停顿,转而将小刀放在指尖把玩。
他开始期待能否在这个队伍里找到所谓伙伴。





——然後,世界就變白了。
她睜開眼睛,視野里是一片白色。
眨了兩次眼后,從籠罩著一層薄薄水霧的朦朧逐漸轉成清晰,她轉動眼球,才看清那片白色的全貌。
方形的天花板。門和梯子。意味不明的字符。
她疑惑地閉了一下眼再睜開,所看見的場景在記憶中找不出相符,於是她準備坐起、詳細去看一下所身處的狀況時突然感受到某種異樣。
在前幾日已經熟悉到幾乎感受不到的某種重量不知何時消失了,兩手空落落的。
她愕然,跟著將視線轉過去。
武器、首飾甚至是衣物全都消失了。在那裡只有全無設計感的灰色衣袖褲筒、以及同樣毫無品味可言的靴子,——就連眼鏡也不知所蹤。她慌亂地摸著自己全身上下所能觸及的口袋或是任何能藏東西的縫隙,沒有、沒有……
哈維爾送的「護身符」,不在。
從臂鎧消失起就盤踞的不安驀然炸開,她四處環視著方形房間,見到自己的同伴正一個接一個從地上爬起來,身上是與她同樣不知被什麼人更換的同款衣物。紛紛檢視著自己周身的人開始露出或不解或煩躁的表情,她看見房間的一角有另外幾張陌生面孔,正緩慢地爬起來并環顧四周。
在一片沉悶接近死寂的空氣中,有人開口。
「有人知道這是什麼片子嗎?」
向她伸出手的青年如此問其他人,溫暖有點粗糙的手掌接觸到她的一瞬間,讓她感覺有某種像是心裡懸吊著的驚惶瞬間沉澱下來的感覺。她扶著對方的手臂站起,悄悄鬆了一口氣。
沒事,她不是一個人,沒有被丟下。
於是她朝男性扯出了一如既往、毫無陰霾的微笑。
「……啊,你……」
在同伴的青年朝著尚不明情況的四名新人講解時,她原本是因不擅長在有陌生人的場合過多表現而沉默著,直到有個模糊的輪廓出現在腦海里;她遲疑地向著新人中的一人搭腔,「……是阿逸嗎?」
她的回憶里有個身影,高高瘦瘦,總掛著有些輕佻的笑,言語間親暱而不失分寸。
「誒?你是那個……」對方似乎有些困擾地撓了撓眼角,「啊啊抱歉,記性不太好……我是羅逸沒錯,好久不見啊。」
他盯著她像是要確定什麼般瞇起眼睛,片刻笑起來:「——檸茶。」
「怎麼,認識的人嗎?」哈維爾看向她,而她肯定地頜首:「大學的同學,叫羅逸……以前一起上過選修課。」她努力挖掘出記憶裡模糊的影子,一一同眼前的人對應上,「人挺不錯的,對了,他是學醫的。」
她尋求確認地看向對方,白髮扎著馬尾的青年也笑著握起她的手:「對哦,我跟檸茶當時可是搶座位的好搭檔,沒想到會在這種地方見到……」
兩人擊了個拳,順勢交換了幾句寒暄,像是凝結的氣氛被稍微融化般,零零落落地另幾個人接上聲音。
有強健身材和深色肌膚的罪樹是搏擊教練,俄羅斯裔的狙擊手Sparrow就像她與羅逸一樣同陸仁是舊識,最後一人是個相貌中性的女生,待人態度異樣冷淡、卻意外地似乎是他們突破僵局的關鍵,三言兩語便道出他們所處房間的通關密碼。
名為諾布的女孩解開謎題。Moriar製造武器。哈維爾與陸仁一人執掌全局一人身先探路。
她看著,然後什麼都做不到。
「Hilda的話,兌換這個如何?低級氣功,一個D級支線加500獎勵點。」那時男人這樣對她說,微笑裡隱約有種寵溺般的意味,讓其他有幾個閒閒看好戲的隊友鼓譟起哄了好一會兒,「各方面的身體素質都能提高,這樣即使是你遇到危險,我也不怕來不及英雄救美。」
但那只能自保。在被剝奪了武器、沒有值得貢獻的智力的此刻,她只能看著、什麼都無法做。
她仍然是無力的。
「諾諾……我可以叫你諾諾嗎?」她面前的女生有平靜近乎死水的深瞳,她站在對面就感覺自己像要被吞噬,脫口的話語連自己都感到無稽與可笑,「我們都經歷過一樣的事,會保護你們、等回到主神空間以後你們也能擁有力量,所以不用擔心,大家都能活下去。」
——她在說謊。
她連自己能做到什麼都一無所知,更不用說偽裝成強大的盾給人依靠。
「哇,檸茶真可靠。」搭在她肩上的羅逸露出毫無心機的笑,令她扯動嘴角的弧度越發僵硬,她大約是想證明自己仍有價值,但實際是此刻她能做的甚至沒有對面的少女多,自己的影像映在諾布毫無動搖的眼里像是某種嘲諷。
她閉了下眼,平復自己的情緒后主動伸手去拉住了對方。沒有被避開讓她鬆了口氣。
Be a good girl.
BE A GOOD GIRL.
DON’T LET THEM KNOW.
「——我們一起加油吧?」
她笑起來,將自己所有的心虛、恐慌和自卑壓下去,繼續扮演她開朗、友善,勇敢並且毫無畏懼的角色。
永遠只有這樣的角色才會被需要。
被世界需要,被他人需要,——被「他」所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