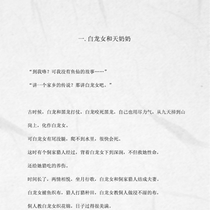【圣诞】圣诞快乐
作者:菲心
评论:随意
纷纷扬扬的雪花随风飘荡,雪白的颜色将眼前的色彩趋于统一。圣诞节的街道显得冷冷清清,一个醉鬼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被大雪埋没的路上,嘴里骂骂咧咧地抱怨着天气,一边裹紧了身上的外套。
“先生,可怜可怜我吧,我已经两天没有吃饭了。”一个瘦弱的身影拦住了醉醺醺的男人,干柴般的胳膊仅仅用单薄的破布裹着,在这种天气里已经冻得发紫。
男人犹豫了一瞬,那被酒精腐蚀了的脑子正努力思考眼前是什么样的情况。一阵冷风刮过,男人打了个哆嗦似乎清醒了一些,“搞什么,今天可是圣诞节啊。”他嘟嘟囔囔地说着,扫了眼蜷缩在角落但固执伸着手的男孩。“喂,小子,凭什么你只是坐在这里伸着手就能得到钱?”他摸了摸自己的左边口袋,那里面装着一些钱币,他的脸上换上一副厌恶的表情,“小寄生虫,像你这样的人怎么能出现在过渡区,该不会是偷偷从乱域跑出来的吧,啧,警察呢,谁知道你们身上有没有什么传染病。”
男人居高临下地看着男孩,为生计而不得不低声下气的模样消失不见,他拙劣地模仿着那些他羡慕嫉妒的人,把受过的气都放在了眼前这个瑟缩着的男孩身上。
可男孩只是抬着头,麻木空洞地重复着这么几句话,“给一点吧先生,求您了先生……”男人的趾高气扬没有得到丝毫的反应,像是一拳打进了棉花里,他反而泄了气,“该不会是冻傻了吧?”他上下打量了男孩,看到他穿着仅能蔽体的单衣,不知从哪里捡来的破纸壳围在他身边权当遮风的围墙。雪还在纷纷扬扬的下着,男孩身边积攒了不少雪,将他的身体冻成紫红色。迟来的良心让男人把手伸进了口袋里,两枚带着脏污,似乎被传递了许久的铜币被扔到男孩面前。
“便宜你小子了!”男人狠狠瞪了他一眼,怕自己后悔般匆匆离去。“谢谢您……圣诞快乐。”男孩嘶哑的声音让男人脚下一顿,片刻,一声不太清晰的如同轻哼一般的祝福传来,“……圣诞快乐。”紧接着男人又恶狠狠咒骂起天气,重新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雪地上,只是背影看起来似乎轻松了一下。
……
白默辰收回了通识水晶,下意识地摸了摸手腕上的手表,等在他旁边的陆铭珵迎了上来,“怎么样辰哥,找好目标了吗?”白默辰没说话,只是看着窗外纷飞的大雪,良久,他答非所问地回答,“今天是圣诞节,珵子。”“嗯?”陆铭珵被这一句弄得摸不着头脑,“呃,圣诞快乐?”
他这一句倒是把白默辰逗笑了,“圣诞快乐。”他站起身,在从衣兜里掏出的烟盒中抽了一支烟点上,淡淡的烟雾将他的脸遮住,“去找玖爷要人,珵子。”
陆铭珵心下一惊,“可是你之前不是说……”白默辰摆摆手止住了他没说完的话,“替我跟他道一声圣诞快乐,以后的事情都要麻烦他了。”陆铭珵沉默一瞬,“那个合同明明对你很不公平,辰哥,实在不行我去乱域找人,那里就算有人失踪也很正常,大不了我就……”“珵子。”白默辰第二次打断他的话,“我们不能轻易判断一个人的价值,就算他穷极恶煞,但也许他还有父母还有孩子,我们选择了他,那么之后呢?”他转过身看向陆铭珵的眼睛,“谁能保证他的孩子会不会被人抚养长大,谁来照顾他年迈的父母?”“抱歉,辰哥……”陆铭珵低着头一副认错的样子。白默辰深深吸了一口烟,看起来很是疲惫,“去吧,早点回来,我等你吃晚饭。”陆铭珵应了一声离开了。
白默辰透过窗户看向光域的方向,即便下着大雪,但透过雪色仍旧能看到光域闪烁着的霓虹光,那边正在为了圣诞节而举办着各色的活动和酒会。他脑海里闪过刚刚通过水晶看到的那一幕,一声叹息在安静的房间里格外明显。
“圣诞?”他嘲弄一笑,“不过跳梁小丑自以为是的献媚罢了,又有什么意义呢……”他摆弄着手表的黑色表盘,“倘若祂们真的在意,又怎会让这里落得如此境地?”纯黑的表盘反射不出一丝光线,那黑色似乎将所有照过来的光全部吸收,就像他的眼睛一般,黑得映照不出任何人的身影。
“在被神遗弃的地方,又怎么说‘快乐’呢?”

作者:苑竹
免责声明:笑语
由于作者有独立世界观和故事,此类作品仅作为单篇作品存在,本篇与后续其他作品无关。(连载故事会单独发在作者主页,客官不如赏光一看)
作品中任何人名、地点、三观等皆为虚构,仅为故事本身服务,请勿对号入座,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本篇打磨不够,观看建议:不要带脑子,当乐子看。
——————
明亮而嘈杂的食堂里,夏溦霖将最后一口饭送入口中,接着将盘子碗筷收好,送到回收处:她一秒都不想多待。
颧骨因咀嚼的动作隐隐作痛,那里青紫一块,是实战课对方“不小心”留下的伤。
——如果不是她躲得好,那这里就不是青紫了,她还得在医务室的床榻上吃午饭。
夏溦霖抬手,手机连震两次,母亲的生活费到账了,屏幕上清一色都是转账记录。
她点击收取,然后回复一个卡通狼的头像:
[教官让我上完今天,大概下午五点结束。]
对面的回复有些慢,但她并不急躁,一种紧绷的无所谓滞留在胸口,像是冰水般镇静着她的情绪。
[好,我会在门口等你们。]
[明白。]
————
教室很近,她走进去时目光刺人起来,夏溦霖面无表情的走到位置上,将布置在桌脚的水弹陷阱拆掉,扫视了一遍确定没有不该有的东西后,坐下,打开手机戴上耳机,开始看小说。
窃窃私语都被隔在耳机外,目光仍然刺人,而夏溦霖已经习惯了无视这些异样的现象。
在第一天转入这所学校时,她就受到了别出心裁的“欢迎”。
————
作为一个出身“贫寒”的“觉醒者”,却被分配到了高等班进行课程,教官还是那个以无情闻名的“奥古斯都小姐”。这招来的流言蜚语就像苍蝇一样四处乱飞,她既没办法,也不想理。
夏溦霖心态很好,她对自己没有疑问,还擅长从周围人身上吸取好的习性,比如:来自母亲的一点就是:自省,但不质疑自己。
所以当她用优秀的成绩和绝佳的射击天赋证明自己时,那些苍蝇曾一度销声匿迹。
可惜这短暂的“寒冬”没有持续多久,展现天赋后迎来的就是各种麻烦,她不知道拒绝了多少个“墨镜先生”,也避开了众多个“打扰一下”。紧接着,“谣言”成为了苍蝇们的食物,而更近一步的谣传让她迅速卷入这个凭空出现的旋涡。
“平民”怎么可能根据自我判断拒绝那些招揽?
夏溦霖在几天内成为了众矢之的,各种流言不断,甚至影响到了正常的训练,比如各种介于严重和轻微的伤口,一句轻飘飘的“不小心”就能盖过去。
至于发酵的这么快,怕是要追寻到母亲的前一个孩子,同时也是他哥哥夏遥旭的三年失踪案之前。不夸张得说,她在这里的每一份阻力,都和母亲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还是消极意义上。
奥古斯都教官不傻不瞎,也不和稀泥,专门在班会上澄清了数次无果后,这位“无情”的教官为她申请了长期任务,让她提前考取“探索者证件”并开始实战任务,期末测试前回归。
实际意思就是让她先从风口浪尖上消失一下,也算是让她摆脱那些已经不会有提升的课程。
奥古斯都教官在通知她前就与她谈过话:
“你是否想得到一个能够教导并保护你的队伍?如果他们在探索者协会有注册身份,你可以直接告诉我,可以让你免去匹配或者随机队伍的麻烦。”
夏溦霖当然知道,她哥哥与母亲断绝关系后自立门户,在探索者协会有注册名“夏尔”,而奥古斯都教官对此知情,她当天就和哥哥谈好了事,第二天用了一个上午确定完了手续。
今天就是最后一天,等到下午五点,她就该跟着那位漂亮的白发小姐一起接取任务,出发封锁区了。花费不到一周,这其中也有奥古斯都教官的帮助。
夏溦霖很高兴,特意感谢了奥古斯都教官,然后兴冲冲的同那位白发小姐发了消息。
她的目标很明确——掌握力量,然后离开这里,为此不择手段。
这所学校是扇门,只够她踏上这条路,她的哥哥将这个机会给了她,而夏溦霖近乎偏执地学习训练着。
这一切动力都来自她人生中那长久不息的愤怒。
东区对异能者的偏见像浮在海面下的冰山,看着只有一点大,实际上处处刺人。似乎拥有异能就不是人类了,哥哥就曾因为这种偏见一度找不到工作,同时也被四处排斥,邻居都不愿照应他们。
她小时候不理解,现在理解但仍然愤怒。因异能觉醒或失控造成的事故只多不少,人类趋利避害,减少接触、进行管控都是正常的防护措施,但在之后愈演愈烈,逐渐变成了“偏见”,东区尤其严重。
还好,那时他们都已明事理,能自己做点家务,独自在家也没问题。
东区治安虽好,却也只是不错的程度,在安保措施尚不完善时更常有入室盗窃、抢劫等案子发生,而一个经常只有一个七八岁小姑娘在的家庭,很容易成为那些人的目标。
她依稀记得,某天家中进了贼,在刀子的威胁下年幼的自己甚至不敢说话,只能看着天色一点点暗下去,一边看着蒙住脸的男人翻箱倒柜,一边蜷缩着祈祷着哥哥不要那么快回来。
她似乎被打了,脸上很痛,现在却已经不太记得,然而记忆中强烈的情绪不会轻易消退,她能够清晰的回忆起那时的些许片段:
哥哥比平时晚了几分钟回来,因为要照看她,他总是第一个走出校门,也总是喘着气到家,夏溦霖总会为他冷一杯水,在休息几分钟后,他就会带着她准备晚饭。
在恐慌中,夏溦霖的思绪茫然飘飞着:前些天,家里的剔骨刀似乎拿出去叫人磨了一下,今天早上父母出门前还交代哥哥要记得拿……
钥匙打开门锁的时候,一大一小都抖了个激灵,夏溦霖缩在角落里,视角刚好能看到缓缓打开的门缝中,那张年幼而清秀的脸上平静到诡异的表情,和反射着楼道灯的尖刀。
她的哥哥是冷淡的,很少出现情绪表现,甚至被指责有精神病,哪怕被孤立、被排斥,他也从没显露出丝毫愤怒;他也是懒惰的,似乎只有睡觉能让他开心近乎没有的些许,父母常常催促他吃饭,让他别总是睡觉,而他也从不听这些话,只是沉默的做自己的事。
这就是她对这个陌生亲人的印象,也是从那天晚上起,这个亲人不再陌生。
他们这一家人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哥哥是捡来的,自己是领养的,后来她再想起这些事情的时候就不再是恼怒、羞耻,而是哭笑不得和大方承认。
————
之后发生了什么?
顺着小说主角的经历,她忽然回忆起了很久以前的事,就在她要继续回忆时,一个声音打断了她。
“夏溦霖小姐,”满怀讥讽的声音阴阳怪气的喊着她的名字,夏溦霖在心中慢慢地叹了口气,有些不悦地抬眼看向面前这个长着小眼睛的男性。
似乎是叫徐书行?
他后边还站着两个人,带着肉眼可见的嘲讽笑容。
怎么说呢,怪扭曲的,五官,就像走投无路一样。
“和人说话要放下手机!”他就像小孩似的,一把抢走了夏溦霖的手机,夏溦霖摘下耳机,用看傻子的眼神看他。
作为插班生,夏溦霖是这里年纪最大的,大多数人才15岁,没一个到了法定年龄,确实都是小孩。
徐书行仗着富家子弟的身份,常常骚扰女生,大多数女生选择虚与委蛇,他便涨了气焰,直到某天被夏溦霖冷声呛了回去。
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一帆风顺的人生路上会有绊脚石,接着对她展开了各种针对,而大部分操作因为干扰教学而被奥古斯都教官搅黄。
“你这脸是怎么了?不会是被打了吧?哎,这叫不叫报应啊?”徐书行说着在她看来幼稚的要死的话,就算把徐书行换成一个十岁的小孩也不会有任何违和感。
夏溦霖懒得和他怼,她早就过了不服气的年纪,只是伸出手,平静道:“还我。”
“你没手吗?还是手上也被打了?”徐书行嘲讽她,脸上的表情像极了炫耀羽毛的杂毛鸟。
没等她再说话,另一个清亮的声音就插了进来:“还她你听不见吗?”
仇寒晗冷着脸抢走了手机,这个一米六出头的女孩是她的好同学,家境堪堪算上流人,但因为“油盐不进”而被上流社会排斥。到现在仇家仍然支持“以行动和功勋装饰自己”的祖训,在坐吃山空和资本家里格外亲近军方和科院。
徐书行被惹怒了,从小肆无忌惮的他能够服从校规已经是极大的“委屈”,作为一个家财万贯的少爷,居然还有不长眼的女人敢反抗自己?
“一个没爹的小姐和一个没爹没妈的平民真是好搭配啊?”
“你说的对,有爹妈的小孩成绩不如没爹妈的。”仇寒晗上下打量他,眼神里极尽嘲讽和鄙夷。
“你!”
眼看就要朝着无意义的骂战发展,夏溦霖翻了个白眼,拍拍仇寒晗的肩膀安抚道:“别和他争。”
仇寒晗撇撇嘴,既没说话也没走,好像在上课前就打算赖在这了。
夏溦霖拿回了手机,也被打断了回忆,眼看距离上课就剩几分钟,干脆将耳机摘了,打算和仇寒晗闲聊那么会儿。
可惜话题还没开启,徐书行就又开口了,活像个不甘被无视的小丑,说出来的话却让夏溦霖瞳孔一缩:
“这个人的哥哥,是个杀人犯呢。”
混乱嘈杂的交谈在一秒寂静后立刻充斥了教室,夏溦霖冷冷瞥着他,收紧了手指,某种危险的情感在她心口升腾,催促般挑动着她的神经。烦躁、愤怒、气闷、无奈……可她不能做出任何回应,因为即使否定,也会被扭曲变成承认事实,而她表现出的情绪更是有着宽阔的解读范围。
况且,这是真的,这句话本身就是真的,徐书行只是隐瞒了其他条件而已。
断章取义是造谣最基础的操作。
“杀人犯的妹妹也能来这里,真像森林里掉进陷阱的野兽一样可笑。”
夏溦霖看都不看他一眼,只是拿起手机打开页面,继续看她的小说,还拍了拍仇寒晗搭在她肩上的手,让她别生气。
徐书行来找茬的目的达成了,又补了几句不疼不痒的嘲讽,见夏溦霖没反应,便撑着面子放了狠话走了。
仇寒晗对着这人的背影翻了个白眼,良好的教养让她没能骂出几句脏话来,只是担心道:“谣言又要有变化了。”
夏溦霖嗯了一声,平静道:“它变得还少吗?差不多了,快回去吧,上课了。”
仇寒晗拍了拍她的背,意思是:别放心上。
屏幕被她摁灭,映出她冷淡的脸,青紫消下去一些,异能者的恢复能力比普通人好一些,这点伤并不严重。
连血都没出。
————
奥古斯都教官没有走进教师,班长收到消息,提前两分钟带领班级去了训练场——看来是换了课,今天下午原本是理论学习。
刚进入训练场,夏溦霖就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白发披散,一身简装的白秋夜,仍然是清凉的风格,与他们第一次见面一样。
她诧异到顿住脚步,后方的同学不满的咂嘴,绕过她走到前面去。白秋夜显然也注意到了她,视线在她的脸上逗留了几秒,接着平淡地点了点头。
有男生和女生的嘀咕和尖叫响起,也难怪他们这个反应,白秋夜美貌惊人、身材又好,恰到好处的肌肉毫不吝啬地暴露在天光下,哪怕只是短袖短裤都是极其养眼的。
夏溦霖呼出一口气,仿佛受到了鼓励,打起精神加快步子走到了最前面。
一旦进入奥古斯都教官的视线范围,不管是尖叫还是讨论都会自动消失,班级的所有人快速排好队,在报数和报告后,好奇的打量着这位从没见过的美丽女性。
“现在开始上课。”奥古斯都简单说明了换课相关,接着对全班介绍道:“这位是前来参观的探索者协会一级成员白月小姐。”
“各位好。”白秋夜还是那副冷淡模样,只是象征性点了点头,打了个招呼,毕竟这里的所有人加起来都不够资格让她低头超过30度。
夏溦霖想到了她们聊天时对方说的“顺便”,原来是这个意思。
奥古斯都没有预留时间给她说些什么,白秋夜同样不是能言会道的人,无论那些目光是好奇、惊叹、仰慕、憧憬还是思索,课程就在这短暂的插曲后开始了。
异能者无论什么能力,在这所学院都有几门战斗必修课,比方说体术。
不同的教官会有不同的倾向性,奥古斯都最为看重的就是实战,因此她的班常常带伤出席,由此也被冠上了“恶魔”的中性前缀。
在热身、攻守互博结束后,就是“单独指导”,或者叫做打擂台更合适些。
在不使用异能的情况下,对人战往往快速而短暂,几个来回便会被叫停,接着就是奥古斯都的动作剖析和纠正指导,夏溦霖总是最后一个,也总是仇寒晗和她对打。原因有二:一是她遭受的孤立。二则是这个班上的大多数人并不那么拼命练习学习到的技巧,逐渐被她甩在身后的早就不止一半了。
白秋夜双臂环胸,看似认真的斜靠在墙边,可若有人敢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她眉眼微垂,视线也没有明确的焦点,分明是在无聊。
夏溦霖偷偷瞄过她几次,终于确定这位姐是真的无聊,大概在她看来,这写课程只是玩闹吧。
相比与晶兽战斗、执行区域扫荡、探索未知封锁区,这些东西拿来参观还是过于幼稚了。
————
这位教官小姐在不久前宣布休息十分钟时,短暂与白秋夜交谈过一次,寥寥数句便没了下文,接着就有好奇的学生大着胆子上前攀谈,仇寒晗靠的近,听见那白发小姐都是以礼貌疏远的态度回应问题,旁边还有奥古斯都看着,学生们都不敢太放肆。
“徐书行想犯贱,被呛死回去了。”仇寒晗说,压低了声音忍着笑,复述起对话:
‘您这么漂亮,追求您的男性恐怕要排出这所学校了。’
‘我为什么要找一个累赘当伴侣?’
‘呃……但毕竟可以互相关照,毕竟封锁区的探索很危险。’
‘的确,所以更不能找个累赘拖后腿了。’
“哈哈!你不知道那个二货的表情!他怎么觉得那姐姐会关心这个事的啊!
“我觉得她说得对,城区里大部分人到了外面还不如提早干掉。”
她的好友甚至忽视教养说了个现在看来有点可爱的脏词,好似被感染了似的,夏溦霖想象了一下徐书行的表情,估计和吃了苍蝇一样难看,于是也忍不住笑了出来:“他一向那么自信,他才十五。”
两个女孩抱着膝盖,一直压着声音笑,仇寒晗甚至笑到肚子疼才靠着夏溦霖停下来呼气。
仇寒晗早看徐书行和那些谣言不顺眼,这下算是把一肚子气都笑了出来,夏溦霖也难得笑的这么高兴,她对这个学校的留恋和不舍几乎全系在仇寒晗身上,这个比她小两岁的女孩拥有与她不同的理想,在三观和道德上却与她一样坚定不移,与仇寒晗相处的时光总是放松又温暖的,她很感谢仇寒晗。
随着太阳不知不觉间移动,从窗口洒进的,白亮的阳光也变得澄黄柔和起来。
“夏溦霖!”奥古斯都喊道,夏溦霖站起来,自觉走到空地上。
按照平常的流程,夏溦霖的对手应该是仇寒晗,但显然,奥古斯都教官有些新的想法:“白月小姐,您愿意指导一下我的优秀学生吗?”
优秀学生。
夏溦霖微微睁大了眼睛,看着奥古斯都教官的侧脸,好似与平时并无不同,又好似柔和了许多,就连她锋利的眉眼都添上了一些感性。
空地边缘,仇寒晗已经找好最好的位子,听到这话更是鸟儿般转过头来,带着雀跃和兴奋看着自己的好友。
而其他目光则聚焦在白秋夜身上,相比起教官语言里直白的认同,他们更高兴能够看到一位协会认证的、真正活跃在封锁区的一级异能者出手,哪怕只是一些体术。
她放下手臂,打量着她,略做思考后点点头:“当然。”
“感谢您。”奥古斯都说道。
白秋夜只是摇了摇头,道:“小事而已。”
围成一圈的学生们自觉让开一条通道,白秋夜向他们点头致谢,随后走向空地中的夏溦霖。
奥古斯都指挥学生们拉开距离,并站在内圈准备宣布开始。
夏溦霖已经摆好了架势,而白秋夜只是直直站着,金色的眸子看着她,在这一刻,夏溦霖感受到了自己呼吸的颤抖。
“开始!”
夏溦霖毫无顾忌。
她的出手迅猛与否在巨大的实力差距面前毫无意义,何时出手也不存在优势,在这个前提下,她更应该尽最大努力,将自己的一切都展示给对方,并在败北后细细复盘,吸收技巧。
一拳一掌,夏溦霖在脑中判断着时机与方向,七次进攻,次次不离面门与下盘,可白秋夜就像幽灵一般,无论她如何努力都没办法触及对方一下,她甚至不需要格挡。
而在逼近与后退间,她似乎看到白秋夜永远冷淡的底色上,出现了一抹转瞬而逝的微笑。
白秋夜忽然放弃了一个后撤步。
而夏溦霖没有任何不进攻的选择,她屏气握拳,凝聚起自己最大的努力将这一拳挥出——
白秋夜接住了这一拳。
轻松、游刃有余、意料之中。
夏溦霖抬头,细密的汗滴从额头渗出,在人造光源下反射光芒:她没看到笑容,白秋夜的表情似乎自始至终都没有变化过。她慢慢站直身体,慢慢平复呼吸,又慢慢向人群走去,步子有些虚浮。
没有任何意外,没有任何惊呼,也没有任何掌声,所有人都理所当然的看着这一幕,接着理所当然的等待教官宣布结果。
“白月小姐胜。”
此时,掌声才哗然响起。
紧接着,掌声又迅速消失,逐渐只剩下两个掌声仍在响起。
夏溦霖本以为是自己的好友,她的倔强从不输自己分毫,而在听到另一个掌声时,她诧异的回过头去:白秋夜确实笑了,不是她的错觉。
“努力与勇气应当给予鼓励和嘉奖,你……你们都很好,真好。”白秋夜的金眸注视着她,夏溦霖愣在了原地,卡壳的大脑缓缓转动,她觉得这个“你们”或许说的不是她的班级,也不是她和她的好友,而是……她和哥哥夏遥旭。
“喂!别愣了!”仇寒晗压着声音喊,但没什么意义,现在很安静,她用气音说话所有人也能听到,但她不在乎,甚至用双手做喇叭状,生怕夏溦霖听不到。
“啊?哦!谢谢您的肯定!我会继续努力的!”夏溦霖回过神来,脑子里什么都没想到,全靠灵魂说话。
好在奥古斯都解救了她:“归列。”
“是!”
仇寒晗似乎在她旁边兴奋的说了什么,但夏溦霖已经没在听了,她意识到自己宕机了,却不想从这种状态里脱离出来,她有多久没这么脑袋空空了呢?
夏溦霖开始回忆,她发现自己并不了解白秋夜,但这位漂亮姐姐就是让她直觉亲近,这让曾经嘲笑过夏遥旭的“盲目”的她感到脸上有些疼痛。
真神奇……夏溦霖忽然理解哥哥为什么那么信任白秋夜姐姐了。
————
仇寒晗帮着她清点行李,足足两个行李箱,夏溦霖无奈拜托她陪自己前去校门,顺便帮着推一个行李箱。
两人都对路上的目光视若无睹,她们聊着自己的事情,有关生活,有关未来,有关嘱咐……仇寒晗了解她,知道她能照顾好自己,但还是以防万一,确认了一遍联系方式,毕竟仇家的私人号码与公开号码是不一样的接通渠道。
来到校门口时,一辆车对他摁响了喇叭,夏遥旭在驾驶位对她招手。
“哥。”夏溦霖看到后座白秋夜也在,也喊了一声:“秋夜姐。”
两人朝她点头,夏溦霖便介绍起自己的好友仇寒晗,仇寒晗充分展示了作为大小姐应有的礼仪和作为夏溦霖好友略有跳脱的一面,四个人聊过几句便各自离开。
路上,夏遥旭斟酌着开口:“感觉怎么样?没有后悔吧?”
只见夏溦霖一伸手臂,用力深呼吸几次,身边终于没有注目礼,耳边也没有窃窃私语——真清静啊!
她放下手,扭头望向心情愉快的哥哥,露出一个带着兴奋和解脱的笑容:
“轻松多啦!”
作者:格子
评论:笑语
【记者】
你杀了人。
清澈的童谣声在你的耳边回荡,你看着自己手心的血,精神有点恍惚。
你杀了人。
“一根棍子轻轻打,二双筷子里外扒,三人小组爱说话,四个小兵不害怕, 五个朋友力气大……”
是家乡孩子们常常唱的童谣,但你已经来不及分辨其中的意思,满心只有不能被小孩子们看到尸体。
你慌不择路地拖着尸体塞进车的后备箱里。死者你认识,是常常来杂志社闹事的家伙,之前不依不饶说你报道失实,让老板扣了你一笔工资。但你想不起来自己为什么又会跟这家伙对上了,上次的记忆还停留在中午有些心情郁结,多喝了两杯。
现在想起来,隔壁桌确实有个人看着很像这家伙。
不过现在不是想这个的时候,你抹了把脸,看了看手表,19:10,你计上心来,朝着郊外一处荒废的野地开去。
没一会儿你就到了,把尸体丢进猎人废弃的陷阱坑里,没提防自己也跟着滚了进去。
头好痛。大概是宿醉吧。
你站在埋好的土堆边,按下通讯珠给欠你钱的同事发了个消息,让他代替你去参加今天假面舞会的采访,并要求他保密,不然就揭发他购买违禁品的事情,他连连称是,让你放心。
之后一切风平浪静,那个地方偏僻得很,你打赌他们连尸体都找不到。
你还是那个著名的记者,报道着花边新闻和名人八卦,听说劳班阁下是个萝莉控,对娜娜莫殿下有不一般的心思,艾默里克阁下似乎有见不得人的喜好,与埃斯蒂尼安同吃同住。哗众取宠的标题给你带来大把的收入,也让你淡忘了醉酒后不明不白的那件破事。
艾欧泽亚每天死那么多人,有谁会在意少了个闹事的家伙呢。
直到有一天,你隐约听到通讯珠响了响,没等你接起来,一个低沉的声音就从里面传来:“我知道你做了什么,但我不关心,晚上8点到神意白银乡来,帮我破了这个案子你就继续做你的著名记者。否则就等着身败名裂吧。”
你惊慌失措,分明,分明不应该有人知道的。你又觉得那天给坑里填土的时候似乎确实感受到过一阵诡异的视线,但你记不清了。
无论如何,你要藏住这件事,就要帮那个神秘人破案。你心想,“凭我这么多年的经验,一桩小案子还不是易如反掌。”
你如约到场,门口带着面具的仆人递给你一个滑稽的头套,你撇了撇嘴,不暴露身份倒是正合你意。
“各位,你们都是我找到的聪明人,这桩案子非你们不可。如果能破案,每个人都有重金酬谢,如果不能……想必各位心中很清楚结局如何了……”
包裹在一团黑衣服中的主持人顶着滑稽的鲶鱼头,说出的话却让你心底发冷。
你定了定心神,开始听案件的全貌……
【跑腿】
你杀了人。
清澈的童谣声在你的耳边回荡,你看着自己手心的血,精神有点恍惚。
你杀了人。
“一根棍子轻轻打,二双筷子里外扒,三人小组爱说话,四个小兵不害怕, 五个朋友力气大……”
是小时候常常听到的童谣,配合着野外森冷的气氛,显得格外的诡异。怎么会这样,你只是想做做兼职跑腿啊。你懊恼地想着。
昨天因为送错了东西被罚了奖金心情不好多喝了两杯,结果醒来的时候就已经跟没呼吸的尸体躺在一起了。这个尸体好死不死还就是你送错东西的对象,仔细想起来,昨天喝酒的时候似乎隔壁桌确实有个人看着很像这个家伙,但你只是个跑腿啊,你就算跟人起冲突,也不可能……
你懊恼地挠了挠头。索性这个坑足够大足够深,你抄起旁边的树枝和铲子手脚并用把土往坑里堆,把自己累个够呛,才终于把土堆填平了。
你力竭瘫坐在地上,对着土堆发呆。
事情怎么会这样呢?你不过是……
还好,除此之外一切都很顺利。甚至没有人来问过你这件事,也是,艾欧泽亚每天死那么多人,有谁会在意少了个不起眼的家伙呢。
直到有一天,你隐约听到通讯珠响了响,没等你接起来,一个低沉的声音就从里面传来:“我知道你做了什么,但我不关心,晚上8点到神意白银乡来,帮我破了这个案子你就继续做你的跑腿。否则就等着被辞退吧。”
你惊慌失措,分明,分明不应该有人知道的。你又觉得那天给坑里填土的时候似乎确实感受到过一阵诡异的视线,但你记不清了。
无论如何,你要藏住这件事,就要帮那个神秘人破案。你心想,就算是,就算了为了生计,你也要用你见多识广的能力把问题给解决了。
你如约到场,门口带着面具的仆人递给你一个滑稽的头套,你撇了撇嘴,不暴露身份倒是正合你意。
“各位,你们都是我找到的聪明人,这桩案子非你们不可。如果能破案,每个人都有重金酬谢,如果不能……想必各位心中很清楚结局如何了……”
包裹在一团黑衣服中的主持人顶着滑稽的鲶鱼头,说出的话却让你心底发冷。
你定了定心神,开始听案件的全貌……
【死宅】
你杀了人。
清澈的童谣声在你的耳边回荡,你看着自己手心的血,精神有点恍惚。
你杀了人。
“一根棍子轻轻打,二双筷子里外扒,三人小组爱说话,四个小兵不害怕, 五个朋友力气大……”
是家乡孩子们常常唱的童谣,但你已经来不及分辨其中的意思,土坑里味道差得很,你也不知道前一天分明在喝酒的自己怎么会在这个倒霉的土坑里醒来,身边还有个满头是血的家伙,仔细想起来,昨天喝酒的时候似乎隔壁桌确实有个人看着很像他。
如果是你崇拜的伟大调查员希尔迪布兰德,一定会在这个时候沉稳地思考得出结论,但你不是,你只是个又懒又丧的死宅,你只想懒在家里一睡一整天。
不过现在不是想这个的时候,你抹了把脸,手脚并用往坑外爬,然而这个时候,你似乎感觉到身边的尸体动了动,你吓得魂飞魄散。慌乱中,你似乎踩到了一块松动的石头,身子一歪又磕晕了过去。
等你再醒来就已经在医院里了,隔壁床的病友关切地询问了你的状况,你问他是谁送你来医院的,他摇头并不知道。
头好痛。大概是宿醉吧。
该不会刚刚的那些想法也都是梦吧……
你再次回到印象里土坑的位置,那里已经被填平了,你懒得多想,索性把这一切都抛在脑后。之后果然一切风平浪静,你还是个废柴的死宅,一睡一整天。
直到有一天,你隐约听到通讯珠响了响,没等你接起来,一个低沉的声音就从里面传来:“我知道你做了什么,但我不关心,晚上8点到神意白银乡来,帮我破了这个案子你就继续做你的废柴死宅。否则就等着失去自由吧。”
你惊慌失措,分明,分明不应该有人知道的。你又觉得那天从坑里爬出来的时候似乎确实感受到过一阵诡异的视线,但你记不清了。
无论如何,你要藏住这件事,就要帮那个神秘人破案。你心想,“是时候追随希尔迪布兰德阁下运用智慧了,说不定我也有调查员的天赋呢。”
你如约到场,门口带着面具的仆人递给你一个滑稽的头套,你撇了撇嘴,不暴露身份倒是正合你意。
“各位,你们都是我找到的聪明人,这桩案子非你们不可。如果能破案,每个人都有重金酬谢,如果不能……想必各位心中很清楚结局如何了……”
包裹在一团黑衣服中的主持人顶着滑稽的鲶鱼头,说出的话却让你心底发冷。
你定了定心神,开始听案件的全貌……
【调查员】
你杀了人。
清澈的童谣声在你的耳边回荡,你看着自己手心的血,精神有点恍惚。
你杀了人。
“一根棍子轻轻打,二双筷子里外扒,三人小组爱说话,四个小兵不害怕, 五个朋友力气大……”
是小时候常常听到的童谣,你不知道眼前这个家伙为什么会唱。小时候你一听这个就头疼,小朋友也不爱跟你玩,但没关系,你自己读书学习,因为天赋異稟,你成为了一名调查员。
虽然没有那位调查员那么有名,但你也为很多人解决了问题,甚至在城市的护卫队里颇有名气,这让你有些得意。
这次的委托人有些诡异,他非但不崇拜你,甚至经常用奇怪的眼神看你,一副看不起人的样子。
你下决定要向他证明自己,可偏偏他要你找的人就像根本不存在似的,你气闷得很。
“鼎鼎有名的调查员也不过如此嘛。”他嘲讽的嘴脸怎么看怎么恶心。
再回过神的时候,你已经在面对着埋着他的土堆发呆了。身边有不少人知道你接了他的委托,如果他失踪了你一定脱不了干系,你看了眼时间,现在是19:55,你从口袋里拿出争执时从他身上摸走的通讯珠,联系飞空艇订了两个小时后往返于乌尔达哈和格里达尼亚的飞空艇票。你一向未雨绸缪,这是聪明的调查员必备的。
一切都很顺利。甚至没有人来问过你这件事,也是,艾欧泽亚每天死那么多人,有谁会在意少了个麻烦的家伙呢。
直到有一天,你隐约听到通讯珠响了响,没等你接起来,一个低沉的声音就从里面传来:“我知道你做了什么,但我不关心,晚上8点到神意白银乡来,帮我破了这个案子你就继续做你的著名调查员。否则就等着身败名裂吧。”
你惊慌失措,分明,分明不应该有人知道的。你又觉得那天给坑里填土的时候似乎确实感受到过一阵诡异的视线,但你记不清了。
无论如何,你要藏住这件事,就要帮那个神秘人破案。你心想,“凭我这么多年的经验,一桩小案子还不是易如反掌。”
你如约到场,门口带着面具的仆人递给你一个滑稽的头套,你撇了撇嘴,不暴露身份倒是正合你意。
“各位,你们都是我找到的聪明人,这桩案子非你们不可。如果能破案,每个人都有重金酬谢,如果不能……想必各位心中很清楚结局如何了……”
包裹在一团黑衣服中的主持人顶着滑稽的鲶鱼头,说出的话却让你心底发冷。
你定了定心神,开始听案件的全貌……
【混混】
你杀了人。
清澈的童谣声在你的耳边回荡,你看着自己手心的血,精神有点恍惚。
你杀了人。
“一根棍子轻轻打,二双筷子里外扒,三人小组爱说话,四个小兵不害怕, 五个朋友力气大……”
是家乡孩子们常常唱的童谣,你每次听到都烦躁得想打人。
眼前倒在血泊里的家伙刚刚也唱了,你挠了挠头,烦躁地想着,怎么有人不怕死敢来惹你呢,难道没听说过你打架有多凶吗?你手里拿着粗糙的木棍,又往他头上招呼了一下。
你开着车,尸体在后备箱里,你看了眼时间,19:15,宿醉让你头昏脑胀,今天是几号来着?你恍惚记得昨天是1号你跟别人约架的日子,结果对方失约了,你恼恨地喝了一晚上酒,那今天大概是2号。你打算把这个尸体随便找个地方丢了就去找失约的嫁祸打一架。
把事情都解决完已经是20:05了,你一向有一边走神一边把事干完的能力,你想了想,径直去不远的地方找到那个失约的胆小鬼,虽然自己也挂了点彩,你还是把他揍了个半死,然后一起被送进了医院。
今天医院格外的忙,没什么人关注你,你自己找了个床躺下睡了。隔壁的呼噜声真吵。
没什么人问过你死人的事情,毕竟,艾欧泽亚每天死那么多人,有谁会在意少了个碍眼的家伙呢。
直到有一天,你隐约听到通讯珠响了响,没等你接起来,一个低沉的声音就从里面传来:“我知道你做了什么,但我不关心,晚上8点到神意白银乡来,帮我破了这个案子你就继续做你的街头混混。否则就等着被恒辉队抓走吧吧。”
你暴躁不已,分明,分明不应该有人知道的。你又觉得那天给坑里填土的时候似乎确实感受到过一阵诡异的视线,但你记不清了。
无论如何,你要藏住这件事,就要帮那个神秘人破案。你心想,“凭我这么多年混社会的经验,一桩小案子还不是易如反掌。”
你如约到场,门口带着面具的仆人递给你一个滑稽的头套,你撇了撇嘴,不暴露身份倒是正合你意。
“各位,你们都是我找到的聪明人,这桩案子非你们不可。如果能破案,每个人都有重金酬谢,如果不能……想必各位心中很清楚结局如何了……”
包裹在一团黑衣服中的主持人顶着滑稽的鲶鱼头,说出的话却让你心底发冷。
你定了定心神,开始听案件的全貌……
【主持人】
和你约好的医师失踪了。
那是一个神神叨叨的医师,他说你的身体里不止有一个你,你的精神确实不太好,总是容易恍惚,但是一个身体里有好几个人这种谎话你根本不相信。于是他和你打了个赌,他会变换不同的身份来接近你,并且留下点什么证明,让你意识到真相。你可有可无的答应了,能直接揭穿一个骗子也是好的。
一天,他接通了你的通讯,说是一切都准备好了,5天后会再和你联系,还让你去莫古力那里查收一份邮件。
你没有在意。
当你意识到医师失踪的时候已经差不多是半个月后了,最后的消息是他预定了3号晚上从格里达尼亚到乌尔达哈的飞空艇。
3号那天?你做了什么?你完全没有印象了。
你决定先去看看那份邮件是什么。
邮箱里是一份厚厚的计划,里面写满了那5天里他会用什么样的身份和理由同不同的你接触。
你翻看着这份计划,调查员、记者、跑腿、混混、死宅……这是你完全没想到的。
按照计划,1号那天医师会作为委托人和调查员接触,而在这之前,他已经去记者的杂志社投诉过、点名跑腿送过东西。
时间断在2号那天,你完全没有相关的记忆,但如果真的和医生说的一样,他们说不定会知道些什么。
你闭上了眼睛,学习着医师曾经跟你说过但你不屑一顾的方法,想象着通讯珠的声音:“我知道你做了什么,但我不关心,晚上8点到神意白银乡来,帮我破了这个案子……”
“各位,你们都是我找到的聪明人,这桩案子非你们不可。如果能破案,每个人都有重金酬谢,如果不能……想必各位心中很清楚结局如何了……”
你看着逐一出现的5个人,心底有些泛冷,幸好你提前给所有人蒙上了头套。
“请你们来的目的,是找一个人。失踪的人是一个医师,最后被人看到是上了从格里达尼亚到乌尔达哈的飞空艇,再之后,就神秘失踪了,希望各位可以解开医师神秘失踪之谜。”
END.

“呕!呕!咳咳……咳咳……”
“皮兄你还好吧!我给你拿点水漱口去!”
“没事,不用麻烦,过会就好……呕!”
皮良抱着恭桶不撒手,白天吃的干粮都吐了个干净,早知道就少吃一些,免得浪费!窗外漆黑一片,屋内烛火摇曳,忽明忽暗,时而一道闪电照亮船舱,万物皆煞白,片刻又转黑。白船在风雨中飘摇,皮良晕船晕得厉害,吐完之后病怏怏地躺在塌上,心里十分懊恼。
实在是不像话!吐成这样,宋慧肯定要觉得自己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书生了。可皮良再略一思索,又觉得自己的确如此,不免黯然。现在他只庆幸烛火昏暗,宋慧看不见他涨得通红的脸。
宋慧给他拿了碗水,让皮良冲淡嘴里的味道。皮良道了谢,又躺下,窗外电闪雷鸣,风雨呼啸,令人颇为不安。
不知这船能否顺利到得了白岛?可别在半路就沉了!皮良不禁起了悲观的念头,草草睡下,第二日早起又见着大雾,心里更是担忧。
“小兄弟不必担心,见着大雾,就是快到白岛了!”船上商人模样的乘客见他愁容满面,出言安慰,皮良这才放下心来。
又过了两日,船竟缓缓地下沉。皮良正在房内整理白船记事,忽听得外头女人高喊:“白岛将至,大家都回房,向那仙儿诚心祈愿,方能如愿以偿!”
祈愿?皮良一时不知祈何愿。他来此处是为了亲眼见一见鱼仙,现在心愿已完成了。虽说也想见一见那仙药,可那种罕物,他也不是非得到手中不可。他没病没灾,父母康健,要那起死回生的灵药做什么?思来想去,他当下的愿望竟与白岛和鱼仙都无关,不由得有些心虚地看了宋慧一眼。
她双手交握,双目微闭,显然在祈愿。等她睁开眼睛,皮良便问道:“宋兄许了什么愿?”
“嗯……想亲眼看一看鱼仙儿,还有,想听鱼仙讲的故事!”宋慧毫不隐瞒地答了,又反问皮良,“皮兄你呢?”
“我?和你一样。”皮良撒了谎,他的愿望可完全不是这个。
待到白船靠岸,皮良才终于感受到踏上大地的安全感。回程的时候不会又要吐吧……想到这里皮良就心有余悸。码头上好不热闹,人们纷纷下了船,有的熟门熟路往白岛里去,有的迎上来,想为新客人介绍一二,也不知是否安的好心。皮良仅仅回了个头的工夫,宋慧就已经跑得没影,他只好一边找她,一边去听周围的细碎闲谈。
“我瞧那人手上多了朵花儿,准是鱼仙赠的,那小子好福气啊!”
“你与我就没这福分。得了这花,仙儿也要优待几分,集市上也能占便宜。去年我有一同乡,得了此花,仙儿赠他珍珠宝石无数……”
那花真有那么灵光?皮良知道传闻不可尽信,多半是以讹传讹,受鱼仙馈赠是真,数量却不一定有那么多。不过那花儿应该确实有其用处,也许是仙儿们喜爱之人才能得赠……皮良正思索着,余光瞥见宋慧蹲在水洼边,墨色头发的鱼仙正往她头上戴一朵白花。皮良快步过去,还没走到近前,就闻见花的香味,知道那是朵茉莉。
“皮兄快看,鱼仙儿给了我一朵花!”宋慧拨弄着头上小花,高兴得像个小孩儿。皮良心中暗骂自己从前愚钝,怎么就看不出宋慧是个姑娘?他觉得脸发烫,轻声夸赞道:“宋兄戴这花真好看。”
鱼仙大概是觉得这场景无趣,作势就要沉到水里去。眼看鱼仙要走,皮良赶紧喊住了他,厚着脸皮开口道:“仙儿您能不能也给我一朵?我听说有了这花,在集市上能方便些……”
鱼仙眨了眨眼睛,一会儿看向皮良,一会儿又看看宋慧。那双金色眸子唤起了皮良的一些记忆,那一夜房间里的金色光芒,似乎就与这双眼睛一模一样。皮良突然觉得有几分害怕,但鱼仙猛然沉了底,浮上水面时捧着一朵湿透的茉莉:“给你的。”
“感激不尽!”
皮良顿时就把那点害怕忘在脑后,喜滋滋地把茉莉别在发间。虽然湿了点儿,但也是一朵茉莉花,和宋慧的可是一对儿!
他怀着这点没人知道的小心思,乐不可支地跟着宋慧往白岛里面去了。
白岛上浮桥遍地,连通各个深浅不一的水洼。往岛内走,地势渐高,坡上有一片洁白屋舍,听说供人随意居住。皮良宋慧二人找了间空屋安顿下来,默契地分住在两间房里,暗地里都松了一口气。
皮良放好行李,睡了个午觉,醒来天已经黑了。窗外月光静静照进来,皮良来了兴致,干脆提着灯出门闲逛。夜里的白岛一片寂静,沿着山坡往下看,月光照得水面一片雪白,分不清哪里是沙,哪里是水。皮良在心中记下眼前所见,正在啧啧称奇的时候,却看见个熟悉人影一半没在水里,远远冲他招手。
此情此景让皮良颇为熟悉,就仿佛在梦中见过许多遍似的。他提着灯笼走过去,离得近了些,才看清她头上的珊瑚珠翠。
“真巧,在这里遇见。”
青黛眨着一双凤眼,语气再平常不过。皮良挨着她在浮桥上坐下,略微有些紧张。这次不是梦里,没有香气扑鼻的桂花酒,也没有月光似的酒盏,倒让皮良不知说什么好了。
“先生这回可带了故事来?”
好在青黛还像往常一样与他说话,皮良也就自然而然地答话:“带是带了,可都是你听腻的鱼仙奇闻。”
青黛立刻说:“那我不要听了。”
皮良犹豫一会儿,说道:“不过……倒有一个故事,或许可讲。”
“哦?”青黛身子往水面上浮了些,两只手臂也搭在了浮桥上。虽然面上看不出什么表情,但尾巴尖在水里轻轻晃动,惹得水面上起了小小涟漪。
皮良于是讲道:从前有一书生上山游玩,路遇大雨,只好夜宿破庙之中。那日破庙内还有一少年人在此避雨,与书生颇为投契,二人相谈甚欢,共宿一处,本以为此事再普通不过,第二天醒来,书生竟意外发现那少年人是个女子。这下书生慌了手脚,虽不知那女子为何男装打扮,但孤男寡女共宿一处,实在大大坏了礼法,丢了女儿家清白。于是书生就决定,要迎娶这位女子……
青黛打断皮良的讲述,问道:“我不懂,为何只是同宿一处,就坏了你们人的礼法了?”
“这女儿家的清白是最最要紧的,若是被人知道两人同宿一处,恐怕那位姑娘今后要嫁不出去了。”皮良赶忙解释道。
“清白又是什么?”青黛又问。
皮良支支吾吾,不知道怎么开口。鱼仙儿与人不同,多半不知男欢女爱之事,他要怎么和青黛解释什么是清白?
“总之,总之就是很重要的东西……”
青黛理所当然地反问:“既然是重要的东西,东西丢了,为什么不去找回来呢?”
皮良哭笑不得:“不是那么一回事,清白就像……对了,就像一块白布上泼了墨,怎么洗也洗不净……”
“你是说,那书生朝姑娘身上泼墨水,所以没人再愿意娶她?”青黛仍然没能理解皮良的意思,但皮良已经不知道该如何解释,只好硬着头皮说下去:“就当是这样吧!但是书生没有泼墨水,只是孤男寡女共宿一处,旁人免不了会觉得……”
青黛奇道:“你们人可真奇怪,好端端的,干嘛往人家衣服上泼墨。再说,衣裳脏了,换一件便是了,和婚嫁又有什么关系。”
皮良知道实在是解释不通,只好硬生生跳过清白不清白的部分,径直讲了下去:“总而言之,那书生决意要娶这位女子,便打听她家住何方,姓甚名谁,好日后上门提亲……”
青黛不满道:“你别以为把梁祝的故事换个样儿讲,我就听不出了。后来呢?是不是那女子家另有婚约,书生一病不起,两人双双化蝶去了?”
皮良连忙摇头:“当然不是,书生后来当真将那姑娘娶了回家,日子过得美满幸福。”
“那这故事怪没趣的,比不上梁祝二人轰轰烈烈。你今日讲的,可比不上以前的。”青黛撇嘴。
皮良无话可说,他也知道这个故事没什么意思,要是按以前的讲法,那女子多半是什么山中精怪,画中仙人,若为凡人,也该是世家千金,身份不凡才好。书生想与她厮守,必然要历经考验,最后仍可能抱憾终身。可这次他带着私心,不肯那样去讲,故事自然无趣。
“下次,下次一定找个有趣的来讲,”皮良双手合十,对青黛保证道,“实在是因为我涉世尚浅,话本子也看得少……”
“我看是因为没有那桂花美酒,你才不肯讲我爱听的,”青黛哼了一声,“你在这里等着,我一会儿就回来。”
皮良不明所以,只见青黛倏忽入水,留一方泛着涟漪的水洼,在月亮下粼粼地闪光。过了不久,水面又是一阵波动,青黛浮上水面,手中捧一枚贝壳,不由分说往皮良膝上一塞:“拿着!从前不曾给你报酬,今天算是结清了。”
皮良低头一看,贝壳当中有珍珠数枚,银光闪闪,圆润无瑕。
“青黛姑娘,这实在是受之有愧……”
“你要是真受之有愧,就捡点好听的故事讲给我听吧!”
青黛说完,尾巴一甩消失在水中,徒留皮良在原地发愁:下次见面时,要讲个什么样的故事给青黛好呢……

《七宝楼》
沈太荣,秦州人士。进京赶考不得志,颓然返乡。经晋州,巨雨骤至,马匹受惊而奔。暗天暴霆,不辨昼夜,至沙地,过沼泽,沈生只知死握缰绳,不知身在何处。
忽见前方晴日碧空,群芳遍地,身后狂岚如同隔世。沈生远望,有亭台楼阁在前,通体皓白,艳阳之下,熠熠不能直视。良驹力尽而亡,沈生不得已,徒步而去。及近时,先过一小桥,继至屋内,家具如珠似贝,杯盘陈设镶金嵌银,流光溢彩,精妙非凡。大柱雕游龙,廊下悬飞凤;琉璃作梁,玛瑙为栋。院内玫瑰,庭中玉树,一叶一花皆是红白珊瑚雕就;其间啼莺飞雀、舞蝶戏蜂,细看也为珠宝琥珀;又有曲水一弯,波光粼粼,乃是贝母铺成。沈生虽讶异,心中甚是喜欢,四下张望无人,偷折一只南红蝴蝶藏于袖内。
红蝶落袖,便听身后有人问:“何人在此?”,沈生回头,见一戎装少年立于桥头,答:“过晋地忽逢暴雨,至此马亡,见有屋而来。”少年道:“虽意款待,然阿母将至,此处不宜久留,请先生出庭外。”
沈生问:“此处何处?”
少年曰:“塞外凉州。”
沈生又问:“此楼为贵府?”
少年怪曰:“非也,先生莫非目不识物?”
遂出庭外,少年弹指间,草叶化为桌椅,桌上并两盏白玉盅,其内有茶。沈生方觉渴极,一口闷下唇齿生香。再看盅内,又已香茶满盈。
沈生问:“尊上可为上仙?”然少年笑而不答。
二人候至半夜,沈生恍惚梦中似见一大手自月中降下,双指连根拈起楼宇庭院复又上升。至半空,沈始觉此宅连同贝母流水,造型竟如宝簪一支。
睡意朦胧间,沈生听闻少年道:“阿母来也!此回寻得失物,于吾定有大赏。先生既在此,也当同乐。”
于是又一弹指,桌上笔墨纸砚齐备,少年疾书几行,道:“吾与先生指路,先生此去能有大富贵。”沈生接纸,上书江南某地某家,沈生叹道:“明日出凉州难上登天,何至江南?”
少年道:“倒也容易。”话音落,马嘶,竟得复生。
谈话间,早已不见楼阁。少年向沈生拜别:“吾随阿母去也!”亦悠悠向月奔去。
及次日,沈生醒来不见桌椅,仿若昨夜仅为一梦。所幸信纸仍在,却也非纸,乃缸口大一枚鱼鳞。
沈生依少年所言,骑马赴鳞上所载之地。至,乃贸丝富商住家。沈生登门拜访,富商以礼待之,茶过三巡,自言有独女,样貌丑陋,十有六不能人言。令婢呼之,女至厅下,甫见沈生便能开口言语,众人皆惊。于是入赘,大喜之夜,新娘容貌似是娇俏几分,过数月,竟成美人。又经数年,二人得三子,富商生意多半交于沈生,家业益大。
忽有一日,沈生午夜惊醒,见一人立于床头,提灯照去,是那日所遇少年仙人。
少年怒言道:“当日以为清廉之人,又是同喜同乐才助之,未想也是偷鸡摸狗之辈!惜赐福不可收,定教汝后世偿还!”窗外晴天霹雳,少年已不见身影。
沈生终夜未眠,天明遍寻当年所偷赤珠蝶不见,回首见庭中铺天盖地红蝶翻飞,如血潮翻涌。沈生惊叫,妻至,然妻未见一蝶。
自此沈生郁郁终生。其三子有二染疫而亡,余一膝下有四女,无子。此后数代,皆是如此。
《鱼辩》
淮水有鱼为兄弟,一日弟鱼谓兄鱼曰:“吾闻人不知鱼之乐。”
兄鱼问:“缘何出此言?”
弟鱼曰:“他日出游遇人间书生,口中朗朗。”
问:“其言为何?”
弟鱼答:“‘子非鱼,安知鱼之乐’,‘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不知鱼之乐’,云云。”
兄鱼曰:“子沐仍与施论此事?”
弟鱼曰:“否,青头后生也,然亦未可知知之否。”
兄鱼曰:“自是不知。”
弟鱼问:“为何?”
兄鱼曰:“若其不知,则为不知;若其自以为知,却不知吾以为其不知,亦为不知也。”
弟鱼道:“胡哉!人定知之。若不信,问他鱼便知。”
兄弟溯游,往嵯峨洞天寻得大鱼曰白玉娘娘者。二鱼问安罢,弟鱼问:“人安知鱼之乐耶?”
娘娘曰:“汝知飞鸟之乐乎?此异族其异也。”
弟鱼曰:“吾言不然。吾知兄长心,故知其乐;鱼亦可知人心,心既能得相通,自知之。”
兄鱼驳曰:“汝知吾心,吾亦知汝心,此为通。然人不可知鱼心,何言相通?”
弟鱼曰:“兄长非人,如何知人不可知?”
兄鱼叹曰:“此旧辨也!既非人,成人便知。”
娘娘曰:“若如此,恰有一事相求。”道是有前缘恩怨者,可借成人。又云:“观其后人有姻缘入云衢。觅此婿化之鱼,可问为人龙凤者安知汝之乐也。吾与彼债亦销。”于是传将妙令心法,教二鱼如何化人。
弟鱼道:“妙哉!定不负所托。”,遂与兄往浮玉山去。
次年,兄鱼通人心,弟鱼自兄鱼处闻其妻儿;又明年,许之秘宝,得身;弟鱼得此人妻身。及化人,弟鱼急不可待,是夜便问其女:“子非鱼,安知鱼之乐耶?”然女茫然不知。
弟鱼心言:“败矣!人心无趣,早知不与兄辩。”



作者:诸子百
免责声明:笑语
(世界观为架空世界观,大部分地方与现实三次元世界不符,文中地点皆为虚拟。)
寂静的深夜下垂着亮光,那不是天空的玄月,而是落地工厂的灯光。灯光之上,黑夜作为背景板偷抹几串黑烟窜出,灯光之下无数杂房屹立其中,街道由石板汇成,道路却不见丁点平整,向前延申隐约听见众人杂乱的脚步。再向前处望去,勉强称得上房屋的房子内忽闪着光。此刻这算不上一个好天气,屋内服务员拎着牌子,忍不住呼了口热气,匆忙将带有酒瓶标志的牌子挂到屋外。
他止不住的向前眺望,那同样也不是月亮,月亮的光照及不到他们身上,五彩斑斓的霓虹光透着黑暗的云雾闪着,这里的每个人都止不住的抬头望着,这种五彩靓丽的光硬生生的刻在他们的眼球上,烙在他们的脑子上,最终也只是传说里禁止到及的地方。
门缝内有声响传来,“今天不会有客人来了,他们接到了命令今夜加班。"
那是带有南方口音的嘶哑音,分不清男女。那人语气透着不悦,对着账本寥寥无几的数字不断叹气,上面的紧急状况将他们耍的团团转,今夜是赚不到钱了。
门外服务员摩挲着门牌。他倒是乐观,透过半掩的店门丢出一句:
“万一有客人呢?”
前台侧耳听到几串马克皮靴声,踢踢踏踏的真令人不爽,她默默的收起桌上的账本,随口道:“不会了..”
店内她看到一只大手突得紧握门框,门口高大的身形全然遮盖住服务员,强烈的气场使得服务员本能后撤两步,带着店牌呆呆地站在原地,身旁涌现的推力逼着他不敢抬头。
来者身高十尺有余,他是毫不客气擅自推开大门,服务员从慌乱中回神,舍下门牌偷偷打量着那些人。高大男子前脚刚进,后脚店外随行人员自行整齐两排,他们的身上没有这里人浑身块土的酸气味,只有葡萄酒的香气味儿。
现在的葡萄酒只供桥墙内的贵人们饮用,这种味道引得服务员十足的好奇,个个腰间束有皮革腰带,腰间携有一管器枪,一双双长筒皮靴擦的锃光瓦亮,比这边最高的钟楼相比更为一尘不染。
“那个反叛者叫什么名字?”
除却远方滴滴荡漾的钟铃外,街上那是十足的安静,面前这群奇怪家伙的悄悄话能让这个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听得一清二楚。
“叫,奥斯汀.杜威,是名从墙桥内逃出来的废物。”
奥斯汀杜威。一个让服务员熟悉的名字,这个名字在酒吧内又一次的重复:
“奥斯汀杜威在哪里?”
高大男人拳头重重砸向前台,瘪薄的桌面被震得嗡嗡作响,钢笔差点弹了起来。他可不想太久呆在这里,空气中廉价酒气溢满他的鼻孔,他不喜欢这种酸臭的味道,他只想速战速决。
他看着眼前还算是风情万种的女人,一个简单的单马尾不掩她散发的气质,他看见她胸前的胸牌——梅,这个名字令他不觉的语气稍有收敛下来:
“我是国家警卫团分队长泽姆拉克,奥斯汀杜威是通缉罪犯,他在哪里?”
梅斜眼望向窗户外,那是整团模糊的身影,她不禁蹙眉,他们来的人数不少,仅靠她与门外的小赫林二人..情况也是不容乐观。
“警官我也不想跟你兜圈,”梅试图用放松心态回应前台外的这位高大“巨人”,
“他给的实在是太多了,我们只是见钱眼开的贱民。”
梅手指绕着桌上那块烧掉的痕迹,她的嗓音条件并不完美,话语间的诚恳竟然被粗糙的嗓音表现的更为真诚:
“还得请警官多多饶恕。”
梅借着说话遮掩,轻敲痕迹处三次,声响并不明显,只是在这里不明显。前台桌下正如平常布置那般是常人见不到的地方,对于一些特殊的小客人来说,这可能就是绝妙的秘密课堂。
这里仅有简单的几只桌椅,和几只正在认真书写的孩子们。孩子们的前方是一块简陋的黑板残骸,黑板钉在墙上,残骸形状歪七扭八可被钉的正正当当,不歪不斜。照明的只有几支小的可怜的蜡烛,昏黄的烛光下能够看清黑板上写着简单的声调,黑板下被一堆堆书籍垫着,黑板旁站着男子,他手中握着三块书写用粉石,另一只手捧着书他正聚精会神的看着,他的穿着就不似酒吧的员工,是一身破旧的西服,他没有员工的胸牌,可他右手袖口上绣着他的名字,奥斯汀杜威。
咚咚咚。
声音微弱在这里却明显,悉悉索索的写字音怎么做也盖不住顶上任何的响动。
三声为号,他合上书抬头望去,他有些不舍,他还想要在这里停留更久,至少把这些孩子教会——
“老实说女士,他犯的罪可不是简单的杀人罪,是知识传播罪!是反叛分子!”
顶上再次传来不耐烦的声响,烛火被震得摇摇欲坠,几个孩子停下手中的动作好奇的抬头张望,杜威拍拍手吸引孩子的注意力,
“同学们,我们得先下课了,一会呢从后门出去,都明白吗?”说罢杜威摆出嘘声手势,示意孩子们小声行动。
几个孩子相互对视后明白老师的意思,纷纷点头,安安静静收拾着桌子上的东西。
泽姆拉克他不想再浪费更多的时间,上面的人已经不允许他再浪费任何的机会将这个反叛分子放跑。在警团的10年生涯里迫使他练就观察入微的技能,反常的动作引起他的警惕,桌下有暗房!
对面女人的行为将泽姆拉克性子消磨的一干二净,几发子弹出膛射向高处。梅深知不妙,这是发起进攻的指令。酒吧门外的警队听见屋内响声后不敢再小声言语迅速站直,几列警卫整齐划一拿出器枪屋内。
梅来不及作出反应,一管管器枪怼向酒吧门口,梅透过这群钢铁管子的间隙看见门外赫林缓慢举起了双手。
泽姆拉克抬手宣读,“妨碍警卫办案罪,理应击毙。”
毫不留情的条律加之繁琐的指挥条令,构成了这一帮政府饲养的哈巴狗们,这个女人不合时宜的笑出声。她没有再说过一句话,上扬的嘴角让在场的警卫们恼羞成怒。
突突突,突突突。
杜威头顶剧烈摇动声音逐渐逼近,杜威不知该擦去黑板的东西还是藏起手上的书籍,还是带走孩子。
孩子,杜威望着台下的孩子们,每个孩子的眼神,每双孩子的眼睛都迸发着求知的火。火焰微弱,无法点燃一根火柴,可火光更亮,比远处的昼夜升起的厂灯还要白亮,这团火抵得过墙桥内迷人眼的霓虹灯。
杜威扒开墙边堆砌的纸张,漏出一扇石头门,石头有小腿高还沉,他搬走石头后露出暗道,暗门狭窄只供瘦小身型的孩子们能进出。
孩子们纷纷相望,多少次意外状况让这群孩子异常熟练。可今晚杜威老师急促的反应让孩子们摸不到头脑,其中高个子的孩子似乎看出了端倪,小小的手心攥紧半截铅笔,笔杆太短导致铅笔灰染黑了他的手指不少。
在这里橡皮是个稀罕物件,落笔下去的那一刻就不允许出现错误,无论是多么小的黑点就再也擦不掉了。
“杜威老师,我们还会再继续上课吗?”孩子们叽叽喳喳哄上前,杜威摸了摸几个小脑袋,他们的头顶还参杂着灰尘烟絮,但眼神中透着真挚,杜威不忍,只好脱口而出:
“一定可以的,老师向你保证。”
一墙之隔的声响简直要把这宽窄的小教室给掀翻了,最后一声枪起,整扇木门被一只厚重如灌铅的皮靴硬生生的踹开,木门破开,风声将烛火被硬生生扯断。
杜威也知道,已经来不及了,在黑暗中他将所有的孩子引进那条隐蔽的暗道当中。
“说谎话就是小狗哦。”
临走前高个子孩子塞进杜威手里一块东西,那道昏暗的明亮让杜威的眼前没有了迷茫,他将小小的缝隙尽可能的用书籍填补洞口,将这个暗道彻底掩盖在知识的壁垒中。
“奥斯汀杜威,我知道你在里面。”
泽姆拉克举起器枪,眼神示意身后队员重新装填火弹拿起器枪。
没了烛光的照耀,地下室一片漆黑像是深不见底的无底洞,黑暗的深处若近若离传出声响。杜威站在暗处却能将门口的人尽收眼底,泽姆拉克不敢确认里面的人究竟是普通的教师还是那伙极端分子的成员。之前也有先例,他们极为狡猾常常伪装成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上面的决绝无情的口令在他脑袋里不断盘旋:
“射击。”
泽姆拉克心想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他们要把地下室全部烧毁,烧的连只书渣都不剩。点点火弹散着刺眼红光,数发焰弹淹没进眼前的黑雾,数几秒后却似投石问路埋入深处没了动静,点滴火弹伸进深不见底的谭水不见丝毫回应。
“这。。不可能。。”
警卫兵互相对望,按照平常这回儿里面烧的正旺,怎么打了一圈的弹药里面竟还没有任何的火点,这不符合常理!这,这超出了他们的认知范围内,雄赳赳昂着的枪头挨个停了下来。
泽姆拉克推开这群没用的废物向前走进,他看见了尽头微弱的明亮,幽幽朦胧散着蓝色光晕浮在半空,光晕向后退着散出纸张被踢踏的声响。
快射,快射。
杜威捏紧手中的石头不断祈祷,拳头大的蓝色矿石似乎无止境的吸收着火光,2号矿场的器石能够短时间吸入火焰,蓝光越来越强,这块石头已经到了极限,强烈的光芒让杜威看清门口高大的长官,看清那把正在蓄力的器枪,杜威不得不再次作出选择,书还是自己,还是。。
带有星火的燃弹最终是射向了蓝色的矿石,泽姆拉克眼睁睁看向杜威抓住矿石朝后墙扑去,这次子弹如愿以偿引爆矿石,霎那间的明亮贯穿整座小小的课堂内,仅仅瞬间吹动脚下的书页微微浮动,墙角书籍垒的坚固却是不再摇摇欲坠,碧蓝色焰火在杜威左手炸开,剧烈的波动炸破墙面,那一盏小小的蜡烛颠碎折断,碎在了坍塌的石墙废墟内。
废墟堆成小山,泽姆拉克拿起其中碎掉的一块衣袖,上面写着杜威的名字,有这就足够了。这时的他才敢抬起头颅,长舒口气如释重负。
泽姆拉克深知无数发子弹蕴含的强大能量,上面的人也不敢打着保票这玩意有多么的安全,不过这些对他而言不是他该做的任务,这个叛徒是被自己的愚蠢杀死的,舍弃那种令人艳羡的生活来到这个鸟不拉屎的穷地方,他一定被炸成了碎片,因为这就是背叛的代价。
泽姆拉克放松警惕后,鼻腔里再次灌满厌恶的酸臭味儿,这次可不用再忍了,他道:“任务完成,我们走。”
身后杵在门外的警员这才敢前进,有胆大的队员见队长放松了警惕,见缝插针:“那这些书怎么办?”
泽姆拉克环顾四周,
“那两个武装教师已经跑了。”
这个蠢蛋牺牲了自己换取了这些书籍的安慰,只可惜。。他笑道:
“至于这里,已经没有人看懂里面的文字了。”
-end-
朝阳即将升起,宣誓清晨的不是太阳而是已经熄灭的电灯。霞光映满半角天边,半缕赤光悄无声息洒下,光芒低微比不起火堆最后半点灰烬落在矮矮的废墟当中,天空泛白开始亮起,赤光穿过后墙最终铺在黑板之上,墙角的书籍早就消失不见,那根蜡烛也跟着不见了踪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