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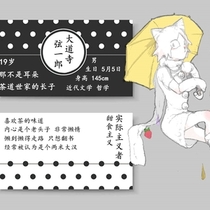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個故事。
慣例用這樣的講述開頭,是因為回憶從來都比正在經歷的現實溫暖,人的大腦會自動濾去不愉快的雜質,只留下圓滿和幸福。
生命是孤獨的,這句話貫穿老頭子的一生,直到他鬱鬱而終咽了最後一口氣。沈無心不知道他說的是否正確,因為老頭子說話行事從來半真半假,就連教他的捉鬼符咒都有大半是不靈的——沈無心當然不承認那是因為他學藝不精。老頭子咽了氣以後他還守著他的尸體過了三天,以為他會像以往數次裝死一樣在他滴了幾滴眼淚以後大笑著跳起來說你哭了羞羞。但是沒有,直到那具肉體在夏日的高溫下發出腐爛的臭味,他才意識到老頭子這次是真的死了。孤獨一生,無兒無女,陪伴身邊的唯有沈無心這個撿來的便宜徒弟而已。
其他人的生命是不是孤獨,沈無心沒有思考過。至少山下那個有五個老婆的胖員外,是絕對沒有時間在老婆們的廝打中思考這樣的問題的。沈無心把老頭子髒了以後突然福至心靈,也許只有他們天師才會過得如此孤獨,他想。
沈無心是老頭子撿回去養大的孤兒,老頭子無名無姓,給小孩子取名字無非為了使喚起來方便。隨手拿了案上一本封皮打皺發黃的書,無心集,唐代沈颯著,好,今天起你就叫沈無心了。
真是不走心。
沈無心跟著老頭子十年,有七年時間都在炒菜做飯洗衣服砍柴買鹽打醬油,長期交流對象只有山下賣雜貨的陳瘸子,養成一個沉默寡言的性子。第八個年頭老頭子自覺不行了,把他喊到床前,鄭重其事的跟他說。
無心啊,師傅我其實是天師世家的人,因為愛上了妖怪才被逐出師門居住在這裡。
說到這裡他停頓了一下,雙眼盯著沈無心,似乎在等他反應。
沈無心瞅著老頭子早上沒洗乾淨眼角還粘著眼屎的眼睛,沉默地等他開口。
半晌老頭子尷尬地咳嗽一聲,說你性子沉穩根骨不錯,聽了這樣的消息也能不動聲色,這樣吧我就把我一身道術傳授於你,希望你一定能捉住一隻妖怪…不要辱沒我的師門。
哦。沈無心說。
天師是介於和尚趕尸人道士之外的職業,在三教九流都沒有記載。老頭子教得隨心所欲,沈無心也學得磕磕絆絆。老頭子死的前一週他剛剛能開眼見到鬼怪,死的前一天他才成功把老頭子養給他訓練用的鬼捉住。那鬼一把鼻涕一把淚的跪下來說大爺你捉住我算了,不要再用那些莫名其妙的咒語來騷擾我就好。
沈無心給老頭子守過了頭七,靈前蠟燭安安靜靜的,說明老頭子安心去投胎了。挺好,沈無心想,老頭子喜歡的那個妖怪據說早被他家族的人煉了丹。老頭子的床頭掛著的那片鱗已經灰敗得不成樣子,沈無心知道那是本體早已湮滅的憑證。
安心去投胎了,說不定還能遇上。他覺得以老頭子的智商,大概不會再往天師世家躥了。
頭七過完了,沈無心就收拾東西下了山。雖然老頭子是個不肖的師傅,但他好歹也養了沈無心這麼些年。既然他的遺願是讓沈無心至少捉住一隻妖怪不要辱沒師門,那麼他就去這麼做好了。
雖然,他也不知道他有什麼師門可以辱沒。
沈無心下了山,來到他經常提著野兔換鹽的小鎮上。這座城鎮東面臨海,他和老頭子居住的山說白了也只是一座高點的小丘。晚上睡覺時候海浪聲清晰入耳,但不像鎮裡連呼吸的空氣都好似浸在深海。
他並不知道自己可以幹什麼,捉鬼嗎,這鎮子處處透著安定祥和的氣息,幾乎可以送去參與比拼年度人鬼和睦先進小鎮。何況沈無心這種說得最熟練的話是老闆來袋鹽或來瓶醬油的傢伙,要他上門用三寸不爛之舌忽悠幾個金主看戲法簡直就是天方夜譚。
沈無心買了一個燒餅叼在嘴裡,從街頭走到街尾,又從街尾晃回街頭,如是几番。街頭那裡有個算命的小攤坐著的瞎子忍不住開口。
這小哥,你在這走來走去多次了,是否在尋找失物?
沈無心站住腳看著瞎子。你怎麼知道?
天機不可洩露,不過若你心誠,我倒能拼一拼替你測算。瞎子高深莫測一笑,手指輕輕拈過鬍鬚,端的是仙風道骨。
不是。沈無心頓了頓走到瞎子攤位前,他還不太擅長說太長的句子。我說你,不是看不見,怎麼知道我在這裡來回了多次?
瞎子一愣,頓時老臉一紅,起身扯住沈無心衣袖壓低嗓子。都是明白人,你別這麼大聲說出來啊!
沈無心並不明白瞎子說的什麼明白人。原來你沒有瞎啊,他說。
廢話,真瞎了誰擺攤兒算命啊。瞎子見街道上沒什麼人,索性一包捲了身後神機妙算的旗幡和桌上紙筆。得,今天算我倒霉,明天我換個位置。
瞎子把翻上去的眼珠翻了回來,原來有黑黑的一雙亮眼。故意沙啞的嗓子也還原了,原來是清冽洌一把好聲音。沈無心愣愣地看著不瞎的瞎子收拾東西摸著自己的光頭走開,又摸了摸他留下來的破爛桌凳。
老頭子好像有教過算命吧。
隔天,臨海鎮上的閒人都在奇怪,街頭算命的攤子換了人,從光腦袋的瞎子變成了一個木呆的小哥。
沈無心坐了不瞎的瞎子的攤位,雖然很是引起了小鎮閒人的好奇,但對是不是有人來找他算命並沒有什麼用。須知小鎮真的太小了,小到街頭算命攤的變動都可以成為街頭巷尾的新聞。但一個木訥的算命小哥是沒有辦法維持這個新聞的持續性的,所以甚至那一天還沒結束,鎮上的人已經習慣了沈無心一臉木然的坐在那裡,好像原本小鎮的算命先生就一直是他一樣。
沈無心在那個攤上坐了五天,沒有人前來算命。他每天買三個燒餅,倒是和買燒餅的少年郎認識了。
你那樣又不吆喝又沒表情的,怎麼會有人來找你算命啦。第六天沈無心買燒餅的時候發現身上沒有一個錢了,少年用火鉗夾了一個燒餅給他,像模像樣地勸說道。
那要怎麼做?沈無心接過熱騰騰的燒餅,非常虛心地求教。
少年想了想,指著他的臉。首先你就不能總這樣發呆,臉看起來很蠢啦。
哦…沈無心第一次聽到有人這樣說,不由得摸了摸自己的臉。
就算你擺不出看起來很厲害的表情,也不要露出這種讓人一看就知道你在發呆的表情。少年對著他的臉指指戳戳,沈無心被他說得暈頭轉向,除了連連點頭什麼都不會。
賣燒餅的少年畢竟孩童心性,憑著好玩擺佈了一會兒沈無心,看他這麼信任自己也有些慚愧,便湊到他耳邊悄聲。你就假裝你一直在思考,如果不知道想什麼就想今晚吃什麼明天吃什麼,保準能唬住別人。
沈無心點點頭嚥下最後一口燒餅,一面思考今晚沒有錢了該怎麼辦一面露出了神遊天外的表情。少年滿意地一拍大腿,對他豎起了拇指。
然而剛剛習得唬人技能的沈無心還沒來得及摩拳擦掌實踐一番,小鎮上就遭了災。
直到很多年以後,沈無心才從當地的縣誌上看到關於那天的記載。寥寥數語概括了一座小鎮從安寧到荒涼的整個過程,沈無心後來見過很多城市的變遷和王朝的更替,但沒有一個是像那座臨海鎮那樣短的。他念完這段話過後,才聽到了手裡的茶杯在地上摔碎的聲音。
背井離鄉的遊子對家鄉總會抱有特殊的情誼,隨時間的沉澱愈加深厚。所以沈無心雖然在東瀛過得很好,還是會不自覺的懷念那個呼吸都好像來自深海的小鎮,不知老頭子的墳上野草又長高了多少。
遇倭襲,無人生還。
沈無心認的字是杉教的,杉是他在東瀛認識的女妖怪,永遠保持少女模樣的天狗。他知道倭是代表東瀛這邊的人類,即使他不明白為何只是隔了一道海洋就要這樣劃分。他吃力地回憶起那天的情形,好像先是起火,橙紅色的火焰卷著黑煙從鎮子口的茶樓一路燒了過來。鎮上的人都開始大喊大叫,像被狼群驅趕的山羊一樣拼命向鎮外奔逃。沈無心沒有見過這樣的場面,他坐在算命攤上,嘴巴因為驚訝不由自主地張大。突然他的手被賣燒餅的少年一把拉住,那少年本來早已經跑掉了,現在卻折回來尋他。沈無心剛準備向他道謝,一片刀光閃過,少年的頭就掉在了算命攤的小桌子上。腔子裡噴出一道熱乎乎的鮮血,濺了沈無心一臉。
少年的身子歪倒下來,露出一張猙獰的面孔。閃著寒光的刀鋒再一次砍了下來,沈無心猛地往後一縮避開了去。那個舉刀的人似乎很意外,嘴裡喊著沈無心聽不懂的話語,追著他劈砍起來。
這讓當時的沈無心覺得很煩,他看了看地上身首異處的少年,慢慢從背後拔出了老頭子留給他的桃木劍。
少年送了他一個燒餅,又教他怎麼唬人,還回來拉他走,那麼就是他的朋友。這個人殺了少年,那麼就該給他償命。沈無心難得進行這麼條理清晰的思考還迅速得出了結論,這讓他很滿意。
舉刀的男人再一次嗚哩哇啦地衝上來的時候,沈無心畫了一道符,然後一劍刺穿了那個男人的魂魄。
看過野獸捕獵的人都會知道,它們幾乎不會單獨行動。常來海邊城市滋擾的倭人更不會,所以那個男人剛倒在地上,下一個就紅著眼睛向他撲了過來。
杉看到沈無心的時候,後者站在一小堆尸體裡面,手裡握一把桃木劍,幾片紙符像粉蝶在他身邊翻飛。青年的臉上沒什麼表情,好像在思考誰也不會明白的問題。
賣燒餅少年傳授的唬人技術,實證有效。
杉輕而易舉的把沈無心拐去了東瀛,誘惑的低語不僅狐妖會,天狗也一樣擅長。杉自認為食物是世界上最難以抵抗的誘惑,是以讓沈無心看到的是琳瑯滿目的吃食。
事實上若換了任意一個天師,小天狗這方式獨特的幻術都不會奏效,可正趕上沈無心因為沒有算命生意已經一天水米未進,擺出那樣高深的表情也其實只是在思考一會兒吃什麼。所以天狗的幻術一施展,他立刻就著了道。
我頭一次看到這麼容易被誘惑的天師,真辱沒妳師門。
這是杉事後對沈無心的評價。
我完成了師傅遺願,並沒有辱沒師門。沈無心很淡定。
妳師傅遺願是什麼?杉好奇地湊過去。
有生之年抓住一隻妖怪。沈無心非常老實的交代。
你抓住了?杉有些迷惑,她和沈無心待在一起這麼久,從未見過他殺過一隻妖怪。就連上次差點弄斷她一隻翅膀的鬼車女,沈無心也只是在戰斗中拔了她的牙齒就把她放跑了,說是以前殺過人,不願意再積累殺業。
對啊,你不就是麼?抓住一隻妖怪又不是要殺了它。沈無心十分理所當然地抱著天狗,少有表情的臉上竟然難得地露出鄙夷她智商的表情。
杉震驚地發現她竟然無法反駁他,憤怒之下她用翅膀對著沈無心的臉猛地扇了一記,迅速丟下他飛開。天狗的飛行速度相當驚人,很快就看不到她的蹤影。
沈無心也不著急,從懷裡掏出半隻包好的山雞,燃起一張火符就地烤了起來。
不一會兒,頭頂傳來翅膀拍打的聲音。沈無心一抬頭,就看到杉坐在不遠處的樹枝上,眼睛一眨不眨地盯著他手裡開始散發香味的山雞。察覺到他的視線,天狗臉一紅,惡聲惡氣地朝他丟了幾根樹枝。
蠢蛋,烤個山雞也這麼磨磨蹭蹭!
我還是頭一次見到這麼容易被抓住的天狗,真是辱沒鞍馬山的聲名。沈無心慢吞吞撕下一隻雞翅擲上枝頭,天狗極其靈敏地撲過去接住了。
不要你管。
故事主角從一個人變成了兩個人,也無非喜怒哀樂生老病,沈無心活了很久,杉也是。他們走遍了東瀛,也去了幾次海那邊沈無心的家鄉。那座小鎮後來又繁榮了起來,百姓就像草原上的野草,不管遇到怎樣的磨難,都能在時間的撫平下重新一茬茬地生長起來。沈無心沒有找到賣燒餅少年的墓,他雖然將少年視作了朋友並為了他報仇,但他其實連他叫做什麼都不知道。
你就當這裡所有的人都是他的後代就好。察覺到同伴隱藏在面無表情之下的低落,杉手一揮指了指他們正經過的院落裡的一家人。女人背著一個嬰兒正在和面,男人則彎著腰推一個半人高的石磨,磨盤中間時不時有白色的粉末落下來,一個穿著肚兜的男孩子拿著小笤帚和簸箕跟著掃。旁邊的水井裡面,烏龜模樣的傢神正抬頭端詳著門外的客人。
他們的歲月也是和百年前一樣祥和寧靜,可以送去評選傑出人鬼和睦城鎮。
沈無心在街頭買了三個燒餅,自己和杉一人一個,第三個放在了老頭子的墳墓跟前。那墳墓塌方得厲害,哪怕這百多年沈無心來清理過好幾次,野草也幾乎將沈無心當年立下的可憐巴巴的石碑都吞噬掉。每次都是是杉幫忙找到老頭子沉睡的地方,天生對危險敏感的天狗能嗅到天師身上殺過妖的業證。
沈無心並不知道原來他總是笑呵呵老頑童一樣的師傅也殺過妖怪,杉說他只殺死過一隻妖怪,不知為什麼那妖怪的氣息就伴隨了他一生。
沈無心揮了揮手讓杉不要再說,那是他師傅與那個妖怪的故事,如今既然主角已經退場許久,故事也沒有再被刨根究底的必要。
那片灰敗的鱗在老頭子嚥氣的時候就碎了,沈無心把粉末和老頭子髒在了一起。杉曾經用非常惋惜的口吻告訴過他,那片鱗聽他的描述可能來自龍一類的生物。
沒有內丹,你吃了那片鱗,至少也能給你再增加幾百年壽命。
沈無心搖搖頭,輕輕摸了摸杉的臉。他的手掌已經皺得像樹皮,需要倚仗杉的攙扶才能勉強抬起。杉看著他又擺出看起來高深莫測的表情,噙著眼淚笑起來。
今晚吃烤肉哦。
不…沈無心喘了口氣,微笑起來。我其實在思考,投胎以後…要怎麼找到你。
你居然會思考別的,真是難得啊。
這句話只有杉自己聽到,沈無心的手指在她手中毫無生氣地踡起,指尖開始瀰漫死亡特有的灰白。
狡猾的傢伙,留下這句話,不就是為了讓我去找你麼。
……
雕塑作業總算告一段落,沈榭抬起頭揉了揉因為握刀太久酸痛的手腕,有些茫然地望著窗外。
今天食堂吃雞腿。有個清涼涼的聲音在他身邊響起。
沈榭偏過頭,看到一個抱著一袋零食的女孩。
哦。他說,一起去吃飯嗎?
女孩點點頭。





·此系列为小段子(?)集合,一篇两个小段子
·OOC
·我也不知道自己在扯什么淡(NTM
1.新室友
啊,大家好,我是贝丽卡,我现在正在图书馆的一角看书。
最近一直都很和平,不过对我来说怎样都好。今天氷那家伙没在图书馆,她说她昨晚夜观天象,预测到今天我可能要遇到我的新室友,所以她要留在宿舍里整理房间。
“新室友个鬼啦,氷你也太会扯了吧,我去图书馆了。”我当时听到这句话差点就没往她嘴里塞上几粒APXX-4869,这家伙不是只看弗洛O德的书吗,怎么还学会这么说了?!夜观天象是什么鬼?!你当你是什么,学习机啊?!
不知为何,现在的我比起以前没来到学院的我,说出的话连着朋友一起增加,而且开始吐槽了,氷说这是件好事,我也就没在意了。
最近没有遇到什么熟人,不过我不感到孤单。反正我有氷陪着,虽然整天看着老妈的脸有点压力,但她不像老妈那样,反倒是很像一个朋友的存在。
而且我相信,我一定能和他们再次相聚,
“今天心情也很不错呢,也许是咖啡的作用吧?”我这么想着,继续看我的书。
这本书里讲述的是一个女孩子一直以来都是幸运E,朋友们因为这件事都疏远她,不过她遇到了一位知己。这位知己是个幸运S,和她一起可以抵消掉女孩的幸运E。但好景不长,知己因为家庭变动转学了,她又变回了独自一人,和她的幸运E一起。
最后女孩收到了知己的信,里面说不会忘记和女孩的友谊,而女孩也在花园中找到了一片五叶草。既然四叶草代表幸运,那五叶草一定代表着超级幸运吧。
“可喜可贺,可喜可贺。”我合上书,准备放回去,不小心撞上一位女孩子,她手上的书掉了一地,有些砸在她的脚上,女孩忍不住皱了皱眉头。
我有些慌乱,那些书都是些厚书,如果走不了路的话该怎么办?我连声道歉,女孩子只是摇了摇头,说没关系。
这是我才注意到她的衣服,她没穿校服,而是穿着露脐装,手套和袜子上的骷髅手臂也很显眼,手上还拿着一把日本刀。
…确定这个女孩只是个学生,而不是那种所谓的杀马特吗?虽然发型看起来根本不像。她捡起散落的书,转身就走了。
“那个,不,不要勉强啦。”我看着她有点摇摇晃晃的背影,还是有些担心。“我帮你处理一下吧?”
女孩的动作停顿了一下,然后转过身来,向我这边走去。
我拿出随身携带的挎包,从里面掏出了一个水袋。虽然可以用我的能力冰冻住而变成防瞌睡神器(?),不过因为我不在下午看书,所以一直以来派不上用场。
我握住水袋,心里想着把这个水袋冰冻住,然后我从手心里感受到了水袋的温度正在下降,直到我摸到了硬硬的一块,这个水袋才算是被冻住了。
女孩把左边的鞋子和袜子脱掉,露出她的脚。果然,脚掌上出现了一些淤青。我把冰袋放在她的脚上冷敷。女孩也没什么反应,只是随手拿了一本书认真地看着。
等等,那本书是我的吧?我只能无奈的叹了口气,去隔壁的书架上再拿一本书来看。
“那个…脚还好吧?”出于愧疚,我还是忍不住开口问了下伤势。
“没问题。”
“真是对不起呢,都怪我不看路…我叫贝丽卡,你呢?”
“…米白。”
米白啊,这个名字很好听的样子。
“米白桑是学院新生?”最近陆续有一些新人来到学院,因为我没看过米白,所以我断定她肯定是学院新生。
米白点了点头。“你的能力?”
“如你所见,冰元素。”我随便的回答了一句。“平常只是用来降温和冰冻的,到了夏天还可以做冰沙。米白是什么元素?”
“死元素。”米白说完就合上那本书。“以及这本书,可以借给我吗?”
“嗯…可以,毕竟是图书馆的书,只要想着还书就好。”然后我看见她摇摇晃晃的扶着墙站了起来。
“你先在这里坐着吧。”我扶她坐下,重新放好冰袋。“我去借这本书。”
“那,借完书后,那本书不就是你的吗?”
“我再借给你不就好了?”我突然有个大胆的想法。“你能住进我的宿舍吗?”我试探着问了一句。
“……。”
米白沉默了一分钟,之后轻轻地点了点头。“请多指教。”
氷居然说中了,在带她回宿舍之前,我还得陪她拿行李,顺便帮她熟悉校园呢,看来今天算是有的忙了。
当然,回到宿舍后,氷从我衣柜里跳出来把我吓一跳的事,那就是后话了。
2.楼顶
晚上好各位,我是氷,现在正在陪着隔壁床的米白一起在楼顶上吹风。
主要原因是米白突然就出门了,我也不知道她要做什么所以跟了出去。
贝丽卡在宿舍里睡着了,反正今天她破天荒的只喝了一罐咖啡,而且是摩卡,并不能阻止她睡觉。
嘛,贝丽卡这次找到的室友是个无口,看见我说话也只问了一句“这是什么”,亏我还想现场大变活人吓她一跳呢,简直扫兴。
最重要的是,她的元素神一直都没冒泡,难道和洛霜纹的元素神一样是个闷骚?毕竟不能真的在她面前变成人形,我只能无聊的陪米白待在楼顶。
“米白,脚伤好些了吗?”我这么问她,贝丽卡说这事她有责任,但作为米白室友的元素神我也应该有责任,毕竟我没有跟在贝丽卡身边。
米白点点头。
不过,她的元素是【死】,虽然在学校估计只能在夏天用来打打苍蝇蚊子,但是伤口治愈的速度可能会慢一些,例如【生】元素使如果要治疗她的话,就可能要花费一段时间,所以我才会这么问。她手里还拿着一把日本刀,估计是擅长近战的吧,如果脚伤耽误了她的速度就不好了。
“话说回来,好久没有陪着别人在楼顶上吹风了呢。”我看着夜空,今天晚上的月亮是满月,空气很新鲜,能看到很多星星衬托在纯黑色的夜空画布上。
见我这么说,她疑惑的看向我这边。
“哈哈,我突然这么说,你不感到奇怪才不正常呢。”我笑了笑。“那个人还说她偶尔会有苦恼的事情,但是她又不敢和别人说出来呢。”
我所说的人当然是贝丽卡啦,她加入黑组的前一晚,她偷偷跑出去,我在楼顶上找到了她,那一晚我们在楼顶上聊了一会儿,她说她一直都不喜欢和人说出她的想法,特别是关于她母亲或者是她父亲的事。
…所以你就因为我是元素神而找我吐苦水?我庆幸我当时没说出这句话来,不然我觉得我会被贝丽卡做成刨冰。话说回来,那天貌似也是个满月。
“话说米白你为什么要在半夜偷偷来屋顶?”我这么问。
“………。”面前的人没有说话。
“…我有点不明白。”良久,她还是开口了。“我…真的叫米白吗?”
瞬间我没有说出话来。
这个孩子居然不知道自己的名字?
“嗯?你还有别的名字吗?”我努力保持镇定,继续说着。
“不,不是那样…"米白摇摇头。“事实上,我想不起来以前的事情…”
米白失忆了。如果我现在变成人形,我的脸色一定很难看吧。她为何失忆?失忆前是什么样的?我现在不能知道,毕竟我不是她的元素神…
我的目光转向楼梯口,那里不知何时站着一位白色和服的女人,正面无表情的看着米白。感觉到我在看她,她立刻打开门,头也不回的走下了楼梯。
那个人是谁呢?
“别担心,这种事情通常不是你想不起来。”我这么安慰着米白。“可能,是你有什么不愿意想起来的事情吧。”
失忆有时候是因为不好的经历或者是意外,不过她身上没有什么疤痕,所以应该是前者吧。
“喂喂,哪有你这么安慰别人的啦。”我背后传来一个极为熟悉的女生的声音,贝丽卡也跑到这里来,不知道要干什么。“氷你果然是看弗洛O德的书看太多了吧?”
“喂,弗洛O德研究的可是梦好不好?梦可是与性有关系的!”我不假思索的说出了这么一句话,顿时让贝丽卡面红耳赤。
“你你你你你在胡说个什么鬼?!”
“啥,性可是人类最基本的欲望。原来你还没有看过h——”
“你住嘴你不用说这个?!我19了你可以对我这么说,可是!米白!还未成年!”
对哦看米白的年龄貌似是17岁来着,现在对她说这个还是早了点,我闭嘴了。
“我本来想去厕所的,发现你们两个都不在,而且不知为何我又睡不着了。所以我顺便出去买点东西。”贝丽卡手中拿着一个塑料袋。“去楼顶一个人待着,结果你们居然在这里。”
“里面装了什么?”米白问道。
“唔,一罐白咖啡,一罐牛奶,一包巧克力饼干还有两大包薯片。”贝丽卡直接席地而坐,把塑料袋里的东西拿了出来。“哦对了还有罐杏仁露。售货员也不知道为何,说什么我是本店第六百名消费者所以给了我这么个东西。”
“比起杏仁露我还是想要你手里的那包薯片啊,那包原味的。”我可不对杏仁露感兴趣,那味道对我来说有点不能接受。
“好,等下给你,是说你现在没嘴没手的,怎么吃。”在我还在纠结于要不要为了食物变成人形的时候,贝丽卡已经拿起塑料袋里的罐装白咖啡,拉开拉环喝了一口。“果然还是晚上喝咖啡才爽啊!”
她已经完全喜欢上咖啡了,唉,有个名人说他会死于一万杯咖啡,我觉得她迟早也会死于一万杯咖啡的。
嗯,好吧,她会死于一万杯黑咖啡。
“米白你也随意吃吧,好东西得一起分享啊。”我招呼米白过来。“不管你现在是怎样,吃点东西才能有力气找到真相嘛!”
“你们在我不在的时候都在说什么啊…"贝丽卡吐槽了一句,继续喝她的白咖啡。
我看见米白在塑料袋里摸索了一下,拿出一罐饮料,估计是看不清楚,米白打开手机,借助手机的光亮看到,那是一罐杏仁露。
于是她把那罐杏仁露一饮而尽。
“还有吗?”她转过头来问贝丽卡。
“没有了,你想喝牛奶吗?”贝丽卡拿出那罐牛奶。
米白重重的点了点头。
“好吧好吧,本来我想留着自己喝的。”贝丽卡把牛奶也递给了她。
趁着米白喝牛奶的时候,我迅速的把米白失忆的事情告诉了贝丽卡。
“原来是这样…那么她不能使用能力了?”贝丽卡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
“我不知道呢。”我摇摇头。“我又不是她元素神。”
“说的也对。”贝丽卡干脆躺在地面上。
“嘛,这件事你还是不要说出去的好。”我说。
贝丽卡只是呆呆的看着星空。
“好久没有看到这么美丽的星空了。”她突然这么说。“可惜我没有带望远镜。”
“是啊。”
“我倒是想起以前研究馆事件的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了。”
“啊,那件事啊。”我仔细的想了想。“那次不就是你在海面上造出冰道还被发现,拖着受伤的前室友一起逃出生天的事情吗?”
那个时候,要不是她那么努力,我才不会提醒她呢。
“是啊,我差点就晕倒了。”贝丽卡说。“嘛,人品问题,如果不是我找到那个小岛的话我会撑不住的。”
现在总算没有什么不好的事情了,但是总觉得很无聊,除了看书就是看书。
“喂,你不觉得无聊吗?”我这么想着,继续问贝丽卡。
“什么?”
“你想一下,是每天看书打发时间,还是出去闯荡好一些?”
“如果是令人感到愉悦的日常的话,我想我会接受。”贝丽卡坐起来,认真的对我说。“当然,我也会了解一些新事物,不然我可能会觉得枯燥。”
“氷,现在我的我有伙伴们,即使没有他们至少还有你在陪着我,这样就足够了。”
“以前的我如果不能走出那种寂寞感,我也不会有机会来到这里。”
“虽然我也怀念能够有机会在外面经历事情的时候啦。”她微笑着,见我没说话,先是在我眼前挥了挥手,然后拿出了打火机。
“喂你干什么?!”我自然被吓了一跳,立刻飞到了空中。
“你没在听,所以我吓你啊。”贝丽卡笑的很令人害怕。“你想什么呢?”
“当然是米白的事情啊。”我说。
“如果我和米白打一架,你看怎么样?”贝丽卡问我。
等一下,她是不是说和米白打一架?
“你你你你要干什么…”
“打架啊。我们去训练场就可以了。我觉得她应该是打架时遇到了什么事情导致失忆的吧。”
也对,现阶段最令人记忆犹深的事情,只能是在谈判船上被侵染者袭击的事情吧?连贝丽卡都差点在潜水艇里昏过去,那些侵染者应该会对她,或者她的朋友干了什么很过分的事情才对。
“嗯,我没意见,你们注意别受重伤就是。”
贝丽卡走向米白,她们说了什么我没听到(主要是因为我离她们太远),估计是打架的事情。
我只听到,一片寂静后米白的声音。
“请多指教。”
箱子☆
箱子。
箱子可是好东西。
他蜷在箱子里头这样想着,纸箱的边缘碰触着他的身体。
猫喜欢箱子,猫又也不例外,他安定地甩了甩自己的两条尾巴,打了个哈欠把脑袋搁在箱子的边缘。
今天的天气着实不错,明朗的阳光落在院子里,空气里都没有任何尘埃。
他满意地蜷起身体,两条尾巴在半空中微微一晃就变成了一条――活了这么长时间,这点本身他理当拥有。
深谷辽满意地舔了舔自己的爪子,猫又们时常都不会记得自己的年岁,他也一样,时间在漫长中失落成了“这么长”这样的词汇,毫无意义,并且被轻而易举地抛在身后。
“哎,还真是无聊啊。”他叹息着说,闲得发慌这个词恰如其分地消失在了隐藏起的尾尖,“虽然也算是悠闲啦但是真的闲下来就觉得有些无聊啦――?”
原本就不打算说给任何人听的话语就这样消失。
他轻声笑了笑,在箱子里转了一个方向。
箱子。
还是箱子最好了。
他知道哪里可以找到箱子。
在这个路口左转有一个院子,院子的主人似乎姓公孙,名不详,反正就是那么样一个人,女孩子,经常出现在院子的角落。
她喜欢猫,在她的院子里有很多个猫食盆,随着时间推移又多了许多猫喜欢的玩具。
其中当然有箱子。
他喜欢箱子,他当然知道这里。
猫又标志性的双尾被藏起了一根,黑色的野猫慢悠悠地混进了野猫群中。
……哦,不对。
他无声地抿起唇对自己笑,吐出的言语演变为呢喃只有自己才能听见。
“野猫可从来不能以‘群’论啊……”
深谷辽就这样走进了院子中。
很不幸,今天的箱子已经有人捷足先登。
他站在墙上看着那只箱子里的猫,后院里的玩具不少,不见得每个都有野猫光顾,他跳上一边的架子,居高临下地注视着整个院落。
箱子被占领了,逗猫棒那头有只野猫玩累睡着了,金鱼缸前头的那只黑猫,是新来的吗?
“还真是糟糕啊。”他伴随着呼吸喃喃自语,阳光的温暖从脊背一直扩散到了尾尖,“看样子我来迟了?”
没有人回答,所以他自己回答了自己:“下次得来早一点——嗯,不、还是随缘吧。”
反正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事情不会有改变,就算他努力也改变不了什么。
深谷辽蜷在架子上,打了个哈欠。
他喜欢这种姿势,体温明晰地传递给了他自身。
猫的体温一向很高,它们也喜欢温暖的地方,而有时,最为温暖的就是他自己。
深红色的眼睛在阳光下似乎也变淡了颜色,他打了个哈欠,一眼瞥见院子的一角、一个空着的蛋糕盒孤零零地被留在那里。
只剩下一根的尾巴甩了甩。
他喜欢箱子。
喜欢在箱子里蜷起身体。
箱子可是个好东西。
……不。
然而神经深处有什么东西发出了警告。
他扭过头,正巧看见院子的主人打开了房门。
那个被他们称为公孙的女孩给猫粮盆添上了食物,野猫们发出了一阵骚动。
箱子里的猫跳了起来,它们可要在那只贪吃的野猫到来前吃到属于自己的一份。
深谷辽跳下了架子。
猫爪上的肉垫将落地的冲击轻巧地吸收。
“那我就不客气了——”
他这样说着,自顾自地占据了纸箱。
——果然,还是箱子最好了。
深谷辽心满意足地蜷在了箱子中,瓦楞纸的外壳散发着独有的气息。
他嘟囔着一些什么把自己整个缩了进去,脑袋搁在纸箱边上,发出舒服的“呼噜”声。
阳光正好。
深红色的眼睛眯起,他安然地想着。
既然这样无聊一点也没有什么关系吧——
他打了个哈欠,呼吸里满是青草的味道。
反正岁月静好。
喵生安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