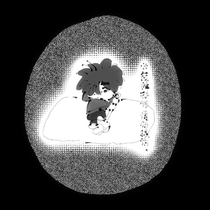评论要求:笑语
那不过只是一艘地中海上的短途游轮。
她曾经在那么一小撮人中小有名气,珍珠安妮号,号称拥有地中海上最上流的服务和配置,是奢华的代名词,她不会在乎那些没有听说过她名气的人。
但她终将要在全世界的人们心中瞩目,带着她华丽的裙摆和曼妙的舞姿,以另一种方式,完成她的绝唱。
那不过是一次求救,来自这位地中海上的明珠,而那天,地中海上晴空万里,波涛美得如同王冠上的宝石。
当人们赶到时,只剩下了她支离破碎的身体,混合在三头灰鲸,以及数万条破碎到难以分辨的鱼组成的漂浮物中,填满了目光所能及的全部海面,她高贵的闪着彩虹色光泽的血,混合着和鱼群的血液一同,如同舞女的裙摆在海面上绽放开来。
那本该是一次寻常的求救,如果是那样该有多好。
三天后,第二艘死状相同的渔船出现在新加坡附近,紧接着是第三艘,第四艘……残骸上爬满贝壳和藤壶,船桨上缠满了被打成糊的章鱼,排水口堵满水母,船身外壳上插着脊柱断裂的死鱼,和它们散布满海面的同胞一样的死法。
一个月后,人们终于找到异变的中心,那是南太平洋中的某个区域,途径那里的生物仿佛染上了什么病毒,而后在迁徙的过程中又将它扩散开来,使得整个海洋变得极具攻击性。
联合国派出军队和科考船潜前去探查,然而在抵达的当晚整个队伍便失去了联系。救援抵达时,船依然还和他们出发时一样崭新,而甲板上躺满了像猿猴般自相残杀的人们,但是他们也带回了影像。
那是在浅海与深海的交界处,光影在此处模糊了界限,然而在过往记录中本该空无一物的海水中,他们看见了一团五光十色的东西,只是初步估算,那个东西的长度就已经接近两公里,宽一点五公里。摄像机拉进时他们才看出那是成千上万不同种的水母,从寻常的海月水母,到深海的冥河水母,它们的身体边缘已经模糊消融,连为一体,触须之间紧密缠绕,构建出如同神经网一般的矩阵,一道又一道光在触须间传递,到达神经末梢,这时所有人才看清,那里缠绕着无数条鱼。
下一秒,所有的鱼一起回头,目光对上了摄像机。
阿莱克计算着这个世界在毁灭前还有多少时间。
第三匹马车经过店门前的时候,服务生为他端来一杯咖啡,然而阿莱克只是端起来就放下了杯子。甜腻的味道昭示着咖啡里面加了最新进的一批诺炎花,新到这些花甚至都没有窖藏到成熟的地步,独具特色的酸味完全被甜腻的花蜜掩盖下去。
于是他把这杯咖啡推到刚刚坐下的罗伯特面前。
“只是推给我?”过于甜腻的味道让罗伯特也皱起了眉头,“真少见,你竟然没去打店长一顿。”
“看在这是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天,这点冒犯我可以原谅。”阿莱克展开报纸,油墨的香气随着清晨的一缕海风飘散。从咖啡店这里能够俯瞰港口,白色的海鸥盘旋在近乎黑色的青色大海之上,这时第一批出海的渔船已经归航,浅黄色的风帆飘扬在水面上。
淑女们撑伞走过,裙摆于风中摇曳,搭着车夫的手缓步登上马车。小贩沿街叫卖,卖花的姑娘拎着篮子,妄图能够在大剧院门前卖出个好价钱。
“你还是舍不得吧。”罗伯特突然说。
阿莱克回了他一个你解释解释的眼神。
“最后一天了,还点诺炎花咖啡。”甜香的味道熏得罗伯特有些烦躁,他把半凉的咖啡推到一边,“现在市面上早就不卖你想要的那种酸味的诺炎花咖啡了。”
“一时兴起而已。”
“……但你连续这么干了三年。”罗伯特就差没把阿莱克的报纸扒拉下来了,“一边发动世界毁灭计划一边找酸味的诺炎花咖啡?”
“那是我的个人爱好。”阿莱克终于把报纸收起放在桌上,身体前倾,眼神对上罗伯特的,“工作之余我也要享受生活。”
那语气真诚到几乎是真的了。罗伯特嘀咕着:“狗屁的工作。”然后他起身准备出门。
“不喝一杯再走吗?”
“我得去看看你又从海里引了什么怪物上来。”
“走好。”阿莱克展开报纸,挡住了罗伯特瞪过来的视线。
三分钟后,伴随着十字路口一辆翻倒的马车以及混乱的呼救声,这成为了他们说过的最后一句话,阿莱克的倒数在这一刻终于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