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十一招】宅斯特
评论:随意
“抱歉,所以你的意思是,因为主张‘怪谈是不存在的’,所以加入了怪谈社?”吴炆露出一个疑惑的表情,看着眼前申请入社的少女。
“是的。因为怪谈……”翟芊芊歪着头,面无表情地思考了一阵。
思考了一阵。
“……是不存在的。”翟芊芊收回目光,看着吴炆点了点头。
“哈哈哈哈……”坐在社团活动室一旁玩手机的女孩忽然笑了出来。
“呃……那,这个‘不存在’该怎么理解呢?啊,欢迎加入怪谈社。”吴炆把报名表收进抽屉。“社费20元,扫桌上那个码就行,谢谢。”
“社费一般是用来作为车旅费,去调查存在怪谈传闻的地点。”坐在一旁的少女收起手机。“我叫白叶,是副社长,你好哦!”白叶笑着对翟芊芊打了个招呼,她有着浓艳的妆容和挑染的紫色刘海,一眼看上去很难让人把这位精神小妹和985、211高校联系在一起。
“嗯,社长好。副社长好。”翟芊芊向二人点头问好,依旧面无表情。
社团活动室不大,只有十几平方米。怪谈社和围棋社共用一间活动室,但是围棋社的人几乎不会在活动室露面,他们更多地选择在自习室或者中心花园中进行活动。
“如果把怪谈分为概念和现象的话,那从概念角度来说,怪谈可以从神怪故……”翟芊芊忽然停了下来。“社长要听长的还是短的。”
“叫我吴炆就行。长的会很长吗?”
“会很长。”
“那短的吧。”
“好。”翟芊芊点了点头。“怪谈是不存在的。”
房间静止了8秒左右。
“没了?”
“嗯。”
“哈哈哈哈哈……”白叶在一旁捂着肚子笑成一团。
“呃……”吴炆挠了挠头。“我们倒也没什么坚持或者主张,只是大家讲讲鬼故事出去探访一下出现怪谈的地点,和春游差不多……”
翟芊芊的面无表情让吴炆搞不懂她是在认真听讲还是不置可否。
“社费不退了哟。不过我可以请你喝奶茶。”白叶笑眯眯地看着这位新社员,一副饶有兴趣的表情。
翟芊芊歪着头思考了一下,说:“谢谢。这样就好,我没有退出的念头。”
吴炆笑了笑,说:“这周六有社团活动,我们去博阳路46号那边,最近红小书上在传一个伪人的怪谈……”
“啊,不去也没问题。我们社团很自由的。”白叶随意地摆了摆手。
“我会去的。”翟芊芊微微点了点头。
周六14点。博阳路地铁站。
吴炆和翟芊芊差不多同时到,等了十分钟左右,白叶也到了。
“整理一下情报……”白叶划着手机屏幕,一边往前走一边向两人进行解说,新做的指甲在阳光下色彩斑斓。“这次的怪谈和一般网上的怪谈故事相比,有两个不太一样的特征。其一是发布源并非灵异领域的博主,而是本地city walk博主,在偶然向路人搭话的时候聊起的事件;其二有复数个被随机采访的路人都提到了这件事……啊,买个奶茶吧,芊芊喝什么?我请你。”
“柠檬水,全糖。谢谢。”翟芊芊的面无表情不受时空环境影响地维持着。
“我要青梅绿茶。等下微信转你钱。”吴炆看了看奶茶店里等着取单的人,在门口找了个椅子坐了下来。
“要我说,应该是节目效果吧。博主为了话题性所以加进去一点小小的灵异元素之类的……”白叶熟练地扫码下单,然后在门外的吸烟处点了一支烟。
“去逛一圈完了吃个咖喱吧。那附近好像有个还不错的咖喱猪排饭……”吴炆悠然地靠在椅背上,刷着大从点评。
翟芊芊站在一边一言不发,在看上去耐心等待和看上去显得拘谨之间选择了看上去琢磨不透。
博阳路46号是一个写字楼,因为沿街而且地段好,里面充满了私家厨房、美发沙龙、律师事务所、桌游吧、烘焙坊等各类企业和商铺。
三人上了电梯,按下了9楼的按钮。
“传言是说在9层楼梯间,有概率见到跟自己长得很像的人,但是跟对方说话也不会有反应,只是会站在那里看着你。但是当你再一转头,对方就不见了,像是凭空消失一般。”白叶吸了口手里的噗噗脏脏芋圆珍珠奶茶。
“像是从那种‘遇见了世界上的另一个自己’的元故事来的……”吴炆掏出手机简单搜索了一下。
“芊芊害不害怕?”白叶看了眼一路上都没怎么说话的翟芊芊。
翟芊芊叼着吸管摇了摇头,说:“不害怕。”
9层的电梯间写着各室的标牌,这里有一家传媒公司,一家健身房,一家观影咖啡厅,一家陶艺工坊,一家外卖寿司店,以及一些没在电梯间挂名牌的房间。
“怎么有四个楼梯间……”吴炆看着楼层结构图。“这应该远超出消防安全标准了吧……”
“应该是风水方面的考虑吧……啊,网上好像是有这样的说法。”白叶盯着楼层结构图看着。
“我去问问这里的人。”翟芊芊向正对着楼梯间的观影咖啡厅走去。
“那我去上个卫生间……”吴炆走向远处的一侧。
吴炆在走进卫生间前回头看了看,见二人都没有跟上,于是转头钻进了旁边的楼梯间。他看见一个身穿偶像团体T恤和休闲短裤的男性站在楼梯间看着他。
“哟,你这T恤……你也是AAOO的粉丝啊,这都能遇到同好!”吴炆笑着向那个人搭话。
“对啊对啊,我也是AAOO的粉丝,这也太巧了。”那个人笑着向吴炆点了点头。
“你是从哪场的时候开始追的啊?”吴炆靠在了楼梯扶手上,攀谈了起来。
“我是……哪场的时候开始追的来着……”那个人歪着头开始思考。
“确实,时间久了也容易记不清。你推的是谁呀,还是团推?”吴炆从口袋里摸出一粒润喉糖,放进嘴中。
“我……我没有推,没有人掉下去……”那个人也在摸索着口袋。
“大罗天罡,弗弗阴阳,玄火焚煞……急急如律令!”吴炆念出拗口的咒文,面前的空气中忽然爆出一团火焰。火焰沿着空中不可见的轨迹向吴炆对面的男人迅速爬行,静默却猛烈地点燃了此人的全身,猛烈吞噬着他和他周围的空间事相。
被点燃的人没有叫喊,只是仍摆着摸索口袋的姿势被火焰吞噬着。四秒左右后,火焰和被其包裹着的一切凭空消失,只有空气中的一点余温证明着刚才它们存在过。
“还好来得早,都会学人说话了。”吴炆自言自语着。“我的这个秘密,可不能让别人发现了……”
白叶看着吴炆和翟芊芊走开,转身推开防火门,进了电梯间深处的楼梯间。她看见一个挑染着紫色刘海,挎着蓝色痛包的女性站在楼梯间看着她。
白叶盯着这个人,从挎包里摸出一个化妆镜,打开后确是一个风水罗盘。
亥坤午……酉丙乙癸巽……白叶熟练地拨弄着罗盘上的各层转轮,一个白绿色的虚影像幻灯片一样投影在她的身后墙上。而对面的人也跟白叶学样拨弄着手中的化妆镜,却什么都没发生。
虚影渐渐清晰,那是一只白色的四蹄兽,有着晶莹透绿的毛冠和弯曲成美妙弧形的双角,但是嘴巴上交叉贴了两张写着“封”字的符纸。
“白泽,上。”白叶紧盯着眼前的人,刷了睫毛膏的眼睑一眨不眨。
白泽的投影从墙面上放射而出,冲向对面。投影映射在对面的人身上和后面的墙壁上,形成了两个层次,就好像放电影时有人在大荧幕前走动一般。说时迟那时快,那人身上的投影边界开始消失,平滑地与墙壁上的投影合二为一,再看那个人,已经从原地消失不见。
“回来吧。”白叶点了点头,收起了手中的罗盘,对面墙上白泽的投影也一起失去了痕迹。
“又解决一个怪谈。”白叶吸了口奶茶,看了看紧闭着的楼梯间防火门。“我的事要让别人发现可就麻烦了……”
翟芊芊在店铺门口站着,两人很快赶来回合。
“怎么样,店员说什么没。”吴炆双手插着兜走来。
翟芊芊说:“店员说,他听店长提起过,但是她没亲眼见过。我们应该更多收集信息吗?”
“啊,我刚才去那边的楼梯间看了一下。”白叶指了指电梯间的安全出口。“那个楼梯间什么都没有,而且好脏……”
“嗯。”吴炆挠了挠头。“我就说什么都没有吧。我觉得也不用打听,一起去看看,没事就闪人去吃咖喱了……”吴炆的语气中透露着轻松,像是内心中知道问题已经被解决了,有着根本就不怕被人检查的余裕。
“确实哦,还是去看看最直接。”白叶把喝完了的奶茶丢进垃圾桶,拍了拍手,像是刚刚解决一件难题,有着已经完全没关系了的自在。
“好。”翟芊芊点了点头,像是面无表情是她唯一的表情一般地面无表情。
三人来到电梯间的安全出口楼梯间,打开了门,空无一人。
三人来到了卫生间旁的楼梯间,空无一人。
三人来到了楼层另一侧的楼梯间,防火门闭着。
“肯定没问题。”吴炆说。
“啊?难道会有什么问题吗。”白叶笑了笑。
翟芊芊打开门,空无一人。
三人来到了最后一处楼梯间,它在大楼远端的深处。也许是因为刚好在阳光照射不到的地方,也许是因为久未打扫,又也许是因为这里有个中央空调的出风口,总之这个楼梯间的入口前散布着一股更为幽森的气息。如果说其他几个楼梯间周围的环境都像是通往温室的花园小路,那面前的这个楼梯间附近的气场就像站在什么魂类游戏BOSS的雾墙前。
“最后一个,赶紧看完走了走了……”吴炆不经意地轻轻皱起了眉头。
“这里怎么有点冷……”白叶下意识地挑起了一边眉毛。
翟芊芊打开门,走了进去。门的弹簧很重,啪的一声迅速弹回关上。
吴炆和白叶几乎同时冲上前去,再一次打开了厚重的防火门——
只有翟芊芊一个人站在那里,依旧是面无表情地看着二人。
“怪谈是不存在的。”翟芊芊面无表情地说着。
三人去吃了咖喱猪排饭,坐地铁回家。
白叶在地铁上一边用手机P图,一边和翟芊芊交谈着:“看不出来芊芊还挺外向的,主动会去跟陌生人了解情况。”
翟芊芊歪了歪头,思考了一下,说:“一般的人类,都是会这么做的吧。”
吴炆抓着地铁拉环,看着张芊芊白皙的脸庞,说:“芊芊是因为不害怕,所以会主张怪谈不存在,还是因为认为怪谈不存在,所以不会害怕这些?”
翟芊芊歪着头思考了一阵,说:“不是后者,因为有的东西会因为其‘存在’而害怕,也有的东西会因为其‘不存在’而害怕。也不是前者,因为我害怕不害怕,和怪谈存在不存在,没有必然联系。”她把头回正,看着吴炆说。“总之,怪谈是不存在的。”
“如果怪谈存在的话,会发生什么吗?”白叶抬头看了翟芊芊一眼。
翟芊芊摇了摇头说:“如果怪谈存在,常理的膜就会被感染,会变成存在怪谈的世界。”
“就是说,兹要一点儿怪谈都不存在,都不会有一点儿怪谈存在是吧。”吴炆笑了笑,但心里暗暗对翟芊芊在意了起来,因为她说中了这个世界正在被怪谈入侵的现状。
“可是如果大家都承认的话,就算你一个人自己不承认,也没有用呀……好,发送!”白叶把终于P好的照片发到了朋友圈。
“怪谈是不存在的。不管是谁,不管相不相信怪谈,都不应该相信怪谈的存在。我会否定怪谈。”翟芊芊依旧是面无表情,但白叶似乎读出来了一点执拗的味道。
“对了,我问你们个问题……”吴炆露出一个微微难堪的表情。“我的眼睛是很小吗?我觉得还行吧?没有那么小吧……”
翟芊芊回到家时太阳刚刚落山。在她进门正准备开灯时,手机忽然响了。是白叶发来的消息,她说:芊芊,你身边有没有什么遇到那种怪谈的人,或者你自己有遇到过吗?
翟芊芊很快地回了消息:没有。怪谈是不存在的。
回完消息后,她收起手机,打开灯,和房间内另外23个自己一起平躺在地板上,等待第二天的到来。
同人,纸房子,xmm
想了想还是没写成限制级(也不会写((#`O′)
免责:随意
徐敏敏看人的时候总像在笑,就像她对所有人的态度一样,轻飘飘的,说不上是善意或者是温和,但也不带什么贬损。而这一点是赵颖最感到痛苦的,这也许是赵杰在她身上留下的伤疤,她最无法接受的就是这样空洞而不带痕迹的目光,喜欢或是讨厌都没有关系,可为什么这样什么都没有?
那个时候她还不知道徐敏敏的名字,但她总想起她,这个女人莫名其妙地出现在她每一个丢脸狼狈的现场,不用多说一句话,就让她轻而易举地选择跳进海妖的领域之中。
陈水是个小县城,但也不乏那些出格的铁t来彰显自己和其他人不同的样子,她的宿舍里就有一个,赵颖并不评判他们什么,她本来就不记得人脸,泛泛人潮里何必有那么多能让人记住的东西呢?
但徐敏敏不一样,徐敏敏就像是她幻想出来的东西一样,书里不是说什么青春期小孩的幻想朋友吗?徐敏敏就是了。
“我可不是你幻想出来的。”徐敏敏看了一眼厨房里还掂着条草鱼的赵颖,突然说道,声音被烟雾绕住,让人听不真切。
简直像读心一样,赵颖在心里回答她,她能感受到徐敏敏的视线落在她身上,平静的、不留下任何痕迹,却轻而易举地让她的疤痕开始发烫。赵颖讨厌这种感受,她更讨厌徐敏敏,如果有新的幻想朋友的话,总要第一个丢掉这个家伙。
但她没有回答徐敏敏莫名其妙说的话,只是专心致志地处理那条草鱼,在菜场买的时候鱼贩已经给这条鱼掏了膛,她则把鱼腹里的黑膜撕干净,鱼还算新鲜,黑膜撕的时候也就不会很困难。她手上沾着鱼腔内残余的血,不知道为什么想起徐敏敏的手,徐敏敏的手算不上好看,但足够苍白,所以沾上其他的颜色就会很突出,她突然想看徐敏敏手指被折断的血腥景象,又知道这种一瞬闪过的想法算不上可以展示出去的健康产品,徐敏敏做饭又实在是让人难以下手,连个低劣的代餐场景都无法设计出来。她忍不住笑出声来,为自己这莫名其妙的想法。
徐敏敏在抽油烟机底下吐出最后一口烟,其实她之前从来不考虑在哪里抽烟的,但看着赵颖做菜很有意思,赵颖看起来不像是厨艺很好的样子,她发色浅,又老是臭着一张脸,像所有人都欠她一包烟一样,很难想象这样的人在厨房里会乖乖地按照流程做菜,甚至口味还相当不错。不过也不算奇怪,就像赵颖这个人一样。
徐敏敏觉得自己算不上很喜欢赵颖,她只是觉得这个人有点意思,她和很多人上过床,男的女的都有,但和未成年上床的机会不算多,赵颖算是自己跳进来的,她也就懒得拒绝。有的时候她会觉得赵颖想把她杀了,尤其是在床上的时候,赵颖下手没轻没重的,偶尔她看着赵颖的眼神落在她前胸,再往上看,停在她的脖子那,然后久久地没挪走。赵颖太有趣了,如果是她的话,早就掐上去了,她这么想过。
不过也可能也不会吧,她靠着厨房的门换了个姿势,悠然地想。都无所谓的事情,到时候自然有自己的答案就是了。
她丢掉已经灭了的烟头,贴到赵颖身上去,头搭在赵颖的肩膀上,兴致勃勃地看着赵颖继续处理这条鱼,赵颖在用刀刮鱼鳞,刮得整条鱼惨不忍睹,鱼鳞一部分拖在刀上,一部分顽固地留在鱼皮上,剩下的四散天涯。她一时兴起地从赵颖腰边划过去,手落在鱼皮上,赵颖没反应过来,刀就蹭到她的手指,划出一道明显的伤口。
这下倒真是有些血腥和残暴了。赵颖愣了一下,拉住徐敏敏就去冲水,破碎的鱼鳞和新鲜的血液混杂在一起,在苍白的手里展现出诡异的生机,徐敏敏还在笑,赵颖倒是有点急,语气不算太好:“你在干嘛?没看到我在用刀啊,就这么凑上来?”
徐敏敏还是一副不当回事的样子:“觉得好玩就试一下了,嘶……你轻点,有点痛。”
“你怕痛?”
“你不是早就知道我怕痛吗?”
赵颖有时候真会觉得对徐敏敏这种人没什么好说的,她动作粗鲁地拉着徐敏敏到了客厅,拿出碘伏和棉签,真碰到她的伤口的时候又还是收了力。徐敏敏还是那么淡淡地笑,赵颖听不出来她想说什么,也懒得再思考这空空如也的容器到底想传达些什么,她只是想亲她,于是她说:“我想亲你。”
赵颖闭着眼睛亲她,她已经习惯和徐敏敏的亲吻了,徐敏敏看着赵颖,轻松地回应着她的亲吻,用另一只手牵引着赵颖的手,虚虚地来到自己的脖子上。赵颖绕着她的脖子环绕一圈,像掐住她,也像是抱住她的头颅,更用力地亲了下去。
徐敏敏,你真的是幻想朋友也没有关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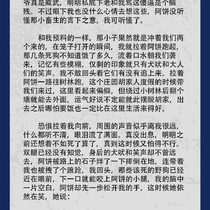





7.雪中求炭——斯塔哈•赫尔墨斯
“咚”“咚”“咚”
棒球棒敲击的声音有些沉闷,就像沉水的铁箱受到水压而扭曲发出的脆响
面前的尸体已经逐渐失去鲜血和温度,殷红染过了我的衣服,没有一丝温暖留在上面
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忍住,我不清楚自己为什么想要杀他
只是在我印象中,那个因为我不小心切菜划伤手指而破碎的夜晚
被藏匿起来的漆黑深夜中,这个人藏在血雾后面,与周围的漆黑格格不入的是,他是一身白衣
我的大脑在看到他的脸的瞬间就警铃大作,明明我们应该是见过一面的关系,而他却依旧能平静的对我微笑,轻声说道
“一份炸鸡,和一个汉堡套餐,谢谢你”
为什么能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样子呢,我不解的看着他坐在椅子上安静的享用他的最后一餐
为什么能装作若无其事呢,明明我的手沾满鲜血了,明明地面已经一片血海了
明明还在擦着枪管?明明还在和人交谈?明明还在指着地面大笑?
为什么能做出从未经历过这些事的样子呢?我目送着他走出了店面
我看着那张好看的脸从疑惑,到愤怒,到惊惧,到最后变得布满汗珠和眼泪,跪在地上开始求饶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杀他,我在清醒的时候无数次向我的大脑提问
杀了他对我有什么好处?什么都没有。杀了他能改变什么?什么也不会
似乎有些事情就是发生了,但我不记得
只有我的双手还在跳脱着攥紧了球棒,我想,或许他是那晚切割我的手指的菜刀吧
如果他能多说点什么就好了,我看着他慢慢的转过头去,缓慢的起身,就连他身体的抖动都一清二楚,他想逃离这个垃圾堆,只是他的动作太慢了
如果他能多说点什么就好了,对不起啊,我错了啊,我不该开枪的,我不该和他们一起做这种事的
我不该杀人的,我不该这样做的,我不该把你的———
“砰”或许是有几颗牙飞出去了吧,我对着他的后脑一挥而下,他很快就没了声响,溺死在了自己渗出的血海里
而我的手没有办法停下来,就像呛水的人一样,我的手臂不断的扑腾着
“砰”“砰”“砰”
好冷啊
当我终于停下来的时候,面前已经变成了一片白骨的山谷,血肉的礁石组成的猩红的大海,我的眼前有些发红,身上的味道有点难闻,沙拉酱和炸鸡块的味道,还有服装店说不出来的淡香味早就被腥臭的腐烂的味道包裹,我变成了深海里的一具死尸
好冷啊
我不知道自己想要追求什么,也不清楚为什么要这样做,我熟练的清理起这片大海的蛀虫和遗骨,海水并没有带给我温度,也没有唤醒我的大脑,只是让我在这份不知名的情感中反复翻滚,我的大脑无法给我答案,双手也无法给我,求助于他人也无法收获任何的东西,看来这次又是做白工了
好冷啊
处理好血海之后,我有些恍惚,不知道是夜晚的风太冷了,还是自己失温,我感觉手脚有些发麻,头脑发昏,身上莫名流出的汗和迸溅的海水混在一起,血红色的留下来,歪斜的灯光下,白色的西装已经变了色,但就算是暖色调,我依然感觉自己不住的发颤
我讨厌这种心底的不安和耳边的鸣叫声,我的大脑不停的拉住我的缰绳,但这就像一块沉重的石头不断地将我向下沉去,而求生的本能让我迈开双腿挣扎着上岸,海风让潮湿的衣服裹住我的身体,我抱着头蹲下来
好冷啊
我有些记不清怎么走到的街上,今晚格外的安静,月亮早就撑着脸在天上看了许久,和我一样没有温度的空骸骨恐怕早已被它带走了灵魂吧
我摸着墙漫无目的地走着,突然,熟悉的吉他声从遥远的地方吹进了我的耳朵里
————斯塔哈女士坐在她常去的酒吧门口整理着吉他弦
看样子应该是刚和一起演出的人分开吧
她一边轻哼着一边整理着吉他箱,或许很快就要离开了
我站在阴影下注视了一会儿
熄灭的篝火,我想着
就像即将被最后一桶水泼灭的篝火,她的声音仿佛灰色的烟尘,飘在空中,为我这个即将冻死的可怜鬼丢出了信号弹
我可以去依靠那把火吗,但它很快要消失了
我的手似乎要扣进手边的墙皮里,而我的腿又迈出了一大步
溺死吧,求救吧,看一会儿吧,走近些吧
她抬头了
我看到她的口型,好像是要说什么,但我只在靠近她的一瞬间就晃神了,有点听不到,我的大脑仿佛在海里浸泡太久了,除了一些回响,就像关在铁箱里一样沉闷
这下糟了,我想着,我记得她不许我伤害尸体来着,而我现在背后的吉他包里还装着那个沉甸甸的沾满血的棒球棒,如果她问起来,我可没有什么借口搪塞过去
我看着缓慢跳动的火苗,暖意忽的挣扎着从柴火堆底冒出来
一条雪白的毛巾赫然出现在我面前,对于看了一晚上红色与黑色的我有些刺眼
“有些事”我听到她的声音终于变清晰了,“不想让别人看见,就不要留痕迹”
“拿去擦擦吧”我接过那个带着一点点鸡尾酒香气和木头湿漉漉的味道的毛巾,顿时觉得指尖重新染上了一丝温度
“血腥味有点重”她说。那用这个盖住不就好了,我直接把毛巾蒙到了头上
“好好休息,你这几天别去打工”我擦完了头发上的水滴
“今天雨很大,回去洗个热水澡吧,小心感冒”我擦完了脸上的螺肉与海草
“我差不多也要回家了”我打了一个冷颤
柴火的咔咔声变得支离破碎,好不容易找到的温暖山谷很快要淹没在黑夜的寂寥中
先别那么快熄灭,至少等我暖完身子
先别那么快消失,至少等我清醒过来
先别那么快离开,至少等我……
“斯塔哈女士”我想握住这份身体仅能感受到的热度
她停下了动作转头看着我
“我想我的头上应该没有沾上血迹,脸也没有”我小心翼翼的拨弄着木头,企图再找到一点跳动的火舌
“是的”山谷里传来轻柔的回音,与外面哭嚎的冷风顶撞着,包裹住我的耳朵
“擦得很干净”
“那么…可不可以…”我紧紧攥着还没有被浇灭的木炭炭块,试图把它们揉进身体里
“请您摸摸我的头”
我想斯塔哈女士应该是沉默了一下,但她依旧抚上了我的发丝,我感觉到那块曾经被我认为烙铁一般可怕的手掌变得细腻轻柔,盖在头顶是如此温暖,仿佛熄灭的篝火滚落的火种,从头顶滑进心底,烧断了束缚着我的沉重巨石,熔毁了锁着我的闷重铁箱
我的耳朵终于听得真切了,我听到没有温度的风吹来,但因为我的怀里有着一团炭火,我不再发抖了
“回去吧”我听到她轻轻说,无比真切的声音,像休闲的沙滩边,海螺里清透的回响
“嗯…”
“谢谢您”
哈,不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