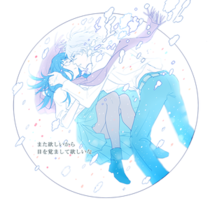说明:
第五章日常搜查游戏补档。原档已删。
五章案件日常探索方法较为特殊,采取使用游戏软体进行探索的方式。
【【【日常含有大量线索,可能会在案发后学级裁判当中要求出示截图作为证据,请想要推理的各位务必玩过】】】
游戏本体地址:
1.0ver
微盘:
http://vdisk.weibo.com/s/zfqy9ZAeOxcQD
各位玩家也可通过群文件下载本体。
游戏内容为:玩家操作NPC见取神加在5L进行的探索。探索时长为1日。
由于制作软件问题,游戏※不可能※与弹丸论破原作类似或者有同样的机制,只是一个简单粗暴的R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