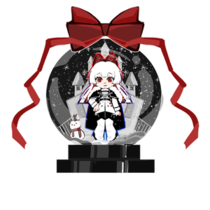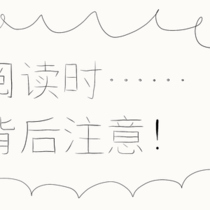

平凡的人只能做好一件事,而天之骄子却可以做好每一件事。
当周围出现越来越多看似无所不能的“多面手”时,冬月惠总是会陷入短暂的自我否定。
就比如现在,她再一次将写满字迹的草稿纸揉作一团扔进垃圾桶,长叹了一口气后取下了眼镜。暖黄色的台灯下,她的眼圈微微发红,也不知是困乏所致还是情绪所致。椅子侧边的垃圾桶里已经堆满了废弃稿纸,好似对无才之人的嘲笑。
星奏戏剧社的演出剧本向来由戏剧社的成员来撰写,社团中不乏乐器、表演、文学样样精通的精英学生,每一次在社团征集剧本时,那些人都能拿出自己的不俗的作品来。这是冬月惠十分羡慕的事——扮演自己所创作的剧本中的角色。
可她到底不是上帝的宠儿,别人轻而易举就有的创作灵感,她冥思苦想也得不到半点,别人落笔有神的文字,她绞尽脑汁也挤不出几个。
眼看着明天就是提交原创剧本的最后时限,她仍是拿不出一份让自己满意的作品,想来这次也只能放弃了。
冬月惠从桌旁起身,转身呈大字倒在床上,看了天花板数秒后,摸出手机侧过身去,开始浏览社交平台上的消息。她有在网络上分享一些东西,时不时也会从路过网友那里得到有用的评论。不久前她曾分享了一个改编《蓝胡子》的剧本故事,如今下面有不少回复。
这个改编的故事是这样的。
主角是一名贵族公爵,因为他长着蓝色的胡子所以被称作“青须公爵”。这位公爵的样貌奇特,性格诡谲,但拥有着庞大的财产,住在豪华的城堡中。他曾娶过很多任妻子,但每一任妻子最后都下落不明,尽管如此仍有很多向往富贵的人将女儿嫁给公爵。在剧本的开头,有一户富贵人家的小女儿被迫嫁给公爵,小女儿叫琳达,长得十分美丽,她上头还有一个姐姐跟一个哥哥。琳达并不愿意嫁给可怕的青须公爵,但为了保全家人她不得不嫁,好在恐怖的青须公爵经常不在城堡,她不需要日日担惊受怕。
琳达嫁给青须公爵后,某日青须公爵要出远门办事,离开前留书嘱咐琳达,不可以进入地下室的小房间。但这样的嘱咐却助长了琳达的好奇心,最后琳达偷偷进入了地下室。在地下室里,琳达看到了血腥的场景,地面上满是血迹,天花板上吊着好几具女人的尸体。琳达被吓得不轻,就在她惊慌失措的时候,一个穿着红裙子的女人来到她身边,带她离开了地下室。那个红裙女人告诉琳达,她叫作特蕾莎。地下室里挂着的女尸都是青须公爵的前几任妻子,她们都是被青须公爵杀害的。特蕾莎说自己是城堡的女佣,想要帮助琳达离开这里,否则琳达会成为新的受害者。但就算青须公爵不在,城堡里还有各种守卫,琳达想要逃离并不容易,特蕾莎便提出自己可以帮忙。琳达让特蕾莎去城堡外找自己的哥哥来救自己,然而还没等特蕾莎回来,青须公爵已经回到了城堡,他发现琳达进入过地下室,而且正想要逃走,非常愤怒,决定立刻杀掉琳达。琳达情急之下喊出了特蕾莎的名字,没想到青须公爵听到特蕾莎的名字后变得更加异常,直到特蕾莎再次出现在地下室中。
特蕾莎其实是青须公爵的第一任妻子,也是青须公爵所爱之人。她早在很多年前便死去了,是被嫉妒她获得青须公爵喜爱的其他女人毒害的。而失去爱人的青须公爵自那之后就将灵魂卖给了魔鬼,他将那些嫉妒过特蕾莎的女人都娶回家,然后再杀掉,长此以往他终于彻底变成了疯子,不断娶新的妻子再杀掉,仿佛成为他悼念特蕾莎的一种方式。
故事的结局是琳达的哥哥杀掉了青须公爵,救下了琳达。青须公爵死去后,作为妻子的琳达继承了所有的财产,成为城堡的新主人,有了新的丈夫。然而,就在所有人都以为故事就这样以琳达的幸福生活结束时,琳达杀死了自己的新丈夫,然后将他吊在地下室的天花板上。在新丈夫不敢置信地叫着琳达的名字时,琳达笑着说道:先生,请叫我特蕾莎。
网友们的评论褒贬不一,但其中指出的诸如人物行为逻辑不够严谨之类的细节却也让冬月惠有所受益,毕竟她是个乐于接受各种建议的人。翻看着这些评论时,冬月惠被其中一条吸引了目光——
“博主是星奏学院戏剧社的学生对吧?我经常去看星奏的演出,不知道有没有机会看到博主这个剧本的现场演出!”
冬月惠在网上并未掩饰自己在星奏就读的事情,但对方的期待却让她隐隐不安,连忙回复了评论——
“QAQ谢谢您的喜欢,但我们戏剧社的原创剧目一般都是用全原创的本子!这个改编只是我的个人兴趣,并没有投递到戏剧社那边。”
冬月惠回复完这条评论后便放下了手机,她明白自己目前的创作极限就到这里。相比之下,她现在更期待看到星奏戏剧社即将公开的新剧本,那也是下一次戏剧社公演的本子。
彼时的冬月惠不曾想到,在看到戏剧社即将筹备演出的新剧本时,她会萌生出如此强烈的欲望——想要演绎这个故事的女主角。
那是讲述了两个女性的故事,剧本的名字叫《蝶恋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