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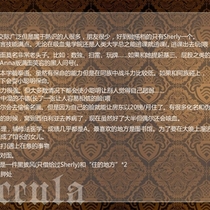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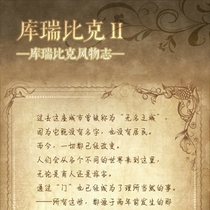

※修改了一下标题
======
——如果有一个可以实现你任何愿望的机会放在你的眼前,你会为了赢得它而赌上所有、甚至包括自己的灵魂吗?
——是的,我会。
-
托勒的一生是不幸的。
诚然,他曾经有一个还算幸福的家庭。
他的母亲是一个温柔的冬格兰女人,父亲沉稳可靠。他们家在赛里郡的乡下拥有大片土地,生活优渥,他甚至还差点拥有一个弟弟或者妹妹,如果他或者她能够出生的话,一定会是一个如同天使一样美丽可爱的孩子。
如果,能够出生的话。
那是一个阴雨连绵的冬日,门外突然来了许多身穿黑衣的人,他们手里拿着白纸黑字的字据告诉托勒一家——你们的房子归我了。
一夜之间天翻地覆,他们的房子还在原地,他们却被扫地出门,凡是属于那座老宅里的东西,他们一分钱也不被允许带出来。
他们一无所有了。
“我不该相信他的,”父亲终日哀叹着,“我以为,我们已经认识这么多年了……唉,我不应该相信他的……”
母亲原本身体就不好,加上贫穷后的劳顿与抑郁,流产之后自己也很快就去了。
父亲的白发与日俱增。
有一天,父亲在路上走着,突然激动地对着一辆马车冲了上去。
“畜生!!是你骗了我!!”他被周围的仆从挡住,但仍不放弃地从地上捡起碎石扔了过去,石头打在了马车的梁柱上。
马车停了下来。
父亲大吼道:“你给我滚下来!!你看看我现在的样子!!你的良心能够平静吗?啊???”
马车的帘子被掀起一个角,但还没能看清里面人的相貌就又放了下来,在周围人群人群视线的簇拥下驶离了此处。
托勒躲在一旁,悄悄地记住了扬长而去的马车上的徽章。
我们家落魄至此,欺骗了我们的人却依然富裕幸福。这样的事情如何能够忍得?
但是想要打败的人太强大,纵是托勒费煞苦心,成功也遥遥无期。
二十岁生日那天他站在河边,神情悲苦,几近放弃,却没想到迎来了人生中的第二个转折。
“你需要帮助吗?”
那是一个在寒冬中依旧穿着单薄、神情肃穆的黑发女孩。
他看到女孩刘海的两侧有两个小小的盘羊角,鲜血一样浓稠的双目中是不似人类的长方形瞳孔;他看到女孩踩着尖尖的高跟鞋,心形的尾巴尖儿轻轻敲打着大腿;他还看到女孩的身后那双蝙蝠般的黑翼。
恶魔向他伸出了手,说:“如果你有舍弃灵魂也想要实现的愿望,就和我订立契约吧。”
获得恶魔的帮助,需要支付灵魂作为代价。
可是,灵魂?那种东西早就千疮百孔、病变成乌黑一片了吧。
“要的话就拿走吧!”
他嗤笑出声。
后来他借助恶魔的力量和自己的努力,用了半辈子的时间从仇人身上夺回了本属于自己的一切——但是父亲早在这一刻的到来之前就过世了。
他连一个能说心里话的人都没有了。
大概人年纪大了之后,都会为年轻时所做的某些选择感到后悔吧。
三十年过去依然形如少女的恶魔站在他的眼前,时时刻刻提醒着他——你将要坠入地狱。他是知道自己为了报仇做过多少不为人知的恶事的,仅存在于想象中的永世的炼狱之火使他感到了恐惧。
他后悔了。
他什么都没能抓在手里,连自己的灵魂都不再属于自己。
为了逃离现状,托勒想办法支开了那个恶魔,买了一张远去南洋的船票,从好不容易寻回的优渥的生活中一跃而下坠入了颠沛流离的下半生。
只要不被那个恶魔找到,去哪里都可以。他不断地更换姓名和住址,因为担心被认出而时时戴着口罩,不敢与人大声交谈,甚至因为暂居旅店里有人多看了他两眼,就半夜里从三楼沿着水管爬下,连夜逃往另一个城镇。
他以为自己成功了,任何人都不可能再找到他的,任何人都不可能。
时间如同白驹过隙,眨眼间又是三十年过去。八十岁的托勒躺在床上,两眼浑浊,脸上沟壑纵横。
这个旅馆房间可以看出有被尽可能干净地打理过,但即使如此也无法掩去床单的皱褶里散发出廉价旅馆里特有的异味。
而托勒,他即将死去。
在他逃离的这三十年中,恶魔确确实实一次都没有在他的生活里出现。可是他终究没能逃离那个契约。
“还是被抓到了……”
恶魔安静地站在床的一侧。
“不能再多给我一些时间吗?你看,我已经是一个可怜巴巴的老头子了……”
“抱歉,托勒先生。”恶魔叹气,“你能活多少岁这件事并不是由我决定的,如果可以的话我也希望每个人都能够长命百岁。我只负责回收契约者的灵魂这一件事情。按照我们当初定下契约时的约定,你死后灵魂会由我送入地狱,如果你需要做出什么变更的话,现在还可以告诉我,否则等你过世之后我就会依约执行了。”
“被吞噬还是下地狱?呵呵……”他粗哑地笑起来,“我有时候觉得,比起永生永世的痛苦折磨,是不是一秒钟的彻底灭亡反而更幸福一些?”
他看到恶魔因为这句话突然犹豫起来,心里不由得又升起逃脱契约的希望。
但是让他的希望升到顶端的,却是突然出现在窗外的洁白羽翼。
“天、天使……?”他情不自禁激动地喊叫起来,声音里甚至恢复了些许活力,“仁慈的天使啊……求求你,不要抛弃我这个可怜的信徒!从恶魔的手里救救我吧!”
与他的喊叫几乎同时发生的,是恶魔以人眼难以看清的速度从手中的伞里抽出一把泛着寒光的钢剑,面对窗户摆出对峙的架势。
天使站在窗台上向前倾了倾身体向里张望,她好像没有看到那个向她发出请求的老头,反而向着恶魔试探地开口;“小黑?”
恶魔在看清来人的面容之后,出人意料地,相当干脆的收回了自己的武器,露出了有些不好意思的笑容:“你怎么来了!抱歉抱歉,能稍等一下吗?我有工作没有完成。”
“好,我在楼下等你。”天使露出浅浅的笑,转身张开翅膀一跃而下。
不知是不是眼前的情景太过惊世骇俗,托勒一瞬间觉得自己要背过气去,然后等他头不晕眼不花了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真的已经背过气去了。
恶魔抿了抿嘴唇,恢复了公事公办的严肃神情。托勒只觉眼前一花,转眼间已被枷锁铐住,悬浮在虚空中,目之所及空旷无物。
托勒的一生是多么不幸啊……而现在,这不幸将永远延续下去了。
-
传说中,当一个人死去之后,他的灵魂就会脱离肉体成为“亡灵”。而“引路人”则会将亡灵带去归处。
Nancy Tse工作的机构名叫“艾格尼斯坦”,所有的西方国度引路人都是由这个机构所管理的。
虽说是由同一个组织管理,但其实“艾格尼斯坦”机关下的引路人有两个截然不同的分类——被人类歌颂为天使的“艾琳”会将亡灵引向天堂,而被人类赌咒为恶魔的“穆尼克”会将亡灵拖入地狱。Nancy就是一个穆尼克。
“如果你以为,穆尼克是一个勾搭勾搭人类、嚼吧嚼吧灵魂就能完成轻松工作的话,那你可就大错特错了!”在她当年通过艾格尼斯坦一年一度的入职考核之后,考官曾挥舞着教鞭这样向新人们发出警示。
穆尼克是一个在“引路人”中也十分特殊的存在。他们首先需要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一个愿意和恶魔缔结契约的人类,为了提高成功率他们通常会用“帮你们实现愿望哦~”作为卖点来吸引意志薄弱的人类,而在缔结成功后,就需要暂时留在人类的身边,履行那个“实现愿望”的约定。直到人类死后,灵魂归穆尼克所有,他们可以自由地选择将这个亡灵拖入地狱亦或是吞吃入腹。
“呼啊——”Nancy收起伞,伸了一个大大的懒腰,“真是累啊……那时候可是你说要报仇夺回家业,我为此连续好几年每周去图书馆恶补心理学和经济学呢!结果,你还满世界乱跑……真是让我好找。”
托勒并不是她所契约过的亡灵中最难对付的一个,事实上她已经习惯了契约者的出尔反尔的借口和花样百出的逃跑方式。虽然偶尔也想抱怨一下,如果不想下地狱也不想被吞噬的话,一开始就不要和穆尼克签订契约不就好了?既然订立了契约,白纸黑字公平交易,那就应该言而有信嘛?
但其实,她也能够理解。就像不相信神明存在的人越是到临死之前越会恐惧死亡一样,契约者越是接近死之期限就越是会恐惧永恒的地狱或者永恒的消失吧。
“比起永生永世的痛苦折磨,是不是一秒钟的彻底灭亡反而更幸福一些?”
刚才那个契约者的话语再次回响在她的耳畔,她闭上眼睛,心脏泛起丝丝的疼痛。
喂,如果你当初能够选择的话,你会选择永世的折磨还是瞬间的灭亡?
这两个选择都如此令人痛苦……但是,不幸之中的万幸是你还存在,所以我还有一线机会能够救你。
这次的比赛,一定要赢。
Nancy眨了眨眼睛,她在旅馆外的路灯下看到了安静地等待着她的白色少女。她瞬间将烦恼抛下欢快地奔跑过去,牵起了少女的双手握在胸前:“嘿小白!来找我吗?抱歉啦,刚才在工作!”
“没关系,”白色少女低着头怯生生道,“是我打扰到你了……”
Nancy连忙安慰她:“不用放在心上!我很高兴你来打扰我的!”
这个白发白翼白裙、被Nancy昵称为“小白”的艾琳少女,名叫Chasity。她们两个是以前Nancy在人间进行契约任务的期间认识的。
当时好像发生了一些复杂的事情,牵扯到了人类和其他艾琳,事后据说还有一个穆尼克也因此受到了牵连。具体到底发生了什么Nancy一直都没有很弄明白。她觉得Chasity可能知道,但Chasity没有说,她也就没有问。总之从那之后,她们两个就逐渐熟络了起来。
与东方引路人之间通常比较友好的相处不同,西方不同阵营的引路人之间往往针锋相对,大多数艾琳和穆尼克都看彼此极不顺眼,即使没有仇视到见面你死我活干一架的程度,故意避开彼此也是常有的事情。这是双方的信仰差异所造成的难以调和的矛盾。
不过Nancy并不把这些放在心上。在她眼里,Chasity就像是一朵经由温室栽培、柔弱无害的小花,无论是被那双羞怯又波光涟漪的蓝眼睛凝视着,还是被用轻轻软软的声音小心翼翼地昵称作“小黑”,都完完全全激发起了她的保护欲,让她想要好好保护这个胆小的女孩子。
“有什么事情就尽管说吧!”
Chasity在她期待和鼓励的目光下,怯生生地问道:“小黑……你会去参加‘浮游之境’的运动会吗?”
这个问题实在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浮游之境每三百年才会开放一次,如果能在举行的运动会中取得最终的胜利,就能够被凝神召见,获得一个向凝神许愿的机会。
几年前Nancy第一次从别人那里听说这个“运动会”的时候,就决定要拼尽所有去夺取那个唯一的许愿机会。
现在,第三百年即将到来,这件事早已经传遍了整个艾格尼斯坦,Chasity会在此时提起,实在是再正常不过。
Nancy握紧了拳头:“是的,我会去……”
她的手突然被回握住。
抬起头,对上的Chasity满怀真挚的眼神:“小黑,你愿意和我组队吗?”
这个眼神让Nancy难以拒绝,但她还是沉思掂量了一会儿,尽量考虑到组队之后的利弊——至于那些没有想到的问题,就等遇到之后再想办法好了!
“可以啊!”
“咦?啊……那真是太好了!”Chasity露出一个清浅的喜悦笑容。
-
Nancy正打算躺下休息的时候听到窗外传来了“扑棱扑棱”的声音,她打开窗户,一只小蝙蝠就跌跌撞撞地飞进来,在房间里环绕一圈,最后停在了她的肩上。
“甜甜圈?那么晚给我送什么来啦?”
被叫做甜甜圈的小蝙蝠吱吱叫了两声,抬起一只爪子,让Nancy看它抓着的那个牛皮纸卷。
把纸卷展开,是一张手掌大小的通知书。Nancy仔细地读完了文字,把正反面都看过确认没有漏掉什么后又将它卷回了原来的样子。
“噗嗤!”她捂住一只眼睛笑起来,“我还以为只是名字叫运动会,其实会是对战之类的……原来真的是进行运动比赛呀!沙滩排球,需要好好研究一下规则呢……”
她提起睡裙的裙摆转着圈回到窗边,趴在窗台上抬头看去。
穆尼克的居所在炼狱底部,仰头看去的时候,能看到无数亡灵如同星星一样点缀在地狱的虚空中。
那是在炼狱底所能看到最美的景色,但是对那些亡灵而言,一定只有无比的煎熬与痛苦吧。
她的嘴唇动了动,声音溶解在空气里,最终什么也没说出口。
-
浮游之境内部的一草一木都是由其本身虚拟而成,无论是阳光、沙滩、海洋,实际上都并不存在——理论上来说是这样的。
Nancy半蹲在沙滩排球场的场地旁捞起一把沙子,感受着它们从指缝里慢慢流走的触感。
“和真实的感觉一模一样!”
Chasity用手指轻点嘴唇:“……看来不用担心触感不同导致的不习惯了。”
“是哦!啊,有其他人来了?”
“哈欠——好困——”就在Nancy感应到有人的转瞬之间,束着双马尾的白裙少女就出现在了场地的对面,“呼啊……要睡着了……”
将圣典怀抱在胸前的穆尼克少女小步赶上,她将一撮散落到额前的褐发捋回耳后,无奈地小声提醒道:“BP前辈,这个时候就不要犯困了啦……”
“嗯……嗯嗯。”白裙少女一边努力地点着头,一边却好像马上就要站着睡过去了。
Nancy看着觉得有趣,挥手向她们打了招呼:“你们好——你们就是我们这一轮的对手吗?”
“看起来就是这样了。”褐发穆尼克少女和善地向她们微笑,自我介绍道,“我是Saipal,这位是Bori Pori。”
“你……呼……你们好……”BoriPori揉了揉睡意惺忪的眼睛,看清对手后瞬间清醒了过来,“呀——我们的对手是可爱的小姑娘吗?”
“谢谢夸奖,”Nancy真诚地弄错了重点,“你们也是非常可爱的小姑娘呀!”
“谢、谢谢,”Saipal抱紧了圣典,停在她肩上的小黑鸽“咕咕”地叫了两声,“为了爱与和平,我们是不会输的!”
她话音刚落就被BoriPori伸手圈住,用力扯她的两边脸颊:“小Saipal觉悟很高呀?嘻嘻……”
Saipal努力表现出的成熟冷静瞬间崩塌,眼角挂着吃痛的泪珠:“唔唔唔!BP见辈杭该我惹啊(BP前辈放开我啦)!呜……”
Chasity若有所思地看了看她们。
“宣扬爱与和平的穆尼克……吗?”
柱子顶端的扩音喇叭突然传出广播的声音。
“嗞……咳咳……嗞……试音,能听见吗?啊,看来各位选手都按时到达了场地,真是令人欣慰。正式比赛将在十五分钟后开始,请大家提前做好准备工作……嗞……啪!”
在“啪”的一声结束后,喇叭又恢复了安静。
说到准备工作,首先、当然、是要换衣服!
她们现在身上所穿的服装虽然符合平时的工作需求,但对于运动而言就很不方便了。无论是密不透气的西装外套还是长度过膝的长裙,对于沙滩排球而言都简直是灾难。
是的,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应该穿上相对应的服装,就好像参加舞会的时候要穿礼服、做饭的时候要围围裙、上阵打仗的时候需要披盔戴甲,打沙滩排球的时候自然也要穿上与沙滩排球的氛围向符合的衣服——那就是泳装!
可不能小看这小小的泳装,在打沙滩排球的时候它就是礼服、是战斗服啊!
以上是Nancy给为了这次比赛特地去挑选新泳衣的自己找借口时的脑内活动。
Nancy和Chasity来的时候就把泳装穿在了里面,此时此刻只要将扣子一解、裙子一褪,当Saipal和BoriPori从扩音喇叭的方向回过头来的时候,她们两个身上已经只剩下泳装了,穿着豹纹泳衣的Chasity瞬间成为了大家瞩目的焦点。
“唔哇泳装小白好棒呀!!给你撑伞不要晒到啦!!”
BoriPori两眼放光地绕着她转了两圈:“啊啊啊————!好可爱,好可爱啊!!泳装意外的是性感路线呢!”
“输了……!!”Saipal鼓起脸颊低头盯着自己的胸,“呜啊、我不会输的!为了爱与和平!我、我一定!我一定也!”
一分钟后。
“呼呼,所以小Saipal你的不会输就是偷偷把绷带叠在泳衣里胸部的位置上吗?”BoriPori丝毫不给队友面子地揭露出来。
“才、才不是,这里有伤口,还……还没好呢!”Saipal红着脸故意挺了挺胸,想要表现出一副很自然的样子。
BoriPori趁机把手伸进了Saipal的泳衣里,抓住绷带一扯。
“我抽——”
“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Nancy无奈地看着对面两个人绕着圈你追我赶、打打闹闹的样子:“比赛还没开始就内战了呢。”
随着“bong”的响声,一群小蝙蝠凭空出现在了赛场的上方,爪子上还抓着两个用来抽签的竹筒。
“一起去抽签吧——”Nancy打算提醒一下她们,没想到她回过头刚刚开口,一阵风就从她身边刮了过去。
Nancy惊讶地看着BoriPori已经跑到蝙蝠旁的背影:“好快!?我甚至都没有看清她的动作……”
真是厉害呀!她赶紧也跟了上去。
场地抽签的小竹筒里只有两张签,因为BoriPori一马当先拿起了写着“东”的那张签,所以场地就这样定了下来。
而发球抽签总共有四张,抽到写着“1”的人需要第一个发球,这是一个先发制人的好机会,Nancy还挺希望自己能够抽到的。但是很可惜,她抽出来的签上一片空白。
等大家都抽完签之后,Chasity把自己的纸签展开在大家的面前——上面正是一个大写的“1”。
Chasity拧起了眉毛,像是有些苦恼的样子。以为她是没有自信的Nancy安抚地拍了拍她的背,竖起大拇指鼓励道:“没事的,尽力就好!”
-
“现在请各位选手各就各位!”
带着咸味的海风穿过沙滩,给被炎炎烈日晒得滚烫的沙滩带来了稍许凉意。
参加比赛的两组人分别在球网两侧各自的位置站定。
Nancy双手相扣,扭动了一下肩膀、手腕和腰等部位。她身量纤瘦,因久居地狱而略显苍白,粉色碎花泳衣正好给她增添了几分亮色。她平时总是穿一身漆黑,其实是为了符合穆尼克一贯带给人们的印象,因为这次并非参加工作,她才按照自己原本的喜好,穿上了清新田园的风格。
Chasity站在Nancy的斜后方,轻轻垫了垫球。她的四肢柔软而白净,吊带从细细的脖颈后绕过,承托起泛着柔和光晕的胸部,腰和大腿之间的曲线格外的迷人好看,衬上豹纹的泳衣泳裤,使人更难以移开视线。
与Chasity相对站在球网另一侧的是单手叉腰、粉色双马尾在风里荡漾的BoriPori。与日常服装里短而翘起的小裙子不同,她里面穿了抹胸,斜披在肩上的希腊式外裙裹住了柔软的腰肢和臀部,营造出一种意想不到的保守可爱的效果。
BP旁边的则是个子小小的Saipal,外面有一层薄纱的背带式泳衣和连着小裙子的泳裤让她看起来有几分孩子气,虽然她好像努力想做出成熟淡定的姿态,但略显笨拙的样子反而更有些青涩。
所有人都准备就绪,蓄势待发。
响亮的哨声划破空气,首先将由Chasity发出第一球。
Nancy摒弃掉一切杂念,压低自身重心,集中起注意力,随时准备好应付对手击回的球。
Chasity将球高高抛起,屈膝起跳,右手的拳头用力地击打在球上。
“嘭!!!!”
球重重砸到地上。
“等等……那是什么?”
Nancy震惊地看着从对面沙地上弹跳而起、压在边界线上的排球。
刚才那一击速度很快,角度也很刁钻,一点也不像是平时的Chasity打出来的风格……她完全不知道原来她排球打得那么厉害!
对面的Saipal和BoriPori也十分震惊……不,BoriPori的神情看起来与其说是震惊,倒不如说是兴奋过度。
“咿——呀!Chasity不仅非常可爱而且还超——厉害的样子啊!好棒啊好棒啊好棒——啊!”伴随着她喊声的最后一个字,一记高速球从球网对面飞来。
Nancy想要回头去看一眼后排的Chasity,但BoriPori移动速度极快,往往是Nancy刚刚击出一球,BoriPori就已经移动到了球的落点处出手反攻。Nancy要接住她眼花缭乱的攻击就已经焦头烂额,根本找不出空闲回头。
“呯!”接到了!
Nancy稳住奔跑的身形,原地颠了两下球,跳起来两手轻轻一拍,打了一个刚刚过网的短球。
BoriPori还在距离球网很远的位置上,就算是以她的速度,也不可能在球落地之前赶回来。Nancy觉得终于能再掰回一分了,在心里稍稍松了一口气。
“不会让你破坏我的‘爱’的!”
突然出现在球网前的面无表情的Saipal毫不留情地来了一记扣球。
对面又得一分。
自从比赛开始之后,Saipal一反常态,既不再刻意模仿成熟女性的举止,也不再露出天真青涩的笑容,变得神情冷淡起来,就好像刚才那个笑容和眼泪都十分生动的Saipal并没有存在过一样。
这样下去情况可能会不太好,Nancy咬牙思考着对策。
当BoriPori再一次飞快移动到球的落点准备回击的时候,突然之间三个魔法弹从空中越过球网向她袭去。
“祝福之盾!”眼看着魔法弹就要打到她,三面由砂砾组成的盾牌瞬间拔地而起防护在她的周围,当魔法弹撞上盾牌的一瞬间,四散开来的黄沙帮她挡住了攻击,这一耽搁却也让她没能够接到球。
Nancy的球得了分。
BoriPori伸手抹去脸沾到的沙子:“哼哼……还是忍不住了啊。”
在她视线的末端,Chasity正手持着短剑,身体还保持着用剑挥出魔法弹的姿势。Nancy感觉那双蓝眼睛里有冷色的火焰在燃烧。
“那我也不客气了!”
BoriPori右手摸出七把银制的小刀,匀给左手三把,然后将它们展开成两个扇形:“礼宴EX!!”
数量众多的餐刀和叉子从她背后凭空浮现出来,随着BoriPori的一挥手向Chasity射去,Chasity像挥舞指挥棒一样,随手将三个魔法弹拉伸成盾叠加在一起抵御攻击,又挥出三个魔法弹反击。
那边两个Archer互射,你来我往乱弹齐飞,殃及无辜砸坏了排球场附近的各种柱子和花花草草。这边Nancy和Saipal还在努力地进行正常的排球比赛。
Nancy一个扣球。
“啪!”“得分!”
总算追回来一点了,当她松一口气的时候,一个射偏了的瓷盘向她砸了过来,旋即一个魔力盾从天而降弹开了那个盘子。
无论是打斗还是排球似乎都进行到了白热化的阶段。
当再一次轮到Saipal发球的时候,她却停在原地没有动。正当Nancy感到疑惑,Saipal突然蹲下身,从地上捡起一块盘子的碎片,对着自己的手腕割了下去。
Nancy惊呼一声:“喂!?你?”
伴随着她的举动,那只小黑鸽盘旋着飞到她周围,Saipal吃痛地举起手,让鲜血滴在小黑鸽的躯体上。浸染了血液的鸽子长鸣一声。
Nancy警觉地盯着Saipal,不知道她接下来要使出的招数是什么,但Saipal一直安安静静地站在原地,反而是BoriPori好像发生了什么变化。
在刚才的远程战中,虽然有盾牌,但BoriPori还是受了些擦伤,而就在现在,那些伤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了起来,她的眼神也渐渐发生了某种变化。
“死吧!!!!”
她张开羽翼从球网另一边瞬间移动了过来,嘴唇咧开成一个嗜血的笑意,眼神如同无机质一样冰冷。银刀、银叉、瓷碟、高脚杯,一切都以高速地向四面八方放射而出。她的移动速度和“礼宴EX”的射击速度都提升了三倍不止。
Nancy连连后跃躲避攻击,身上还是被划破了好几道口子。
Chasity把Nancy放在场边的伞扔了过来,Nancy伸手接住,从中抽出一把剑。
“风牙!”
随着她的轻喝,风以剑为中心蔓延开来。Nancy高高跳起,借助自身重力向着BoriPori挥剑劈下。剑被餐具聚集而成的盾牌挡下,烈风卷起餐具并瞬间将一切金属和瓷器粉碎,但不过短短几秒的时间,更多的餐具又从空中涌现出来。Nancy横劈纵刺,与Chasity的远程魔法弹一起与“礼宴EX”抗衡。
伤口在增多,不过Chasity不时地会用魔力帮她回复血量,所以行动并无大碍。
不知道什么时候,原本站在球场对面的Saipal移动到了球场边缘,那本褐色封皮的圣典被紧握在她的手上。她将圣典环抱在胸前,双目紧闭,神情虔诚地吟诵道:“请赐给我指引众生的力量,将爱与和平降临世间吧!”
从书里钻出来一只用墨水形成的小黑鸽,以极快的速度在空中划出一条黑色的弧线,一头撞进了Nancy的大脑里消失无踪。
“啊——”
Nancy只觉得头突然极痛,再睁开眼时发现自己悬浮在虚空中,她动了一下,发现自己的手脚都被束缚住,仔细一看那些捆住自己的“绳子”是由许许多多很小的“LOVE”组成。
随即周围浮现出许多巨大的LOVE字样往她身上砸去。
“接受大爱的感化吧!”
当Nancy被困在精神里的时候,她的身体正被控制着向Chasity举剑挥去。Chasity展翅飞到空中避开了被风延续的攻击,张开魔力盾堪堪挡住了来自两边的同时攻击。
Nancy一击未成,行动却停了下来。Saipal为了维持BoriPori的狂化状态失血过多,这会儿对Nancy的精神控制有些力不从心,她微微喘着气半蹲在地,勉力支撑着自己。
恢复意识的一瞬间,Nancy浑身脱力地跌坐在地上,心有余悸。刚才的具现化“LOVE”攻击太可怕了……她可能最近都会对这个词有些心理阴影。
“嗯?好像有什么过来了?”
Nancy抬着头,看着一个巨大的,呃,炮弹从天而降越来越近。
“呃啊快跑!!!”
等她飞出球场范围的一瞬间,背后轰地炸开,炸了Nancy满身的黄沙。
她飞到安全范围才回头看去,在爆炸的另一边,一只小黑鸽拼命扑棱着翅膀向上飞去,它的爪子上抓着Saipal的后领,将她拎出了爆炸的黑雾范围。
“哎呀哎呀……虽然场地不花钱,但也不能这样炸着玩呀……”
沙滩远处的树丛后,沈京举着望远镜十分无奈地说道。
“嗯……不过看到了好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