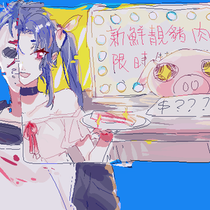两个笨蛋的相遇之章,努力学习了日本轻小说腔,自己在读的时候一直在脑补日语对话哈哈哈哈
--------------------------------------------
因西比奥是位于绿洲最中心的行星,是这个大型线上游戏的“新手村”。
尽管这个游戏已经运营许多年了,但新手村仍旧每天活动滞留着无数无法支付昂贵传送费的贫民玩家,以及新的——登录玩家。
糟糕的现实与宛如梦境的网络,只要有钱就无所不能的可能性,一个可供喘息的地方给予了许多人活下去的希望,同时也给了许多在现实无法释放自我本性的人一个扮演他人的机会。
你永远想不到线上的ta,在线下到底是人还是狗?
在商铺与商铺之间的阴暗小巷中,一个带着漆黑斗篷浑身上下只露出护目镜的身影正鬼鬼祟祟地蹲在建筑阴影下,诠释了什么叫完美藏匿。
“啊……这个,之前跟他玩过了……”双眼盯着来往的玩家,他小声嘟囔着,“真无聊呐新人桑呢新人桑呢。”
盯了快半个小时什么收获都没有的Chickenlovelove打开了自己的收件箱,开始逐个逐个将里面讲粗口骂自己的发件人拖入黑名单。
“诶真厉害啊这封邮件,居然用分隔号同声字等等操作避开了各种屏蔽词,完美地用各种生殖器官把我骂了一顿……”
“这家伙是中国人吗?”
一边查看着邮件一边用余光瞄着巷口,终于在一个小时后,他迎来了梦寐以求的新登录玩家。
银色的长发,褐色画着萤黄诡谲符文的皮肤,黑色眼白内镶嵌了一颗宛如红宝石般的瞳仁,完全没见过的角色设计。当然最重要的还有动作神情,绿洲的在线玩家千千万没有人能确保自己的角色设计是最独一无二的,对方正四处张望着街道的店铺,神情挺兴奋眼里还带着好奇,完全不符合他那张酷帅的脸和名叫山鬼的id。
啊!这可爱的神态举动,百分百是新人桑啊!而且看id和角色设计应该跟他一样是日本人,绿洲里日本玩家还不多呢。
“哈喽你好啊。”心动不如行动,Chickenlovelove同志瞬间窜到了对方的背后出声道。
新的风暴已经出现,怎么能够停滞不前~❤
“诶?!!”对方顿时被这突然出现在耳边的声音吓了一跳。
“哈喽你好啊~”从背后转到正面,他咧嘴露出一口白牙展现了一个人畜无害的微笑重复道。
这山鬼愣了一回估计在思索从哪冒出他这一号人来,半晌才突然醒悟连忙回应:“啊你好你好……”
“嘿嘿你是新玩家吗?我看你在这转了蛮久了,需要帮忙吗?”Chickenlovelove在心底吐了吐舌头,骗你哒其实我一看到你就立马找上门了。
对方害羞地挠了挠那头漂亮的银发:“是的,我是今日刚创建账号的新人,因为找不到任务对象所以找了很久。”
唔哇,居然脸红了好可爱啊,骗起来更有意思了……
“哦哦原来如此,是哪个任务啊你发出来我看看吧,带你去找它。”Chickenlovelove业务熟练地说出了惯用话语。
“诶那样会不会太麻烦你?抱歉。”对方迟疑了,果然是日本人吧会说抱歉。
“完全不会,我这个人经常呆在新手村就是因为喜欢帮助新人桑,让他们早日了解游戏玩法。”不,是早日了解社会险恶。
“没想到一进游戏就碰到如此热心肠的人,绿洲原来是这么一个有人情味的游戏,那个还不知道你怎么称呼?”这人果然完全没看出他这个浑身穿的乌漆嘛黑还隐藏了id的人有问题。
CHickenlovelove稍微考虑了一下,决定告诉对方自己因为id太长而经常被叫的称呼:“叫我叽叽就好了哦。”
“好的叽叽桑!”对方笑了起来。
随后,对方便共享了一个任务面板过来,他凑过去一看一条拐人的路线就瞬间在脑内生成了。
“哦,原来是这个任务啊,那个npc就在街尾的店附近,我带你过去吧。”
“啊真是太谢谢你了。”对方正经地鞠躬道谢了。
“哪里哪里,走吧。”
……
因西比奥的商店街散布各地、全球同步的商店,可以说是最大型的线上交易场所,一路走过去对方看得眼花缭乱还抓着他提问了不少新人问题。
“到啦。”一路闲聊忽悠着对方,Chickenlovelove顺利地把人带到了所谓的‘目的地’。
对方环视了一下周围,终于感觉有点不太对劲:“那个,这里又黑又好像什么都……”
他打断了对面的讲话,一边把背包里的滑板拿出扳成了两块一边缓缓道:“我现在有个问题想要先提问你一下。”
手里拆分成两块的滑板被一阵蓝色的光芒包裹住,蓝色的碎片从中分解随之覆盖到Chickenlovelove的手臂上,咔嚓咔嚓睇安装声音令人为之一振,唰的一下蓝光退去,由滑板分解化成的两个手筒完美地安装到了他的手臂上。
他微笑着将武器对准了对方的头部,此时对方终于露出了与刚才截然不同的表情了,带着惊诧以及疑惑。
每一位玩家在注册的时候都会被科普过PVP的注意事项以及角色被攻击杀害后的惩罚。因西比奥虽然是新手村却有着不禁止PVP的规定,但一般来说还停留在新手村的人大部分都一穷二白,并不是值得抢夺的对象。
“叽叽桑……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沉默许久后终于明白来龙去脉的对方黯然道。
“当然是骗萌新好玩啦哈哈哈,但是我也是不会不近人情的哦,只要你答对了我的质问就放你离开啦。”他假装大度的说道,反正没人会答对这道问题。
“那来吧,是什么问题?!”对方反而莫名其妙地燃起了斗志了。
喂喂为什么不生气啦你这个新人?!
Chickenlovelove在内心吐槽这位新人的反常边熟练道:“那就是——铛铛——‘请问你吃炸鸡的时候蘸什么酱?’”
对面顿时被奇怪问题惊异到了:“??!!”
“那么答案是——???”
“当然是不蘸酱了。”
“噗噗,恭喜你回答错……等等???你怎么会知道我认可的正确答案!”武器口已经凝聚了一半的激光,正想着动手结果对面的他被突如其来的正确答给震惊了。
“诶真的吗?!!因为我现实中有同学喜欢炸鸡问过……诶诶诶等会,难道说……”
对方:“你是响太吗?”
Chickenlovelove:“!!!!!”
在亿分概率万般机缘巧合下,现实中相识的两人在游戏里相遇了。
------------------------------------------------------------------------
随后得知真相的山鬼:“万万没想到,响太在游戏里还有这种爱好呢……”
“别…别说了我都要羞愧自尽了,在net干坏事时碰到熟人的事情我从来没想过啊。”Chickenlovelove捂脸。
“现实里十分老实但游戏里这么调皮的你……真是太可爱啦!!!”山鬼诚恳又痴汉道。
“快闭嘴啦你这个笨蛋骚话王。”




·正片暂时来不及弄,让我投个旧的给自己混条线索。
·时间线大概在企划开始的半年前或者一年前,没仔细算。
·在CB变CP的边缘反复试探。
·最后一段剧情发生在四章日常。
·BGM是lemon(...
“麻生啊。”
“什么?”
“你有女朋友了?以前你还会在社团露个面的,现在连社团都不来了啊。”
“哈哈,怎么可能。“红发的人拉开易拉环,把可乐一口气灌进喉咙里,带着刺激感的甜腻填满了口腔,他把易拉罐捏扁晃了晃,扔进了垃圾桶,”是工作,我放学会去接个人。”
“啊,之前说过的...钟点工?钟点工为什么要做这个啊。”
“我住那家伙家里了。”
“呜哇,不是吧,我猜猜,你是不是没要钱。”
“...你怎么知道的。不过那家伙出料理的钱就是了。”
“因为你从来不固定地住在某个地方啊,所以肯定不是你自己提出的要求。上次我请你去我家不也是这样。说真的,为什么啊?”
他愣了一下,看着友人一脸好奇的表情,他打开手机确认了一下短信,沉默了一会儿接上了之前的话题,“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因为他长得好看吧。”
“.....你,我就觉得你不怎么喜欢女人,不会对男人有兴趣吧。”
“你猜啊。“他扑哧一声的笑了,然后低下头,闭上眼睛。麻生宙希枝清楚得很——他会选择呆在祭狩御灯身边的理由。那是不能对任何人说的吧,包括他也一样。这样想着,麻生的嘴角在无形之中挑起了一个弧度。
心照不宣地,避开了真实的答案,选择了默然。
——你有颗痣啊。
——是啊,你也想要吗。
那是他见到名叫祭狩御灯的医科生之后的第一反应。而对方显然没有把这件事记在心上——说的也是,把这个人和故人重合这种蠢事只有他自己知道就够了,他在心里嘲笑着自己。然后,在对方说出”你在这里住下吧”的时候,他感受到了一丝不可思议。在大多数人的第一印象里他是一个不可靠的轻浮男人,对此他感到极为不满但是也疲于去纠正。
而这一次,他倒是从祭狩御那嬉皮笑脸的表情里看到了一丝相似的感觉,人类都是喜欢与相似者群聚的生物,顺着这种相似性的趋势,麻生答应了祭狩御灯的提议。
但是那个时候,麻生宙希枝还是孑然一身。
当然祭狩御灯也是不会知道的,这个被雇佣为钟点工,做完应该做的事情就几乎不会呆在他家的人是怎样的来头。他只知道麻生是个孤儿,再多的信息麻生并没有透露的意思,他也不会去追问什么。事实上,最开始的三个月,除了必要的一些交流以外,两个人之间什么都没有。一个人在一成不变的继续着他并不感兴趣的医学学习,另一个人不曾停止地为了活着四处奔波。
只不过是,处于同一空间里不会交汇的两条直线罢了。
“他身体不好。“他继续说着,“你当成我是喜欢把自己当成救世主也行。”
“哇塞,你可算了吧,我觉得你肯定是出点什么灾难跑的最快的那个人。一般人谁会找体育老师学一堆自保自救的招数啊。”
“哈哈,你真懂我,不过理由真的是这个啦。”但他还是在某个关键部分选择了沉默,且不说擅自告诉别人这件事是对不起祭狩御,那件事涉及到的某些黑漆漆的东西也是他不会撕开的——麻生宙希枝并不学得会这种表达方式,似乎从很早以前开始,他就选择了不与太多人交心的生活方法。那些人都是过客,麻生一边听着友人的闲聊一边这么说想着,至于祭狩御...
祭狩御。
他在心里重复了一遍这个名字,然后整颗心脏陷入了默然。
心脏病突发,麻生并不是没见过这样的事,在工地里工作的时候有时就会看到这样突然呼吸困难,捂住自己心脏倒下的人——他当然看不得,但是能够处理这件事的人总是会比他更快,他只要选择为那个病人松一口气就可以了。他不觉得自己会陷入和当年相似的某种焦躁,因为他不用伸出自己的手。
那么,该如何定义这件事?还是跟他无关吗。
当然不是。
他几乎是第一时间做出了反应,换做平时,他能够很快地得出结论,这一次理性却被冲动毁的一干二净。那个时候他究竟是如何救助祭狩御的,祭狩御是何时被转移到医院的,他已经记不清了。他只记得自己在做心脏复苏的时候——那一遍遍的,没有人能听到的“别死啊”。只有他知道,他什么都没说,但他也是真的在大声嘶吼。
——别露出这么可怕的表情啊,麻酱,我不是没事吗。
苏醒以后,祭狩御看着麻生阴沉的几乎变成了青灰的脸,伸出手揉了揉红色的额发。
——我知道。但我不想看到你死在我眼前。
——嗯,谢谢你帮了我。
麻生宙希枝一定不会知道,他也无法知道,在祭狩御灯说出那句话的时候。他脸上闪过震惊之后留下的表情,就像是终于找到了灯塔的水手。
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变味了的吗,他想着。然后看向了蓝的几乎虚幻的天空,然后他伸出了手,又收了回去——不对,他想,要再往前一点。或者说,从一开始,这也许就不是简单的雇佣关系。
他原本是渴望着从祭狩御灯身上寻找一些能填补某个空缺的东西,当然那个位置是无法被替代的,有些记忆也是无法被抹平的。只是,借着少年的存在,让它变得浅淡一些罢了。——不,不对,他想。他看向自己的手,然后愣住了,最后他得出了结论。
也许,祭狩御灯才是向他伸出手的那个人。
最后一个隐藏在不真实的默然里的故事。
某个雪夜,少年倚靠在窗户的玻璃上,他觉得有点冷(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暂时没有可以支付冬装价格的资金)。他开始后悔自己一时冲动买了那样永远也不会送出手的礼物。然后他换了个姿势蜷缩在行驶在雪夜里的电车里,开始翻看起招聘网络。
——学生模特,我这一身是伤应该不行吧。
——照顾幼婴...会吓到他们吧。
——啊。
一条招聘小时工的广告映在他的眼睛里。
“麻酱?”
祭狩御灯的呼唤把他唤回了现实。
“啊,抱歉,我这就放你下来。”他把少年放下来,用和平时别无二致的语气道了晚安,接着转身离开。他悄悄地回过头,又一次地看向了那个人的背影。 然后再转回去,“...要是能留下就好了啊。”
“即使从一开始就做好了不留在任何人身边的打算,但是居然,有点想让雇佣关系持续的再久一点了。”
他缓慢地说着,声音融化在了空气里。




○概要:亲爱的,离别时请为我唱支歌。
是很容易猜到的事件真相
——
“也许你想不到……”女鬼喃喃。
男子最终停下了脚步,垂下头去。
“他/她应该已经不再爱我。”两人同时停下动作,眼神复杂,说出同样的话。
一人一鬼,看着地铁车顶,落入名为过往的漩涡。命运将两人带上同一辆列车,忘记了也是它叫两人生死相隔。
真的是这样吗?在人与鬼的无尽落寞中,你似乎听到命运在低语:
他们不是梁山伯与祝英台,不是罗密欧与朱丽叶,也不是焦仲卿与刘兰芝。
命运的声音细碎难便又夹杂着轻微的嘲讽:我什么也没有做。
“起初我们也是很浪漫的。”女鬼说着露出怀念的表情。
“我们是在大学认识的。”男子笑得像是个孩子。
“他/她那时候非常耀眼。”
他们接下来所说的话却与这一句自相矛盾。
“他那时候只会穿格子衬衫头发长了老长才知道去剪,嘴上念叨小姐姐小姐姐但一到社团聚会就缩成一团。”
“她那时候从来不会打扮说话大声举止只能说man,社团破冰的时候扳手腕比赛能把三个大老爷们扳弯。 ”
“我当时怎么就看上这样一个人呢……”两人骂着骂着突然笑自己。
“也有过诺言。”
“他说过等他当上代行就一起去挑戒指。”
“结果那天她加班……”
“她说过等她跑完业务就请年假我们一起去海南堆沙雕。”
“结果假请好了他却生了病住了很久医院……”
“相互理解……”两人喃喃,“我当然理解。可是如果总是这样……人都是会厌烦的吧?”
“她做的菜真的不是给人吃的。”
“他进屋总是忘记换鞋。”
“真搞不懂为什么要把东西全都藏起来,我修个灯泡她还说我把地弄脏了?有没有搞错?”
“他难道没有基本常识吗?为什么用厨房的拖把拖卧室的地!?故意给我找事做吗?”
“我明天还要工作啊!”两人这一喊把旁边的小鬼吓了一跳。
“那天是他的生日,我特地给他买了蛋糕。但他回来晚了,脸色也很不好。”
“那天我手底下的小子出了些差错,我替他背了锅……回去路上那个毛小子请我喝了几杯。”
“他平常不喝酒的……”
“那小子告诉说我既然已经买好戒指了不管怎么样她都会喜欢的,让我快点给她……结果……”
“我没有真的认为他对我不忠……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了……竟然说出这么过分的话……”
“她可能真的受够了这样的日子……”
“也许是因为虽然住在一个家里却根本见不到对方几面,待在一起的时候又都已疲惫不堪……”
“也许是因为明明努力工作但一交房贷就不剩多少,省吃俭用到头没了时间。”
“也许仅仅是因为那天下了场暴雨吧……”男子说着抹了抹眼睛。
“她说我们从一开始就不应该在一起。”
“他说如果后悔了就滚……”
“我看着她哭着跑出去。”
“后来他追出来了……如果没有下雨的话,他就不会滑倒吧……”
“如果我没有滑倒……”男子咬牙。
“不过,还好他滑倒了。”女鬼露出窃喜。“不然——”
“那辆车就一下把我们两人都撞了。”男子与女鬼听到了对方在说同样的话。但两方言下之意却截然不同。
两方为了见到彼此都豁出了性命,但如今碰头却一语不言。或许是因为愧疚,或许是因为恐惧,男子颤抖起身子。女鬼想要安抚他,但想起自己的模样,缩回了手。
即使没有这方面的知识,男子也看得出来她剩下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
“这个。”男子从兜里拿出一个丝绒礼盒,他想要帅气的打开,但用错了门道。经过一系列毫无美感,甚至称得上暴力的摸索,他终于找到了正确答案。黑色绢绸上躺着一枚很小的钻戒。“你喜欢吗?”
“……”
“……”
“你为什么可以这么精准地挑中我最讨厌的这款啊!”
“你不是盯着这个看了好久吗?!”
“因为我在想——我就是死了也不会戴这么丑的戒指啊!”
“……”男子本能反驳,但死这个字眼叫他立马住嘴。他拿出戒指想交给女鬼,但女鬼无法触碰到它,也无法拿起它。他只得捏住戒指,让女鬼将手指伸进去试试大小。
在穿越指环的一瞬间,有什么跨过人与鬼,生与死,唯心与唯物连接起这两个个体。它并非如你所想,是热烈温暖的东西,相反它冷冰冰又湿漉漉。诚然,双方对于彼此的热情早被琐碎而平凡的摩擦淹没。名为甜蜜的火热在生活中风干磨碎随风飘尽。
他们不再热爱彼此。也因此不再小心翼翼,不再以他/她为先。所有潮水都会退去,并非因为命运做过什么,而是因为自然就是如此。
而他们失去彼此的那一瞬间,命运的确做了件过分的事。他将他们生命中的一块砭石硬生生扯走。
他们并非失去了恋人,他们失去了家人。
指环内女鬼的手指一点点消失。
“去找个喜欢它的女孩儿吧。”她终于笑了起来。
“还有,生日快乐。”
从远心端到开始,女鬼本就不稳定的躯体一点点化作无形。男子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没有做出任何回应。女鬼唱起生日快乐歌,那是她生前没能道出的贺言。
今天,也是他的生日——她想忘也忘不掉的日子。
她走了。男子愣在原地半晌,终于动了起来。他朝着帮助过他的孩子们深鞠一躬,在下一个站台下车。
门灯闪烁时,他仍有些呆愣。地铁缓缓启动,他的眼眶似乎红了。
“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站台上,有什么东西轻拍他的肩膀。回头,那是之前闹事的鬼魂方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