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黑亦)小矮
关键词:磷
文体:小说
标题:《自走火》
·
他们假笑着说你这易感体质,可千万别走入深夜墓地,会染上永恒燃烧的病。
可我在那里晃荡了整夜,蛇一般没有脚步地游抚过无数碑文。自然,我久久站在你的墓碑前,忘了身躯僵硬了多长时间,忘了任何酸痛与夜风寒冷。我爱着的,深爱的,愚忠于的世上唯一的存在啊,却已不复存在了。
怎么说呢,墓碑上的黑白照片是我记忆中你最好的模样,也最清晰,其它的脸都模糊不清了,但你占据我心二十九立方中的一点一分之一。你对我露出的笑颜,太过完美发光,便更像是我臆想。但无论如何,我对你有七洋般广阔深邃不可计量的爱,新大陆却在你死后才被发掘。太晚了,这来得太晚了。
不。只要我还存在,就不晚。你会染上燃烧的病,当你听见墓中有人声传来。听得清而不实际存在声波,仿佛其实来自于自心最深处。火像是他人点燃的,像是将他人丢弃的枯树枝捡成一堆,从中聚发的。人们的态度像墓旁生长的杂草,覆于石砖上的落叶。他们不爱你,谁都不爱你,自然对你变成怎样都认为无所谓,就算显露惋惜,也假得令人作呕。只有我为你没一滴眼泪地彻夜哭泣,嘶哑的声丝结茧,从中羽化出新的你的我。
我会为你奉上我的全部,请用你的指尖轻触来点燃我。来吧、一点点、就一点点、那极度细微的触感、是否是我将自己逼到最高峰的幻觉呢、也已无所谓了。
将你害死的正是成排成列整齐成群的冷漠的恶毒,我都知道,因为我也曾站在其中冷漠地看着、所以我也是我将报复的之一。就以将我献于你作为我的请罪、我的报酬,成为你那至死也未展开的、矛尖向外的意志的执行者。我成为你的意志的延伸实体化,我成为你的火。
啊啊,这燃烧的感觉。你害怕燃烧,我知道,为了不被自己一口呼吸点燃,咬紧牙关、咬破了嘴唇,擦下一手背的血。你那么隐忍那么痛苦煎熬,但你越忍耐,他人越不察觉、越肆意妄然,眼里只有自己周身圈中的利好欢愉,生命皆是如此!不必要,你不必要这样蜷成一团,我早该说出口的,那么为了偿还,姗姗来迟的我要为你掀起举世的狂浪。
翻涌火焰边缘的浪花。燃烧,你无比害怕着它,这也是不必要的,生命本身就是燃烧,何必多争一朝夕的苟存?你已不存于此,我便更钉死了这般认知。在与你一同最后见证的夜空之下,我没有身躯、只由焰光组成,这令你毫无力量反抗、一举掐灭你的漆黑夜幕,也被我一燎边角、便消噬至尽。
人们见到灼烫的有形恶魔张牙舞爪的模样,会恐惧便反抗;但无碍,无论深夜白日,他们看不见我。不受任何限制轻步游走,我是无声无情无面容的鬼,散播的瘟疫贪求将一切化为灰。让他们感染莫名痛楚,让他们再分享给他们深爱的、去拥抱去亲吻的亲朋,让他们感受不到、看不见彼此的笑容扭曲。让一切从长针刺入的内侧开始崩坏,将劣化因子灌满他们的血管,让他们的脑被远古深林包围,给他们展示他们最不愿看到的景象。那不会让他们瞪大双眼恐惧得想转身逃,那只会让他们失去一切行动能力,仅剩一种高效处死自己的方式。但是,不行,我不允许他们那么轻易从中逃脱。用他们认为早已驯服的野兽撕咬他们吧,一点点地慢慢地,直至消化掉最后一片角质,优雅端庄地小口品尝,将它们拉长至无限,这美艳味觉这临终哀嚎。
对他们我不会有一丁点怜悯,但仍夜夜增长对你的哀伤。我反复咀嚼我记忆中你的一切,将模糊的影像重绘涂色。我记得你的一切,包括婴孩的你在野路上第一次直立行走,抬起头看不存在的我。我记得从那时起我就最爱最爱着你了,朝你张开不存在的拥抱。可我从来没有抱住你,从未给你你应得的温暖,让你短暂的生命一直跋涉于冰川。为什么我什么都没做,我无尽地哀悼你、懊悔我自己,这是我永动的燃料。
走在雨里我想,我是什么呢。雨水让一地活该死尸更不成样子,但不会浇暗我一分。我是怎样坚持着注视着深爱着,从未看过我一眼的你,至死你也没有回过头。
你迈着虚浮脚步走入墓群之夜。各位有名的、多名的、无名的神与灵啊,你哼唱不被任何文字记述过的歌谣,请听我一根虫一粒尘的一声祈求。你的眼光、在虚空沙漠里,挖向最深去寻一颗残星。于是夜风燃起向你扑来,将发丝切断吹散,将皮肤破碎为飞扬纸片,刮断散开如蛛网的神经血管。将这一切消化为虚无,仅剩放射物般沉重的骨骸原地屹立。
不必问我从哪里、由谁授意而来,只需知我降临于此、从无成为有。我是可燃物、助燃剂、残留物,我是燃点、火焰、光与热。我是你的欲望,我成为你的欲望,我听从了你,最终我是践行者。
“点燃我。”
若你能见到这一切,你一定会第一次露出真诚明媚的笑容。然后,我希望你牵起我这副手骨。
·
备注:
免责mode:笑语






【第二章 穿梭在东方的街角,追寻大葱鸭的身影】
火系道馆挑战开始,其中还发生了一些突发事件...?
火系道馆战视频: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9t4y1S7cn?p=3
霍或BGM: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bK4y1v76F?p=2
胡地BGM: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bK4y1v76F?p=3
这次道馆发布的时间比较晚 小编感到非常的抱歉(つД`)・゚・
企划里的剧情没有完成期限 可以随时参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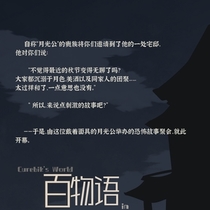


*全文1070+字
*BGM:boom boom satellites—《LAY YOUR HANDS ON ME》
*剧情只和可乐讨论了大概,如有ooc,纯属演技
——————————————————————————
那不过是一次充满偶然的相遇。
一篮饼干,两根逗猫棒,一只惹人怜爱的猫咪,还有一张不含杂质的灿烂笑脸,组成了那个下午的一切。
渡边凉司从未想到这个笑得纯真无暇的女性就此闯入他的世界。
他曾一度派手下调查雨宫由里奈的底细,得到的结果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她在一家知名医院里做护士,娴熟的技法与亲和的笑容令她颇受赞誉。待人友善,乐于助人,甘于奉献。一直温暖别人的她仿佛是太阳本身。
起初凉司只把她当普通朋友看待,且没有深入关系的打算。只是太阳的光芒一次又一次地照在他身上,让他这只过街老鼠也禁不住想再靠近她一些。一次,两次,他应约与雨宫由里奈在猫咖见面,为的只是片刻的安宁。
但是,两人的身边终究是起了流言蜚语。凉司心想这段机缘还是走向尽头,该向对方坦白一切了。
“雨宫小姐。”
“嗯?怎么了?”
在夜晚的霓虹灯下,走在前面的雨宫由里奈转过身,微笑着看向他。
“……鄙人其实是做这行的。”
凉司从大衣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由里奈。粉发女性接过名片过目一番,眨了眨澄澈的双眼。渡边凉司交握在腹前的双手微微出汗,耳边仅剩下人来人往和车水马龙的嘈杂。
没过一会,由里奈眼睛发亮,像是发现了什么宝藏似的说:“原来凉司先生是道上的人啊!好帅气!”
由里奈的反应令他出乎意料,渡边凉司也诧异地眨眨双眼。
“住在这一带的人不可能不知道典朝组,雨宫小姐为何……”
“所以?有什么问题吗?”
由里奈向前跨一步,凑到渡边凉司跟前歪了歪头。凉司被她噎得有些语塞,默默移开视线。
“……你会被卷入本与你无关的纷争与纠葛,遭受身边人的冷言讽语,到最后甚至会遍体鳞伤——”
“没关系,我早就做好觉悟了。”由里奈同以往一样灿烂地笑了。
凉司抬起头,聚光落在他与她的身上,和她伸出的右手。
“能和我一起走吗?凉司先生?”
——若是按照剧本安排,“他”应当在那一刻握住她的手,获得救赎。这出戏码便到此为止。
然而渡边凉司心中警铃大作。
——不行。
——不可以。
这份感情如毒一般腐蚀着他,亦侵蚀着她。
那是会伤及彼此的,绝对不能接受的毒物。
在男人的指尖即将触到她细长的手指之际,渡边凉司猛地抽回了手。
雨宫由里奈微微皱眉,显得有些困惑。他后退半步,眼神四下游离,就是不敢同搭档对视。
“凉司先生,只要握住我的手就结束啦。”他听见由里奈小声的提醒,或许在她看来自己只是忘了剧本。
“……不。”凉司摇摇头。
“我不能接受它,对不起。”
要他用这双曾沾满鲜血的手去牵那双济世救人的手?他怎么可能做得到?
舞台上的气氛瞬间降到冰点,他与雨宫由里奈的单元剧就此收了尾。哪怕帷幕降下,女性一脸担忧地跑来问他怎么了,他也只是杵在原地缄口不言。
不过,渡边凉司深信自己已经找到答案。

旁观者视角,算是对人设的补充
随笔,且做饭后谈资
——————————————————————————————————————————
姜师兄走了,我送他下的山。
那天天很黑,没有月亮,林子很静,能听到落下的松枝被踩断的声音。坡陡,深一脚浅一脚倒也走得快。他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
我问他,为什么要挑这阴气最重的时候走。
“人少。”他没有回头,只是急匆匆地赶路。
冷风飕飕地吹,我打了个寒颤。大晚上的被胡咯起来,连夹衣都忘了穿。
一点生息也没有,静得让人发毛。师兄脖子上胡乱挂着的红围巾在黑夜中飘舞,晃得人眼睛生疼。我迷迷糊糊地想到,我第一次踏进观里的大门,第一次见到他,他就戴着那条老旧的不知落了几层土的围巾,无论寒暑,都没有摘下。
我想起这些,忽然鼻子有点酸。可能是天太冷了,我想。我揉了揉眼睛。
“哥,”观里我和他最亲,外人面前我叫他师兄,私下里我管他叫哥。“一定要走吗?”
“师父叫我去。”
“可是师父他不是……”我们口中的师父,上一任住持,已经仙逝多年了。
一阵沉默,我看到他的手微微颤抖。
……
“当年我们家穷得要饿死,爹娘求当时云游的师父带我上山。”
“他说,行啊,不过每天要打两份柴,担三次水。”
“我从小吃惯了苦。我说,只要能吃饱饭,让我打几份柴,担几次水都可以。”
“我就上了山。戴着我娘给我的红围巾。”
……
“师父教我道法,我学得快,他很惊讶。我说我从小就能看到一些奇怪的东西,他突然笑了,说没有看错人。”
“后来他病了。”
“病得很重,做了斋醮,请了灵符都不管用。”
“他把我叫到榻前,说,别哭,为师是要得道成仙了,你们应该高兴才是。他握着我的手,跟我说,要出去看看。”
“我说,看哪天给你领回来个徒孙。他哈哈大笑,说我真是他的好徒弟。”
“他走了。”
“我舍不得他。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又在观里待了三年,算是守孝了。”
“现在时候到了,我得出去看看。”
……
师兄很少一次说这么多话,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他顿了顿,又说道:
“娃,我走了就没有人给你开小灶了。”
他终于转过头,咧嘴笑了一下。我看到他的眼圈红了。
我的泪也簌簌地流下来。
……
不知不觉到了山脚,我站在一棵老松树底下,目送他渐行渐远。
我想,我早晚也要出去看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