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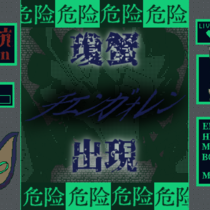








你猜怎么着?这篇文章有《希弗·史密斯,瓦尔基里》的call back!(https://elfartworld.com/works/9625988/)
以及,是的,我写到最后又不是很清楚该怎么写了,sad,毕竟希弗就是这样一个比较自私又有些执念在心里的人,你让她奉献自己去打世界boss很难的啦……除非答应给她一栋楼啥的。
我也一直在担心我会不会把希弗的角色弧光搞得很奇怪……我希望没有>.>这么看来的话,我一开始给希弗的人设就有些单薄了,导致后续的角色发展束手束脚,额……好吧,说的够多了,感谢你的阅读!
“希弗,长大以后你想干什么呀?”记忆中的脸庞模糊不清。
“我想成为像爸爸妈妈一样厉害的铁匠!”记忆中的声音蒙上了一层雾。
“这孩子真是,一点天赋没有……趁早放弃吧。”记忆中的色调晦暗不堪。
“这真的是你的作品吗?好吧……我和你妈先回家了。”记忆中……
唯有鲜血弥漫。
如铁器上的锈。
从创口去深入。
内里完全腐朽。
被啮咬,被刺穿,被腐蚀,被……
“额……我操……操,他妈的,这他妈啥啊!”希弗不知自己昏迷了多久,但当她睁开眼时,身边已经围满了漆黑的荆棘。荆棘一点点向她靠近,将她刺得鲜血淋漓。她抓起锤子,硬生生撞开了一条路。
倦怠。这是希弗在橡林镇里穿行时所能感受到的一切。肉体上的疼痛,精神上的孤独,还有某种更深的东西。她不愿细想,但她害怕,她害怕自己像一块生锈的铁,从一个红褐色的小点向内深入,最后变成空有其表的壳。她不知道生存的压力和自我的认知哪个需要优先去考虑,但她知道她停下脚步就会死掉。
“妈的,血注的人都去哪里了……这鬼地方他妈的比城里还乱!”棘骨如同潮水,从面前的路上涌来,希弗来不及多想,一脚踹开身旁的房门,冲了进去,把门砰的关严。她背靠着门,瘫在地上,拿出碎了屏幕的手机。
“凯莱布,你要是还能回消息的话拜托告诉我我该去哪儿待着,你他妈把我放下之后我他妈差点死路上我操你……“希弗愣了一下,还是把没说出口的那个字咽了下去。她闭上眼睛,脑子里被门外杂乱的声音充满,让她浑身不自在。
“希弗……“
“希弗·史密斯……“
“我说过的吧,你的灵魂……“
“你要如何在这深渊之中……“
希弗有点犯恶心,不知道是谁凑在门边上低声叨咕。按理来说橡林镇的壮丁都被抓走献祭了,怎么还会有这么一个男人闲的没事跟她说悄悄话?她干呕了一下,把窗帘掀起一个小角,看到外面几个漆黑的骨头架子正在朝着一个方向缓慢前进。希弗眯起眼,感觉这群人跟那个巨人有点像,身上还散发着一种熟悉的气息。“啧,这怎么一半瓦尔基里一半死棘的,这不是瓦尔基里的地盘吗……”
希弗盯着她们看了一会儿,盯着她们从这头走到那头,再也没有回头,这才放下心来。她走进厨房,找了个绝对安全的小角落,开始整理自己的随身行李。手机屏幕碎了,三角铁的铁棒丢了,车钥匙也没了——她的车大概率已经被巨人踩扁了,要么就是被裂隙吃了。希弗有些泄气,但好在她的锤子还是一如既往的靠谱。希弗把锤子抱在怀里,缩在角落准备小睡一会。莫名的倦怠涌上大脑,希弗很快就昏睡了过去。
希弗不知自己睡了多久,只知道她的四周陷入了一片漆黑。一切声音都归于寂静,只在远处传来叮叮当当的打铁声。希弗想要起身,却觉得身体异常沉重。她几乎用尽了自己的全部力量,才从这黑暗的泥沼中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她拖着自己的身体向着声音的方向走去,好像她的灵魂本身在寻找那遥远的声音。她看到一个瘦弱的男孩拿着一把不适合他的锤子,像锄地一样在铁砧上敲着。希弗喘着粗气,觉得眼前的场景太过熟悉,却又认不出那男孩究竟是谁。她下意识走上前去,拿过锤子:“你这动作也太外行了,来,看着,打铁是要这样打的。你要让锤子去带动你的身体,让它在铁砧上弹跳,就像这样。”希弗非常自然地敲打起来,如同一个老练的铁匠。锤子在铁砧上发出清脆的响声,让希弗的心情也好了不少。
“姐姐,你好厉害啊。”
“那是当然,我在做我自己喜欢的事嘛……”希弗低头看向小男孩,小男孩却不见了踪影。她听见液体滴落的声音,不敢低头看向铁砧,手里的锤子却自然落了下去。那声音她再熟悉不过,那是一块优秀的原料被敲打成作品的声音。
啪唧。希弗低头,看到一片血肉模糊。小男孩的半个头颅成了肉酱,粉红色的脑组织还在跳动着。男孩的嘴仍在动着,向外不断涌出着鲜血和希弗不愿去理解的话语。哪里有什么铁砧?只有希弗再熟悉不过的街道,再熟悉不过的原料,再熟悉不过的锻造法。鲜血几乎要将希弗淹没,熟悉的声音随着粘稠的猩红一同涌入耳道。
“你当真是一个铁匠?”
不知究竟是因为来自“他”的质问还是震颤大地的一声惊雷,总之希弗从角落里惊醒,出了一身冷汗。她费劲站起身来,确定刚刚的一切都只是梦,然后找了扇窗户。
窗外简直就是地狱。暴雨敲打着窗户,哭声,喊声,鸣笛声,尖叫声,不绝于耳。窗外漆黑一片,不是夜,而是蔓延的荆棘。
“啧,那个鬼东西是她们说的那个邪教头子吗……”希弗看着空中一个巨大的黑影翻腾着,不断用手中燃烧着紫火的军刀切削着巨人的身躯。巨人愤怒的挥舞着爪子,身上干脆利落的断面迅速长出全新的骨头,然后又被砍下。
“啧啧,真是把好刀……我草你妈妈什么玩意!”希弗正看得入神,一坨死棘却拍到了玻璃上。缠在一起的荆棘扭曲地翻开,露出一张仅剩些许皮肤的脸。希弗感到本能的反胃,在那张脸发出尖锐的叫声,尝试打破窗户冲进来时,她的反胃更严重了。但她来不及干呕,就看到那坨荆棘背后,一群又一群跟它一样畸形的怪物听到了刚刚的尖叫,纷纷向希弗的方向冲来。希弗感到同类的气息越来越浓,立即转身向门外冲去。她刚摸到门把手,就听见身后玻璃应声破碎。她踹开门,随手击碎了路边的狩骨,然后挥舞着锤子穿过堵路的荆棘。她掏出手机,看到凯莱布发的位置信息,心理多少安心了一点,但这安心感很快就被一根破空的暗箭打破。希弗急忙扭转身体,却还是被射过来的荆棘划伤了脸。身后的半瓦尔基里半死棘怪物快步向她冲刺,还有人在硬生生掰下增生的骨组织当作箭矢向她射出。
“他妈的,这儿是地狱吗?地狱都没有这么多怪吧!”希弗觉得这场面她绝对在某个游戏里见过,但眼下,她唯一的出路就是跑,不顾一切地,转身,跑,越快越好。荆棘像是有自主意识一样,从地上钻出,从小巷涌出,没有时间清理,跑,就算衣服被撕裂,就算脚底被刺穿,跑。身后的怪物仍在尖叫,脚步声从未减缓,仿佛不知疲倦,它们在跑,希弗也在跑。
“疲惫了吗?”希弗不知是谁在问自己。她抬起头,看到那团巨大的黑影从她头顶掠过,留下一阵能扼住咽喉的裂隙气息。
“是你自己把自己丢进了这深渊之中。”希弗掏出三角铁,用锤子不断敲打着,但身后巨大的怪物堆却一点没有停止,前面的怪物停下了,后面的怪物就会涌上来。
“我说过的吧,希弗?“希弗觉得她能看到……他。从玻璃的倒影中,从磅礴的雨水中,从渗出的血珠中。他注视着她,似乎不存在,却又无处不在。希弗越是跑,他的声音就越是清晰,越是难以忽视。他只是盯着希弗,在希弗看得见或看不见的各个角落盯着她,仿佛在观赏一场结局已知的戏剧。
“我说过的,你会被放逐的,孤身一人。而这都是你咎由自取。“
希弗停下了脚步。
她又回到了那黑暗之中。
身后的怪物,荆棘,橡林镇,似乎全都陷入了停滞。希弗抬头看向天空,一道明显的界限将晦暗与阴影分割,希尔维亚正又一次掠过她的头顶,胸口的裂隙迸发出浅紫色的光芒,但她此时此刻正在空中停滞,一动不动。就连雨滴也停滞在空中,呈现出完美的球形。在这黑暗的正中央……他正站在那里。她走上前,与她自己面对面。他自己倒是波澜不惊,只是拿着一块被鲜血染红的抹布,默默擦拭着铁砧。
半晌,他先开口了:“你把我的铁匠铺弄得很脏,我费了很大力气才打扫干净。“
“这里也是我的铁匠铺。“
“真的是铁匠铺吗?这里只有一个铁砧,连炉子都没有。如果这就是我们的铁匠铺的话,那太可惜了。“
“我有炉子,在家里。我自己亲手搭的。“
“但它熄灭了。你也知道父亲说过什么吧。炉子熄灭了……“
“……就很难再点燃了,我知道。“
沉默充斥着他们的“铁匠铺“。
“……我一直能听到你的声音。”
“那是你内心的声音而已,我只是替你说出来而已。”
“……为什么?“
“什么为什么,这话应该你问你自己,会有这样的顾虑不全是你的问题吗?你也问心有愧吧?“
“……我是说,为什么是现在?是在这里?“
“哦,你是说这个啊,我还以为你敲人把自己脑子敲傻了呢。“他笑了,希弗也笑了。他笑完了,却露出惆怅的神色。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如果你问我,我大概会说可能是因为你越来越接近裂隙了,或者就是那个邪教头子在从中作祟。毕竟你就是这么想的。但这不是你想要的答案,答案需要你自己去寻找。“
“但我要怎么……“
“我也不知道。你把自己丢入了虚空之中,你让自己深陷绝望与孤独之中,你欺骗自己,你苟且偷生,你靠着嗜血的欲望度过了一天又一天。到了这种绝望的地步,你甚至不能像某种主角一样,大喊什么……‘我所做的一切都不是白费’,或者‘我还有我的朋友们在身边’。毕竟你的情况只有你自己最清楚。“
希弗没说话。
“你甚至都难以称呼自己是一个铁匠。“他收起抹布,向着黑暗深处走去。
“喂……喂,等等!你要去哪儿?“希弗从恍惚中抬起头,向前赶了几步,朝着他伸出手,但又下意识地停下了脚步。
“向前。你也要向前了吧。不过……你的前方不远处就是一条死路,周围没有任何出路,跑到那里,你就是死。你当然也不可能回头了,你的来路已经被吞噬了。你当然也不可能留在当下。这里很快就会消失的。你一直以来走的路都行不通了,不是吗?“他回头低语,声音却仿佛直接传达到了希弗的脑中。
“……你还会回来吗?”
“或许不会了。你还想我不成?“
“鬼才会想你。我只是……很想当一个真正的……“
他没有回答,也没有回头,更没有回应。他只是一路向前走,直到他淹没在一片漆黑当中。希弗低下头,看到铁砧正立在她的脚边。她伸手抚摸铁砧,铁砧坚硬,粗糙,让她感到熟悉的温暖。她感觉有些难以呼吸,握着锤子的手却自然而然地抬了起来。
叮。
希弗感到一阵震颤,她右手有些发麻,眼前也冒着金星。她扶着她能扶住的最近的东西,大口大口喘着气,她隐约看到眼前密密麻麻站着一大团黑影,下意识伸出了锤子,准备保护自己,但当她眼睛重新对焦时,眼前站立着的却是仿佛失去意识一般茫然战栗的变异怪物。她后退两步,准备跑路,却看到地上那异常熟悉的铁砧。
“一直以来走的路……是这样吗。嗯。”希弗微笑,然后笑容又消失在脸上,“这玩意到底该怎么带走……应该也算我的灵装,咋整呢。”她把锤子揣进兜里,准备把铁砧搬起来,结果发现它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沉。
“我靠,好像也不沉?”她把铁砧放回地上,又明显感觉到整个地面都震了一下,“我去……“希弗举起铁砧,脸上洋溢起笑容。
之后?之后啊……之后希弗发现铁砧抡起来比锤子杀伤力还要大。但她感觉自己胳膊要被拉伤了,所以她左手把自己的新铁砧夹在腰间,右手拿着锤子,就这样跑向血注的临时据点。
额?哦,有关邪教头子和疯子巨人的决斗,希弗说实话不管这个的。她连命都差点丢掉了,哪里还有心思为世界和平作斗争?或许他改变了什么,或许他什么都没有改变,希弗或许还是那个嗜血成性的希弗。
但是,当她带着从未有人见过的笑容到达临时据点,把自己的新铁砧往地上一丢时,她或许真的找到了一条新的前路。
只是血注的成员们必须得把她拦下来,不然她就要把整个屋子的铁器都丢到铁砧上一顿乱敲了。
她到底会不会打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