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止是个捡破烂的么,总穿破烂衣服。只有件冬衣,过节了才拿出来穿,也很少洗,有一次托人打理,老板发现流苏打了个结,就问,我帮你拆了吧?徐止说拆了就不会打了。老板说,我教你。徐止说,我会。老板不明白了,留着那个结没敢动。
来拿冬衣的时候,发现徐止果然是会的,因为他尾巴上有同样的结,只不过拴着块骨头。那骨头是姐姐徐行的,徐行给徐止打完冬衣上的结,第二天就死了。
人生缓缓,徐行徐止,那结却打在了徐止的骨头上。
于是元宵热闹,却没有去的必要。岭南遥远,同姐姐被骗来后再无识途的本事。所以前二十年,除了他自己的破屋,待最久的该数太和观。
少时野猫命贱,夜里以天为盖,以地为席,若运气好,能从朱雀大街捡了残食口粮,再去观里菜园便可以睡个好觉。后来他就在菜园里捉老鼠——这是个不值当的差事,或言元人将异人当畜生使唤,或言没人管教这可怜孤儿……
但那都是人言,人言便是无用的。
徐止不在乎那种东西,其实做人也好,做猫也罢,都活得不是东西。何况他确实擅长捉鼠,夜视如白昼,手脚轻而快,身过无痕,又不监守自盗,道士们很喜欢他,总说去屋里睡,他不干,只留那草棚里。
他和其他孤儿处不来,只同道长聊天。有新来的道长问,你为什么拾荒,却不拿观里的东西?徐止说,观里的东西是观里的东西,不要的东西是不要的东西,我只拿不要的东西。
他停一下,又问,我是不要的东西吗?从那以后,观里的人便不怎么逗他,反而和他讲起老庄来。
徐止面色寡,又没表情,听与不听并不明显,睡与不睡十分相似。有一次道长问,小白,我方才说子非鱼,你点了点头,是有什么要说的?徐止说,我想吃鱼。
问白是他的字,却很少对外说。
这样的野孩子居然有字:徐止骨子里和姐姐一样都是很温和的,因为他是雀猫,雀猫说到底还是猫,有毛茸茸的一颗心。可是姐姐那样温和,死得还是那样惨,他便不明白这世道,什么是黑,什么是白。
徐止,字问白。不是徐行给他的,是徐止自己改的,他姐姐最开始入了青楼,学了诗,欢天喜地给的徐止的,叫信白。
妓子不见白发,道士不通鬼神,百姓不救天下。
这次他又回来,故人老的老,死的死,问他子非鱼的那个道长还在,说,小白怎么和十年前没什么变化啊。
徐止就说,哦,我长生不老。
道长对他这张嘴见怪不怪,问,来捐冬衣吗?徐止说,也想捐命,主要是不能。
他轻车熟路,几步就到了地方,还能帮上些忙。道士们陆陆续续认出他来,要徐止留下来。徐止问,有鱼吗?道士说,有老鼠。徐止说,你狗拿耗子。道士拿拂尘打他。
但最终还是留下来吃了饭。徐止不愿和人坐在桌上一起吃饭,自然而然地失礼:捧着碗,碗里夹几筷子肉,去爬那棵桃花树,在树上一口两口,把青菜叶子吃得脆响,不知道的以为他在嚼树枝。
道士找他不见,出来一看果然在这。又骂:造孽!七八年前不是你踩断它的?快下来!
徐止说,我同它叙叙旧,它说别来无恙,身体尚可,搭我一刻,并无问题。
道士恨不能把树砍了,把这该死的猫一并弄倒:“树上还要挂灯的,你再胡闹,晚上留下来帮忙!”
徐止说,管饭么。道士说,我们又不是黑心商人。徐止说,我自然知道,毕竟你们比我还穷,只能管饭了。道士说,你这黑心商人。徐止说,我天人合一。道士让他气死。
他手脚依旧快,做完也不吭声,仍是去打一碗粥,领份咸菜,去菜园吃。那棚子早没了,换一座小瓦砌的房,徐止坐在顶上,像猫猫土地神。
酉时三刻,未至人定,天要黑了。他找到一块地,左右翻翻,把怀里锦囊埋了进去。又对那破烂土地神拜一拜,说,老鬼,你帮我存好,我来年来取。若没命来取,你也不要让人捡了,这不是不要的东西。
他又停一下,居然笑了:我才是不要的东西。
十五夜,祈福者众。夜中烛光温润如玉,散落街头,零星成线。游人往复,烟火半勺,泼了满空。其中徐止点灯百盏,却未求一个愿望。
道士送徐止下山,问,你怎么不去考个功名,或者去行会做些正经生意?拾荒到底不能长久。徐止难得笑了,说,老家伙,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
海家家主按惯例大摆宴席,左右觥筹交错,他明里暗里谈完几桩生意,正闲走,一路上左右搭话,话没停过。宾客来往间,忽然看到只眼生的猫,沉默寡言,啃着鸡腿,那扇子一合,转了步子走过去攀谈。
徐止说,我是『百宝回』的当家。海霁说,我没见过你。徐止说,我前年也来过。海霁上下打量他,问,是吗?
徐止说,是的,我那时是『百宝去』的当家。海霁说,那不是同一家吗?徐止说,好像是。
这邋遢的猫说:“我随我哥来的,我哥叫我给海兄问个好,说你家的槐花树,这两年若是漫过墙沿,就该修剪了。”
偏偏海霁的正房旁确实独有这棵树。
他听了这一嘴,问,你哥是?徐止张口就来,我哥姓白,我也姓白。他是大白,我是小白。海霁欲言又止,心想,这世上该死的姓白的应该没这么多吧。
但是他面上无波无澜,端的是清风明月,笑:“那,小白老板,玩得尽兴。”
徐止确实尽兴,他吃饭时看到旁边有人私藏违禁火器,顺手摸了。别人临走时发现了,暴跳如雷,要找海霁理论。海霁岿然不动,笑里藏刀,只说,海某今日包了场,便敢包这话:今日此地,未,曾,进,过您说的东西,若不信,大可报个官彻查。敢问客人丢了什么?
那客人暴跳如雷,心说方才一顿饭,你我还商量了如何购买,谈笑风生,全是放屁,现在转头翻脸不认人,怕是帐也做不下去!可是嘴上还哑巴吃黄连:难道和镇安司说,你们前几日缴的火器,我丢了一把同样的,麻烦你帮我抓抓贼?
贼乐得开心,回到家里一一拆了,倒也不卖,这丁零当啷的,比毛线好玩。
徐止收拾好了,去符逸店里转一圈,问,这个怎么卖?符逸看一眼,说,二两银子。徐止说,黑心。符逸说,同行来问价,不黑心便是好心。
徐止说,你也可以好心,十两收了,我告诉你谁做的,你再去镇安司报个案。符逸说,徐止做的,他今日来典当火器,还造谣我哄抬物价。徐止说,黑心。
符逸说,那怎样才不算黑心?徐止说,咱们互相都能帮助对方进一回镇安司,此谓生死之交。符逸点点头,笑意更加浓郁:二两银子确实黑心了,还是给小白老板十文钱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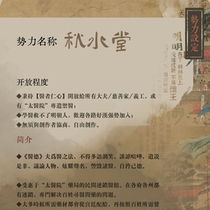




当丝线与尸骸组成的假体出现在葛瑞福斯眼前的那一刻,木头被撕裂的声音在安静的森林里格外明显。几乎是瞬间,葛瑞福斯将对准诱饵的剑转向了侧边,闯入视线的琥珀色眼睛同时也转动着调整视线,最后饱含恶意地对准了自己,八只……还是十只?葛瑞福斯没时间去数清那颗巨大的头颅上有多少只眼睛,那张一开一合的口器中有多少利齿。
之前袭击难民的真凶,人们口中传说的“噬魂暴君”此刻就那么明晃晃地站在在树枝与树枝之间,尖利的后肢劈进树木地站着,似乎不毁坏一下所过之处就感到不爽一样。镰刀状的前肢间隙里布满了卵囊,葛瑞福斯几乎能看清楚里面挤满了的神经和血丝。
一只阿兰托迪亚,长得跟蜘蛛一样的怪物,怪不得会设陷阱这种把戏。葛瑞福斯想起之前被丝网缠绕住的孩子,他还能回忆起血液是怎么从白色的线中溢出的。而现在,像这样受到残害的人类难民们因为被卵囊里的神经寄生控制而一群群地围绕着那只怪物。
他该庆幸那个孩子最起码没有成为傀儡吗,最起码不用与他为敌。
耳边突然划过一阵气流,由血液凝结成的箭矢朝着阿兰托迪亚身边的傀儡射去,倒地声接连响起。
“不要愣着,这是塞勒尼斯,智力很高。”艾德的声音响起,一根根血红的箭矢在半空中围绕着他,刚刚的血魔法应该是他放出的。
那只怪物巨大的钳子探向地面,想要将这群见到自己真身的血族全部变为傀儡,卵巢里竹节状的神经蠕动起来,渴望能驻扎在其他生物的后颈里。
“这可是场豪赌。”葛瑞福斯低声自言自语道,身边血魔法的气味浓郁起来,队友都开始行动了。
眼看着锋利的爪刃就要抓到自己头上,葛瑞福斯朝前疾跑避开钳子前段的卵巢处,塞勒尼斯巨大的口器就悬在他的头顶上,牙齿缩紧着就要喷出毒镖。他转过身抬起剑,改反手握住剑柄将剑结结实实地插在了塞勒尼斯的下颚,怪物坚硬的口器卡住了剑锋,下一秒,葛瑞福斯借助剑柄的支撑将自己吊在了空中,毒镖喷在了他原本立足的地面上。
葛瑞福斯感受着逐渐湿润的空气,被腐蚀后的地面上出现了一道血痕,过了几秒又消失不见。他在心里估计了一下自己血魔法的威力,虽然不足以直接摧毁掉对方的脑袋,但至少可以将口器毁掉,让它没办法再喷射毒镖,为那两个家伙争取点时间。
葛瑞福斯抓着剑柄往前荡了几回后,附着在剑锋上的血魔法瞬间迸发。失去了着力点,葛瑞福斯借助惯性甩着剑飞在了半空中,剑插进了塞勒尼斯在空中挥舞着的左前肢钳子间的卵巢,重力让沉重的剑毫不费力下滑着斩断了那些卵囊,血管和被切断的神经在空中飞舞溅在了怪物的脑袋上,破碎的血膜随着微风摇晃,而葛瑞福斯已经沿着计算好的角度和前肢的利刃擦肩而过。
而由于卵巢的阻力,葛瑞福斯甚至只是滑行了一段距离,没有摔倒。
葛瑞福斯撑着剑站了起来,他正好停在了埃莉诺身边。刚刚葛瑞福斯砍掉左前肢卵巢的同时埃莉诺也解决掉了右前肢上的,现在他们不用担心这些恶心的卵巢和毒镖了。
“你的祝福挺有用的,我的头没被打掉,但是那些卵着实恶心死了。”
埃莉诺提着还沾着血的枪,指了指葛瑞福斯的左后方。
嘶吼声在身后震起,葛瑞福斯迅速反应过来,挥剑准备砍向身后袭击自己而来的傀儡,却见着了傀儡被血箭矢没有分毫偏差地穿刺了脖颈,直直倒在了地面上。
傀儡倒下后,被它遮住的身后也露了出来。带着面具的艾德维亚闲庭信步地走在傀儡军队之中,随着他的移动,一旁的跌跌撞撞扑向队友的傀儡一个接一个的倒下。漫天飞舞的血箭仅凭主人的想法收割了一条又一条生命,方圆五米内无人近身,无人存活。
葛瑞福斯将剑上残留的神经甩在地面上,空气中突然凭空凝出来了血液将那些神经碾成了渣。耳边似乎传来了喃喃的咒语声。
“谢谢了。”葛瑞福斯不知道是对着谁道了句谢后再次举起了剑,上边金色的花纹在血液的洗刷下反而亮眼了一些。“埃莉诺,我去解决右前肢。你去左前肢,那边有艾德维亚。”
“好的,葛瑞福斯先生小心一点,帕杰德先生也在右前肢附近。”
“我会去找他的,你要是撑不住的话暗示一下,让厄尔给你开个盾。”葛瑞福斯提着剑避开了头顶落下的傀儡,干脆利落地将对方斩了头后再次奔向了塞勒尼斯。
被疼痛激怒的塞勒尼斯反复将尖利的足尖扎入地里再拔出,葛瑞福斯刚再次投入战斗就看到了帕杰德在足尖与足尖的缝隙里灵敏地穿梭着,星星点点的血色痕迹附着在那些后肢上,而他们的使用者清理傀儡的速度完全没有减弱。
见着破坏自己口器的凶手,塞勒尼斯挥舞起了前肢,卵巢遗留下来的透明粘稠状液体和血液混在一起随着爪钳的摆动散发出腥臭味。对前肢攻击的躲避使葛瑞福斯没有时间去蓄力一击,平日里的攻击根本砍不断怪物被甲壳保护住的节肢,只能留下一些伤口。
葛瑞福斯握紧了手中的剑,准备试着集中攻击一下前肢的根部,那里或许会更加脆弱一点。
可突然,一个身形似小孩的傀儡闯了过来,眼神中没有光采,却足以让葛瑞福斯楞神了一瞬。而塞勒尼斯那颗不怀好意的脑袋上一半棕色的眼睛早就带着狡诈望向葛瑞福斯了,就这失神的一瞬,它已经抬起来的前肢就准备落下了,被炸的血肉模糊的口器蠕动着近乎要发出笑声。
可那只喜欢设置陷阱欺骗人类的塞勒尼斯却偏偏在这种时候利爪有了误差。在塞勒尼斯已经见着自己将面前毁坏自己口器与卵巢的敌人割裂成碎片时,却突然发现那家伙正完好无损地站在自己的爪钳旁边。
两个从战斗开始就不在它视线范围内出现过的血族这时候却突然蹦了出来,一个浑身不沾一丝血迹地站在树林间,一个则拿着权杖半跪在地口中念着咒语。这时塞勒尼斯才发现自己的利足下是已经布置好的法阵。
塞勒尼斯刚准备破坏地上的法阵,葛瑞福斯却拎起了剑重重地砍向它前肢与躯体的连接处,不偏不倚,血液从整齐的切口喷涌而出。
“送上门的弱点。”
塞勒尼斯的巨眼中满是惊慌失措,而埃莉诺也早就准备好,一枪捅入早就一直着重攻击的伤口中,血魔法钻入钳爪,瞬间的爆发使塞勒尼斯左前肢的碎肉上还挂粘着外壳。
右边三只利足也被帕杰德提早渗透进去的血魔法爆了开来,惨状堪比左前肢。葛瑞福斯突然觉得自己整只砍断的处理方法算得上仁慈。
口器的事另说。葛瑞福斯想着,和其他的血族一起退出了法阵之外。
一直念着咒语的路西终于停了下来,法阵的魔力让他金色的长卷发飘在空中,他单手撑着地面,紫色的瞳孔中映照出法杖顶端宝石发出的亮光,在漆黑的森林里格外明亮。一旁整洁的厄尔庇斯一脸兴致盎然地看着失去了一边所有节肢的塞勒尼斯像是穿了滑轮鞋的蜘蛛一样,挣扎了半天也立不起来身子,空气中的湿润逐渐消失了。地上的法阵发出了亮光。
“砰。”厄尔庇斯适时地卡了个点。
瞬间,几乎不等塞勒尼斯发出哀嚎,在一片亮光之中,残留的傀儡与塞勒尼斯剩余的肢体一起被炸成了新的血雾。
“是个好配合。”葛瑞福斯拉起自己勇火的斗篷隔绝了血腥味并评价道。“愿受害者们安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