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共计3032字。
-
一
“…该洗洗了。”
他生怕对方没有听懂,又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说辞:“我说你,该去洗洗了。”
这是归海青上下打量了一番,像是做出什么决定一样才郑重开口的。在某种意义上他说的一点不错,千真万确,面前的这个家伙是应该好好清洁一下自己——到不是说归海青有多么爱整洁,而是那人脏的太过分了一些。
他的头发,触感甚至比看起来更加糟糕,并且这种邋遢感并不局限于此。可以说他全身都是脏兮兮的,归海青看着这惨不忍睹的模样犹豫了许久,总算是以一副严肃口气将这个事实陈述了出来。他显然知道被这样要求后这家伙会拒绝,所以干脆直接一手抓住对方的衣领,一手提起一桶水开始忙活。
归海青当然没有给别人洗过澡,他就这样粗暴又蹩脚地将纠缠不清的发丝理顺,在意到被自己牢牢制住的人的挣扎后反倒用双腿夹住他的腰部,解下了那个扎起某人稻草般头发的发圈。
那很普通,就是平常用来束发的细绳而已,看样子还用得有些旧了,谁都能看见那上面浅浅的磨损痕迹,除此之外它便没有任何奇特之处了。取下它的少年把玩起这小东西,连压制住眼前人的性质也在那一刻消散掉了,他久久没有出声。
“……”
他托着下巴,专注的顾不上眨眼,那样子像是不把这东西的最里层看穿誓不罢休,但却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是看些什么。
后来,他的眼睛像是捕捉到何物似的突然黯淡下去,那并不是沮丧,而是陷入了某种深层次的思考。夹在景箫腰上的力量也放松了些许——他总算是因此喘过了一口气,却在抬起头的时候看见了那双无光的蓝色眸子。足足有数秒钟,没有任何多余的色彩进入这两汪纯粹的蓝色之中,它们专注而又毫无波澜,像是某潭深不见底的死水——他怀疑起自己注视的是否真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非什么精致的人偶。
只不过相比被遗弃的玩物,他那柔软散乱的发丝也太过真实了——倘若这真是出自人手的被造物,那两块纯蓝色的琉璃中夹杂的温柔神情,便只能用鬼上身来解释了罢。
归海青凝视着躺在手上的物品,那个躺在他白皙手心中的小东西,他像是察觉不到身旁人的视线一般,重复着收束五指又松开的动作。那上面还保留着发丝的残温,或是某样其他的,但事后他本人怎样也无法想起那一时是什么吸引住了他,只得对着自己或者是询问起它的人耸肩糊弄过去。
思绪飘到了哪里呢,在短暂的走神后少年受惊般浑身一抖,从不晓得内容是什么的白日梦中醒过来。最初他还迷糊着,然后就被拧了一把大腿。
“…?”
他看见面前的人明显是露出了困惑的表情,毕竟从来不会有人会对着一个发圈发愣。“…没什么,”归海青将它挽在了手腕处,“最近有点容易发呆。”他这样解释,虽说这理由连他自己都信不太过,但总不能说“我看到它就失了智”吧。
…大概如此。他将最后这四个字咽了下去。
很快他们就回归正题,打闹似的开始争执起来,这小插曲还是在留有一个疑问的情况下不了了之了。
最后当然是顺利的完事——或许称得上顺利吧,虽然被逼着洗澡的家伙不情不愿,但至少在一场混战后达成了目的,少年终于可以正大光明又心安理得地将下巴搁在景箫的肩上,顺带满意地说出“这还差不多”的台词。像是什么动物的本能一样,他又半无意识地拿脑袋蹭了蹭旁边人的脸。
“…那铃铛最后怎么样了?”他突然发问,提起早上的事情,不能确定这家伙是真不清楚还是假不清楚,还不忘补充一句,“你扭头干什么。”身上有个人趴着,这样是很自然的事情吧——很久很久之后归海青回忆起当时,觉得有点好笑,这句话在对方那儿肯定就只差说出来了。
……早上…吗。
对于那块废墟的清理工作也逐渐迎来尾声。在收拾最后一些零碎的建筑物残片时,同行者玩弄起在那一片狼藉中发现的铃铛,也说不清为何人总是会执着于一些本身不太重要的东西,他将铃铛有些变形的外壳敲打回原来的模样,坐在姑且算是空地的地方摇动着。归海青撑着下巴,注视着他的动作发愣。
要说随后发生的事,大概就没有那么和平了。
“我说……”在归海青想要开口提醒景箫,可惜还是晚了一步。不知道从哪来的小家伙突然窜了出来,以那个发出声响的铃铛为目标,和持有者扭打作了一团。当时的场景无非是“喂把铃铛给我一下”“给个锤子”一类的,起初归海青不太理解为什么要为了一个铃铛大打出手,他本打算去劝架——那自然是没有成功的,甚至还在略微保护住了(看似)弱小者之后被反咬一口,彻底卷入了战争。在那之后他就不知究竟是谁在打谁了,不知道谁出的拳头甚至还打到了自己稍微有点肿的脸——那是前些天在这里被揍出来的,如今没有彻底痊愈便又吃了一拳,看这样子又得痛几天了。
“…给我他妈的停一下停一下!”
归海青被地上的灰土呛得停不下来,在把这句话完整骂出来的时候他没忍住在内心狠狠感谢了一把自己。当全部的尘埃散去,最终呈现在眼前的景象本可以令他震惊的——但他实在没有力气了。
起先来挑事的罪魁祸首已经不见踪影了,也没有再看见什么铃铛。归海青乏力地瘫倒在地,后知后觉地感受到自己的腰部有被重物压住的感觉。他很快就发现景箫跨坐在自己的腰上举着拳头,手腕也被这家伙当做是惹是生非者的手死死抓住,如果再晚些制止,自己的另一半脸也要遭殃了,归海青愣愣地想,咽了口唾沫。俯视着自己的人也一副不清楚情况的表情,气氛瞬间凝固在了最尴尬的瞬间。
也就是说,真正该被揍的人早就拿着铃铛跑了,刚刚一直是他俩在互相打对方?
也就是说,他们这种愚蠢的行为不但两个人都没有发现,还很有可能被某人看到了全程?
“…大哥你眼神儿不好吧。”归海青面无表情地总结道,然后觉得这句话用来形容自己也挺合适。
“……”
两个人面面相觑,没有人再发话。
两个人面面相觑,没有人再发话。
归海青从景箫的眼神中读出了“还能咋样,被拿了呗”几个大字。不过好在最后还是把那块乱七八糟的废墟给整理干净了,收获也是相当可观的,今晚也可以暂且放下心来歇息了。夜晚总是比白天要宁静些,他懒散地靠在刚刚被洗干净的人身上,难得地感受到了一丝倦意。为了打破这不知接下来该说什么的氛围,对方比归海青抢先了一步开口。
“你头发有点长啊,要不要扎一下试试?”他一面这样说,一面打量着瘫在自己肩上的男孩。
“你过来。”
景箫示意对方把脑袋凑过去,取下了那个之前被那孩子盯了好久的发圈儿,他已经变得柔软的头发随着动作散开来,残余些还没有风干的水分,不再纠缠。归海青发现他把散发的模样比原先秀气了不止几度,乖巧地转过身任由他摆弄。
“虽然只有一点长度…你不剪掉吗?”
“这样就好。”
归海青捻起一小撮刘海,眯着眼轻声回答道。发尾被拨拿的触感是很明显的,好在发丝打结的不算严重,不然这一片祥和就要被抱怨声打断了。
室外寂静得很,除了两人发出的轻弱呼吸声与束发的声响外再也听不到其余的杂音,若不留心观察,还真的会错认为分秒的运转在这一瞬卡壳。
“…好了。”
不长的等待之后少年甩了甩脑袋,遂后不长不短地“嗯”了一声,看样子还算是满意,他又把视线对上另一人的,似乎是期待着他的评价。
景箫点头道:“挺好看的,要不就给你这么扎着?”
“…但是我拒绝。”归海青轻松将它解了下来,塞回原主人的手中,“散着头发很容易弄脏,你扎回去。”
对方没有赞同,也没有反对,他只是淡淡地应了一声,蓝眼睛的少年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就像是自己对着发绳发呆那时一样,他报复性质地捏了一把室友的大腿,从他身上爬了下去。
归海青回头瞥了一眼被自己要求躺在床上的人,在门边找了个可以靠着闭眼的地方,却只是从墙体裂开的罅隙间向外看去。刚才玩闹产生喧嚣的都如同泡影般消失,现如今只有一片空白。
那外面什么也没有,只不过是空荡荡的明日与可能永远也结束不了的绝望。
那外面是无际的夜晚与永远也接触不到的,天与山峦的边界线。
没多长,3121字,废墟收尾
病了一周半,我觉得我差不多死了
压扁的铃铛不要扔,裹上蛋液,粘上面包糠,下锅炸至金黄酥脆控油捞出,老人小孩都爱吃,隔壁海豹都馋哭了
---------------------
最近几天的天气相当不错。
景箫晃着个铃铛躺在已经被他们收拾得差不多的酒馆废墟上发愣,嘴里还嚼着两颗在火里烤酥了的黄豆。
他们在废墟里刨出了不少东西,有面粉有豆子还有酒,景箫对酒没什么好感,但这么久过去他也只会在别人喝酒的时候说句“喝酒误事”而已。倒是那一袋黄豆得了他的心,少年从里面捞出那么几把来扔进那个平时煮汤烧水的铁锅,用石子和树枝凑合着炒了炒,搞了个布袋装在腰上,没事就捏两颗出来嚼嚼,配着西北风倒也怡然自得。他手里的铃铛也是刚从废墟里刨出来的,它看起来应该是原先挂在酒馆门上的门铃,黄铜质地制作精致,同普通的圆铃铛不大一样,铃铛舌头是个小小的铜水滴,铃身是一圈花瓣似的裙边。酒馆被山石压塌之后它竟然没被压成一块废铁片,只是被压得扁了点,景箫找了块不那么尖锐的石头小心翼翼把它砸回了圆形,还想办法把舌头给捯饬回去了。虽然外层的花瓣被他砸得有点变形,这铃铛还是大概恢复了它原来的样子,除了连着门栓的铜环断了以外基本完整。
归海青在不远处一边整理淘出来的东西一边发愣,一言不发——他好像对这个地方还是不太喜欢。现在这座废墟上只有景箫一个人,这片小天地突然安安静静地成了他自己的。白色的云层从他头上流过,在少年暗红色的眸子里映出一片影子。
“初云”,景箫莫名想到了这个叫法。
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他十五岁,遇见一个名字奇怪的黑发姑娘,那姑娘说话文绉绉的,他连人家的名字都没记住,就记住她说,一年里最初的、雪刚停的那些日子,他们那里的人叫那时候是初云。
一年里最初的,白色无瑕的云。
景箫眯着眼睛,黄豆的香味在他嘴里弥漫开来,伤痕累累的铃铛在柔软起来的微风里轻响。他突然觉得有点累,想要安安稳稳地睡一觉——他很久没有这种安全的感觉了,寂静而安逸,连昆虫的叫声都听不到,就像回到小时候的感觉。
那是他不长的十几年生命里最开心的时间,他甚至在半梦半醒里不自觉地翘起了嘴角。
正因如此,打破这片寂静的人才显得尤为可恨。
海豹妖精站在景箫躺着的石头下面叫他“喂”的时候,他已经基本上睡着了。被人从梦里吵醒本来就让少年腾的升起无名火来,何况那个还没他一半高的白毛小东西还在废墟下面叉着腰一脸的理所当然。
“喂,”海豹妖精开口了,“能把那个铃铛给我吗?”
“……”景箫坐起来看着那个小东西,把烦躁尽量压下去,“我不叫喂,我有名字的。”
小东西点点头:“我知道,但我不记得你的名字了。”
景箫暴脾气突然上来了:“那你就喂来喂去的?这是请求别人帮助的态度吗?”
“少废话,你到底给不给?”小个子似乎上头了。
景箫彻底火了,一把把铃铛扔在旁边:“我给你妈给!”
之后的混战,成了景箫一辈子的污点之一,以至于后来他朝着哪个不记得名讳的神发了誓,他这辈子再跟妖精打架他就是猪。
这一天很快就又过去了。
“别动,不然会戳瞎你眼睛。”
归海青的手劲比景箫想象的大很多,那只瘦削而白的手捏着他的下巴竟然愣是把他没什么肉的脸捏出两团凸起来。
“我不动,你轻点。”少年被捏的声音发闷,他闭着一只眼睛,粗糙的布料正在他的伤疤上近乎粗暴的摩擦,他看在上午差点又揍了归海青的份儿上没挣扎也没反击,“捏得我疼。”
“我如果放轻了你还会跑吧。”
景箫看不清归海青的脸,挣扎着睁开的左眼只看见男孩细细的手臂在他面前晃来晃去。
“我不跑,你轻点……是真的疼。”景箫不敢挣扎,他怕他再挣扎会惹得归海青一使劲把他下颌骨捏折了。
“好,那你不准跑。”男孩依言放轻了力道,景箫终于觉得呼吸的自由被还回来了。
两人之间这场不大不小的战争是从晚饭之后开始的。最近这几天景箫不知是因为觉得找到了放心的同伴还是怎样,总是困得特别快。归海青从外面进来的时候景箫已经开始靠着墙打盹了,丝毫没有注意到那一大锅咕嘟咕嘟的热水意味着什么。
少年惊醒的时候,他的同居者正拖着一桶相当于平日里他们至少半天用水量的水进门。
“你半夜出去打水干什么?”景箫脑袋里一片迷茫。
“你该洗洗了。”归海青的语气十分严肃,好像在宣布什么重大决定。
“啊?”睡眼朦胧的景箫当下没听清也没明白。
“你,该去洗洗了。”归海青重复一遍以后举起了一块巨大且看不出颜色的布料——景箫本能地觉得那东西没比自己干净到哪去。
“我不要!”景箫瞬间清醒,噌地蹦起来就往门外跑。
“你给我停下!”归海青丢下布就去拽景箫的后脖领,伸手抓了个结实。
景箫挣扎着往前跑,拖着归海青和那桶水在地上摩擦:“你把我放开!”
“你先洗澡!洗完我就把你放开!”
然后景箫就被身后人一个虎扑给按在地上压了个结实,归海青好像怕他又跑掉那样坐在他身上,拿两个膝盖夹着他腰,男孩凸出的膝盖骨结结实实顶着他白天被人踹了的地方,痛得他龇牙咧嘴。
“拿掉拿掉快拿掉!”景箫忍不住一边呼痛一边去拍归海青的大腿。
“你不准再跑!”归海青抓着他头发。
“好好好我不跑你松开腿!”景箫已经顾不上等着他的是什么了,只想让背后这个让他感觉随时会要了他命的家伙赶紧离开。
“那你别跑。”归海青好像有点犹犹豫豫地把膝盖挪了个地方,却还不肯放松力道从他身上起来,手里又捏住了他脑后的辫子。
“我不跑我不跑,哎呦祖宗饶了我吧。”景箫被拽得梗起脖子来,归海青拽他头发的手劲不小,他不得不仰着脑袋防止男孩突然发难用那身蛮力把他头皮给揭下来。
男孩摸摸索索地把他头发上的发绳给取下来了,之后便没了动静。景箫闭着眼视死如归地等了半天却没等到哗地浇上来的凉水,偷偷睁开半只眼往后看,却看到归海青正对着他的头绳发愣。
“怎么了?”他心里奇怪。
他记得那东西是一个和自己差不多年纪的孩子送的——之所以说是孩子,是因为那时候他也还是个小孩。还没加入之前的佣兵团时他会接酒馆发布出的悬赏,经常在山野里四处乱跑,有一次他顺手救了一个长头发的小男孩,他自始至终只和他说过一句话,最后却把这个送给了他。到现在少年连他是出了什么事都记不太清了,就记得他始终不肯抬头,皮肤白的像象牙,头发却黑得像夜空一样。
“喂,我说你下什么神儿呢。”景箫伸手拧了归海青大腿一下,那里肌肉的手感好得他一愣。
“……没什么。”归海青好像突然惊醒一样,把景箫那个脏兮兮的发圈套到了手腕上,被他分明的骨节绊在那里,“最近有点容易发呆。你别动,我给你洗。”
那层布蒙到自己头上来的时候,景箫在心里叹了口气,恐怕自己以后要多一个克星了。
对景箫的大清洗终于结束的时候,少年觉得自己像是脱了一层皮,被归海青搓得全身无力。好事是归海青终于放开了对他的禁锢,景箫光着膀子趴在火炉边的地铺上瑟瑟发抖——他的上衣被归海青泡进了水里,要不是他据理力争估计这家伙连条裤子都不给他留。
这他娘的冬天还没过完呢!把人扒光是要杀人吗!少年在心里有气无力地骂。
归海青好像不这么想,他小动物一样把鼻子凑到景箫身上嗅来嗅去,最后满足地把下巴放在景箫肩膀上。
“这还差不多。”归海青拿脑袋蹭了蹭景箫的脸,没等少年做出什么反应就整个人放松了趴在他背上,压得景箫几乎气绝。
归海青身上温凉,大片的皮肤被裸露在没好好穿的上衣外面,贴着他的背让少年觉得寒毛直竖,那头半长不短毛茸茸的头发又在他颊边拱来拱去,景箫竭尽全力才把头扭过去。
“那个铃铛怎么样了?”归海青一边蹭一边发问,还特别不开心似的又把脑袋靠过去,“你扭头干什么。”
景箫瞥了他一眼,心想这家伙真够没常识的。
“那还用说。”他嘟囔了一句。
和那小东西扭打在一起之后,他再反应过来就是自己骑在归海青身上的场景,不仅归海青愣了他自己也愣了,俩人前后找了一番既没看到铃铛也没看到海豹妖精,显而易见那家伙趁脑袋不太管用的景箫跟归海青错误混战的时候带着赃物跑路了。
“……算了。”归海青又放松下来,甚至还像只动物那样眯起了眼睛,压得景箫噗咳吐出一口气。
“……你倒是……给我……起来啊……我要死了……”少年哪还有心想什么铃铛,只能在重压之下发出几近窒息的呻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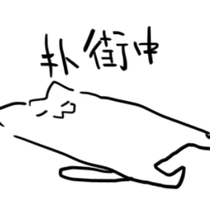
字数:10031
本来不应该相信深夜爆肝的自己,今天应该再看一遍的,改改遣词造句前后连缀啥的,还有可能ooc之类的问题没好好跟亲妈确认过。但今天已经累傻了,甚至左右不分,根本处理不来文字信息。
窗了狩猎,就这样吧(躺平)(请帮我把棺材板钉好谢谢)。
如果有任何问题锅都在我。
————————————————————————
他们遭了贼。
不是海豹妖精,不是兽人,又或者是其他随便哪个精灵或者妖精或者人类。这件事并非发生在他们之中任何一个单独的人身上,而是令人气愤地,降临在了他们所有人的头上:
他们囤积食物的大仓库被窃了。
第一个发现这件事的是弗洛丝缇。狗妖精就像过去的一周里任何一次那样,带着自己消耗不了的熏肉前往大仓库,准备用它们交换一点黑德也能食用的豆子之类的东西时,她灵敏的鼻子在空气中嗅到了不和谐的味道。若说这在开始时还并没有引起她的警惕的话,那么在打开仓库的门框上那一扇摇摇欲坠的门板之后,她所见到的、宛如飓风过境一般的景象使她不得不搁置一切她本来计划要做的事情,转而去将所有她能够找得到的人聚集到仓库前。
只可惜这事情不那么顺利。能够在整个世界都几乎被毁掉的灾难之中生存下来的人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即便依靠狗妖精灵敏的嗅觉,弗洛丝缇能够找得到(而且能够保证在这个过程中不迷路)的人并没有几个,与此同时,在听取了这一情况之后,愿意跟着她一同前来的人则更少。狗妖精的努力并没有很见成效,但至少,海豹妖精是肯看在这段日子里与她一同狩猎并且制作陷阱的份上跟着去看看的。
好在这件事情在演变成幸存者之间的信任危机之前就已经被定了性:弗洛丝缇本人以狗妖精过人的嗅觉作出了“做这件事情的肯定是外来者,我闻到了不属于我们中任何一个人的气味”这样的证言,随后不久,抵达现场的巡林客浪歌也在附近的地面上发现了并不属于他们中任何一人的脚印。
“是狼人。”海豹妖精带着嫌恶的表情说,“肯定是狼人,除了这种该死的东西之外,不会再有其他用两只脚走路的狼了。”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认得出这脚印是来自狼人的,不过他凭一种发自内心的愤怒与灼烧着的痛恨知道,这结果绝不会错,是以他的语气十分笃定。来到仓库前的幸存者们将信将疑地面面相觑,表情各异,不过大都将忧心或者忌惮写在了脸上。
狼人这个令人生厌的物种在灾难之前或许还并不那么常见,稀少的数量所能造成的戕害也非常有限,只能勉强算是一种不成气候的威胁;但是在灾难之星坠地,带来大群的狼人之后,基本上所有幸存下来的人都已经领教过了这种东西的厉害。在世界上的八九成智慧生物都因灾死去,剩下的一两成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时,相比之下基数有所增长的狼人就成了所有幸存者的心头大患。
狼人找到了这里——即便只是有这个可能性,也足够让人心焦了。这一次它们毁坏储藏的物品,下一次它们会毁坏什么呢?没人希望继续深想,更没人希望这件事真的发生。幸存者们在这个坏消息所造成的沉闷气氛中重新清理了一团糟的仓库,结果比他们预想得好些。他们的公共财产蒙受了一定的损失,不过由于所有人在身边都留有能够令自己安然度过这几天的物资,他们还不至于一下子便难以为继。
这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海豹妖精想。去追寻到底是因谁的疏忽而致使这件不幸的事情发生是一种毫无意义且耗费精力的举动,况且他们之中也不存在一个明确的责任人。但这丝毫不妨碍浪歌发誓,如果凶手落到了他的手里,在给它个痛快之前,他至少要联合所有其他人一起上去把那该死的黄毛杂种打出屎来。
另一方面,他也觉得,他不能让这群会直起身子的杂种狗再这么耀武扬威下去——未来镇是他们的地盘(他,勉强再加上一个文丘里吧。是的,他是在自己暗暗地划分地区的所有权),那群只是长得有点像人的蠢货不能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绝不。
他不知道别人是否会想要对可能存在,又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次光顾的狼人做出对策,也不知道其他人会对一种神出鬼没的侵略者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单论海豹妖精自己,他是非常想要弄到一个捕兽夹的,这样下次那些该死一万次的混蛋自以为毫无破绽地潜入时,就会付出至少一条大腿的代价——前景非常诱人,但可惜,浪歌自己也觉得这并不现实。巡林客在过去的一个星期里基本已经探索过这片曾经叫做“未来镇”的废墟中的大部分残破的建筑了,他没找见几个店铺的招牌,废墟当中也并没有任何一堆瓦砾看起来曾经是一座猎人小屋或者冒险装备店铺之类的。或许就像那些更有学问的人推断的那样,这座城镇里原来的住户以农耕为主要经济来源,或许他们有制作捕猎用陷阱的道具,但并不常用,只是被束之高阁,然后在灾难来临的时候,顺理成章地连着保存它们的箱子一起被埋进一堆瓦砾当中。
浪歌也是看上了几座废墟、觉得它们有些亲切的(这一般是指他觉得那下面可能有些好东西),但挖开粗粝的砂石、移走沉重的石板和木材显然不是他这样的一个小身板能够胜任的工作,想来与他有着差不多体型的狗妖精和猫妖精也是同理,即便她们回应了他的求助,对瓦砾堆来讲都会是一样的结果。而他又不能回头去寻求兽人的帮助——文丘里确实足够高大健壮,但贪婪地兽人只会将所有他从废墟中找到的东西据为己有(“我凭本事找到的”),如果让他来“搭一把手”的话,海豹妖精就别想从那片可能有好东西的石堆里得到哪怕一粒有用的沙子。
他思考了半天,最终确认了自己无法可想,并因此泄气地坐在了废墟上,忿忿不平而且气鼓鼓的,就好像此时此刻他求助无门,因此整个世界都亏欠了他一样。本就不擅长、也不喜欢思考的海豹妖精坐在那儿,一边生气,一边思考着他还能凭借现在有限的条件做出什么样的陷阱来。巡林客的知识向他展示了许多种设想,但总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绳子不够长啦,缺少合适的弹簧啦,没有人手去收集合适的木材或者削尖木桩啦等等等等——他根本没办法将那些看起来非常不错、甚至仅次于捕兽夹的设想变成现实:这块贫瘠到几乎什么都没有的废墟正在处处掣肘他。意识到这个事实之后,本来就不算是有个好心情的海豹妖精立刻变得更加暴躁了。
但又能怎么样呢?他没法解决那些问题,生气和暴躁也不能。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巡林客只好在自己计划着制作的陷阱规格上一退再退,因为缺少的材料和环境的限制由杀伤性的陷阱退步到束缚性的,再退步到警示性的——这是底线,说实话,从这往后也根本没有继续让他退步的空间了。海豹妖精最后的挣扎是一个触发式的警报陷阱,并且相当不优雅的,在找到合适的示警用发声器(比如铃铛,铃铛,又或者铃铛)之前,在他无数次不得不退而求其次的计划之中,当陷阱被任何东西碰到而触发时,负责发出警报声的将会是一个从高处落地的木质破水桶——这东西虽然不至于到处都是,但浪歌还是很有把握他能从废墟中找到一个的。
或者什么别的东西。他想。反正只要是个物件,从高处落地就肯定都会出声的。区别只在于动静响不响而已。
不过归根究底,他还是得去翻垃圾。这一项认知令他感觉非常不爽,但事情不是会因为谁不爽了就会自动自发地产生进度的。海豹妖精清楚这一点,是以他虽然满心的不高兴,但还是决定站起身来,开始寻找他所需要的材料。
料峭的春风轻轻拂过,远处响起了点点铃音。
海豹妖精往那个方向猛地转过头去。
微风带来清脆的铃声。
空灵,悠远,仿佛潺潺流水一般的音色回荡在空谷幽林之间。环抱着羊肠小道的不是常见的树丛灌木,而是高耸入云,苍翠欲滴的竹子。与竹子相比,更加罕见的兰草生长在触手可得的路边,尚还羞涩地捧着自己的花苞,而一缕缕幽香已经隐约浮动在空气中了。
海豹妖精用力地眨了眨眼,向着铃声的来向看去。理所当然地,除了倾颓的屋舍与倒塌的断墙之类一如既往的景色之外,他什么也没看见。
幽深竹林中细长小径的景象只出现了一瞬,就好像那不过是他一时间眼花了那样——但那不可能是真的眼花:他要怎样才能从眼前灰败的景色之中看出青翠的颜色呢?
他隐约意识到了,这一闪而逝的景象是他残破过去的零星碎片之一。他敏捷地将那块闪着和煦光芒的残片抓进了手里,但接下来,他又不知道该拿它怎么办了。海豹妖精不惯于思考,不惯于多愁善感,更不惯于用过去曾经见过的一小点零碎的画面作为线索,逼迫自己从空空如也的脑海之中拼凑起过去曾发生过的一段事件来。于是,他所做的只是将那景象重新记到自己空白的大脑里,暂时将它束之高阁:他还有事情要做。
巡林客循着铃音在废墟中穿行,妖精精巧的尺寸和轻盈的体重让这件事情多少更容易一些,但矮小的身高也同时令他在障碍物的遮挡下无法一下子看到很远。他走到距离铃声很近的地方,不知第几次绕过一座瓦砾堆成的小丘,才终于看见了声音的发源处。海豹妖精的面前是一片显然被清理过的空地,进度过半,只是还不彻底。画着刀叉与装满麦酒的橡木杯的招牌安稳地被放置在一边,一半的废墟仍旧是废墟,另一半的废墟则被人力仔细地清理过了:无法使用的石块与瓦砾被堆在一边,可能还有些用处的木材被堆在另一边,不知用途但还相对完好的杂物在干净的空地上排列整齐,同样被妥善安置了的还有尸体——那些在灾难伊始时,便不幸被压在倒塌的建筑之下的可怜人们。
瑞图宁女神轻捷的脚步刚刚莅临这满目疮痍的北地,自东方吹来的风仍带着料峭的寒意。低温令那些尸身不会腐烂,是以空气中暂时还没浮现出什么令人不快的气味,只是人类被重物击破头部碾压致死的样子实在是有碍观瞻,却又着实吸引目光。海豹妖精在好奇心的驱使下瞥了一眼,这一眼就立即令他心生厌恶,并且不在愿意朝那个方向看了。他拧过头去,向着尚未被清理、仍是一片混沌的那一半废墟的顶端——断断续续的铃声真正发源的地方——投去目光:
只在前额处有一绺白色的黑发少年踞在那队杂物的顶部,空茫地望着远方出神,他手中持着一只形状不大规整的铃铛——可能原本是门铃之类的东西——有一搭没一搭地晃着,那铃铛便听话地随着他的动作,有一搭没一搭地叮铃铃地响。
海豹妖精记得这个少年。弗洛丝缇曾经提到过,正在清理原本是酒馆的那座废墟的是两个人类的男性,想必这少年正是其中之一了——另一个白净些的青年人就坐在不远处,也发着呆,什么也没做,也没有向同伴搭话的意图。
平心而论,那少年在外形上便已经很容易引起浪歌的注意了:他额前有着突兀的一簇白发,虹膜是一种容易引发不祥联想的暗红色,仿佛正在凝结的鲜血一般,再加上时不时交替着盘踞在他眉宇间的冷漠与凶悍,这一切归总在一起,使他相当能给人留下负面的印象。浪歌凭自己的第一印象,已经早早地给他打上了一个难以接近的标签。但那又怎么样呢?他对自己说。这少年再怎么难搞,也不会比一个顽固而愚蠢的兽人更加难以应对了。
成功地与一个兽人(大致上)和平共处的经验让海豹妖精怀着满腔的自信向前走去。只不过,当他抵达少年所在的土堆脚下时,才忽地意识到了一个相当致命的问题:
这个少年,叫什么名字来着?
在最初的那一天里,这少年肯定是说过自己的名字的,海豹妖精也肯定是听到过他的名字的,甚至于在这之后的几天里,也还有别人在海豹妖精能够听得到的范围之中呼唤过那个名字的——但是浪歌不记得。
他向少年的同伴,那个曾自称“我没有名字”的青年人投以求助的目光,可惜对方显然只在专心致志地发呆,甚至根本没有注意到正大光明地接近到一个冒险者的警戒范围之内的海豹妖精——这一点,那位同样神游天外的少年人也一样,在场的两个人根本不肯分给他哪怕一丝一毫的注意力。
浪歌苦恼地抱着头思考了一下,即便只是近几天的记忆,到了关键的部分却也蒙上了一层恼人的雾气。他只依稀记得那是个两个音节、短促但拗口的名字,并且坚定地认为就是因为它太过拗口,自己才没有记住。
他隐约感觉,从前的他好像也认得一个有着同样风格的拗口名字的人,到最后,那个名字也同样没有被他刻在自己的记忆里。
是太拗口的名字的错,不是我的问题。海豹妖精这么想。
有了这个想法之后,浪歌再开口的时候就理直气壮得多了:“喂,”他毫无顾忌地顺从自己的第一反应,选择了这个完全谈不上礼貌的字眼作为那少年的代称,“可以把那个铃铛给我吗?”
在他出声说话了之后,呆坐着的两个人才终于发现了几乎已经站在他们脚边的海豹妖精的存在。两双颜色不同,但空茫的神情异常相似的眼睛齐齐向着海豹妖精的方向看过来,又带着相似的疑惑神情转向对方,最后,暗红色那一双眼睛的主人才通过浪歌面对着的方向和那句话中的关键词意识到,这个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的、语气相当没有礼貌的小东西,想要交谈的对象是自己。
“我不叫喂。我有名字的。”少年不再去晃铃铛了,叮铃铃的乐音戛然而止,令他语句中明显不快的感情在一片寂静中更加突出。
海豹妖精点点头,理直气壮的语气仍旧不改,就好像这真的完全是那少年的错一样:“我知道,但我不记得你的名字了。”
这态度显然令那少年更加生气了,他语气之中所蕴含的愤怒更加明显:“那你就‘喂’来‘喂’去的?这是请求别人帮助的态度吗?”
愤怒是会传染的。不幸的是,不论是海豹妖精,还是黑发红颜的少年,显然都是很容易愤怒,且很容易被传染的那一类。
“少废话,到底给不给?”原本便由于遭窃与狼人等等原因接近燃点的浪歌显而易见地暴躁了起来,而回应他的是更加暴躁的少年:
“给你妈给!”
黑发的人类少年在盛怒之中睁圆了双眼,自废墟上站立了起来。他不算高,但与连一米都没有的海豹妖精相比,他站起身的那个动作堪称拔地而起。再加上地势的因素,站在高处的少年完全是俯视着站在低处的浪歌。这个享有极大优势的视角并没能让他的心情好一些,少年仍旧没有更改自己原本的打算:他随意地将手中的铃铛弃置在身旁,然后迈开步子,气势汹汹地向着海豹妖精扑去。
黄铜制的铃铛落在地上,当啷一声响。
微风带来清脆的铃声。
竹林的深处有一座小屋,同样是用竹子搭成的。它同周围的竹林一样苍翠,同周围的竹林一样散发着清香的气味,同周围的竹林一样,在风吹过的时候会发出低沉的飒飒声响。
但与竹林不同的,微风拂过小屋是,还会自屋檐下带起清脆的铃声。
不知是谁对他说,他可以住在那。他可以在那里学着做很多事:学着认字,学着狩猎动物,学着与森林和植物共处,学着做一个巡林客。他觉得这点子当真不坏。
一晃神的时间里,黑发的少年已经欺近了海豹妖精的身前,被劲风裹挟着的拳头自上而下沉重地下落。浪歌愣了一下,紧接着,他做出的闪避动作与其说是他主动的,不如说是下意识的反应。他惶急地移动着自己的重心,让整个身体向着侧面翻倒过去,暂时地降低高度——险之又险,不过他没受伤。人类少年的拳头几乎是擦着他的头发丝掠过去的。
即便是战斗的初学者乃至门外汉都可能会知道,在如此接近的距离之下,体型较大、站得较高的一方显然会占据优势,而海豹妖精两样都不占。他处于劣势的一方,却显然并不打算坐以待毙:他是巡林客,是荒野林木间出色的猎手,他所善于等待机会,在无暇等待时,也不介意自己试着制造一些。
他有些别扭地向着侧面倾倒,而不是更顺势而为的后方,就是为了让自己不至于在劣势的基础上失去更多地利。少年的一拳落空,而下一次的攻击还未到来之时,海豹妖精已经以一种难看的姿势跌在了地上。他没有纠结姿态的好坏,甚至顾不上摔倒在地而产生的疼痛,便已经紧接着缩起身体,将自己团成了一个球——这个动作使他又以毫厘之差,避开了俯下身来、想要抓住他的脚的少年的手掌。
下一个瞬间发生的事情,对人类,或者任何一种身高超过了一米以上的双足行走动物来讲都有些匪夷所思了。将自己团成一团的海豹妖精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成功地在原地滚动了小半圈,在几乎完全没有移动的情况下更改了姿态,让自己的双脚落了地,然后顺理成章地站起了身,在向前冲过了头的少年转回身来,继续向他发起攻击之前,成功地猫着腰向着土堆的高处爬了一小截。
浪歌转回身来,飞快地盘算着自己该怎样向对方发动攻击。现在他们互换了位置,站在较高处的人变成了海豹妖精,可他所能取得的优势仍旧有限——即便站在高处,与人类相比过于矮小的身高使他仍旧只能达到与少年平视的高度。更别提他与身高配套的短手短脚了:双方都赤手空拳的话,少年只需要用一根手指抵住他的额头,就能让他完全碰不到自己了。
有那么一瞬间,海豹妖精想要拔出自己腰间的匕首,但下一个瞬间里,那个少年转回身来,怒气冲冲地寻找着下一个可供进攻的位置时,他便打消了这个想法。少年没有犹豫很长时间,便决定张开双手,左右开弓堵住海豹妖精向两侧躲避的去路,将他直接抓住好好修理一通。这时,站在高处对浪歌而言反而没有任何帮助:这是个与少年的身高正相合的高度,他甚至不需要弯腰,只要向前走一步,就可以将海豹妖精纳入自己的攻击范围。
事实上,少年也的确是这么做的。他上前一步,向左右伸直了手臂,仿佛要给海豹妖精一个大大的拥抱一样——可能他想要做的动作与拥抱也没什么本质性的区别,只是它显然并不代表善意与友好。在少年判断他够得到自己的目标之后,那两只手臂便飞快地向着中央的海豹妖精剪去,铁箍似的意欲将这个气人的小混蛋困在中间。向上爬是个错误的决策,起码不太正确,这让海豹妖精陷入了一个相对危险的境地。只可惜,浪歌也不是只会乖乖站在原地的稻草堆——他是个巡林客,一个足够灵巧的巡林客,他不可能就那么乖乖站着被抓住。
要知道,一个人的劣势绝不是绝对的。海豹妖精的身材决定了浪歌在力量与攻击范围上低人一等,甚至在长途奔袭的速度与耐力上也不占优势;但另一方面,短小的体型令他有着轻盈的体重和在狭小空间里灵敏活动的自由:他在那双手臂迫近时出人意料地向上跳了起来,面对的方向甚至就是想要将他按住狠狠揍一顿的少年。他避过了那双将要擒拿他的手掌,在手臂与手臂之间的缝隙间闪转腾挪,又接着低下头去,在向前迈步的少年双腿间的缝隙之间穿过,一溜烟地跑下了废墟的土坡,在空地上站定,转回身去,又觉得气不过,还向着少年做了个鬼脸。
这一下可算是彻底点燃了战争的狼烟。本就生气的少年被海豹妖精的一个鬼脸气得一佛出窍二佛升天,立刻放弃了原本的地形优势,也下到平地上来,一边骂一边追着海豹妖精四处乱跑,而后者则从地上捡起各种各样的杂物,向着自己的追击者不断投掷。一时间,本来被理得整整齐齐的空地上变得鸡飞狗跳,在场的最后一个人有些茫然地看着这一切,有些理不清为什么几句话的功夫,整件事情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但这样是不对的。青年人想。首先,这无用地耗费了本该用于劳作的珍贵体力,还可能令人受伤,对效率造成影响;其次,这片空地上的东西都是他们好不容易才从废墟之中整理出来——他们不应该就这样平白地破坏这份劳动成果,即便堆在地上的那堆破烂里没什么有用的东西。
在场唯一一个没有被愤怒控制的人尝试用语言劝解产生争端的二人,但那两个人兴之所至,完全没有听得进别人的话的意思。迫不得已,他能使用的方法也只有试着以武力介入这场武力争端了。青年人注视着几乎一刻不停地运动着的两人,思忖着合适的时机来插入这场丝毫谈不上文明的交流。起初,他还有些犹豫,但当他下定决心时,这件事就变得分外简单:产生争端的两个人似乎都没有将他视作一个障碍,他站在那,就仿佛是一个死物,完全不会引起少年或者海豹妖精的警惕——他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不过这帮了他大忙。
青年人同样下到空地上去,在原地站了一会儿,四处乱跑的海豹妖精就在偶然间凑了过来,并且试图把他当做一块石头或者其他什么东西,用作对抗少年的掩体。只可惜浪歌没问过掩体的意见,在他试图转到青年身后时,视角却不受控制地陡然提升了起来。
海豹妖精毫无防备地被青年人从地上一把抄了起来,然后单手夹在了手臂和身体之间。
“停下吧,别打了。”浪歌听见青年人这么说,然后在下一秒,他确信少年根本连一个字都没听进去。
浪歌被青年人用一只手夹在怀里,全身都被牢牢钳住,完全动不了。他看着那人的另一只手挡在自己身前,巡林客和少年人之间的那一小段空白里。那位一直在追着他打的好对手却对这一切视而不见,只是一个劲儿地要追着那个毫不懂得尊重的小混蛋揍——青年人的手臂挡在他们中间,可少年人的拳头浑不在意地直落在自己同伴的肢体之上,皮肉相击的沉闷响声和自青年人身上传递而来的不自然的抖动令什么都没感觉到的浪歌也不禁牙酸。
得了吧。海豹妖精想。这家伙生气起来竟还六亲不认的,看来他的同伴也没法阻止他。毫无愧疚的浪歌丝毫没有这一切的起因完全是他自己的自觉,径自开始考虑脱身的方法:首先,得叫这个本不该掺合进这一场混乱,却还是伸手将他抓住了的人松手——
这很简单。他的手脚没法乱动,可他还有牙齿。
从做出这个决定,到脱离青年人的钳制只花掉了海豹妖精几秒钟的时间。他是有点愧疚的,因为那青年人至少在行动上是想帮助他的,却被他在手臂上深深地刻了一个牙印。他咂了咂嘴,口中没有血腥味,便觉得事情还没有坏到头,算是有寰转的余地。他可以过后用点什么补偿那个没名字的青年人,但现在嘛……
海豹妖精几乎是贴着地皮从青年人的身边滑开去的。少年人没有继续跟来,反而跟试图阻止他的青年扭打在了一起。浪歌保持在一个足够谨慎的距离上观察了一会儿,发现这两个人竟然势均力敌。这个发现令他又有些不太开心。浪歌忿忿不平地从地上捡了点小石块之类的杂物,假装自己有个弹弓,向着那个想要打他的少年砸过去,砸中了几颗之后,才觉得多少消了气。
然后,他终于想起了自己本来的目的。
海豹妖精转过头去看废墟的顶上,黄铜制的铃铛在阳光下泛着灿灿金光。
这是个拿走它的好机会,而善于抓住机会的巡林客不应该错过它。浪歌这么想。
铃铛来得不怎么光彩,但海豹妖精不是很在意这一点。他终于又是以一种愉快的心情在整理绳子、捡来的木片,临时削出的木桩之类用于制作陷阱的道具了,鼻腔里还哼着不成调的歌谣,就连文丘里嫌他吵,咆哮着威胁他要把他囫囵个儿吞下去,也没能破坏他的好心情。
他只要一摇,铃铛就叮铃铃地响。他喜欢这个声音。他意识到,这声音能令他想起一些过去的事情,而在维持生命的需求不那么急迫的时候,他也是很乐意做一些这方面的追索的。
浪歌到底还是没有忘记自己本来要做的事情。他整理好所有的工具与材料之后,便仓鼠搬家一样,一趟一趟地将他们搬运到大仓库的门前,分批分次地埋下机括,绑好引线,开合着因为地动山摇的灾害而有些变形,也因此不太灵光的门板,不断地测试着放置触发点的合适距离。
整个陷阱的布设耗费掉了他整整一个下午的时间,到暮色四合的时候,他终于认为一切都完美地达到了他的标准,于是便庄重地从海豹皮的包袱里拿出了铃铛,小心地将那个金属的物件捧在手里,在一种肃穆庄严得没必要的气氛下,几乎是仪式性地屏着气,将它加入了整个系统之中。
以现有的条件来讲,一切都是非常完美的。海豹妖精满足地端详了一会儿他的杰作,又让自己的视线重点照顾了一下那颗黄澄澄的铃铛。它显然是被压扁过,埋在了土里,上面还有些泥土的污渍,还有被石块敲击、粗糙地休整过的痕迹。但它在海豹妖精的眼里,又显得那样的可爱——就连刚出生的小兔子都没有这么可爱了。
浪歌转过身去,假装自己并没有很在意那个铃铛。他又仔仔细细地将所有暴露在外的线头遮掩好,确定自己已经完成了所有的工作之后,才又回过头来,凑到陷阱的最终端边上,蹲踞在铃铛的旁边。
他小心翼翼地伸出手,碰了碰那颗饱受疮痍的黄铜制品。
叮铃铃——
微风带来清脆的铃声。
山茶开至荼蘼的季节里,有淙淙的山泉灵巧地自竹林间蜿蜒而过,细长的竹叶悬在清澈的流水之上,随着微风袅袅婷婷地摇摆。曾有不知是谁说过这景象是美的、自然的,清新而富有生机的——或许如此吧。他无可无不可地想。这画面出现在他的脑中,他想起不知是谁对他说过的那些话,但要问他自己有什么想法,他只觉得那条山溪的水冷得刺骨,但里面生着的小鱼烤起来很好吃。
他过去一定是在那里生活过。浪歌已经能据此笃定这一点了。但这仍旧不够,仍旧不能回答他所想要知道的、有关自己的一切问题。于是,他再次伸出手——
叮铃铃——
微风带来清脆的铃声。
不知是哪年的那一年,竹林开花了。
那不是个很好的景象,也不像是个很好的预兆。
海豹妖精有些忐忑,但仍再一次地伸出了手。
叮铃铃——
微风带来清脆的铃声。
枯黄的竹枝上悬挂着垂头丧气的细小白花,空气干而冷,地面上却结了一层白霜。白霜之下,是被猛兽巨大的利爪翻出沟壑的殷红土地,大片的鲜血倾泻在本应干硬的地面上,让它变得柔软,从而留下了足迹。凋落的竹花被碾进带血的泥土之中,沾上深沉丑陋的颜色,风中浮动着的血腥气浓重得仿佛能化成红雾,沾了血的竹枝凌乱地东倒西歪着萎顿于地。一切都肇事者这里肯定发生过什么,但不论是什么,流了这么多血的东西都已经不在了。
叮铃铃——
微风带来清脆的铃声。
不知是谁对他说,他该向善,因为妖精总是向善的。瑞图宁女神在创造他们时,就已经将善良的立场写进了他们的骨血与灵魂。何况,向善总是好的,能为自己挣得福报,也能帮助身处困境的人:要是说话的那人不是向善的,那么海豹妖精就不会有机会……不会有机会怎么样?
叮铃铃——
微风带来清脆的铃声。
他从沉积在地面上的雪白竹花之中,殓起几块被嚼碎的骨头。
向善不是好的。他在竹花的大雪中得出结论。向善不会让他有得吃喝,不会令他感觉愉快,也不会有福报。
就像神祗从不注目于这个没有法术的世界。
叮铃铃——
烈风之中,铃声戛然而止。
他将小屋埋葬在烈火之中,整片正在枯萎的竹林则是殉葬者。它们还没有来得及结出种子,来年这片土地上将不再有竹笋重新生发。这是不合巡林客的规矩的,但他不在乎。
他将他的铃声埋葬在竹子的灰烬之中。
然后,他发誓自己绝不应该忘记:竹林的那一篇血迹中被留下的足迹,是狼人的脚印。
海豹妖精收回手,抱着膝盖在原地坐了一会儿,有些颓丧。
他早该想到,过去的记忆不可能全是些美好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