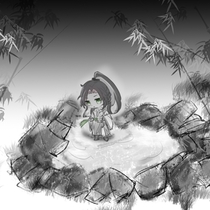※可能有令人不适的描写
没想到吧小杜是这种混沌角色,大奸臣你崛起吧!
中之人其实不会写文但是我画不完了(就这样土下座)
————————————————————————
京城已进入了夏日。略显燥热的风轻轻刮过官署前的地砖,带来一点汗水混合着青草的味道。奔跑的声音由远及近而来,杜玦心中一跳,手里拨弄得噼啪作响的算筹便飞出去一根,正巧打在急匆匆入内的主簿身上。因着被这"暗器”吓了一大跳的缘故,主簿一时忘记捏紧手中的诏令,那卷纸在地上打了两个轻巧的滚,撞在杜玦的脚边停下了。
"简而言之,限司天台两月内呈上驯服长春使者的法子?”杜玦翻了翻诏令,挑眉看向汗如雨下的主簿,"若是陛下没有其他特别交待,你就回去工作吧。这件事我自会处理。”近来桃树伤人尸体凭空消失之事传得沸沸扬扬,杜玦早已猜到陛下肯定又会给自己出一些难题,只是未曾想到难题根本不是司天台职责所在。
要研究尸体倒是找刑部去,星象难道会告诉我人死了为什么没有尸体吗?她暗自腹诽道。推算思路被打断,杜玦干脆将星图与算筹通通一推,趴在了案上。许是这么一趴让气血重新供回脑袋的缘故,杜玦突然有了一个绝妙的主意。若是成功,不仅可以完成陛下的差事,说不定也可以借此折断那张玄铭灵牌。
天下万事万物皆能与天象相对,倘若异变也能找到规律呢……?
杜玦直起身,指尖无意识地敲击着案几。窗外的蝉鸣一阵响过一阵,细碎的阳光顺着半敞的窗户打在窗边地上,衬得屋内这昏暗的一方天地更是死一般的寂静。
太妙了,就这么办吧。
“悄悄放出消息,就说夜间活人浊气减弱,不与桃树仙气相冲,此时移植便不会发生异变。”目送着亲信带着吩咐走远,杜玦脸上的笑意复又逐渐漾开,连带着中断的推算也重新连上了思路。正巧那妖道正蛊惑陛下进行人牲献祭,虽不知祂是如何欺瞒世人的,但京城的达官贵人都跃跃欲试,正是需要移栽桃树的时候。她一边拨弄着那把算筹,一边用毛笔在星图上勾勾画画,连袖子落在了砚台里也不知道,墨汁顺着丝线的经纬蜿蜒而上,静静染黑了衣服上绣得栩栩如生的蝴蝶。
几日后。
今日是杜玦的休沐日。按照她的作息,一睁开眼必定已是酉时一刻。太阳有些西斜,暮色伴着隐隐传来的市井喧嚣声渐渐笼上来,衬得室内一片寂静。杜玦批衣从床上坐起,在一阵令人不快的心慌中一只温热的手摸了上来:"大人,打听到有几户富商雇了人今晚结伴去移栽桃树,是否要跟上去看看?”她在渐浓的黑暗里静坐了片刻,感受到心脏随着夜色的降临逐渐趋于平静,随即在脑中复盘了一遍整个计划。时机正好。"备车吧,我亲自去。记得带上我的星图。"
下床,更衣。
杜玦的计划中并不包含与异化了的人交手这一可能,为了尽量不引起注意,她今天在衣服外面罩了一身利于夜间行动的深色便服。沾了墨迹的衣服她一向懒得管,正巧今天可能要在地上滚来滚去,干脆便穿在里面,还可以省下再买新衣服的时间。袖口那墨迹染了的蝴蝶被隐在外袍下面,仿佛也蛰伏了起来。
打点妥当,正巧杜玦需要的典籍也被从司天台取回来。她握紧了手中的星图,稳稳登上了去往桃源的马车。天边蒙着一圈白茫茫的晕影,星星已经开始挂上穹顶了。马车绕路到了离桃源尚有一段距离的一处矮山背坡。此地视野极佳,且极为隐蔽,能俯瞰大半桃林,却又远离大道,不易被察觉。
坡上一树下早已备好了简易的案几,摊开的星图与观测记录。杜玦坐下,望向不远处在夜色中显得更加幽深的桃林。不知为何,当她注视着那棵仙树时,总有一种自己也被仙树注视着的感觉,那种无处不在的目光一样的感觉紧紧笼罩着她。堪堪将视线移开,林间已有星星点点的光亮在移动,晃动间仿佛鬼火,是那些仆役开始行动了。
"记住,一但看到异象,一人记时,一人立刻记录天象。"杜玦吩咐道,她紧握着一只蘸了朱砂的笔,声音冷静到有些无情。夜色彻底笼罩下来,星星渐次浮现。山风带来山下隐约的挖土声,以及偶尔压抑的惊呼。那惊呼也许代表着一条人命的消失,也许更预示了这十几条人命的消失。但是这都与她无关。
她没兴趣也没义务阻止悲剧,只要能够得到她需要的东西,能够证明她一直以来相信的天地真的客观正确,即使牺牲的是她自己的命也没关系。
本来也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戌时三刻,东南位,火把熄灭后有一声短促惨叫。”亲信短促惊叫了一声,"那人似乎半个身子都变成桃树了。惨叫大约是他同伴砍去了他半个脑袋。"
杜玦立刻抬头望向对应星域,边说边手中不停圈画星图对应区域:“奎木狼值守,地气涌升……”
过了一个时辰,期间又有两人异化,被赶来的富商家丁悉数斩杀,也是一样的半身木化。剩下的仆役哆嗦着几欲逃跑,被家丁的刀横在脖子上逼迫,不得已继续挖树。“亥时二刻,偏北位,异变似有延迟……啊,变了!这次桃树枝条从腹部刺出,竟是开出了几朵桃花!”另一名亲信禀报。杜玦眼中闪过一丝喜悦:“延迟?此刻是……井木犴偏斜,阴气正盛。尸解过程因星位偏移而产生了变化?好好好!记下,此变体或可用于验证‘神不灭’之速!”
杜玦越写越兴奋,她完全沉浸其中,好像林中发生的不是血腥的变异与死亡,而是一场盛大而残酷的星象与人体奥秘的演示。星象为线,提着林里的每个人献上独属于杜玦的木偶戏。也许此举足以让她被那些自诩正义的假正经抨击为邪魔外道,麻木不仁,但是如果没有这些牺牲,只迷信那妖道的仙术只会让死的人更多不是吗?至少每一次惨叫,都为杜玦提供着一个宝贵的数据点;至少每一次尸解消散,都让她对那规律的理解更深一分。墨迹与朱砂在星图上交织蔓延,如同一张正在缓缓织就的掌控生死的罗网。
直到子时过半,仅剩的两个仆役说什么也不肯继续挖了。其中一个吓破了胆一头撞在桃树上死了,桃树经由人血灌溉幽幽发出了红光,缓缓开出了几朵桃花。见此情状,家丁们面面相觑,犹豫了一会儿还是拖着剩下的那人回去复命。林中重归寂静,只有明亮的月光透过树枝照在地上,跟着沙沙吹过的夜风轻轻摇晃。
杜玦放下笔,轻轻叹了一口气,嘴角是压不住的微笑。案面上摆满了布满标记的星图与厚厚的一摞记录,比她预想中的成果还要多得多。"走吧,可能再观测两三次,我就足以总结出详细的尸解成仙之法了。"
杜玦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桃瓣被风一吹,打着卷落在地上。桃源干干净净的,除了挖出的坑洞以外,那些死去的人没在桃源留下任何痕迹,在杜玦的心里也一样。夜风顺着马车开着的窗户灌进去,吹得她的袖子呼呼作响,那只染墨的蝴蝶被清亮的月光照着,仿佛下一刻就要振翅飞入这月色中去。
此后月余,杜玦又如此进行了数次“观测”。消息在坊间流转,总有人被“夜间移树无恙”的谎言引诱,或派人前去或被人派着前去,成为杜玦验证理论的祭品。司天台的观测册越来越厚,星图上的标记也愈发繁复精准。
不观测的日子里,杜玦废寝忘食,日夜推演。官署的烛火常亮至天明,算筹噼啪声与纸张翻动声经常响上一天。尽管面容憔悴,她的眼睛仍然是亮的。那里面的光一天比一天灼热,仿佛要将自己烧起来一般。
终于,在两月期限将至的一个清晨,杜玦合上了最后一卷记录。她面前摊着一份奏疏,其上以工整小楷写着:以长春使者尸解成仙之法。
翌日,宣政殿。
皇帝看着杜玦呈上的奏疏,初时尽是惊讶之色,越看却越是热切惊喜。“杜爱卿此言……当真?”皇帝的声音带着兴奋和一丝狂喜,“真能利用仙树助人尸解成仙?”
“回陛下,千真万确。”杜玦垂首禀报,语气平稳笃定,“臣观测良久,发现其与天象星宿对应极其严密。凡被桃木所伤而躯体消散者,并非死亡,乃是经历木解之过程,蜕去凡胎,神登仙籍。所谓长春使者,实乃接引之仙使。”
她顿了顿,继续道:“然尸解过程凶险,凡俗之人易生惊惧,故显异象,酿成骚动。欲驯服之,非是以力相抗,而是需顺应其规律。臣已推演出安全引动及平息桃木仙气之法,可令其不再无故伤人。同时……”杜玦微微抬眼:“若能依臣所奏之星宿时辰、地脉方位,辅以特定仪式,或可……主动求得这木解仙缘,虽肉身解化,然元神不灭,可登临仙道。”
殿内一片寂静。朝臣们面面相觑,尸解成仙之说自古有之,但多被视为虚无缥缈的传说,如今却被杜玦以如此确凿的星象规律和观测证据呈于御前。
皇帝的目光扫过那些详细的星图和玄奥的仪式步骤,沉吟良久。这结论匪夷所思,却又似乎无懈可击,更暗合了历代帝王追求长生的隐秘渴望。若真能掌控这成仙之门……“爱卿果然不负朕望。”皇帝最终缓缓开口,语气中带着难以掩饰的探究与一丝热切,“此法……朕需细细参详。若果真有效,爱卿乃国之栋梁,功莫大焉。”
“臣不敢。”杜玦恭敬行礼,随着咔咔两声脆响,怀中的青铜征服卡已应声而断。趁着低头,杜玦暗自翻了好几个白眼,她就知道,皇帝已然心动。对长生仙道的追求,足以让这位君王忽略掉推导过程中那些微不足道的代价。
退出了宣政殿,杜玦迎着宫门外略显刺眼的阳光,微微眯起了眼。陛下的差事完成了,玄铭灵牌也已经折断。两件麻烦事一起解决了,这让杜玦久违地有了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过些日子便是八月十五,今年让她们包些蛋黄馅的月饼吧。
蝉鸣仍是一阵接着一阵,一只蝴蝶飞过来,正巧落在发呆的杜玦的袖子上。她抬手一送,那只黑黄色的蝴蝶便振翅飞向远方。身后,一阵风带着落叶,稳稳地停在砖石上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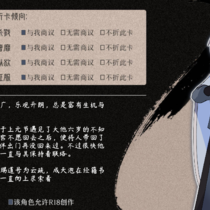



周拂桢牵着马,一步一步地走在长安的街道上。
今日早些时候,自己进了驿站,借连总戎的信件要了间下房——这几个月来朝廷不知出了何种事故,官员或升或贬,在外的进京,在京的出外,这一番热闹下来,倒使得驿站自开国来未曾这般爆满过。驿站非是一间高楼,而是数个连在一起的街区,凭着入住者的官位大小以白墙画出大大小小近百个院子来。在院落深处是上房,周拂桢未曾见过——以他的身份地位,莫说住进去,就是看一眼也是万万不可的。他只知道有几处连廊通往那一些个僻静的院落,内处大得好似一处府邸,莫说书房餐厅,甚至有一整个置有假山流水的院落,供那些出行时前方举着“肃静”、“回避”,后方举着万民伞的大官们休憩会客。至于下房,不过是一些只够放得下一两张床的狭窄小屋,开窗便对着喧闹的大街,说个梦话都能被街上买汤饼的人接上话。
周拂桢将那头完璧归赵的劣马交予小厮手里,几番叮嘱这马近来奔波了千里路,须得多喂些豆饼,养一养这劣马的身子,也不知那小厮听进去了没有。想来是没有的。周拂桢饮了一口驿站台上买的酒,又险些吐了出来。为了这许多客人,连酒里掺水都不算了——已经是往水里掺酒了!他悻悻地饮着淡酒,心想明日得出门打听一下连总戎的住处。自己前去霜原出使前,对方正忙着升官的事宜,自己一去月余,想来已是披了新的官身,也不再住这一处挤人的驿站了。
想到自己投靠的连大人已升了官,连仍是白身一个的周拂桢也不由得扬眉吐气起来。想来自己这一步棋走得极妙,有一处投靠总比朝中无人要好,如今只要自己肯豁出命来,总能换上一两个官做的。想到这里,周拂桢又忍不住啜饮这马尿似的淡酒,果然又差点没把酒吐出来。明日——他想着,若是自己这位新投靠的上司看得中自己,恐怕明日上午便会派亲兵或伴当前来寻自己。不过自己毕竟还是新人,按朝野的规矩——得自己先去寻人拜访,才能显得自己对上峰的尊重与挂念。不若今日便放出消息,称自己在寻人如何?这下倒是将尊重做了个十成十,谅再挑剔的腐儒也挑不出自己礼仪上出了什么错。
于是周拂桢当下便将手中那碗越喝越想吐的淡酒搁在桌上,向着刚与什么人攀谈完的小厮走去。“劳驾!”周拂桢打着招呼,“烦请您一件事……”
“客官,可有甚事使唤小的?”小厮将巾子往肩膀上一甩,对着周拂桢拱了拱手。
“请您打听个人。”
“嗯。”小厮站定了,努了努嘴,周拂桢当下把准备好的铜钱递上。小厮掂了掂,见着上边阳刻的“天顺”二字被磨得锃光瓦亮,心下知道是分量十足的旧钱而不是成色更差的承和通宝——先帝时铸的铜钱用料扎实,铜锡有九一之数,而新皇所铸承和通宝成分不到八二,所以这新钱反而远不如旧钱来得紧俏了。小厮乐开了花,对着周拂桢点头哈腰:“您请问,您请问……”
“你可曾听闻连子仪——连总戎的事?”
“可是近日里高升那位?”
“正是,正是。”
“先生来得不巧,那位大人升官后便不在这里住了。”小厮憨厚一笑,擦了擦铜钱,将其塞进了腰带里。
“大人搬出去后,可有说去了哪里?”周拂桢连忙将手伸进袖中再掏几枚铜板出来,可这时又有人大声扯着自己名字呼喊起来:
“周拂桢——可有人见着周拂桢?我家大人请。可有人见着——”
周拂桢连忙迎了上去。身后的小厮见自己拿不着第二份铜钱,立刻拉下脸来,啐了一口,悻悻离去。喊叫那人身着号坎,未着甲,想来是哪位大人派来亲兵前来。周拂桢心下一动,难道是连大人听闻自己回了长安,立刻派了亲兵前来?——但自己不过一位刚刚投靠的小小幕僚,哪使得动一位兵部尚书以这样的礼节相待呢?
“是周先生?”那亲兵似乎认得自己,顿时眼睛一亮:“真是周先生,您从霜原回来了!”
“可是连大人在寻我?”自己并不识得多少士兵——这么说来,这来找自己的必然是连衡派来的亲兵。周拂桢心中一暖,自己可算是跟对了人!常人对远行回来的幕僚,隔上一两天再寻人也算是姿态好的,若是一些无甚功绩的小幕僚,晾上个三四天也是常有的事。至于归来的当日便派人来寻?那便是一个十足十的招揽姿态,怎不叫人感动万分呢?
“是,是。连大人说您这次霜原之乱解得好,特地唤我来请您回去接风洗尘……”
“某奔波多日,实在不好见人!”周拂桢毕竟是个儒生,礼数这一点自然是不会缺:既然对方以礼待自己,那么自己也得以同样重的礼回敬对方。“还请稍待,我沐浴更衣完便一同前去。”
于是一番沐浴更衣,换上了新衣服的周拂桢便牵着马随着亲兵一同走在了路上。——那驿站果然没喂豆饼!周拂桢恨恨地想着。那马发着脾气打着响鼻,但好在还听周拂桢的使唤,踏着蹄子跟了上来。
“先生怎不骑马?”
“唉!某不善骑,之前路途颠簸,倒使我双腿疼痛不已……”
“先生若不能骑,小的去寻一辆轿子便是……”
“不可,不可!”周拂桢连忙拦下那亲兵:“岂能以人为畜?”
这话是先帝未曾继位时所说。大烨向来是骑马人多。马车——有,只是达官贵人可乘。至于轿子,自先帝那一句话起,便无人敢乘了。只是先帝的话在本朝不甚好用,于是禁令松弛,坐轿子的人也渐渐多了起来。然而周拂桢心下已定,自己在连衡面前当做个无可指摘的儒生,岂能有这样的道德瑕疵呢?只能挪着磨破了皮的双腿,与亲兵慢慢走去。
一面聊着出使时的趣闻,一面便走近了新的连府——却未曾想,连衡竟从府中迎了上来。
这使得周拂桢大惊失色,饶是以他科场蹉跎近十年的经历,也终是惊得手足无措——哪里有主君亲自迎接的道理呢?自己有何长材足以被这位长官这样看重迎接么?周拂桢几乎感动得落下泪来。然而连衡不仅迎了上来,还伸出手来,亲切地握住了周拂桢的手:“军师,可算回来了!”
“是,是——托大人的福……”周拂桢一时间手足无措起来,只一味握着伸来的那双手不知如何是好。
“军师千里跋涉,可辛苦了您哪。”
“所幸不负使命。”周拂桢感动地一笑。
连衡也不放手,只空出一手虚扶着周拂桢的肩背,将他往这府中带。“军师这一行,闹出来的动静可不小。一月前宣威渡便传来消息,称有成建制的霜原士卒前来买盐,这一下,霜原怕是再难起兵了。这还多亏军师巧舌如簧,策反了那些士卒啊!”
听着这夸赞,周拂桢不由得觉得一股暖意从丹田升至四肢百骸。自己有多少年没有听到这样的夸赞了?科场十年蹉跎,尝尽了人间冷暖,本以为自己便一直这样沉浮着了,谁知自己真有奉命奔波、归来后受高官重视的一日?“这说得哪里话。”他诚恳回话,“也要多亏主公赏识,不然某之计策也无有得见天日的时候啊。”
“军师这是见外了。当今堂上,敢提一个好计策的人已是少之又少,更何况是军师这样敢于单骑赴会的勇士呢?”
连衡领着周拂桢从堂上入得门后,在连廊中拐了七八个弯,终于领到一处画舫上。大烨的官员任免后,往往住进被分配好的房子。现如今,连衡官至兵部尚书,朝廷自然是拣选了兵部的一处空闲院落分配给他。这处院落原来属于前任兵部尚书,姓张,名唤二字宣和,向来有美髯之称号。周拂桢只听闻此人自先帝时便声名鹊起,由于对西域诸国颇为强硬,被派去了哪处都护府坐镇前线。连衡却摇一摇头,原来张尚书是先帝提拔不假,然自诩军功,不与今上倚靠的那些官员亲近,此次被派去西域坐镇,原来是明褒时贬,将其踢出了政治中心。
“子成,你将来既为我做事,还需得多多了解朝堂消息才行。”连衡亲昵地唤着周拂桢的字,领他往画舫上的一处桌椅坐下。桌上早已布了酒菜,虽不过六七盘菜食,那些个大宴会上常有、做得精细漂亮却不可吃的看果一概没有,只一桌家常宴饮的水准,但这也对周拂桢十分受用。席间没有下人小厮,于是周拂桢亲自取了酒壶,先为连衡斟了一杯酒,再为自己也倒了一杯。从两人的座位处向画舫外看,便是假山流水、花团锦簇,从假山园林特意留下的缺口,甚至能远眺长安南的一处佛塔,真是借的好一处景!想来那位远赴西域的前任兵部尚书张大人也是醉心园林之人,不知在这一处小宅花了多少心血,只是一纸令下便让张尚书与自己精心侍弄十余年的花园相隔万里,怎不教人叹息呢?
“在下洗耳恭听。”周拂桢举起酒杯,先敬了连衡一杯酒,接着一饮而尽,将杯底微微外翻,示意自己已饮下一杯。黄酒已然温过,口感醇厚,回味尚佳,这与不久以前在驿站饮的那杯掺了水的酒比实在是甘霖!连衡微微一笑,想是认可了周拂桢饮酒时的豪爽。“军师喝的好酒!军中正需要如军师这般能饮的壮士——将士们驻在边关,没有几分豪气那可不行。”
这话颇为受用,周拂桢更是诚惶诚恐。两人又饮了一杯,拣起菜吃了起来。
“军师,你这次可帮了我大忙。”几口酒菜下肚,连衡果然又故事重提,“像你这般有大才之人,怎得就这样埋没于市井中呢?”
听得这话,周拂桢的眼中显出一丝阴霾。却不说话,又斟了一杯酒,自顾自地饮了下去。连衡见得此事,心下了然,这是戳到了这位军师的伤心之处,只待这一杯酒喝完,便听到周拂桢开口:“想来是我的命不好……”
“怎得这样说呢?”连衡显露出一副大惊的神色来,“子成你有这般才学,哪怕换个进士来也是理所应当的……”
“进士、进士,进得甚事!”周拂桢将手中的酒杯重重地往台上一撂,“若放在十年前,某说什么也得豁出来考个功名再说。‘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谁人最初不是这样想的呢?可是那进士!呵呵……”
眼看周拂桢心底里的怨气被激了出来,连衡微微一笑,伸手夺下周拂桢手中的酒壶,亲自为他斟起酒来。周拂桢连声道着“不敢、不敢”,饮着这一杯连衡倒来的酒。
“我如今也是明白了。科举,说甚么拣选人才?我看不过是挑些家世好的人来。那些个琼林赴宴之人,可真有寒门出的子弟么?……只是世家连着世家,若没点关系,也是没法在朝堂上立足的。”
“唉!军师看得准啊。”
“这朝堂上盘根错节,又怎会看得起我这般寒门呢?就说我头一次科举吧……”周拂桢拣了几筷子菜送入嘴里,絮絮叨叨地说着自己记忆犹新的科举过往:“……我写‘百山分作关外关’,只是那‘关’字犯了主考的徐大人家老祖母的讳。——谁人能避得到这样的讳呢?便是因着‘关’字未有缺画被黜落了。后来才听闻,当年的状元,他二姨舅外甥妻子的三侄子是主考官徐大人七叔父家老幺的学生,想来也就是攀着这样的关系考上的吧……”
“又过了两年,进士再开,这次我可打听了主考官全家老小的名讳,确定了诗中撞不上任何人的名字,可未曾想过,韵书竟在当年换了一版!我写的诗文中,又刚好用错了一个韵脚。这般又被黜落一次……”
看着周拂桢摇头叹气,连衡忍不住伸手抚上他的肩膀:“军师竟过得这样辛苦……”
“自此,我便知晓了,若在朝上与几位公卿扯不上关系,在科举一道可是万般进不成的。——便是如主公这般慧眼识珠之人,在堂上怕也是万分不自由的。”
连衡心中一动。自己靠着军功常年在外,倒是少有维护京城里的关系,若是除去了几位在京任职的同年,怕是想送礼也无处可送。正遇上自己得幸升官,正是须大肆用人之际,可这军师是怎样看出来的呢?
“那还用说,因为主公您是清官哪。这朝堂上,清官又怎能做得成事呢?怕是只有与那些世家老财同流合污的虫豸才能入得了他们的法眼。可与这群虫豸在一起,怎能治得了大烨呢?”周拂桢愤愤地饮下一杯酒,与连衡倾诉着。
“唉!”连衡听了这话,摇了摇头,顿时把这些年来当官收的什么三节两敬、夏冰冬炭抛之脑后:“人人常道当官是天底下第一的好事,却不知道这份差事也不是那么好相与的。”
周拂桢恭敬地拱了拱手,作出一副洗耳恭听的模样来。连衡也不接着说,只自顾自地拣了几口菜吃,复又端着酒壶给二人的酒杯满上,这才缓缓开口:“我与军师相逢已有数月,军师也见识了不少我军中事务。可有何看法?”
周拂桢沉吟片刻,抬头迎上了连衡的视线:“主公所言之文书我具已看过。想来总结不过三字:繁、细、难!”
连衡微微抬手,示意军师继续说下去。“大人驻扎灵州,行伍配置、钱粮周转,皆需递交文书。如此以来,文书经手之人众多,上溯兵部、下至伍长,人员繁多,耳目混杂,众人意见不一,而文书须得协调众人意愿,此为‘繁’。”
“至于地方事务,行军非是将军队放出自待驻扎,原是砍柴、分粮、就食、就寝,皆有命令,为主官者,向下分配任务不可笼统,此为‘细’。”
“至于军令落实,此番种种,皆是‘难’!”说到这里,周拂桢忍不住也叹息起来:“主公所给文书上,甚至有逾期三月未曾运到的钱粮,又说换人传令,与之接洽,竟是花费许久才筹到了那几十石米粮……”
连衡点了点头:“军师看来已是颇有几分远见了。”
“一点拙见而已,不敢当,不敢当。”
“这军中事务这样困难,若是军师畏惧,与我说了便是。”
周拂桢定了一定,瞬间便从连衡的语气中读出了一个意思:连大人想要将文书工作交予自己!自古军中文书,向来是交给主君最信任的部下,如今自己也有这一殊荣了么?一阵狂喜席卷而来,周拂桢恭敬一揖:“必不负所托!”
二人一番言语下来,兴许是将文书这一重要工作交托给了幕僚,两人暗暗认下了这嫡系的地位,连席间的气氛都轻快不少。又一番宴饮,连衡向周拂桢举杯:“军师以白身行事可是多有不便?”
周拂桢心下一凛,知道这场家宴的戏肉来了:“为大人做事,哪怕赴汤蹈火我也在所不辞,岂能因白身便有畏惧呢?”
“哎!军师助我许多,不给回报,岂非明主?子成,你莫要推辞……”
“幸得大人提拔,某感激涕零,铭感五内……”
连衡微微一笑,“子成,你回答我。”见周拂桢微微抬头,认真倾听的模样,于是缓缓开口:“我知军师是想有一番大作为的。我已写好向朝堂上奏的文书,为你请一个官来,只是却还有一个空未能填上。——子成,你是要留在这长安做事呢,还是与我回灵州,在我身边做事?”
做官当然是要做京官,这是连周拂桢都知道的道理。大烨立国多少年,世家与官员便在这京城盘根错枝了多少年。论起消息灵通、资源便捷,世上无处可出长安其右——甚至于京城买饼子的小贩都比其他地方的口才好些。若是当官,京官一年的升迁速度可比得上出外官员的三年,若是有京官而不做,那实在是对想做官者的不敬。
然而这话实在不能在恩主面前说出口。自己花费众多力气,不就是为了博一个升官的可能么?若是为了做京官恶了恩主,岂不显得自己是一个眼里只有官身地位不知感恩的恶人么!再说,主公本就年轻有为,近日里更是得了圣眷,往后成就不可估量。到时自己巴结一番,从对方指头缝里漏下几个官身,也好过自己无头苍蝇一般在长安钻营得好哇。
“大人这说得甚么话,某既是由大人自市井中提拔而来,怎能忘记大人的恩情?”周拂桢对着连衡长拜,激动不已,“愿随大人左右!”
“好!好。”连衡连道了两声好,终于是喜上心头,“既如此,我隔日便上奏朝廷,为你请一个朔方节度掌书记做。”
“朔方节度掌书记?”
“不错。你在此锻炼几番,若有功绩,便可为你请功。”连衡一笑,“这倒是个很能锻炼人的去处。当年我经由座师薛承旨的路子去往云中,便是在此做事的。”
周拂桢果然狂喜:将自己安置在主官曾经的位置,这向来是主官表示自己看重这一部下的体现。想来自己又走对了一步路,于是连声道谢,果然见得连衡亲切地将自己扶起。
“军师才识敏捷,将来一定大有可为呀。”二人复又坐回桌前,连衡握着周拂桢的手,道:“此情此景,倒是让我想起座师来。——那时琼林宴刚过,我与同年们一道去拜访恩师,那时他便对我们说,我等皆是世之英才,将来必大有可为……唉,只是……”
薛承旨的名号,周拂桢是听说过的:两朝老臣,不谓名禄。据说此人在先帝时官至內相,只是新皇登基后欲以他为宰相,薛承旨却说自己无意高位,不受宰相。周拂桢竟不知这样的老人还会有如连衡的描述一般温情的模样。
“大人为何叹气呢?我倒要说大人是天底下稍有的英杰,他日必当建功立业,封狼居胥!”
连衡摇一摇头:“今时不比往日了。当年先帝在时,哪有宗室敢四处勾连?……哪知现在,唉……”
“主公!……”周拂桢连忙凑近,举起酒杯来:“这样的事,主公还是莫要操心了……”
“嗯?……嗯。你说的是。不提这些了!来,饮酒,饮酒!”
两人复又举杯饮酒,直至天色近昏。周拂桢的酒量稍差,已然醉去,待得依然清明的连衡前来扶他时,只听得醉得糊涂的军师在梦中喃喃道:“……建功立业,……封狼居胥!……”
感谢陈珠绛大人借的铜杀戮
写不完了只好假装自己是文言文压缩一下orz
不对我格式怎么又没了
·
·
·
霜原进犯在即,朔方危困之境就在眼前,哥舒凌念及其父乃河东节度副将,遂欲请调援兵,以助朔方。
凌率亲兵数骑,疾驰河东。道阻且长,军情如火,众人不敢稍息,终日驰骋马背,所骑虽天山良驹亦惫极,副将久出军旅,亦股磨厚茧,血濡长衫,然无一人有怨言,竟五日即达河东大营。
众人尘满面,鬓如霜,形同流徙。守营士卒疑其身份,验看凭证方入禀哥舒将军。将军闻子突至,愕然出迎。见其狼狈之状,大惊曰:“吾儿何故仓皇而来?莫非遭王家欺辱?”
从骑皆怒目相视,哥舒凌即答:“非也,儿此行特为求援。此前朔方主将新丧,如今连总戎又困于京师,霜原乘虚而入,恐朔方危矣,凌恳请父亲分兵相救,以解危局。”
将军蹙眉叹曰:“于私,父子之情岂有不助之理?于公,河东朔方唇齿相依,朔方若陷,河东亦危。然吾仅为副将,无权发兵。”遂引凌沐浴更衣,拜见阎无咎将军。
阎将军乃国舅,皇后之弟,太子之舅。然其人以军功显,非凭外戚进身。凌整衣拜谒,见其人以帛覆面,威仪凛然,虽无刻意施压,自令人肃然。
凌揖而陈情:“今朔方群龙无首,霜原人猖獗作乱,更兼朝中有奸细与其暗通款曲。若不相救,恐朔方军腹背受敌,望将军借兵破局。
阎将军颔首曰:“凌所言极是。然河东亦与霜原接壤,若分兵助你,本方有失,为之奈何?
凌对曰:“河东有长城之固,山岭之险,易守难攻;朔方则平野千里,无险可恃。今愿请骑兵一支,此于河东或为余力,于朔方实乃雪中送炭。况朔方若破,京师危矣,太子与陛下皆在长安,吾等岂容君父陷于险境?”
阎将军深以为然,乃允借精骑三万,另嘱:“若霜原攻朔方,吾必自河东出击,围魏救赵以分其势,为尔等解困。”
凌喜出望外,然兵马整备需时,遂先辞别,轻骑返朔方。愈近边关之地,景象日益萧肃,百姓知战事将起,多有欲南迁者。
是夜,凌于城外休整,忽见一骑趁夜自北而来。凌觉有异,率众围之。其人自称驿丞,奉朔方军令驰报京师。
凌察其貌不类中原,且坐骑神骏异常,心知有诈。乃佯称同路,邀其暂歇,暗中将其击晕。从者遍搜其身,果得霜原密函。凌自知无力押俘行军,遂斩之焚尸,掘土掩埋,乃继续赶路。




作者:【十一招】宅斯特
评论:随意
一
李二狗得了个宝贝。
李二狗的宝贝是从王员外家里偷来的,王员外是从胡商那里买来的,胡商是从陈二麻子手里收来的,陈二麻子是从祁镖头的货里抢来的,祁镖头是从朱掌柜家里得来的,朱掌柜是从孙白虎的赌注里打麻将赢来的,孙白虎是从赵大傻的家底里骗来的,赵大傻脑袋被马蹄子踢过,啊啊呀呀说话说不明白,谁也不知道这宝贝他是从哪弄来的。
二
县太爷得了个宝贝。
县太爷想把这个东西献上去讨点好处,问师爷有什么思路。师爷眼珠子滴溜溜一转,说此宝乃是“无价宝”,虽然神奇,但不比金玉。若是寻常奉上,那可能上官把玩一阵,也就忘了这个好了。若是想要别人看中此物的价值,得花点功夫做个局,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
县太爷说,在师爷看来,这局该怎么个做法,又是需要什么样的天时地利人和?
师爷说,此物最为方美之时,得是寒冬腊月,冰天雪地之时,若是春夏之交,百花争艳,自然显不得此物的特殊,此为天时。而地利,则指若将此物置于山野寻常之间,林木丛生之地,必是埋没于树草尔尔,落了下乘,而若将其置于泥瓦金石之上,廷堂楼阁之中,方能一眼夺目,卓然独秀。至于人和……
县太爷说,这人和可是甚么难为之事?
师爷沉吟少许,说到,若是老爷登门献宝,此物分量恐有不足。咱们得让苏郡守自己过来拜访才行……
县太爷皱起眉头,捋了捋胡子说,这确实不太好办,师爷有何高见?
师爷回到,小人自有一计。獬头山的大当家三年未来上供,是时候敲打敲打了,若是向郡守请兵,那苏郡守自是要来亲自督战,不然功劳也不好算在他身上。咱们可以定在腊月讨伐山贼,届时在府中设宴,撤去寻常树草,只在中间摆上这个宝贝……
县太爷连连点头,隆冬时节,偏偏有此花盛放于堂府正中,这下想不注意到都不行。到时候咱们谁也不提这事,待宴席散去,直接将此物悄悄赠予郡守……妙,师爷此计甚妙!
师爷嘴角扬到了眉毛,说,老爷这胃口吊得更妙!相关事宜,小的这就去操办!
三
皇上得了个宝贝。
皇上把宝贝端在手里,摸了摸异常嫩绿的枝桠,提不起诗兴,也没有地方题字,于是草草拓了个章,便让太监收走了,再也没有拿出来赏过。
四
周大帅得了个宝贝。
周大帅用宝贝讨了芳梦的欢心,芳梦用宝贝跟于掌柜换了两根小金鱼,于掌柜用宝贝跟周大马换了三太太的小命,周大马用宝贝跟刘连长换了三把盒子枪,刘连长用宝贝跟许护士换了五支盘尼西林,许护士用宝贝跟小德子换了一袋白面,小德子把宝贝埋在了自家后院,后来小德子被飞机炸死了,没人知道这事儿了。
五
黄子丰得了个宝贝。
干废旧电器回收的,从垃圾堆里淘出来点啥本来一点也不稀奇,但是这玩意儿还有点……不太一样。
黄子丰给这东西擦了擦泥灰,看到上面写着一行英文。拿出手机对着查了查,是“时空传送枪”的意思。黄子丰把手机往桌上一扔,靠在椅子上不屑地笑了笑,心想这不知道是哪来的洋垃圾小玩具,不过这玩意儿手感沉甸甸,可能有不少铜件可以拆出来。
对着灯,黄子丰打开了这玩具的外壳,眉头一下子皱了起来。他对着里面的线路看了半天,于是又把盖给原封不动合了回去——这玩意儿里面是啥鬼东西啊?从来没见过这么精密的线路和组件……
靠着门口抽了两根烟,他坐了回去,在手里把玩着这个“时空传送枪”,枪体上面有四组滚轮,一组写着时间,一组写着经度,一组写着纬度,最后一组写着高度。都是英文。经纬度的滚轮坏了,磨损的很厉害,高度的滚轮更是卡住了。黄子丰一边拨弄时间那组的滚轮,拨弄到了一千年前,一边心里琢磨着这玩意儿该怎么使,用不能真把东西传送到一千年前吧?
试试就试试。黄子丰对着贡台上的苹果抠动了“时空传送枪”的扳机,只听见枪身里传来磁圈启动的嗡鸣声,然后一束光线从枪口射了出去,打歪了,打到了苹果旁边的一盆塑料花,随着一阵低沉的尖鸣,塑料花从黄子丰的眼前消失了。不是化成灰,也不是坏的四分五裂,就是凭空消失了。
我去,搞不好这玩意儿是真的啊!
【《时空枪神黄子丰》的免费试阅章节到此结束,喜欢就来订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