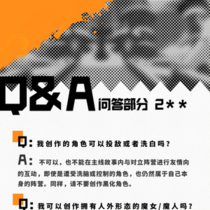轻微g向,可能引发不适,谨慎阅读……2002字
——————
当人类站在高处向下眺望,总是会产生再向前多迈一步、靠近边缘的冲动,重力成了一种魔力,吸引着人以最直接的方式——坠落——回归大地。罗威尔在一本书上看到过,这是大脑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可以阻止人们靠近那些有生命危险的地方。
但早在他了解到这一点的很多年之前……在遥远的童年时代,他就已经体会过了。
那被称作一起“生产事故”。在阿斯塔特的钢铁厂,事故是一个并不能被随意提起的隐秘词汇。实际上没过几年,还记得这事的人也确实就不多了。事情的起因不过在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周末,烂醉的工人漫不经心踱到了上班的地方,又在不清醒的状态下启动了大型轧钢机。或许是靠太近的缘故,莫名其妙地,他自己就被卷进去轧成了片。或许也不该叫作是片;这位工人最终留下的绝不是什么规整优雅的姿态,只不过是均匀分散在整个履带上、又从边缘滴落的血和碎肉罢了。人们赶到的时候,除了尚在轰鸣着的巨大机器,便是这样一副惨烈的光景。罗威尔跟着父亲也混在人群中,还没走到边上就嗅到空气中大量的铁锈味(还夹杂了一点酒味,死者分解得有够彻底,甚至混入空气中连同呼吸一起沾染了在场每个人的身体)。他透过人群的缝隙勉强看到了一点粉色的人体组织,看起来就像市场摊贩卖的肉馅。人类真是非常奇怪的生物,一旦认识到那些看起来再平常不过的血和肉都是自己的同类,瞬间就会被凉意侵袭脊背;唯独孩童对这类事情的敏感度还算差些,因为他们尚不知死亡为何物,也没有彻底形成共情能力。罗威尔只对“危险”有隐隐约约的概念,就像亮起红灯时火车的铁轨、动物园猛兽的牢笼一样,轧钢机也是不能随意靠近的存在。他再大一些才能明白更深层的含义。
他本以为他不会再回到这台机器前了。
高大冷峻的机器沉默在眼前。机油气味一阵一阵,在冬日的冷空气中飘荡又凝滞。老旧的厂房墙皮有些脱落迹象,角落还发了黑霉;天花板边沿的水管高高盘踞头顶,锈红色蜿蜒出崎岖的纹路。换气窗小小圆圆的,视线透过去还能看见一片狭小的蓝天。
罗威尔抬起右手,皮肤光滑完好。他很快意识到自己身处梦中,不仅仅是因为他想不起家人的模样;这个厂房早在前几年就关停了,讨薪的工人跑到新城区,拉起人墙把交通主干道围了个水泄不通。此刻在眼前的不过是他童年的景象。谁知道呢?他也希望这一切都没有改变,衰败的街道、烂病和光天白日下飞行的天使才是虚妄的幻想。
而且他知道自己为何出现在这里,要做的事情也再明显不过——
一副鲜活、有弹性的肌体,多么具有碾碎的价值。
罗威尔平静地启动了轧钢机,调到慢速挡位。他很轻松就跨过了黑黄相间的警示栏杆,一只脚踏上了移动的钢卷。做出这种事,已经完全称不上正常了吧?机械对所有喂给它的东西一视同仁,先是鞋子、脚,很快就开始吞咽脚踝和小腿。罗威尔听到声声脆裂,身体探进缓慢运行的关卡被一点点碾碎,却因为这早已在脑内模拟过一万次的场景终于实现而感到宽慰。
剧烈且大量的疼痛从已经不存在的身体末端爬了上来,灼热彻骨。他感觉自己像一块口香糖被肆意地压扁拉长,早已失去了内脏的概念。痛觉像万花筒里的虚像裂成无数碎片,被放大到几亿倍,流遍每一个神经末梢。他发现自己在过呼吸;的确,过不了多久连呼吸用的肺部也即将不复存在。他正在一节一节失去自己。
人类的大腿骨硬度堪比混凝土,罗威尔的脑中突然冒出这么一句。没有走马灯,他这一生什么都没有,只剩眼前冰冷的现实。进度条在他身上走到一半,他眼看着自己从履带另一头递送出去。滴答滴答,鲜淋淋的血液;扑通扑通,活跳跳的心。都是他自己。
谁会在意一个无名之辈的死?所有人都会淡忘。他们只是说:“可惜了,这么大一卷钢。”
但他还是想要,即使无人坐在观众席……他渴望着一场盛大的死亡。 那个工人,在生命最后的时刻,究竟有没有一瞬是清醒的?他知道吗,他的细胞涂布在这具钢铁身躯的每个缝隙里,许多年如一日,依然窥视着这座城市来来往往的所有人。
时间的确是相对的。超越生理承受极限的痛觉,让他感到思维速度成倍加快。他要用每一秒记忆这种感觉,无论能留存多久。他不是什么擅长观测记录的研究者,不是执着于缔造美丽情节的作家,不是杀伐果断的英杰也不是虔诚善良的教徒;他什么也不是,他只是故事里一个不起眼的逗点,一个承上启下,一个未完待续。
钢辊徐徐转动,闪着炫目的光,一边全无悲悯地倾轧牙齿和下颌骨。机器的内部也一定十分美丽吧,不知道他还能不能看到。耳鸣取代了机器的隆隆声响,把他一生中听过的所有话语尽数回放。癫狂的思念随死亡到来归于平静,也归于浓稠的黑暗。
阳光亮得刺眼,意识从汗涔涔水淋淋的噩梦里被打捞起来。晃了一会神,罗威尔才敢确信自己已经醒来。梦里许多不连续的片段一点点变明晰,他才敢小心使用贫乏的知识存储中、那几个并不算熟悉的词汇。
原来在潜意识深处的角落里,他还是隐约想过去死。
但反过来,罗威尔又发觉,也许他只是想要不成样子地嘶喊;他想要疼痛——独属于人类的疼痛,那让他感觉到生命的余量尚存。
而不是像现在……缓缓注射的、冰冷液体般的死亡,和空洞的、近乎痕量的恐惧。

写在前面的,是群里给的闪光一现出现的文,关联了好几个人,打扰抱歉
———————————————————————
老街区·罗谢尔的卧室
艾莉莎离开了,当晚,罗谢尔做了一个梦,梦中的他看见的一切都不一样了。
他,准确的来说应该是它,它的眼中出现了一座城市,而它此时正站在靠近城市的一根电线之上。
“嘎!”它振翅而飞,同时还大声叫了一声,以宣扬自己的存在,黑色的羽毛在它离开时缓缓飘落在地面。
快速飞上天空,翻身转了一个大回环,它向着视野中的城市前进。
在它的前方,是阿斯塔特,原本就是个工业污染严重又没有什么风景可看的城市。赖以为生的人力在逐渐被大量机械所取代,逐渐变成了一座钢铁森林,而现在,森林变得腐朽、杂乱,像是繁盛过极而走向了枯萎。
大量高楼大厦倒塌,到处都是残桓断壁,钢筋裸露在外面,像极了树上无法重新生长的枝杈。
城市并不大,它振翅几次就跑到了另一端,那里也是一样,没有任何人烟,有的只是寂静与枯萎的森林。
而这一路上,它不光看到了塌掉的楼房,还看见了被压在断裂墙壁下面的人腿,那是只露了半截小腿的人类,想来应该是已经死了吧?它这么理解着。
视野稍偏,一道掉落的招牌出现在它的视野中,那上面写着《幻梦境》,而此时的招牌已然碎裂,耀眼不再。在招牌的边上,仰面躺着一个人,肚子上被一根掉落的钢筋穿过,这人头发天然白,一动不动。
是百眼井小子,不知为什么,它的脑海中跳出了这个名字。
那么旁边的那名血肉模糊的小女孩他的妹妹了吧?她还如此年纪小小,就遇到了如此不幸。
它如此猜测着,却并没有停下自己的翅膀,而是转头向另一个方向飞过去。
在离两个人不远的地方,也躺着一个青年,拥有着一头火红。他的胸前破开了一个大洞,几只黑色的同类正在啄食尸体,看起来报餐了一顿。
嘎!它高亢的叫声一闪而过,算是打了一声招呼,而在它的身后,传来了几声回应。
继续前行,几个街口闪过。
一名头发棕色的男子站在地面上,一动不动,胸前一片血红,他的脚边掉落一把乌黑的手枪,它以前应该在其他的地方见过,所以才知道手枪这个词,但那是它此时无法理解的死亡。而在他的身后则躺着一个少女,身穿蓝白色的衣服。
是埃罗伊特和菲奥娜,它知道这两个人,只是想不起来在什么地方见过。
一阵狂风吹来,将它不由自主的向后退去。为了躲避这阵阻碍,它再一次调转了自己的方向。
汪汪汪!
狗吠,那是它讨厌的声音。
几只不知道从哪跑来的流浪狗正在舔着地上的污水,而在讨厌的它们旁边,却躺着一个人。穿着它根本不认识的装备,帽子上的水管破裂,管中的水早已漏光,变成了流浪狗的补给。
欧文,有些神秘的男子。
穿过高耸的钢铁森林之间的枝杈,越来越多的尸体出现在它的眼中。他们要么肠穿肉烂而死,要么身上一片血红,插着一种名叫做刀的东西。
而在这些不断出现的尸体中间,再一次出现了它觉得熟悉而且知道的身影,那人叫罗威尔,是爽朗的青年。此时,他的一只手不知丢到哪里去了,患病的那只脚也只剩了一半,泡在充满了垃圾的污水中,不只漂向何处。
滑行向前,它的眼珠转动,扫视着这片已经变得荒凉的城市。
远处,白色的建筑一如既往的屹立在那里,只是它的背面早已不再完整,变得跟其他地方一样破破烂烂。
一个转身,返回了老街区,它来到了别墅区的一栋房子前面。穿过打开的窗子,它到了一间白色的屋子。
这里应该叫做实验室吗?它的脑中疯狂转着,浮现出不属于它的知识。
两个一人高的大玻璃罐放在角落,里面装着一名十几岁的男孩子和一名已经成年的大人。罐子上的标签是它不认识的字,它只知道标签的读音,阿列克斯和克里亚斯。
而罐子的后面,躺着一个白发青年,紧闭双眼,胸前被手术刀破开一道割口,皮肉翻出,血早已流干。为什么克莱因会在这里?发生了什么?它容量不够的脑袋瓜思考不明白。
它停到了这个白发人的面前,啄食着流出来的肠子。
飞了这么久,有些饿了,吃饱了再出发,它如此想着。
将肚子填饱,再一次穿过窗子展翅飞翔,向着随便一个方向而去。
城市中,没有一个活人,有的只有到处流浪的野兽,它们靠着啃食死尸生活。这里是食腐动物的乐园,是被人遗忘的地方,是人类放弃之地,是魔鬼肆虐过的城市。
沙尘随着风卷而起,掩盖了地上的一切。它此次并没有受到阻碍,而是得到了强大的助力。
它随风爬升,一直向着昏黄的天空而去,在那里,有着火热的太阳,它想到那里去。
突然,在它的身旁快速飞过了什么,那个不明生物拥有一双白色的翅膀。它还没有来得及看清不明生物的样貌,就被对方带起的强大气流吹得在空中转了好几个圈,而当它稳住自己时,不明生物已然消失不见。
不再去想,它仍然继续向上飞着,不断挥动自己的翅膀,奋力向上攀升。只是,这一切并没有如它所愿。
它,或者说是他,他的翅膀渐渐变成了双手,而爪子也变成双脚,他在此时变成了人。他记起了自己的名字,罗谢尔。
他停止了自己的飞行,他开始下落。
而在他掉落于地面之前,他感觉到自己的双脚开始溃烂,肉片,肉块,血肉化成了碎片开始下落。溃烂的速度非常的快,就像砂糖融化于水中。
他的视野开始旋转,他看见了自己的嘴唇与鼻子。
而此时,一个声音出现在他的脑海中,说道:
百鸟在天空飞翔,
天使回归天堂,
复仇杀戮疯狂笼罩大地,
神说:试着去原谅吧,
却无人听从,
邪恶的怪物露出身影,
血腥,再次降临
巴别塔倾倒,
人类无法沟通,
魔鬼喜笑颜开,
他们,
同人类交易,
同天使交易,
同彼此交易,
将欺诈与隐瞒带来大地
黑暗中,
勇者试着寻找出路,
却发现,
尽头只有深渊,
投入其中吧,
他的心中有个声音呐喊道,
只有那样,
才能得到救赎
罗谢尔的眼前变得黑暗,他的双眼慢慢睁开。这里没有尸体,没有残破的城市,这里只是他的家。
原来是一场梦,他看着高举的那只手,那里有一道银光闪烁。
这样的情景也不错,你说对吗?我的女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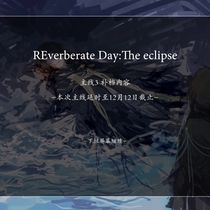
老街区·菲尼克斯诊所
女孩睁开了双眼,木然转头,昨天的那位医生站在她的旁边,对她微笑。
她的手臂已经经过专业的手法被包扎完毕,还被打了个好看的蝴蝶结。而她所在的这间屋子是昨天看着医生收拾出来的,一切都被重新布置过。
与晚上的气氛不同,白日的客房之中阳光和煦,暖洋洋的照在她的脸上,而她的眼睛却一眨不眨。从窗外隐约传来了说话的人声,那是邻居们在闲谈。
“早上好哦,艾莉莎。”菲尼克斯向躺在床上的女孩招了招手,“衣服就在床边的柜子上,起来自己换衣服,要吃饭了哦。”
但女孩没有任何动作,仿佛是没有听见一般,也没有任何的回应。
…………
菲尼克斯看着没有任何动作的女孩,安静思考了十几秒钟,然后走到了窗边将隔光窗帘完全拉展关严。
几分钟后,换好了衣服的女孩被他带着离开了房间,前往楼下的厨房吃早餐。
“不知道你爱吃些什么,只能随便做做。”
他将夹着鸡蛋、鲜虾、番茄和培根的三明治放在了女孩的面前,还有一杯正温的牛奶。
“来,我拿着,你吃?”
坐在了女孩的旁边,他伸手拿了一块三明治举着。
“…………”
女孩没有回答他,不过也没有拒绝他的意思,只是慢慢的,一口口咬着三明治。只不过因为有半张脸的肉已经烂光,只能用还算完好的那面咀嚼,一些三明治的碎渣掉在了女孩的身上,被他轻轻收起放在桌上。
“还有牛奶。”
眼见着一块三明治快要被吃光,他将牛奶如法炮制,也被喝了个精光,在牛奶调皮的从敞开的一侧溜出来的时候,被他抓了个正着,接在手巾上。
看起来,以后吃饭的时候要想想办法,不过这个精神状态,是脑子被侵蚀了吗?
菲尼克斯看着眼前这个女孩,放下了杯子的手中多出了记录用的纸笔,将女孩的状态完全记录了下来。
接下来的时间,是整理的时间。
菲尼克斯在帮女孩换衣服的时候,就按照以前的照顾玛莉亚时候攒下的经验,给女孩洗了澡。
简单的事情变得不那么简单,给病人洗澡不能按照平常的习惯来进行,他只能用浸湿的布慢慢擦着,血污,掉了的皮肉,混合着血水,弄了一地,缓缓爬行,消失在下水道的入口。
“我要检查了,如果痛的话要开口说。”虽然知道大概没有什么回应,但他还是习惯性的说了一句。
女孩患病的部位已经看过了,主要在手腕和脸颊的这些位置,他在病例记录人体图上画上了对应的位置,还额外加上了双手。
在他的记忆中,那双已经烂了的手因为女孩的粗暴复仇而彻底掉落。
他小心翼翼的将已经烂了的皮肉收集在袋子中,并且从女孩的病患处轻轻刮下了一些还带着健康细胞的皮肉。但就算是这样,女孩也毫无反应,只是默默的看着他在做事。
旁边的电视中传来了阿格尼斯的歌《烂吉他》,爵士的曲调悠悠扬扬,摇摆跳动的乐符欢快衬托在词句之下。音乐声引起了女孩的注意,她将头转到了电视的方向,脸上的表情有了些许的变化,那是沉浸在音乐中享受的微笑。
“你喜欢阿格尼斯?”菲尼克斯注意到女孩的变化,摘下了手套,刚好他做完了手边的事情。
“嗯。”这是第一次,他听到女孩发出了声音,不同于昨晚的嘶吼,是那种略有些柔弱的感觉。
“刚好,我儿子也很喜欢,他还吵着让我带他去演唱会,你要不要一起来吗?”
“嗯。”女孩点了点头,“我想去,谢谢您。”
“不用这么客气。”
“那个,医生您可以帮我缝这个小熊吗?”女孩用仅剩的手臂指着放在手术台旁边,被撕烂的小熊,那是她一直抱在怀中的布偶。
“叫我菲尼克斯就可以了。”菲尼克斯想起自己还没有报过姓名,然后他看了看那只小熊,点点头,“可以哦,不过要等检查结束?”
“谢谢您,菲尼克斯。”女孩再次恢复了平静。
“这个熊对你很重要吗?”菲尼克斯有些好奇的问着。
“嗯,这个是妈妈送的,但被我不小心撕坏了。”女孩点点头,眉头皱了一下,似乎是因为菲尼克斯的手术刀碰到了健康的皮肤,鲜红的血珠滚落皮肤,掉落在手术台上碎裂,溅到了两个人的衣服上,还好只是些许污迹。
“抱歉……”注意到女孩反映的菲尼克斯也注意到了自己手术刀的错误指向,连忙用酒精棉球对伤口进行消毒。
女孩摇了摇头,没有其他的抱怨,而是开口转向继续回答医生刚刚的问题,“妈妈死后,它是我唯一的陪伴,所以我不想让它那个样子。”
“我明白了,那你先休息一会。”菲尼克斯将女孩身上的伤口都处理好之后,帮女孩将衣服重新穿好。他将人扶到了客房的床上躺好,还盖上了被子。
而后,他转身从客房的柜子中拿出了针线,又将被撕坏的小熊从手术室拿了回来。一针一线,穿过小熊身上的可怕裂口,布料听话的随着他手中针飞舞而合在一起。
一侧的伤口缝合,菲尼克斯找出了家里还剩下的最后一点用作填充物的棉花填进小熊的肚子,以补充遗失的部分。另一侧的伤口,被他用漂亮的外伤缝合针法,针脚密实,尽量藏在了让人不注意的地方,就好像是一道装饰在小熊皮肤上的拉链。
“小熊已经缝好了,你看看怎样?”他将手中的小熊举到女孩的面前,“可以吗?”
“嗯,谢谢您,医生。”女孩点点头。
“那你好好躺着,我去做午饭,吃过饭之后我们去外面走走。”
“好。”
喜欢阿格尼斯的音乐,珍惜妈妈送的小熊,妈妈已经死了,精神状态稳定,看起来会对给自己带来美好回忆的事物反应稳定,而且会恢复正常。其他症状,待进一步观察。
在刚刚那个记录的本子上,菲尼克斯填上了新的观察记录。
午后的阳光暖融融的,让人很想在毯子上睡一觉,就像路边的猫一样,暖和而舒适。菲尼克斯开车带着艾莉莎到了离自己家最近的河边,但这里的风景并不好,垃圾漂流在河上严重污染,还好离着比较远,没什么特别难闻的味道飘过来。
菲尼克斯皱了皱眉,他拉着艾莉莎刚想转头走向另一个方向,却突然看到了一个双手溃烂的女人正慢慢走进河里,他不清楚对方想要做什么,也不打算去做这件事,只是慢慢看着。
那个女人的计划似乎没有成功,被呛了一阵之后就重新回到了岸上。而此时,在他身后安静跟着的艾莉莎突然有了动作,她挣脱了他的手掌,奋力向那个女人跑过去。
“妈妈!妈妈!”女孩大喊着,“妈妈!不要丢下我!”
“艾莉莎,那不是你妈妈!”菲尼克斯虽然不知道艾莉莎的妈妈是谁,但他记得艾莉莎刚刚还对自己说过她的妈妈已经死了,死人显然不会复活。
他在女孩跑出去之后也赶紧追了过去,抓住了女孩还没有溃烂的部分,只是比较轻微,害怕再次早晨新的伤口。
“放开我,那就是我妈妈!”并没有顾及到自己的病情,艾莉莎用尽所有的最大力气挣脱抓着自己的手,被抓住的部分血肉一点一点剥落,让菲尼克斯的双手染上了血红。
“……”菲尼克斯没有再辩解什么,只是拦在了女孩的身前,轻轻抱住了对方,让女孩无法继续前进。
“妈妈……”女孩的眼泪滚落,带下了片片皮肉,仿佛飘散的纸片。
就在菲尼克斯以为这件事还要经过好久的时候,他感觉一片阴影飘过头顶,女孩的动作突然停下了,她呆呆的看着天空,嘴里说着两个字,“天使。”
天使?
菲尼克斯在确认女孩真的不会再挣扎之后,才顺着女孩的方向看过去,却只能看到有什么飞向了远方。
“天使带着妈妈离开了。”女孩自从刚刚那一幕之后,不再哭也不再闹,而是慢慢变回了早上的那种状态,只是这次她的口中一直在念叨着这句话。
将女孩送回诊所的客房,菲尼克斯替她打开了窗。
“我出门一趟,你好好的待在家里。”他如此说着,这次却没有得到回应。
老街区·某条小巷
菲尼克斯将脸埋在刻意耸立的衣领当中,眼睛躲在头上帽子的帽檐后面,他没过几秒钟就向巷口看看,却无果而回。
就在他马上要失去耐心的时候,巷口传来了沉重的脚步声,他等着的男人深一脚浅一脚的向他走来。
“钱呢?”那个男人问着,手里拿着身份证件。
菲尼克斯没有回答,只是点了点头,并且从自己的衣服口袋中拿出了一个信封。
那是他们在昨天相遇时谈好的价钱,用来购买男人手中的病人身份证件。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场交易中不存在声音,一切都在寂静中进行。
衣着破烂的男人将信封中的东西倒了出来,那是一沓钱币。他仔细又小心的数了数,是五千块,比他索要的价钱还多了两百块。
再次抬头,得到了身份证件的男人已经离开了巷子,在他数钱的时候,对方已经验证过证件的真伪。
离开了巷子的菲尼克斯的眼前出现了一张黑色的小卡片,上面带着他有些熟悉的log,那是Sphinx研究所的标志。但他还没有看清那个卡片上的信息,卡片突然被一个黑色卷发,身穿黑背心的少年捡走了。
“前面那个先生,可以请留步吗?”菲尼克斯快走了两步,追上了那个黑发的青年。
“你有事?”对方有些警惕的看着突然出现的陌生人。
“你是想要去Sphinx研究所应征试药员吗?”凭借着医生的直觉,看到了对方手脚上的绷带,菲尼克斯迅速做了判断。
“……”这名看上去只有19岁的少年并没有回答。
“我劝你不要去,我按照街上贴着的告示打了电话,是研究所的电话没错,但对方说自己并没有进行招募试药的工作。”菲尼克斯直白且坦诚,“而且我自己就是一名医生,我也在进行研究工作,也许我可以帮你?”
“……”少年沉思了几秒钟才回答“可是我已经应征了消息群中发的那个试药项目,也发了市民编号给邮箱,得到的结果是那个研究所署名的入选邮件。”
“那能麻烦你……”菲尼克斯请少年为自己写下了邮件的地址。
“这是怎么回事?两个招募的详细情况却不一样……”少年似乎在思考着什么?
“……”菲尼克斯摇了摇头。
“想不明白。”
“菲尼克斯,很高兴认识你。”决定离开的菲尼克斯主动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
“啊,罗威尔,您好。”罗威尔同样的回应,也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
“那么,再见。”
“再见。”
偶然碰面的两个人,擦肩而过,去向不同的方向。
轻微的钥匙声伴随着门锁的转动,诊所的大门被轻轻推开。
“艾莉莎?”
怀中抱着装着一个纸袋的菲尼克斯发现房间中黑漆漆的,而且没有人回应。
熟练的伸手按下开关,光明被人工制造了出来,但艾莉莎却没有出现在他的视野内。
放下了手中装满食物的袋子,他走去了二楼的客房,只是艾莉莎也不在哪里。
人会去哪儿呢?
他站在原地思索,按理来说,艾莉莎那个情况应该不会到什么地方去才对。
而就在此时,咚咚咚,咚咚咚,楼下传来了敲门声,同时传来的还有一个陌生男子的声音,“ASPD,阿斯塔特警局。”
警察?为什么警察会找上门?难道前几天废弃工厂的事情暴露了?一边思考着各种可能性,菲尼克斯一边走下了楼。
“请问有什么事吗?”
他打开了内侧的屋门,却没有打开外面的防盗门,外面站着两个身穿制服的警察。
“请问您认识艾莉莎·伊万斯小姐吗?”门外的警察向他询问道。
“……艾莉莎?她怎么了?”菲尼克斯反问道。
“艾莉莎小姐被在河中找到了,是自杀。”
“……”听到这个消息,菲尼克斯的本来有些惊慌的目光慢慢变得冷静,“她是我的病人,最近刚刚被我带回来治疗。”
“原来如此,那可以让我们看看她的私人物品吗?”
“当然。”说话的同时,菲尼克斯想到了一个问题,停下了开门的手,“请问可以看看两位的证件吗?”
“没问题。”两位警察拿出了自己的警察证,菲尼克斯看了看,确认是真的。
“请进吧。”他打开了自己家外面的防盗门。
随后的事情就很常规了,警察们带走了艾莉莎的私人物品,包括那个小熊。这倒是给菲尼克斯省下了不少的功夫,不用他去收拾和丢掉那些东西了。
自始至终,他都没有去再看艾莉莎一眼,仿佛这个人从来没出现在自己的生活中。
这天晚上,菲尼克斯做了一个梦,梦中的他变得有那么些不一样。
————————————————
梦在日常线,传送门链接http://elfartworld.com/works/8276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