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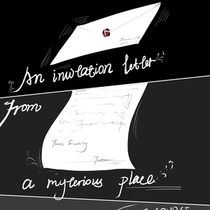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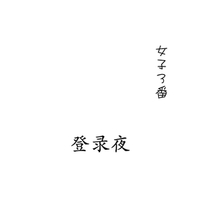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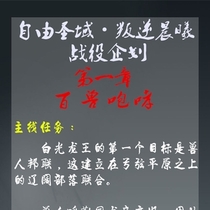
暑假即将更新沙滩寻宝的活动敬请期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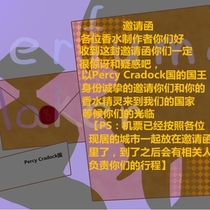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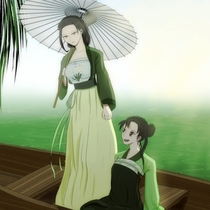



"你不应该生存在这里"
脑子里响起了这个声音
周围是一片火海
我做了什么?
只记得……老师逼着我念出了火魔法的咒语
我的周围什么都没有 火焰在渐渐熄灭
我的身体正在消失
我受够了
这次终于连神都不允许我存在了吧
妈妈把我一个人丢在这个世界便不见了踪影
这样也好
我也能从这个孤独的世界解脱了吧
感谢神明
我终于解放了
晚安
这就是那个什么吧?看不到明天的太阳了?
哈哈哈…
……
"喂,醒醒"
……醒来干什么,让我睡过去就能解脱了
"——再不睁开眼睛的话会很痛哦"
……?
好刺眼的光
啊 有位天使
真美啊……这是来迎接我去天国的天使吗
打个招呼吧
"接受天诛吧,垃圾。"
"……诶?"
诶————怎么冲过来了!?
天使杀人啦!
啊 神啊……
……连天国都没有我的位置了吗?

【规则更改】
暂时不会用到的第三人将定义为场外人员,不实质参与当前世界主线
但是请务记得创作,ta是必须存在的
举个栗子
AC组合的B是存在的,但是因一些缘由并没有去【基地参观】,变成了照常在做自己的事情
=======
特殊设定【观剧者】
观剧者是处于ABC世界外的,和魔女处于不同位置的上位观测存在
也可以是等同地位的魔女存在,但不能接触,更无法干涉
【GM的魔女是观测记录和在不干涉的前提下引导世界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