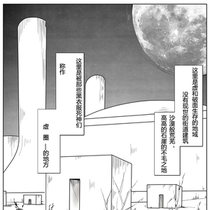不知为何,今晚小镇上出现了一些奇怪的生物。
丁汐小心地抬起右脚,后退了几步。‘它们’中的其中一只正若无其事地走过。
“……”
对,就是‘它们’。连公园里也出现了。
‘它们’从外形来看,就像是人类的眼球,不过大小却是掌心一般大。
这些‘眼球’在两侧和底部长有黑色细长的类似于‘它们’四肢的须状物。‘它们’利用这些须状物,模仿着人类的行走方式,正在小镇的各处走动。
总觉得还是调查一下比较好,于是丁汐电话联系了同班的几个目前已知的‘勇者’。
Anight和奈落的电话没有打通,沈行灿和Hilda有说要一起过来,但是现在还没到……
除去‘它们’外,目前公园里大概就只有我一个人。
不过按动物来算的话,有一只黑猫静静地趴在长椅上,它的眼睛在夜晚显现出独特的光。
不过自从进入到这个公园以来,这只猫就保持着这个姿势,虽然尾巴有在轻微地扫动,但它一直没有叫出声。偌大的公园中传人耳中的只有风吹动树叶发出的‘沙沙’声和‘它们’来回走动发出的声音,不管怎么说也太安静了。
安静得有点儿…不,没事,他们应该马上就要来了。约好了在公园汇合的,在此之前只要不轻举妄动就不会有事。
丁汐走近了长椅,那只猫没有挪动,也没有叫出声,只是目光相对,静静地观察着彼此。
万一惊吓到它,说不定会被抓伤,还是绕开好了。于是丁汐走到了椅后树下的空地,她注意到了椅背上刻着的几行字:“大地母亲的珍宝,由血之精灵守护着。那黑夜中的潜行者,是最重要的钥匙。”
是在暗指着什么吗?丁汐一时脑袋有点儿发蒙。不太懂,先记下来好了。
“那个,是丁汐同学吧?”
“嗯。沈同学和Hilda同学,晚上好。”
站在公园门口正四处观望的少年正是沈行灿,他向我挥了挥手,露出了表示友好的笑容。一旁紧跟着他的少女是Hilda,她的神色看起来有些紧张,似乎是在拼命忍住不要去看周边走来走去的‘眼球’们,做出了相当大的努力呢。注意到我的目光,她赶忙开口道:“噢…晚上好。”她努力牵扯嘴角想要微笑,不过笑容还是有些僵硬,透露出难掩的不安。
看来是很害怕‘它们’吗?
嘛,最终还是按约定出来了,路途上应该也有遇到吧?也是辛苦她了。
虽然我对‘它们’也是…
不过已经一个人在公园看着‘它们’那么久了,感觉某种程度上来说,自己已经麻痹了。
“所以说...不知为什么,镇上今晚出现了这些家伙。”丁汐指了指离自己最近的一只‘眼球’。
“啊......”Hilda下意识地顺着丁汐指的方向看去,紧接着又赶忙移开了视线,缩了缩脖子。
“你在看什么呢?”沈行灿好奇地凑了过来。
“我发现了一些东西...你们过来看看。”丁汐向站在稍远处正躲避着走过来的‘眼球’的Hilda招手,示意她也过来。
“……”他们盯着这些字认真地思考了一阵子,丁汐眨了眨眼等待着他们的反应。
“钥匙,听起来像是重要的道具呢...”Hilda点了点头,开口道。
他们想到什么了吗?
“对啊,只是这个钥匙要打开的是什么,这一点我们需要确定一下。”
说着丁汐望向了沈行灿,而他沉默着起身打量了一下四周,好像发现了什么,他走向了公园中央的那棵大树,蹲下在地上摸索着什么。“血?”
丁汐和Hilda凑在他一旁看,沈行灿的手指上沾有猩红色的粘稠液体,确实有点像是…血液?
这种液体似乎是从树根旁的草下渗出的。
“树下一定是有什么……”得出这样的结论后,沈行灿掏出了一只…呃,这个不是炒菜用的…锅铲吗?
虽然用了很大的力气,但每次他只能削掉薄薄的一层表皮的泥土。所以他是想要用这只锅铲…来挖土?
Hilda默默看了一阵子,进展的速度太慢让她有些按耐不住了。“还是让你见识一下正版铲子的威力吧!看招!”她掏出了一只铁铲,顺着沈行灿挖出的痕迹挖了起来。
唔,这次是正规的园艺用铁铲了。
丁汐有些手足无措地后退到了一旁。
他们在挖土…可是我,出来时并没有带什么工具啊,帮不上忙…
怎么办…怎么办…有了!找个话题一起来讨论吧!至少自己不是闲着的!
啊呀……这…
嘛,还是算了吧。
为了不影响他们,丁汐走到了稍远的地方。
之前的那只黑猫仍趴在那里,看来不怕生呢。
试试有什么办法能让它从椅子上下来?
丁汐在草丛中拔了一棵狗尾巴草,凑到它的面前晃了晃。“……”猫只是定定地望着,没有做出什么反应。
虽然有些丢脸…算了!豁出去了!
“喵——喵——”变着幅度晃动狗尾巴草的丁汐,此时死死地盯着面前的黑猫,小声地模仿猫的叫声向它示好。
丁汐感觉自己的声音在颤抖,不,是全身都在轻微地发抖。
好丢脸…拜托了,千万不要让前面正挖土的他们听到!
丁汐偷瞄了在树下忙活的他们一眼。
沈行灿似乎在用手中的锅铲大幅度地舀起什么东西扔出去,重复几次。哎?是挖土有了什么进展吗?只是土片的话是不需要…
与之形成对比的,Hilda的动作好像不是在挖什么倒像是在用力用工具向地面按压着什么的样子,一上一下的频率很快…
他们都取得成效了吗?可是…猫咪我求求你倒是理我一下好不好?!好不好?!
可是猫咪并没有听到丁汐心中的哀求,它只是舔了舔爪子,目光澄澈。
唔,它其实…还挺可爱的。猫咪我抱你一下你不会抓我吧?
丁汐小心地伸出了手,见猫并没有什么抗拒的反应,她轻轻抱起了它。
还是不敢用太大的力气,总之不能弄痛它。
猫咪的毛,好柔软…
“想要钥匙吗?”正当丁汐想要顺势抚摸一下猫咪背上的毛时,猫突然开口道。
对,它终于开口了,而且说的…是人话?!
敢情我刚刚“喵喵”了半天都是……
丁汐此时的心情很复杂。
对了,它刚刚有说到‘钥匙’。就是椅背上的字所说的‘钥匙’吗?
‘黑夜中的潜行者’,啊,对了,指的就是它啊。
“钥匙的话,可以给我吗?”
“今晚不能给你们。”猫停顿了一下,“明天来找我吧,我不会离开这里的。”
“好。只是...能先告诉我,这把钥匙所要打开的是什么吗?”钥匙由它负责的话,它一定知道些什么吧。
“……你们所希望得到之物,这场游戏中最至关重要之物。”
‘最至关重要’…吗?所以一定要取得钥匙得到那个东西啊。是不是这样…我们的生活就可以恢复正常了呢?
不过还是觉得不会有那么简单的。
“那么,那个东西...现在藏在哪里呢?”
“就是你们刚刚挖的那里。”这样说着,猫咪望向了树下沈行灿他们的方向。
啊,那么果然,树下藏有什么东西!只是…
丁汐注意到了原本只是漫无目的走着的‘眼球’们,正纷纷走向树下的他们那里,甚至数目好像增多了。而他们的动作,也不太像是正在挖土的样子。
是被阻碍了吗……啊,也是。不可能那么简单就把这样重要的东西交给我们的吧。
“它们...在阻拦我们挖开那里。想要避开它们取得那样东西的话,有什么办法吗?”
“没有我的允许,你们是不可能得到的。”猫轻微地动了动耳朵,“我会考验你们是否是一名合格的勇者,也算是在执行莉莉亚大人交给我的任务。若合格,你们自然会拿到手。”
又是莉莉亚…所以最近发生的不正常的一切都是和我们的校长大人脱离不了干系啊。来自猫的考验?其实说是来自莉莉亚的考验也差不多吧。
“是什么考验呢?”
“这个嘛,你们明天就会知道的。”猫看起来已经不再愿意透露什么了。
明天不知又会发生什么,还是小心为好。猫的话,也算是一个预警。
“那...就明天吧。明天我会再来找你的。”丁汐小心地把猫放到地上松开了手,“那么再见啦,猫咪。”
猫轻巧地跳上了长椅,还是以之前的姿势趴下了。
“祝你安康。”
………
“丁汐!除了我们这边,公园里其他地方还有眼球么?”沈行灿突然喊道,丁汐循着声音望去,他此时手里正握着一只平底锅。
哎?从哪里变出来的吗?
啊哈哈…
“这种眼球的话...各个地方似乎都有,只是它们现在在向你们那边聚集,发生了什么吗?”
“我们只是觉得树底下应该有什么……难道这些玩意儿就是血之精灵吗?”沈行灿说着用平底锅拍飞了在他脚旁的一只‘眼球’,“此地不宜久留。”
“也不想久留就是了,快走吧...”Hilda收起了手中的一只…一只匕首?!
原来你们出来都有带上这些东西吗?!
唉…下次,我下次出门也随身带些什么好了。
“走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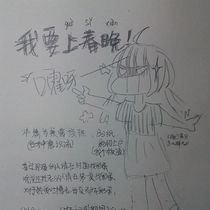
一
“在北極的海洋上,常年覆蓋著厚重的冰山和薄薄的浮冰。其並不是在短暫的時間內形成的,不消說冰山是在遠古脫離大陸架的冰山,而浮冰則是在海洋下降至冰點以下後,在海面上緩慢形成的……來,托比亞斯,你看,這就是浮冰的樣子。”
溫柔的母親將圖畫書上面的資料指給他看,托比亞斯瞇起眼,盡自己可能地看著書上那白白的一片,隨後,他放棄了。
“媽媽,講騎士和公主的故事書吧。”他哀求道,以小而軟的手抓住母親的衣角,“我想聽那個故事。”
他母親躊躇了一會兒,似乎是在思考要不要嬌慣孩子,但還是放下了手中的地裡書,她從暑假上拿了另一本,封面上的彩色模糊成一片。托比亞斯憑著自己熟悉那本書封面的顏色,推測出那是他最喜歡的書。
“托比亞斯,坐好了。”
“嗯。”他騰出座位來,等母親給他講那個故事。
“很久很久以前啊,在一個國家裡,有位正直的騎士——”
騎士的養父因恐懼預言,而讓騎士去尋找一個寶藏,那便是被侏儒化成的龍,所看守的戒指。就這樣啊,騎士帶著劍上了路。等他到了巨龍藏身的地方,便吹響了號角,被號角聲引來的巨龍從洞穴裡鉆了出來,騎士便將刀劍刺入巨龍的心臟。就這樣啊,巨龍的血濺到了騎士的身上。
騎士因而可以聽懂小鳥的語言,在他們的叫聲裡,他知道在遠方有位被火焰囚禁的公主,騎士被小鳥們的請求打動,便去解救公主了。騎士將阻止他尋找公主的人打敗,而後在火焰中喚醒了公主。啊,那是他所見過的,最為美麗的人,金色的長髮如同黃金的瀑布一般,她醒來後唱起了好聽的歌,隨後問騎士她的英雄是誰。
“是我。”騎士回答道,隨後他們在太陽下立下了永久的誓言,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托比亞斯聽完了這個故事,想再纏著母親給他講一次,但女僕來敲門了:“夫人、少爺,老爺正在客廳裡會見親戚。還請您不要與他們發生接觸。”
“好的,放心吧,我們不會出去的。”母親這麼說道,她們又說了些別的,托比亞斯靜靜聽著,直到女僕合上門。
“親戚是什麼呢?”他小聲問道,母親聞言笑了笑——只是那笑容裡,帶這種違和感罷了,而托比亞斯還不懂其中的含義。
“親戚啊,就是有血緣關係的人哦,可以是爸爸媽媽的叔叔,或者爸爸媽媽的姐姐弟弟,堂兄表兄也是哦。”母親溫柔地摸起他的頭,“還記得美和堂姐吧,那孩子也算是托比亞斯的親戚哦。”
“美和表姐……”托比亞斯搜索起記憶來,他確實記得有個語氣很溫柔、摸過他的頭的姐姐,“親戚都是好人吧?”他輕聲問道。
“……不是哦,親戚裡面也是有好有壞的,我們家很不幸的,有很多壞人親戚呢。”母親這麼說著,托比亞斯歪了歪頭,表示不理解,但也只是得來母親的擁抱而已。過了會兒,他從母親的懷裡掙開。
“媽媽,教我怎樣像爸爸那樣下棋。”他說著,母親聽後從書架上拿出黑白相間的棋盤,還有形狀各異的棋子。托比亞斯摸索著棋子上面的小型雕刻,主教和城堡各有各的特色,在那些棋子裡,他最喜歡騎馬的騎士。
“上次已經說過,棋局裡,一旦國王的棋子被吃掉,棋局就結束了哦。”母親把他的手放在其中一個棋子上,讓他感受那人頭上的皇冠與其他人的不同,“國王的位置旁是女王,女王啊,是整個棋盤裡最為強大的棋子。”
“他們是夫妻嗎?”
“是啊。”
“就像爸爸媽媽一樣嗎?”
“嗯。”母親輕柔地答道,托比亞斯聽後懇首,好顯示他聽懂了,“剩下的棋子裡,城堡只能橫豎走,教皇只能斜走,騎士的走法是這樣。”她抓起托比亞斯的手,讓他拿住一個騎士,隨後再在棋盤上反復重複一個跳躍的動作,“這樣就是騎士的走法了。然後這些,”母親讓他摸放在棋盤前列的、較小的棋子,“這些是士兵,只有第一步的時候,可以走兩格,在棋盤上,他們通常只能向前走一格。”
“哎?那那樣其他的棋子,都是在欺負弱小了吧。”托比亞斯說,聽到這評價,母親搖了搖頭。
“不一樣哦,士卒並不弱小,在戰局的最後,也可以通過走到敵陣的最後,而獲得無論哪個方向都可以走的能力。僅僅只是能力上,與其他的棋子有些許不同罷了,但是這並不代表他們就是孱弱的棋子。身為棋士,是要理解每種棋子的優點和特質的。”
“優點……”托比亞斯用拇指摸索著那個棋子。他母親隨即讓他比了一盤,托比亞斯就毫無懸念地輸了。事後,他母親安慰他,並說明天會再下棋,他也就點頭答應了。過了會兒,母親說要去看看他妹妹睡得如何,讓他乖乖待在房間裡。
托比亞斯翻動著自己看不懂的童話書,玩著白色的騎士棋子,他想象它是活的,如馬一般的四蹄,能跑動起來,背上的小人會舉起劍,衝鋒陷陣,拯救他的公主。他把棋子舉過頭頂,在自己的頭腦裡上演又一出童話。他想象馬背上的騎士將巨龍殺死,利劍刺入龍的心臟,他站在那裡,為騎士助威。
如此一來騎士和公主一定能獲得幸福。
他滿心期待地想著,知道有人又敲響了門,他踮起腳打開,看到女僕手中拿著茶壺和茶水,面色沉鬱。他剛想說些什麼,卻被對方用食指按住了唇。
“少爺請小聲些,老爺正在會客。”
托比亞斯那時還不懂女僕眼中所劃過的一絲猶豫,只是疑惑為什麼要如此戒備“親戚”。
“可以帶我去拿茶點嗎?”托比亞斯問道。
“在那幾位出去前,還請您忍耐……”姓為左左村的女僕拘謹地說道,向他呈上一杯帶著玫瑰花香氣和水果酸甜味道的茶,“畢竟,櫻庭家木宮分家的那些人,簡直和暴徒沒什麼兩樣……”
“暴徒是什麼意思呢?”
左左村略微一滯,隨後猶豫地說道:“就是壞人的意思吧。”
“哎……這樣嗎。”托比亞斯看著手中的騎士棋子,“也就是,會被好人懲罰的傢伙們吧。”
“……嗯,是這樣沒錯哦,少爺。”女僕輕聲說道,她將窗簾拉開一小條縫,托比亞斯感到陽光的灼燙,便換了個位置,“車子……還沒走。”
遠遠地,在走廊裡,有爭吵的聲音。托比亞斯指了指門,想打開它,卻被女僕阻止。隨即,他聽到門被踹開時發出的巨響。走進來的人身材高大,踩在地上步子很重,他起先以為是父親,但之後意識到那人的腳步比起他爸爸要更為拖沓些。
然後是更多的人湧入的聲音。
“怎麼了嗎?”他問,迎來的是那男人的破口大罵。
“看看你們兩個不孝子孫做的事情,老頭子在天有靈,肯定要氣得暈過去,櫻庭這麼大的家族,哪有兄妹相奸的道理?就是分家在外也臉面無光了!畜生!畜生!”那個素不相識的成年男子喊道,“我們可是名門望族啊,這就要被你們兩人毀於一旦了!你怎麼負擔得起!”
“還請您不要在孩子的面前講這些……”在男人憤怒時阻止的聲音正是托比亞斯的父親。
似乎是經這麼一說,男人注意到了托比亞斯的存在,隨後冷笑了起來:“早就聽說你們倆生下兩個小畜生啊,這個模樣,是有病吧,全身一片白……嗯,怎麼,還眼盲?還是弱視?這便是報應啊,報應哈哈哈哈哈。”男人的語氣令托比亞斯感到不適,對方卻並沒有停下來,而是湊近他的臉,“聽好了,小鬼,你的父母就不應該相愛,你就不應該生下來,你們所作所為,就是帶給整個櫻庭家不幸——我這麼講,你聽懂了嗎。”對方的語氣咄咄逼人,內容則讓他聽不大懂,唯一能懂的,就是那句‘你的父母不該相愛,你不應該生下來’。
孩子被這番話刺激,是會立刻掉眼淚的。男人見狀,像從訓斥一個孩子中生出了快感,繼續罵了下去。托比亞斯原本就模糊的視線裡,變的更為難辨。
“像你這種生來就有缺陷的孩子,大概不懂都是自己父母的錯吧,你聽好啊,要是你父母沒有生下來你反而更好……他們原本就不該在一起!道德何在!法律何在!就是因為這種人,我們櫻庭家才會變成這個樣子啊——”
“您不要再說了!”打斷男人的,是父親幾近哀求的聲音,“他不過是個孩子而已,怎麼會懂這些。托比亞斯,我和你媽媽,都愛著你,我們也很相愛,請不要擔心。”
隨後是,女僕左左村移動的聲音。似乎是被打中了吧,方才還氣勢凌人的男人,發出了一聲哀鳴,然後被拖了出去,臨走之前還在咒罵著。
終於走了。托比亞斯跌坐在地上,直到父親把他扶起來。
“剛才那個人說的都是真的嗎?”他問他父親,後者只是沉穩地摸了摸頭。
“我和你母親確實是兄妹,其餘的事情,都是他在瞎說,托比亞斯不用去想那麼多,爸爸媽媽愛你。”
“這樣啊。”聽到父親這麼講,托比亞斯便生出了安心感,眼淚也止住了。大概是因為方才哭過的緣故吧,他感到倦意,左左村帶他去洗臉,冰水打在臉上,意外得讓人感到安心。這時,母親走過來抱住他,安慰他。
“沒有關係的,其他的事情我不知道,只是我和你父親彼此相愛,也愛著你們這件事,是無論發生什麼都絕對不會改變的。即使別人否定了一萬次,也絕對不會改變。”女人輕柔地摸著他的頭,安撫他道。
托比亞斯聽著女人的話,感受到對方掌心裡的熱度,然後問:“我長大以後也要和櫻子結婚嗎?”
這樣的問題迎來的是母親噗嗤的一聲笑,但是她還是回答:“不是啦,不過,我想說的是,托比亞斯喜歡什麼人都可以,愛誰都可以,這並不是什麼有錯的事情,喜歡那份心情,是不可能輕易改變的。還記得我剛剛給你讀過的故事嗎?即使隔著火焰,騎士也仍然要拯救他的公主,這便是愛情啊。”
“愛情?”
“嗯,在唸的時候輕輕捲舌的lo,然後是牙齒摩擦嘴唇的ve,L-O-V-E。”
“愛(love)。”托比亞斯學舌道,母親似乎很滿意這個發音。
“就是這樣哦,托比亞斯,這個世界上,愛是可以跨越所有的鴻溝的。無論什麼都無法阻擋,這就是世界上最厲害的東西。”
“嗯……”他躺在母親的懷裡,瞇著眼看眼前那團溫暖的色塊,在那片怪異的氣氛中感到疲倦,最終睡著了。
二
在稍年長之後,父母便開始教他成為滅卻師的技巧,并另聘了老師教他識字學習,雖然看不清遠處的東西,但讀書這種事情,還是能做到。但也因此在學習如何成為滅卻師時,總也無法掌握拉弓射箭的要領,因此就放棄了這種武器,而改用佩劍。大概父母是希望有朝一日,自己也能有自保的能力吧。雖然做的不好,但也要學習怎樣畫陣。慢慢地,身為滅卻師的第六種感官覺醒,代替了原本就沒什麼大用處的視覺。或許是錯覺吧,但是托比亞斯能從空氣中靈子的流動,來分辨每個人。自從意識到能感覺到靈子的位置,便慢慢有了這種能力,好像在水邊可以通過觸摸水面,辨別漣漪,來確認船是往哪個方向、什麼位置行駛的一樣,是萬千種觀測世界的方式裡其中一種。
在十二歲生日那天,托比亞斯收到了“劃破靈魂之物”作為自己的武器。對於父母就好像贖罪似的舉動,托比亞斯只是覺得悲傷罷了。
明明不需要這樣做也可以。
偶爾,也被父母帶去,在遠處安全的地方,“看”左左村與虛們作戰。遠遠地,能感受到一種令人不舒服的靈子。
單單是感知到,都會感覺自己的全身被那種靈子玷污。
托比亞斯站在高處,聽到在下方左左村的弓箭劃破空氣的聲音,疑惑著為何是那位腳步聲輕柔的女僕負責這種事情。隨後他被父母解釋,因為左左村是混血滅卻師的緣故,只有混血滅卻師能討伐虛,這是為了防止滅卻師純血者的血統遭到虛的玷污。
因為虛無縹緲的血統,所以要讓混血滅卻師們戰鬥。這樣的系統,讓托比亞斯感到不可思議。
“那麼,混血滅卻師們要更為強大嗎?”他小聲問他的母親,婦人聽後只是笑笑。
“純血滅卻師的天賦和力量,都要更強些。”
“那為什麼還要讓混血做這些危險的事情?這樣不是很奇怪嗎?難道不是身為強者的人,保護弱者要更好些?”托比亞斯輕聲說著,等待著回答,這次,卻沒有得到答案,只是母親歎了口氣後,用這些事情你還不能理解而一筆帶過了。左左村還在和那種擁有令人會生出雞皮疙瘩的怪物們搏鬥著,好像這就是她的生存意義。
在托比亞斯的觀念裡,父母都是開明的人,卻在這種地方固守著過去的傳統,不知為何,令他感到違和感。
當晚,左左村端來睡前的牛奶時,他聞到被香水掩蓋的腥味。女僕將熱好的牛奶放在他面前,托比亞斯才意識到那人的手上纏了繃帶。
“手,沒事吧?”托比亞斯問道,左左村愣了愣,似乎為這突如其來的關心而嚇到了,隨後才說道:“啊啊,沒事的,並沒有被虛傷到,要是到了那種地步,才是沒法救回來了。”
“啊啊……為什麼是混血滅卻師在戰鬥呢?你知道嗎,左左村?”托比亞斯拿起攪拌勺,輕輕地攪動起溫熱的液體。
“您是在擔心我嗎?”
說是擔心也不盡然,更多的是為身為純血滅卻師卻無法保護弱小者的自己感到惱怒吧。托比亞斯想著,左左村笑了笑,卻沒有答話。
“怎麼講呢,保護櫻庭血統的潔淨,就是左左村我一族的使命,還請少爺您不要擔心,這就是我們所有混血滅卻師必然會踏上的道路。怎麼說呢,這種事情,是類似進化之類的東西吧。”
“進化……?”
“這是生物學上的一種理論,舉個例子來講,就是有對兄弟,在長大後,其中一方選擇放棄生育,轉而用自己的力量去幫助自己兄弟的子嗣,結果上,就是更少的後代可以享用到更多的資源……雖然對少爺您來講,可能很難理解吧,但是,這就是混血滅卻師與純血之間的規則運作的方式,我等貢獻力量,保持你們血統的純淨,你們不需要去戰鬥,單單是維持那純血,對我們來講便已經是報答了,而換來的是整個滅卻師族群的昌盛……”
“那樣……也太奇怪了吧。”
“哈哈,果然您還是沒有能夠理解這種事的能力吧,不過。等您長大後大概就會明理解。左左村一族原本也是櫻庭的分家,所以兄弟的例子,也算不得奇怪……”左左村笑笑,收起了托盤,“等您享用完牛奶後,再叫我吧,屆時我會將用過的杯子收起來的。”
“嗚……”托比亞斯點了點頭,女僕關上了門,視線裡,室內的色塊一下子昏暗了很多。他處在一片安靜的黑暗中想到自己身為純血的意義,那就是純血扎根於混血之上,吸取同類的養分似的,將那些混血壓榨至枯萎。但是被壓榨的那方卻心甘情願,口口聲聲地說是為了滅卻師的昌盛。果然很奇怪啊。如此一來,不如說滅卻師這個種族本身有種奇特的病態,以植物來比喻,就是從根部開始,便被鐵圈縛住、畸形地生長的盆栽。
這就是身為滅卻師,無可奈何、不得不去面對的事情吧。
“不公平。”生來就擁有比別人更加優渥的環境,此生除卻生來的疾病並未受過多少折磨的托比亞斯,頭次生出了這種想法。他無疑是明白自己才是這不公的受益人。但是心緒裡好像有什麼在作祟,讓他無法容忍這種事情,“無論哪邊都有問題啊……”體制從一開始就出了差錯,所以才會導致整個制度產生扭曲。要是能以自己的力量……稍稍改變哪怕一點就好了。
那時他還未意識到,上百年建立的體制,是不會在一朝一夕間被瓦解的。
隔日,與家教練劍時,托比亞斯在外庭裡聽到有鳥兒的叫聲。對鳥兒不甚了解,他只是意識到原來現在已經是鳥叫的季節了。抬起頭時看向四周,雖然模糊,卻也能看到濃郁的綠色色彩。
隨後他便被擊飛了手中的劍。
“給我認真……認真啊!”家教大聲喊道,托比亞斯回過神來,這才意識到對方在說什麼,“你才不只這樣而已吧!把劍拿起來!”
“剛剛掉到哪裡了……啊,在腳邊嗎。”托比亞斯回過神來,低下頭看到自己那把擦得銀光閃閃的劍,他把劍舉起來,看向那片銀色上,自己朦朧的肉色倒影。不知道是原本就很模糊,還是自己的眼睛有問題,恐怕,兩者兼而有之吧,“是您很厲害的緣故吧。”
“喂喂,就算你再怎麼會看人臉色說話,在我這裡也是行不通的哦?我可是會罰你跑十圈的!”家教這麼說著,但語氣裡面能聽出來,似乎有些開心。
看人臉色嗎。托比亞斯在腦袋裡想著這個情況,不知道為何感到好笑。明明只不過是隨口說說、發自真心的言語,卻被當做奉承的話。如果自己是會看人臉色的人倒是好了,這樣就能明白什麼時候可以說奉承的話,什麼時候不可以吧。
教官是分家椎名家的人,不過似乎因為滅卻師的血統過於單薄,早在一世紀以前就已經放棄了身為滅卻師的那部分,似乎是受到了家人的推舉,姓椎名的男人才過來做自己的教練的。雖然已經成為了局外人,卻還是對櫻庭家的事情有半分了解。
“給,左左村凍好的綠茶。”男人拿過來一個筒形的茶杯,托比亞斯道著謝接了過來。綠茶似乎是很早就泡好後再放入冰箱的,裡面並沒有茶葉,喝著的時候,有種並不是在喝茶,而是在喝什麼其他的液體的錯覺。
“噗哈——”椎名將茶水喝掉幾口後,這麼歎了口氣。
“為什麼椎名的家庭放棄做滅卻師了呢?”
“嗯……你問一百年前那麼久的事情做什麼啊,都過了四五代人了。”男人這麼說著,短促地笑了一聲,“作為滅卻師血統太單薄啦,而且,本來我們這一系就是去為其他姓氏的事務決斷的中立人……可以說是不需要插手太多滅卻師的事情,所以才自己選擇淡出的。像我,就只能聽到那些傢伙的聲音,連看都看不到。”
“……哎?”
“對我來說,我倒覺得放棄做滅卻師挺好的。每天都要冒著生命危險,多不值得啊。啊,好喝,不愧是左左村泡的。”男人大口吸溜著茶水的聲音,不知為何總讓人覺得很失禮。
“請您不要這麼做,聽起來很像電影裡面的豬。”
“哈哈哈哈,你這小子,意外的也有嘴巴不留情面的時候啊。”對方好像絲毫不在意似的,不留情面……但也只不過是說出來自己想說的事情罷了,“明明剛才還那麼誇我……”
托比亞斯決定不去在意椎名說的這些話,只是問道:“冒上生命危險,幫世界除害,保護普通人,這不是很好嗎,如果有像你這樣靈力高,卻不懂得自保的人,就需要我們了吧。”
“哈哈,你小子對滅卻師這個職業的理解還真是錯得離譜。”椎名笑著,卻並沒有半分笑意,好像只是單純地用氣流掃弄喉嚨發出那樣的聲音來,“才不是那麼簡單的事情呢……滅卻師從來就不是伸張正義的職業啊,要說是正義的夥伴,明顯是死神更合適吧……嘛,也無所謂啦,無論是勝者還是敗者,都有書寫歷史的自由,哪怕是毫無道理的強辯也是可行的,只要讓自己的孩子相信自己這邊是正義的,就好了吧……”
“為什麼這麼說……就算是滅卻師的問題,死神也不應該發動戰爭吧。”
“所以說,不懂啊,托比亞斯。”椎名不知從什麼方向伸出了手,彈向托比亞斯的額頭,托比亞斯捂著額頭,繼續聽對方說了下去,“滅卻師之所以要消滅虛,只是因為生來就無法接受這個種族而已,啊,以普通人類的角度來講,從石器時代至今,過去兇猛的豺狼已經成了自己的夥伴,雀鳥過去危害農業,但隨著城市的拓建,卻慢慢成了籠中的玩物,虎豹之類的猛獸被關在動物園裡面,不成威脅,反而成為人類充滿力量的象征……只有蟑螂、老鼠、蒼蠅,從過去開始,就是被生理性厭惡的,到了現在也依然如此,因為他們確實地搶掠了人類的資源,傳播疾病。說白了,就是人類和這些種族之間,生來不對盤吧,而滅卻師對虛也是這樣啊,如果不把他們殺死,被虛傷害到一點的話,就會充滿痛苦的死去……身為滅卻師的一族,從頭到尾所考慮的,不過就是自己這個種族的安危罷了。”
“……難道,不是因為襲擊魂魄的虛是邪惡的存在嗎。”
“你這孩子,還真是天真啊。”
“哎?”
“感性、好騙得不可思議。大概是因為從小時候開始,就只在這個小小的庭院裡活著,從未見過外面的世界的緣故?到了你這個年紀,其他孩子再怎麼愚笨,也會稍稍開始思考起這個世界吧。”
“……唔。”被對方這麼評價,托比亞斯不知為何並不生氣,而是繼續聽對方說了下去。
“你有見過虛吧?”
“嗯……昨天……”托比亞斯回想起昨夜跟父母在遠處觀摩左左村戰鬥的情景,那股自遠處而來的不寒而慄又回到了身上。
椎名把空了的茶杯仍在草地上,隨後說道:“那你應該也能感覺到吧,那種不舒服的氣氛,就算我的血統淡薄,也能感覺出來啊。這就是滅卻師為何要和它們戰鬥的根源。”
“……原來如此。”
“哈哈,你應該是不會相信我說的話吧,”被說中了的托比亞斯,盯著視線裡面一點漂浮著的綠色點看著,似乎是隻鳥、或是昆蟲,“畢竟,讓你放棄十二年來所建立的價值觀和世界觀,也太困難了點。”
“你真的認為你是正確的嗎?椎名先生。”
“我只是站在旁觀者的角度,以自己的鏡頭來講話罷了……我的眼睛就是鏡頭,傳達所看到的東西,原封不動地還原。因為椎名這一族必須要做到立場上的絕對中立。”
“……啊啊。”托比亞斯歎了口氣,“可是,脫離滅卻師只是這個原因的話……”
“也太淺薄了點?”椎名問道。
“嗯……”
“你知道你父母的事情吧。”
被這麼問到,托比亞斯打了個激靈,他常常聽到別人充滿惡意的、或是好奇地問起這件事,原來椎名也……
“你不用在意。我對你父母是親兄妹也好、是表兄妹也罷,或者是陌生人……我都不在乎,只是覺得周圍的傢伙們,對你父母身上發生的事情,也反應得太過了點。明明幾代以前也有過因為金錢或是其他關係,無法迎娶外界的名門純血滅卻師,而在族內通婚,沒想到到了戰後,卻成了這個樣子……哈哈,也是很可笑呢,明明之前的所作所為,都和配種沒什麼兩樣,包括你爺爺沒有任何感情,只是為了優秀的後代而去迎娶國外的純血滅卻師來壯大櫻庭一族,周圍的人都在支持,到了你父母那件事……他們卻表現得天塌了一樣。真是的,明明做的事情要惡劣得更多倍,把人當成種豬也不在乎的傢伙,也敢用道德去綁架亂倫常的傢伙……不過彼此彼此罷了,或許還要更惡劣些呢。”
“……啊。”托比亞斯輕聲答道,他聽到耳畔有微風吹動起庭院裡的枝葉。正如那人所說,縱使這言語如同刀鋒一般刺入心臟,他也仍保持著十二年來的想法。
畢竟,要相信自己不是正義的,對一個十二歲的少年來說也太難了。
“什麼才是正義啊……”他喃喃著道,椎名並沒有回答。對托比亞斯而言,他的正義大概就是家人都能獲得幸福吧。
那麼既然如此,所有人的幸福,就是普世價值觀的正義。
三
“到了這個年紀,也該出去上課結識同年的朋友比較好。”
被椎名這麼說了,父母便給托比亞斯安排了補習班,那也是他十四歲的時候第一次接觸那麼多人,周圍都是同齡的孩子,他拘謹地坐在席上,第一次意識到世界上原來有這麼多與自己不同的人。大概是因為自己的樣貌很顯眼的關係吧,儘管看不見,卻能意識到別人刺眼的視線。
總之……先專心看看教案吧。托比亞斯低下頭,在那些人小聲的議論中低下頭去,萬幸的是大家很快就轉移了話題。隨後,他意識到有什麼人踏門而入。
那是與自己相似的某個人,彼此間能感覺到對方身上靈子的波動。托比亞斯抬起頭來。
“啊。”“啊。”
——對方的名字名叫林飛鐮,這是在日後對方帶著自己逃課時,托比亞斯知道的。原本就不怎麼喜歡人群的托比亞斯,對此事並無過多的負罪感,而林似乎是其中的老手,無論是翻墻還是躲人,都做得很快。相比之下,托比亞斯就略顯笨拙了。
“請等我一下……”托比亞斯撐著墻體,頭一次為自己那只能看到狹窄的視野而感到不安,對方催促著他快點跳下來,他試著跳下來,卻因為左腿沒有調好,而擦破了膝蓋。接著他跟在對方的身後,“請問您要做什麼啊?”
“嗯?去狩獵虛唄。”
“哎……以前沒做過呢,要拿武器嗎。”托比亞斯向著那人模糊的黑影問道,對方無聲地回過頭來拍了拍他的肩膀,緩了一會兒才再開口。
“你姓什麼?”
“敝姓櫻庭……”托比亞斯回答道,對方聞言再度沉默,然後又拍了拍他的肩,“在下是第一次做那種事……抱歉。”
“有帶武器嗎?”
“有……是靈魂劃破之物。”托比亞斯答道,林這才好像稍微放心了點。
“那等虛找來我們之後,我用弓把它殺死,那時候若是它還留著口氣的話,你來最後一擊?如何。”林晃動著十字架,問托比亞斯,後者聽後拘謹地點了點頭。說是如此,但是少年控制不好力道,放出去的箭矢總能一擊擊殺,弱小的虛很快便被殺死了。於是場面便變成托比亞斯跟在林身後,在結界之外,虛似乎會被滅卻師高濃度的靈力吸引,而自主找上門來——托比亞斯一整年都如此度過了,直到現世爆發了介於虛、死神和滅卻師之間的戰爭。
大概是永遠沒法忘掉那天的景象了吧。
原本只是與林在補習班外數十米的街道上尋找著虛,卻在那時突然感受到了之前從未意識到的龐大靈子波動,靈子好像洪流似的,在空氣中湧動著,在那裡他意識到,那是數十、數百乃至數千的死神、虛、滅卻師所發出的。
這是他從未遇過的場面。
“啊,請問怎麼了嗎?”托比亞斯問林,對方只是支支吾吾,他意識到空氣中多了他曾在負傷者身上聞過的氣味,他踩在什麼滑膩、粘稠的東西上。血與肉塊洩了一地,接下來是最為糟糕的死的氣味,其惡臭混合著陰水溝和血味兒。父母保護得很好的托比亞斯,是頭一次問道那種味道,其劇烈地攪動起他的胃,全身上下所有的細胞,似乎都在抗拒著面前發生的事。
“嘔……”他忍了會兒,隨後終於受不了,在尸體旁邊吐了出來。等他緩過神來時,林已經不見了蹤影,大概在剛才離開了吧。他在旁邊佔了會兒,忽然明白過來那尸體背後,也都有著各自的故事,也有各自的家庭,會有人在某處等待著他們回去。肯定不會有人想死吧……他掐了掐自己的掌心,好讓自己不要產生那樣的感覺。
然後在那片戰場上,他感受到另一種奇特的靈子流動。那無疑是滅卻師從外界提取,再散發出來的——只是那人,身為滅卻師的“器”,比他所見過的任何一位都要龐大上許多。托比亞斯在感到怪異的同時,又覺得他似乎很懷念那人。
血管裡的液體開始奔騰,似乎是在為那個無上的存在而沸騰,本能的,他意識到那個人是他必須臣服的對象,接著是什麼奇特的、撥弄心弦的聲響。恍惚間他又回過神來,踩在尸體上跑了起來。
到底是怎麼回事啊。他克制著那種反胃的感覺,向著沒有尸體的方向跑去,在路上被什麼奇怪的東西絆倒了,但他仍跌跌撞撞地向著前方走去,直到跑不動為止,眼前的色塊一片漆黑。
“啊……”他坐下來,瑟縮在那裡,等待著有人來找他,手中的劃破靈魂之物好像什麼用都沒有,明明在比試裡操練了千遍,卻連保全自身都做不到。意識到這點後,他展開了那東西,淡藍色的靈子不知緣何在視野中意外的清晰。
與其說是武器,不知道為何對他來說更接近“玩物”。大概,這便是沒有接觸過死亡的他,所能想到的有限的事吧。
不知緣何,他終於意識到了自己過往的天真。明明不過是接觸尸體而已,就已經有了這樣的念頭。
“真奇怪呢。”他想著,然後合上了眼,恍惚間他聽見左左村叫他的聲音。
四
整理好衣衫之後,托比亞斯向家人告了別,隨後走出了庭院。加入無形帝國,大概是他能為這個家族所做的唯一的事情吧。大概是目不能視的緣故,路程漫長得無以復加,等到了目的地後,輕輕吻過了十字架,才安心走進了無形帝國的王殿。
不能忘記禮儀,不可忘記身為臣下,再默念遍父母告知他的事情,他抬起頭來看向王座上的人影。
王,似乎又兩位,視線裡,能看到紅色的地毯和金黃色的王座上,一黑一白兩個人影。
“請問……是……無形帝國的滅卻王嗎。”他小聲問道,王發出銀鈴般的笑聲,從聲音上聽來,不過是比他妹妹櫻子還要小上幾歲的孩子罷了。但是與之相對的,另一件讓他無法忽視的東西,王身上那令他無法忽視的“器”。
“正是。”“我的子嗣!”
黑白之王一應一和,語句裡聽不出絲毫地不協調,如果不是聲音的語氣有微妙的不同,大概會以為是一個人吧。
“在下是櫻庭,為滅卻師的正義而來,還請您多指教。”
“正義。”“正義呢。”
“在下認為……正義便是所有人得到幸福。”托比亞斯繼續說了下去。
“聽啊,白,他這麼說耶!”黑色的王好像聽到了什麼非常有趣的事情,用了興高采烈的語氣。
這是說明自己的價值觀被理解了嗎?托比亞斯心生困惑,那兩位好像抱著有些許興趣的樣子繼續說了下去:“但是,在下一直有疑問,那便是如果為了保證大多數凡俗者的幸福,那麼少數處於塔頂的人,應該做出犧牲嗎?還是大多數者為了那絕對的少數,而放棄自我的存在?”
王者聽完了這句話,只是輕輕笑了笑,嘴中所答的,卻是另一件事:“櫻庭,疾病讓你頗為受苦吧。”
“……是。”托比亞斯生來便是弱視,加之純白色的外貌,多數的出門時間,都是在別人的視線和小聲議論聲中度過的。
“能看出來,你的父母一定很愛你。”“感覺是個好孩子呢!”
……好孩子嗎。不知為何托比亞斯總覺得這個評價讓他感到怪異,這樣的自己是好孩子嗎……或說,父母真的是愛著自己的嗎?他們是真的沒有片刻,為了想贖罪的心情,而做出那些溺愛似的舉動嗎?自己除了想幫忙的那份心情,也有想要讓他們不要再想那麼多的意圖,才會來無形帝國吧。王的話語明明毫無棱角,一塊被磨得平平的石頭一樣,卻不知為何刺痛了他的心。但同時,他又意識到眼前的王,有著一種奇特的天真的殘忍。
不知為何,好像能理解椎名那時所說的話了。這種奇異的天真,似乎很吸引他的心。
“那麼……屬下……”他輕聲說道,卻被王座上的雙子制止了。
“成為星十字的一員,要和我喝下交杯酒。”
“……是。”托比亞斯點了點頭,走向那王座,在模糊的色塊裡,滅卻王遞給他一個鮮紅的酒杯,杯中瓊漿散發著甘甜的味道,他一口氣喝了下去。
不知為何,視野清晰了起來。有生以來第一次,托比亞斯能看清眼前的事物了。
“……這是。”他遲疑地抬起頭,看向眼前的少女們,白色的少女有著捲曲的雙馬尾,黑色的少女則是男孩子般的短髮,不知為何,她們那身影好像使他產生了印隨的心理,約莫是因為人生中第一次能清晰看見的臉龐,托比亞斯為那種天真的美產生了憧憬之心。
“剛才給你的酒杯中,有我的血液。”“所以櫻庭將會獲得身為星十字團員的字母哦!也就是能夠戰鬥的能力!”
“……感激不盡。”他單膝跪下行禮,謝過滅卻的王,“在下該如何報答……”
“既然你已喝下了我的血,那麼便在戰場上戰鬥吧。”“作為報答,為我拋下熱血哦!”
他連忙將手放在心臟上,向那二位一體的王宣誓,初次得到視覺的托比亞斯,在謝過王之後,便快步走出了殿堂。陽光亮得人感到雙眼發痛,能看到浮雲遮掩著太陽,不知道為什麼光線能穿透雲層,把原本沒什麼色彩的地方照得好像教堂。托比亞斯再看向身後的宮殿,雖然在此之前從未見識過建築的美,他卻知覺無形帝國的王殿便是美的。他看了好一會兒外面的景色,才感到心臟那處狂亂的跳動停歇下來。
在他身後的王殿裡,少女模樣的王者發出一聲輕輕的嘲笑,這是他未能所聽所見的。
“吶,白,櫻庭那孩子還真無趣啊。”黑色的王者端詳著空了的酒杯,隨後隨意地將其摔在地上,杯底殘留的液體肆意地濺撒於紅地毯,王絲毫不在意這幅景象,只是任著自己的性子做出這些事。
白色的王者聞言笑了笑:“是個愚蠢的孩子。”
“竟然覺得會有所有人都能獲得幸福的景象,應該說真是沒見過地獄的天真啊。”黑色的王者說著。
“無趣。”“真是太無趣了啊。”兩人異口同聲地說著。
END
似乎也不是什麼人都能在商場裡迷路的。
“啊……請問……您知道這個地方該怎麼走嗎……”托比亞斯只要能看見人,就會上去問路。不只是因為問法的問題,還是自己的相貌過於可怖,無論問到誰,得來的都只是搖頭或是一句簡短的我不知道。他輕輕拍向一個栗色頭髮行人的肩,然後向對方問道:“請問您知道怎麼去車站嗎……”
對方聽到這話後愣了愣,隨後指了指商場裡的商標,隨後指了指商場上懸掛著的牌子,往有那個標記的方向走就是了。
“原來如此,實在是太感謝您了。”他鞠了一躬,小雞啄米般不停地道謝,等那人離開了才起身,向著懸牌上的標記走去,隨後,又在車站裡研究了一番怎麼換零錢,才終於上了車。
列車的車輪咬合著鐵軌,發出咯噔咯噔的聲響,他走上去,看向窗外的風景。因車速的緣故,植物的綠色模糊成一片


少女从天台上跃下之后。
红色的鲜花飞散开来了。
-
第四章 亡者幻境
又一次。
又一次见到了。
那个“幻境”。
-
妇女的尖叫声在房间里砰然炸开,一声一声撞击着耳膜,被掩盖的是玻璃互相碰撞的回响,看不清脸庞的男人狞笑着,举起了手——
“求求你!放过孩子吧。”
-
一切又重归于寂静。
-
不是第一次逃课,但如此一般近乎逃掉一整天的课实在少见。
在逃避什么呢。
这么想着,少女抬起头,仰视面前高大的书架,一排一排似乎要直通天穹的书架矗立在这一方小小的世界里。
封闭的屋顶,浓稠的空气缓慢的沉降下来,压得人透不过气来。
不要再浪费时间了。
这么想着,少女低下头,恍然间却看见了躲藏在柜子底下的、小小的眼珠正在盯着自己看。
真恐怖呢。
这么想着,少女移开了视线,寻找起自己需要的书本。
-
手指依次扫过书架上的书本,最终停留在一本《圣经》上,小心翼翼的抽出来,打开后却看到里夹着一个书签,上面写着“最靠里的书架。”
在书架里面找到了一本《About Magic》,里面的内容都是一些魔法的种类和介绍,其中的“精神系”被用记号笔涂着。“……精神系魔法是比较高深的魔法之一,使用该魔法的人可建立精神结界,让魔法范围内的所有人进入结界并不被察觉。也可精神控制等。”
真是奇怪的话语。
少女歪了歪头,最终决定还是把书本放回去,继续找自己需要的资料。
走到某一处时意外看到一扇门。
或许里面会有自己要的资料也说不定。
少女伸出手去想要打开门,门上的纸条上却写着“禁止进入。”转了转门把也是锁着的。
回过身,却看见其中一个书架后面刻着什么。好像是不认识的文字。
-
陷入了怪圈之中呢。
虽然自己一直试图躲避这样的事情,但似乎越来越无可避免了。
这么想着的少女,打开了手中绣着金色玫瑰的笔记本。
-
今日的故事是犹太之死。
-------
大家好这里是不知道自己在写什么鬼的中之人。
随手保命。
标题有毒。

本月考试TAG“第三次考试【ELF UTAPRI】”与合宿专用的考试TAG“海边合宿【夏之歌】”已经添加,可以开始投稿。
合宿考试TAG、普通考试TAG可以与交流TAG共用,合宿考试的有效打卡时间至15日24点截止,之后可以继续使用该TAG,但期间外的投稿不能算作打卡,还请各位同学谅解。
普通考试的打卡时间照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