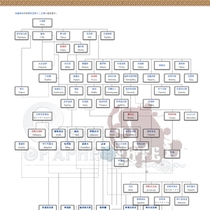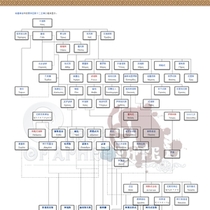【读前注意】
这里的科普是便于参加企划的太太了解神话背景,
不做过多扩展,以下内容摘取自维基百科。
=============================================================
【第十回:特洛伊人的胜利】
翌晨,宙斯召集众神警告他们今天不可帮任何一面,他乘着马车来到伊达山的山顶观战,战争一直持续到中午,此时宙斯拿出天秤,特洛伊人的一边高举,而希腊军一面则倾到地面,宙斯令雷声作响,希腊军全体撤退,只有涅斯托尔一人留在战场,此时帕里斯射伤了他的马的眼睛,马立即变得不受控制,赫克托尔赶到举剑要杀涅斯托尔,刚好狄奥墨得斯赶到把涅斯托尔拉上自己的战车,便去迎战赫克托尔,他刺中了赫克托尔的驭者,马车不受控制,英雄阿尔克普托勒摩斯登上了战车代替驭者,宙斯以闪电投向马前,马吓得乱窜,涅斯托尔劝狄奥墨得斯离开战场,因为宙斯不想见到他的胜利,狄奥墨得斯听从,特洛伊军乘胜追击,赫克托尔对狄奥墨得斯拼命嘲笑,狄奥墨得斯三次想回到战场却都被雷电止住,涅斯托尔明白今天胜利将归特洛伊人,而赫拉请求波赛冬援助希腊军,波赛冬拒绝了她。
战斗直逼至希腊军的围墙边,阿伽门农请求宙斯帮助,此时宙斯起了怜悯之心,带来了吉兆,一只巨鹰将一只鹿攫起并投在宙斯的神坛上面,希腊人士气大增,当中以狄奥墨得斯最为兴奋杀敌,另外,透克罗斯也杀死了普里阿摩斯的儿子戈尔古提翁及阿尔克普托勒摩斯,赫克托尔大怒用巨石打伤了他的肩,幸好大埃阿斯来到掩护他才幸免于难。特洛伊人由围墙攻至希腊军的船边,尽管女神们想帮助希腊军,但宙斯却派使者伊里斯阻止她们并威胁要动怒,女神们都止住了,宙斯对赫拉说在阿伽门农主动向阿基里斯修好前,特洛伊人还要得胜。入夜后,赫克托尔率军在城外扎营,务求明天一举击退希腊军。
【第十一回:赫克托尔之死】
希腊第一勇士阿基里斯由于与统帅阿伽门农的个人矛盾而对战事袖手旁观后,希腊军中无人能敌赫克特,屡战屡败。此后,阿基里斯的挚友帕特罗克洛斯穿上阿基里斯的盔甲假装出战,但是被赫克特杀死。阿基里斯勃然大怒,重新参战,指名要与赫克特决斗。
赫克特在决斗中被阿基里斯杀死,他的尸体也被阿基里斯拖在战车后面绕城,不让特洛伊人安葬以泄其愤。赫克特的父亲普里阿摩斯王冒险亲自拜访阿基里斯,才说服他把送还赫克特的尸体。虽然历经数日,但是尸体由于众神的保护,却完好无损。
(《伊利亚特》以赫克托尔的葬礼和对他的悼念而结束。)
【读前注意】
这里的科普是便于参加企划的太太了解神话背景,
不做过多扩展,以下内容摘取自维基百科。
=============================================================
【第七回:阿基里斯和阿伽门侬的争执】
终于到了围城的第十年,阿波罗祭司克律塞斯来到希腊军中,恳求阿伽门侬能释放其女克律塞伊斯并愿支付的大笔的赎金,然而贪恋克律塞伊斯美色的阿伽门侬怎么可能轻易放人,于是他骂走了克律塞斯。带不回爱女的克律塞斯难过之余则向阿波罗控诉,于是阿波罗降瘟疫予希腊联军作天谴。十日后联军将领招开会议,会议上阿基里斯要求卡尔卡斯揭示神为什么发怒,若其肯坦言不讳则必保其周全。卡尔卡斯闻之即和盘托出并要求阿伽门侬归还克律塞伊斯。此时自知理亏的阿伽门侬面对众人质疑的声浪虽怒不可遏,但众目睽睽下也只得遵从。然不堪蒙受琵琶别抱之痛的他立即要求在场的阿基里斯、奥德修斯及大埃阿斯等三人把得到的战利拿出来补贴。面对此等无礼的索求,义愤填膺的阿基里斯亦扬言将即刻退出战役返乡,而不甘示弱的阿伽门侬则更叫嚣将没入阿基里斯的女奴布里塞伊斯作为恫吓。拿挚爱作威胁,此时阿基里斯真的被彻底激怒了!说时迟、那时快,被激起杀意的阿基里斯拔出利剑,欲斩向早已恼羞成怒的阿伽门侬,而在一旁监看的雅典娜则见状即刻上前阻止,只因两个英雄对赫拉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更何况战役已达十寒暑,在此般胶着的战况下不能再为任何无谓之事而内耗自损、折员损将了。而为了安抚及稳定阿基里斯的情绪,雅典娜则预先告知阿基里斯,阿伽门侬不久后将会为自己的狂妄而付出惨痛的代价。虽然阿基里斯仍咽不下这口怨气,但冲着雅典娜的面子也只能带着满腹的怨气,悻悻然地与挚友帕特罗克洛斯一同离开并回到营帐。而奥德修斯则依阿波罗神谕,将克律塞伊斯带往埃提翁城将克律塞斯送回。
然而,正当奥德修斯离开之时,颜面尽丧又怒火攻心的阿伽门侬则立刻派传令官塔尔提比奥斯及欧律巴忒斯两人拿下阿基里斯的女奴布里塞伊斯作为报复,来抵偿其失去克律塞伊斯的忿恨。阿基里斯深知这都是阿伽门侬的主意,对方竟如此张狂,但为了不起太大纠纷使赫拉为难,也只能先让他们将心爱的布里塞伊斯带走了。于是悲痛欲绝阿基里斯望向在大海的母亲忒提斯哭诉,忒提斯答应会向宙斯禀报阿伽门侬的无礼,并央求能降厄于他。然而,母子两人岂知宙斯早已去了埃塞俄比亚人那儿赴宴了,最快也要十二天后才会回来。而也就从这天起,阿基里斯就一直闷在帐篷,不参与任何战事,也因此让早陷入泥淖联军战况更加地雪上加霜。终于挨到了第十二天,此时宙斯已回到了奥林巴斯山,忒提斯乞求宙斯在阿伽门侬未向阿基里斯道歉前,让特洛伊人先取得胜利。尽管宙斯知道此举势必引发赫拉不满,但念在忒提斯在过去诸神欲推翻宙斯之时,曾唤百臂巨人布里阿瑞奥斯帮过他,便如其所愿扰乱希腊联军作战。
宙斯于是派睡神许普诺斯给阿伽门侬托假梦,让他以为神预兆他破城在即。而是阿伽门侬在梦醒后立即召集所有的将士英雄,然后在广场上向大家宣布将要撤兵,借此试探大家反应以探知众人意欲。此时,众人之返乡之情溢于言表,欣喜若狂地将船推回到海边。然而赫拉担心阿伽门侬会弄巧成拙,即刻派雅典娜严正地告诉奥德修斯阻止众人,奥德修斯立时取了阿伽门侬那象征最高权力的权杖并命令众人回到广场,最后大家都也只能鱼贯般的回到了广场,欢喜的喧闹又回复到日常的平静。而此时只有忒尔西忒斯一人仍不断叫嚣,他勇敢地站出来反对国王,他尤其反对阿伽门侬及阿基里斯,在广场上他辱骂阿伽门侬自私没胆。奥德修斯走到他的面前警告他住口,并用权杖痛殴了忒尔西忒斯,奥德修斯此举重新鼓舞希腊人,于是军队在向宙斯献祭后向特洛伊城进攻。然而,他们却不知道宙斯早已拒绝了他们的献祭。
【第八回:墨涅拉奥斯和帕里斯的决斗】
众神的使者伊里斯变成普里阿摩斯儿子波吕忒斯的样子向特洛伊人通报希腊军的迫近,特洛伊军列队走出了城,两军对峙时帕里斯从特洛伊军走出来,示意跟墨涅拉奥斯单挑,墨涅拉奥斯亢奋起来,他终于可以亲手报仇了。帕里斯看到墨涅拉奥斯亢奋的样子,怕得缩在朋友的旁边,赫克托尔就责骂他是个胆小鬼,并指责他是战争的罪魁祸首,帕里斯硬著头皮迎战,于是两军都停息静气,此时墨涅拉奥斯要求普里阿摩斯见证这场决斗,同时伊里斯女神化作普里阿摩斯女儿拉奥狄克的样子,叫海伦登上斯开亚门的塔楼观战,普里阿摩斯与阿伽门侬、奥德修斯等向众神作了献祭,立誓遵守条约后就回到塔楼上,他不忍近距离看到任一方的死亡。
决斗开始时由帕里斯先向墨涅拉奥斯掷矛,他的长矛中了墨涅拉奥斯的盾牌却没有穿过它,当墨涅拉奥斯掷矛时,矛穿过了帕里斯的盾牌及铠甲,帕里斯反应快才跳到一边才得救了。墨涅拉奥斯以剑作攻击,但由于用力太猛剑断为四节,墨涅拉奥斯便徒手抓着帕里斯,把帕里斯拖往希腊军中,帕里斯透不过气来,此时阿芙罗狄忒女神割断了帕里斯的头盔带令墨涅拉奥斯手中只剩下一个头盔,并用浓雾遮住墨涅拉奥斯,伺机将帕里斯摄回城中。墨涅拉奥斯大怒,阿伽门侬宣布墨涅拉奥斯的胜利,要求特洛伊军交纳贡赋,却得不到回应。
这时,赫拉要求宙斯派雅典娜去挑动特洛伊人毁约,宙斯不愿地顺从,雅典娜化身为安忒诺耳的儿子拉奥多科斯走到潘达罗斯面前,说服他用箭射死墨涅拉奥斯,潘得罗斯发箭,雅典娜却刻意让箭只射进墨涅拉奥斯的肌肤,并无大碍,希腊军的医生玛卡翁在伤口上撒了药粉。随后,阿伽门农检阅将士,发布命令,两军开始鏖战,随后死相枕藉,战场上尸横遍野。指挥希腊军的是雅典娜,而指挥特洛伊军的却是战神阿瑞斯,希腊人势如破竹,阿波罗告诉特洛伊人阿基里斯并不在希腊军中,而雅典娜则特别加助狄奥墨得斯力量,潘达罗斯见状向狄奥墨得斯发箭,箭虽中却没伤了狄奥墨得斯性命,潘达罗斯以为狄奥墨得斯死了,却不料狄奥墨得斯已叫另一英雄斯忒涅洛斯叫到跟前拔箭,并求雅典娜替他报仇。雅典娜赋予他力气,让他在军中杀伤阿芙罗狄忒女神。特洛伊的英雄、阿芙罗狄忒之子埃涅阿斯叫潘达罗斯一同击退狄奥墨得斯。狄奥墨得斯掷矛刺死潘达罗斯,埃涅阿斯保护潘达罗斯尸首,狄奥墨得斯向埃阿涅斯掷大石,幸得阿芙罗狄忒保护了他。狄奥墨得斯追上了女神并刺伤了她,阿芙罗狄忒退走遗下埃阿涅斯,狄奥墨得斯再向埃阿涅斯猛扑,三次都被阿波罗挡回,第四次进攻时被阿波罗喝退。
阿波罗把埃阿涅斯带到他在特洛伊的神庙里,而造了一个假替身放在战场上,阿波罗叫战神阿瑞斯制服狄奥墨得斯,于是阿瑞斯化身色雷斯英雄阿卡玛斯跑去鼓舞特洛伊人,而埃阿斯兄弟、奥德修斯及狄奥墨得斯则在指挥希腊人,然而希腊军却被杀得连连后退,战斗中,希腊军的特勒波勒摩斯被宙斯儿子萨尔佩冬用长矛刺死,萨尔佩冬也因腰伤而被拖走了。赫拉和雅典娜见大事不妙,雅典娜便变身为英雄斯滕托尔鼓舞希腊人,又对狄奥墨得斯说不用怕对神作出攻击,并劝他攻击阿瑞斯。雅典娜趁阿瑞斯杀死英雄佩里法斯之时,令阿瑞斯看不到她而和狄奥墨得斯两人走到他附近,对阿瑞斯作出了攻击,阿瑞斯受伤后走回宙斯处,宙斯派神医派翁治好了阿瑞斯,并说服了阿瑞斯重回战场。
【第九回:赫克托尔决战大埃阿斯】
赫克托尔回到城中,匆忙走向皇宫,在宫中,他碰到自己的母亲赫库芭,他叫母亲快去召集特洛伊的妇女们向雅典娜作献祭以制止发了狂的狄奥墨得斯,得到赫库芭答应后,他又去找帕里斯,他见帕里斯只在检查自己的武器时就谴责他一点也不紧张,美丽的海伦也同样在谴责他,帕里斯说自己正准备战斗,赫克托尔没多留片刻,就去找妻子安得罗玛克,在城门上他找到了妻子及儿子阿斯提阿那克斯.安得罗玛克知道自己的丈夫将命丧战场,劝赫克托尔别上战场,赫克托尔不许又从斯开亚门那里出去赴战,赶上了刚上战场的帕里斯,他们的出现令特洛伊人士气大振,他们联同格劳科斯杀死了希腊的许多英雄,雅典娜欲帮助希腊人,刚撞上帮助特洛伊人的太阳神阿波罗,阿波罗只答应休战,两位神决定为了止战,必须怂恿赫克托尔向希腊最著名的英雄单挑,赫克托尔的兄弟赫勒诺斯感应到神的意思,就叫赫克托尔如此地做,战场上两军都暂且停战,只有赫克托尔叫阵,希腊军无人敢应战,墨涅拉奥斯非常愤怒,宁愿自己作战,阿伽门侬止住了他,因为单挑赫克托尔是连阿基里斯也没必胜信心的事,长者涅斯托尔教训希腊的英雄,这时,有九个人愿意作单挑,分别是阿伽门侬、狄奥墨得斯、大埃阿斯、小埃阿斯、伊多墨纽斯、墨里奥涅斯、欧律皮洛斯、托阿斯及奥德修斯,大埃阿斯被抽中出战,他非常高兴走了出来,此时赫克托尔也有点胆怯。
战斗开始时,赫克托尔先投枪,被大埃阿斯的盾牌挡住了,大埃阿斯投枪穿过了赫克托尔的盾牌及护甲,可是矛尖却偏了一边才救了赫克托尔一命,两位英雄拾枪再战,大埃阿斯又一次刺穿了赫克托尔的盾牌,并刺伤了他的脖,之后大埃阿斯拾起大石投向赫克托尔,这次伤了赫克托尔的脚,阿波罗迅速将他抬起他,这时两位英雄就要进行埋身战了,然而千钧一发间,传令官来到制止了战事,以避免两败俱伤,两人识英雄重英雄,互相交换了腰带以作纪念,特洛伊人为赫克托尔未受大碍而高兴,而希腊军也看到大埃阿斯的强大而鼓舞,双方同意休战,入夜后双方进行了各自的会议,尽管特洛伊军向希腊军提出交还财宝及额外的珠宝,但希腊军却因帕里斯不肯交还海伦而拒绝停火。

【读前注意】
这里的科普是便于参加企划的太太了解神话背景,
不做过多扩展,以下内容摘取自维基百科。
=============================================================
【第四回:召集英雄】
当帕里斯一登船,众神就派使者 彩虹女神伊里斯到克里特岛找墨涅拉奥斯,墨涅拉奥斯回到斯巴达后,见到财宝被劫走,海伦又离他而去后,他怒火万丈,并找他的哥哥阿伽门侬,阿伽门侬建议召集当年起誓的英雄一起进攻特洛伊,墨涅拉奥斯接受劝告,先找到年长的皮洛斯国王涅斯托尔,涅斯托尔非常生气决定亲自出征,并且带上自己两个儿子特拉叙墨得斯及安提洛科斯。其他征讨的还包括阿尔戈斯国王狄奥墨得斯、欧波亚国王帕拉墨得斯、雅典国王得摩丰、克里特岛国王伊多墨纽斯、墨利波亚国王菲洛克忒忒斯,他拥有赫拉克勒斯的弓箭,预言者预言没有这些箭,特洛伊是攻不破的。另外还有萨拉弥斯国王大埃阿斯及罗克里斯英雄奥伊琉斯之子小埃阿斯,不过尚欠两位国王未到。
伊塔卡国王奥德修斯以机智闻名,他刚与妻子佩湿洛佩结婚不久,诞下儿子忒勒玛科斯,因此不愿同行,当奥德修斯得知墨涅拉奥斯、阿伽门侬、涅斯托尔及帕拉墨得斯来到伊塔卡时,他就装疯把牛套套在犁上耕田,又把盐撒到田里,帕拉墨得斯看出他的假扮,就把他的儿子放在田上,果然奥德修斯就在孩子前停了下来,奥德修斯不得不承认自己是假扮,只得履行当年的承诺,从这时起奥德修斯便恨帕拉墨得斯,并决心要报复。
另一位未到的国王色萨利国王阿基里斯是色萨利国王佩琉斯与海洋女神忒提斯的儿子。忒提斯知道阿基里斯会死于特洛伊,当阿基里斯还是婴儿时,他就把他倒提脚肿浸于冥河斯提克斯,令他刀枪不入,佩琉斯又将他交给喀戎教导,致使他能用各种兵器,当墨涅拉奥斯要出征的消息传到忒提斯耳中时,她便把阿基里斯藏在斯库罗斯岛的吕科墨得斯的宫殿中,但是预言家卡尔卡斯泄露了他的行踪,并告知他们阿基里斯身穿女服,不易辨认,奥德修斯和狄奥墨得斯就假扮商人来到宫殿,把货物放在殿前,公主们都爱看珠宝首饰,只有阿基里斯在看武器,此时传来剑击声,其实这是狄奥墨得斯在殿外发出的,阿基里斯以为有敌人立时拿武器杀敌,就这样他就被认了出来,阿基里斯高兴能参与战事,他还把两个朋友智者福尼克斯及帕特罗克洛斯带去战场。佩琉斯知命运如此,就把结婚时火神赫淮斯托斯所铸的铠甲、海皇波塞冬送的神马及人马之王喀戎送的矛都给阿基里斯。
【第五回:前往特洛伊】
英雄们聚集在奥利斯港湾,希腊联合远征军人数有十万人,船数一千一百八十六。出发前大家都在岸边祭坛作献祭,忽然间祭坛下面爬出了一条血红的怪蛇,它弯曲成环状爬上了树,爬到树最高处的一个鸟巢,吃了一只雌鸟和八只雏鸟,然后变成一块石头。众人大惑,预言家 卡尔卡斯给他们揭示了意思,他说英雄们要围城九年,只有在第十年才能攻下特洛伊,众人大喜,向着亚细亚出发。
开航不久,希腊人在密细亚靠岸,这里由赫拉克勒斯儿子忒勒福斯统治,希腊人以为这里就是特洛伊就开始攻城,阿基里斯令忒勒福斯逃回城中,清晨时希腊人在收拾尸体时才知他们打的是同盟者而非特洛伊人,希腊人与忒勒福斯签订和约,由于忒勒福斯是普里阿摩斯的女婿,他不愿出征打自己的岳父,却承诺会帮助希腊人。
离开米西亚海岸后,英雄们遇到可怕的风暴,他们迷失了方向,最后又回到出发港奥利斯,第一次行动失败,他们将自己的船都拖上岸,在岸上组成一个很大的军营,许多英雄都回家去,连统帅阿伽门侬也离开奥利斯,他们无法得知去特洛伊的路,只有忒勒福斯才知道,可是不久前希腊人才刚与他战斗,在战斗中,阿基里斯伤了他的大腿,伤口痛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忒勒福斯去德尔菲问阿波罗如何可治好创伤,女祭司皮提亚说只有阿伽门侬才可治好他,他就打扮成乞丐去见阿伽门侬,他见到阿伽门侬的妻子克吕泰涅斯特拉,克吕滕涅斯特拉向忒勒福斯建议,当阿伽门侬进来时,可以从摇篮抱起阿伽门侬的儿子俄瑞斯忒斯,威胁他如果不治好其伤就把把小孩撞得粉碎,果然这令阿伽门侬非常害怕并同意治好他,因为他也知道只有忒勒福斯可以指出去特洛伊的路,阿伽门侬派人找阿基里斯,阿基里斯却不知如何治好忒勒福斯的伤,奥德修斯告诉阿基里斯解药就是矛尖上的铁锈,撒在忒勒福斯的伤口上果然快速愈合,于是忒勒福斯就答应带领众人往特洛伊。
可是海面上仍一直刮着逆风,原来是女神阿耳忒弥斯派来的,因为阿伽门侬曾杀死女神的神鹿令女神非常生气。英雄们只得呆等风停,卡尔卡斯告诉大家只有把阿伽门侬的女儿伊菲革涅亚作祭品献给女神才会饶恕希腊人,阿伽门侬得知后宁愿放弃出征,墨涅拉奥斯再三请求,阿伽门侬终让步,并派使者急步前往迈锡尼,隐瞒妻子说女儿要与阿基里斯订婚而要带女儿来军营,当第一个使者离开军营后,阿伽门侬又后悔派第二个使者告诉其妻真相,然而第二个使者被墨涅拉奥斯截住了,并谴责阿伽门侬的背叛,两人争吵间克吕滕涅斯特拉及伊菲格涅娅已到。
阿伽门侬悲恸不已,却装得平静地去看妻女,伊菲格涅娅看出父亲有难言之隐,阿伽门侬出去想找卡尔卡斯有没有其他的方法,阿伽门侬一出去,阿基里斯就进来要求出发或者放他们回家,克吕滕涅斯特拉祝贺这位女儿的未婚夫,阿基里斯不明所以,此时第二个送信的使者向她和盘托出真相,克吕滕涅斯特拉大哭要求阿基里斯保护她的女儿,阿基里斯答允。军营士兵知道后开始骚动,阿伽门侬无奈,奥德修斯率领士兵们直扑阿伽门侬的帐篷,而阿基里斯决定誓死保护伊菲格涅娅。
剑拔弩张之际,伊菲格涅娅站出来请求自我献祭并说服阿基里斯不要保护她,阿基里斯还是服从了她的意志,伊菲格涅娅走到祭坛前,传令官塔尔提比奥斯命所有人保持沉默,卡尔卡斯拿出献祭用的宝刀,高喊阿尔忒弥斯女神的名字,祈求一路顺风,当刀触及少女之焰,天上出现奇迹,阿尔忒弥斯把伊菲格涅娅摄走,刀所触及的只是一只赤牝鹿,大家都欣喜女神的慈悲,因为女神把伊菲格涅娅带到陶里斯的欧克辛斯蓬托斯的海岸边的女神庙作祭召,就在此时海上已刮起顺风,全体士兵整装待发。
【第六回:围城前九年】
希腊人再次出发,沿途风平浪静,预言家告诉他们必须在莱姆诺斯岛旁的克律塞岛上对女神克律塞斯作献祭才能攻城顺利,菲洛克忒忒斯知道这个祭坛的位置,领袖们在岛上跟着菲洛克忒忒斯来到祭坛,此时一条大蛇窜出并咬了菲洛克忒忒斯的脚,蛇毒令菲洛克忒忒斯脚痛得很厉害,臭味四溢,他早晚呻吟令大家都埋怨起来,最后奥德修斯建议把他抛弃到莱姆洛斯岛的海岸上,就当菲洛克忒忒斯在船上熟睡之际,领袖们把他放在岛上两个岩石之间,给他留下了弓箭衣服食物,菲洛克忒忒斯就这样被遗下了,但因为没有他是攻不下特洛伊地的,希腊人在围城第十年不得不再请他回来。
希腊人终于来到了特洛伊地的海岸,预言家警告谁第一个踏足海岸的就会先死,奥德修斯为了吸引将士上岸,自己把盾牌扔到岸上,灵活地跳上盾牌,普罗忒西拉奥斯渴望建立军功,没留意到奥德修斯的诡计,就立即跳上岸杀敌,特洛伊英雄赫克托尔以长矛一飞,他就结束了性命,大家万众一心杀敌,特洛伊人抵挡不住退回城里。第二天双方停火收拾尸体和埋葬战士,之后希腊人把船拖上岸并修筑防御工事,阿基里斯及大埃阿斯的帐篷设在工事的两端,以便防御偷袭.阿伽门侬及奥德修斯的帐篷则在中央,以便统率全军,修好后就派墨涅拉奥斯及奥德修斯与特洛伊人谈判,他们要求归还财宝及海伦,本来特洛伊人自知理亏已准备接受一切要求,但是帕里斯第一个不从,部分兄弟而支持他,被收买的安提玛科斯甚至要求逮捕墨涅拉奥斯并处死他。特洛伊先知赫勒诺斯认为神会让特洛伊胜利,最后特洛伊人拒绝和谈,战争正式开始。
希腊人开始围城,攻了三次都无功而还,特洛伊人也不敢贸然出城进攻,希腊人只得侵占附近的城邦,这包括忒涅多斯岛、莱斯博斯岛、佩达斯城、吕尔奈斯城等。当中彼奥提亚的忒拜也被占领,此城是赫克托尔妻子安德罗马克之父埃提翁所治理,阿基里斯一天所杀了安德罗马克七个弟兄,并俘虏了阿波罗祭师克律塞斯的女儿克律塞伊斯及布里塞伊斯,希腊人把克律塞伊斯送给了阿伽门侬,而布里塞伊斯则归阿基里斯所有。
这九年间,包括对希腊人作出了无数的贡献的帕拉墨得斯之内希腊很多英雄都战死了,可是奥德修斯出于嫉妒之心,加上当时帕拉墨得斯揭穿了奥德修斯装疯的诡计,奥德修斯就趁帕拉墨得斯想议和时诬陷他,奥德修斯把黄金藏在他的帐篷,并流传他被普里阿摩斯收买了,很多人开始相信,另奥德修斯又伪造文书,阿伽门侬得到文书后,召集所有领袖到账篷,这包括帕拉墨得斯,帕拉墨得斯百辞莫辩,被判钉上锁链被人用石头砸死,帕拉墨得斯求饶不果后就在海边被处死了,这导致后来他的父亲欧博亚国王瑙普利奥斯(Nauplius)的报复,起初阿伽门侬甚至不允许埋葬帕拉墨得斯的尸体,然而大埃阿斯不相信帕拉墨得斯背叛而安葬了他。
【读前注意】
这里的科普是便于参加企划的太太了解神话背景,
不做过多扩展,以下内容摘取自维基百科。
===============================================================
【第一回:美女海伦】
斯巴达王廷达柔斯的女儿海伦的美貌冠绝希腊,求婚者接踵而来以致内讧争斗,令廷达柔斯不知所措,最后其中一位求婚者机智的奥德修斯向廷达柔斯进言:“让海伦自己决定,并让所有求婚者起誓,他们对海伦的丈夫永不拿起武器攻击他,并且要求援时全力帮助他。”所有求婚者应允后,海伦就挑选了阿特柔斯之子墨涅拉俄斯。
廷达柔斯死后,墨涅拉俄斯就成了斯巴达国王。
【第二回:婚宴上的金苹果】
另一边厢,在色萨利国王佩琉斯及海洋女神忒提斯的婚礼上,只有不和女神厄里斯没被邀请参加,厄里斯心怀愤恨,便想出诡计,将一个写着“给最美丽的女神”的金苹果扔在宴会上,送给赫拉、雅典娜及阿佛罗狄忒三个女神。三个女神各自理所当然的认为自己是金苹果的应得者,争持不下后唯有请求宙斯裁判,但宙斯却拒绝作出裁判,于是三位女神就带着苹果到伊达山上,找特洛伊国王普里阿摩斯的儿子帕里斯作出裁决。
【第三回:帕里斯的裁决】
帕里斯是普里阿摩斯及赫库芭的儿子。赫库芭生他前作了一个噩梦,梦到特洛伊受大火洗礼,预言家告诉赫库芭这个儿子将毁了特洛伊,因此普里阿摩斯就把帕里斯抛弃在伊达山,后来由阿戈拉奥斯养大了他。
此时三个女神来到帕里斯的面前要他作裁决,三个女神都以奖品诱惑他,赫拉答应给他当全亚洲的王,雅典娜给他最高的军功,而阿芙罗狄忒则给他世上最漂亮的女子海伦作妻,最后帕里斯把金苹果交了给阿芙罗狄忒,成了阿芙罗狄忒的宠儿,而赫拉及雅典娜则因此决心毁灭特洛伊人。
其后,帕里斯在特洛伊竞技会上力压其他对手,并被普里阿摩斯认出而正式成为王子,帕里斯受到阿芙罗狄忒的唆使,乘船到斯巴达找海伦,他和朋友埃涅阿斯作为客人探访斯巴达国王墨涅拉奥斯,宴上帕里斯及海伦互生情愫。过了几天,趁着墨涅拉奥斯到克里特岛时,帕里斯就唆使海伦离开丈夫,跟他同赴特洛伊,海伦为了爱情抛弃家庭,三天后他们就回到了特洛伊。
特洛伊战争(Trojan war)以荷马史诗之伊里亚德为中心,加上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埃阿斯、菲洛克忒忒斯,欧里庇得斯的悲剧在陶里斯的伊菲革涅亚、安德洛玛刻、赫卡柏,维吉尔的史诗埃涅阿斯纪、奥维德等多部著作而成,故事详细地描述了特洛伊战争的情况。
特洛伊战争是以争夺世上最漂亮的女人海伦为中心,道出以阿伽门农及阿喀琉斯为首的希腊联合远征军进攻以帕里斯及赫克托耳为首的特洛伊军的十年攻城战。
现代考古和历史研究在对特洛伊的“神话”“传说”几百年的嘲讽和忽略之后,证实特洛伊和特洛伊战争的确存在。但现代科学否认特洛伊战争是如几千年前荷马史诗中记载的一场复仇战争,而是古希腊为争夺特洛伊的重要地理位置和贸易权益联合赫梯发动的侵略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