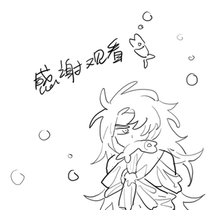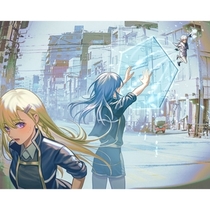*rank1 赛前讨论与准备
一般来讲,整个那须野小队可以用“静如处子、动如脱兔”来形容。
队长那须野祈爱性格沉稳,松谷水木闲散温和,但这两个在训练场对练的时候可都是能把场景拆得七零八落的狠角色;其余三位里,电波系的操作员三枝真夜和认真靠谱的狙击手高幡久己负责静如处子,夜海百慕一个人负责全队分量的动如脱兔…
咳咳,开玩笑的,我们言归正传。
不管他们平时是怎么不动如山,此刻的训练室里也只能看到五位比脱兔还要上蹿下跳、几乎能出现残影的抓狂人士。究其根源,用脚趾头想也知道肯定是那张先到达队长那须野手里、又经了每个人的手传过一遍,现在已经被反复擦拭确认搞得皱皱巴巴的B级排位赛对战名单。
【那须野队vs小林队vs青仪队】,白纸被反复磋磨来磋磨去,可惜黑色的印刷体依然坚挺地待在皱巴巴的通知单上,既定的事实再怎么戳也没法更改。
小小的休息室里充满了快活的,啊不,痛不欲生的空气:
“模拟赛成真,真的是小林队,这也太巧了...”
“B01?B01?B01?确定吗??”
“救命啊!!!”
“哪队选地图?我看看通知——完了,是小林他们选。”
“振作点、振作点...也算是好事,咱们两周前和小林队约了模拟赛,这还没开打就直接升格成正式对战了,相当于少打一场,省了不少事...”
“是啊救命啊,正因为约了模拟赛、提前研究了小林队的战术,才会头痛啊!!你看看他们常用的触发!(咔咔挥舞纸张的声音)蜘蛛,护城盾,铅弹!你看看他们队长的战术规划评分!再加上这次还是他们选图,有多烧脑已经可以想象了…”
“…”
“......”
(难以名状的惨叫声)
(此起彼伏的难以名状的惨叫声)
两岸猿声啼不住的状态大约持续了三分多钟,再嚎下去隔壁两间训练室想必都要来敲门看看是不是发生什么凶杀案了。不过如果真的有“凶杀案”发生,想必逝者也一定是平日里弧月蛋糕玫瑰牙膏的夜海吧……啊,又扯远了。
失意体前屈了一会儿,大家纷纷或快或慢地回归工作状态,训练室里回荡着翻找纸质材料的刷刷声和敲打终端的咔哒声。高幡久己打开厚厚的队内总结笔记开始顺着边缘粘好的便利贴翻找积攒下来的条目,从中检索出本次对手队伍小林队和青仪队的信息,并单独整理成一份文档。
夜海百慕和三枝真夜一块在终端上翻翻找找,挑选适合的训练场并爆手速预约——单人训练场的供应还是相当足够的,但好的多人训练场,那难抢程度堪比考试周的图书馆。更何况对战通知是同时发放到各队伍手中的,大家商讨完战术肯定都要用训练场来实践,正式赛前一两天的多人训练场简直堪称一座难求,因此预约当然要先下手为强,要不然根本抢不到合适的训练场地。
松谷水木和那须野祈爱各自抱了一摞白纸往沙发上一坐,两人对视一眼,双双露出苦笑:对手没确定和确定了,二者的战术规划难度根本没法比。战场上每多一个人都是巨大的变数,何况要同时面对两个队伍。研究对方、调整自己,并且根据天气和环境快速策划几套基础战术出来供一会赛前讨论时备选,这是相当需要脑力的工作。
从分组到选图再到公布触发器,流程中有一段时间的间隔。前几天里既不确定场地也不知道对手,没有什么特别好针对性训练的项目,普适度、性价比最高的训练就是对练。四个人打过来打过去,打到差点把训练室拆个五六七八次,每个组合都搭配了一遍以上,现在终于等到了具体地图和触发器配置表。B01和B06...不用想就知道一定是相当艰难的战斗。
几小时后,赛前基础的材料整理和系统统筹已经有序地处理完毕。夜海和三枝预约完场所就去帮高幡整理资料,效果提升了不少:高幡按按眼眶,把薄薄一小摞筛选好的材料在桌面上墩两下码齐,推到桌子中间。那须野揉揉脸去小冰箱里掏了几小杯果冻分发给大家,冰箱里的果冻沙拉便当盒都是松谷从店里带过来的,库存定期更新,用料绿色健康,保证训练后能及时补充体力:厨师本人则是已经躺在铺满了废草稿纸的沙发上,被长时间的高速思考推演累得连一根手指都不想动了。
整理整理衣装,把地上掉落的抱枕捡起来,众人窝沙发的窝沙发、骑凳子的骑凳子,各自在训练室室里找个位置待好,转转脖子松松筋骨,夜海一拍弧月触发器充当惊堂木——那须野小队赛前研讨会,开幕!
那须野祈爱在终端上放大地图,率先发言:“地形图外景中间看起来有点像大楼商场。大致辨认了一下,虽说还是有点太模糊辨认不清,但是右边黄色圈的那块,”她伸手在电子地图上画了个圈,“应该有很多纵横交错的小路。左边也有很多小路小巷,但是看起来似乎还是以大块地貌为主。”
高幡久己点头,“从俯视图的光影推断,我理解的比较高的建筑是这些。”狙击手非常熟练地几下点出四五栋楼顶,在上面加注星形。
“诶,要是有人被投放在高楼顶部,那岂不是位置大好……”
大家异口同声感叹:“上帝视角啊!”
“大家兜里都揣一片儿瓦片,防铅弹。”那须野在白板上刷刷写下瓦片关键词,潇洒地画了个大圈当重点。
“优先处理小林队,他们选图,东道主肯定在地图上有想做手脚的地方,但我们没法提前预测是在哪里做手脚挖坑...最便捷的方式就是在最开始切掉,哪怕切不死也要给他们的后续计划造成影响。优先级的话,小林队三个人里把北原放最后,是因为他没带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放着一个蜘蛛携带者和一个榴弹炮铅弹使在地图上乱跑,想想都令人窒息……”
松谷水木把定稿的各队伍触发器表格往旁边一推,拎起手边的保温杯。“久己可能得不断换位置打游击。我们和小林队的模拟赛还没打,他们沿用模拟赛地图的可能性不高,但天气很有可能近似,六成以上可能性依然是和台风相似的天气。这种情况虽然不利,但是相对而言也方便久己你撤退和隐藏。我倾向于先把小林队的枪手大竹切了,她带了榴弹和铅弹,这种触发器要破坏地形简直易如反掌。”
“嗯嗯,”那须野点头在白板上简单勾勒两下权当记录,“应该根据我们的对策考虑一下我们的行动路线!然后看看三队的路线会不会撞上,撞上就有遭遇战了,现在应该先根据我们落地后肉眼能看到的人考虑一下怎么作战,但这个非常随机……”
松谷顺着她的思路往下接,“咱们揣摩别人,其他两队也会猜咱们的行动路线。考虑到天气,无论落地点在哪里,我都建议夜海避战,潜行直到汇合。小林队没有狙击手,选图必然会考虑到这一因素,久己这次要辛苦了…长距离狙击考虑到可见度的话不太可行,伪装信标、星形标记这种偏门的触发说不定有用。”
高幡冷静地举起那须野队的触发器表格吐槽道:“可是触发器表格已经定好交上去了。谁带了伪装信标吗?”
大家面面相觑——哦,没人带啊,那没事了。
那须野无意识地把长发在指尖绕了两圈,她思考时常会这样:“嗯…汇合确实会方便一些。那等到落点公布之后,真夜就把信息传给我和水木,视情况,条件相较之下轻松的那个做主指挥。我们主要往人数较多的一侧行动先汇合,如果遇到大竹则优先向其方向移动。”
松谷点点头,望向夜海的方向。“如果给你提供一个援护的话,你有信心和场上遇到的任何对手打一打吗,我们的主输出?”
“当然。”夜海毫不犹豫地回答,本次排位的攻击手能力都相当优越,金色眼瞳中灼烧的战意几乎能满溢出来。他手指不安分地上下抛接把玩着触发器,这动作大家都无比眼熟,是他非常期待的表现。“那就打!”
“有斗志是好事,以夜海的能力被集火也能杀出来,但是不能拖进持久战。”松谷给夜海人工降温,“青仪队在场,我们要非常谨慎小心以免被收割。战斗拖延时间太长会直接暴露我们的位置,到时候被包饺子可不是好玩的。其他人也会向你那边集合,能当场解决对手最好,打不掉就以‘造成流失足够多触力能的伤口’为目标。毕竟伤口造成的触力能流失也是实打实的,甚至流失到一定量还会把击杀者给到造成伤口的人、而非最后一击者,这样很大可能分数还能归我们,相比于硬战拿分合算得多。”
那须野认真点头,“援护的话我应该没有问题,夜海对战枪手这种高火力职业比较麻烦,我们两人尽快会合,配合先尽量迅速攻击周围敌人,然后再视情况会合行动吧。天气是黑夜雷暴雨,很不适合狙击手的天气,小林队应该是考虑了只有他们队没有狙击选的。我们之前研究过小林队,说起榴弹枪的话……很容易破坏地形啊。这样也确实可以缩小地图,方便枪手集中火力,毕竟在这种天气下瞄准目标所需要的精确度不低。”
粉发少女摩挲着触发器表格上蜘蛛一栏,比划了两下:“在这样的暴风雨天气,我觉得蜘蛛很难辨认。破坏地形…..如果是把大部分地形破坏了,只剩下已经布好蜘蛛的地方呢?”
”...那他们拆迁得也挺累的。”队内知名摸鱼人松谷谨慎吐槽道。
“僵持战的话,恐怕他们胜率比较高,我也建议是走骚扰路线。”队长点头肯定了大致作战方针,松谷放松下来,躺进沙发里补充发言。
“枪手难对付,那就冲着手砍,目标是削掉持枪惯用手。小林这种不好找又一不留神就丢了的,遇到就冲腿去,拦他们的移动。攻击手,对面也就青仪小林和泉,青仪…遇见就跑吧……”
大家一致露出了“我懂”的表情,纷纷痛苦面具点头。
那须野祈爱双手一拍,“那我们这次主要的作战方式就敲定啦!是以突袭骚扰为主,尽量削减对方战力的方针,具体细节场上随机应变,ok!”
“好耶——”
“辛苦啦!!”
松谷水木和那须野祈爱是两座岿然不动的默契指挥塔,一主一辅,无论是两人都在场上还是一人脱战,都能够确保全队的战术指挥紧跟变动并迅速传达向所有人。高幡定位灵活、枪法精准,远中近狙击都能够驾驭,夜海更是机动优越、本身作战技巧极强,几乎不用给他什么战术上的细节策划,他自己一人成军。这样灵活性极强的队伍战法飘逸奇巧,没有固定战术但成绩依然相当漂亮。
你一言我一语中,赛前战术被拍板敲定。说来有趣,整个会议的持续时间没超过十五分钟,堪比雷厉风行火花带闪电,放在所有边境队伍里横向对比都短得惊人。真的够用吗?答案是肯定的。敲定一个方向已经足够了:定一个大方针,然后随机应变——这是他们多次磨合后寻找到的,那须野全队最适合的战斗风格。
会议结束,夜海一撑椅子跳起来,拽着那须野风风火火地冲向训练室,争分夺秒地要在今天解散之前多针对射手练习两轮;高幡沉稳地做了一套单眼眼保健操,端起狙击枪抬手预约了单人训练室里的模拟黑夜场。松谷水木在沙发上缓了一会,爬起来把桌上已经化掉一些的属于他的那份果冻解决,站起来晃晃头伸个懒腰,拎起观察本往B级训练大厅的沙发走去。
距离排位开始,观赛厅人声鼎沸,光幕降下,众人载入场景仰首四顾,发现夜海的随机位置在包围圈里而松谷和高幡各自随机到地图最边角——还有两天一十八小时。
#4093